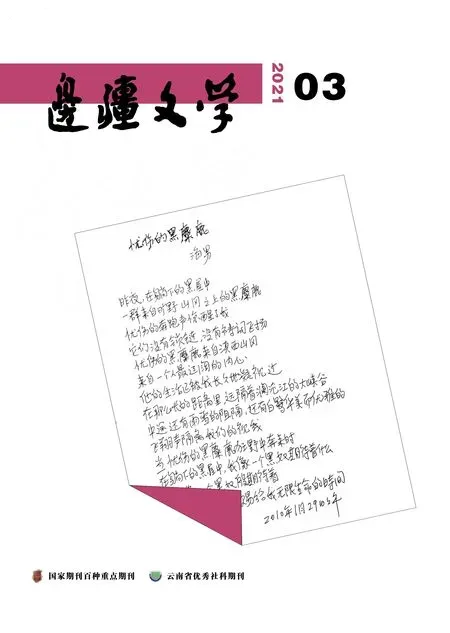楼河的诗
楼河
紫薇葡萄
葡萄很脆,也很甜。
他吃着葡萄,
一颗、两颗、三颗……
好像上瘾了停不下来,
好像在尝试、在探索。
葡萄的紫色让他想起了地念,
森林里让人吃到嘴唇乌紫的
隐蔽果实。
但葡萄串的形状让他想起紫薇,
些许葡萄皮勾留在骨架上
像枯萎的紫薇花瓣。
童年时他就在家乡的山坡上采过紫薇,
把它们插在洗过的农药瓶里,
等着它们枯萎。
他不知道紫薇花的名字,
但记得那些时光里的阴雨天气。
他记得那时的阴凉,
虽然现在总是在
炎热的夏天遇见紫薇开放。
种花的男子
那是一片花田,
花田在丘陵下的一大片平地上,
蔷薇、玫瑰和向日葵。
他在花田里松土,
噗噗的声音听起来十分清脆,
混合了干牛粪的土壤。
像松脆的巧克力饼干。
他的锄头上装了根弹簧,
而塑料鞋踩着一只鸭子。
天很蓝,云朵很白,
他已经劳动了一个下午,
日头转动,他的影子
从花田移动到了玉米地,
放大了他消瘦的形象。
他沉浸在劳动中有点愉悦,
还要抡起锄头多久他心里有数。
他比许多人更加自由,
但仍然不希望
儿子延续他的工作,
像他那样
总是在夕阳下沾染尘土。
蓝色摩托车店
街头有三家摩托车店。
这一家是蓝色的,
放着黑色、白色和红色的摩托车。
蓝色的摩托车在中间,
年轻的店员在那儿擦拭
看起来并不存在的灰尘。
还有另一个店员在一旁扭动扳手,
取下一颗颗螺丝,
再装上镜子、盖子和垫子,
再试用电池、刹车和油门。
电动摩托车缺乏那“轰”的一响,
转弯的时候不像在飞奔,
后轮像在飘逸,
仿佛骑在一朵没有重力的云上。
你会有点担心,
也会有点欣喜,
就像你此刻在蓝色摩托车店
等待它那样,
忽然有点重回童真。
商场门口的老夫妻
经过了无数次争吵以后,
他们的生活重归平静。
他们可能还会争吵,
然后再次回归平静。但有点不同的是,
他们大概知道,
无论怎样的争吵已经难以将他们分开。
可能是因为爱,也可能是因为
衰老后没有力量抵抗孤独。
所以这一次,
他们在商场门口争吵了一番以后,
默契地坐在了门口外的长椅上,
先是继续嘀嘀咕咕,
接着有人沉默,有人自言自语。
几分钟过后,忽然,
他发现她衣服上的毛球,
于是从衣领到衣摆,
一个个地揪了下来。
她顺从地抬起脖子,同时
说起了另一个年轻时的记忆。
他笑了,但不是因为她说起的往事,
而是觉得
自己此刻认真的样子
就像动物园里捉虱子的猩猩。
翠鸟
“你看那鸟”,“它站在草尖”,
陌生人在河边指给我看,
带着欣喜,丝毫没有陌生的隔阂。
那是一只翠鸟,胸前绿色的羽毛
在午后的阳光中闪耀,
枯瘦的爪子抓住草茎,
在引力的平衡中摇荡。
“真漂亮!”他赞叹,
就像欣赏一个女人而毫无欲望的杂念,
那羽毛装饰的小身体,
也是肉体与温度的美。
它转着头,眼睛跟着滴溜乱动,
又好奇又惊恐的样子,
像稻田里的鹭鸶和人群共存的时刻,
可能随时都会飞走。
“竟然只有一只!”
他指出了它的孤独,
他的自行车踏板上撑着他的解放鞋,
露出了一个脚趾,
橙色工作服里塞着条毛巾。
“我们那里到处都有”,
他有点轻蔑地说完这句话,
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和我告别,
然后骑上了自行车,
去到另一个由他清扫的地界。
墓园里哭泣的女人
她趴在黑色的墓碑上,
在那儿大声地哭,哭出了满脸的泪水。
但她随时都能
停下来应答旁边人的对话。
她的哭是一种仪式。
那逝者是她的弟弟。墓石发亮,
掩藏在墓园的微风中。
她哭他痛苦的死和不幸的生命,
苍黄的脸充满了倦容。
她的哭是一种真实的悲痛,
把她身旁的女儿也惹哭了,站在那儿
颤抖地点燃了三支香。
但死者的儿子没有哭。
年轻的他也许还没到二十岁,他可能不懂
如何在哭的仪式里控制自己的悲伤,
让今天的情景成为恰当的
告别的纪念。
避雨时间
都挤到了一起,偶尔
把手伸出公交站台,
仿佛用手指触碰
装满沸水的不锈钢水杯,
推断雨停的时间。
就这样静止着。
陌生人凑到一起
就会有人试着说几句话,
并不像询问,也不期待
有人回答。
沉默,在每个等待的时间里
构建着不同的
记忆中的画面。
漫长的细雨,忽然的急雨,
湿淋淋的小路或者扬尘的气味。
在十分钟的时间里
翻开相册,用于遗忘,
直到在另一个避雨的站台下想起。
思念,或者没有思想;
逃避,但却无法终止。
戴白色花帽的男人
他戴着白色的圆形草帽,
帽子上有朵白色的花。
四点钟,下过雨的天空
蓝得不像话,
高原的微风有些凉。
他沿着商业街的阴影向上走,
要走到山坡上的小区,
胳膊里夹着一把扫帚。
他一边走一边嗑着瓜子,
那么瘦,
那么慢,
那么平静。
去看大海的路上
去看大海的路上,
是下过大雨的晴天,
凉风像丝线吹着脚踝的时候,
尘埃全被土地收拢。
所以去看大海的路上,
是蝴蝶闪烁的花田。
逆风飞舞的蝴蝶,
捕捉迅速摆动的花蕊,
舌尖刺破花蜜的时候,
雨滴睁大了花瓣的眼睛。
所以去看大海的路上,
是蝴蝶弯腰的形象。
蝴蝶飞过的溪流,
在石头上抽出了纤维,
杉树在水面上长出森林的时候,
草垛中传来了秋天的气息。
所以去看大海的路上,
是石头变成鞋子的一天。
溪流经过了梨树,
蝴蝶编织着花蜜,
花田移动到海滩的时候,
大海失去了波涛。
所以去看大海的路上,
是自行车代替石头的日子。
唱颂
周末,尖顶下的高窗里
收拢了神的光辉。
脚踏风琴正在吞咽
明亮洞穴里虚无的声音,
每个声音都像在哽咽,
哽咽而同时战栗,
为突然到来的温暖在发抖。
一共有三十个人,
二十只沉默的鸭子
和十个吃木头的哑巴。
每个人都准备了自己的故事,
灵魂浮荡在水中
仿佛游泳时双脚探不到底。
生命并不会溺亡,
但会因为永远的寻觅恐惧而死。
是的,全都七十多岁,
全都戴着帽子,还有不同的鞋。
多难啊,多真实,多衰老。
有人胖得像迷糊的泪水,
而另一些人消瘦,身上始终有点风。
阴天的云翳像灰色的癌症,
在脂肪里点了一根蜡烛,
照着肉身昏暗的迷宫,
在半睡半醒之间自言自语,
仿佛在回忆,仿佛在唱颂,
使煤气炉上墩着一壶水的厨房
变成一间教堂,或者相反。
年轻时缝纫机嗒嗒的马达声中
丢失的那颗珠子,
现在戴上眼镜缝补时捡起来
像灵魂。
已无热情表达爱,
但有太多的空闲怀疑自己。疲倦,
脑海里有一艘船经过了海难
但仍在迷雾之中。
静默、静默,游荡的丝线,
一声咳嗽后收拾脸容,
用安分守己的表情倾听传道者的故事,
站起又坐下,尝试认识自己的罪,
罪里的根源,
然后才能在空荡教堂的钟声里,
抓住那根绳索,
就像眼睛看到岸,双脚踩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