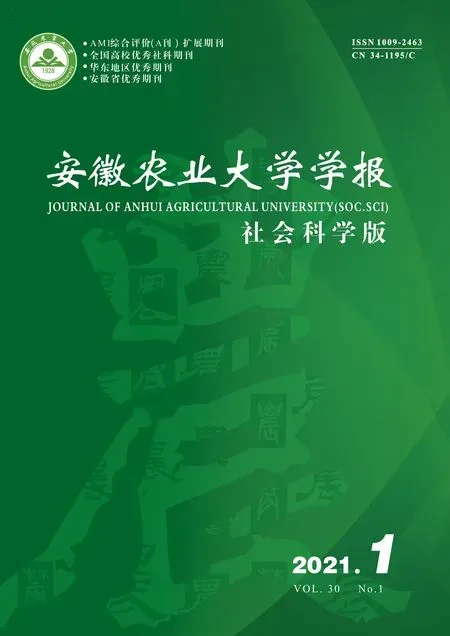文化承认:一种本体论的考察*
马晓艳,李和佳
(1.安徽建筑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 合肥 230601;2.合肥工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 合肥 230009)
当全球移民和通讯潮流所带来的文化多元主义的突起,以及随之而来的作为国家调节系统的福利国家被终结,公民身份与文化认同问题成为认同政治领域内最核心的讨论话题,遍及社会各个领域。关于多民族国家内部的族群关系、少数民族的政治权利、弱势群体的话语权、种族问题研究、女权问题以及多元文化的共存等问题,成为认同政治的基本问题,人的文化身份和平等地位问题也受到了人们前所未有的关注。另外,随着20世纪中后期整个西方社会科学经历了从结构主义到后结构主义、从现代理论到后现代理论的震荡,凸显出来的认同危机加速了社会科学研究的文化论转向。
与认为社会再分配已经过时的“福利国家终结论”不同,关注公民身份与文化认同的“文化承认论”者认为,社会运动不仅要在社会政治层面抨击不平等的分配和不负责任的权力,还要在文化层面维护生活和价值体系的多元存在。不平等的文化分配抑制了个人和集体自我表征与发展的自由。一系列的社会运动以否定性的方式揭示了当代社会中作为文化共同体的成员确认自己生活方式和社会价值的资格与权利。这无疑突出了文化承认在多元文化社会中的现实性意义。
一、平等共在:文化承认的实质
每个人都是作为共同体成员的平等存在。每个个体都被当作不同共同体的成员,可以在不同的意义上建立起主体间性关系,既是承认诉求的发出者,又是承认诉求的接受者。在政治共同体内部,个人既是法律的“作者”,也是相互负责的公民,并有平等参与公共意志形成过程的权利。在道德共同体内部,所有人作为道德人格要求得到道德尊重。无论政治共同体,还是道德共同体,首要的是要确认其成员的身份以及此身份的现实化问题,即保护一个人作为自由和平等的权利人格所具有的“伦理认同”。当我们在讨论这种确认人的自由平等权利之存在的身份时,这种身份可以在不同意义上得以指称,然而不可回避的事实是:从人的交往生活上看,每个人的自由平等权利确认是通过公民身份的确立来实现的。公民身份作为一种减少社会不平等和创造平等机会的策略,无论在道德上还是在政治上均具有合法的地位,因为它是确保所有公民有效实施自主权的根本途径。
公民身份必须植根于生活世界中主体间性的联结,公民的权利和责任是相互确认的主体间性关系的法律形式化。在这个意义上说,公民身份的地位需要一个共同体的正式成员资格最基本的平等。因此,公民身份取决于人们是否被其所在共同体看作是其中的平等成员。公民身份地位得以确立的前提是,人们被看作自主的、有自我意识的人,其计划和信仰得到尊重。
作为共同体的一成员,个体主体所享有的资格与权利是在主体间性的生活世界中得以实现和维护的,同时这种主体间性意味着此个体在得到他人承认的同时必须承认他人有尊严的平等存在。承认是双向的,是互惠的。要真正成为一个“人”,成为一个共同体成员,就必须把他人看作同自己一样是自主的、有自我意识的人。如是,公民必须承担起对自己共同体的责任,给予其他公民同样的尊重,因为对他人的尊重与承认恰恰是“我”自己得以有尊严存在的前提条件。得之,人之为人;失此,人将不人。在这个意义上,作为共同体的成员所拥有的成员资格是权利与责任的统一,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黑格尔通过对康德道德理论中具有原子论特征的个人主义前提的批判,揭示了共同体与个体之间的内在联系。在黑格尔看来,人类的共同体不应被想象成孤立主体的组合,恰恰相反,人的主体间性行动之动因源于获得承认的渴望,来自道德感。“在承认中,自我已不复成其为个体。它在承认中合法地存在,即它不再直接地存在。被承认的人,通过他的存在得到直接考虑因而得到承认,可是这种存在本身却是产生于‘承认’这一概念。它是一个被承认的存在。人必然地被承认,也必须给他人以承认。这种必然性是他本身所固有的”。主体间的相互承认,不仅仅体现在个体之间的道德承认,也是共同体形成的基础。
和黑格尔一样,米德坚持认为“认识他者优先于自我意识的发展”。米德从自然主义角度,主张从“他者的视角”,即“普遍化的他者”的视角出发来观照自身的存在与意义,并阐释公民责任的规范内涵。一个有组织的共同体或社会群体,能使其中个体的自我获得统一——自我的态度就是整个共同体的态度。这种折射共同体态度的自我,可以称为“普遍化的他者”。米德指出,通过“普遍化的他者”,共同体对其个体成员的行动加以控制,以朝着共同体的整体性方向发展,而个体则在社会过程中对他自己采取普遍化的他者的态度。因此,自我的完全发展有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自我由其他个体对他以及彼此之间所持的特定态度的一种组织所构成;在第二阶段,该自我由对普遍化的他者即他所属的整个社会群体的社会态度的组织所构成。所以,一个人要成为一个自我,就必须首先成为一个共同体的成员,并逐渐取得该共同体的组织态度。“自我只有在与其他自我的明确关系中才能存在。在自我与他我之间不可能划出严格的分界线,只有当他人的自我存在并进入我们的经验的时候,我们自己的自我才能存在并进入我们的经验”。因此,“普遍化的自我”,并不是抽象的“我”,而是你与我、他与我的统一,是有限性与无限性的统一,即“我们”。
米德的社会心理学从一开始就阐明了一种社会行为意义的意识在人类交往中出现的机制。米德理论的出发点在于,仅当一个主体能够在自己身上产生与他在他者身上刺激起来的表达行为相同的反应时,他才获得关于其行为的主体间性意义的知识:“我”在共同的行为处境中体验到自己的行为对互动伙伴的意义。此处,米德提出了一种承认关系:正因为承认了他者,自我能够在共同体中自我持存,能够在共同体中获得承认。权利的存在有赖于共同体每个成员的认同与尊重。没有对共同体的共同态度,权利系统在社会中就不能维系下去。基于“普遍化他者”的规范立场,他者在规范意义上有义务尊重主体的权利,也有义务满足个体要求,这无疑赋予了主体以承担道德责任的能力。而正是在这种权利的满足中,主体发展出一种积极的自尊态度。
无论是在政治共同体之中,还是在文化共同体当中,由共同体成员身份所担当的文化人格是资格、权利与责任的三位一体的统一体。这种人格应是完整的存在,而不是分裂的存在。而且对这种身份的承认在现代法律平等原则规范框架中得以保障,以免除外在的歧视与伤害。否则,文化歧视则会构成对个体尊严的伤害和对自由的限制。在霍耐特看来,文化多元主义存在的可能性条件在于社会成员的一种霍布斯式消极自由的获得,即免除某种限制或阻碍的法律自由。这种法律自由可以通过制度性结构得以充分体现与保障。这种消极自由的实现与保障,凸显了一个重要问题:一个社会只有在经过充分分化的基础上,不同社会群体或个人彼此间获得平等身份、相互承认、相互尊重,才有可能是多元社会。这种多元是合理的多元,基于这种合理多元而建立起来的社会,是一个非排他性的生活世界。在这个生活世界中,所有存在者身份都是平等的,并以一种理性的态度在经验生活中彼此商谈、对话,构建起相互承认的主体间性关系。但正如霍耐特所强调的,多元社会中文化承认的实现仅仅通过社会成员的公民身份资格的确认这一消极自由是远远不够的。除此之外,每个社会成员必须拥有属于自己选择生活方式的社会权利。这种体现个体道德自主的积极自由关涉到多元文化背景下的文化归属问题。
二、文化归属:文化承认的意义
当我们阐明了特定文化共同体内部成员之间的主体间性平等关系之后,我们必须基于这种平等关系进一步来揭示社会成员对其所在文化共同体的认同与归属。
文化承认,即人们作为文化共同体成员而相互承认,并服务于他们对美好生活方式关心的价值评价标准。文化承认不仅可以在一种间接意义上通过共同体所实施的制度性保障而实现,也可以在特定生活方式得到社会尊重的直接意义上得以实现。文化承认不仅仅是无偏见、尊重文化差异性和文化实践的自由,还包括对占主导地位的公共文化和教育进行多元主义的修正。这反映了社会成员对于自己共同体的伦理自觉、伦理认同与文化归属。
所谓文化归属感,是作为特定文化共同体的成员在与他者的交往中对于“再生产活动”的不断积极地促进,并由此所产生的对所在共同体的认同和归属的感觉与态度。这种再生产活动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特定的社会秩序的认同与促进,另一方面是在促进这种社会秩序过程中对于自己的认同。在这两个方面的综合视角中文化归属得以充分诠释。在人们的行动有助于再生产的现实中,人们获得一种“归属感”,一种“在家”的感觉。这种文化归属感的获取,使人们明白一点:我们都是属于这个文化共同体的,而且我们都是这个共同体的创造者和建构者,尽管每个人可能在进入这个共同体的时间上有先后,创造的价值有大小。这是一种平等参与,每个人的努力都将会得到认真的对待,每一个人或群体的声音都将受到认真的倾听。
人们在两种再生产活动中获得了个体存在与发展的本体论资源,即由共同体提供或授予的成员资格与个体在自我认同中发展出的文化归属感(或能力)。人们知道自己的“位置”所在,确认自己的行为与此相关,并对这些行为完全负有责任,因为“我”是共同体的一员——这是我的行为,这是我的共同体。这表达的是对于自己置身其中的共同体的连带责任、对于当下的关切和对于未来的历史感和使命感,表达的是一种公民自我实现的康德式进路,即“我们”基于公义和良知对于共同体的个体性实践,同时为一种道德理性和公共意志表达而尽心尽力、奋力打拼。
人的个体性并不是一种霍布斯意义上的“我”与他者疏离的原子式对立状态,而是一种不受他人支配的行动能力,一种与他者相互承认、并对他人负有责任的特定性存在。自由的个体,即权利的持有者,应设想泰勒意义上的积极自我认同,并履行义务去完善、恢复或者维持这种认同。这是一种本体论的论证:文化归属问题不仅关系到社会主体生存与发展于其中的文化共同体的构建与完善,也关系到人们成为“自由个人”的真正社会条件。在非排他性的生活世界中,我们作为共同体的成员资格是无条件的,这是我们进入共同体的本体论机会与条件。同时,这种“承认的政治”理论表明:如果“自由个人”归于一个特定的文化共同体,那么这个自由个人的“自由”的本质不仅仅在于他的资格与权利问题,也在于他应该,也能够积极地参与到该共同体的管理与维持的过程之中。加拿大哲学家金里卡与泰勒都对作为个体文化归属的积极自由进行了辩护。在金里卡看来,作为文化归属的积极自由应被理解为个体道德自主的成长条件。在泰勒看来,作为文化归属的积极自由被理解为文化生存的规范条件。他们都以各自的特殊方式揭示了社会成员能自觉“嵌入”到他所处的文化共同体之中,并能自觉参与到共同体的建构之中,来表达它对该共同体的认同归属。
特别值得关注的一个现实问题是,在多元文化社会,“文化归属”概念并不是在同质性的族裔文化意义上使用,而是建立在平等基础之上。这里也会存在两种误区:首先,将本处于边缘地带的社会成员或群体与它生长于其中的社会整体性文化相分离的做法,会导致其被重新边缘化。而恰恰相反,那些边缘性群体会通过社会流动、文化教育来选择、合并新的社会变化因素,以形成一种“造就的存在”,从而对社会主导性文化产生积极的影响。其次,无视同一社会内部存在的多样性文化现实和文化机会平等化原则,而通过国家权力强制某种文化存活的做法,将会导致大范围的社会运动。现代性多元文化社会中社会运动的频频发生,以一种否定性的方式揭示了个体或群体的文化承认诉求,以及这种诉求所遭到的破坏对于社会成员文化认同与文化归属的消极性影响。
因此,一个成员对于其所在共同体的归属感的形成,不仅体现在共同体保护其成员作为自由和平等的权利人格所具有的“伦理认同”,而且体现在共同体本身的包容性与开放性——尽一切可能免除其成员遭受文化歧视,并允许一切文化成员与群体在公共领域之中在维持自身的文化价值的同时,参与到共同体的建设与发展之中。这种公共领域恰如米德所强调的“普遍化他者”所形成的生活世界境域——每个社会成员于其中都将会体验到一种真正的“家”的感觉,也都会在这种境域中自觉将自己视为这个“大家庭”的一个成员,一个具有建设性意义的成员,因为他将不会感受到来自他者的漠视与排斥。
三、作为一种伦理生态的公共领域④:文化承认的可能
既然一个共同体的成员资格是无条件的,那么我们又如何真正成为一名享有资格权利的公民?也就是说,我们作为一名文化共同体的成员,应该做什么?这个问题既属于个体行动的层面,也属于共同体制度性结构层面,我们统称之为一种伦理生态。在现代多元社会,这种伦理生态在公共领域中得以体现。
如果文化承认要获得充分实现,就应该有一个能够发挥作用的公共领域。文化承认依赖于生活世界的基础,即作为本体论方式存在的政治、经济、文化机会,但也同样依靠那些对共同体建构负有责任的成员的积极介入。公共领域是在多种文化的相互承认中形成的一种充满对话、交流的生活世界系统,是一个人人都以在其中有“声音”、并以不同方式形塑自我发展的本体论资源与生活机会的“盛大狂欢节”,是一种具有包容性的、日趋稳定的自由平等政治文化背景。在这种生活世界系统之中,每一文化群体或个人不仅在本体论意义上得到充分发展的平等机会,而且他们都能从伦理生态系统之中获取对于自己所在共同体的确证与认同。
在多元文化社会,我们需要一种能将我们所有人联合起来的制度安排形式和文化承认领域。根据亚里士多德式理论预设:个体只能作为一个共同体的成员才能充分表现自我、发展自我,我们可以推导出:文化承认不仅在于对于他者权利和身份的承认,而且在于承认其参与到共同体生活方式之中的权利与责任。在这个意义上说,社会主体或群体在文化承认形式中形成的文化归属感,取决于文化的联合与人的联合。福利制度拒斥将市场作为社会组织的核心原则,而将自由作为社会组织的核心原则,这无疑在个人自主与伦理认同的意义上增强了社会的凝聚力和文化归属感。
哈贝马斯在《公民身份与民族认同》一文中比较了自洛克以来的个人主义与溯源于亚里士多德的共同体主义对于文化归属的理解。在洛克看来,文化归属是在一个获得法律地位的社会组织中社会成员通过授予、接受而实现的,而在亚里士多德看来,社会成员只能在共享的传统和主体间相互承认的制度范围内形成个人认同和文化认同。哈贝马斯批判了前者的工具性意义,充分肯定了后者基于相互承认的平等主义关系而形成的主体间共同实践与团结关系。这种共同实践关系是多元化主体或文化群体在公共领域当中形成集体意志的前提基础。一种集体意志产生于对有意识地接受自身特定伦理和文化共同体传统的认同和归属。这就意味着,一种自由的伦理文化生态所培育的只是一种普遍主义意义上的“公分母”或者多元文化之间的“重叠共识”,它使人们对一个多元文化生活中各不相同但彼此共存的生活方式的多元化和整体化这两方面的敏感性都得以增强。像中国和瑞士这样多元文化社会的例子表明,一种自由而又富集体意志的文化归属,并不意味着多样性文化的同质性,也并不意味着所有公民都共有民族上、语言上和文化上的共同来源。文化、语言、地域等的多样化恰恰构成了社会多元生活方式的一个前提。而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原旨主义设想决定了近代民族国家在给予一些族群以这种民族主义的集体认同形式的同时,实际上剥夺了另外一些族群的同种可能性。大规模的种族冲突与频繁的恐怖事件,说明了一种缺乏以公民权利的普及为杠杆和以对于文化完整性的公共表达的容忍为条件的集体认同形式,很可能是缺乏归属性与凝聚性的、不稳定的、内含致命冲突因子的制度安排。相反,公共领域并不会赋予某个特定文化以特权,而是文化聚会和交换价值的场所。公民身份是公共领域中文化多元化的前提条件。它不是建立在固定种族化的群体的共同表述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普遍权利和共和主义的公民身份基础之上。这种共和主义的普遍权利观念预设了一个不争的事实:文化权利的有效程度取决于每个个体或群体的意志与观念得以有效的表达。当然,这种表达的有效性会涉及到共同体成员参与公共领域的能力、机会与资源。但毫无疑问的是,只有在参与公共领域的建构之中,才能改变公共领域的结构。
如果我们撇开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中的语言的和形式主义的倾向,我们就会发现,哈贝马斯的主体间性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种“主体对主体的语境”。这种语境对于我们理解作为伦理生态的公共领域建构具有重要意义。在哈贝马斯的主体间商谈对话的社会团结性框架中,作为人与人之间平等交往对话的生活世界境域,公共领域的本质性内涵在于包容而非排斥、参与而非疏远、承认而非蔑视。正如哈贝马斯所说,“在决策制定的组织内部所推行的各种协商需要对来自其非正式环境的议题汇集、价值定位、贡献和规划的开放,并为其所理解”,一种包容性的公共领域组织取决于一种自由平等的政治文化日趋稳定的背景。自由平等的政治文化背景是在不同文化取向的交流与对话中分化、凸显出来的,而且,基于这种共同的政治文化自我理解,所有的共同体成员或文化群体可以、且能够从公共领域中获取其独立平等存在所必需的一种本体论意义上的生活资源、机会资源。如此,文化承认不仅仅是消极拥有由国家权威赋予个人的各种权利,更重要的在于每个成员或群体能将这种消极自由权利转化为积极自由权利,即准确定位自身的“位置”与处境,并强化与自身位置、处境相关的公共议题的开放性讨论。
四、结语
主体间文化承认呈现了人的本体论层面的美好生活图景。人们作为文化共同体平等成员而相互承认,并关注他们在文化差异基础之上构建起来的多元美好生活方式。主体(包括群体)间的文化承认以及由之形塑的文化归属,既为免受文化歧视的消极自由与作为道德自主的积极自由之间的融合提供了多元视角,同时为社会道德秩序的构建形塑了一种浓厚的自由文化氛围。
具体来说,有三个方面:其一,共同体制度要保障其成员免受某种文化歧视,并增进其成员安全感、获得感、幸福感;其二,在社会治理意义上,共同体成员积极参与并融入社会公共领域的建设中,并将这种参与视为应有的责任义务,不断增进对于共同体的制度自觉、文化自觉;其三,基于人的生活世界的存在本体论视角,公共领域的本质性内涵在于主体间包容而非排斥、参与而非疏远、承认而非蔑视的平等交往对话。所有的共同体成员或文化群体可以且能够从公共领域中获取其独立平等存在所必需的一种本体论意义上的生活资源、机会与条件。这体现了一种具有包容性、开放性、平等性的政治文化背景与氛围。
注释:
①针对自由主义所提倡的福利国家制度,在现实层面出现的社会成员对于福利的依赖感与进而由之产生的人与人之间的冷漠感,以及福利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滞缓,新自由主义高声宣扬“福利国家死了”。
②虽然我们讨论的主题是围绕文化身份来展开的,但是作为主体间文化承认的普遍主义前提,即每个主体的平等身份获得真实的确认,每一个人都是作为平等的公民而存在。文中关于共同体的使用,笔者没有做出学理上的区分。这并不影响文章主题的论证。
③许多西方学者认为在罗尔斯自由主义的分配公正理论中存在文化同质性的假定:为了实现个体生活目标,需要权利、资源、机会和权力,而抹平了多元文化之间的差异性因素。
④这里对于公共领域的关注不是在政治意义上、而是在伦理生态意义上来理解,但这也并不意味着这种独特的视角对于政治意义上的公共领域建设没有启发意义。
⑤哈贝马斯的共和主义观点还认为,公共权力机构有义务恳请公众积极参与,尤其是那些没有充分代表和组织较弱的公众。参见HabermasStruggles
for
Recognition
in
the
Democratic
Constitutional
State
, in Taylor C and Gutman A(eds),Multiculturalism
,Examining
the
Politics
of
Recognition
.Princeton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5:85.⑥国内人口流动与农民工进城大潮虽然从直接和间接两个层面强化了社会的多元文化差异,并带来了一系列新的公共性问题与挑战,但是在多元文化社会大背景下,与其说这种公共性问题与挑战为我们所担忧和焦虑,毋宁说这些内生性的问题与紧张关系(如户籍、教育、社保等)有效推动了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不仅在于它们是否合理解决,还在于它们会激发社会的公共性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