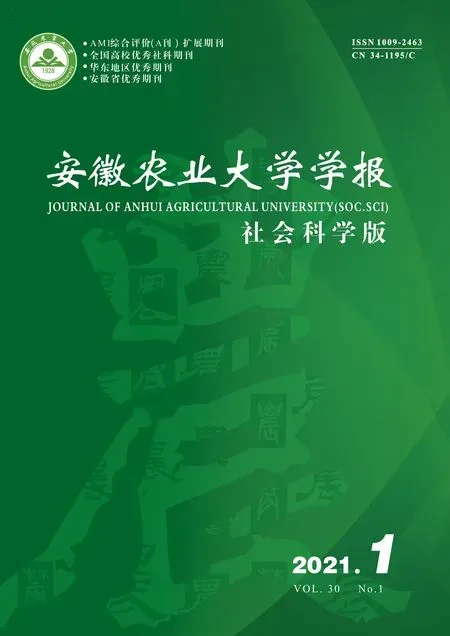熊十力与儒家历史哲学的现代发展*
林家虎
(安徽中医药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 合肥 230012)
与西方哲学从自然的探究开始,直到十八世纪才产生了历史哲学的学科分支不同,中国哲学则是“以生命为它的对象”,在开端处就特别关注社会人生问题,因而关于社会历史的哲学思考自始即成为中国哲学的重要内容。因此,从历史哲学的视角展开对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研究,对于全面认识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精神实质和独特面貌,进而构建中国自己的历史哲学学科和历史哲学思想史都具有重要意义。然而,从当前的研究状况来看,“我国的学者对中国历史哲学理论的研究较之西方历史哲学的研究,不但起步晚,而且几乎还是一块未加认真开垦的处女地。……这种现状与我们中华民族几千年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和丰富的思想文化遗产是很不相称的”。这种研究现状在中国近现代历史哲学的研究上也有相当的表现。因此,从中国传统儒家历史哲学近现代危机与变革的角度,探究现代新儒家代表人物熊十力的历史哲学思想在儒家历史哲学现代发展中的作用和贡献,对于深刻认识中国近现代历史哲学的发展历程,积极推进儒家历史哲学的现代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一、儒家历史哲学的古代发展与基本特征
早在商周时期,中国先民即已具有浓厚的天命观念和历史鉴戒意识。到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出现所形成的“哲学的突破”,也同时宣告了中国古代历史哲学思想的问世。孔子、孟子、荀子、老子、庄子、墨子、韩非子、邹衍等儒、道、墨、法、阴阳等各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围绕着天人、古今、王霸、礼法、时势等范畴,对社会历史发展给出了自己的理论回答,交汇成中国古代历史哲学思想形成期百家争鸣的学术盛况。与道家的“小国寡民”、墨家的“兼爱”“非攻”、法家的“变古易常”以及阴阳家的“五德终始”等各具特色的历史哲学思想相比较,孔子发端的儒家历史哲学主要承续和发展了周王朝开创的礼乐制度和伦理宗教的文化精神,“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礼记·中庸》),强调道德仁义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决定作用。另外,孔子提出的“因革损益”、孟子的“治乱循环”、荀子的“礼法并举”以及战国后期《礼运》《易传》的大同、小康和历史通变等思想都是儒家历史哲学形成期的重要内容,对后世儒家历史哲学的发展和演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随着秦汉大一统帝国的建立,法家和道家思想相继短暂地取得了统治思想的地位,但到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取代法、道两家成为此后两千多年中国社会的统治思想,自此,强调道德仁义和三代之治的儒家历史哲学成为中国古代历史哲学思想发展的主流,对中国社会生活以及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其中,两汉时期,儒家历史哲学以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和“三统三正”的神学化儒学形态为代表,是一种与大一统王朝统治相适应的天命史观;到魏晋隋唐时期,面对玄学与佛教思想的冲击,儒家历史哲学开始吸收佛、道二家思想中的思辨精神及其历史观上的合理内容进行理论上的融合和转进;及至两宋,最终孕育并产生了以理学形态为代表的新儒学,更加精致思辨的天理史观取代了两汉时期较为粗糙的神学化的天命史观,成为宋代以后中国社会主导性的历史哲学思想。
但到了明清之际,面对当时的社会变革和西方实学思想的传入,王夫之、黄宗羲等人在儒家历史哲学内部发出了变革与发展的声音;尤其是王夫之的历史哲学思想,堪称传统儒家历史哲学思想集大成的产物。他在传统儒家历史哲学思想内部展开了许多批判性的总结与反思,尤其批驳了宋明以来的复古史观及其历史退化论思想,认为人类是由上古的野蛮走向后世的文明的不断进化的过程。王夫之的这种历史进化观及其“以人造天”的主体性思想,体现了儒家历史哲学自我更新与变革的时代趋势。但在当时整个社会生活和学术思想领域的影响有限,在中国社会占主导地位的仍是两宋以来理学所代表的天理史观的历史哲学形态。
回顾中国哲学思想史可以发现,孔子、孟子、荀子开创的儒家历史哲学,在中国古代社会长期占据着主导地位。儒家历史哲学思想在历史发展中虽然也有不同的形态变化和理论差异,但强调诸如仁义、天命、天理、心性等道德因素在历史发展中的本原地位和决定性作用,是其一贯持守的最基本特征。作为传统儒家历史哲学的集大成者,王夫之曾对这一特征揭示说:“要归之旨,则以有道而兴,无道则丧,……为废兴存亡之本。”能否以德行道被视为决定社会历史兴废存亡的根本因素。这一道德决定论思想,也成为中国人观察社会历史和修身立世的基本观念,在中国古代历史发展中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坚守道德决定论思想的同时,儒家历史哲学在历史走向上大都持有循环论与退化论的观点。受中国古代朴素辩证法思想的影响,儒家历史哲学没有形成像西方进化论历史观那样一种线性时间的历史观念,因此虽然在历史发展中也不乏有在经验事实层面肯定历史进化发展的朴素的历史进化思想,但在哲学理论的高度,则始终是以阴阳气化的辩证运动所形成的治乱兴衰的两极对立与转化的循环论为理论主导的。而且,由于儒家传统对三代之治的推崇,还进一步形成了诸如《礼运》中的大同、小康和宋代理学家所谓“三代天理流行”“汉唐人欲横流”等各种厚古薄今的历史退化论思想。这种历史走向上的循环论与退化论的理论特征,即便在具有突出的历史进化思想的王夫之的历史哲学思想中也同样存在着显著的印迹。最后,与道德决定论的基本特征相联系,儒家历史哲学在理论上融道德、政治与历史于一体。因为在儒家的观念中,“政治同历史是二而一的事情。政治上的治与乱,也就是历史上的兴与衰”,二者都被视为人类道德生活的延伸,因而在理论形态上,“政治哲学、道德哲学与历史哲学是一种三位一体的关系”。这也成为传统儒家历史哲学在理论形态上的一个重要特征。
二、近代儒家历史哲学的危机与应变
主导中国社会两千多年的儒家历史哲学,在鸦片战争后,面对西方文化的强势东来,遭到了严峻的挑战。经辛亥革命和新文化运动,传统的儒家历史哲学完全丧失了在中国社会生活中的主导地位。取代儒家历史哲学而支配中国人社会生活的新观念,则是严复、梁启超等人引进的进化论历史观,以及其后李大钊等传播的唯物史观等各种强调人类社会进化发展的历史哲学新观念。从此,历史进化论取代了儒家历史哲学所强调的历史循环论与退化论,生存竞争的本能与物质生产等各种非道德因素也取代了儒家历史哲学所强调的道德因素,而成为历史发展的主导力量。中国人的历史哲学观念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转变。
在这种时代与思想变革的背景下,儒家历史哲学如果要在中国社会继续发挥其影响,实现其价值,它就必须要进行理论的调适,以适应现代社会的新发展。如果说儒家历史哲学因为盛赞三代之治的理想属性而形成的历史退化论与历史循环论在变化日新的新时代必须要让位于历史进化论,这一思想发展的趋势在明清之际王夫之的历史哲学中已经出现,在鸦片战争前后龚自珍、魏源以至康有为等人的公羊“三世”说的儒家历史哲学内部发展中也已得到了进一步的开展,那么,儒家历史哲学所一贯持守的道德因素在历史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能否与进化论历史观相融合,换言之,在现代社会历史进化论的基本观念下,儒家历史哲学所强调的道德因素是否能够在现代社会的发展中继续发挥主导性的作用,便成为决定儒家历史哲学在现代社会生死存亡命运的关键。
实际上,自从严复翻译《天演论》将进化论历史观传入中国,将中国传统历史哲学与进化论历史观相融合以解决现时代问题,便成为中国先进的思想精英的理论自觉。康有为是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作出这一探索与尝试的先驱。他将传统的儒家公羊学由据乱世到升平世和太平世的思想,解释为一个由专制而立宪而共和的进化历程,从而在公羊“三世”说的历史哲学基础上展开了与西方进化史观的理论融通,并且创造性地将儒家“仁”的本体论与进化论历史观相结合,认为:“不忍人之心,仁也、电也、以太也……为万化之海,为一切根,为一切源。一核而成参天之树,一滴而成大海之水。人道之仁爱,人道之文明,人道之进化。至于太平大同,皆从此出。”但是,由于他在理论上将作为宇宙本原的“仁”等同于物质性概念的电与以太,以及在人性论上对于人的“去苦求乐”的自然本性的强调,导致他的历史哲学未能坚守儒家历史哲学道德决定论的基本立场;而公羊学“三世”说的历史哲学本身所具有的循环论因素,也使得康有为的历史哲学思想与进化论历史观仍然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与距离。
如果说康有为以公羊学“三世”进化的思想推进了进化论历史观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那么,章太炎则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率先展开了对于进化论历史观的质疑与批判。由于深厚的经史功底和哲学素养,章太炎在早期接受进化论思想时,就提出了有别于机械进化论的万物“以思自造”“以妄想生之”的独特理解;到20世纪初面对列强纷争的现实,他更深刻地揭示出进化论历史观将生物进化规律应用于社会历史的种种缺陷和负面效应,认为伴随着人类智识进化而来的,是“善恶、苦乐二端,必有并进兼行之事”的“俱分进化”。他并由此指出,所谓的进化,是“有进于此,亦必有退于彼,何进化之足言”,对达尔文主义的进化论历史观及其进步信仰给予了一种否定性思考。此后,尤其是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建立在生存竞争法则之上的达尔文主义的历史进化论,其理论缺陷进一步暴露,由此在中国思想界各种有别于达尔文主义的,诸如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进化论、伯格森的创造进化论、杜威的实用主义进化论,以及被视为进化论高级形态的唯物史观等各种历史进化的新思想开始传播与盛行。而梁漱溟的“意欲说”历史哲学与冯友兰的“新理学”历史哲学也正是利用上述进化论思想资源所展开的与儒家思想相融合的理论产物。
其中,梁漱溟通过吸收伯格森创造进化论的生命哲学思想,将与生命冲动类似的“意欲”的满足与不满足视为历史的本质,并按意欲向前要求、意欲调和持中与意欲反身向后,将人类历史分为西方、中国与印度三种文化类型,进而将这三种空间上并列的文化类型理解为人类历史发展上的一个时间的序列,即沿着西洋—中国—印度文化的顺序,渐次发展与复兴。于是在新文化运动激烈反传统的思想氛围下,梁漱溟断言“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这一“意欲说”历史哲学,在吸收进化史观线性进化观念下,凸显了中国儒家文化在现代社会的独特价值,但是,其西洋—中国—印度文化“三期重现说”的历史发展观,由于突出的主观色彩而受到诸多批评;他的“意欲”范畴,也由于所具有的非理性的本能内涵,与儒家历史哲学的道德理性精神存在重要的差异,因而被他自己在后来的探索中主动放弃。
自梁漱溟之后,冯友兰在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建立的“新理学”哲学体系,通过逻辑分析方法的运用,重申了儒家哲学的“内圣外王之道”。在内圣层面,他延续了儒家哲学关于道德因素对历史发展的决定性作用的传统,认为“圣人,最宜于做王”;在“外王”层面,他依据唯物史观的社会类型思想,认为历史发展主要表现为从“以家为本位的社会”进入“以社会为本位的社会”的进化历程。但是,这一外王层面的历史进化观念,“从‘新理学’那个‘经虚涉旷’的哲学体系中推演不出来。那个‘理世界’虽号称具有一切事物的可能性,但丝毫没有在逻辑上也不可能推出任何具体的现实性”。因此,冯友兰并未能够在儒家道德决定论的历史哲学基础上,逻辑地推导出从“以家为本位的社会”进入“以社会为本位的社会”的历史进化观念。在他的哲学体系中,儒家的道德史观与进化论历史观,只是一种外在的关系,二者之间有机结合的理论任务并没有完成。
综上可见,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面对着进化论历史观的严峻挑战,儒家历史哲学仍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进行着理论上的调整与变革,以冀在进化论历史观主导下的现代社会继续发挥其影响与价值。但是,从康有为到冯友兰,几代中国学者虽以不同的方式通过吸收中国传统的历史哲学资源,对进化论历史观作出某种理论上的回应与融汇,但是,由于各种不同的原因,他们都未能在理论建构上实现儒家道德决定论的历史哲学与进化论历史观有机融合的任务。真正完成这一理论融合任务从而开辟儒家历史哲学现代发展道路的,恰恰是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上长期被忽视的熊十力,他通过“本心”本体论哲学体系的构建实现了这一理论融合。
三、熊十力的哲学建构与理论创获
熊十力,现代新儒家哲学形上学的奠基者,自小即通过其父而深受清末民族民主思想的影响,青年时期在进化论等维新思潮的鼓荡下,投身民主革命运动,成为辛亥革命的重要一员。在辛亥革命与护法运动相继失败后,熊十力开始重新思考传统儒学强调的道德修养与身心工夫对于革命成败与中国社会现代转型的重要意义,由此弃政从学,希冀通过讲明学术,来“认清中国何由停滞不进”,从而实现对辛亥革命“终无善果”的理论总结,为中华民族的未来发展辨明道路。此后,经过二十年孤往穷体的哲学探究,到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熊十力相继完成《新唯识论》文言文本和语体本,构建了一个较为成熟的会通华梵、融贯中西的“本心”本体论哲学体系。
“本心”范畴,作为《新唯识论》哲学体系的基石,被熊十力视为“宇宙实体”。它“是吾身与天地万物所同具的本体”,其“德性有常,德用无穷尽”,“备万理、含万德、肇万化、法尔清净本然”,“元自昭明,无有迷暗”等观点,融存有、健动、创生、清净、昭明的属性于一体,具有突出的儒家道德理性精神,因而在中国近现代哲学思想史上,既纠正了康有为将儒家的道德本体“仁”混淆于物质性的以太和电的理论谬误,又避免了章太炎的“思”“妄想”等范畴中的染识和迷妄性质以及梁漱溟“意欲”范畴中的本能因素;而“本心”范畴所具有的能动创生内涵,也克服了冯友兰静态的纯逻辑概念“理”因缺乏具体的现实性而导致的理论局限。正是这一极具创造性的“本心”范畴所具有的丰富内涵,不仅为熊十力从《新唯识论》的本体论向《读经示要》等历史哲学主题的转进提供了形上依据,也为他在历史哲学思想上将儒家道德决定论的历史观与近现代进化论历史观的有机融合奠定了理论基础。
“见体以后大有事在。”熊十力《新唯识论》的本体论建构,由于强调“本心”本体的创生内涵与宇宙的大用流行特征而具有突出的历史性向度;而他的哲学探究本身又具有“认清中国何由停滞不进”的明确的社会历史旨向。因此,当1944年熊十力完成标志其本体论哲学走向成熟的《新唯识论》语体本以后,他便转向了以“化理”“治道”为主题的“治化论”领域的历史哲学思想的探索,以实现自己在近现代民族危亡背景下“明先圣之道,救族类之亡”的治学旨趣。此后,除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进一步阐释其本体论哲学的《新唯识论》删定本和《体用论》《明心篇》外,熊十力最主要的著述就是以《读经示要》《与友人论张江陵》《论六经》《原儒》《乾坤衍》等为代表的一系列有关群化、治道主题的撰述,表达他在《新唯识论》“本心”本体论基础上对于“治化论”的哲学思考。因此,虽然熊十力没有进行明确的历史哲学主题的独立撰述,但是通过《新唯识论》的“本心”本体论与《读经示要》等一系列融贯经史的“治化论”主题的撰著,他对人类历史的本质、变易发展、历史主体、历史理想、历史价值、历史认识以及“治化论”视域下中西文化会通的现实历史发展道路等,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探究。这些诸多内容,在他哲学形上学的“本心”本体论的统摄下,已经构成了一个内容较为丰富与系统的“本心”本体论的历史哲学思想体系。
历史哲学涉及社会历史发展的诸多理论问题,但通常需要解答两个最基本的问题:一是历史何以可能——关于人类历史的本体或存在根据的思考,二是历史如何展开——对人类历史的演变、发展与趋向的总体性的理论回答。对此,熊十力在“本心”范畴所构建的本体论哲学基础上给予了理论解答。首先,他从“体用不二”的本体论架构出发,将历史的本质归结为作为宇宙本体的“本心”的显发。而“本心”在其哲学体系中作为宇宙实体,又同是道德本体,亦即传统儒家哲学的“仁”体,由此,道德本心成为人类历史的本体与存在根据。这就在本体论的高度确立了道德心性在历史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而另一方面,“本心”“仁体”又是一生化不已的生命本体,在其创生和主宰作用的推动下,通过熊十力对周易辩证法思想的改造与发展所提出的“翕(物)辟(心)成变”,即“翕以显辟,辟以运翕”的心物之间相反相成的辩证发展的演化机制,宇宙发展经历了一个由物质至生命直至心灵的由自然而至人文的层级突现的创化历程。人类历史由此在物质宇宙的发展基础上得以成立,并在“本心”本体创化不已的发展中,进一步通过历史领域心物之间“翕辟成变”的相互影响与制约的创化机制,实现“由愚而进于明,由闭塞而进于开通,由简单而进于复杂,由野蛮狭陋而进于智慧,与合群公德,及声明文物之盛”,直至出现“本心”本体充分显发的“仁道始成”“仁体全显”的太平理想世界。由此,熊十力就在道德本体的生命哲学基石上,将传统儒家历史哲学所强调的道德因素在历史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在现代社会所强调的进化论历史观背景下予以了理论重建,使儒家道德决定论的历史哲学由古代的循环史观甚至退化史观推进到进化史观的现代形态,成功实现了儒家道德史观与进化论历史观的有机融合,从而在现代社会历史进化论的理论信仰下,重新肯定和高扬了传统儒家历史哲学所强调的道德理想和道德实践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主导性地位,为儒家历史哲学的现代发展开辟了道路。
除了上述关于人类历史的本质与发展问题的理论思考,熊十力对于历史主体、历史理想、历史价值、历史认识也都围绕着“本心”本体论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探究。如,在历史主体观上,熊十力提出“士民并重”的思想,并在儒学道德决定论基础上实现了崇圣与重民的内在统一;在历史理想观上,熊十力通过“本心”本体“体用不二”的哲学诠释,重新确立了传统儒学由“内圣”而“外王”的思想进路,展现了由儒家“内圣”学的道德践履开出民主、科学与太平大同社会的“新外王”的理想社会憧憬;在历史价值观上,熊十力通过“本心”显发的历史本质与主体修养工夫的阐述,凸显了传统儒学“人者天地之心”的价值论立场;在历史认识观上,熊十力通过“本心”本体的形上规定与本习之辨的修养工夫论,对历史认识何以可能给予了本体论回答,并在历史认识方法上强调以“性智”统摄“量智”,传承了儒家历史哲学强调以道德理性统摄知识理性的基本特色。而他在《读经示要》中提出的“以仁为体”的治道“九义”,更集中阐发了他的“治化论”思想“不舍器而求道,亦不至睹器而昧于其原”的“道器为一”的理论纲领。这一治化论纲领,在近现代社会背景下,强调既要重新高扬传统儒学视道德心性即“道”为社会历史本原的基本立场,以克服西方文化因不识本心仁体而致纵欲殉物的弊端,又要积极吸收与肯定西方近现代社会重视物质生产与政治制度等“器”的物质层面的发展与变革的合理思想,突出体现了熊十力的历史哲学思想强调在中西会通中通过对儒家传统治化思想的现代阐释而实现“救治西洋之弊而亦融西洋之长”的理论特征与致思旨向。沿着这一致思方向,熊十力将传统儒家的历史治化思想与近现代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相结合,对社会历史中的“道”“器”层面与要素,中国历史盛衰发展的道德、政治与学术根源,以及中西文化交汇背景下中国与人类社会的未来发展道路,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从而揭明通过融会西方文化的民主与科学以实现儒家“道统”的全面重建来完成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熊十力认为,这种合道德、民主与科学为一体的社会历史与文化发展道路,不仅“救族类之亡,亦即以此道拯全人类”。熊十力“治化论”探讨的这一理论结论,不仅标志着他的历史哲学思想建构的完成,也标志着他“以体用不二立宗”的“本心”本体论哲学融贯本体论、宇宙论、人生论、道德论、知识论与治化论六大领域的理论体系建构的最终完成。
总之,熊十力通过《新唯识论》的本体论与《读经示要》等治化论主题的撰著所实现的哲学创辟,使他的历史哲学思想以一种儒家道德理性主义的生命创化史观新形态,跻身于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占主导地位的进化论历史观大家族,而成为其中的重要一员。他的“本心”本体论历史哲学思想所具有的道德理性精神,使它既与斯宾塞的机械进化论、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进化论和伯格森的创造进化论以生存竞争、互助或生命冲动等本能因素来理解进化区别开来,又与杜威的实用主义进化论以及萨缪尔·亚历山大等英国突现进化论对进化理解的自然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态度有别,更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从物质生产角度理解人类历史的进化不同,展现出鲜明而独特的中国传统哲学的精神意蕴和思辨智慧。而他的历史哲学思想所揭明的通过对儒家心性之学的“道统”及其发为大用的民治与科学思想的“治统”与“学统”的全面重建来实现中国社会现代转型的理论结论,对于中国与世界向何处去的时代问题,给出了有别于马克思主义和西化派的自由主义的创造性的回答,在理论实质上也揭启了其弟子牟宗三等人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明确提出的以儒家心性之学为本原以实现道统、政统与学统“三统并建”为标志的“第三期儒学”发展的理论纲维与时代使命。
熊十力的哲学在他生活的时代,诚如学界所论,“一直被排斥在时代的主流之外,其影响始终局限在一个有限的学术圈内”,在现代中国哲学的发展中“势力最小,地位最低,而知道他的人最少”,因此,直到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随着他的弟子牟宗三、唐君毅等第二代新儒家群体在香港、台湾的活动,熊十力及其哲学才逐渐引起了大陆学者的重视,并在八十年代后获得了多方面的研究,熊十力由此也被誉为二十世纪中国哲学发展的“中心的角色”而备受尊崇。但是,由于深受传统儒家历史哲学理论形态的影响,熊十力的历史哲学思想也是融贯在《新唯识论》与《读经示要》等道德形上学与治化论等主题的阐述之中,而未能取得独立的理论形态,因此,蕴含在他上述著述之中的历史哲学思想,一直未能得到学界的关注而沉隐不彰。直至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作为当时大陆熊十力研究的主要开拓者,郭齐勇在他的博士论文与后来出版的专著《熊十力思想研究》中,才对熊十力的历史哲学思想进行了首次探讨。他在该著第五章“熊十力的经学思想——‘政治—历史哲学’阐秘”中,以专节“经学外壳下的历史哲学”为题,揭示了熊十力“德性史观的社会进化论”和“道德理想主义的历史观”本质。但由于郭齐勇是以熊十力的经学思想的阐释为目的,并以“熊十力的政治—历史哲学着力表现他以现代批判传统、防止传统僵化的一面”为主旨,在对熊十力历史哲学思想的认识上无疑受到了其经学著作的限制,从而认为“熊十力的历史哲学思想也是比较零散、不成体系的,也是利用解经的形式表达的”,因此对熊十力历史哲学思想内容的丰富性、系统性及其在儒家历史哲学思想史上的重要意义并未予以足够的重视。此后,国内学术界对于熊十力的历史哲学思想给予了一定的关注,如张文儒等在本世纪初将《读经示要》明确定位为“代表熊十力政治、历史哲学的著作”,但是,对熊十力的历史哲学思想及其在儒家历史哲学现代发展中的意义的进一步探究却仍近空白。
然而,深入研究熊十力的“本心”本体论哲学体系与《读经示要》等治化论撰著,就会发现,在中国近现代哲学思想史上,正是熊十力通过孤往穷体的哲学创辟和融贯经史的理论拓展,最终在历史哲学思想上完成了自康有为直至冯友兰始终未能完成的融儒家道德决定论的历史观与进化论历史观有机统一的理论任务,将儒家历史哲学推进到进化史观的现代形态,实现了儒家历史哲学在现代社会的创造性发展,从而为牟宗三等第二代新儒家学人更具现代学术形态的历史哲学思想建构开辟了道路。当然,作为特定时代的产物,熊十力的历史哲学思想也具有不可避免的理论局限。如,他在“翕辟成变”的宇宙演化机制的阐释中,由于过于强调“辟”的绝对性而忽略了它在心物辩证统一的发展过程中的相对性一面,因而在理论上使他对于传统儒家的道德心性论与理欲、义利之辩等理论框架突破不够,未能真正走出传统儒家历史哲学过于强调主观内省的道德修养的既有视域,使理论与现实生活的具体历史世界出现相当的隔阂。另外,他的历史哲学思想由于未能进行独立的体系化的理论构建,在内容上较为分散、繁杂,在表达形式上与现代学术的明确分化和系统发展也有一定的距离。
在治学、思想上深受熊十力教益的王元化,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文化反思中曾经指出:“他(熊十力)早就说过东方文化其毒质至今已暴露殆尽。他所关怀的是发扬其中固有的优质。”熊十力在进化论信仰的现代社会背景下,重建传统儒学道德史观的哲学创造,也正体现了他在对中国传统历史哲学的清醒认识基础上对于其中德性主义的“固有的优质”的现代阐释。而长期从事熊十力思想研究的景海峰,在近来回顾时也特别强调:“从熊十力研究中生发出很多中西哲学差异问题的思考,这对重新理解中国哲学有非常重要的启示。……过去我们主要看西方哲学框架下的哲学在中国的传播、解释和翻译,而对中国哲学从古典向现代转型过程中的努力和创造问题不是很重视,对熊十力的认识和理解是影响上述问题转移的重要资源。”因此,深入发掘与梳理熊十力的历史哲学思想,并揭示其在儒家历史哲学现代发展中的作用、贡献与局限,在民族文化复兴的时代背景下,对于深入认识中国传统儒家历史哲学从古典向现代转型过程中的努力和创造,积极推动包括儒家历史哲学在内的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发扬其中固有的优质”于世界,都将具有重要的理论启示与时代价值。
注释:
①“三统三正”说是董仲舒为论证汉王朝统治的必然性和合理性而提出的历史观。“三统”是指历史朝代必须按照夏、商、周三代所代表的黑、白、赤“三统”依次循环更替;“三正”是指凡异姓受命而王,都必须要改正朔,黑、白、赤“三统”要分别以寅月(一月)、丑月(十二)和子月(十一月)为正月。参见汪高鑫《中国史学思想通史》(秦汉卷),黄山书社2002年版,第172页。
②关于王夫之历史哲学思想中的历史循环论与退化论的相关论述,参见蔡尚思《王船山思想体系》,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18页、第118—120页。
③ 唯物史观与进化论历史观的思想实质虽不相同,但它们视历史是进步发展的基本观念是一致的,因此,在中国现代史上,“唯物史观开始是被当作另一种更高级的进化论传入中国的”(参见王增智《社会进化论:唯物史观在中国早期传播的理论中介》,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4年第9期,第202—209页)。正是在此意义上,将唯物史观也纳入到这种视历史为进步发展的广义的进化论历史观的理解之中。
④关于熊十力的“治化论”主题的历史哲学属性及其与熊十力《新唯识论》的哲学本体论之间的逻辑关联,参见林家虎《熊十力思想的历史哲学向度与研究回顾》,载《孔子研究》2013年第6期,第69—76页。
⑤治道“九义”,包括“仁以为体”“格物为用”“诚恕均平为经”“随时更化为权”“利用厚生,本之正德”“道政齐刑,归于礼让”“始乎以人治人”“极于万物各得其所”和“终之以群龙无首”。详见熊十力《读经示要》,《熊十力全集》第3卷,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581—624页。
⑥关于哲学的六类划分,参见熊十力关于《新唯识论》的论述:“新论建本立极,而谈本体。学不究体,自宇宙论言之,万化无源,万物无本。……自人生论言之,无有归宿。……学不究体,道德无内在根源。……学不究体,治化无基。……学不究体,知识论上,无有知源。”(参见《十力语要·印行十力丛书记》,载《熊十力全集》第4卷,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6—7页)。六类中,他的“本体论”“宇宙论”“人生论”“道德论”已融成一片,而“知识论”也如学界所论:“知识论与本体论合而为一,遂不复有另成一系统之知识论的必要。”(参见张学智《从熊十力的本体观看其量论未造出之由》,载单纯主编《国际儒学研究》第14辑,九州出版社2005年版,第434页),因此,“治化论”的探讨便成为他完成其哲学体系所需探究的最后的领域了。
⑦ 突现进化论在中国影响较小,关于此派进化论与机械进化论、生命进化论和实用主义进化论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参见张汝伦《现代中国思想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6—8页。不过,张汝伦在论述影响中国近代进化论观念的“西方近代进化论观念的家族”时主要列举了上述四派,而忽略了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进化论也是对中国现代进化观念具有重要影响的西方近代进化论观念家族中的一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