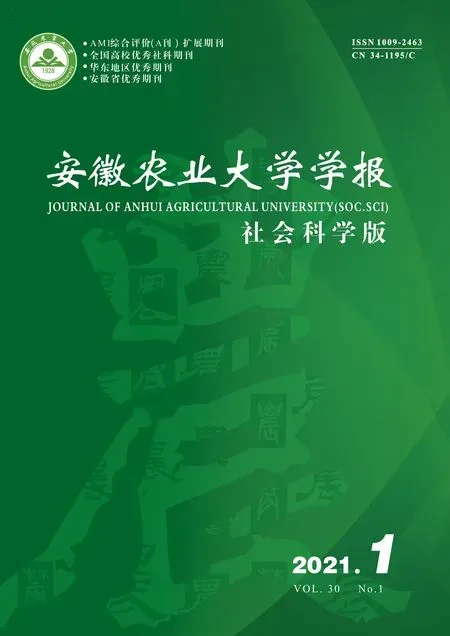论萨拉·沃特斯《轻舔丝绒》中的女性亚文化风格*
陆道夫,魏韵玲
(广州大学 外国语学院,广东 广州 510006)
萨拉·沃特斯是当今英国文坛备受瞩目的新锐女作家之一。她早期创作的三部长篇小说《轻舔丝绒》《灵契》《指匠》,均以19世纪英国维多利亚时代为创作背景,通过戏仿的形式,在历史和当代社会现实之间展开对话,创作主题侧重表现女性情感纠缠和女性婚姻等同性恋问题,通过重新编撰历史,构建并呈现维多利亚时期被社会边缘化的女性生活状态,因此,这三部小说常被称为“维多利亚三部曲”。小说出版后,文学界和读者们一时间内大力追捧,媒体称赞沃特斯“笔触深邃、情节巧妙、人物刻画幽微,充满了维多利亚时代特有的压抑情绪和蠢蠢欲动的禁忌氛围”。萨拉·沃特斯甚至还被“Granta”杂志推选为“20位当代最好的英语作家”之一(2003年),获得了《星期日泰晤士报》“年度青年作家奖”(2000年)、“年度英语作家奖”(2003年)、“CWA历史犯罪小说匕首奖”(2002年)。她多次入围“柑橘奖”(2002年、2006年)和“布克奖”(2002年、2006年、2009年)等。
《轻舔丝绒》以英国海边小镇的牡蛎女孩南希的三段情感故事为主线。南希在游艺宫看表演时,对男装丽人演员姬蒂非常痴迷。在姬蒂的鼓励下,南希远离家乡,与姬蒂同去伦敦大剧场演出。南希对姬蒂的初恋并没有如愿以偿,遭到好友姬蒂的情感背叛后,她不得已成了贵妇人戴安娜的小情人,两人终日无所事事,纸醉金迷。后来因为南希不满于戴安娜的侮辱与蹂躏,被戴安娜赶了出来。沦落街头时,偶然遇到曾有一面之交的朋友弗罗伦丝,经历了各种生活磨难和精神洗礼,南希和弗罗伦丝的姐妹情终于发展成共同为事业奋斗的好伴侣。
一、“亚文化”与女性亚文化
“亚文化”最早出现在20世纪40年代芝加哥学派的社会学研究中。1964年,英国伯明翰文化研究(The Center for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 简称CCCS)中心云集了诸如斯图亚特·霍尔、菲尔·科恩、迪克·赫伯迪格等为代表的重要学者。在他们看来,社会、地区、阶级等方面的差异导致了许多不同类型的文化群体。其中,在一个社会中占统治或主导地位的文化往往被称为“主流文化”;而某一群体所持有的足以区别于他者的社会文化或行为特性则被称为“亚文化”。主流文化所代表的是一个社会中占支配地位的阶级或群体的意志,而亚文化是社会中处于边缘地位的群体的文化表达,是从属的、次要的文化。伯明翰学派的学者们从文化的角度对亚文化加以界定:“正如前缀sub所示,亚文化是更广泛的文化内种种富有意味而别具一格的协商。他们同身处社会与历史大结构中的某些社会群体所遭际的特殊地位、暧昧状态与具体矛盾相应。”这一定义显然强调了亚文化的抵抗性、风格化及边缘化三个重要特征。然而,由于该学派对于“亚文化”的研究具有强烈的男性意识,是对男性表达和男性风格的唯我独尊式的关注,女性群体很难成为他们的研究主体。
20世纪60年代,由于受到第二次妇女解放运动及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女性群体日益壮大,女性文化乃至女性亚文化在更包容多元的世界得以凸显。以安吉拉·麦克罗比为代表的妇女研究小组继承与批判伯明翰学派的亚文化理论基础,推动了女性亚文化的研究。在麦克罗比看来,女性在亚文化研究中并不总是处于“缺席”状态,亚文化的特殊表现方式和社会特征使得女性“不露面或者是部分出场”。麦克罗比重点关注女性在亚文化中处于怎样的地位、扮演着怎样的角色,以及通过何种方式建构了一个有别于男性的文化空间。女性亚文化与男性亚文化的差异主要表现在“风格”与“文化空间”的不同。事实上,女性亚文化的形成经历了从第一个在亚文化中出场的女性群体“无赖女孩”到“慕嬉士女孩”的风格演变。文化空间主要在家庭、学校及俱乐部等空间中。萨拉·沃特斯的小说《轻舔丝绒》体现出了维多利亚时期的女性亚文化表征以及维多利亚时期女性亚文化风格与主流文化进行“抵制”与“反抗”。
二、《轻舔丝绒》中的女性亚文化风格表征
众所周知,英国维多利亚时期(1837—1901)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都开创了一个崭新的时代,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日不落帝国”。然而,工业革命迅速发展的同时也激发了一系列的社会矛盾。在这一时期,英国社会群体分化严重,社会阶层愈加复杂化,女性的生活状况也被卷入这场变化的洪流之中。工商业的发展培养了一批有闲阶层的女性。同时,社会化大生产将女性从琐碎的家务中解放出来,越来越多的女性不满足于成为男性的附庸,走出家庭谋求工作,从而也推动了妇女运动的发展。因此在这个时期女性亚文化显现在社会中的方方面面。萨拉·沃特斯在重构历史的过程中,极大地还原了维多利亚时期的真实社会风貌,把女性亚文化风格的表征赋予在服饰、场景及语言等三个维度。
首先是女性服饰的细致描述。小说自始至终出现了大量描绘维多利亚时期女性服饰的段落篇章。罗兰·巴特曾说过:“服饰可以被当作符号来对待,一面是样式、布料和颜色,而另一面是场合、职业、状态、方式,或者我们可以进一步将其简化为一面是服装,另一面是世事。”因此不同服装特色体现不同女性的社会阶层。当时贵族女性华美又多样化的服饰引领社会时尚,平民女性的服装是对上流社会的学习和模仿。维多利亚时代初期,复古风盛行,蕾丝被大量使用,配在衣服的领口、袖口、下摆等处。另外,还大量运用了荷叶边、蝴蝶结、包钮以及具有王室风格的高腰、公主袖等。在当时,贵族还掀起了男女服饰元素混合的热潮。小说中的戴安娜让南希置换角色扮演,装扮成珀尔修斯、丘比特、亚马孙女战士、安提诺乌斯等男性角色,配上弯刀、翅膀、弓箭、古罗马宽袍及腰带等配饰。一时间,上流社会的女性服饰元素竟然成为平民女性争相模仿的对象。当南希还是“牡蛎女孩”的时候,在重要的场合穿上有绸缎腰带和蕾丝的晚装长裙、用中国丝绸做的低领短袖裙子。在音乐厅和剧场工作的女演员的服饰也出现了大量男性服饰特色。南希第一次在剧场见到台上表演的姬蒂,她当时“穿着一套剪裁得体的男士西服,袖口和前襟镶着闪亮的丝绸。翻领上别着一朵玫瑰,前袋里插着一副淡紫色的手套。她背心下面穿的是雪白笔挺的衬衫,立领有两英寸高。她的领口系着一个白色蝴蝶结,头上戴着一顶礼帽”。水手服、禁卫军制服、法兰绒西裤等都是当时“男装丽人”非常热衷的装扮,系领结、穿裤子对于女演员们来说非常普遍。同时她们的装扮也会融入蕾丝、蝴蝶结手套、丝绸背心和长筒袜、天鹅绒等女性元素。南希和姬蒂成为双人组合登台表演之后,掀起了模仿热潮:“一对穿男装、戴礼帽、穿长靴的女孩比单独一个更令人激动,更有魅力,更有一种说不出的活泼俏皮……她穿着一英寸高的鞋子,我穿着女性化的平底鞋,那剪裁得当的西装凸显我苗条的身材和女性的曲线。”后来南希和姬蒂一同在不列颠剧院演童话剧《灰姑娘》时,女演员的服装都非常精致美观,“简直是你这辈子见过的最好的演出服”,其中包括有金色的裤子、闪闪发亮的背心、马裤、薄纱、水手服等。男女两性混搭的服饰装扮,应该是维多利亚时期一道独特的女性亚文化风景。
其次是女性“在场”的场景设置。小说通过女主人公南希的个人成长缩影,折射出维多利亚时期女性逐渐挣脱家庭束缚,寻找社会位置的尝试。因此这个时期的女性有更多在社会活动的空间。南希最初是英国小镇惠特斯特布尔的“牡蛎女孩”,在坎特伯雷游艺宫与姬蒂相识。姬蒂是女扮男装的“男装丽人”,剪着帅气利落的短发,在舞台上歌唱舞蹈。由于南希对姬蒂的爱恋,她决定远离家乡,跟随姬蒂到伦敦,免不了家人的担忧:“她抱着我,哭着说放我走真是愚蠢。还有戴维,他荒谬地说,我现在去伦敦还太小了,一到伦敦就会被特拉法加广场的有轨电车撞倒。还有艾丽斯,听到这个消息她什么都没说,而是哭着跑出了厨房,谁也劝不动,直到午餐时间才出来干活。”南希在离家前,家人的反应从侧面看出,对于当时的女性,尤其是偏远小城镇的女性想要外出闯荡,是不被主流文化观念理解和接受的。
布利斯带领南希和姬蒂参观伦敦时,看见许多剧院和歌剧院,如瑞典著名女高音珍妮·林德首场演出的女王剧院,还有克里剧院、帝国剧院、阿尔罕布拉剧院等,众多女演员、女歌唱家都在这些地方成为明星,也吸引了不同阶层的女性观众,如“从马车上下来的淑女”“端着鲜花和水果的女孩”“披着披肩的女人、系着领带的女人,还有穿着短裙、露出脚踝的女人”前往剧场观看表演。然而,姬蒂并没有像他们预期的那样会大红大紫,因为“她的对手太多了,男装丽人太多了,这个行当原来和玩杂耍的一样具有专业性质,现在突然就成了个人满为患的行当”。可见维多利亚时期演员成为女性在社会上谋生的重要职业选择之一,并且倾向于模仿男性的角色以获得更多关注。在沃尔特的鼓励之下,南希从原本姬蒂的服装师变成与姬蒂一同登台表演的演员:“双人组合!来个士兵,和他的伙伴!或者一个花花公子,和他的朋友!总之,两个可爱的女孩穿着裤子,比单个更强!你们什么时候看过这种演出?我们会引起轰动的。”新颖的形式让她们的表演成为热门节目,大受欢迎,且掀起模仿热潮。南希和姬蒂放弃音乐厅生涯之后,选择到霍克思顿的不列颠剧院演童话剧《灰姑娘》的第一、第二男主角。有许多女性都在剧院中谋生,如跳芭蕾舞女孩、看管衣橱的女孩、饰演仙女和灰姑娘的女演员等。
第三,女性群体的语言表达也表现了女性亚文化风格的特征。从小说中,我们得知,南希与弗罗伦丝重逢之后,由于弗罗伦丝参与到女性运动及慈善活动之中,因此她们与身边人的交流也常常涉及这些方面的话题。弗罗伦丝家中经常有人来做客,常常谈及妇女自由联合会、妇女工会联盟等与女性相关的组织。弗罗伦丝经常为改善底层妇女生活现状费尽心力,在与南希交流时提到“女人的工会”“选举权”等,体现出当时小部分女性群体努力争取女性权益,冲击男性主导的社会。女性之间的谈话不再仅仅停留在如何照顾好家庭成员,而是能寻找在社会中的位置。女性帮助残疾人、移民和孤女找工作、找房子等,慈善组织进行家访、组织募捐。女性走出家庭聚集在一起,使社会意识到女性群体的需求。
女士俱乐部是当时女性休闲娱乐的隐蔽场所。弗罗伦丝称其为“享乐”。弗罗伦丝第一次带南希到“船上的男孩”女士俱乐部时,谈到“女同”在女士俱乐部可以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生活,不用在意他人眼光。在维多利亚时期,女性群体处于社会边缘,女同性恋者更是受到社会的排斥。她们在繁华城市的隐蔽酒吧中汇集,享受属于她们的自由空间。她们可以随意地喝酒抽烟,拥抱情侣,穿上任何想穿的服装。南希“曾经以为自己是唯一一个这样的人”,但是在此处寻找到了女性身份认同,不再需要生活在男性的目光和管控之中。
小说临近结尾处,南希与拉夫尔在剧场里共同完成的即兴演讲,将情节推向了高潮,还原了当时女性自行组织游行、演说活动的场景。拉尔夫在演讲中大胆地谈到了“社会的大变革”“没有人再需要救济”的未来愿景,鼓励男女参加工会,有选举权的人“为女同胞们争取权利”。语言是社会文化现状的真实反映,维多利亚时期女性语言中出现诸多“社会主义”“民主”“集会”“薪资”等词汇,正是体现了女性群体在社会中现身与努力争取自己的权益。女性积极投身慈善活动及女性运动是她们踏进社会十分重要的一步。她们逐渐涉足英国社会的各个方面,努力纠正社会弊病,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维多利亚时期的社会矛盾。
三、“抵制与反抗”的女性亚文化风格
亚文化是通过风格化的和另类的符号,对主导文化进行挑战,进而建立一种认同性的附属文化方式,如无赖青年、光头仔、摩登派、朋克等。风格是亚文化最具有吸引力和可读性的特征,是亚文化的标志或符号。菲尔·科恩将亚文化的风格概括为三种元素:形象、风度、行话。所谓“形象”,主要是由服装以及发型、珠宝饰物和手工制品之类的配饰构成的外表;而“风度”则由表情、步法和身姿构成;“行话”是一套特殊的语汇以及它被传达的方式。亚文化群体打破了日常符号系统的规则,以不同的文化作为原料,进行挪用、改换和拼贴,对主流文化进行解构,因而形成了具有独特风格的亚文化现象。
值得一提的是,女性亚文化在萌芽状态时是个人行为或狭小团体的自我愉悦和发泄,在社会上逐渐扩大规模并掠夺公众视线的过程中形成了女性亚文化风格,并对权威符码和社会制度带来一定的抵制与反抗。
作为社会风尚的侧面反映,服装和服饰非常明显地见证了女性权利的演变,甚至在20世纪40年代后,以亚文化的形式参与了女权运动。20世纪初,皇室贵族、富人名媛以及高级时装会所掌控着社会风尚。上流社会的女性为了应对各种社交场合和礼仪场所,用大量奢华的装饰衬托富丽堂皇的外观,夸张的裙裾长度、高耸的蓬裙、在裁剪上尽可能突出女性的身体曲线,配合紧身内衣,以及锥形胸罩勒紧腰部来追求所谓完美身材。这些时装的背后,承载着男人对于女性的欲望,对于女性身体的极致凌虐。
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的衣服使个体变成了女人,在社会中看不到女性个体服装的真正自我,只能看到繁复、华丽、高度性别化的服饰。衣着不仅能够营造出一个性别化主体的假象,甚至能在身体上烙上二元对立性别规范的痕迹。英国主流社会女性服装旨在创造完美的女性形象,于是,很多女性都以穿着束腰胸衣、衬裙、裙撑等为时尚。殊不知,这样的装扮也限制了女性的行动,身边需要男性的保护。《轻舔丝绒》中女性演员在舞台演出也是站在男性审美视角。小说中剧院的经营者都是以男性为主,为了迎合多数观众的“性别”审美,预设演出角色的性别化视角。姬蒂和南希初到伦敦西区时,剧院经纪人布利斯先生建议她们“在城里四处走走,观察一下男人”,并且“观察他们的性格、他们的举止和走路姿势”,目的就是为了拓宽戏路,获得更多观众的认可和喜爱。姬蒂尝试穿上警察制服、水手服等具有男性气质的服装,扮演警察、水手等角色,在潜移默化的过程中把“男性化凝视”加以“自然化”,使之成为占主导地位的观看行为。这种男性化视角令南希“明白了一个关于自己的真相”,认为“无论我当女孩有多成功,都比不上扮成男孩获得的成就更大,哪怕是扮成一个很女孩子气的男孩”,并“顺理成章地剪了头发,换了名字”。南希急于摆脱女性特质,塑造男性形象,实则是内心受到社会对于女性刻板印象的影响,对女性身份感到自卑和不认可。直到南希重遇弗罗伦丝时,才逐渐尝试打破男性审美主导的服饰文化符号。南希在弗罗伦丝家时“穿着裤子在家里做家务”,“穿着裤子走出了门”,被邻居们看到后也丝毫不介意。弗罗伦丝外出时穿上“一件女式衬衫、一件背心和一条短裙”,更加休闲舒适,没有太多束缚。女士俱乐部中有很多女性都“穿着裤子和背心”,“想穿什么就穿什么,不在乎别人的眼光”。女性服饰随着女性在社会中的角色多样化而形成更加多元的女性亚文化服饰风格,颠覆原有的主流男性文化意义,形成女性自我的意指实践,将男性与服装特色相融合,冲破过去二元对立的服装性别差异。
有趣的是,20世纪的爵士时代,英美出现了“flapper girls”,一度非常流行,这让传统意义上的女性曲线美审美观遭到了挑战,女性们开始否定女性身体特征。香奈儿在1923年的一次访谈中表示,是她给了女人自由。因为之前的女性们基本上都是精致时装的统一配置:蕾丝、束衣、内衣、厚垫等,层层包围,让女性们每每汗流浃背,身不由己。香奈儿很自豪地认为,是她把女性自己的身体还给了她们自己。
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的不少女性大多被“囚禁”在社会权力中。当时的家庭被赋予极高的象征意义和神圣地位,而家庭生活的方方面面充斥着杂志、广告、手册和小说。“甜蜜的家”观念的内涵中一个重要的观念是“家庭天使观”。“家庭天使观”认为女性应该柔弱、纯贞、善良、优雅,是家庭的天使。因此“家庭天使”只能是装饰性的、被动的和依赖性的。《轻舔丝绒》中刻画了许多女性走出家庭束缚,以自己的方式建构起一种不同于传统的私人文化空间。南希“在十八岁以前,我从来没有怀疑过自己对牡蛎的感情,也从来没有离开父亲的厨房去寻找事业或者爱情”。父母也是期盼她“嫁给一个惠特斯特布尔的男孩,就在他们身边成家”。但是南希后来为了追求爱情,勇敢摆脱家庭的安逸及束缚。南希在重返家庭之后与家人产生矛盾,正体现了女性亚文化风格对传统家庭观念的抵抗。南希在为家人分发礼物时,父亲的“笑声听起来却不那么自然”,母亲“仿佛不敢去拿似的”,屋里甚至“出现了一阵尴尬的踱步”。姐姐甚至批评南希唱歌是“荡妇的生活”,在姐姐看来,姬蒂“做的事,没有一件是好的!她把你带走了,让你变得古怪了。我一点都不了解你了。我真希望你从来都没有跟她走,或者再也不要回来!”探亲“开始就不顺利,随后也不太美妙”,“我越来越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回家了”,甚至在最后离开家的时候“母亲笑了笑,但是笑容生硬。艾丽斯到最后依然态度僵硬”。南希从开始哭泣想家到在家中一连串负面情绪的变化及不适应,可见女性从以家庭为主的活动场景挣脱出来,尝试对家庭权力关系进行解脱和违抗,走上独立和自由的道路,就难以融入到原本传统的文化形态中。女人如何看待自我身份,这不单单是其个人自我评价的指标,同时也是女性地位的象征,女人不该一味臣服和取悦于男性。就像西蒙·波娃在其《第二性》中所强调的那样,女人必须真正拥有女性特质,才能成为与男性平等的完整个体。拒绝自己的女性特质无异于否定自己的一部分人性。
相比较而言,当时的男性亚文化风格多数以公开的大街场景来展现,而女性亚文化大多是在相对封闭、相对隐秘的私人空间里得以呈现的,形成了独特的“卧室文化”及“俱乐部文化”的女性亚文化风格,对公众性的男性主导文化进行隐秘抵抗。“卧室文化”是女性在自己或朋友家的卧室里建构起来的、与女性伙伴分享生活体验的一种集体性文化。这种“女孩帮”式的集体性文化显示出安全、私密、排外等特征,散发着自我想象、彼此依赖的气息。弗罗伦丝的家中经常有不同职业的女性聚集在一起,“她们经常来喝茶,带来书、小册子或者八卦”,又或者是在客厅“召开紧急会议”,“进行无聊的辩论”。工业化的快速发展拉大了社会贫富差距,许多底层平民失去了原本的住所,露宿街头。女性群体自发地成立民间慈善组织帮助有困难的群体,甚至在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形成了颇具影响的“家访运动”。“俱乐部文化”是女性在俱乐部休闲娱乐形成的女性亚文化风格,但是她们只能在城市的隐蔽空间中立足。卡文迪什女士俱乐部在“一栋狭窄的灰色建筑”中,楼梯很窄,名牌很小,门很窄,有“一位女士站在阴暗的门槛处”。“船上的男孩”女士俱乐部在“路的尽头”,是个“低矮的建筑”,“从后面一个更小更黑的入口进去。一个坡度很陡的楼梯把我们带到地下”,女性能够在其中谈论男性话题,找寻属于女性的自主意识。女孩们赢得了属于自己的时间和活动空间,建构起了不同于男孩的休闲和个人空间,也为她们提供了不同的“抗拒”自己处境的可能性。
在男权秩序的主宰下,无论是在政治、经济还是文化空间中,男性始终占有主导地位。
“社会性别通过家庭、学校等社会化机构,以及社会分工,大众传播媒介的作用等建构和再造,并由个人在接受社会既有规范的过程中加以内化”。因此,社会的性别刻板印象极大地影响性别语言风格的不平等。《轻舔丝绒》小说人物之间的对话使用到“便宜”“贫困”“拘谨”“笨拙”等较为负面的形容词来描述女性,而男性则是被描写成有野心、希望、梦想的群体。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第一次女性主义政治运动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女性,为女性争取公民权、参政权等政治权利。在新的社会背景下,进行革命的女性群体尝试对男性主导话语体系进行抵抗。女性书籍和杂志是女性亚文化语言风格重要的宣传途径,是女性亚文化风格对男性统治权力反抗的重要阵地。戴安娜为慈善机构捐钱出力,参与制作一本名为《箭矢》的女性参政杂志,内容涵盖了女性参政、女性教育等革新性观点,宣传英国女权运动。弗罗伦丝家中存放了一些颇具革命色彩的杂志和书籍,如《正义》和《走向民主》等。小说中引用了美国诗人沃尔特·惠特曼《草叶集》中的内容:“忘掉差异吧!犯下的美德一样多的罪孽!让职业和性别平等!让所有达成一致!”男性作家为女性发声,作家笔下的世界正是对真实社会现状的反映。惠特曼写到的“差异”“罪孽”无不是对男女地位不平等的控诉,呼吁社会“平等”及“一致”。女性借助传播媒介在女性群体中迅速地传播、扩散,消解和颠覆主流文化符号、抵抗主流意识形态。除了女性书籍和杂志之外,女性日常生活谈论的话题不再仅仅停留在家庭琐事,而是更多地加入了女性的个人想法,谈论社会问题、工作状况、未来愿景等。相比于当时大部分底层女性对于是否参加工会抱有犹豫的态度,以丈夫的意见取代自己的想法:“我丈夫不想让我去,并非因为他自己不是工会成员,而是他觉得女人对这种事没有什么发言权,他觉得没必要。”而弗罗伦丝对于自己所做的工作不论多么艰辛,始终都在坚持:“如果像我这样的人不去努力,那是因为他们只看到了不公和肮脏,看到了这个国家的堕落,并且随之沉沦。但是肮脏的土壤里会长出新的东西——新的工作制度,新的人,新的活法,还有新的爱……”语言上的性别差异,归根结底是男女在阶级地位、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不同造成的。以弗罗伦丝为代表的女性群体看到了社会不平等现状,积极为女性奔走,是对社会女性固有刻板印象进行批判和抵抗的一种文化类型。
由此可见,女性亚文化风格的形成绝非空穴来风,而是它对现有的物品、服饰、音乐、语言等文化符号进行拼贴、挪用后所形成的新意义。正如迪克·赫伯迪格在其《亚文化:风格的意义》一书中指出的那样,亚文化“抵抗”所采取的不是激烈和极端的方式,而是较为温和的“协商”方式,最后都无法摆脱被收编的命运。从对抗到缓和,从抵抗到收编,这样的过程构成了每一个接踵而来的亚文化的周期。亚文化被整合到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秩序中去主要靠两种途径。第一种途径是通过“亚文化符号(服饰、音乐等)转化为大量生产的物品”的商品形式来实现整合;第二种途径则是由“统治集团(如警察、媒介、司法系统)对越轨行为进行‘贴标签’和重新界定”,从而实现意识形态的整合过程。女性亚文化风格在主流文化的收编过程中以新的形式保留下来,使得第二次女性主义政治运动最初以亚文化形式出现,到后来这种文化价值观则被主文化认同和吸纳。
四、结语
萨拉·沃特斯作为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出现的“新维多利亚小说”的一员,她将历史与虚构、真实与想象糅合在一起,呈现维多利亚文学史中被边缘化的女性,比如女同性恋者、女囚犯、女欺诈犯、女变装演员等。她以其当代女性知识分子的视角对维多利亚时代的历史进行了重构,改写或颠覆了那个时代女性呈现出来的娇弱、拘谨、压抑的刻板形象,试图消解由男性话语所主宰的历史“真相”。
然而,受维多利亚时代大环境的影响,女性生存空间毕竟有限,社会主流文化对于女性自我身份的建构依旧是以男性为标准。“定义和区分女人的参照物是男人,而定义和区分男人的参照物却不是女人。她是附属的人,是同主要者相对立的次要者。他是主体,是绝对,而她则是他者。”就此意义而言,沃特斯在其“维多利亚三部曲”的结局中明示道:虽然女性觉醒之后努力冲破其身份禁锢和阶级固化,但最终还是被安排到边缘化的地位。《轻舔丝绒》中南希和弗罗伦丝只能在工人阶级女同性恋群体内部得到认同;《灵契》中多丝和薇格离开伦敦,远走他乡,而拜尔只能投入滚滚的泰晤士河结束自己的生命;《指匠轻挑》中苏珊和莫德远离尘世,隐居荆棘山庄。所有这些,无不带有女性逃离的意味,这当然可以看作既是维多利亚时代处于边缘的女性群体在追求自我的残酷现实之间所做的妥协,也是作者在现代和历史之间所做的平衡。如此一来,女性亚文化在不断融入社会主流文化的过程中必然要受到重重阻隔。正如斯图亚特·霍尔对女性主义介入文化研究所抱持的敌视态度:“它就像一个贼在夜晚破门而入,扰乱安宁,制造了不适宜的噪音,伺机在文化研究的桌上胡闹。”不容忽视的是,女性亚文化在社会生活发挥的积极和消极作用也是一体两面的存在,是解构和适应男性主流文化的一把双刃剑。毕竟,在一个动态和变迁的社会中,主流文化与亚文化之间随时都有可能会相互转化。女性亚文化是人类社会文化结构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与处于社会主导地位的文化形态共存于同一个文化体系中。主流文化是对整个社会价值系统的集聚,因而也对女性亚文化因素加以吸纳。女性亚文化在保持了自身特殊性的基础上,又补充了主流文化的建构。女性亚文化研究对于父权制主宰的文化研究具有较强的补充性和深刻的启发意义。研究女性亚文化的发展,正是为了能更加关注当代女性群体的生活状态,更加关注女性亚文化对主流文化的补充及影响。维多利亚时代女性亚文化处在被男权社会审查、监视的位置,女性冲破牢笼的行为,彰显了女性在传统道德与现代文明相互交织过程中对亚文化的抵制和反抗风格,这无疑是维多利亚女性开始向现代女性转变的一种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