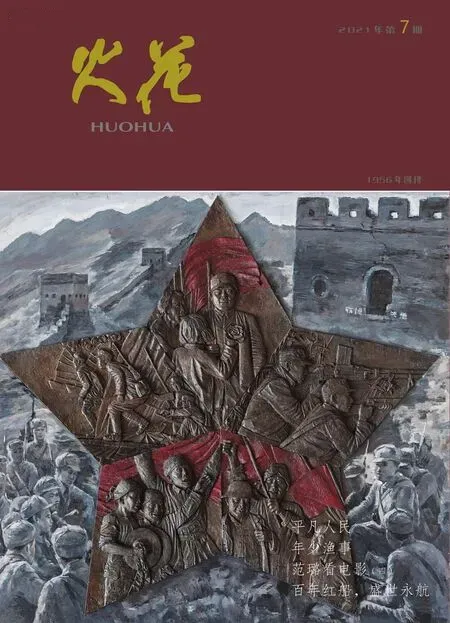史与诗的交响
——评田耘《石家庄长歌》
宋菲
网上曾经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在全国的省会城市中,石家庄是最没有存在感的。“石家庄是一座火车拉来的年轻城市”,这是坊间(甚至主流媒体上)广泛流传的说法,甚至很多石家庄的老百姓对自己所在的城市也多有“抱怨”:“石家庄土气”,“石家庄没历史,没文化”。而田耘用她的诗向我们呈现了一座有历史、有文化,蕴含着燕赵精神与人情温度的城市。
一
大家都知道,河南有殷墟、朝歌,却不知道今石家庄平山、灵寿地区是大名鼎鼎的殷商王朝发祥地说法之一【参见政协石家庄市委员会编:《石家庄历史文化精华》,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7年版,第326页】;大家都知道,正定是一座千年古城,却不知道东垣(今石家庄长安区东古城)、正定、石家庄同祖同根,实为一体;大家都知道,第十一届亚运会艺术节开幕式上有常山战鼓,却不知道常山战鼓与史籍记载两次亲临东垣的汉高祖刘邦有关,他两次亲临东垣平叛,得胜后命令手下擂响了常山战鼓;大家都知道,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有2008个充满动感色彩的“缶”,却不知道这些“缶”全部产自石家庄藁城;大家都知道,藁城有藁城宫灯,却不知道藁城宫灯起源于光武帝刘秀,他与真定王刘杨的外甥女——藁城郭圣通联姻,盛大的婚礼就在挂满藁城宫灯的真定王宫(今石家庄长安区东古城)中举行;大家都知道,石家庄之所以在近现代成为华北重镇,必须要感谢一条铁路——正太铁路,却不知道为什么正太铁路的起点并不是正定,而是石家庄……
作为一名石家庄的青年诗人,田耘做了大量的资料爬梳和实地考察,她以诗的艺术形式,用富有情感的语言描摹了跨度达三十万年的石家庄历史。她把时间定格在了一个个历史关键点上,把全书分为“起”“承”“转”“合”四个部分。“起”主要追溯了石家庄地域的古代文明,从三十万年前井陉地区的人类先祖、藁城台西商代遗址、东垣古城跨越多个朝代的发展、古中山国的文明遗迹、滹沱河对周边地区母亲般的孕育到对赵佗、刘邦、刘秀等历史人物有关“石家庄故事”的追忆,让一个有着历史延续、文明传承的石家庄走进了读者的视野。“承”主要对解放战争前石家庄近现代史上发生的重要事件和人物进行了描写和记述:正太铁路(石太铁路)的修建及对石家庄产生的重大影响,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家吴禄贞在石家庄策动反清起义失败遇害于此,老石家庄地标建筑———解放纪念碑及高克谦烈士的事迹,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和太行山人民的抗战事迹,国际友人白求恩对燕赵大地的情义,聂荣臻元帅救助日本女孩美穗子的国际主义精神。“转”则是对石家庄解放战争时期重要事件的追忆,其中,不少为石家庄解放做出过重要贡献乃至献出生命、但一直鲜为人知的英雄们在诗中得以披露。“合”则落脚于建国后老“庄”里人抹不去的记忆:华北制药、环宇电视机厂、棉一到棉七、中和轩饭庄、36524超市等等。如果说前三部分由于时间久远,今天的读者们只能通过田耘的诗以遐想的方式去再现历史,最后一部分则一下拉近了读者特别是“庄”里人与诗的亲切感,一座城市跨越几千年甚至几十万年的长幅乐章以诗歌特有的律动跃然纸上。
把一座城市的历史用诗的形式展现出来,是需要坚实的史料支撑和诗歌创作功力的。田耘长期践行着现实题材诗歌的创作,为创作《石家庄长歌》她查阅了大量历史资料,成为博物馆、图书馆及各类资料馆的常客,并实地走访了可以捕捉到痕迹的古迹、厂房、街道……用她自己的话说,“石家庄附体”成为一个时期田耘创作生活的真实写照。而支撑她这样做的原因则是对石家庄这座生养她的城市的热爱和作为一名诗人所受到的情感驱使。
二
田耘曾多次谈到她创作《石家庄长歌》的动机,是想让石家庄人认识、熟悉并爱上自己的城市;想让更多的人了解、喜欢上石家庄这座存在感很低的省会城市;想要增添石家庄地域的文化色彩,传播这片土地鲜为人知的人和事,唤醒乃至激荡起一座城市的人文精神。
而这样的创作目的,建立在一位诗人的责任感和强烈的情感之上。对历史、对城市记忆的执着追求与强烈情感的迸发造就了我们今天看到的这部诗集,田耘用诗歌的形式去展现一个城市的超长时段发展,具有积极的探索意义和价值。
“史诗”或“诗史”在文学发展史上均有特定的指向对象,前者诞生在人类文学的早期阶段,一般指以民间传说或英雄故事为主要内容的长篇叙事诗,可以分为创世史诗和英雄史诗;后者可以泛指中国诗歌发展过程中那些能反映某一时期重大社会历史事件的诗歌,也特指杜甫的反映社会现实的诗歌创作。所以诗歌与历史的结合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但无论是中国古代诗歌,还是现当代诗坛,抒情短诗一直占据主流,长篇叙事诗一直不是中国诗歌创作的主导。我认为《石家庄长歌》将这二者做了融合,它既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史诗或诗史,也不同于一般的抒情诗,作者尝试用组诗的形式,选取了地域范围内重要的历史人物,截取了不同历史时期重要的历史事件,对这些历史片段进行了蒙太奇式的剪辑。在叙事过程中,我们能明显地感受到作者澎湃情感的支撑,当创作对象(材料)与创作情感兼具时,创作也就成为水到渠成的事了。田耘的诗歌在历史史实与诗歌艺术之间形成了一种张力。
她为我们展示了一个隐忍的刘秀:“那个低三下四表示效忠,请求持节/巡行河北的西汉宗室后裔、粮商刘秀/在草包刘玄面前,隐藏了内心/熊熊燃烧的火焰。星夜兼程北渡黄河/是为亡兄复仇,更是为了自保”(《石家庄汉朝那些事 刘秀篇》);
她让我们闻到了井陉古驿道上秦始皇腐尸的味道:“秦皇尸车上,鲍鱼和腐尸的味道还在/秘不发丧的赵高,将大秦帝国/由顶点推向深渊的那团阴云还在”(《在井陉口》);
她让我们对安史之乱中那座血流成河的正定城感同身受:“白麻纸本上流淌的,不是268个字/是炙热的泪,是一泻千里的岩浆/没有笔,没有墨,唯有一腔悲愤/如熔金出冶,遍地流走/一篇反复涂改34字,奋笔疾书的祭文/在台北故宫博物院,竟成了/万人膜拜的“天下第二行书”/就让‘祭侄文稿’中,颜真卿/墨迹未干的千年悲愤,复原那个/内缺粮草、外无援军的真定城/复原史思明屠刀下横尸塞路、/血流成河的真定城中,几百颗/宁肯被砍,也绝不低下的头颅/复原未及成为国之栋梁,便已/身首分离的侄儿颜季明/复原安禄山手中那条冒着热气的舌头、/舌尖上颜真卿兄弟颜杲卿仍未止歇的/‘叛国造反,涂炭黎民’的骂声/复原颜杲卿幼孙颜诞、侄儿颜诩、/幼子颜询、长史袁履谦散落一地的手足、/割下的肉、刮净的骨头”(《真定,真定》);
她这样解读卢沟桥事变:“半钩留照三秋淡,一练分波平镜明/一座桥闻名于世,不是因为/永定河上燕京八景的‘卢沟晓月’/而是因为一名‘失踪’的士兵/志村菊次郎,因为1937年7月8日/凌晨五点,那蓄谋已久的炮声/北方最大的石桥上,被迫与/一群举枪狂笑的日军合影的/485个怒目圆睁的石狮子/眼里喷射出的,是血与火”(《在太行山上》);
她这样入木三分地刻画一个机智勇敢的地下党员:“‘殷志杰’进入石门法院街4号军统/虎口拔牙的方式/是沿着一条线顺藤摸瓜/收买机械零件的天津人刘文贵、/大兴纱厂机修车间主任张志华、/华北饭庄的一场饭局、保证书/是这条线上的点/对付背上的芒刺、藏在暗处的/无数双眼睛的最好方式/是在殷志杰的角色设定里/再随机加上无数场好戏/是成为最佳男主角、最佳导演、/最佳编剧,殷明飞婶子的葬礼上/那个身穿重孝、痛哭流涕/守灵7天的侄儿,谁能想到/他此时修炼的不是‘悲伤课’/而是‘一个演员的自我修养’”(《石门情报站》)。
三
历史和地方志是相对客观、冰冷的,然而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却能够让逝去的历史和人物重新鲜活、丰满起来,可以填补冰冷的历史书和简单的历史数据留下的大量空白,用文学的形式更好地去记录、传承历史。《史记》被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是对其史学价值和文学价值的双重肯定,《史记》中项羽和虞姬的对话不可能为第三个人所知,更难以为近一百年后的司马迁所知,但没人为此去否定《史记》的价值。文学的真实更大程度上是一种情感的真实,即符合历史、生活逻辑,得到了读者的情感认同。田耘的《石家庄长歌》做出的探索,是值得肯定和鼓励的。在田耘看来,用诗歌的方式挽留那些已经逝去和行将逝去的人、事、物,正是文学存在的价值与意义。她让我们这些21世纪的现代人重新触摸到历史的纹路,她穿梭于历史人物和事件中,却未被纷繁复杂的历史细节所淹没,从而丧失自己的声音,并力图保留诗歌的意境与意蕴。
田耘说:“诗歌像血液一样在我体内流淌,我的生命因为诗歌充满温暖和无限可能”。田耘从不否认自己对“宏大叙事”的执着,她在用诗歌写史的道路上,也曾遇到过质疑的声音——“写历史干什么?诗歌就应该写你自己,写你熟悉的东西。”确实,用诗歌写史并非易事,除了搜集整理史料的困难,还有表达上从何处下手的困难,以及如何让已经远去的历史引起读者强烈共鸣的困难。《石家庄长歌》的出版发行,让田耘的尝试有了实实在在的成果,也许它还有这样或那样的不足(如一些史实细节还有待考证),却值得我们有更进一步的期待。据悉,田耘另一部用现代诗形式书写党史的作品——《红色史诗》也即将问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