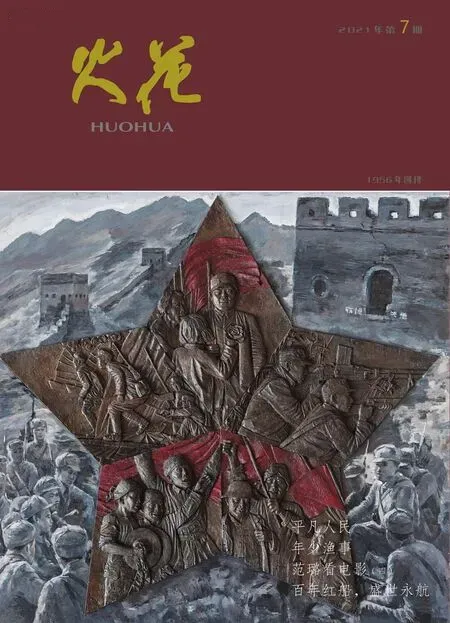迷迷糊糊的童年
苏斌
我拥有一个非常幸福的童年。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社会的朴素,从没影响我获得一个色彩斑斓的纯真童年。在那个“拨乱反正”“百业待兴”的年代,我也真切地见证了国家物质逐渐丰富,见证了家庭温暖的亲情,见证了指向我的挚爱的向心力,见证了孩童时代那些我至今难忘的历历往事。
懵懂
幸福源自出生。从小,街坊邻居都用不同调式的各地山西方言说我“生在福圪洞里了”。我是家里的男孩儿,出生时虽然父母年龄都年轻,但祖辈四人已经都非常年长了。在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的带领下,大家对我格外偏爱,所以经常还能吃到“偏饭”。比方说,小的时候,过年时,压岁钱慢慢从“毛票儿”涨到了“拖拉机”(第三套人民币的一元钱正面图案)。我却常常是在公开拿到一张拖拉机以后,长辈们再悄悄把我叫到一个较为僻静的所在,再悄悄多给一张,并嘱咐我万万不可让除了爸妈以外的他人知道。
从小的生活中,各种偏饭经常有,即使读书认字的时候,也吃到了不少“偏饭”。我们排上的乔二哥可以算是我的第一个语文老师了。在我四岁之前,便系统地教了我全部汉语拼音,也把他们的课文只言片语地“传授”给我。现在还清楚记得,“我爱北京天安门”是我接触比较早的“课文”。大人们轮流担任着我的“常识”老师,零打碎敲地教着我各种知识。爷爷主要负责我的“思想品德”,很小,他便拿着书给我讲雷锋、焦裕禄的故事,教我一定做一个好人。
此外,还有很多比我大几岁的“小老师”给我上图画课。我从小就喜欢拿着石笔在邻居家门前的水泥地上画各种我能知道的东西,花花草草是我经常描绘的对象,我对各种动物也非常有兴趣,不过我更喜欢拿着带图的书,把各种动物“嫁接”。现在想起来,我在小时候就如此有创新的头脑,常思极喜!在我的妙笔下,不是生花,却比生花更有意思。时而把猴子的脑袋画在长颈鹿脖子上,猪的身上又长出一个熊猫的脑袋……其实,我最喜欢画的还是那一年级语文课本上的庄严的天安门城楼,百画不厌,尤其是能够奢侈地用彩色粉笔的时候。
在那个马路上并不多见汽车的年代,我还经常画出救护车的样子,或许因为比较容易画且有特点。方方正正车厢前面一个车灯,后门一个排气筒,下面是轮胎,上面带着顶灯。每每画完,我总对我的画作加以欣赏,暗自叫好。小时候,我经常在邻居乔大爷家玩,所以,题画地点也经常就在他家门前平坦光滑的、新抹的水泥地面上。看着新鲜出炉的画作,我对他说:“乔大爷,等你老了,要去医院,你就坐这辆车去吧。”大人们哈哈地乐得合不拢嘴。现实中,2000年前后,乔大爷患了癌症,我得到消息时,他已经多日不能吃东西了。我买了很多罐头去做最后的探望,再想起小时候“坐救护车”的呀呀往事,想起老人家对我的种种的好,我失声痛哭,说不出话。
说起我受到正统的教育,爷爷功不可没。家里,爷爷和爸爸文化都不能算高。尤其爷爷从小就没有上过学。他说,小时候也想上学呀,没有钱没办法!他小时候在地主家干活,也曾偷偷听过人家背诗,解放以后,通过“扫盲班”的教育,学会了一些基本常用字,写字不一定能准确,但已经可以独立整篇地读报纸,用毛笔做工整的书写。爸爸“生在红旗下,长在新中国”,初中没有结束,便因那场浩劫而终结了在校学习。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吹暖了神州,全国百废待举。工厂趋于正常,学校恢复教学。大人们也急着把我送到学校去,好像他们不只是为了让我适龄上学,似乎更是为了在一个新的生命的起跑线上点燃新的希望。
上学
通常,小学入学以生日在上半年和下半年作为分水岭。我出生在十一月,属于下半年。为了能够让我顺利通过学校招生,乔二哥请来了他的张老师。了解情况后,简单对我进行了测试,张老师非常满意。就这样,我便毫无悬念地在不到六周岁时,成为一名一年级的小学新生。
——上一年级第一天,爸妈用一分钱在学校门口给我买了一大枝“醋溜溜”。那是绿色天然的美味!我边走边吃,到教室门口时,原本非常宽裕的时间不够了。为了不迟到,我放下所有斯文,快速吃着,即便沙棘的刺把嘴刺破。直到打铃上课的最后一秒钟,我还是忍痛把剩下没有吃完的一多半扔到了教室后面的教室与学校围墙隔起来的狭长的“一线天”。可想那时候的一分钱是多么有价值!
——学校门口,胡校长的老伴推的冰糕车是当时的一个鲜活“地标”。胡校长的老伴,也是我们同班同学胡彩虹的奶奶。在我们学校曾经上学,以及住在我们那条小街的人,时至今日都很难忘却胡奶奶那慈祥可亲的面庞。放学后,她经常喊住我,揭开四四方方的木头盖子,撩开厚厚的白色棉被,拿出一根价值五分钱、学校冰糕房自产的冰糕,递到我手里,说:“你爷爷刚才来过,他给你买了一根冰糕,让我看到你下了学给你。”
——学校里,课间是我们最快乐的时光。现在孩子们可能都很难想象那些丰富多样的游戏:用削铅笔刀在湿润的土地上“掠夺”土地,是“栽刀刀”的游戏;同学们弯腰抱紧前面同学连成串,有同学助跑以后尽可能向前骑到同学背上,叫“骑驴”;搬起来一只脚,另一只脚“金鸡独立”和同学弹跳抗衡,唤之曰“撞拐拐”;拿发黄掉落的杨树叶强壮的叶柄相互拉拽,比试拉而不断者,是我比较喜欢的“杠树叶”游戏。其实我最喜欢的户外游戏,当属“打木杆”,用木板击打两头尖的小木块,待木块腾空后,向外用力击打,看谁打得远,这一危险项目被列为学校的“恐怖袭击”项目,因此在被禁止的情况下,只能是偷偷地玩,不宜公开玩之。学校经常会爆出平房教室玻璃被击碎、木杆飞出伤人等“重磅”消息,以此,再次鸣响学校安全之“警钟”。
——伴随杠树叶游戏的开始,也到了学校全民“打煤糕”的时节。老师要求同学们每人带必要的工具,学生或自行商议、或由老师统筹安排,不约而同地从家里带来了一尺长二寸厚的长方形“模子”和大小不等的“泥抹子”。高低年级齐上阵,关系好的抬水,臂力大的和泥。逐渐,学校的房前屋后,凡是空荡之处,均被黑色“方饼”所占据,好不壮观。
——四年级时,胆子和个子一起长大。在更胆大的同学带领下,我参加了一次绝密的“冒险行动”。当时的学校给教职员工占用学校操场盖的宿舍楼开工了。施工队挖地基,挖到一个“神秘洞口”。有年长者说,这是一个防空洞的入口,这防空洞是当年“备战备荒”时的“暗道”,四通八达,连网成片,向西而南转可通迎泽大街,另一侧却直上东山。记不得这个下着绵绵小雨的下午为什么不上学了,同学们叽叽喳喳地嚷着,要去防空洞看个究竟。那时候,手电筒作为家庭的大件电器,基本都保管在家里的“户主”手中。怎么办?东拼西凑找到了木柴、破笤帚,甚至还有自行车报废的内胎。拿着火柴,同学们十几人依次排队“下潜”,前面第一人负责点燃“火把”照亮,后面则一个拉着一个的衣角。我在后面,基本是看不到东西的,听到的只是前面同学的话语声。即使我们的个头儿都不高,我的头上还常触到防空洞的拱顶,左右偶尔擦到长长通道潮湿的墙。确实能感觉到,防空洞里是黑暗、阴冷、潮湿,通道是低矮、狭窄的。走了很长时间,前边同学说,“看到了,向右有一个小道。”我们感觉猫腰走了很长时间了,并极力劝说前边同学不要冒险走岔道。也因为燃料不足,我们后队变前队,往回走。慢慢的,前方出现了隐隐约约的亮,随后才能准确感知到那是“光”,呼吸也变得畅快起来,终于回到了出发的“原点”。仿佛“洞口”的人比刚才增多?坏了!我妈怎么也来了?
回到家,一场“批斗”迎接着我的光荣“凯旋”。
烟火
学校和家离得很近。从家走到学校,大概也就不到二百米远,溜溜达达也就三两分钟。从学校到家,顺着一条窄的土路,沿着我们大院的土围墙,拐个弯就到。从我小时候记事起,就每天出入于这青砖盖成的、住了二三十年的平房里。排房整齐,明显是有规划工程建设的结果。虽然日子好起来以后,有的人家把门窗用油漆重新刷过,但也还是木扇玻璃窗,外面刷成枣红色,里面刷成乳白色;墙围子基本是用油漆刷过的浅绿或乳白;家家都是整齐划一的青砖拼成的地面,后来有人用水泥抹一层,这样,原本只需要用笤帚扫,变成了可以用墩布擦,但老人们还改不了经常用水泼在地上的习惯,以增加室内的湿度;顶棚是用芦苇杆编结,麻纸裱糊而成。门户看着整齐划一,住户也都是同一工厂的职工家属,家家户户之间总有着千丝万缕的革命友情、兄弟感情,或存在着一些说不清的磕磕绊绊。生活之美也许就产生于这“锅碗瓢勺进行曲”当中。
小的时候,回到家,总能看到爷爷在厨房炒菜,总是炒着“亘古不变”的主菜——清炒白菜。厨房光线并不充足,水缸旁的案板上,白菜还是那种规规矩矩的长条状,按照爷爷的习惯,总在热油里面放一些花椒和葱花,咸盐、酱油、味精。还是这些配料,味道也还是那传统的炒白菜。自盖的厨房,顶子比较高,随着白菜投入油锅吱吱的声音陪伴下,蓝色的油烟升腾,在厨房宽敞空间的上三分之一的地方,缕缕交织,织出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美好的生活图景。
我出生,基本伴随着“浩劫”结束,紧接着拨乱反正,开启了经济建设的大幕。换言之,我出生后,国家经济从恢复到发展,从起步到腾飞,这也改变着家里的生活水平。虽然,我小的时候,父母每月人均工资只有二三十元,但逐渐市场供应趋于充足,生活水平得到了根本的改善。
生活的日常不仅是土豆和白菜,我们家,也包括当时走上温饱之路的左邻右舍,也开始各显神通,托到各种关系给家里置办一些原来离了票证买不到的东西。
1979年,家里买了12英寸的春笋牌黑白电视机;1983年,还买了电唱机;1985年,搬回了20英寸的“大”彩电;1987年,家里第一次添置了一台双开门电冰箱;1988年,双缸洗衣机落户我家厨房。生活发生着“越千年”的巨变。邻居们,家家户户也开始都能在过年的时候买一扇子猪肉,炸丸子、做烧肉;洗头不再用碱面了,还会在头上抹上头油;过年的衣服色调也开始丰富,大家笑容多起来……
小时候,我就没有挨过饿,家人总是给我花样繁多的各种饮食。为了提高厨艺,父亲赶着潮流买了一本《太原饭菜》,研究着过油肉的标准做法。听说用香精、甜味剂加水可以自制汽水,父母不辞劳苦,赶到桥头街买原料,回家试制。
这天,丸子汤刚刚出锅,我闻味儿溜进厨房,趁人不注意,揭开锅盖,水汽升腾,眼前一时看不到东西,掀锅盖的右胳膊突然一疼。哎呀!稚嫩的胳膊上,起了一大片的水泡,大人们手忙脚乱从邻居家借来治烫伤的獾油。不过,胳膊上还是不可避免地褪掉一层皮,疼了好多天。当时的记忆,就作为父母偏爱我的一个见证吧。
当年,我爸在单位是卡车司机,经常外出跑车。那时的司机家庭是很多人所羡慕的。凡是我爸出车跑长途,总有人登门托他捎各种东西。现在人们基本没有了这种想法,不会有人想着让人捎点什么东西,更不会有人主动提出我要去某地,是否谁需要帮助。父亲除了从各处买回“京广杂货”,更少不了买回“南北特产”。从小,我见识着缤纷世界的种种,还品尝着同学们难以见到、甚至很难想到的美味。
又一个寒假的到来,又一次春节盛宴开启。家家户户为着过年而奔忙,这家买了整扇猪肉,那户研究着烧肉丸子的制作方法。大年三十上午,人们开始擦玻璃,挂灯笼,小小灯泡隔着皱纹纸制作的灯笼,显得并不明亮,但节日气氛足够。除夕的下午,我总帮着家人和邻居揭下来褪色的旧对联,用笤帚扫干净后,用自家白面熬好的浆糊,把从市场上买来的春联贴上。过年了,又可以穿新衣服了。
我穿上新衣服,踏上新鞋,伴着春晚的节奏,先到前院的毛叔叔家走个秀。这个项目保留多年,一直到我结婚以后,只要工作不忙,不在单位值守,我便总要去毛叔叔家打个前站。
那个年月,鞭炮是不可或缺的。大人们放着双响炮和大鞭小鞭,记载着又一个年头的开启。除了大人们买了魔术弹、胜利花以外,我们还偶尔大胆地拿着过年“赚”来的压岁钱光顾商店、小卖部,擅自做主去花九分钱买一挂一百头的浏阳鞭炮,回家拆开炮捻,一个一个放。爸妈也会给我买各式花炮,吸引我更多的,并不是它会将烟花向上窜起,还是喷薄火焰,或旋转腾飞,抑或燃放后吹出一个彩色气球,而是花炮绘制的孙悟空、小动物等活灵活现的可爱的图案。
除夕到初五,除了给长辈拜年,吃各式美味,每天走街串户联系同学必不可少。炮还在放着,我也和同学们一道研究着。我们从地下捡着残留的花炮,或找到炮捻再次点燃,或把那些无法下手点燃的炮集中在一起,把撕开的花炮外皮一层一层裹着的纸展开,作为火堆的燃烧物,将各种火药集中在一起点。此时,各种炮的响声、火药球的升腾、各个方向的爆燃,伴随着蓝烟升腾,交织在一起……
那个斑斓的年代,烟花绽放的烟火气和万户千家的炊烟此起彼伏,成为独具特色且难以复刻的时代印记。
庭院
春天就在我们这帮不知疲倦的孩子点出的鞭炮声中到来。这个大庭院里,点点绿色把气温缓缓抬高,孩子们厚厚的衣服慢慢减去,天气在南风的眷顾下渐渐变暖。同学们吵吵着看谁家有退役的竹门帘,纷纷找来做风筝骨架;有同学“捐”出了家里的旧报纸;小同学在高年级同学带动下有模有样地做起了裁剪,因为他们并不知道什么比例是合理的,怎么样才能使风筝平衡。现在看着各式图案、色彩丰富、南天高挂的纸鸢,却还能想起小时候那种流行的、如同当年人们穿着那么整齐划一风格的、四方头、拖着两溜报纸裁条拼接而成的“黑白”风筝。我们从不顾忌脚下窑洞里住着人们给我们的再三警告,到前院南门外的窑洞平顶上,显得如此宽阔。我们舒展地去助跑,使风筝晃晃悠悠、一颠一颠地点着头升空。春天的下午,放学后,这就成为一种常态化的活动。这种节奏每天也就在大人们下班回家后结束。孩子们的家长不是怕给人把窑洞踩坏,他们担心的是如果不小心失足从窑洞顶上掉下去,掉进人家院子。并不是怕砸到人家的“花花草草”,而是有失去性命的危险。所以,到下午六点多,孩子们多数就又自觉地回到了“大杂院”。生活在宿舍南边窑洞的人们终于可以放心地端起碗来,稳稳当当地吃饭了。这时候,一定不会有淘气的孩子用土坷垃和石子骚扰院落。此时,大院排房里的爷爷奶奶、叔叔阿姨可就开始闹心了。回到院里的孩子们开始了自己团队的快速组建。
———有人组织了“游击队”,开始绕着排房跑。规规矩矩的十几排房子被一条平展的土路等分为东西两片,一排排房子等距排布,且互通互联。在排房之间,家家户户盖了厨房,厨房随着排房也是平行着连成一线,这之间的通道就显得狭窄。回到家的“上班族”们开始忙着做饭,效率高的人已经开始支起小方木桌,一家人坐在自己制作的矮矮的小木凳子上围坐一起吃饭。本来就比较紧张的过道上,像走马灯似地一遍又一遍地出现着我们这群小“土匪”,着实让大人们眼花缭乱。有心情不好者,便会对我们大声呵斥,不准再次通过。由此,大家保持“游击”本色,迅速传递“路况”信息,重新规划好比较通畅的、或者大家都还比较“合作”的通道游荡。
——女孩们非常喜欢的项目当属“跳皮筋”。一般都会在自家排房,两个小朋友一边一个,“架”起皮筋,嘴里念叨着“学习李向阳,坚决不投降……”悠然着又蹦又跳……
——“踢钵钵”,貌似女孩儿的项目,其实也是我们男孩子喜欢的活动。一个“钵钵”,地地道道的太原话,听着非常亲切,让我顿时就能想起了一句古文“吾欲之南海,吾一瓶一钵足矣”。用粉笔在地上画几个方框,有进口,有出口,方框编号,把空鞋油或者雪花膏“钵钵”扔到地上,单腿踢之,按编号依次踢到下一个框内。就这样,格子里面荡漾着乐趣无限。
——捉迷藏,这是全球通用项目。在太原,吾辈谓之曰“藏门门”。月上枝头,天色渐暗,小朋友不分男女,不论长幼,参加到了这个群众性活动中来。一人掩目面壁,按照约定数多少个数,数字念完后,开始四处寻找到处藏匿的小伙伴,如被找到,喊“逮住”;躲起来的小伙伴趁着黑,悄悄潜回面壁处摸墙,大喊一声“电报”,则完胜。那时候,的确有趣,趣不在当时活动单调,更在于当时大家生活在非立体的、比较平面的所在,不需要高处,只需那平房高度内便妙趣横生。藏在大树后的孩子屏住呼吸,偷偷张望;躲在煤糕垛子后面的娃娃探头探脑,心乱如麻;溜进人家平房旁边自盖杂物棚子的人,生怕即将胜利的自己被里面老鼠咬了;胆大的孩子竟然径直溜进了漆黑的邻家厨房,心里乐开花,结果经常会被进到厨房并吓得心跳加速的主人大骂出场,让面壁的伙伴抓个正着。多少年,想到当时的游戏场景,还经常自己傻笑一下。的确,童年回忆纯真无邪。
——我们还经历了两个“水枪”时代。现在可以看见孩子们用的是冲锋式带储罐的水枪,很是豪华。在我小的时候,还没有现在的自压水枪。那时候,中国已经成为首屈一指的自行车王国,家家户户必有的大件当属自行车,飞鸽、永久、凤凰、红旗……这些品牌是那个时代挥之不去的记忆。有自行车,当然就有内外轮胎,有“里带”,一定有一个给这内胎打气的气门嘴,气门嘴上有一节短短的气门芯,原理就是使通过气门芯的压缩空气进入内胎后箍紧进气口避免撒气。本来是用于修理自行车的配件,却成了我们大家伙儿的玩具:把气门芯一端栓个疙瘩,用手夹紧另一端,把手使劲捂在院里的大水管子上,气门芯在水压的冲击下,水慢慢注入。待一根气门芯被水“撑”大变粗后,用手掐住端口。拿在手上,我们兴冲冲的,好像在手臂上搭着一条温顺的小蛇。走着走着,突然发现可以戏弄的“目标”,便对准对方,轻轻松开小口,水便在气门芯的收缩力下喷发而出。当年输液用的胶皮管,成为我们手中的巨型武器,搭在胳膊上好似巨蟒。这就成为了原始的“水枪”,我们爱不释手的“玩具”。时间转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手枪款的塑料水枪成功在集贸市场上市,当时两元的价格的确不菲,考虑到还是符合“军火”行情的,第一支“真家伙”入手。
和现在的孩子相比,我们真是幸福许多。虽说不曾见到“池塘边的榕树”,但知了的确声声叫着夏天。天热了,除了传统项目,我们还经常在邻家的煤堆、土堆上看月亮,数星星。小时候的天是那么低,星星又多又亮,真是在和我们眨眼睛。我经常用手电筒聚了光,照向星星,偶尔也按手电筒上那个绿色的塑料键,给星星发出频闪的光。我想,那颗星星上的人一定会看到我发出的光,兴许,还会给我同样的回应。
晚上,煤堆上的孩子们在谈天说地。孩子们发现,旁边有一堆一堆的东西,借着小伙伴划着火柴微弱的亮光,看到了,这些好像是张爷爷捡来的片材、油毡和纸片。有人提议取之以为燃料,可以搞一个“篝火晚会”。好主意!火宜虚,以木柴为框架,盖以油毡纸片,内以报纸为芯,篝火迅速燃起。随后,我们被去旁边厕所方便的张爷爷的儿子发现。再然后,被追捕扭送,送回家里,面对家长的暴风骤雨不可避免。
随着柳絮横行的日子结束,大院里办喜事的多了起来。遇上家里条件好的,会到距离大院相对近一些、但也有二里地外的沙河饭店吃一顿,那叫“风光”!当时,绝大多数人的喜宴也有着另外一种特色。大人们说,玉生叔叔要结婚了。一天,院里的一个开阔处搭起了棚子,一群人上阵,一头猪在挣扎和哀嚎中还是被杀掉。随后,放血,用打气筒给猪打气,再扔进热水中洗净、褪毛……排房中开始喧闹起来。当天,典礼仪式上介绍人讲话,小两口介绍恋爱经过,主婚人、证婚人致辞;一直到晚上,喝高了的亲戚朋友出节目、闹洞房,搞得连看热闹的人都羞红了脸,这些传统项目,现在已经基本看不到了。除此之外,最有气氛的便是办喜事人家隔壁很多间房子被借用,集中借来很多张桌椅板凳,来帮忙和看热闹的亲戚、朋友、同事开始吃“席”。伴随着划拳声,喧闹的“哥俩好、六六六、五魁首……”高喊声中,一道道大菜蜂拥而至———烧肘子、小酥肉、过油肉、糖醋丸子、香酥鸡……那些鲍鱼、鱼翅和大闸蟹缺席的日子里,也绝不会看到土豆这类的产品。不是没有,而是“山药蛋”是不上席面的。这就看出了这“席”还是有讲究的。白酒当属六曲香,饮料还有“小香槟”,甜的不只是这一款,清徐产的柔丁香红葡萄酒也是不可或缺的明星。在大人们的劝说下,我喝了一杯时下流行的“甜水水”,下午不误上学。结果,我在熟睡的音乐课上,被老师“请”回了家。
我的八九岁的童年里,在身边的一些老人悄无声息走了,同学王炜的爷爷、我的奶奶……我对人的死亡有了初步的认知。我十岁那年,暑假的一个下午,宿舍里传来震天的哭声。院里的人向传出哭声的地方集中。一个小孩儿平展展地静静地躺在他家平房外间的床上,在他那已经失去了丈夫的母亲恸哭声中,儿子离他而去,他是在游泳时不幸溺亡的。曾经每天一起写作业,一起玩耍,一起偷吃家里蜂蜜瓶里沉淀的甜甜的结晶体的那个鲜活的生命就如此结束?由此,再每走过他家那排房子,我心里总有一种隐隐的痛。
就是这样,院里就像剧本一般,喜怒哀乐此起彼伏,嬉戏怒骂偶有上演。伴随我的童年,庭院里还有许许多多故事,当时记着的和不太记着的,现在还能想起来的,使劲想能记起一点针头线脑来的,还有也许永远记不起来的。发生的事,已经发生了;过去的事,也都过去了。庭院时过境迁,年轻的,变得年长了;年长的,也开始变老了;老年人,或已经去了另外世界,或他们安享晚年时更不记得那些林林总总。庭院里的人,也像走马灯一样,搬来的,替换了搬走的;北上的,换走了南迁的。生生不息!我看着这个大庭院变迁了四十年,再过四十年,这里是什么样子呢?谁也无法预测。但上百户人家在这里,悲欢离合,构成了改革开放初期的新的美好生活画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