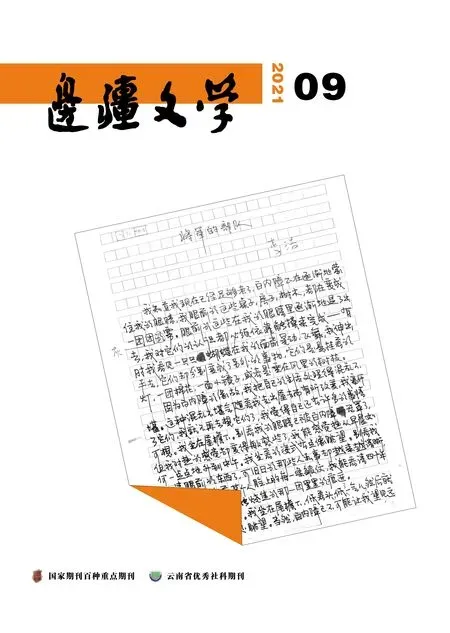大雪多么锋利 组诗
桑子
交给每一位过路的人
每一天的终结,沉重得足以流泪
涌动的黑夜,多么无望
没有任何倾听者
无知在折磨已知
谁在修补无边无际
山顶的积雪正在融化
它们将成为真理的河流
交给每一位过路的人
红蝙蝠倒挂在夜的广场
澄亮的翅膀啊,天空的兄弟
正在高处燃烧
咬破的唇鲜红,保留了纯粹
啊!每一颗星星都应该熄灭
枯草堆上我们乱蓬蓬的负担
请收下这看不见的暖洋洋
孤独困在自己的迷宫里
寂静把那夷为平地
盲目的天空不需要牺牲
大地才是永恒的十字架
侧面
光在刈草
切开的伤口凝结着旧日的露珠
楼道的侧面如同峡谷的深喉
词与词流逝,我们所看到的
并不等同于我们所理解
光预示了即将发生的事,但
谁又能真正理解
你站着的地方
谷物正大片大片生长
你并不一定能看到
光笼罩着我们
如阴影抵达自身的纵深
永不被驯服的庞然大物
那张野性的脸
总有与我们相似的面孔
它将在我们体内苏醒
俯瞰我们赤裸的身子
院墙斑驳,夏日长又宽
阴影是永远的沼泽
光的锯齿割着白花花的骨头
光线最亮处,可以穿透时间
门楣上亮出未曾到来的时日
许多年的树叶在那纷纷坠落
像告别仪式,真是好日子
阳光像河水一样长流不息
死亡是另一个新鲜的存在
这是生命最好的礼物
如一条鱼游入永恒之河
我们几乎来自另一个地方
进入空房子
光锯着光阴,来来回回
后山被钉在高处,披着铠甲
万物皆在迁徙
是时候了,溪水注入大湖
火苗蹿起
我们几乎慌乱
目睹黎明设下的陷阱
死亡的祭礼如此隆重
灰白尸身让天空变得肥沃
大墓被掘启
白雪落在棺木上
光模仿鸟的鸣啁
荡起一个个漩涡
谁在等待,一封没有地址的信
我们可以感知湖底石头的温度
和雪线之上炽烈的光芒
万物皆在迁徙,伟力犹如神迹
道路发白,光在无限拉伸
空房子在阴影处复活
浮皮潦草的一天从旧的时日中分离
年轻的恋人走在步行楼道上
光四散逃逸
火车抓住枕木,急驰在一望无尽中
光阴啊,一大片光秃秃的光和影子
我们踩着迅速下降的暮色
镜子上布满荆棘和从前的笑容
屋外是连绵的雪山和呼呼的大风声
星相家在暮色中主宰着村落的命运
技艺娴熟已达到了死而复生的境界
湖是我们仅有的孩子
从明亮处走入浓荫
洪水淹没了我们,在我们体内汹涌
使得我们借助浮力从灰暗的底部
升上来
灵魂呈现,初具形体
光不假思索的每一步
都蛰伏在令人信服的时间里
我们忧心忡忡于命运的无常
光在赦免,在寂静中闪耀
时间的仆人来回穿梭
像一首诗被反复记起
我们住在大湖的东岸
湖是我们仅有的孩子
她头顶有大片的云
云在冬天更好看,我们灰蓝的湖
是大地永恒的迁徙者
是炽热的正午与严霜的隆冬
是一场暴雨后
变得深蓝的我们的眼睛鼻子和身体
是我们的此时此刻与百倍的加速度
雪山浴雪,天空空着
时间虚构,声音存在亦不曾存在
我们害怕暗处的敌意和亮处的盛大
光从不同的角度进入
阴影是永不离开的死亡本身
是无法征服的自身和陌生人
那个小小的堡垒是灰烬安放的地方
太阳已登堂入室
窗玻璃空有敌意
在黄昏与伟大的正午之间被孤立
空房子通过一道生锈的铁门
进入屋内,杀死自己
肉体掉进肉体中,眼泪流入干涸处
藤本植物在攀援,果实累累
空房子统治着一条街、一片原野和永恒的天空
人人将一无所有,在身体里迎接风暴
这是离去的时刻
水手在舱底也在浪巅
光和影是最好的罗盘
探险者死于探险,火焰自火焰升起
我们在世界之外,在一百所空房子中间
大地抖动自己的鳞片
朝南的房间都洁净
阳光下,我们坐下
湖深蓝,天空深蓝
波光似脉搏跳动
巨兽沉睡已千年
它缄默,幻觉一样存在
太阳被厚实的皮毛击碎
阳光落下,我们上升
血液流向四面八方
流向每一株植物的根
那个茂盛的夏天,空旷的身体敞开
向万物敞开,在任何一个地方复活
我们耐心观看植物生长
与陌生人友好相处
割草机突突奔走
大地抖动自己的鳞片,蠢蠢欲动
太阳高悬,光几乎吞噬了一切
许多年许多人路过
没人会记得这一天
锯齿形的闪电在追逐
白雪的波涛卷到天边
光冲出黑夜,吞没自己
它重复着死亡重复着爱
无论在何方
我们都能看到升起的群星
天空多么贫瘠多么富饶
年轻的自由和无尽的宝藏
它从不显露,也不隐藏
空房子藏在灰色的院墙中
如我们藏在无尽的时间里
有时洪水一样涌出
四下漫散
大地上所有的流浪者
带着从前的经验
在四面八方彻底的虚空中
观看古老的星阵
追问将来会是怎样——
时间还在
中年后变得迟钝的人
细腻又枯燥
简朴的食物值得信赖
月亮从老旧的时间里发出叹息
全能的哑巴在修建房子
如一幅没有上色的图画
历史不是时间
未来不是时间
它们只是时间的问题
暮春的夜晚属于所有人
直到所有人都成为石头
时间还在,时间还没到
谈论时间如同谈论一个危险
它从没有存在过,但无所不在
谁能了解那沉默的语言
夜吞没了每一条道路,真正的无边无际
黑暗无所顾忌,朝每个人的内心崩塌去
谜和谜底,来自同一个问题
问题总是存在
一个庞大的不可捉摸在指挥我们
感受来自不可知的触摸
缓慢地、迅疾地向着寂静与喧嚣
此刻一切光都能把我们打碎
夜里的猫有独特的眼睛
我们胆怯地认识另一个自己
如当众被识破的谎言
此时此地
落日向大地深深鞠了一躬
森林浓密的毛发和浑圆的曲线
多么令人压抑
黑夜发出了拓荒者劳作的声响
一只鸟在枝头竖起羽翎
星星穿越时空来到此时此地
打更人把它们局限在人世的缺憾中
仿佛一切的命运
黑夜饱含着对事物的批判
我们无所不能又无法辨认的自身
既是开始也是结局
劳作是一种古老的象征
仍有一半的花园荒芜着
阳光深入其中
太阳总是西行,大地啊
——那里的松涛和墓地
每天交出爱与希望
有翅膀高出人世
山是人的另一副骨架
现在太阳布下浓荫
与黑夜别无二致
灵鹫教会所有眼睛可怕的平衡术
关于未来的狂想
比果实的内核更准确
深入所有人强烈的渴望中
寺庙在一条溪流和十大戒律之间
有些地方不需要抵达
无限就在此
在一张旧照片看到果实成熟
死亡多沉重
造山运动以反向的力让它变轻
无可抵达的尽头
有翅膀高出人世
松针上行走的人陷入光的沙丘
无计脱身
植物庞大的根系藏着巨大的激情
过去它们是大海和流云
现在它们是一个人的身体和灵魂
有所疾
存在,目睹自身的瓦解
怀疑是旧事物的新死亡
死亡不可避免
一次长长的交谈后
雄辩或者言简意赅
赞美找到了所有物体的沟通点
世界值得关注
梦却常欺骗我们
众人在打发时间
整个大陆在流逝
城市都那么小
一次瘟疫一次饥荒
时间承担了生与死
我们站在阳光照耀的地方
一眼能认出的事物到处是
破败疲倦的事物需要辩护
很久以前它们就成为我们
用以研究种种疾病
——世界的,我们的
蜜蜂螫起的地方长满了荆棘
它或许知道
——山河半途而废
石头带着暗红色的火
太阳给予万物强烈的暗示
全部的经验
连死亡都带着自我证明
旱季归于喜剧,树干摇晃
但无法从自己掌心逃出
枯萎仍是最大的危险
很长时间,夜吞噬了所有
一滴露水在花豹鼻尖
白鹭是一棵树一束光和一个梦
白色的羽毛忧郁而明亮
天空在大片灰烬中提及了死亡
蜜蜂螫起的地方长满了荆棘
白鹭的眼睛识得邪恶的咒文
我们跟随它进入阴沉沉的丛林
把太阳的骨灰洒在了头顶
众人有缺陷
你得保持距离来观察
酷热像一团白色火焰
熟透的杏子掉了下来
消除了四肢的疲劳
狂风在掩饰又在揭露
核心的事物藏在娇嫩的皮肤下
个体在这一刻被无限
每一枚种子都被爱过
就像众人有缺陷
坏天气带来各式消息各种企图
所有人所有的危险
数字被统计在规律之中
新人文主义要成为这样的人
它逃避时间,主要由思想构成的时间
所有的数字而不是任何数
所有的人而不是任何人
上等的风景像歌剧场景
我们集体奔走在时间的大口袋中
似一场屠杀,似一路朝圣
从不指望得到自由的人
有了片刻的不安
在空房子的迷宫里
一条陌生而寂静的路
通向小小的蜂鸟和最庞大的山系
一切,除了秩序
以广为接受的言辞
和一个恰当的主题
来到我们中间
言说“就是这么回事”
所有人的目光都朝向远处
光在永恒中行走
在阴影处我们看到夜的蝙蝠
以一道锋利的瓷片割开了
血的咽喉
所有受惊的鸟都尖叫
从破绽处发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