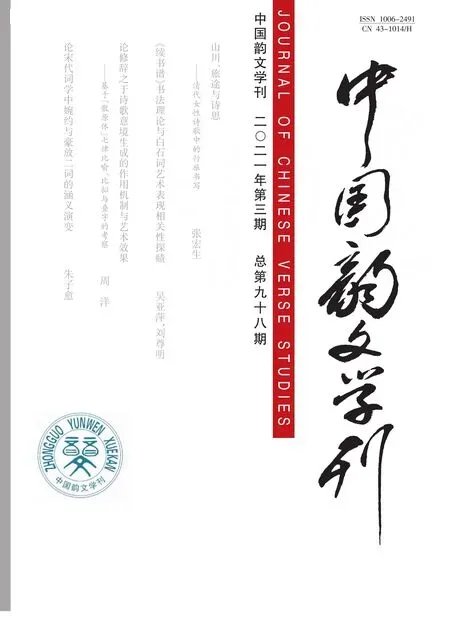简论清初京城诗坛的宗宋风尚
白一瑾
(北京大学 中文系,北京 100871)
清初宋诗派的兴起,与随之而来的宗唐与宗宋之争,是清初诗学发展演进中的大事件。历来研究者涉及清初宗宋诗风兴起,多集中于宗宋诗风在江南诗坛的流布。江南是明清两代文化中心,历来诗学发达,特别是涌现出首倡唐宋兼宗的文坛巨擘如钱谦益等人,在清初宋诗派的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作于康熙十一年(1672)的邓汉仪《诗观初集·凡例》对当时宋诗风的批判,即着眼于宋诗风在江南的传播:“然近观吴越之间,作者林立。……或又矫之以长庆,以剑南,以眉山。”
不过,在千里之外的京城,宋诗风流传之迅速广泛,并不亚于江南。在京城诗坛上,不仅有康熙十年吴之振携《宋诗钞》入京这一清代宗宋诗风发展史上的大事件;甚至还出现了王士禛以诗坛盟主之尊,继钱谦益之后,公开宗尚宋诗的局面。在康熙时代,京城俨然已经成为清初宋诗派的重镇。江南文人毛奇龄在《何生洛仙游集序》中,提到他于康熙十八年(1679)应博学鸿词科入京时,惊异于当时京城竞尚宋元诗的氛围:“吾乡为诗者不数家,特地僻而风略,时习沿染,皆所不及,故其为诗者皆一以三唐为断。而一入长安,反惊心于时之所为宋元诗者,以为长安首善之地,一时人文萃集,为国家启教化,而流俗蛊坏,反至于此。”由此可知,在康熙十八年(1679),京城诗坛已经成为清初宗宋风尚的主要来源甚至引领者,京城文士们对宋诗风的热衷程度,甚至已经超过江南。
宗宋诗风在清初京城诗坛上的兴起与扩展,经历了相当长的过程。关于宗唐与宗宋风尚在清初京城诗坛上的消长,邓汉仪《慎墨堂笔记》中的一段文字颇值得注意:“今诗专尚宋派,自钱虞山倡之,王贻上和之,从而泛滥其教者,有孙豹人枝蔚、汪季甪懋麟、曹颂嘉禾、汪苕文琬、吴孟举之振。而与余商略,不苟同其说者,则有施尚白闰章、李屺瞻念慈、申孚孟涵光、朱锡鬯彝尊、徐原一乾学、曾青藜灿、李子德因笃、屈翁山大均等人。”邓汉仪提到的当时主张宗唐的著名文人,如施闰章、李念慈、申涵光、徐乾学、朱彝尊等,乃至邓汉仪本人,都曾在顺康时代京城诗坛上活动。而宗宋文人中,王士禛为康熙时代诗坛盟主,汪懋麟、曹禾、汪琬等人也曾是京城诗坛风云人物,吴之振更有携《宋诗钞》入京,在京城大规模传播宋诗风的行为。可以看到,宗唐与宗宋之代表人物,在清初的京城诗坛上,有着旗鼓相当的分布。这正与京城诗坛“五方杂处”而带来的多元化特征有关。
本文立足于梳理清初京城诗坛上宗宋风气的产生和发展,展现京城诗坛由宋风不兴,直到成为清初宗宋诗风最盛行地域之一的过程。
一 顺治时代的京城“宋调”:宗唐不废宋论的出现
由于以明七子为代表的宗唐复古文学观的影响,明人对宋诗颇为排斥。宋荦《漫堂说诗》:“自明嘉靖以后,称诗家皆讳言宋,至举以相訾謷。故宋人诗集,皆庋阁不行。”虽然到了晚明,先有公安三袁为宋诗特别是苏轼张目,后有钱谦益明确提出唐宋兼宗的主张,但总体上,宋诗在明代还是相对冷落的。尤其是在“畿辅为辇毂近地,较之前汉,乃左冯翊右扶风,比其沐浴于圣化,而以仰承至意,鼓吹休明者,尤非他省所可跂及”的京城,更缺乏公安三袁、钱谦益这类力排众议、崇尚宋诗的大胆尝试。在晚明时代,虽然公安、竟陵诗风都曾一度流布到京城,但京城诗坛上却从未出现过有影响力的宗宋主张。
京城诗坛上宋诗风冷落的局面,一直延续到入清以后的顺治时代。虽然“五方杂处”的京城诗坛上,也不乏一二宗宋诗人的身影,如顺治六年(1649)进士唐梦赍,王士禛即称他“论诗以苏陆为宗”。但宗唐仍然是顺治时代京城诗坛的主流。黄传祖在编纂于顺治十二年(1655)的《扶轮广集》之《凡例》中指出:“畿辅首善地,近日倡兴古学。……台阁气象,远追开元大历。”即使是后来以倡导宋风而著称的王士禛,当他于顺治十五年(1658)在京城诗坛开始活动时,也仍然是一个纯粹的宗唐派。
以宗唐占据主导地位的顺治时代京城诗坛,颇有因门户之见而对宋诗持排斥态度者,其中以“京师三大家”与“燕台七子”最为典型。
清初号称“京师三大家”的王铎、薛所蕴、刘正宗三位诗人,是清初顺治时代在京城诗坛影响力较大的台阁诗人。彭志古《桴庵诗》跋语:“长安以诗名者,为王先生觉斯,刘先生宪石,暨吾行屋薛夫子,所谓三大家也。”“京师三大家”中,王铎、薛所蕴出身于中州,刘正宗则系山左诗人,他们均明确以本乡先贤李梦阳、何景明、李攀龙之传人自居,严格遵循七子复古宗唐的诗学主张,极力排斥宋元诗风。王铎自称“卜宅终须依水石,学诗誓不傍苏黄”。在“三大家”看来,宋元诗风以至于承其余绪的公安、竟陵,内涵境界单薄狭窄,语言风格浅近俚俗,与明七子所推崇的汉魏盛唐的沉厚深奥的古典审美理想严重不符:“言诗者曰:里巷女戌之诗,皆自然明白者也。古则害气害调,创则害韵害清。……傥如害气害调害韵害清,必推白居易、元微之、黄鲁直、秦少游、陈简斋一派登坛作祖,则风雅十三经离骚汉人乐府,皆当复付之咸阳一炬。呜呼,此诗道之劫数,不亦大可痛哭哉?”所以,“三大家”对“宋元诗文单薄嫩弱狭小,不能博大深厚”、“明嫩如宋元稚语”的风气痛加挞伐。作为京城诗坛上年辈较长的北方诗人,“京师三大家”力主宗唐反宋的影响力,未可低估。
“燕台七子”是活跃于顺治时代的年辈较晚的诗人团体,由顺治十八年(1661)严氏选刻《燕台七子诗刻》得名。其成员包括张文光、赵宾、宋琬、施闰章、严沆、丁澎、陈祚明七人。“燕台七子”明确提出,这个文学团体,是有意识仿效明代后七子而建立的:“仿王李宗梁之遗事,有燕台七子诗行世。”这个以“仿王李宗梁之遗事”为己任的文学社团,其成员也均系宗唐派,大多数成员都沿袭了明七子扬唐抑宋的主张。张文光“以绝代奇才,振兴大雅……一洗公安、竟陵陋习,而北地、信阳之本来面目,于焉复睹”。赵宾“古诗法曹刘,近体法初盛,尤宗少陵,兢兢守先正之矩矱,毋敢尺寸逾越”。曾是“西泠十子”之一,受到云间派影响较大的丁澎,更持有宋不如唐的观念:“要之风雅之会,必因时代为盛衰。宋兴,崇尚质厚,才人硕儒,殚精研思,悉务明经术理学,非若唐以诗取士为专家。且熙宁元祐间,士大夫多以讥讽获谴,咏歌之事,遂以不振。”丁澎认为宋人在经术理学与党争风波的双重影响之下,创作环境远不如“以诗取士”的唐人,因而“咏歌之事,遂以不振”,褒贬之意甚明。
“燕台七子”中,对宋诗态度较宽容者,只有宋琬与施闰章。宋琬门户之见本来不强,晚年放废江南之际,还曾一度涉足宋诗。但在顺治时代,他还是较彻底的宗唐派。施闰章的情形则比较特殊,已有宗唐而不废宋之倾向,留待下文说明。
顺治时代京城诗坛上还有一些诗人,虽然自身创作宗唐,但对宋诗尚能持较宽容的态度。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龚鼎孳。虽然也有研究者认为,龚鼎孳并不是完全“不染宋调”的,陈允衡《国雅初集》评价龚氏在顺治后期的创作:“见称量于三唐之间,兼得其一二宋元别调。”然而,考龚氏实际创作,可以发现,认为龚氏“兼得宋元别调”是站不住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证据是,龚鼎孳平生最喜作和韵诗,但他所步韵的前人作品,虽然颇多追和汉魏盛唐及明七子的作品,却根本没有任何针对宋诗的和作。由此可见,龚鼎孳的实际创作,主体还是七子宗唐的路子,并无主动学习宋诗的迹象。
不过,龚鼎孳本人的创作虽然沿袭七子派宗唐的旧路,诗学观点却不似“京师三大家”那样执着于门户之见,而是颇有兼收并蓄的气量。他即使自身创作并不宗宋,也颇能包容宗宋的后辈诗人。据王士禛记载,他于顺治十八年(1661)赴任扬州推官时,龚鼎孳曾盛赞年轻诗人王又旦之诗:“其年冬,予之官扬州,合肥龚端毅公集诸词人赋诗祖道,联为巨轴,推幼华诗最工。”而王又旦恰恰是一位“其诗兼综唐宋人之长”的诗人。
龚鼎孳对宗宋诗风的宽容态度,主要是出于他一以贯之的兼容并蓄的诗学倾向,并未在理论上为宋诗张目。清初京城诗坛上还有另一些文人,在自身宗唐的同时,也能明确承认宋诗的成就。不过,他们为宋诗张目,并非源于对宋诗艺术特色与成就的体认,而主要是基于儒家道统诗学观。申涵光就是一例。他是相当彻底的宗唐派,明确排斥唐宋兼宗的风气,倡导何李以唐为宗:“诗之必唐,唐之必盛,盛之必以杜为宗,定论久矣。……若宋诗日盛,则渐入杂芜。”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位宗唐派诗人,对宋诗却也有相当公允的议论。他在顺治八年曾云:“人言宋元无诗,其实真山民、苏子瞻、萨天锡自出手眼,尚有一段精光。”对明人的人云亦云鄙薄宋元诗的态度,颇为不屑。而申涵光能在宗尚盛唐明七子的同时,对宋诗亦公允评价的真正原因,与他的理学家背景有极深的关系:“近尝把玩宋儒语录,聊以检点身心,为晚年寡过之计。”
借由儒家道统诗学观为宋诗张目,这在清初京城诗坛上并不罕见,特别是一些持有传统“诗教”主张,具有官方色彩,试图以道统诗学观开创清代新诗风的京城仕宦文人。魏裔介就是其中的典型。他虽然自身诗歌创作成就有限,却是一位为清廷积极从事文化建设的高官文士,曾选当世名家之作为《观始》《溯洄》二集,又选定《唐诗清览集》《古文欣赏集》以为新王朝“诗教”之标杆。而他的文学观念,则是相当典型的征圣宗经、文以载道的儒家道统文学观。所以他与“京师三大家”“燕台七子”相比,更少门户之见:“诗,心声也。今之心犹古之心,何分于三百篇?何分于汉魏六朝?何分于唐宋元明与?”在他看来,只要符合“六义美刺之旨”的诗教道统,那么无论是何朝何代的文学,皆有可取之处。这等于从根本上消解了宗唐派与宗宋派的界限。所以,魏裔介对历代诗人的评价标准相当宽泛通达,认为“以诗人论,后世善为诗者,晋有陶渊明,唐有杜子美,宋有苏子瞻,明有李空同”,“而诗集之中又有佳者,则陶渊明、王摩诘、韦苏州、杜工部、李太白、陆放翁、李空同”,将宋诗代表人物苏轼、陆游与盛唐诗人、明七子并列为“佳者”“善为诗者”。而他对陆游更是有较大好感,“近代如陆放翁、杨铁崖、徐文长,皆神明朗照,意境超忽,不肯袭人牙后”,“陆子放翁诗万卷,后来老练更疏狂。须知深得庄骚意,莫与唐人较短长”,“南渡诗家有放翁,才高不与众人同”。在他晚年的康熙十年(1671)冬,他甚至还曾阅读并选定陆游诗集。魏裔介对陆游的好感,显然与陆游“报国有怀”符合儒家道统文学观有关。
二 康熙初年的京城“宋调”:由潜流暗涌到渐成气候
宗宋风尚在清初京城诗坛上的真正兴起,毫无疑问是在进入康熙时代之后,但具体时间还有争议。可以肯定的是,早在康熙十年(1671)吴之振携《宋诗钞》入京之前的京城诗坛上,宗宋之风已经弥漫开来。宋荦《漫堂说诗》指出,吴之振《宋诗钞》之所以在京城受到广泛的欢迎,正是因为当时的京城诗坛本来就有宗宋的倾向:“近二十年来乃专尚宋诗,至余友吴孟举宋诗钞出,几于家有其书矣。”
欲确定康熙时代京城宋诗风广泛传播的起始时间,必须由王士禛入手。王士禛是继康熙初期“诗坛职志”龚鼎孳而兴起的新一代京城诗坛盟主,又是康熙时代京城宋诗风的最主要来源,他到底于何时开始宗尚宋诗,并在京城诗坛传播其主张,相当重要。
虽然早在顺治时代,对诗学具有兼收并蓄态度的王士禛即已开始涉猎宋诗,作于顺治十三年(1656)的《渔洋诗集·丙申稿》中,即有《谢送梅戏集涪翁句成一绝》,说明至少在这一年,王士禛已经开始接触黄庭坚诗。但是,直到就任扬州推官之前,王士禛的诗风都没有明显的宗宋倾向。他在《自题丙申诗序》提及他在顺治十八年(1661)的诗学渊源:“十年以来,下及汉魏六朝,初盛中晚四唐之作者。”虽上溯汉魏六朝,而旁及中晚唐,却尚不及宋元诗。
王士禛对宋诗真正发生兴趣,是在他就任扬州推官以后。他在《癸卯诗卷自序》中,提到自己在青年宦游之际,对苏轼诗有更深入的理解:“尝读东坡先生集云:少与子由寓居怀远驿,一日,秋风起,雨作,中夜翛然,始有感慨离合之意。”他还在康熙二年,写下著名的《戏效元遗山论诗绝句三十六首》,对苏轼、黄庭坚均有好评,公开为宋元诗张目。
在康熙三年(1664),另有一重大事件,对王士禛形成宗宋倾向,有较大的影响,这就是其兄长王士禄以科场案入狱,直至是年冬方获释。在狱中,王士禄因自己的处境而联想到苏轼兄弟,因此开始对苏轼感兴趣,并仿效苏轼诗风,步其诗韵,与时在扬州任职的王士禛唱和:“念予兄弟即才具名位,不逮两苏公;然其友爱同,其离索同,其不合时宜同,其车感轲困踣,为流俗所指弃,又无不同。而坡公俊快,复善自宣写,乃稍取其集读之,读而且吟且叹,遂不自制,时复有作。”
王士禛与王士禄手足情笃,且在诗学领域受到兄长极大影响。王士禄以步韵学苏之诗与他唱和,也使得王士禛的诗风不能不受到苏轼所代表之“宋风”的濡染。虽然王士禛集中并未保存下这段时间与兄长唱和的诗作,但王士禄《次韵贻上用坡公东府雨中别子由韵见寄诗》序云:“今年春,贻上用坡公东府别子由韵作诗见寄。”可知王士禛在康熙三年(1664)春,还有主动步苏轼诗韵与兄长唱和的作品。
康熙三年(1664),王士禛还曾对陆游产生较浓厚的兴趣。他在淮上舟中读陆游诗,作有《甓湖舟夜读渭南诗集偶题长句》及《陆放翁心太平庵砚歌为毕刺史赋》,对陆游入蜀诸诗,评价极高。
所以,关于王士禛提倡宋诗的时间,笔者以为始于康熙二年至三年间(1663—1664),只不过他开始宗宋的尝试时,尚在扬州为官,其诗学观念一时还无法流布到京城。所以他的宗宋主张真正在京城传播开来,至少是要到他康熙五年(1666)再度入京以后。
值得注意的是,在康熙三年(1664),王士禄在京城被羁押期间,也曾通过与友人唱和的方式,将自己在狱中的诗作广为传播。王士禄本人在其自传《西樵山人传》中回忆道:“会因而置狱,山人内省不疚,啸歌自若也。……退而命酒赋诗,翌日诗传都下。”不过,王士禄性格孤介,不喜交际应酬,所以在京的酬答之诗并不多:“兼以疏拙,性厌献酬。……以故自鞧轩驰驱邮壁驿柱之外,其居京师两岁中,为诗不过三十许篇耳。”而他在京城诗坛的人脉关系,更无法与乃弟匹敌。因而他的宗宋之作,虽然能够一时“诗传都下”,但在当时京城诗坛上,未能造成较大的持续性影响。京城宗宋诗风的真正抬头,仍然是在王士禛入京之后。
康熙五年(1666),王士禛复原官,北上入京。此时的王士禛,在创作上已经展现出相当明显的宗宋倾向。《古夫于亭杂录》:“康熙丁未戊申间,余与苕文、公甬戈、玉虬、周量辈在京师为诗倡和,余诗字句或偶涉新异,诸公亦效之。苕文规之曰:兄等勿效阮亭,渠别有西川织锦匠作局在。”与此相对应的是,康熙六年(1667)汪琬有诗云:“渔洋新诗与众殊,粗乱都好如名姝。”汪氏所言“渔洋新诗”的“粗乱”倾向,显然也是向宋人风调靠拢。由此可见,在王士禛甫由扬州回京后的康熙六年至七年(1667—1668)间,他的诗风不但已经表现出相当鲜明的“偶涉新异”倾向,而且,他的宗宋,已经可达到令“诸公效之”的地步。而康熙八年(1669)冬,王士禛作《冬日读唐宋金元诸家诗偶有所感各题一绝于卷后凡七首》,咏苏轼、黄庭坚、陆游诸家,更是明确为宋诗的成就张目了。
康熙初年的王士禛,在京城诗坛的影响力虽然还不能与“诗坛职志”龚鼎孳相比,但也已隐然成为京城颇有影响力的士林名流。《香祖笔记》:“康熙初,士人挟诗文游京师,必谒龚端毅公,次则谒长洲汪苕文、颍川刘公甬戈及予三人。”因而,王士禛的宗宋,必然对京城诗坛风尚有较明显的引领作用。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王士禛及其追随者的宗宋,此时尚不能在京城诗坛上达到后来施闰章所抱怨的“诸诗伯持论,近多以宋驾唐”的地步。其证据就是:以康熙初期活跃于京城诗坛的“海内八家”的情形而论,宗唐派与宗宋派,也只是各占半壁江山。
有些研究者认为,“海内八家”是一个有显著宗宋色彩的诗学团体。这一方面是因为,“海内八家”的形成,恰恰是在王士禛大力倡导宗宋诗风的康熙九年至十年(1670—1671)间。《居易录》:“己酉奉使淮浦,庚戌冬入都,会考功兄再官吏部,莱阳宋按察琬玉叔、嘉善曹讲学尔堪子顾、宣城施参议闰章尚白、华亭沈副使荃贞蕤,皆集京师,与予兄弟暨李陈诸子为诗文之会。”另一方面,可能也是受到了吴之振《八家诗选》序言所谓“余辛亥至京师,初未敢对客言诗,间与宋荔裳诸公游宴,酒阑拈韵,窃窥群制,非世所谓唐法也”这一略带夸张色彩的描述的影响。在吴之振的描述中,“海内八家”大部分成员的诗风,都倾向迥异于“世所谓唐法”的宋调。但这一定论,其实并不符合“海内八家”的真实状况。对“海内八家”诗风宗尚进行逐一考察,就可以发现,宗唐派仍在“八家”中人数过半,而明确宗宋者,王士禛之外,只有自称“鄙人称诗慕韩杜,谓及苏陆皆文雄”的王士禄,以及早期宗唐尊七子,直到流寓江南之后方有所变化,涉染宋风,“浙江后诗,颇拟放翁”的宋琬而已。
其余五人中,施闰章是已经被邓汉仪定性为对诗坛的宗宋风潮“不苟同其说”的正统宗唐派。程可则系岭南诗人,自称“仆本滨海人,赋性多寡昧”,诗学好尚比较保守,且一直以“古贤逝不作,大雅将谁陈?汉魏邈千年,唐风委荆榛”为憾,可见其诗学主张也是沿袭明代中后期以来的宗唐复古旧辙,而不濡染新兴宋风。陈廷敬虽然能对宋代大家若苏轼等予以好评“苏公天上人,万丈银河垂”,且多有和苏韵之诗,但其自身诗歌创作仍以宗尚杜甫为主。《渔洋诗话》:“陈说岩相国少与余论诗,独宗少陵。”曹尔堪并无诗集传世,其诗风仅能从《八家诗选》《百名家诗选》收录的两百余首诗中略见端倪。不过,《晚晴簃诗话》评价他“尤工于诗,庶几乎登开元之堂,入大历之室”。由此可知,曹尔堪风格亦趋向于宗唐一路。身为云间派后学的沈荃更是严格遵循宗唐尊七子云间家法,“独会心于高岑王孟,颇足见其性情”。而且,沈荃对当时流行的宋诗风颇为不屑,在康熙十一年(1672)所作《过日集序》中,他对当时的宗宋之风有极严厉的批判:“今之号为宋诗者,皆村野学究肤浅鄙俚之辞。”由康熙初期京城诗坛上风云人物“海内八家”的构成看来,康熙初期,京城宋诗风虽在王士禛的大力倡导下初见端倪,但尚不能压倒宗唐派的强大势力,更不可能出现后来冯溥、施闰章辈所批判的“以宋驾唐”的局面。
在京城诗坛这种“宋风”隐然兴起,“唐风”声势仍盛的状态下,康熙十年(1671)吴之振携《宋诗钞》入京,就成为京城诗坛上影响唐宋诗风消长的大事件。这一年,宗宋派的诗人吴之振携多部《宋诗钞》刻本入京,赠送京中著名文士,又在京城诗坛上展开了广泛的交游唱和,其文学创作活动与《宋诗钞》双管齐下,起到了有力地向京城文士传播宋诗风的作用。
在吴之振入京的康熙十年,虽然江南已有文坛耆宿钱谦益扛起唐宋兼宗的大旗,与七子遗风相抗衡,但吴之振却并不敢确定,他的宗宋主张是否能为京城诗坛所接受。然而,当时京城诗坛的宋风之盛,远远超出了他的预期:“余辛亥至京师,初未敢对客言诗,间与宋荔裳诸公游宴,酒阑拈韵,窃窥群制,非世所谓唐法也。故态复狂,诸公亦不以余为怪,还往唱酬,因尽得其平日之所作而论次之。”这使得他惊喜若狂,在京城展开大规模的文学活动,一方面广泛赠送《宋诗钞》,另一方面也大力结交京城著名文士,拓展影响。施闰章《吴孟举见寄舟行日记有述》:“遗诗表宋元,断简无失坠。(注云:吴刻有宋诗钞)鼔棹入京师,万卷悉捆致。摩娑石鼓文,时把公卿臂。”即言吴之振在京大规模赠送《宋诗钞》且与京城名士唱和的盛况。
吴之振及其《宋诗钞》在京城诗坛所引起的反响,高下不一。既有陈祚明“论诗莫为昔人囿,中唐以下同郐后。何代何贤无性情?时哉吴子发其覆。……近时浮响日疏芜,矫枉宜将是书救”的高度评价,也有沈荃“今之号为宋诗者,皆村野学究肤浅鄙俚之辞”的严厉批判。由此可见,康熙十年(1671)的京城诗坛上,虽然宗宋风气颇盛,但原有之宗唐风气并未因此衰落,而是与“宋风”并驾齐驱,形成互角短长之态势。
吴之振于康熙十年(1671)冬进京,次年二月即离开京城,在京活动时间不过短短数月,但他所造成的影响力却是惊人的。他在京到底赠出了多少部《宋诗钞》,已难确考。但从《黄叶村庄诗集》卷首的赠行诗,以及与其诗歌唱酬的诗人来推测,至少有40余家。仅以刻于《黄叶村庄诗集》卷首的《赠行》诗,即康熙十一年(1672)春京城诗人送吴之振由京师返乡之诗来看,其作者即有28人之多,与吴之振在京期间交游唱和则数量更多,当时在京的文章巨子,几乎全部囊括其中。其中包括康熙初期京城诗坛风云人物“海内八家”,老一辈贰臣文士王崇简、高珩,“燕台七子”之陈祚明,后来成为“金台十子”成员的田雯、汪懋麟、宋荦等。
三 康熙十年以后的京城诗坛:“以宋驾唐”现象的出现
吴之振携《宋诗钞》入京事件,所给予京城诗坛的影响是巨大的。首先是在康熙十年(1671)之后,王士禛创作上的宗宋倾向趋向于明朗化。他已经不满足于仅以论诗诗为宋诗张目,而是以自身的实际创作,大规模效法宋诗。康熙十一年(1672),王士禛入蜀典四川乡试,其间所作之诗,编为《蜀道集》。此集是王士禛学宋最突出的作品之一。盛符升评曰:“比于韩苏海外诸篇。”王士禛此行入川,曾在四川谒苏轼故里,作有多首吟咏追和苏轼的诗作。并还有手书陆游诗赠友人的行为,如《阆中怀沈绎堂》:“予近为绎堂书放翁诗。”而其《晚登夔府东城楼望八阵图》《登白帝城》等,更是公认的宗宋名作。甚至在康熙十七年(1678),他得以内直南书房,并蒙赐御书,需要咏诗谢恩的重要场合,他也毫无忌惮地使用宋人故实。《蒙恩颁赐御书恭纪四首有序》其四云:“寄语紫薇花下客,休夸三十四骊珠。”注云:“宋臣苏轼迩英赐御书诗云:袖有骊珠三十四。”使用的正是苏诗的典故。
在王士禛的引领下,京城诗坛的“宋风”,在康熙十年(1671)以后达到高潮。以康熙十五至十六年间(1676—1677),活跃于京城诗坛的“金台十子”的情况来看,宗宋诗人已经超过半数。关于“金台十子”的成员,《居易录》载:“丙辰、丁巳间,商丘宋牧仲(今巡抚江西右副都御史)、郃阳王幼华(后官户科给事中)、黄冈叶井叔(后官工部主事)、德州田子纶(巡抚贵州右金都御史)、谢千仞(刑部员外郎)、晋江丁雁水(官湖广按察使)及门人江阴曹颂嘉(后官国子祭酒)、江都汪季甪(刑部主事)皆来谈艺,予为定《十子诗》刻之。”“金台十子”中明确宗宋的成员,至少包括如下诸位:
宋荦。他于康熙二十九年(1690)任江西巡抚时曾以《江西诗派论》课士,为张泰来《江西诗社宗派图录》作序,订补《施注苏诗》。沈德潜言其专学苏轼,“所作诗古体主奔放,近体立生新,意在规仿东坡”。《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亦云:“荦诗大抵纵横奔放,刻意生新,其渊源出于苏轼。”他自称自己在康熙十一年(1672)、十二年(1673)期间入京,受到京城宋诗风的影响,因此转而宗宋:“康熙壬子、癸丑间,屡入长安,与海内名宿尊酒细论,又阑入宋人畛域。”
田雯。他对宋诗各大家的师法更为普遍,且大力肯定他们在各种诗体发展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如:“欧阳文忠公崛起宋代,直接杜、韩之派而光大之,诗之幸也”,“眉山大苏出欧公门墙,自言为诗文如泉源万斛,是其七言歌行实录。神明于子美,变化于退之,开拓万古,推倒一世”,“山谷诗从杜、韩脱化而出,创新辟奇,风标娟秀”,“陆务观挺生其间,祓濯振拔,自成一家,真未易才”。
王又旦。“其诗兼综唐宋人之长,独不取黄庭坚。”
汪懋麟。“其师法在退之、子瞻两家,而时出新意”,“昌黎、眉山、剑南以下,以次昭穆”,甚至因宗宋而与徐乾学公开辩难。
谢重辉。其诗为王士禛评价为“不愧二苏”,“何减坡公”。
曹贞吉。他系“京师三大家”之一的刘正宗外孙,早年属宗唐尊七子一路,但后期渐入宋调,“始得法于三唐,后乃旁及两宋,泛滥于金元诸家”,“夫子诗气清力厚,似根本于杜韩,更放而之香山剑南”。
曹禾。他亦兼宗唐宋,王士禛记其言曰:“杜李韩苏四家歌行,千古绝调。”邓汉仪《慎墨堂笔记》更将他视为康熙初宗宋诗人代表人物之一:“今诗专尚宋派,自钱虞山倡之,王贻上和之,从而泛滥其教者,有孙豹人枝蔚、汪季甪懋麟、曹颂嘉禾、汪苕文琬、吴孟举之振。”
“金台十子”中,能纯然不染宋调者,只有颜光敏、丁炜、叶封三家而已。康熙十年(1671)以后,宋诗在京城诗坛上如此盛行,这也无怪乎康熙十八年(1679)毛奇龄入京时,惊呼“一入长安,反惊心于时之所为宋元诗者”了。
随着京城诗坛的宗宋之风日益兴盛,甚至大有“以宋驾唐”之势,宗唐派对宗宋诗风的质疑,也日渐增多。不过,到了康熙十年(1671)以后,曾经大力尊尚七子的老一辈贰臣诗人如“京师三大家”、龚鼎孳等均已先后去世,顺治时代标榜宗唐尊七子的“燕台七子”也早已风流云散。且经过顺治以来一直延续的对晚明诗风尤其是七子竟陵流弊的反思,也使得借由七子复古诗学观念反对宗宋这一门户之争色彩明显的途径,在康熙时代的诗坛上,已经很不得人心。所以,这一时期京城诗坛出现的对于宗宋诗风的质疑和反对,主要是门户之见不强。但有显著庙堂正雅诗学倾向的仕宦诗人,其中以冯溥和施闰章最为典型,他们的态度较那些执七子旧论以反宋的诗人更加通达,对宋诗并非一味排斥;他们主要不能容忍宋诗凌驾于作为古典诗歌完美范式与新兴清王朝庙堂诗风样板的唐诗之上。清初京城诗坛的唐宋诗之争,逐渐由门户之见,演变为“朝”与“野”、庙堂与草野诗风之间的消长。
由顺治时代的七子复古派宗唐诗风弥漫京城,到康熙前期的宗宋诗风在京城诗坛兴起,再到康熙十年(1671)以后,京城诗坛上宗宋派能与宗唐派旗鼓相当且还隐然占据上风,以至于宗唐派要惊呼不可“以宋驾唐”,这一唐宋诗风的此消彼长是清初文学领域的重要现象之一,也共同促成了清初京城诗坛的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