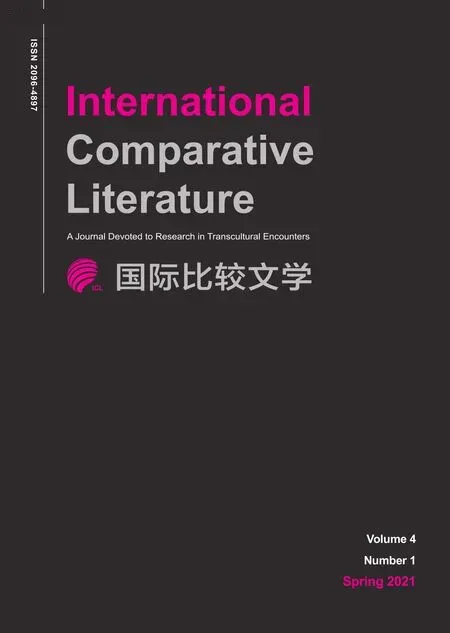诗人译者与个性化反叛*
——论肯尼斯·雷克斯罗斯杜诗英译的翻译策略
徐依凡 复旦大学
引言:“诗人译者”身份的双重性
肯尼斯·雷克斯罗斯(Kenneth Rexroth)既是诗人又是译者,这一身份的双重性在翻译活动中表现为主体性的正反两面:他作为诗人的审美修养、文化自觉与创造能力提供了主动诠释异域文本的可能性,同时,作为译者又受限于文本背后两种语言与文化的不可通约性(incommensurability),以及受到本土读者期待与接受的制约。这两个身份在翻译活动中不断相互促进与约束,从而引导雷克斯罗斯选择最优的翻译策略。
雷克斯罗斯声称进行诗歌翻译“仅仅是经年以来为了使自己愉悦,并非是炫耀学术能力或对汉学这个复杂论题的掌握”。可见他的翻译目的不同于学者,译诗无意于推动汉学研究的发展,而是试图在翻译、改写与模仿的交叉平面上,利用异域文本的素材,激发出更多审美表达的可能性。因此,对于诗人译者而言,对源语文本的认同与共情是不可或缺的环节,而翻译也成为了审美经验的表现媒介。
诗歌作为民族文化的结晶,也是民族语言最高成就的体现,因此诗人的素养使得雷克斯罗斯对语言有着卓越的掌控力,而他也始终保持着对语言历史性的敏感,因为“随着时间的流逝,所有的翻译都会陈旧。在语言变化之前,社会已经发生了变迁。”雷克斯罗斯对翻译当代性的认识,也反映出他对激活英语表达的追求:“翻译,的确可以帮助我们造出许多新的字眼,新的句法,丰富的字汇和细腻的精密的正确的表现。”语言系统的更新能够有效拓宽文学的表现域,从而推动思维方式的转型。于是,诗人的才华能够在译者的任务下得以施展,在诗歌表达的意义与形式两个层面上提炼语言的艺术。
相较于诗人审美的非功利性,译者通常具有明确目的。雷克斯罗斯相信中国诗所展现的美学思想能够为当时已趋乏味僵化的美国诗歌带来新质,希望借助翻译引入这种异域审美思想,从而推动本土审美风尚的转变。
从翻译研究理论史来看,自上世纪80年代起,以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和勒弗维尔(André Lefevere)为代表的文化学派提出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cultural turn),学界才普遍开始关注译者主体性(translator subjectivity)问题,这种对身份的凸显意味着译者地位的提升。译者主体性是指“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在尊重翻译对象的前提下,为实现翻译目的而在翻译活动中表现出的主观介入,其基本特征是翻译主体自觉的文化意识、人文品格和文化、审美创造性。”但另一方面,主体的介入并不是任意性的,而是会受到语言规则与文化语境的规限,以及意识形态(ideology)、诗学(poetic)与赞助人(patronage)的操控(manipulation)。在社会文化方面,二战之后的美国处于后工业时期,民众遭遇了资本主义世界中的价值危机,普遍认识到西方的传统思想、宗教信仰和生活方式已经不足以让他们安生立命,纷纷呼唤自然人性的回归,其中“敏锐的诗人们率先在文学领域向东方文化寻求自救之道。”在诗学方面,此前诗人们的创作都深受艾略特(T.S.Eliot)的影响,但诗坛对“非个性化”(impersonal theory)日趋狭隘的理解使得诗人无法自由表达主观情感;在这种困境下,诗人力求摆脱“非个性化”理论的束缚,追求现实生活中情感的真实抒发与个体的自由表达。
翻译文学正是在这个角度能够对既定的文学系统产生影响,正如佐哈(Itamar Even-Zohar)所言:“当翻译取得中心地位的时候,翻译行为参与创造新的重要模式这一过程,此时译者主要关注的不仅是找寻本国文学中既有的文学模式以翻译原文;相反,在这种情形下,译者已经准备好打破本国的传统。”在这个阶段,雷克斯罗斯把目光转向异域文化,寻找新的审美思想,颠覆本土既有的文学表现样式及其背后的价值观念。
可见,诗人与译者的双重身份,不是简单地代表主动与被动两个相反的方面,而是两者之间相互推进而又相互制约而形成了闭合的循环,丰富了译者主体性的内涵。基于这种身份的双重性,雷克斯罗斯在翻译中采取了与之相契合的策略。
一、“中国式法则”:诗境保留中主客关系的修正
雷克斯罗斯在《诗人作为译者》(“Poet as Translator”)一文中,详细阐述了他的翻译立场与翻译观,并相应地提出了保留“诗境”(poetic situation)与遵循“中国式法则”(Chinese rule)的翻译方法,而实践技巧背后的原理又与他的诗学思想相契合;因此,我们首先需要在诗歌发展史的背景中来考察翻译与诗学之间的交互影响作用。
雷克斯罗斯美学思想的形成不仅与他早期诗歌创作经验有着密切的联系,也受到当时诗坛风气的反向推动。上世纪20年代的美国诗坛以艾略特为领袖,他继承并践行了庞德(Ezra Pound)的“意象派”宣言,又在法国象征主义和英国玄学派的影响下,完成了从意象主义到象征主义的转变;针对浪漫主义过分崇尚个性与自我的现象与“一战后西方精神的颠覆与资本主义的幻灭”,他试图“用象征的手法和晦涩的文字给式微的西方文明提供一个‘图徽’(emblem)。”由此,艾略特提出了“非个性化”的理论主张,他认为“‘感受’本身既不是主观的也不是客观的,但当其发展为一种术语和关系的清晰整体时,就能影响有意识的主体,但不影响主体有意识的客体。”他进一步提出为了实现对非个性化情感的传递,诗人应当所采用“客观对应物”(objective correlative)的手法:“用艺术形式表达情感的惟一方法是寻找一个‘客观对应物’;换句话说,是用一系列实物、场景,一联串事件来表现某种特定的情感,那种情感的最终形式必然是感觉经验的外部事实一旦出现便能立刻唤起。”这个理念力图把诸种客体对应物通过关联连结成网,形成一套把个体情感转换、过滤而理性化的流程。
但雷克斯罗斯对这一思想中所包含的“主体-客体”关系却有完全不同的看法,他把艾略特的理论与立体主义诗歌的特征作了对比:“立体主义诗歌有一个主体,一个静止的生命,那个主体的各个元素都破碎了,并在空间与时间中分解、重组成一个崭新的、更具审美性的强有力的整体,但那却仍是一个主体。而庞德、艾略特与乔伊斯(James Joyce)的做法却不同,他们作品中的主体是模糊的、不明确的以及宏大的,并且展示为各种各样碎片化主体拼贴之后的图像。”但即便如此,雷克斯罗斯依然认为诗歌艺术却达到了殊途同归的效果,《荒原》(“The Waste Land”)正是有这样的表现力。雷克斯罗斯不仅批判艾略特的诗学理论,还大胆指出了他的诗歌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自相矛盾:“大多数伟大的诗篇是根据错误的原理与隐秘的、尴尬的隐私而写就的。”艾略特总是称自己用古典主义的手法写作,但事实上雷克斯罗斯认为他显然在用浪漫主义的方法写作。
雷克斯罗斯的汉诗翻译正是希望能够探求一种实现个性化效果的“正确原理”,于是他全面地总结了中国自然题材诗歌的审美特质,认为“中国诗人不喜欢过于华丽的词藻,他们从不谈论诗歌的材料,也不对生命做抽象的思考,而是呈现一个场景和一个动作。”他发现,诗歌情境本身是中国古典诗词的重要元素,他紧扣这一特点对中国诗歌创作技法总结出一套“中国式法则”:“在诗中表现具体的场景、行为及诉诸五官的意象,并创造一种‘诗境’”。
雷克斯罗斯的目的是能够通过翻译引入异质性元素对非个性化理论及其背后的传统价值进行修正;因此,在对于“诗境”的讨论方面,“异质性”所指涉的内涵不仅是创作手法的更新,更是哲学、美学与价值取向的差异。这种诗学观念的推动力自庞德开始已渐渐渗透到美国诗中,庞德甚至把价值修正的走向类比为文艺复兴:“一场文艺复兴,或是一场觉醒运动,其第一步是输入印刷、雕塑或写作的范本……很可能本世纪会在中国找到新的希腊。目前我们已找到一整套新的价值。”
在具体实践“中国式法则”来保留诗境之时,雷克斯罗斯特别注意采用简洁、明确与凝练的名词性意象,并成熟运用了意象并置(juxtaposition)和意象叠加(superposition)的手法,前者指关系不明确的意象形成的并举,构成多义的韵味,而后者指比喻性意象不用连接词直接与所修饰的意象连在一起,其效果是把读者抛置于大自然中形成一个有机整体,并于其中通过知觉体验来触发真实而直接的情感,而非把情感对应为一种被精密计算与转换的特殊程式。这里以《旅夜书怀》的翻译为例来具体阐明意象、诗境与情感的关系:
细草微风岸,危樯独夜舟。
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
名岂文章著,官应老病休。
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
NIGHT THOUGHTS WHILE TRAVELLING
A light breeze rustles the reeds
Along the river banks.The
Mast of my lonely boat soars
Into the night.Stars blossom
Over the vast desert of
Waters.Moonlight flows on the
Surging river.My poems have
Made me famous but I grow
Old, ill and tired, blown hither
And yon; I am like a gull,
Lost between heaven and earth.
雷克斯罗斯连用四个介词短语(along the river banks、soar into、blossom over、flows on)描绘景物之间交互的律动画面,展现出一股蓬勃的生命力。“my lonely boat”(我的孤舟)则巧妙地引入主体“I”(我)成为意境中的一个元素,在“我”的邀约下,读者一同在“the vast desert of waters”(荒漠般的浩渺水面上)飘荡,船桅入夜,诗情入境,只见水天一色、交相辉映。在结尾处,译者又把“I”(我)比作“gull”(海鸥),于天地间迷茫地失落,这不仅使“I”与“gull”合二为一,也使主体在海鸥的飞翔中悄然隐退,还原了一个旷远的画面,一种飘零的孤独感受被无限地放大。
译诗中主体被自然环境所溶解,主体与意象一同形成自足的诗境,而在其中读者依凭直观来体察意象所带来的情感冲击。霍布斯(Thomas Hobbes)在讨论文艺问题时提出:“想象是渐次衰退的感觉。”雷克斯罗斯正是在翻译中唤醒读者的个体性情感,使他们的感官对“衰退的感觉”保持敏锐,使他们的情绪保持天然的流露。
而为了彰显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共生关系,雷克斯罗斯在翻译实践中刻意摒弃了屈折语中严格的语法规则,尝试模仿“汉语和世界语中的简单句法结构与时态”。这种形式上的转变消除了理性介入的痕迹,而间接指向的则是中西方两种文化视域中看待世界与自身的方式,及建立在这个基础上所形成的价值体系,映射到文学、特别是诗歌的层面上,便会出现审美趣味的差异。西方语言的句法通过逻辑关系组成了严密的布局,而流块顿进的汉语用“字”来组建“句”,使语言在时间的体势流动中彰显局势、表情达意,这种“组块结构”又以“名词中心”为主要特征,这便是“中国式法则”的语言学本质。意象的表达有赖于思维活动中主观对客观的反映,因此在译诗中,没有出现复杂从句和长句的使用,意象保持其纯粹的本来面貌,成为主体情感的直接凝聚与释放。
另一个很具有典范性的例子是《北征》的节译,这在众多的译本中都是极为罕见的,分明地体现了诗人自身的审美趣味和价值判断。雷克斯罗斯在八百余字的长篇叙事诗中,敏锐地攫取了四句环境描写:
鸱鸮鸣黄桑,野鼠拱乱穴。
夜深经战场,寒月照白骨。
TRAVELLING NORTHWARD
Screech owls moan in the yellowing
Mulberry trees.Field mice scurry,
Preparing their holes for winter.
Midnight, we cross an old battlefield.
The moonlight shines cold on white bones.
译诗没有交代安史之乱的背景:“潼关百万师,往者散何卒。遂令半秦民,残害为异物。”他仅截取一个深夜途径战场的片段,形成了一首独立的诗歌。起首两句通过刻画夜间动物来描绘环境,诗人注意到了视觉和听觉双重感官的刺激,增添了猫头鹰的“screech”(尖叫声)和“moan”(悲吟声)以及野鼠的“scurry”(仓皇疾跑声),混杂着凄厉和慌乱。正如雷克斯罗斯所推崇的立体主义诗歌一样,他引领读者感受“眩晕,着迷,狂喜,水晶般凄切的声音,破碎和折射的光线,无限的深度,失重,刺激的气与味,以及综合这些感觉和情绪,感受一种全身心的清澈。”他通过感官的勾勒来反衬寂寥萧索的昔日战场景象,从而触发油然而生的荒凉之感。
最后一句收尾中也有一个看似简单而意蕴复杂的词“cold”(冷),它带来了多重模糊的含义:既可以作形容词指月光的清冷,又可以作副词指月光不顾人事地兀自洒在地面,还可以表现月光下的一片“尸骨寒”;虽然在英语中很难进行准确的语法分析,但这正是汉语古典诗词中常见的表达,一种因歧义而带来的蕴藉美。究其缘由,是源于“汉字具有主体思维性,置诸文学,则灌注了诗人的知觉体验;因为汉字的象形不同于图画,它不是对事物进行写实性的描摹,而是人们观察事物、接触大自然的体会。”诗歌的最后,主体又消失在“moonlight”(月光)里,徒留一堆白骨,与其说主体隐匿起来了,不如说是主体的情感融化在客体的意境中,主体已然不需要言说而化身于诗境,诗境同时也浸润着主体的情绪,二者同时交融在“cold”一词中。
主体与诗境的关系意味着人与世界之间的关系,这不仅是雷克斯罗斯的审美追求,也是他对个体生存境遇的反思。雷克斯罗斯的世界观深受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过程哲学(process philosophy)的影响,过程哲学认为现实是由动态的“成为”(becoming)过程而非静态的“存在”(being)所组成的,其中特别强调事件是由性质与关系构成有机体(organism)。而雷克斯罗斯在自传中声称:“我想怀特海给我奠定的现代哲学基础是其关于有机过程和内在一致性的哲学思想,而不是超验的神性。”生命哲学对创造与变化的关注催生了新的人生观与道德观,尤其是脱离自然科学所构建的理性桎梏对人类精神现象进行重新认识,这是西方现代哲学颠覆逻各斯中心主义的突破口,但另一方面却是东方哲学的基本思想,再进一步说,是道家思想的核心价值。雷克斯罗斯通过阅读李约瑟的《中国古代科学思想史》来了解老庄哲学,书中将其概括为“自然的统一性和自发性”,即把宇宙当作有机的整体,“其大无外,其小无内,一统万物的自然,和永恒常在,自本自根的道。”这便是“中国式法则”背后的哲学内核也是诗境创造所依循的原理,因此这一手法不仅对意象、诗境与主体关系的重新认识,更是指向了对不同价值观的反思。
如果说非个性化理论力图在二元对立中消除知觉的特殊性,通过抽象来追求“客观对应物”的静态程式,那么雷克斯罗斯则关注作为整体与统一的自然有机体,尤其是有机体发生变化与创造的过程,这意味着情感是具象化与个性化的。于是,他所创造的诗境往往是一种天人合一的动态体验,就如同在朱光潜在《诗论》中谈到的那样:“每首诗都自成一种境界。无论是作者或是读者,在心领神会一首好诗时,都必有一幅画境或一幕戏景,很新鲜生动地突现于眼前,使他神魂为之钩摄,若惊若喜。”他引导读者进入诗境,放大个体的感觉经验,细化知觉的肉身观照,使他们面对大自然时感到“若惊若喜”。译者的邀约给不同的个体提供了“此在”(Dasein)和“共在”(Mitsein)的真切生命体验,具体化的意象与知觉化的情感相互渗透而构成诗境,这种主客关系及其背后的语言学及哲学意义构成了对抽象化程式的反拨,从而达成本土价值的自觉修正。
二、文本的“来世”:情感棱面的创造性改译
为了寻找颠覆非个性化理论的具体手法,雷克斯罗斯在艺术领域与异域文化中自觉吸收新的美学观念,重新关照个体生命的独特价值,挖掘“非个性化”所抹杀的个体性与生活性。他反叛的立足点首先是核心的“情感”问题,雷克斯罗斯的诗学立场决定了他的翻译策略,他希望通过翻译实践在异域文本中挖掘具象化与细节化的情感表达,并以此激发自己的创作灵感。
在雷克斯罗斯所译的35 首杜甫诗歌中,大多数作品都有明确的情感线索,而第一人称始终于具体的事件与场景中保持在场。于是,“个性化”不仅指的是作为情感所属者的主人公在特殊情境下的自我抒发,还强调了情感本身也是由主人公通过具体的目之所见、耳之所问生发而来的,因此诗中客体几乎没有象征意义,译者甚至会直接把情绪剖析成简洁明了的词语来诉说。这些个性化的情感类别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第一,在自然中宁静祥和的心绪,这类诗歌中多采用了情景交融的手法,包括“Clear After Rain”(《雨晴》)“New Moon”(《初月》)“Dawn Over the Mountains”(《晓望》)“Homecoming-Late At Night”(《夜归》)“Stars And Moon On the River”(《江边星月二首》其一)“Brimming Water”(《漫成一首》)等;第二,关于时间流逝与人事浮沉的慨叹,例如“By the Winding River”(《曲江二首》)中用“cry out”与“pain in my heart”点明伤春,“Loneliness”(《独立》)中围绕“sorrows”展开,“The Willow”(《绝句漫兴九首》其九)“Moon Festival”《月》与“Jade Flower Palace”(《玉华宫》)三首分别使用“sad”“bitter”与“pathos”来抒写时间意识所生发而来的痛苦;第三,战争带来的无奈与痛苦之情,如“A Restless Night In Camp”《倦夜》中弥漫的“worry”,“Night In the House By the River”(《阁夜》)中直白而强烈的“cut the heart”;此外,还有友谊所带来的宽慰与温暖、思乡所触发的愁绪与忧伤等。但这些诗歌都有一个共同特征,从整体来看,如果说原诗中错综的情感呈现为不规则的多面体,那么译诗便是把这组情感在某一个棱面上的投射表现得尤为充分,这是雷克斯罗斯在处理“情感”问题上所采取的总体策略。
杜诗把个体遭遇与人民生活、家国命脉紧密相连,作为集大成者的杜诗具有厚重的意涵系统,孕育在民族文化与历史之中,形成一个承前启后的连续统一体,其文本的复杂性导致意义必然会在翻译中部分地失落。任何翻译都是把处在转码样态的文本,从其特定的源语(source language)文化传统中连根拔起,从而给予译入语(target language)语境下的本土化诠释,诗歌更是如此;因为诗歌书写的空白点及隐喻的多义性构成其审美形式的文本特质,在诗歌抽象的审美意象中,其极为丰富且多元的意义层次,必然指向丰富且多元的审美文化心理结构。一旦诗歌脱离了源语语境,其审美意象中所承载的歧义性与模糊性,便几乎无法在两种不可通约的语言文化中完成准确的等值转码。
在这种困境下,雷克斯罗斯根据自身对诗歌内容的共情,借助文本变形系统(system of textual deformation)予以弥补,主动选择在译本中呈现的意义以及意义出场的方式,“或是激活原文欠缺的、掩藏的或压抑的成分,或是把多义变成单义,或是把原文折叠的部分展开扩充。”对于雷克斯罗斯而言,对非个性化的挣脱不仅体现在他借助中国古典文学的审美观念来颠覆本土价值,还体现在对中国文学传统的拣选。他舍弃了儒家意识形态在诗歌中的附加意义,因为他需要警惕杜诗可能存在的“非个性化”传统;因此,他选择凸显了诗歌中更为纯粹与直接的情感棱面,并在删削中为诗歌建构同质化(homogenization)的诠释。
其中,《春宿左省》的情形十分特别,因为这首诗歌中的主线情感其实占据原诗情感层次中十分微弱的一部分,是雷克斯罗斯在剥离其政治外衣的同时进行了想象性创造:
花隐掖垣暮,啾啾栖鸟过。
星临万户动,月傍九霄多。
不寝听金钥,因风想玉珂。
明朝有封事,数问夜如何。
WAITING FOR AUDIENCE ON A SPRING NIGHT
The flowers along the palace
Walls grow dim in the twilight.
Twittering birds fly past to roost.
Twinkling stars move over ten
Thousand households.The full moon
Enters the Ninth Constellation.
Wakeful, I hear the rattle
Of gold keys in locks.I hear jade
Bridle pendants tinkling in
The wind.At the dawn audience
I must present a special
Memorial.Time and again
I wonder how long the night will last.
仇兆鳌评价这首诗:“自暮至夜,自夜至朝,叙述详明,而忠勤为国之意,即在其中。”原诗中所表达的急切心情都与心忧社稷、勤于国事的士大夫形象密切相关,“‘数问夜如何’是谏臣之心。”忠君报国和兼济天下是立德的终极目标,这便直接影响了中国文学传统形成自身的普遍性追求。但反观雷克斯罗斯的处理,他首先把诗题改变为“Waiting For Audience On A Spring Night”(在春夜里等待听众),便可知主人公第二天不是向皇帝进言,而是在一众听者面前发表“special memorial”(特殊的纪念演讲),他把词语附带的政治背景与文化心理刻意抹去了,把语境置换成“为第二天将要发表纪念演讲而紧张”,译文中也丝毫没有出现“官吏”、“朝政”与“值夜”等相关语汇,因此诗歌在保留了所有异质性意象的同时,也丰富了一种新的情感。这些景物(flowers, palace, walls, birds, stars, households, full moon, Ninth Constellation)从文化历史的积淀中重新回归大自然本身,能指与所指的对应直接而明确。于是,诗歌前半部分的意象叠加,烘托了一个春夜静谧安详的环境,使人感到愉快惬意;后半部分着重描摹主人公内心的焦虑紧张:“I wonder how long the night will last”(我想,这长夜将会绵延多久),恰到好处地呼应了被“篡改”的标题。
在这个例子中,译者把一种原先处在文本边缘的情感,“紧张焦虑”在翻译时挪至意义的中心,而原本隐含在字里行间并贯穿全诗的“忠君爱民”之义被完全排挤,译诗中的杜甫以“亲切而直接无隐”的语调与读者进行对话。
在雷克斯罗斯对情感的个性化处理中,也存在一些情感线索未必是原诗既有的棱面;通过他的很多处“误译”,我们可以清晰看到译者显身的痕迹,雷克斯罗斯把自己的理解与解释融入了译本中,此时个体情感的不规则投射会无意识地激发出“纯语言”(pure language)的种子,译者借此挖掘出原诗中个性化情感的更多可能。
本雅明在1923年发表的《译者的任务》(“The Task of the Translator”)一文中讨论到“可译性”(translatability)问题,他指出“译作依据的不是原作的现世(life),而是原作的来世(afterlife)。”这标志着译本是生命线的延续,原文若要获得“永生”(eternal afterlife)和“名声”(fame),也就是在历史上确立经典化的地位,则必须依赖译作以经受时间和空间的重重考验。“译文使原文经典化和固定化,并展示了原文中所存在的那些我们未曾发觉的意义流动性和不稳定性。”而在表现形式上,“译作呼唤原作却不进入原作,它寻找一个独特的点,在这个点上听见一个回声以自己的语言回荡在陌生的语言里。”由此,译作也就有了相异的功能,不再局限于复制或传递原作的意义,而是在其特定语言的意指方式中对原作进行补充。
雷克斯罗斯正是承担了这样的“译者任务”,他依凭自我的体认发掘了杜诗文本在注疏传统中都没有出现的特殊意蕴,并且使其在现代英语土壤中重新生长,形成一种跨文化的互补样态。《宿府》的英译是一个典型案例:
清秋幕府井梧寒,独宿江城蜡炬残。
永夜角声悲自语,中天月色好谁看?
风尘荏苒音书绝,关塞萧条行路难。
已忍伶俜十年事,强移栖息一枝安。
I PASS THE NIGHT AT GENERAL HEADQUARTERS
A clear night in harvest time.
In the courtyard at headquarters.
The wu-tung trees grow cold.
In the city by the river
I wake alone by a guttering
Candle.All night long bugle
Calls disturb my thoughts.The splendor
Of the moonlight floods the sky.
Who bothers to look at it?
Whirlwinds of dust, I cannot write.
The frontier pass is unguarded.
It is dangerous to travel.
Ten years wandering, sick at heart.
I perch here like a bird on a
Twig, thankful for a moment’s peace.
译诗以烘托凄凉的氛围与描摹漂泊之苦为核心,剥离了原诗中对于战争的悲愤、官场的厌倦与现实的无奈等一系列复杂情感,而译诗中的三处改写都体现了情感的折射方式。
首先,译诗打破了情景的平和,把悲凉如人低语的号角声替换为终夜“disturb my thoughts”(扰乱思绪)的长鸣,用“splendor”(壮彩)来修饰月色,不惜笔墨地描绘“the splendor of the moonlight floods the sky”(绚烂的月光溢满了天空),情感从无人共赏月色的落寞偏离成为了“Who bothers to look at it”(谁会去看呢)的惋惜,清辉兀自铺满夜空,而人间各有心事,主人公胸中豪情受到压抑。源文本视域中的时代因素被个体的思绪消解了,一点点地融合进深夜独行者的自白;这里,译者主体的审美偏好造成了原诗情感的偏移与转向,成为个性化情感的另一种诠释可能。
其次,“风尘荏苒音书绝”是一处“创造性改写”,原诗从零聚焦(zero focalization)视角呈现了战乱纷繁而音讯难达的状况,与下联“关塞萧条行路难”形成互文;雷克斯罗斯把视角转换为内聚焦(internal focalization)叙述,改译为“Whirlwinds of dust, I cannot write”(风沙飞旋,我无从书写),仅从字面上提取意义,把“尘”(dust)和“书”(write)两个汉字进行了“断章取义”式的拆解,并作为自由创作发挥的素材,立足于第一人称,想象出了一种风尘迷眼而提笔不得的无奈之情。沿着这样的思路,“关塞萧条”不再是对外在历史背景的描述,而是成为了主人公心理活动的一部分,他想到在“the frontier pass is unguarded”(边塞失守)的环境中,对他而言“it is dangerous to travel”(行路危险)。主人公既无法通过书写来排遣苦闷,也无法通过实际行动来改变现状,因此封闭于心的郁结达到了顶点。译者有意地通过主人公的所见所感来安排景物的出场,一草一木都与他产生了直接而密切的逻辑关联,因此能够使他的行动受到影响、使他的情感产生波折。由此可见,雷克斯罗斯始终把抒情主体置于核心地位,借主人公的眼睛看视周遭的景物,借景物的呈现刻画主体的言行与思考,通过拼贴与重组诗歌元素从不同角度补充个体情感的丰富性。
最后,尾联中的“一枝”采用了《庄子·逍遥游》中的典故,后人常用来借代栖身之所,“自禄山叛乱以至于今,苦忍伶俜已历十年而今得参谋幕府,安栖一枝,诚不幸中之幸也,而实非中心之所欲也。清夜思之,宜其展转而不寐也。”“‘伶俜十年’,见此身甘任飘蓬矣。乃今‘移息一枝’,而‘独宿’于此,亦姑且相就之词。”而雷克斯罗斯选择了淡化外部动乱的灾难性,并将其转化为主人公“ten years wandering”(十年的流浪)的个人经验;同时,他也把抒情主体因郁结而累积的“伶俜”之感用日常的“sick”(难受)来取代,成为了一种在个体生命线上蔓延的迷茫与失落。更有甚者,末尾的“thankful”(感激)一扫原作在汉语阐释域中的复杂性,读至此处,前文所堆叠的失意逐渐消褪,一种卑微的知足在反衬之下得以涌现:“我”多么感激有一处歇脚的“twig”(嫩枝)可以让所有的漂泊与寂寞都能被暂时忘却,哪怕只是弱不禁风的“一枝”,哪怕只是转瞬即逝的一刻,哪怕下一秒“bird”(鸟儿)将继续在暴风雨中挣扎,但此时的慰藉足以温热“我”飘忽的生命。
假如我们回到典故产生的原初文本语境中,或许可以对于“一枝”所可以承载的情感有不同的认识:
许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犹代子,吾将为名乎?名者,实之宾也;吾将为宾乎?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偃鼠饮河,不过满腹。归休乎君,予无所用天下为!庖人虽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
尧把天下让与许由,许由却认为不可越俎代庖,实际上是因为他追求的并不是治理天下的“名”,而是自由的境界;许由以治天下者为“庖人”,而以“巢一枝”“饮满腹”之人为“尸祝”,其中的价值判断立见高下。当我们再次返回“一枝”这个能指的时候,它除了可以被诠释为苟且的生存状态,也能够被提炼为一种自我满足的境界。
雷克斯罗斯赋予诗歌抒情者一个由极度烦扰到自我释然的转变结局,纵观全诗,诗歌以较为清晰的情感线索展开,即便这一线索并非是从原诗多层次的情感体系中遴选而得,而是通过译者的想象在原文中生长,对于原诗的改动恰恰可以表明他的内在情感与创作欲望被悉数激发,因此语言也在挣脱原文的过程中增强了张力。译者在前半部分环环相扣地表现了独白者落魄的境遇以作为铺垫,而在结尾揭示了一组对比,使得诗歌的温度由冷转热,在落寞的漩涡中留下一丝希望。或许这是隐蔽在诗歌背面的一层诠释,雷克斯罗斯在另一个时空中挖掘了文本的“来世”(afterlife),不仅作为一个补充注脚了发掘了源语文化传统中被隐藏的意义,还作为一个新的种子播撒进译入语文化中,这正是来源于文本的开放性与个体情感的多种可能性诠释。
个性化的情感并不意味着情感的层次单薄、内容浅显,而是在诗歌主人公和译者主体的体验中富于变化流动。译者对情感的表达同样带有主观性,即个性化的诠释,包括由于共鸣与爱好而形成的情感偏移、通过素材的重新组合而激活的不同情感与挖掘隐藏在语言深处的隐蔽情感,这些对文本“来世”的延续不仅表现了个体情感的诸种可能,也展示了一位诗人译者的充沛活力。
三、“诗友的语调”:友情译写中人称代词的回归
为了归附传统以获得真正的价值和意义,艾略特认为诗人必须逃避情感、消灭个性,而成为传递普遍情感的媒介。“诗人之所以能够引起人们的注意和兴趣,并非是因为他个人的感情、他生活中特殊事件所激发的那些感情;他特殊的感情可以是简单的、粗疏的或是扁平的,但他诗里的感情则必须是一种十分复杂的东西(却并不是生活中繁复而非同寻常的感情所具有的那种复杂性)。”这在本质上即为柏拉图所追求的超验于现象界的理念(eidos)
,现实世界中的个人感情是不真实的、个别的和残缺的,而非个性化的感情是复杂的、精细的和完善的,超越了现实中存在的诸种特殊感情,诗人的个体情感无非是分有(metechō
)了它所属的普遍情感。而为了追求理念世界的普遍情感,所有个性化的情感都需要经过一个理性化的过程,即把第一人称驱逐出文本。“在诗歌写作中,很多东西都必须是有意识的、经过深思熟虑的。事实上,糟糕的诗人通常在他应该有意识的地方没有意识,在他应该无意识的地方却有意识。这两个错误都使他变得‘个人化’。诗歌不是情感的放纵,而是情感的逃避;它不是个性的表达,而是对个性的逃避。”艾略特在文章结尾出,明确地表达了诗人应当对个体情感保持无意识,而在把现实感知综合提升为普遍情感之时保持有意识,此时理性便被引入了艺术的中心。因此,“诗人的任务不是寻求新的感情,只是用寻常的感情来化炼成诗歌,来表现实际感情中根本没有的感觉;在这其中,诗人所从未体验的感情和他所熟悉的感情都同样可供他使用。”由此可见,诗人可以表达的不是自己的个性,而只能作为一种特殊的媒介,把各种感性的印象和经验在其中相互结合,以达到更普遍、更永恒的情感价值;而这种情感超越于书写者本身,诗人只能作为普遍情感的接受者与传递者;在这个意义上说,诗人不再是诗歌的创造者,而是在普遍情感的激发下被动的代言人。
尽管雷克斯罗斯对艾略特的诗歌创作依然保持敬意与赞美,但他仍坚定地站在其诗学理论的对立面上,他在《遗嘱修改附录》(Codicil)一诗中对非个性化诗歌有过明确的批驳:
当然多年来英语诗坛的
统领阶层已经认定
诗歌就是这样,非个性化
构建,不允许使用人称代词。
如果精密无误地
奉行此道,这种理论
在实践中只能走向
反面。他认为“精密无误”地提炼与传递非个性化情感将使得诗歌在机械化的过程中丧失活力,他需要寻找在普遍形式中被禁锢的生命,恢复“人称”中的个体性,释放内在于现实生活的神圣精神。
雷克斯罗斯并不赞同传统儒家意识形态为杜甫所构建的“诗圣”形象,而是毫无掩饰地指出了杜甫“并非完美无瑕”:
杜甫在肃宗(明皇之子)朝担任左拾遗(一种护民官)之时,似乎就是一个脾气暴躁的侍臣。他过于认真地对待这份闲职,作为一个不知悔改的儒家经典信奉者,他不断上书皇帝劝谏他的言行道德与外交政策。
这是命运多舛的一生,而杜甫常用一种趋于自悯的忧愁来书写它。他体弱多病,三十岁时就自称白发老翁;他总是称自己的房子为茅屋,总是把自己形容得穷困潦倒,但实际上,虽然是茅草盖的屋子,但他屋舍数目颇为可观,他也从未放弃过房屋所有权,并始终对附属的田宅征税。
雷克斯罗斯十分关注杜甫具体的生活境遇,把直言进谏当作“脾气暴躁”,把坚持道义当作“不知悔改”的迂腐,把忧患意识当作“趋于自悯”,这是把杜甫从圣坛上拉下了人间,他的缺陷也正是他的个性,是独特的个性成就了更丰富饱满的灵魂。在这里,杜甫不再是普遍意义上儒家道德准则的化身,而是作为生动具体的个人出现;杜诗也不再是中国古典诗歌的典范摹本,而是两位诗人跨越时空进行心灵对谈的平台,是能够激发雷克斯罗斯个体生命体验的文字。可见,雷克斯罗斯并不认为诗歌是通过情感的回避以追求超验的普遍性,而恰然是诗人个性化情感的迸发与放纵。
如果说“中国式法则”所注重的诗境创造体现了个体情感在主客对立的消解中显现,那么情感个性化的回归则需要让第一人称重新进入现象界中,雷克斯罗斯在杜诗英译中通过日常化实现了这一目标。
雷克斯罗斯特别青睐赠友诗与酬唱诗,中国古典诗词中友谊的内涵和表达与西方世界的传统有着显著的差异。在西方文化中,友谊大都被置于政治、宗教与哲学的领域中进行论述;在文学题材方面,友谊往往是被歌颂的主题,而非情感抒发的载体,较之于此,人们把爱情作为一种更为典型的代表。虽然中国文化中同样把“友伦”作为德行的范畴,但在友人之间的相互往来的诗歌里,所呈现出的是基于君子之交的赞美、互勉与相惜之情。而中国的友情诗在选材角度、情感基调与表现手法方面,着眼于日常生活的共情,与西方爱情诗整体所表现出的崇高与热烈不同。赵毅衡在《诗神远游——中国如何改变了美国现代诗?》一书中指出:“美国新诗运动诗人认为中国诗是充分现代化的,甚至题材上都是充分现代的。当然中国诗里没有汽车、摩天大楼等素材,但中国诗用友谊来代替追求恋人的激情,用离愁代替失恋时要自杀的痛苦,用日常事务和自然景色来代替半神式的英雄。”
《中国诗百首》中收录了杜甫的《赠卫八处士》《赠毕四曜》与《奉济驿重送严公四韵》三首友谊诗歌,译诗用生活化的语调、琐碎感的意象和去文饰的表达来传达个体之间简单而细腻的情感交流,这便是一种“与他人共在”的理想状态。雷克斯罗斯把这种朴素的形式称为“诗友的语调”:“像杜甫这样的诗人有一种纯粹、直接和简单,即他作为一个身处全面交流中的人直接地表达自己,很少有西方诗人这么做。”
以《赠毕四曜》为例,尾联“流传江鲍体,相顾免无儿”巧用典故,“江鲍体”言诗文之胜,钟嵘《诗品》曰:“文通诗体总杂,善于摹拟。”“宋鲍参军诗,其源出于二张,善制形状写物之词。”江淹与鲍照的诗歌被推为六朝典范,而“江鲍有诗传后,必定无儿,故有下句。”但在译诗中江鲍的诗学成就与家学传承问题并没有出现,而是着眼于“We can console each other.At least we shall have descendants.”(我们相互劝慰,至少我们后继有人。)译者把“江鲍”简化为“我们”,缩短了语言形式指向意义的路径,流传后世的将会是“我们的诗篇”(poems)与“我们的子嗣”(descendants),借文人有才无儿的缺憾来劝慰朋友,既包含了对前文“our homes are humble”(我们的屋子很简陋)与“our faces are wrinkled”(我们的脸颊布满皱纹)的自我解嘲,也表现出珍视友情、患难与共的积极感。这就意味着,友谊最基本的性质并不是一种社会道德约束,而是可以安放个体情感并获得慰藉的社会关系,因此译诗通篇使用的人称皆为“we”,情感流露简约而平实。
友人之间的唱和互勉正是中国古代文士的传统,诗人常常以真挚的语调,叙述往事回忆,刻画细节,以表达朴素深厚的感情。雷克斯罗斯在谈论杜甫诗歌创作时,特别提及了对士大夫阶层写作惯例的理解:“杜甫对多年未见的妻子,在诗中也只透露出轻淡的感情。他从不给女子写爱情诗,而是与志同道合的男子交游,和他们维持友好的关系,这很大程度上是士人阶级的写作传统。”这种友谊在雷克斯罗斯看来既世俗又深刻,内在的热烈与外在的平淡,着眼生活细节的白描,以对话的方式抒发个体情感,于“共在”中再次确认个体的“此在”。
我们再以《奉济驿重送严公四韵》为例,讨论个体之间的交互情感被抛置于自然世界中的状态,进一步讨论雷克斯罗斯对日常化情感的理解与书写。此诗创作于代宗即位不久,杜甫的好友严武被召回长安,面对着挚友的得志与举荐的承诺,杜甫在诗中却流露出了孤独之意,也杂糅着对仕途无望的落寞。
远送从此別,青山空复情。几时杯重把,昨夜月同行。
列郡讴歌惜,三朝出入荣。江村独归处,寂寞养残生。
FAREWELL ONCE MORE
TO MY FRIEND YEN AT FENG CHI STATION
Here we part.
You go of in the distance,
And once more the forested mountains
Are empty, unfriendly.
What holiday will see us
Drunk together again?
Last night we walked
Arm in arm in the moonlight,
Singing sentimental ballads
Along the banks of the river.
Your honor outlasts three emperors.
I go back to my lonely house by the river,
Mute, friendless, feeding the crumbling years.
译诗随着人称代词在“我们”“你”和“我”之间切换,从二人离别时渐行渐远的现实,进入相伴相随的回忆,最后又被拉回孤独的现实,情感交织着离别的愁绪与记忆的温热。整首诗充满着简朴的场景重现与平实的语言表述,诗人怀念的是那些共饮的时日、同歌的夜晚,特别是译文中有一处创造性改译:“walked arm in arm in the moonlight”(在月色下挽着臂散步)。“列郡讴歌惜”表示了对朋友的政治才能与为人品格的高度赞美,也同时暗含了朋友的仕途顺意与自己落魄境遇的一种对比,但是雷克斯罗斯没有拘泥于对仕途的感叹,而把颈联中溢美的“歌颂”替换为了真诚的“歌唱”:“Singing sentimental ballads along the banks of the river”(沿着河岸唱着感伤的歌谣),用普通而温馨的细节来丰富对友谊的纯粹书写,让回忆的画面中绵延着“moonlight”(月光)和“banks of river”(河岸),充满了“drink”(酒)与“sing”(歌),没有激情的碰撞,皆是寻常之物景娓娓道来。
雷克斯罗斯把这样的诗歌交流模式称为“自然数”(natural numbers),即“句法和措辞上近似于人与人之间实际对话的诗歌”,这个“直接传达”的理念不仅作为修辞手法出现,也是诗人与读者、与世界的交流方式。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在《哲学研究》(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
)中提出了“语言——游戏”(language-game)的概念,强调语言和日常生活的联系,“语言-游戏这个概念突出了语言的言说是活动的一部分,或者说是一种生活形式(a form of life)。”可见,语言延伸到了人类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涵盖日常生活中的各项活动。而雷克斯罗斯在译歌中对语言的处理正是把言说放诸感性生活中,而“自然数”所对应的表达方式更是在介质上消除了传递的隔阂,为语言找到了“生活形式”,而非把生活世界抽象为符号组合。《赠卫八处士》的翻译也同样如此,用自然环境作为友情书写的铺垫与底色,把人际活动包容在一个和谐的整体中,例如把“夜雨翦春韭,新炊间黄粱”译作“We go out in the night and cut young onions in the rainy darkness.We eat them with hot, steaming, yellow millet.”(我们在黑暗的雨夜里出门剪韭;我们就着冒出热气的黄粱品尝。)诗歌主体部分结合了叙事与抒情,把过去的回忆与现在的场景穿插在一起,但仍然以简洁的语词向友人感慨为主,例如用接连的疑问句来惊叹岁月流逝的无情:“what night is this?”(今夕何夕?)与“How much longer will our prime last?”(壮年尚几何?)再如诗友之间毫无修饰也毫不掩饰地袒露真实的情绪:“Fear and sorrow choke me and burn my bowels.”(恐惧与悲伤使我凝噎断肠。)与“It is sad, meeting each other again.”(再次遇见着实令人伤心。)甚至把原诗中含蓄的“感子故意长”变成了对长久友情的坚定信念:“We still love each other as we did when we were schoolboys.”(我们仍然像儿时那样彼此友爱。)
而结尾处想象送别画面,“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被译作“Tomorrow morning mountain peaks will come between us, and with them the endless, oblivious business of the world.”(翌日清晨,山峰将隔开我们,与之相随的还有这世上无尽的琐事);“世界之纷扰”与“青山之巅”并列成为绵延不绝的整体,直闯进来分开了两位友人,喟然感叹之余还交代了友谊、自然与人事的关系,它们都暗示着一种悲剧意识。钟玲对此评论道:“那友情、幸福与爱面对浩瀚的宇宙都是无可奈何地转瞬即逝,这种珍贵的人类关系将不可避免地被无情的大自然与令人厌倦的世事割断。”但钟玲没有意识到的是,人对于时间性的敏感可以催生存在的焦虑,而友谊恰然可以作为克服生命焦虑的途径之一。雷克斯罗斯用介词“with”把自然性与社会性糅合于统一体的世界,而用介词“between”诠释了友情与整个世界的纽带;这种在不同文化语境中的语言表达能够释放本土的“语言剩余”(remainder),译诗的基调反过来利于对友谊的个性化书写,暗示了雷克斯罗斯对这种情感交流的憧憬与肯定,甚至把格局从对人际关系的思考转向了对宇宙的关照。
友谊书写丰富了雷克斯罗斯审美思想中对个性化的理解,被抛置于世界中的个体在与他者的关联中解蔽自身的存在与意义,而友谊便是一种具有代表性却往往被西方文学忽略的人际关系。译诗在表达内容上筛选性地突出了日常化的场合,在生活细节中注入个体本位的真挚性与独特性,必要时则以本土话语增改的方式进行处理;而在手法形式上采用“诗友的语调”,以第一人称与第二人称直接对话的方式不加修饰地流露彼此的情感,无论是叙事还是抒情,大多使用口语短句与简单词汇。友情的书写有利于个体与世界的充分和解,从而在一个更广阔的空间里,个体情感的抒发能够同时具备自然性与社会性,成为对“非个性化”的又一有力回击。
四、典故转码的解释项与传统的现世性诠释
艾略特的“非个性化”在实质上是柏拉图主义传统的延续,他认为诗人的个人才能必须要归附到历史传统中。诗人个体的创作批评往往是局限的、带有偏见的和片面的,没有一个诗人或艺术家有自己完全独立的意义,他的意义必须与历史传统相关联;而传统是具有十分广阔意义的东西,其中的历史意识同时包含了过去的过去性与当下性,伟大的作品在传统中按照完善秩序组成完整的体系,为评判新诗人提供了规则和标准。因此,个人只有融入传统的深厚底蕴中才能体现出真正的价值。
舒斯特曼(Richard Shusterman)认为非个性化理论有两种理解:一是超越狭隘的个性,即“共识客观性”(consensual objectivity),指被社会传统所认可的存在;二是无个性,即“事实对应性”(realist-correspondence),指诗人能够消除偏见而成为中立的、完美的人。前者提出了对普遍意义的要求,呼应了艾略特对传统的归附;后者则对应了局限性的个体在传统中获得完善。从中可以见出艾略特思想中的柏拉图主义倾向,他认为诗人作为个体必然带有缺陷,而诗人只有在传统的脉络中追求普遍的超验价值之时才能够完善自身。
若是按照这样的思路,雷克斯罗斯已然意识到了非个性化理论的局限,翻译更应当回避个人风格,而在源语文本所处的历史传统中追溯完善的理念,来推动本土的价值转向。而作为“集大成”的杜诗恰是负载了最为厚重的文学传统,所谓“子美集开诗世界”,后世学杜甫、注杜诗之盛形成了蔚为壮观的景象,正如闻一多所言,杜甫是“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大诗人,四千年文化中最庄严、最瑰丽、最永久的一道光彩。”但是雷克斯罗斯却没有致力于研究杜甫及其诗歌的诸种历史价值,亦没有选择把译诗当作中国古典文化传统的现代英语载体,而是把杜诗话语当成创作发挥的素材,抛开了传统普遍性的理解以成全诗人个体性的诠释。
传统在文学中最凝练的结晶便是典故,而典故又是丰富的民俗文化在语言上的积淀。韦努蒂(Lawrence Venuti)在《翻译改变一切》(Translation Changes Everything
)这部专著中指出:“源语文本在经过翻译时有三类语境都失落了,分别是:文本内语境、互文与跨语篇语境与接受语境。”典故则集中体现了上述三者的缺失,它通过把不同时空的话语折叠进同一能指(signifier),在本土文化中可以达成文化厚度的累积与含蓄曲折的诗学效果,却对异域读者精准把握所指(signified)造成了很大的阅读障碍。典故向来是翻译活动中的一大难题,正如奈达(Eugene Nida)对译者所抛出的质问那样:“如何在本土读者不了解源语文化模式的前提下传达原作的精髓和风格?如何引导接受者与他自己文化语境中的行为方式联系起来?”雷克斯罗斯在英汉转码行为中持有英语译者显身(visible)的在场性(presence),他在翻译典故时把错位的意义时空拉伸到同一个平面上,根据自身所处的时代社会特征注入现世性的理解。在他看来,“中国式法则”所体现的审美价值固然能带来世界观的更新,但这并不意味T.S.Eliot, “Tradition and the Individual Talent,” 49-50.着译者需要进入产生异域价值的传统中去,否则会在另一种传统中再次消解个体的存在。为了凸显个性化情感的独立意义,其书写必须具有特定的历史性,诗人译者对经典的现代化诠释并不是一种片面和局限,而是把当下的经验与特殊的风格铭刻进传统文本中,最终成为个体存在的注脚。
我们将在《杜位宅守岁》三个译本的比较中分析雷克斯罗斯对传统意义与个体价值的态度,这首诗涉及了“椒盘”和“颂花”两个中国的传统习俗:
守岁阿戎家,椒盘已颂花。
盍簪喧枥马,列炬散林鸦。
WINTER DAWN
The men and beasts of the zodiac
Have marched over us once more.
Green wine bottles and red lobster shells,
Both emptied, litter the table.
“Should auld acquaintance be forgot?” Each
Sits listening to his own thoughts,
And the sound of cars starting outside.
其中,“椒盘”这个民俗可以追溯到崔寔的《四民月令》:“正月之旦,是谓‘正日’。……子、妇、孙、曾,各上椒酒于其家长。”下有补本注:“过腊一日,谓之小岁,拜贺君亲,进椒酒,从小起。”西晋文人成公绥在《椒华铭》中也记载了百姓在元月一日以花椒果实佐食的习俗:“嘉哉芳椒,载繁其实。厥味唯珍,蠲除百疾。肇惟岁始,月正元日。永介眉寿,以祈初吉。”而宋代罗愿的《尔雅翼》亦载录了部分铭文,并对这个习俗作出了进一步的考释:“成公绥椒华铭云‘肇惟岁始,月正元日’,是知小岁则用之汉朝,元正则行之后世,率以正月一日,以盘进椒,饮酒则撮置酒中,号椒盘焉。”而“颂花”这一典故出自《晋书》卷九十六《列女传》:“刘臻妻陈氏者,亦聪辩能属文。尝正旦献椒花颂,其词曰:‘旋穹周回,三朝肇建。青阳散辉,澄景载焕。标美灵葩,爰采爰献。圣容映之,永寿于万。’又撰元日及冬至进见之仪,行于世。”这两个习俗由来以久,不仅作为社会礼仪的实践,也凝聚了民族情感与品格。
艾斯柯(Florence Ayscough)的译本提取了汉字“椒”与“盘”的字面意义并加以首字母大写的方式来表示异域文化的专有名词“The Red Pepper Dish”,“颂花”典故则直接简化为实指“extolled in song”(在歌曲中被赞颂)。洪业(William Hung)的译本则作了更仔细的辨析:“以盘盛椒”之后需要把椒撮点于宴席的酒杯中,因此他称之为“pepper-wine”(椒酒),并用“songs and toasts with pepper-wine”(椒酒中的歌颂)来连结两个民俗。但雷克斯罗斯并没有拘泥于典故背后的传统,而用“green wine bottles and red lobster shells”取代,也许他的灵感正是来源于两位译者的措辞:椒盘为红、椒酒为绿,而他创造性地用“红壳的虾”与“绿瓶的酒”构建了现代美国民众的生活场景,把中国文化传统中典雅庄重的新年祝福,置换成了喧嚣热闹的狂欢气息。空酒瓶与龙虾壳散乱地堆叠,绿与红的鲜明色彩对比,彰显了美国大众饮食与娱乐文化,也渲染了诗人高昂的情绪与不羁的性情,译诗挣脱了传统的束缚而给予文本以当代经验的表达。
另一个典故“盍簪”指朋友聚合,出自《周易·上经·豫》 :“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象曰: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注曰:“处豫之时,居动之始,独体阳爻,众阴所从。莫不由之以得其豫,故曰‘由豫,大有得’也。夫不信于物,物亦疑焉,故勿疑则朋合疾也。”因此,这里的朋友相聚是同心所致,喜乐自来。艾译本处理为“all assembled are of one mind”(我们聚在一起,同心同意),回应了爻辞中的“勿疑”,强调了友人之间的心意相通;而洪译本则直接把“盍簪喧枥马”作为一个整体翻译为“I can hear from the stable comes noise of horses of the guests”(我能听到马厩里,宾客的马匹传来声响),甚至把友人淡化为了“guest”(客人)。雷克斯罗斯却别出心裁地增添了《友谊地久天长》(Auld Lang Syne)中的名句“Should auld acquaintance be forgot”(昔日故友怎能忘),歌名字面含义为“逝去已久的日子”,这里雷克斯罗斯采用了最初诗歌版本的低地苏格兰方言(使用了“auld”而非英译的“old”),在译入语文化中,同样起到了典故的作用。19世纪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的先驱罗伯特·彭斯(Robert Burns)记录并润饰了这首苏格兰民歌;在美国,从1929年起隆巴多小子都会在广播电台与电视节目上演奏《友谊地久天长》,这首歌便成为了美国民众迎接新年的标志。这句歌词传达了原诗中两个不可或缺的要素:家人相聚与辞旧迎新,但歌声的弥漫更渲染了岁末特有的时间流逝之伤感,“我们清晰地看到本土价值观被潜移默化地‘铭刻’进了异域文本,进而遮蔽源语文化。”或者再进一步说,是现世性的审美通过译者的独特情感铭刻进了汉语文本中,这是一种由于个体经验的介入而对传统独断论进行的反叛。
需要注意的是,我们不主张用异化(foreignization)来统括雷克斯罗斯的翻译,他的译诗在形式上表现为本土经验的“铭写”,但真正释放的是特定社会语境中的个人情感。这种个性化“铭写”需要借助解释项(interpretant)才能得以实现,韦努蒂认为“如果解释项能够引发对真理的思考、产生新知识和新的价值观,填补接受语境中站占主导地位的主流价值观的空白和空缺,那就是好的翻译。”实际上,雷克斯罗斯通过“解释项”把现代美国习俗注入到中国文化传统中,却又反过来使个体情感获得更具时间性的表达形式。
在这里,我们需要对这三个译本在翻译史中所处的位置作一个补充说明,进入20世纪前半叶,伴随着新诗运动,英美世界掀起了汉诗翻译的第一次热潮,正如汉学家葛瑞汉(Angus C.Graham)所指出的那样:“翻译中国诗的艺术是意象派运动的一个副产品,这是起始于1915年庞德出版的《神州集》(Cathay
)、1918年韦利(Arthur Waley)出版的《170 首中国诗》(One Hundred and Seventy Chinese Poems
)和1921年洛威尔(Amy Lowell)出版的《松花笺》(Fir Flower Tablets
)。”艾斯柯两卷本的杜甫传正是在这一阶段完成的,《杜甫:一位中国诗人的自传》(Tu Fu:The Autobiography of a Chinese Poet
)与《一位中国诗人的行迹:杜甫,江湖客》(Travels of a Chinese Poet:Tu Fu, Guest of Rivers and Lakes
)分别于1929年与1934年出版。尽管艾斯柯的翻译则执着于汉字追溯而造成颇多的漏译与误译,但她对杜甫其人的品质与孕育诗歌的文化语境给予了较多的关注,例如上述两处民俗的翻译可以见出艾斯柯兼顾了异质元素的保留与实际内涵的传达,推动了英语读者对杜诗的民俗背景有了更为立体的认知。20世纪中期之后,在第二次中国热的推动下,出现了许多名家的杜诗英译专集,在体量和质量方面较前一阶段都有了显著的跃升。得益于译者严谨的版本考据、成熟的翻译技巧与卓越的审美表达,这些译作在美国现代诗坛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力,在学界,葛瑞汉、宇文所安与叶维廉等汉学家也纷纷在英语环境中致力于杜甫诗歌的研究。这一阶段重要的译本包括洪业在1952年发表的《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Tu Fu:China’s Greatest Poet
)与霍克斯(David Hawkes)在1967年出版的《杜诗初阶》(A Little Primer of Tu Fu
),两位译者皆为著名学者,因此作品都集杜诗的介绍、翻译和研究三重功能于一体,因此洪译本除了译诗与简介,还有注释的单行本。雷克斯罗斯正是在20世纪中期开始着手他的翻译工作,那时汉学家译者已经占据了译界的主流,他呼唤诗人译者的回归,是希望翻译能够摆脱对源语文化传统的执着,而是给诗歌语言打上时代的烙印来孕育诗人个性化的生命力。他在《爱与流年:续中国诗百首》(Love and the Turning Year:One Hundred More Poems from the Chinese
)的序言中明确表示:“近15年(1955——1970)来出版了成倍的译作,虽然学术水平提高了,但作为诗歌,近来的译作都比不上之前庞德、戈蒂耶(Judith Gautier)、克拉邦德(Klabund)、宾纳与洛威尔的那些。”因此,“诗人译者”的呼吁是不仅是对翻译史进程的一种反思,也是翻译理念的一次更新,诗人译者的介入意味着诗歌翻译从知识本位走向了美学本位。雷克斯罗斯能够不再背负着对中国文化进行“授业”与“解惑”的任务,而是可以结合时代语境与个体风格,抛却传统的制约而深入杜诗文本内部进行个性化的阐释。这不仅可以使翻译重新回归文学的审美性,还能够直抵两种不同文化的汇通性,他的译诗反映了杜诗翻译从忠实转码向个体诠释的倾斜,折射出一种更为敞开的文学样态和诗学观念,这也是上述典故三种翻译样式背后的翻译史根源。雷克斯罗斯把现世性的审美意象作为民俗文化的解释项,完成了异域文化与本土价值的整合。如果说传统民俗是历史传统的日常化体现,那么个性情感则需要与时俱进的日常化表达,这一手法摆脱了传统的枷锁,而使置身于当下语境中的个体获得时代性的诠释。
结 语
雷克斯罗斯作为一位诗人译者,在翻译史、翻译理论与美学理论的交汇视域中,通过翻译与诗学的双向互动完成了对“非个性化”理论的颠覆。他的双重性身份推动他反思诗歌的审美需求与文化的价值差异,通过拣选异域文本并发挥主体性制定相匹配的翻译策略,在异质美学的创造性诠释中解放了个体情感,同时也把第一人称唤回了诗歌文本。
本文引入了诗人译者身份立场,解析其身份双重性形成的原因与特点,并结合20世纪前半叶美国诗歌发展背景与《中国诗百首》在杜诗英译史中所处的位置,讨论雷克斯罗斯针对“非个性化”理论及其背后的价值取向所展开的反叛。他通过对这一诗学理论的内涵进行反思,包括主客体关系中所反映的人与世界之相处、情感普遍性与个别性以及传统与个人的意义三个方面的问题;他在杜诗英译实践中探索新的表达手法、审美思想与价值观念来予以挑战,其核心是挖掘个体情感的价值意义与美学效果;为此,他总结出“中国诗法则”与诗境创造方法来连结意象、主体与世界的关系,梳理情感的不同棱面并在拣选与想象中发现多重可能性,并且在对日常化与现世性的关注中完成个性化情感的细化与丰富。
雷克斯罗斯的审美思想也在个体情感的探索过程中也日趋成熟与完善,本文通过考察诗人在本土语境中的艺术实践、美学思想与哲学影响,总结出他的诗学立场是基于对情感的知觉观照与自然有机体的追求;而作为译者的雷克斯罗斯在中国古典诗词中找到了更为深刻的根源,于是他在转码中尽可能地探索新的表达手法以彰显这些精神的内核,而这又成为了他翻译的基本立场。论文通过具体文本的技术性分析与不同译本的比读,详细地演绎与归纳了雷克斯罗斯为了个性化情感的表达而采取的翻译策略,并且深入探讨了他在翻译策略中所投射出的诗歌美学思想。
在雷克斯罗斯对“非个性化”理论的反驳中,我们清晰地看到了收录于《中国诗百首》中的35 首杜诗英译整合了异质性与本土价值,杜诗的翻译使异域文化跨越了时空对诗人译者的美学思想进行渗透,从而对其产生撼动性的影响作用。通过特殊的翻译策略,雷克斯罗斯为异域文化引入了差异的审美价值,以抵抗作为柏拉图主义延续的“非个性化”理论,使用中国古代诗学思想推动本土审美观念的转向,也在透视中完成异质性的本土诠释;同时,本土话语并没有被完全抛弃,而是作为历史性印迹成为个体情感的时间底色。这个过程也详细地展示雷克斯罗斯借助翻译进行价值修正的历程,不仅丰富了个性化的内涵意义与表现方式来颠覆权威理论,还在两种文化的视域融合中完成了审美转向,在诗学体系的汇通中重新发现了个体情感与生命存在,从而达成了一位诗人的反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