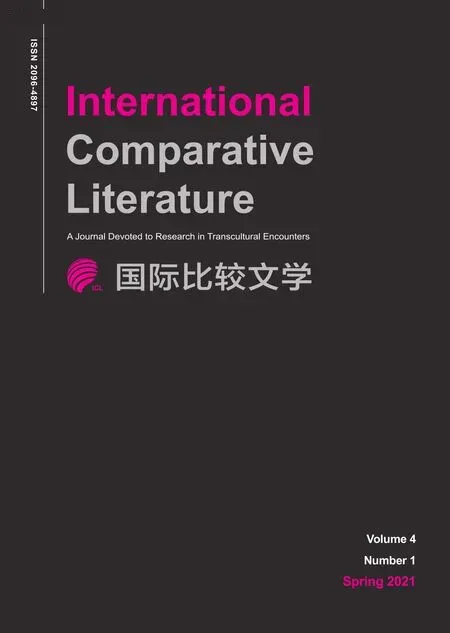娜塔莉·海因里希:《艺术为社会学带来什么?》,何蒨译
《艺 术为社会学带来什么?》一书的作者娜塔莉·海因里希(Nathalie Heinich)是法国当代著名的社会学家,她师承另一位享有世界性声誉的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自然,我们可以将海因里希的学术渊源追溯到布尔迪厄的社会学。的确,海因里希一开始是追溯布迪厄的路径开始其学术生涯的,她早年是布尔迪厄的忠实信徒,但正如每一个后来者总试图摆脱前辈对自身影响的焦虑以获得自我认同,海因里希也在上个世纪80年代前后与布尔迪厄的“批判性社会学”(critical sociology)分道扬镳,开创自己的“阐释性社会学”(interpretive sociology)。而这本《艺术为社会学带来什么》正是她首次正面建立自己的社会学概念,摆脱布尔迪厄的影响(甚至反其道而行之)的转折之作。
在海因里希之前,布尔迪厄的社会学分析范式是最为盛行的,其认为社会的本质是集体性,个人维度是虚幻性。因此,康德美学观下的无功利的“艺术自治”的普遍法则被布尔迪厄揭示为特殊阶级的阶级趣味。布尔迪厄认为,这些所谓的美学品质并非自然而然的,而是特定社会文化条件所生产的。审美的自主成了一个毫无意义的虚幻性概念,艺术家的个人天赋以及艺术品的审美品质都成了需要 “去魅”的对象。海因里希将这种经典社会学的立场,称之为“社会学式”(sociologiste)立场,持有这一立场的是我们熟知的霍华德·贝克(Howard Becker)、皮埃尔·布尔迪厄、雷蒙德·穆兰(Raymonde Moulin)等经典社会学家。
海因里希认为,另外一类与之相对的艺术社会学分析范式来自美学家,美学家出于相反的立场,“坚持审美本位,认为社会学从属于人类常识,因此强调艺术无法被还原为社会性解释”。那么,哪些人会是海因里希所指的美学家呢?海因里希并未马上在书中吐露,但我们或可对应于卢文超所提及的卢卡奇、戈德曼和阿多诺等传统艺术学家,亦即“艺术——社会”学家,他们对艺术与社会关系的讨论重点不在社会学而在艺术,其根本目的不是为了发展社会学,而是为了评判艺术作品。
海因里希认为,这两种立场体现了共同性和独特性两种价值体系,尽管这两种价值体系从内容上看是对立的,但他们确认自身价值的方式是相似的,都以批评他者而确立起自身价值的合法性基础。不过,海因里希指出,这二者并非不可调和,或者说,也只有二者调和才能更好地阐发艺术的基本概念和命题。比如说,艺术家天赋的基础在两种价值体系中有完全对立的解释,一者认为天赋无法还原为他人的影响,一者认为天赋乃是制造不平等的理论虚构的结果。海因里希则将它描述为“一种资源的倾注:‘倾注’意味着劳动,是一种历史过程,‘资源’则暗示了人与人资质秉性的不同”,由此调和二者。海因里希实质上给出了一条连通两种不同价值体系的新的艺术社会学路径,“社会学家的作用是观察上述两套理解方式的意义和价值结构,了解行为者如何采取行动和解读这些意义结构的”。
由此,海因里希从布尔迪厄的“占位”策略中撤出,从带有学科优越性的话语霸权中撤出,重新回到马克斯·韦伯的“价值中立”,或者说回到诺贝特·埃利亚斯的既“介入”(involvement)又“疏离”(detachment)的双重立场。有别于布尔迪厄的批判性立场,海因里希认为社会学的目标不是为了“揭示”假象背后的真实,不是去批判任何主导结构,而是去分析和描述这些结构是如何发生和具体运作的,价值判断和系统是如何被行动者定义、合法化、失效、建构、解构或重构的。海因里希的最终目标是完成社会学的范式转换,即从布尔迪厄的批判性社会学转向阐释性社会学。
可以说,《艺术为社会学带来什么?》是海因里希关于其自身社会学方法论的一本书。这本书正面陈述了她为当代社会学提供的独特视角:从艺术来回望社会学。用达格玛·丹科(Dagmar Danko)的话说,在这本书中,海因里希实现了清晰的转变:从一种艺术社会学(a sociology of art)到一种从艺术出发的社会学(a sociology from art)。她所感兴趣的并非是美学家对艺术的审美兴趣,而是藉由艺术价值的问题促发对社会学学科本身的追问,其最终所要探究的是一种价值的社会学(a sociology of values)。而整本书所回答的“艺术为社会学带来什么?”的问题,实际上是“社会学何为?”的回答。
在社会学研究的所有领域中,艺术与社会学最为疏远,艺术似乎总是强调主体性、灵感、个性、私域,而社会学总是强调集体的、无个性的、公共性的。海因里希指出,无论是布尔迪厄的市场、场域、习性,还是霍华德·贝克的艺术界,亦或是卢卡奇、豪瑟、戈德曼等人的研究,都体现了这种经典的“社会学式”的还原方法,将艺术的独特性以“普遍式还原”的方式还原为经济环境、社会阶层或是习性。以霍华德·贝克的《艺术界》为例,海因里希指出,这本书通过交互性研究说明了艺术创作的集体特征,但是这种典型的“社会学”立场却忽略了艺术领域的独特性,即艺术特有的想象力及象征特征,也就是说,贝克虽然满足于将研究对象解释得无比清晰,却唯独没有触及这一对象的本质。海因里希的这种质疑在分析美学家沃尔海姆那里有所回响,海因里希对贝克的批评与沃尔海姆对迪基的艺术体制论的批评相类,沃尔海姆认为迪基的艺术体制论中也呈现这样的混淆,把“艺术如何被制造成艺术”的外在论混淆成“艺术何以成为艺术”的内在论,但这样一来,迪基的理论贡献就只是一种艺术的“体制”论,而非“艺术”的体制论。迪基面临着与贝克等人相似的困境,其理论中缺乏对艺术的特殊本质的关切。
因此,从艺术来反思社会学,就是反思这样一种“社会学式”的还原是否可行的问题。在艺术领域中,社会学面临的这种不可还原的阻力最大,因为艺术家的天赋以及艺术品的美学特质都被视为“不可还原的”,这就给反思社会学的还原方法提供了最大的可能性。当社会学家勉力去推进这种“还原”时,就与我们对艺术的常识相去甚远;当社会学家勉力从个别现象中挖掘普遍性时,就无法为艺术的独特性进行辩护,也使它无法为艺术和其他领域的“区分”提供清晰的辨识。正是由于经典社会学的还原式的方法在对待艺术时遭遇困境,最大限度地暴露了其本身方法论的弱点,最终被证明是需要反思和拒绝的。
海因里希指出,既然认同类似于艺术等其他领域的特殊价值,那么社会学就不应当高高在上地去质疑其他领域的立场,“即不再致力于论证或否定某类价值秩序,而是尝试理解行为者如何构建这些秩序,如何在言语和行动中证明和实现这些价值”。如果说布尔迪厄的社会学方法是将其他领域对象化并予以批判,那么海因里希所做的是去理解和认同他者的价值,然后对之进行现象学式的描述和分析。因此,海因里希的“非批评”的立场就相当于胡塞尔现象学式的“加扩号”,将一切先行的价值预设都悬搁起来。海因里希认为:“这种新立场更关注争议问题及‘事件’,属于研究价值观的社会学(科学或伦理价值观)。非批判立场并不认为任何冲突都可以还原为‘寻找与众不同的策略’、行使‘象征暴力’、或是‘合法者’对‘不合法者’的‘支配’(引号中都是布尔迪厄的概念),而是试图呈现多样化的行动维度,以及他们判断科学真相或伦理价值的公理依据。”
一旦放弃了还原主义的方法论和立场,艺术社会学也就可以关切到美或原创性问题了,但这种对原创性的关注并非要回归美学的艺术本体论路径,而是转移到对艺术生产和接受过程的分析,“分析的目的并非追问什么是艺术,而是艺术对行为者‘代表’的意义(这里,‘代表’的含义更加宽泛,包括分类、解读和判断的角度及过程,区别于‘本质’或‘事物自身’的概念)”。海因里希认为,这时候艺术学的对象就不再是艺术的内容,而是构成艺术现象的所有话语和行为。在此,海因里希为艺术社会学开启的新路径的方式并非依赖于新的经验事实的发现,而是一种方法论上的转换,是一种现象学的目光转换,即把社会学的目光从意向对象转换为意向性过程。显然,海因里希认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不应再是固定的艺术品,而是构成艺术现象的一整幅活动着的图景。可以说,艺术社会学的考察发生了从“物”到“事”的转变,也就是从对象到发生的转换。
当社会学放弃了还原主义,并准许把艺术现象的整体收入眼中时,社会学就有了为艺术独特性找出缘由的机会。这时候,社会学家的任务就不再是把伟大艺术家独特的秘密“揭示”出来,而是去描述独特性是如何在社会条件下被建构的。当社会学家的任务不再只是去揭示事实的真伪,而关注建构的过程时,就更能使得艺术作为象征体系的形式结构浮现出来。之前社会学家将社会学的还原作为“事实”以此建立起为其他学科确立规范性法则的话语特权,然而,新社会学家则试图从艺术领域的独特性的建构性本质,反观“社会”或“社会的”建构性本质。也就是说,新社会学家除了揭示他者的价值基础建构的根基,也揭示自我的价值基础建构的根基,亦即任何普遍性话语,包括社会学的“社会”,也只是某个价值群体在一定历史条件下运作的话语,是某种“实体化隐喻”。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并不比艺术更为“实在”。因此,实证主义的、还原论式的社会学研究不是唯一对事实的表征,而只是描述现实的方法之一。
海因里希认为,经典社会学的普遍还原的方法不仅具有虚构性,而且极大地伤害了艺术的独特性,因此我们要寻找新的社会学的方法和立场,这就是描述的方法和多元主义的立场。描述的方法和人种学的方法相似,它们观察的对象是行为者对自己的行为赋予意义的过程:“我们可以看到,这种立场的转变为社会学带来很大变化,从对行为和信仰的解释,转变为对行为系统和意义系统的阐释,强调描述,而非规范。”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海因里希所寻求的新立场的转变实际上可以视为知识分子角色的自觉转变:“这种立场转换,要求社会学换一种方式质问学科的社会角色,或者说,换个角度理解知识分子如何介入社会。”在这里,海因里希呼应了齐格蒙特·鲍曼对知识分子角色的“立法者”向“阐释者”的转变。因此,海因里希所做的是对社会学家这个知识分子群体的自我反思:社会学家作为知识分子的一员,到底在面对其他知识领域扮演什么角色呢?以布尔迪厄的“批判性”立场来看,他首先赋予了社会学家面对其他学科的“立法者”特权,认为其他经验现象的独特性都不过是由社会学的普遍法则决定的,艺术那点“灵韵”和“自主性”,在布尔迪厄那里更是消弭无形,被最终指为“幻象”。
毫无疑问,布尔迪厄等社会学家的任务是对审美主义者所建立的艺术的特殊性神话进行祛魅,他将社会学家摆在了高于艺术家之上的“立法者”位置。然而这种“立法者”的位置本身不应当被审视吗?正如鲍曼所揭示的,知识分子享有的“立法者”的位置并非天然,而只不过是启蒙时期具有显著的现代性特征的“知识/权力”的共生现象。这种模式的知识分子角色在一定时期占据主导地位,它许诺某种普遍的世界观。毫无疑问,经典社会学家就致力于将普遍化原则凌驾于其他学科之上,由此建立起自己还原主义的方法论和高高在上的批评立场。但是,普遍性原则并不是天然的事实,而只是一种社会学家据以维系自身话语特权的价值判断。在现代性时期,它似乎充当了为其他学科立法的权力,可是随着后现代性的来临,“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没有任何一个学科和知识团体享有这种“立法者”的特权,“典型的后现代型世界观认为,世界在本质上是由无限种类的秩序模式构成,每种模式均产生自一套相对自主的实践。秩序并不先于实践,因而不能作为实践之有效性的外在尺度”。经典的社会学总是自命为秩序的制定者,但却不能去理解每一种自主性实践的内在意义,因为这套社会学方法无法理解“意义共同体”。与之不同,海因里希将社会学带向新的方向,“不在于给出解释,为(普遍)原因与(特殊)结果建立联系,而是给予阐释,即呈现不同类型的意义系统之间的内在逻辑和连贯性”。换句话说,海因里希认为,社会学家并不是真理的执仗者,能够去除意义从而筛选出所谓的事实,而是去理解那些自治系统内部如何建立起一系列的意义的连贯性。
正因为社会学的角色在于去理解其他系统内在意义建立的可能性,海因里希也就放弃了先前的“唯社会学”立场,赞成价值上的多元主义和相对主义立场,或者说,这可以视为社会学的一次实用主义转向。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尽管海因里希放弃了批判的立场,避免价值判断,从而回到了韦伯的“价值中立”,但并不是说社会学家完全放弃了价值观。海因里希小心翼翼地把自己的立场界定为介入式中立,也就是说,她强调了价值中立的行动效应,“韦伯式中立不是一个事实,而是一种价值观,即一整套行动和判断的程序”。因此,她认为她所持有的中立不是为了保持某种架空行动的好姿态,而是指出哪些是社会学研究的好方法。也就是说,当社会学家以研究者身份介入时,应尝试是去理解和解释社会,并避免价值判断。而只有当社会学家能用自己的身份和分析能力指导和推动更好的方向时,这种介入才是值得肯定的。
海因里希实际上为社会学提供了一种“友爱的伦理学”,将布尔迪厄带有霸权式的社会学话语转为了聆听艺术这个“他者”的友爱之音。在海因里希这里,其他学科不再是社会学亟待征服的对象,而是一个可以共同对话、结伴前行的相互理解的友人。正如鲍曼所说:“阐释者角色由形成阐释性话语的活动构成,这些阐释性话语以某种共同体传统为基础,它的目的就是为形成于此一共同体传统之话语,能够形成彼一共同体传统之中的知识系统所理解。这一策略并非是为了选择最佳社会秩序,而是为了促进自主性(独立自主的)共同参与者之间的交往。”可以说,正是这种立场的转变,让社会学可以召唤其他学科对话,从而拓宽了社会学本身的研究空间,使其走出专业封闭。在海因里希看来,老的社会学立场的“封闭性”,“恰恰属于社会学批评的对象,也即一种固化的认知模式,我们也可以称之为社会学意识形态”。
最后,海因里希所要做的,实质是对布尔迪厄一代现代型知识分子普遍化的批判性立场的再批判,即将批判本身作为批判的对象。海因里希显示了鲍曼所言及的后现代型知识分子特质,他们用“阐释”替代了“立法”。作为阐释者的社会学家,更多不是以超脱立场去揭示常识的非真性,而是去尝试理解艺术领域中的常识基础。与布尔迪厄代表的西方左派的激进批判立场相比,海因里希更温和地在西方左派和右派价值力量配比方面进行调和。对此,她提及当代知识分子对本雅明的痴迷,乃是基于他们想要同时保留民主传统中维护公共利益的价值观和来自大贵族大资产阶级的现代审美倾向的需要。也就是说,这类知识分子希望能在先锋主义与大众民主之间进行调和,进而达到某些平衡。无疑,相对于布尔迪厄等经典艺术学家致力于制定各种法则,海因里希却更多强调策略性,她指出了策略对于促进不同自主领域的交往的意义,“这一策略并非是为了选择最佳社会秩序,而是为了促进自主性的(独立自主的)共同参与者之间的交往。它所关注的问题是防止交往活动中发生意义的曲解”。
因此,“艺术为社会学带来什么”的题意,并非重归卢卡奇和阿多诺的美学路径,用审美主义来替代经典社会学立场,并非在审美和社会之间做非此即彼的选择,其重点是借由“艺术”这面哈哈镜来反观社会学自身的短处,对经典社会学进行自我反思。对此,海因里希借鉴了哲学领域的认识论范式转换,比如唯实论向唯名论的转变,从欧陆现代哲学传统中的形而上学向现象学的转变,以及盎格鲁–撒克逊传统中从形而上学向普通语言分析的转变。她的新艺术社会学路径亦是从本质分析过渡到意义分析的尝试,“从这一角度出发,‘社会’的普遍性或‘艺术作品’的特殊性,科学原理的客观性或伦理法则的普世性,都不再被认为是事物固有的本质,而是行为者常识竞争的结果”。很明显,与经典社会学只致力于对特殊性神话的美学路径的祛魅不同,海因里希的新艺术社会学致力于对“社会”和“特殊性”双重祛魅。当然,她的祛魅方式并不是以某根规范性的权杖去暴力“揭示”艺术特殊性神话的假象本质,而是明确和挖掘假说形成的因由,并且解释这种假说的功能。假说本身应当被中性地描述,而非通过打破假说来抵达真相。因此,海因里希认为艺术社会学家要做的是显示创作者及作品的独特性是如何在现实、详细或象征体系中被建构的,她最终想要建立的是对这种独特性进行辩护的社会学,即所谓的“例外性的社会学”。通过将“例外”置入共同性事物的根基上,来呈现艺术独特性的运作机制。
由于海因里希的最终目标是建立能够辩护艺术独创性原则的艺术社会学,因此她认为社会学家在阐释艺术时,必须调和经典社会学的“他律”说和美学的“自律”说之间的张力,艺术作品应当视为“相互作用物”(interagissant)。在此,我们可以看到海因里希思想中所回响着的当代反基础主义的哲学之音,对此她借鉴了拉图尔的“行为体”(actants)概念,将艺术作品引发的各类行为考虑到艺术特殊性形成中。此外,海因里希还受到实用主义思潮的影响,认为多元主义和相对主义将替代规范性的普世判断,显然,这更加印证了海因里希乃是一位鲍曼所称的后现代型知识分子。
可以说,整本书中海因里希都不断显示其超越经典社会学的“普遍性”迷思的雄心,并小心翼翼地防御自己重归审美主义的老路。无疑,她对经典社会学的还原主义的反思,为社会学到底如何对待艺术提供了诸多珍贵洞见。不过,由于这本书的篇幅太过单薄,海因里希留给我们的更多是宣称,而缺乏更可以落实的关于其新艺术社会学的具体建构方案。因此,海因里希或许较好地扮演了两个相互竞争的队伍的裁判,却未能在此书中展示自己如何下场竞争的实战经验。另外,海因里希对多元主义和相对主义优于普遍性的宣称,会否产生新的危机呢?按照海因里希的立场,真相是否终会沦为不断重演的建构主义游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