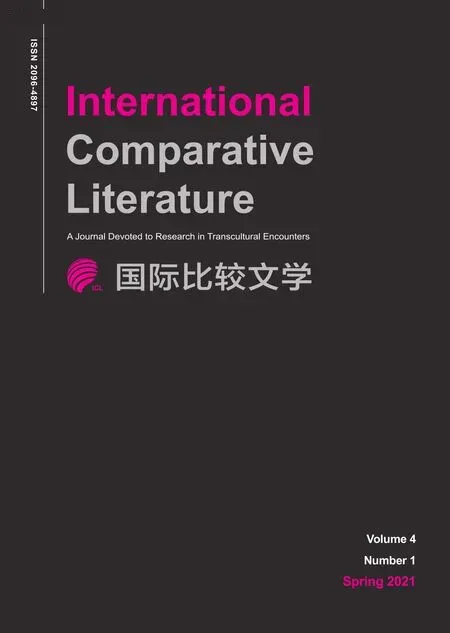童明著:《解构广角观:当代西方文论精要》
一、德里达的名声
1992年3月,在剑桥大学一次内部会议上,一项荣誉博士的提名引发了激烈地争议。提名的对象是当时已在全球范围内享有盛名的德里达。这项提名引发的抵制,让人很容易想到1985年牛津大学拒绝授予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荣誉博士学位。
火上浇油的是,5月9日的《泰晤士报》,刊登了一篇来自多个国家十九位哲学家的联合署名文章《一个荣誉问题》。其中就包括美国著名哲学家奎因(Willard Quine)、法国数学家勒内·托姆(René Thom)等。抵制者除了抱怨德里达的著述晦涩难懂,“似乎主要由一堆复杂的笑话和双关语(‘逻辑阳具’logical phallusies 之类)构成”([英]西蒙·格伦迪宁著,李永毅译:《德里达》,南京:译林出版社,2019年,第14 页)外,更是担心德里达的破坏力,德里达充满虚无主义和达达主义意味的奇技淫巧,“否定和摧毁了奠定所有大学学科基础的证明与论辩水平”。 ([法]伯努瓦·皮特斯(Benoît Peeters)著,魏柯玲译:《德里达传》,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403 页)
在5月16日的最终投票中,剑桥还是通过了这一提案,授予了德里达荣誉博士。剑桥事件可算是德里达一生处境的缩影,盛名之下,批评与误解不断。1999年在一次关于有史以来最被高估的哲学家票选中,德里达高居榜首。
德里达事后称剑桥事件是一次“严肃而滑稽的战争”。其实,是德里达先对西方思想发动了一场严肃的战争。1966年10月,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一次学术会议上,德里达发表了一个演讲,“Structure, Sign and Play in the Discourse of Human Science”,由此揭开了这场名叫“解构”的战争的大幕。
二、解构的广角视野
德里达之所以备受争议,其思想的冲击力是一个原因;难读,容易被误读,也是原因。尽管每个时代的人们往往会落后于时代先知者思考的脚步,但假以时日,也会慢慢读懂他。学界如今已经认可德里达的价值和地位,“他是这个时代最重要的思想家——我们甚至可以说,这个时代已变成解构的时代”。 ([英]西蒙·格伦迪宁著,李永毅译:《德里达》,南京:译林出版社,2019年,第6——7 页)关于德里达的研究,在学界已成显学,优秀著述所在多有。但童明教授的新著《解构广角观》,在诸多有关德里达的研究中,还是有其特出之处,可助我们更好地读懂德里达。
《解构广角观》,接续了童明教授《现代性赋格》所开启的问题,从现代性问题“接着讲”。《现代性赋格》讨论的是在现代语境中启蒙现代性(体系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文学现代性)的形成及其关系,尤其揭示了文学现代性的反思价值及其意义。《解构广角观》则接续着对现代性问题的思考,梳理了“解构”这一“西方当代思辨理论的基石”的内涵及其来龙去脉。贯穿两部著作的连接点是尼采。他既是文学现代性的思考者,也是解构的主要源头。德里达就是对“尼采式转折”所开启的思想道路的继承和发扬。
《解构广角观》和《现代性赋格》这两部书的联系不但在问题的脉络上,还体现在方法和视角上。“赋格”是音乐术语,《现代性赋格》强调的启蒙现代性与文学现代性间的复调关系;“广角”是视觉术语,强调的是观察视界的扩展,在《解构广角观》中突出的是对解构理论的开阔理解。
所谓“广角观”,就是不局限于德里达去理解解构。德里达身上贴着解构的标签,有人就把解构等同于德里达。但德里达之前之后及之外也有解构,解构有广义和狭义之别,要想真正理解解构,还需以广角观之。德里达以尼采、弗洛伊德、海德格尔为解构的思想先驱。童明教授在书中除了分析这些先驱者之外,还分析了拉康、罗兰·巴特、耶鲁派、克里斯蒂娃等理论家对于解构的发挥,以及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夫卡、福楼拜、伍尔芙、福克纳等作家作品中的解构意味。更值得提及的是在中西比较的语境中分析解构,标举出中国古代思想中的解构精神。在广角视野中的解构,不再是一家一派之学说,而是一种思辨方法和思想智慧。
三、逻各斯中心主义与解构
解构(deconstruction)所“消解”的“结构”,不是所有的结构——就像“野路子”(on the wild side)的耶鲁派所主张的那样,而专指由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所建构的逻各斯中心主义的结构。在柏拉图的哲学中,超验世界乃是真实世界(the real world),理念中的床具备高于现实的床的真实性,经验世界只是对于理念世界的模仿。理念为“在场”(presence),现实为“不在场”(absence),在场为尊,不在场为卑。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强调言说(speech)和书写(writing)的区别与对立,言说之字(the word of speech)出自理性,代表真理,是理性的言说(the speech of reason),即为逻各斯(logos);书写之字(the word of writing)来自现实,只是理性的“影像”,远离真理。逻各斯中心造成了哲学与文学、理性与情感、理念与现实的分裂。
尼采反思了西方传统,认为西方问题的病根就在苏格拉底。尼采挖掘被理性压抑的酒神精神,呼唤实践音乐的苏格拉底,就是在解构西方的理性哲学传统。德里达接续了尼采的解构精神,对逻各斯中心和声音中心主义进行了持续的批判。索绪尔把语言符号分为能指(signifier)和所指(signified),能指是声音和形象,所指是概念。在逻各斯中心主义思路中,所指高于能指,语音高于文字。德里达的解构,认为能指和所指的关系并不固定,在不同语境中两者会形成不同的关联,能指和所指的表意关系因此绵延不断、变化无穷,这就是延异(différance)。德里达认为传统语言观念是用在场(语音)的错觉掩盖了不在场(文字)的差异,他打破了语音和文字的主次关系,语言符合只是先验所指不在场的游戏。解放能指,也就解放了语言,让语言回归到自由的游戏状态之中。
解构的对象并非逻各斯本身,而是逻各斯中心主义(logocentricism),以及基于此而建立起来的绝对真理、专制思想、等级秩序和暴力秩序,希望通过自由游戏(freeplay),释放能指的活力,从而使“逻各斯中心的封闭结构转化为语义开放的表意过程(open-ended signifying process)”。
童明总结解构的要义说:
解构,是一种富有创意的解读和写作方式,它针对压迫性的、逻各斯中心的结构,视其中心为非中心,由此展开能指的自由游戏,揭示逻各斯秩序的自相矛盾,以此将封闭的结构化为开放性的话语。(本书第5 页)
解构的天然场域是文学。尤其是现代文学,大多排除了真理的“讹诈”,充分发挥了语言的自由游戏功能,作品(work)成了文本(text),从而有了更灵活和自由的游戏状态。作者和读者的关系也被相对化,作者不再是上帝般的创造者,读者也不再是被动的接受者,阅读本身就是一次新的重写。解构的智慧运用到文学中,生发出了许多批评理论和视角,本书结合一些作品有很多精彩地分析。
四、解构的误读
德里达在选取解构(deconstruction)一词时颇费踌躇,他或许担心的就是这个词身上所携带的“破坏性”。有人就会将它看成是destruction,摧毁,这让人触目惊心。2001年9月12日,德里达在复旦大学演讲,前一天美国发生了震惊世界的“911”事件。德里达一夜未眠。在交流一开始,有人就向德里达抛出了一个尖锐的提问:
您所说的解构摧毁了一切,那么摧毁之后如何建构呢?另外,我想问一下您对刚刚发生的纽约的恐怖事件的看法。
把解构的“摧毁”和“911”事件放在一起,这一提问来者不善。人们会本能地反感和恐惧任何的“摧毁”,哪怕是理论中的。德里达赶紧“辩解”:
我从来没有表示过解构就是摧毁,解构不是摧毁,不是在摧毁一切后建立一个新的东西,不是这样。(杜小真、张宁主编:《德里达中国讲演录》,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第145 页)
德里达似乎一生都在做这样的“辩解”。不是他的著述写的不清楚,而是读者的误解太深。解构自其诞生之初就遭受到诸多敌意、误读和批评,除了历史中常见的原因——思想和社会的错位,时代尚听不懂先行者的声音——之外,也在于这一思想本身的复杂。解构常被看作是摧毁、破坏、消解和否定等。
解构会让破坏者兴奋,许多观点假德里达的名义横行。比如有人认为,在解构主义看来,“任何[文学]文本都不可能有一个固定和稳定的意义”(Chambers Dictionary
)。任何文本都有其结构,德里达针对的是逻各斯中心主义的结构,这种结构号称真理,却压制真正的思辨。有人搞乱了战场,以德里达的解构之名来消解所有结构,这恰恰是德里达所反对的。这样的解构是伪解构。童明教授在书中就反复谈到了大众及学界对于解构的误解,比如说解构常被视为是解读的自由化,任何文本都被认为没有确定的语义。岂知这种貌似解构的相对主义思路,是将相对主义绝对化,而绝对化的相对主义,其实就是绝对主义,这正是解构要去破除的逻各斯中心主义所形成的绝对真理和专制思想。
尼采的解构背后有对于生命的关怀。尼采质疑了整个西方的理性哲学传统,否认“真理”,但不是在走向破坏和虚无,他肯定的是生命:
生命,首先意味着一种酒神生命观,或言大生命观,也就是那超出个体生命甚至人类局限而贯彻宇宙之间那一股生而灭、灭又生、源源不绝、千变万化、无穷无尽的生机,在此基础上肯定生命的各种任务(tasks of living)。(本书第8 页)
德里达延续了尼采对于生命的肯定。
五、解构与传统的重释
以“广角”来理解解构,另一方面的体现就是“将解构深入中国语境”,尤其是将解构放置于中西比较的思路下加以关照。解构不止存在于西方,中国古代亦有解构的智慧。中国也有“逻各斯中心思想”,尽管与西方的形态不同。逻各斯中心形成了严格的等级思想与压迫性的真理结构。但中国古人亦有天然的解构方法,利用文字的自由游戏,消解处于一尊的真理与权力的权威。代表者就是老子:
老子和解构相通之处,具体的一点是:文字符号是喻说性的,能指和所指的关系是不确定的;文字符号在不同的组合中形成差异,表示不同的语义。(本书第160 页)
童明教授在论述中西解构时,更是在讨论中西文化比较的大问题。在比较“逻各斯中心”与“道”,“说西-道东”之后,利用解构的思想遗产来反思中国古典哲学的重释与更新问题。作者出入中西,探赜赏要,应变知微,学问背后的中国情怀在在皆是,尤令人感佩!
本书的文字一如既往地好读,童明教授的文字兼具学人之博与文人之雅,诗性与思性兼备。他与自己一向推重的尼采一样,认为文体和理论同样重要。在这样的文字表述风格中,他也在坚守着解构的自由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