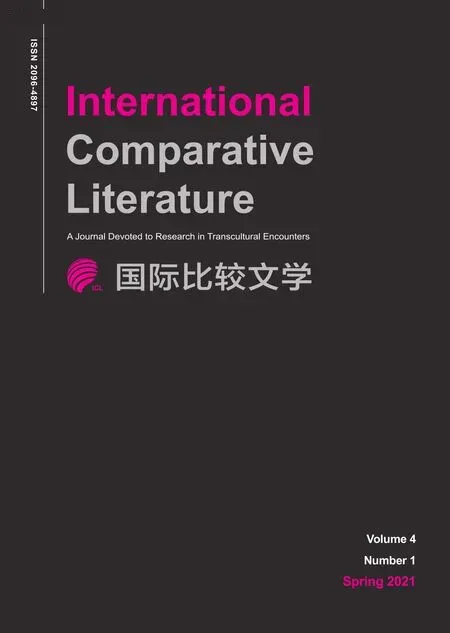历代小说僧尼形象之演变与社会风习*
王子成 宁波大学
僧尼是社会人群中的一类。在历史社会生活中,最初的僧尼当以恪守佛教清规戒律、甘于寂寞、苦苦修行的形象展露在世众面前,受人尊敬,令人膜拜。但随着时代的不断向前,社会生活的不断变化,僧俗之间的社交日益频繁,于是有相当数量的僧尼经不起世俗生活的多方诱惑,公然做出败坏山门、违法乱纪的事情,令人切齿痛恨。而古代小说文献则形象地反映了历代僧尼的演变情况。下文将概述其演变情形,并简析其演变的社会历史根源。
一、历代小说之僧尼形象及其演变概述
现代意义的“小说”概念始于唐代,而颇具文学形象意味的“僧尼”这类人物角色,亦始见于唐代的文学載集,此前的“僧尼”多为史籍里记载的真实出家人,大多系高僧大德而带有人物传记性质的记载。自唐而后,包括各类文学文献所收的小说,皆有不少僧尼形象的描写,既有正面的,也有反面的,但明清小说中所描写的僧尼形象大多为淫僧淫尼,其数量远超此前各朝各代小说中所写。从小说文献所描写的时代先后来看,淫僧淫尼形象则体现为在数量上由少到多,在描写上由简及繁的变化,而中国古代小说文献客观呈现了历代僧尼形象演变的轨迹。
(一)佛教史书中的高僧大德形象
高僧大德形象主要见于历代佛教史书中,而最具代表性的对高僧大德形象记载的佛教史书,当首推释慧皎的《高僧传》,其次为梁宝唱撰的《名僧传》。而《名僧传》虽然是中国佛教史上最早的一部僧传著作,但它在中国早已失传。今所见摘抄本《名僧传钞》(一卷)系《名僧传》传入日本后,被藏于东大寺东南院,由宗性于日本嘉帧元年(1235年)五月所作的摘抄本。《高僧传》所收,皆为学修高深、德行高尚、技艺高超的僧侣。而《名僧传》所载,在慧皎看来,有的名僧未必有真实的修养和学问;而有真才实学之人,又未必能知名当世。即如《高僧传序录》云:“……自前代所撰,多曰名僧。然名者,本实之宾也。若实行潜光,则高而不名。寡德适时,则名而不高。名而不高,本非所记;高而不名,则备今录。”所以晚出的《高僧传》所载高僧,明显要比《名僧传钞》所载少数十位僧人。
其实,《高僧传》不载而《名僧传》所载的僧人中,亦有既名且高者。如卷十的昙恒,学识广博,德行孤高,专志念佛,终于成就。《东林传》有云:“昙恒,河东人。童年依远公出家。内外典籍,无不贯通。德行清孤,常有群鹿驯绕座隅。自入庐山,专志念佛。义熙十四年,端坐合掌,厉声念佛而化。”
总之,佛教史书中虽然是记载高僧大德形象以表达作者和佛教信徒的称扬之意,鼓舞信众以修德精进、行善利世为己任,进而感化世人;但同时也客观记载了一定数量的名不符实的僧侣,更不用说小说文献中所载败坏山门、有损佛门形象的僧人了。
(二)明前小说文献中的僧尼形象及其演变
僧尼形象由正面走向反面,其变化在明以前各期小说作品中皆可找到明显的轨迹。在佛教传入我国不久的汉晋时代,佛教僧人的形象在人们的心目中是非常高大的。如东晋高僧支道林(314——366),他 25 岁出家,初隐于余杭山,后于剡县沃洲(今浙江新昌县一带)小岭立寺行道,僧众百余人。晋哀帝时应诏进京,居东安寺讲道,三年后回剡而卒。但受魏晋谈玄影响,支遁弘佛讲道明显体现魏晋名士的风度,这在《世说新语》里就有一些关于他简略而精彩的描写:
王(王濛)、刘(刘惔)听林公讲,王语刘曰:“向高坐者,故是凶物。”复更听,王又曰:“自是钵钎后王、何人也。”
王长史(王濛)叹林公:“寻微之功,不减辅嗣(王弼)。”(《世说新语校笺》第 259 页)
以上是他人口中的支遁形象,下引系支遁本人的表现:
林公云:“见司州警悟交至,使人不得住,亦终日忘疲。”(《世说新语校笺》第267 页)
于此可见林公支遁对谈玄的浓厚兴趣。再如林公对他人不妥评价的回击,亦体现出魏晋名士的气概:
支道林常养数匹马。或言:“道人畜马不韵。”支曰:“贫道重其神骏。”(《世说新语校笺》第 68 页)
下所引是林公支遁在痛失知音后精神沮丧的情状,读者可以从中想见支遁对至高至圣的精神追求。
支道林丧法虔之后,精神霣丧,风味转坠。常谓人曰:“昔匠石废斤于郢人,牙生辍弦于钟子,推己外求,良不虚也。冥契既逝,发言莫赏,中心蕴结,余其亡矣!”却后一年,支遂殒。
再如林公对佛图澄与石虎兄弟关系的评价,亦可使读者想见作为真正高僧大德的佛理情怀:
佛图澄与诸石游,林公曰:“澄以石虎为海鸥鸟。”(《世说新语校笺》第 58 页)
类似支遁的还有高僧竺法深,《世说新语》中亦有精彩的描写:
竺法深在简文坐,刘尹问:“道人何以游朱门?”答曰:“君自见其朱门,贫道如游蓬户。”或云卞令(即卞壸)。(《世说新语校笺》第 60 页)
有关记录得道高僧的书籍还有北宋释晓莹的《云卧纪谈》。该著又称《感山云卧纪谭》,是晓莹在绍兴年间(1131——1162),于丰城曲江感山之云卧庵闲居期间,随笔记录的笔记体书卷。卷首有晓莹自序,卷末并附云卧庵主书,记述其师大慧宗杲与学人之机缘答问。全书二卷,收于《万续藏》第 148 册里。如东山吉,书中写他品行高洁,道学充茂,谈辩洒落,常与高明士大夫往来。他还颇有神通,能预知未来,是个神通广大的神僧!
本文所谓的高僧大德还包括比丘尼在内,该著“卷下”有大量品行高洁的比丘尼形象。如东都妙慧尼寺的住持净智大师慧光,她出于名门,学理高深,谈吐不凡,令人叹服。
像慧光那样出于名门望族之女而出家的比丘尼,还有无际道人和超宗道人。书中记载了无际道人自幼就有佛缘,以及她圆寂前后的奇闻异事。同时还讲述了无际道人督促超宗道人扫塔径山的一个故事,颇有六祖慧能与五祖弘忍应对之风。
然而,僧尼形象到了明清小说里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从此前的高僧大德一变成为贪财好色、趋炎附势、败坏山门的淫僧淫尼,广受人们的唾弃。其实,淫僧淫尼并非明清时期特有的现象,因为早在隋唐时代就有相关的记载,只不过不像明清时代成为主流现象而已。如唐代刘肃的《大唐新语》,北宋庄绰《鸡肋编》、王辟之《渑水燕谈录》,以及南宋词人康与之的《昨梦录》、洪迈的《夷坚志》等书中皆有不法僧尼污秽行为的记载和描写。而到了元代,还出现了专门描写僧人淫乱的小说,如托名高则诚的《灯草和尚》。至于历史上真实的淫僧淫尼,甚至在唐前就已经出现,像明代佚名辑录的《僧尼孽海》之“沙门昙献”中所写,即为北齐武成帝时代淫僧昙献的无耻行径。
由此可见,从魏晋时的高僧大德,到元明时候的淫僧淫尼,出家人的心性、生活方式、个人行为习惯乃至在社会上所产生的影响等方面,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而小说家们对僧尼形象的变化从简单的记述到细致的描写,让这些富于变化且丰富多彩的僧尼形象,鲜活在读者面前,从而提升了僧尼类小说的文学性、影响力以及劝惩教化的社会作用。
(三)明清小说之僧尼形象的复杂性特征
明清小说中的僧尼形象较为复杂,既有传统意义上正宗出家人严守佛教清规戒律、为善助人事迹的描写;也有对淫僧恶尼为非作歹、贪财好利、淫欲无度等恶行的揭露和抨击;还有些正宗的出家人因其地位低下而受到社会排斥的无奈,体现作者对他们的深切同情;甚至还有些冲破佛教清规戒律,公然名正言顺地还俗嫁娶的事例呈现,体现作者反对禁欲,提倡人性人欲解放的思想情怀。这些都充分体现了明清小说中僧尼形象的复杂性特征。
“三言二拍”是明代著名的两个白话短篇小说集的合称,书中写了各色人等,而僧尼形象也是书中的重要角色,数量亦不在少数。如“三言”中 23 篇,“二拍”中17 篇。这众多僧尼中,既有高僧大德,也有侠僧义尼,但更多的系淫僧淫尼。
明代专门选集僧尼的小说《僧尼孽海》,就名称而言,显然是对淫僧淫尼恶行的集中描写,但事实上,亦有对僧尼同情之意的表达。如《女僧嫁人》中有三则故事,皆与文人士大夫攀上了关系,其中有关北宋婉约派词人的代表作家张先的轶事,虽然曾被传为美谈佳话,主观上是借此对宋明理学遏制人性人欲所进行的抨击;但客观上也暴露了文人恶习以及出家人不耐寂寞的现实,具有一定的讽刺意味。
还有众多长篇小说,诸如《水浒传》《金瓶梅》《儒林外史》《红楼梦》等皆有不同类型的僧尼形象,而陆人龙《型世言》中《妙智淫色杀身 徐行贪财受报》,以及西湖鱼隐主人《欢喜冤家》里《蔡玉奴避雨遇淫僧》等回目,明显告诉读者其中所写即为僧人的淫乱故事。另如明清公案题材的小说,其中涉及僧尼形象的案件,大多亦与淫僧淫尼淫乱行为密切相关。可见,明清小说中,僧尼形象的类型众多而庞杂,呈现出人物形象的复杂性特征。
(四)从历史到文学:历代小说之僧尼形象塑造的文学史意义
在历代出家人中,既有高僧大德,亦有淫僧淫尼,而由各自不同的行为方式所形成的社会风习也确然不同程度地体现出来。但到了文学作品中,作家把他们加以放大、扩充描写,让其活动发展的情节更丰富多彩,细节更具体生动,形象更加有血有肉,将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物形象展现在读者的面前,使读者产生如临其境如见其人如闻其声的深切感受。这就是历代小说中之僧尼形象塑造的文学史意义之所在。
如北齐时与皇后胡氏勾搭成奸的昙献和尚,其荒淫之事在《北齐书》中已有记载,败露后被斩首。但所载属纪实之作,仅仅传递信息而已,没有露骨的描写。而到了小说里,便被敷衍得细致淋漓,人物形象惟妙惟肖,昙献与胡后荒淫无度的嘴脸赤裸裸地展现在读者面前。
再如历史上的女皇武则天,虽然在太宗皇帝时不得宠以至落发到感业寺为尼,后高宗李治将她接进宫,先后为昭仪、皇后、皇帝,但正史没有也不可能对她做详细的负面记载。然而到了署名明代徐昌龄的传奇小说《如意君传》,和署名“不奇生”的《武则天外史》等小说里,武则天被写成专横、狠毒、荒淫无度的丑恶形象,特别是与薛敖曹(见《如意君传》)、薛怀义(见《武则天外史》)的淫乱,写得详尽细致,极尽自然主义之能事,于是一个文韬武略的大政治家、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在历代平民百姓中便成了阴谋、凶狠、淫妇的代名词。
像《如意君传》《沙门昙献》之类的小说盛行于明代,到了清代便有盛传发展之势,比如嘉禾餐花主人编次的三十回艳情小说《浓情快史》(又名《媚娘艳史》),基本上是在《如意君传》的基础上加以扩充而成的。其实,有关武则天的故事,早在唐代就有牛肃的推理小说《苏无名》,但小说中的武则天,却是平易近人、可亲可敬的形象,不像明清小说里那样肆意虚构和歪曲。但笔者所要强调的是,无论如何,这些小说里的主人公不管是以正面还是反面形象流传下来,让原本鲜为人知的帝王将相、后宫佳丽的私生活展露出来,为历代众人所知,皆得力于小说作品对文学形象的塑造以及传播,其文学史意义是非常明显的。
而历史上的高僧大德,到了文学作品里,亦有不同程度的变形,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唐代高僧玄奘,他既是唐代的高僧法师,也是《西游记》里的主要文学形象。普通的平民百姓对唐僧的印象和了解,基本来自于《西游记》这部小说。
更有意思的是,在小说中,唐僧简直就是一位典型的人妖颠倒、是非不分的庸僧形象,却能获得悟空、八戒、沙僧的相护相随。特别是孙悟空,他身手不凡,一个筋斗便能十万八千里,出神入化来往于天上人间,却又忠心实意且能忍辱负重、死心塌地地跟随着唐僧,为之保驾护航。这就充分证明了唐僧虽然看似平庸、懦弱,实际上他却具有坚韧的品性和令人膜拜的人格魅力!只不过他的魅力还不为普通人士所能理解罢了。可见,唐僧作为取经故事的主角,小说的作者没有把他这个有历史真实原型的玄奘法师的艺术形象正面凸显,而是采用欲扬故抑的艺术手法侧面描写,让他合着佛家无欲无名终达无我的思想境界。同时亦可想见,唐僧为取得真经,尽管途中一遇艰险就不知所措,但他从未有过放弃取经的念头,总是在几个徒弟设法将他营救出来之后,毫不犹豫继续西行,这更加充分证明了他对佛教的信仰是何等的虔诚与笃定!这当是他几个徒弟死心塌地追随他,并竭尽全力为之保驾护航的魅力之所在。而小说家吴承恩把历史上的玄奘法师,通过西游故事演绎成文学形象的唐僧,其文学史意义也应在此。
二、明清小说僧尼形象之恶变与社会风习
淫僧淫尼最早出现于北朝,随后各朝事不绝迹,见录于小说文献載集的,自宋至明可谓屡见不鲜。清代一些通俗小说,包括公案题材的小说亦有诸多淫僧淫尼的详细描写。然不法僧尼自产生之日起直至其甚嚣尘上的急剧恶变,是与不良社会风习的延续与恶变密切相关的。现以明清时代创作或辑录的几部代表性小说集子为中心,对其中的相关描写与社会风习恶变之关系进行具体分析。
(一)淫僧形象与“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宗嗣观和“家丑不可外扬”的名节观密切相关
明清小说中有大量妇女尤其是官宦或富商之家的妻女入寺庙烧香拜佛求子,遭遇早有准备的淫僧奸淫的事故时有发生。此类事故之所以频发,且历经封建社会各代而绵延不断,表面上看,是僧俗之间互需互动的影响所致;若深究这种恶习产生与延续之因,当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宗嗣观”和“家丑不可外扬”的“名节观”反复作用的结果。
从受“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观念的影响来看,无论士农工商皆为传宗接代、接续香火起见,在不法僧徒张扬神佛送子的幌子下,将妻女送入庙中斋戒求子;而众多妇女亦因求子心切,不问神佛送子孰真孰假,络绎不绝来到寺庙。然而事实是,不法僧徒把被骗来的妇女以斋戒为名,将她们软禁在密室中以供淫乐。结果是以讹传讹,神佛送子便成为一种习俗并得到广泛的传扬。
从受“名节观”的影响来看,如众多妇女尤其是官宦或富商之妻女,当她们知道自己上当受骗后,为保全其“名节”以至家族的“声誉”不受影响,总是选择隐忍,不敢也不能向外宣泄,以致误入歧途、被淫僧奸淫的丑剧再三上演。更有甚者,连其夫父们为保全面子亦不敢声张。正像小说里写的那样:“那居官的人,多于不理家务,是闺门上不谨的。即有风声,他也不自认丑名。自古云:淫风出宦家。”(见《巧缘艳史》第四回)可见,这些观念在无时空界限地发挥着作用,并长期产生着巨大的负面影响,这就客观上助长了淫僧宣淫为恶的歪风邪气,并形成一种不良的社会恶习延续至今。这类故事及其观念的恶俗化,在明清淫僧类故事中为数不少,其典型的代表性篇章有如《醒世恒言》卷三十九《汪大尹火烧宝莲寺》,《僧尼孽海》中的“临安寺僧”,“闽寺僧”、“水云寺僧”、“宝奎寺僧”等。兹引《汪大尹火烧宝莲寺》中的相关描写于下:
有人问那妇女,当夜菩萨有甚显应。也有说梦佛送子的,也有说梦罗汉来睡的,也有推托没有梦的,也有羞涩不肯说的,也有祈后再不往的,也有四时不常去的。
子孙堂求子的过程只有亲身经历的妇女才知道,他人无从得知。但答案却如此之多,特别是那“推脱没有梦的”“羞涩不肯说的”以及“祈后再不往的”和“四时不常去的”之类的告白,略有思想的人,都可从这众说纷纭的答案和告白中得出结论:那就是被家人送来求子的妇女,皆哑巴吃黄连有苦无说处。所以那有疑而问之人于此发了一番议论:
你且想:佛菩萨昔日自己修行,尚然割恩断爱,怎肯管民间情欲之事,夜夜到这寺里,托梦送子?可不是个乱话!只为这地方元是信巫不信医的,故此因邪入邪,认以为真,迷而不悟,白白里送妻女到寺,与这班贼秃受用。
这议论者所谓“信巫不信医”的话,只是说到了求子的路径或方式方法而已,还未道及向神佛求子的真正原因和目的,但说菩萨不会来管“人间情欲闲事”、不可能“夜夜来托梦送子”的话,倒是说对了。但在今人看来,这求子的目的很显然,不就是为传宗接代么?这就涉及到宗嗣问题。有的人不孕不育如何接续香火?当然可以向医生求助,而小说里说的那个地方是信巫不信医,因此向神佛求助,可见都是方法问题,都给僧尼提供了行骗的机会。可见,那里的妇女为求子屡屡受骗而又不敢声张告发,其原因实际上是受到“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宗嗣观”和“家丑不可外扬”的“名节观”的影响。
当然,也有因入庙求子而受到秃驴奸淫却不顾一切要揭露告发的妇女,她们似乎未受“名节观”的影响,但那毕竟是极个别的现象。如《僧尼孽海》里的“嘉兴精严寺僧”里就记载着一个某仕宦人家的妻子,曾遇到这样的情形,虽然不能幸免被奸,但她聪明泼辣,将淫僧的鼻子咬了一口留下印记,后告官定罪,淫僧被流放,寺被废。
综上可知,淫僧为恶的变本加厉,皆与俗家的集体失语、集体忍让有关,致使僧家由贪淫好色恶习,进一步变成色货兼贪终致杀人犯罪、名败身死、寺毁庵消的下场。所以小说作者们告诫世人:“今缙绅富豪,刻剥小民,大斗小秤,心满意足,指望礼佛,将来普施和尚。殊不知穷和尚虽要肆毒,力量不加,或做不来,惟得了施主钱财,则饱暖思淫欲矣。又不知奸淫杀身之事,大都从烧香普施内起祸,然则‘普施’二字,不是求福,是种祸之根。”(分别见于《欢喜冤家》第 11 回,《贪欢报》第 12 章)
(二)淫僧荼毒良家妇女与“男尊女卑”观念和“家暴”恶习的蔓延密切相关
淫僧肆虐荼毒良家妇女的行为泛滥,也是与男权社会“男尊女卑”观念和丈夫凶悍粗俗、打骂妻子等“家暴”行为有着密切的关系。在男尊女卑观念和家暴行为的影响下,妻子无法忍受便跟他人外逃私奔或出家修行的现象普行于世,结果是妻子为逃离火坑却又落入陷阱的情况屡屡发生。如《巧缘艳史》第十回写孙昌与玉兰感情的变化时写道:“夫妻二人如鱼得水,十分如意。过了半年光景,孙昌忙去走差,去了便是数日方回,就在家,也不像初婚时上紧了,因此云稀雨疏。玉兰心上已觉意兴无聊,况孙昌生性凶暴,与前夫大不相合,吃醉了,便撒酒疯,无端将玉兰打骂。玉兰心中未免冷落了几分。”所以后来吴仁对她示好,她一拍即合、上钩出轨就是自然不过的事情,结果与吴仁私奔了。这可算作莽夫凶暴,打骂妻子,以致妻子出轨的典型例子。这玉兰还算幸运,那个勾引她并带她私奔的吴仁算得上有情有义之人,若是落入僧家之手,那就只能是被软禁起来留作长久宣淫的工具,稍有不如意就连性命都难保了。像《初刻拍案惊奇》卷二十六《夺风情村妇捐躯 假天语幕僚断狱》所写的临安庆福寺,被广明和尚骗来或抢来的那五六个农家妇女,其中一个就是郑举人的中表亲戚,系官宦人家前来烧香求子的妇女,竟然都被广明和尚囚禁在密室中淫乐,甚至连同当时送她来烧香求子的两个轿夫一起关在该寺的狱中,若不是郑举人无意中发现并告到官府,那几个妇女和两个轿夫就几乎没有出头之日,只能等着老死在僧房的密室和狱中了。
而四川成都府汉川县农户井庆的妻子杜氏,就没有庆福寺广明和尚囚禁的那几位女子幸运,更不可与吴仁私奔的那个玉兰相比了。杜氏就因其夫粗蠢,一日与丈夫有两句口角,就跑回娘家住了十来天,被娘家劝住了,然后自己回家,不幸在路上遇雨,于是来到太平禅寺避雨。寺中有一个老和尚大觉(管家的),一个徒弟小和尚智圆,一个小沙弥慧观,总共三人。师徒都是极淫毒的心性,当小和尚见前来避雨的杜氏颇有几分颜色,于是邪念顿生,热情地把杜氏迎了进来,送到师傅房里,师徒与杜氏淫亵不可名状。后大觉因杜氏厌恶自己而喜欢徒弟智圆,醋意大发,将杜氏掐死,杜氏就这样惨死在老和尚大觉的手下。虽然杜氏的死与淫僧大觉及其徒弟智圆的罪大恶极直接关联,也与她自身的淫欲无度、不守妇道密切相关,但其夫粗蠢、鲁莽的家暴也是她致死的重要根由。
正因为妇女们常常因卑贱地位受辱或家暴致伤致残,其身心备受痛苦的折磨,以致赌气回娘家或离家出走,还包括逃荒逃难等致使妇女独行于外的情形,都给淫僧秃驴抢骗良家妇女来寺中淫乐提供了机会。淫僧秃驴们在其屡屡得手之后,便习惯成自然地形成一种恶习,只要有妇女来寺中逃荒避难或避雨或借宿,淫僧秃驴们就伺机淫毒。明清小说里有诸多此类描写,其中以避雨情形居多。如《欢喜冤家》第十一回《蔡玉奴避雨遇淫僧》,《风流和尚》第六回《大兴寺遇雨遭 风波》,《巧缘艳史》第五回《邬妇人坚执不允 二和尚竟使毒心》以及“初刻拍案惊奇”中《奇风情村妇捐躯,假天语幕僚断狱》里的相关情节,皆写妇女因去寺中避雨而遭到和尚的奸淫。
与之类似的就是和尚扮尼姑以实施骗奸。和尚扮尼姑骗取官宦之妻妾以满足其色欲,终败露被处决的现象也大行于世。如《僧尼孽海》里的“云游僧”,就记载着这种情况。故事里的“云游僧”一行五人,皆男扮女装化为尼姑,以采战缩龟之术、妄谈生死轮回之套路骗取吴下某富豪及其妻女的信任,被收寓于富豪家之功德庵中,为首者留为庵主。继而以做会为名,常骗取该城所有富贵人家以及乡村妇女来庵中,选其中美而少者留宿庵中以实施奸淫,还得意洋洋地记下受淫女子的姓名、时间及相关信息。而该豪家功德庵有净室十七间,原为做会而备,结果却被这些淫僧利用作骗奸美貌女子的场所,反而禁止游人,是以无人破其淫网。而被骗奸的妇女,除了刚正不肯受辱而被淫僧“以法迷其神智淫之”者外,其他均乐以从之。
可见和尚扮尼姑骗奸行为的屡屡得手而难以败露,亦为僧俗合力作用的结果,其中女子“欲言不言”的“无可奈何”和“闻其他女子留宿庵中”“只自暗笑” 的社会心理,以及豪家为顾全脸面为僧“嘱托”的行为,皆助推了淫僧骗奸恶习在社会上的蔓延。
此外,和尚嫖妓也成为古代社会风习恶变的突出现象,小说里也多有描写。如《风流和尚》第三个故事《贼虚空痴心嫖艳妓》和《欢喜冤家》第十四回《一宵缘约赴两情人》所写皆属此类内容,只是人名和情节的详略不同而已。
由此可见,上述诸多良家妇女甚至官宦之家的妇人落入淫僧圈套,皆与种种不良社会风习熏染有关。
(三)小说中的淫尼形象与文士富商贪淫好色恶习密切相关
淫僧如此,淫尼亦然。与良家妇女落入淫僧陷阱相对应的,就是俗家男子堕入淫尼淫窟的恶俗也频见于小说家的笔端。如《醒世恒言》卷十五《赫大卿遗恨鸳鸯绦》中的江西新淦县监生郝大卿,被非空庵里的尼姑空照、静真剃去头发妆成尼姑,长留庵中恣意淫乐,致使郝大卿纵欲身亡。又有极乐庵的尼姑了缘,她勾搭万法寺住持觉缘的徒弟去非做了光头夫妻,藏在寺中有三个多月了,因非空庵中的东窗事发,连带使其真相大白,并在受审期间,还害得觉缘老和尚差点吃了无头的冤枉官司。《僧尼孽海》中的《宝奎寺僧》及附辑中之《明因寺尼》《麻姑庵尼》《杭州尼》《京师尼》《女僧嫁人》《西湖庵尼》《张漆匠遇尼》《栖云庵尼》等等,讲的都是淫尼的故事。小说里说他们原是个真念佛,假修行,爱风月,嫌冷静,怨恨出家的主儿,把尼庵变成了淫窟,把个佛门净地弄得乌烟瘴气、臭气熏天,即如《欢喜冤家》里的《黄焕之慕色受官刑》中所调侃的那样:“五更三点寺门开,多少豪华俊秀来。佛殿化为延婿馆,钟楼竟似望夫台。去年弟子曾怀孕,今岁阁黎又带胎。可惜后园三宝地,一年埋了许多孩。”
淫尼恶俗从备受世人唾弃的各自偷摸行为,逐渐变为至少是僧家许可的半公开行为,小说文献中亦有记载。从《僧尼孽海》所记情况,可知元代曾有些尼寺实际成了专供豪僧淫欲的“尼站”(相当于俗世社会的“妓院”)。“明因寺尼”条中如此介绍:
元时临平明因寺,尼刹也。豪僧往来,多投是寺。每至则呼尼之少艾者供寝。寺主苦之,於是专饰一寮,以贮尼之淫滥者,供客僧不时之需,名曰尼站。
这个简短的介绍中,已透露了两个真实的情况。一是明因寺之所以成为“尼站”,是因为往来逆旅之豪僧浸淫已久的“淫欲”之恶习所致。如小说写到尼寺主对庵寺中的淫欲现象,其第一反映是“苦之”,不得已而“专饰一竂”,“以贮尼之淫滥者,供客僧不时之需”。可见这个“尼站”相当于世俗间的“妓院”。另一是出家为尼之人,其中却有“淫滥”者,正所谓淫僧有所欲求者,淫尼必有淫滥者以成之也。从明因寺尼的实际情况来看,不仅淫滥者如此,即使是心坚如铁之人,在那个有供淫僧滥欲之“尼站”之称的环境里,最终也无法抵抗住淫僧滥尼淫荡无忌之恶习的影响,如该寺寺主“知客尼”就是典型的一例。小说如此写道:
知客尼法名性空,故豪家女,以万历己丑冬日,励志在寺修行。为本寺知客,颜色姝丽,见者无不啧啧。
这位法名“性空”的知客尼,她不仅自己出家修道心坚意诚,而且在她的管理下,寺中“门禁甚严,人罕得进。”一年之内只有六月十九观音成道日才开放一次,还在寺内悬挂宋仁烈皇后手书的三十二字戒为众尼静心修持之座右铭,其戒云:“众生自度,佛不能度;欲正其心,先诚其意;无视无听,抱神以静;罪从心生,还从心灭。”就像这样一位知客尼,却未能逃脱开典铺的黄某再三设局而最终入其彀中:
有徽人黄某者,姿环态,慷慨风流。开典铺於临平街上,每至期往观,苟非绝色,未尝瞩目。至庚寅六月,忽见性空,遂魂摇神夺。询之,知去岁冬始来修行者。莫能为计,已而门扃如故,不可复睹矣。越月一日,有老尼持一缣向黄质钺,黄掷钱与之,不留其缣,尼深讶无因。未几,尼以钱偿黄,黄曰: “我方将捐赀,助修殿宇,此微物何必介意。”尼致谢而去,以语知客,知客曰:“黄郎何许人,乃能喜舍如是,我将有以探其隐焉。”
经过多方试探,得知黄某是因自己的美色而不惜重金布施本寺,知客尼不仅没有拒绝,反而是“久作襄王梦,相思日几回”,并与黄某以及从中作伐的老尼间书札传情,诗词送意,所谓“心原无泄,句偶有私。”说的就是她当时的实情。当黄某赤裸裸地向她表白“欲求西域金身,见怜下士”,知客尼竟三次以诗回复,一是答应幽会,其诗云:“断俗入禅林,身清心不清;夜来风雨过,疑是叩门声。”二是表示愿结同心,其诗云:“郎情温如玉,妾意坚於金;金玉尔相契,百年同此心。”三是定下野合之佳期,其诗云:“妾年方及笄,那知月下期;今宵郎共枕,桃瓣点郎衣。”终在“登门觅汉,惯品肉箫”的老尼撮合下,竟演出了“三人共枕求欢”的龌龊丑剧。而明因寺的风气也“自是往来,浸及众尼”,而“黄亦挈伴取乐”。如此这般竟达三四月之久,终为里正所觉,于是“侦黄执之,送仁和县,大尹逮尼得实,断黄配遣,杖尼离寺,另嫁。”
从上述知客尼由坚贞到淫荡的变化可知,其原因并非单一的,而是多方作用的结果,其中人性与社会环境的影响最为明显。
表面上看,麻姑庵中的庵主也因她“操凛冰霜,心坚金石”,所以众尼“不敢逞其芳心”,社会上的浪荡公子也就“无计开其情窦”。然而尽管如此,麻姑庵的尼姑们也终难抵挡住“食色”之天性的激发。比如一日有个云游的小和尚来到麻姑庵,这小和尚原本就是出家人中的败类,他自恃年轻貌美,又练就了一身非凡的“采战术”,借云游之机四处寻欢觅艳,一见到该庵的小尼,便“不觉心动”;而庵中众尼见到这位“身技不凡”的小和尚,她们不约而同的反映是“经也不诵,磬也不敲,金钟不撞,木鱼不响”,皆“目睁口呆,半晌不语”地看着这小和尚。即使是那平日自持“虽极严肃”的庵主,见到小和尚时也不觉“掉落了数珠儿”。这当属人性固有的内在原因之所致。若这位庵主真的像作者开头介绍的那样“极严肃”,对于情欲是“操凛冰霜,心坚金石”,也就不至于有小说后来写到的那些伤风败俗的情况出现。这说明个人的修为和贞操观以及社会环境对人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而麻姑庵主及其所辖下的众尼们与小和尚的淫荡事就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
正因为淫尼恶尼犯下如此多的滔天罪行,所以文人写有“嘲女尼”“挂枝儿”等曲子以嘲讽之。
基于众多淫僧骗奸为恶事件的频繁出现,于是一些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小说家们却要告诫世人:“天下事,人做不出的,是和尚做出;人不敢为的,是和尚敢为。最毒最狠的,无如和尚。”(《欢喜冤家》第 11 回,《贪欢报》第 12 章)这里虽然一针见血,概括精准,但还不够全面,因为尼姑们的淫毒并不逊色于和尚。因此,该段箴言当改为:天下事,人做不出的,是淫僧淫尼做出;人不敢为的,是淫僧淫尼敢为。最毒最狠的,无如淫僧淫尼。世人当时刻提醒自己注意淫僧淫尼,不要上淫僧淫尼的当。
综上可知,尼姑贪淫以祸乱社会的罪行,除了她们自身的问题外,也与商人、文士贪淫好色恶习密切相关。
三、僧尼形象恶变的社会历史根源
僧尼形象是古典小说人物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明清小说通过对历代僧尼形象恶变的现象及其过程的描写,不仅向读者形象地展现出一副古代僧俗世界的连环画卷,而且也客观展露了古代中国社会风习恶变的历史轨迹。产生其恶变的原因,简单地说,是僧、俗共同合力作用的结果,因为僧尼形象的恶变过程始终伴有僧尼之外的各界人士尤其是官宦、商人及其家人的参与。从上述淫僧淫尼及其与之密切相关人士的终极恶果来看,他们贪淫好利、为恶不仁终至落入法网的现象,可谓前赴后继,史不绝迹。究其根源,不外乎这三个方面:一是难以逾越的人性,二是难以改变的习惯,三是难以抗拒的社会环境。
(一)难以逾越的人性
食色是人的天性,真正的佛教徒能够抵抗“食色”诱惑的力量那不是常人所 能企及的,亦非常人所能想象得到的。而普通的个体人也好,社会人也罢,终归逃不出“食”和“色”之天性,即使是修行有大成就的佛教徒中,亦有终未逃出的,只不过他们一旦犯戒,随即醒悟并速返而已(如红莲柳翠故事中的禅师),更不用说那些原本就无意修行、阴差阳错进入佛门之人了,至于像坐怀不乱的柳下惠也就只能作为修行人之理想形象来看待。对于“食色”之天性的肯定,自儒家孔子提出之后,明代李贽并发挥到了极致,而作为人性中之一端的“色”,其受到人们肯定的亦代不乏人,而明清及其以后则更甚。如清代袁枚曾在其笔记小说《新齐谐》中讲过一个“沙弥思老虎”的故事,其主旨是在对人性之色欲的肯定。故事中的小沙弥,自幼跟着禅师在山上修行,不曾下山,未曾见过任何世面。十数年后,禅师带着他下山,一路上见到牛马鸡犬和一个美貌的妇人,他都不认识。禅师一一告诉他,其中那位美妇被禅师说成是“吃人的老虎”。回山之后,禅师问小沙弥路上所见是否还有想着的,小沙弥却不假思索地告诉禅师,别的都不想,心里总是放舍不下那吃人的老虎。这个故事告诉人们一个道理,色之于人是无法回避的天性所在,即使是出家人,尽管理性上要讲着如何戒除色欲,而实际上大多在心里是心心念念无法忘怀。而小说中僧尼形象的恶变,除了要鞭挞其品德的败坏和龌龊社会环境的影响外,也有相当部分系作者关于人之天性问题的思考,或是对人性被遏制的同情和反抗。而作者的思考往往是借小说作品里当事人之口形象地反映出来。《醒世恒言》卷三十九《汪大尹火烧宝莲寺》中有这样一段典型的叙议:
话说昔日杭州金山寺,有一僧人,法名至慧,从幼出家,积资富裕。一日在街坊上行走,遇着了一个美貌妇人,不觉神魂荡漾,遍体酥麻,恨不得就抱过来,一口水咽下肚去。走过了十来家门面,尚回头观望,心内想道:“这妇人不知是甚样人家?却生得如此美貌!若得与他同睡一夜;就死甘心!”
又想道:“我和尚一般是父娘生长,怎地剃掉了这几茎头发,便不许亲近妇人?我想当初佛爷也是扯淡,你要成佛作祖,止戒自己罢了,却又立下这个规矩,连后世的人都戒起来。我们是个凡夫,那里打熬得过!又可恨昔日置律法的官员,你们做官的出乘骏马,入罗红颜,何等受用!也该体恤下人,积点阴骘,偏生与和尚做尽对头,设立恁样不通理的律令!如何和尚犯奸,便要责杖?难道和尚不是人身?就是修行一事,也出于各人本心,岂是捉缚加拷得的!”
又归怨父母道:“当时既是难养,索性死了,倒也干净!何苦送来做了一家货,今日教我寸步难行。恨着这口怨气,不如还了俗去,娶个老婆,生男育女,也得夫妻团聚。”又想起做和尚的不耕而食,不织而衣,住下高堂精舍,烧香吃茶,恁般受用,放掉不下。
小说通过杭州金山寺至慧和尚之口讲述的这段话,从四个层面把一个被动出家(自幼难养被父母送入寺中)之人对于人之天性尤其是“色欲”之天性做了较为全面的肯定。这四个方面的天赋秉性中,除了最后那个对“不耕而食,不织而衣,住下高堂精舍,烧香吃茶”享乐生活的追求,属于天性中堕落性质、应该摒除外,其他三个方面皆属“色欲”之正常范围。一个被动出家的小和尚,没有受过多少教育,但他每天被动诵经受戒,他骨子里有太多的心不甘情不愿,都借那次见到那位“美貌妇人”而毫无保留地宣泄出来,可谓骂尽连佛祖在内的所有出家人及其清规戒律,骂尽历代制定法律的官员以及天下所有无奈的父母。这几个层次皆触及社会问题的要害,其议论和反问可谓精辟之至!
《僧尼孽海》之“麻姑庵尼”条中写了一对僧尼约定还俗结为夫妻的故事,其中亦有类似至慧和尚对人性人欲的肯定之词。现将原文引录于兹:
……尼自怜自恤,百依百从,问僧曰:“以汝慧中秀外,何故剃度为僧?” 僧曰:“以汝粉白黛绿,何故削发为尼?”……尼又谓僧曰:“尔我情乎,何不趁此月光交拜立誓,蓄发归家,定为百年夫妇,庶几我作闺中妇,免尔频敲月下门。”僧曰:“可。”乃穿衣起拜,立誓已毕。尼曰:“以月为题,联诗记事。”…… 联吟方罢,小尼又作诗一律,以志感焉,诗云:旋蓄香云学戴花,从今不着旧袈裟;宁并臼供甘旨,分理机梭弃法华。试宿频知鸳被暖,乍殊谓凤钗奢;禅心匪为春心贰,女子生来愿有家。
从引文的对话中可知,这对少僧少尼当为被动出家者。他们不仅厌恶出家、向往世俗红尘中正常人的生活,而且还涉及到“有情人”理应成为“眷属”的理由和还俗的决心,于是他们趁着姣好的月光“交拜立誓”。在这位麻姑庵尼看来,还俗是极好的办法,因为这不仅能够“免尔频敲月下门”,而且还避免了因“频敲月下门”而带来的非议甚至更大的麻烦。可见,这对少僧少尼的思考和约定是正确而明智的。所谓“禅心匪为春心贰,女子生来愿有家。”说的就是正常的人欲范围。
对此,后人又从生理条件的角度来肯定情欲,并达到为被动出家的僧尼理应还俗甚或破戒进行辩护。如署名吴越唐寅字子畏撰的《僧尼孽海题词》中写道:
混沌之分也,男子生而有孽根,女子生而有孽窟,以孽投孽,孽积而不可解脱,积壤成山,积流成海,积孽讵无所极乎!……
这段话,虽主观上是在说明汇编《僧尼孽海》这部书的动机和目的是为满足当时读者的阅读兴趣,且僧尼的“性禁锢、性变态”以及“性欲望”是历代各类文艺作品中屡见不鲜的内容,但客观上体现且强调了人欲中的“情欲”“性欲”是天生的无可抗拒的生理现象,既然客观存在着“孽根”“孽窟”,“以孽投孽,孽积而不可解脱”,又何必人为的去限制它呢?可谓从新的角度肯定了在不违反社会伦理道德的前提下顺其人性自然之必要。
前述众多僧尼故事中,除了那些品德败坏、贪淫好利、谋财害命等十恶不赦的淫僧淫尼外,其余皆不同程度地带有一些人性的问题,皆受到作者和读者的同情和关注。他们之所以频频犯戒乃至犯罪,可以说,其中一个很重的致罪根由,就是受抑的“情欲”。因为出家人中有相当一部分不是自愿出家,而是被动出家,所以当他们的情欲屡屡受抑时,就会不断寻找发泄排遣的出口,于是就导致犯戒乃至犯罪。所以说天赋“人性”“人欲”问题是难以逾越的,须社会人更高的修养与自律,而高的修养和自律又须人们不断地学习和养成,积极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使得个人修养、社会道德、群体公德在人们的心目中和日常行为上,逐步形成“习惯成自然”的良好社会风习。
也正因为人性、情欲无法逾越,所以明太祖朱元璋曾先后下令,“民家女子年未及四十者,不许为尼姑女冠”(洪武六年即公元 1373年);“民年二十以上者,不许为僧”(洪武二十二年即公元 1389年)。而建文三年(即公元 1401年),又将女子出家的年龄提高到 59 岁。男女出家年龄的相反规定,是从男女生理差异的角度来考虑的。朱明王朝从男女生理差异着眼做出法律规定,目的在于使尼姑、和尚能安于清修,以利于保持佛门庵院的宗教纯洁性和社会的安定稳固性。然而事实不尽如皇帝所愿,前述那因难养而被父母自幼送至寺庙出家的至慧和尚,他并未逃脱情欲的困扰,所幸的是他终于冲出情欲的限制,与少尼私约还俗成家生子。可见,人性这东西是难以逾越的,不可限制过头;否则,人心难定,社会难宁。
(二)难以改变的习惯
习惯有好坏之分,而淫僧淫尼屡屡犯戒乃至犯罪,其致罪根由除了上述“难以逾越的人性”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难以改变的坏习惯”在其中作祟。有些习惯原本也无所谓好坏,但发展到了极致,就变成了坏的东西,于是习惯成自然地发挥着其负面的作用,以致形成社会恶习。
佛教自东汉时期传入我国,虽然历经整个封建社会直到如今,人们崇佛或抑佛现象不曾停息。但总体上来说,佛教在民间还是很有市场的,所以随处可见寺庙庵院和络绎不绝烧香礼佛之人,佛教已成为国民信奉崇敬的主要宗教之一,去庙堂庵院烧香拜佛便成为信徒们礼佛的重要形式。
佛教的人性修养和道德教化及其教化的方式都有非常可观之处,值得肯定。但在其延续发展传播的过程中,难免有走偏入邪的现象,诸如民间出现过不少的淫祠淫祀现象,而民间百姓文化水平普遍偏低,对佛教宗旨教义也不甚清楚,只要能满足自己所求事情的“灵验”就行。于是去寺庙烧香拜佛求子、求庇护就成为了人们生活中的一个习惯,甚至豪门大户自家皆有庵院。长此以往,淫祠邪寺淫祀现象影响到正规的寺庙庵院,以致出现像小说里所写的那些淫僧淫尼贪淫为恶的种种罪孽;也正因为国民的这个习惯,逐渐将求神拜佛求子求庇护便变成了民间习俗。而这个习俗的发展,逐步被不法僧尼利用来行不轨之事,犯不法之条,诸如他们挖空心思利用化缘、扩建庵院、烧香礼佛、做法会等手段,将信徒们诱来寺院以实施奸淫,更有甚者是假佛菩萨的名号,打着佛菩萨送子的幌子,诱骗无数信徒,尤其是官宦富商之妻女来烧香礼佛求子以实施奸淫乃至杀戮。
还有一种现象也逐步变成习惯乃至成为习俗,那就是士人商客为待考或行商常常临时寄寓在寺庙庵院,这就直接给僧家与世俗之人提供共同合力为恶的机会和条件。《巧缘艳史》第十一回,写官差孙昌的妻子花玉兰与浪子吴仁勾搭成奸,为做长久夫妻,吴仁利用孙昌出门的机会将玉兰暂寄在一尼庵住下,然后假意到孙昌邻居处打听孙家情况以为掩护,便暗中将玉兰带到杭州,那尼庵便成了他们私奔的中转站。第二十三章《黄焕之慕色受宫刑》写的是明因寺的尼姑本空、性空和云净庵的小尼了凡,皆与商人黄焕之淫荡,后来性空(该寺的知客)和了凡竟然蓄发与黄焕之做起名正言顺的夫妻。这个故事亦见于《僧尼孽海》中的“明因寺尼”,只是具体的细节不同而已。还有前述那卖珠客曹悦心在寺庙里借住,看上了来庙里游玩的美妇,就到佛前求签问卜以决成功与否,结果得一上签,签文预示其目的可以达成,他便男扮女装混入美妇家诱奸。而这庙宇、菩萨皆为淫灆之徒为恶大开方便之门。而一些官宦之家的私人庵院也往往被淫僧淫尼暗中挪作奸淫之所,如《僧尼孽海》之“柳州寺僧”所写就是其中典型的例子。
还有一个恶习是嫖妓,文人嫖妓,和尚也嫖妓,世俗间有什么恶俗,出家人不但效法,而且变本加厉。《欢喜冤家》第十四回《一宵缘约赴两情人》所写,就是柳州明通寺和尚了然嫖妓而终栽跟斗的故事。小说冷嘲热讽,揭露和尚的虚伪,说他“素有戒行,开口便是阿弥陀佛,闭门只是烧香念经,哪晓得这都是和尚哄人的套子。”一日,一个财主带着柳州名妓李秀英来寺中闲耍,了然这秃驴见了秀英的姿色才艺,竟像没饭吃的饿鬼一般,整日相思,无心念佛。后竟乔装打扮来到妓院去嫖,终因受到秀英的冷遇而击杀了秀英,而秃驴自己也被正法。
书生游学借住寺庙庵院也是常有之事,如唐传奇名篇《莺莺传》中的张生,就是住在普救寺读书待考而得以遇见莺莺母女,并发生一段闻名当时流传后世的爱情故事。而更多的是书生游学暂寓期间而发现和尚秘密的情形,也反映了特定时代的社会现象。
“鄞县僧绛州僧”条中写这两处的僧人,皆有密室藏美妇美女淫乱事,而旁人皆不知,偶被游学书生发现,淫僧知密室淫秽事被泄露,并强逼书生自尽。而发现这二处和尚秘密的书生为逃命,皆躲在该寺的钟下,其一为韦驮指引得救,而另一为钟自开启而得救。这当然是菩萨显灵要惩恶徒救书生的壮举,然而这两位淫僧恶徒虽然身居佛地,口念佛经,却居然在清净佛地菩萨面前纵欲为恶,终皆伏法,其讽刺意味颇为深刻。
“初刻”卷二十六中的临安举人郑生,因在庆福寺读书,时间长了,与寺僧广明“甚是说得着,情意最密”,就因他无意间发现寺僧广明的密室,使得广明大为不安,竟要杀人灭口、以除后患,请看广明和尚得知郑举人发现其密室时所说的:“小僧虽与足下相厚,今日之事,势不两立。不可使吾事败,死在别人手里。只是足下自己悔气到了,错进此房,急急自裁,休得怨我!”然而,结果是淫僧广明反被智慧的郑举人急中生智结果了他的性命。郑举人随即到县官处告发,县官差了公人,急到寺中围住,引出密室地窖中的妇人五六人,问其来历,得知多是乡村人家所拐者。淫僧恶徒广明之流之所以有如此能耐,原在于其背后有着强大的社会环境条件做支撑。
(三)难以抗拒的社会环境
从前述众多小说中的淫僧淫尼形象可以得知,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后,至迟可谓自北齐始,高僧大德与淫僧淫尼就一直并存,而元明之后,出家人中出格乃至出轨现象更加明显。作为出家人理应严守清规,但他们却越来越肆无忌惮地冲破戒律,做出违规乃至违法的事情来。这除了难以逾越的人性、难以改变的习惯外,再次就是难以抗拒的社会大环境。
所谓社会大环境,是指上自朝廷下至民间,僧俗往来过从甚密,为佛门净地滋生淫毒提供了强大的物质基础和适宜酝酿的社会温床。如北宋张师正《括地志》卷十有云:“僧令遵,陕州人也。多智数,善附丽权势。天圣中,出入刘皇成家,因而名闻宫掖,庄献赐予巨万。”这虽然说的是个案,然而从这个案中却能洞见当时整个社会现象。而民间百姓每逢各种法会庆典或入庙拜佛求庇护都要进贡,因此,一些不法僧尼有了强大的物质支撑,他们不愁吃不愁穿,于是干出玷辱佛门伤天害理的勾当便成了僧尼常态。就像小说里写的那样:“你道这些僧家受用了十方施主的东西,不忧吃,不忧穿,收拾了干净房室,精致被窝,眠在床里没事得做,只想得是这件事体。”(这件事体:指淫荡事,笔者注。)正如民间俗谚所说的“饱暖思淫欲”也。
从理论层面上说,明代中后期的心学特别是王学左派对人欲有放纵的倾向,如李贽公开宣称“成佛征圣,惟在明心,本心若明,虽一日受千金不为贪,一夜御十女不为淫也。”这一强大的思想理论支撑,不仅造成世俗间人欲横流的现实,而且进一步波及到出家人中,于是一些出于无奈而非本心所愿的“被动”出家人,也就自然抗拒不了红尘中的诱惑,做出违规破戒有辱佛门的事情来,使得宗教的神圣性尽然消失。
从具体的环境来讲,其现实条件影响人也是不争的事实。一些僧尼原本在寺庙庵院中修行也还是比较正气的,但因具体情境的诱惑,比如俊男靓女常在面前过往,他们本被埋藏在心灵深处的“原欲”易被激发起来,正如凌濛初所说的那样:“虽然有个把行童解谗,俗语道‘吃杀馒头当不得饭’,亦且这些妇女们,偏要在寺里来烧香拜佛,时常在他们眼前,晃来晃去。看见了美貌的,叫他静夜里怎么不想?所以千方百计弄出那奸淫事体来。”这些议论虽然说的是人性问题,但也涉及具体环境的影响,亦可算作对环境诱惑的精辟概括。
由此可见,淫僧淫尼为恶,其社会大环境的助纣为虐不可低估。这种社会大环境,也不仅仅表现在物质基础和思想理论上的支撑,而且还体现在上自朝廷后宫下至民间百姓的亲身参与。如前述众多小说中所及淫僧淫尼形象,其与俗家的合力情形均有涉及。而君王后宫的直接参与是淫僧淫尼为恶的最大靠山,像北齐的胡后、唐代的武则天、高阳公主、杨玉环等人皆与寺庙的关系密切。淫僧淫尼有了强大的政治靠山和至高无上的社会地位,他们自然胆敢胡作非为而无所顾忌。再如文人士子、官吏富商亦是其为恶的强大的社会力量,如前述庆福寺里的和尚广明,小说写他做人是“俊爽风流,好与官员士子每往来。亦且衣钵充轫,家道从容,所以士人每喜与他交游。……一日殿上撞着钟响,不知是什么大官府来到,广明正在这小房中,慌忙趋出门外迎接去了。”而由此忘记给密室上锁而致使淫窟秘密被败露。这些都说明了不仅读书人喜与“衣钵充轫,家道从容”的和尚交游,而且有雄厚物质基础的和尚们也喜逢迎趋奉达官显贵,而达官显贵便进一步成为淫僧淫尼肆无忌惮地为非作歹的强大社会支撑,佛教的神圣性日益淡化,社会风习日益恶化。还有普罗大众信神佛以及烧香拜佛的习俗,为淫僧淫尼贪淫享乐、为恶不仁提供了最为广泛的群众基础,进一步使得僧寺尼庵公然成为淫僧淫尼玷辱佛门、危害社会的污秽之地。
综上所述,通过对明清小说僧尼形象恶变的现象及其轨迹的探索,发现其恶变的原因,这对进一步深究僧、俗间为何要如此合力为恶以致造成社会风习恶变的根由,有着深层的文学史意义和积极的社会学意义。因为它不仅为小说的深层研究和拓展研究开辟新的学科领域,形成文学社会学;而且还为社会学家研究相关社会问题提供可资参考的文献史料和思维上的启发,进一步彰显文学的社会功能和教育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