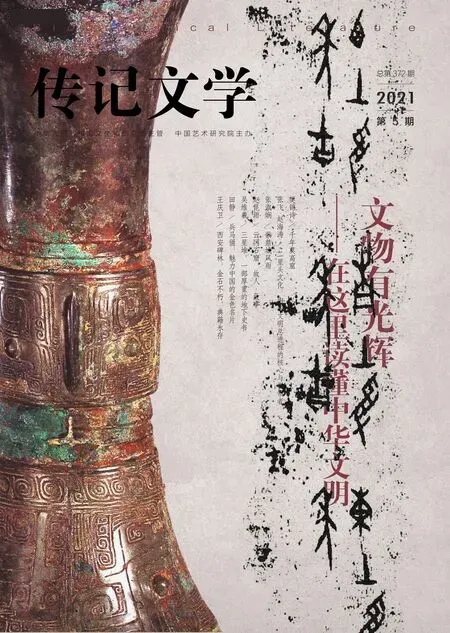现代传记研究新拓展
——论张立群“中国现当代诗人传记研究”的价值与意义
袁 昊
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
一
史料研究已成为近年来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话题与热点,“史料”甚至作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方法”而备受推崇。众多学者参与到这一研究领域中,纷纷撰写论文,探讨史料研究的新理论和新方法;一些高校与研究机构召开多个学术会议,推进史料研究发展。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界对史料如此重视,一方面是因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有重视文学史料的研究传统;另一方面与近些年学术界对学术风气的扭转及学术趋向变化有重要关系,即从“文学史”转向“文学史料”,由“叙述”回到“材料”;同时与社会及文化思想变化也有关,“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发展与繁荣,依然更多联系着一系列轰轰烈烈的社会思潮事件”。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再次出现史料热,与对后现代思想在中国人文学科影响的反拨纠偏的思潮相关。外来理论的生搬硬拽无法解决中国学术研究的实际问题,从中国具体社会历史出发成为必然趋势,落实到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从最基础的史料开始就成为应然之举。有学者呼吁并论证创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料学,以便切实有效地推进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重视史料的价值甚至以史料作为方法,从观念上看有其合理性,问题在于如何在研究中具体实践,而且这种实践不是零敲碎打的个案研究,是要形成具有一般意义上的研究范式。张立群的“中国现当代诗人传记研究”是近年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料研究的重要成果,或可作为文学史料研究的一种可资借鉴的研究范式。
其成果主要体现在新近出版的两本著作上,一本是编著《中国现当代诗人传记版本辑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5月版);一本是专著《中国现当代诗人传记史料问题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8月版)。前者是资料性质的中国现当代诗人传记版本分类辑录,后者是对中国现当代诗人传记的史料问题进行专门研究;前者是研究基础,后者是对前者问题的发现与研究。这两本著作,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界第一次对诗人传记作了全面整理与研究,不仅对传记研究有重要贡献,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的史料问题研究也有重要价值。
《中国现当代诗人传记版本辑录》收录自第一本现当代诗人传记到2019年出现的各类中国现当代诗人传记。根据不同分类方法,该书辑录六个类别的中国现当代诗人传记版本,分别是:“现当代诗人他传版本辑录”,收录101 位诗人、1090 本传记;“现当代诗人自传版本辑录”,收录47 位诗人、263 本传记;“现当代诗人年谱版本辑录”,收录24 位诗人、54 本年谱;“现当代诗人部分日记、游记、书信版本辑录”,收录24 位诗人的相关日记、游记和书信;“现当代诗人部分研究资料、纪念文集版本辑录”,收录81 位诗人研究资料和纪念文集;“部分含现当代诗人合传(包括小传、传略、列传),收录系列合传16 套、单行本合传86 部。从收录的类别之全、数量之巨,就可看出这本《中国现当代诗人传记版本辑录》的重要价值。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来说,这本资料集无疑是填补了空白,为中国现当代诗人研究、传记研究等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比如较为齐全地收集了大家非常熟悉的现当代诗人胡适、郭沫若、徐志摩、林徽因的传记版本。一提起这几位诗人,我们大致知道关于他们的传记很多,但具体有多少,没有人整理过,这本资料集就收集齐了这些诗人的传记(他传为主)。以郭沫若为传主的传记116 部,以胡适为传主的传记183 部,以徐志摩为传主的传记140 部,以林徽因为传主的传记151 部。通过具体的传记版本信息收录,使研究者能较为快速地找到需要查看的传记,为研究者提供了研究便利。
能够较为详细地把中国现当代诗人传记版本信息收集齐全,已经为学术界做出了贡献,张立群还在版本收集基础上进行了深入研究,以专题形式对中国现当代诗人传记的史料问题进行了理论与方法探讨,其成果集中体现在《中国现当代诗人传记史料问题研究》这本专著中。根据现当代诗人传记中存在的史料问题,张立群从“传记性史料的定位”“现当代诗人传记的史料价值构成”“现当代诗人传记的史料层级划分”“现当代诗人传记史料的生成与实现”“传记家的素养与传记史料的关系”“影响现当代诗人传记史料价值的其他因素”等方面进行纵深研究,形成了关于现当代诗人史料问题的比较全面的理论体系。这本专著的价值就在于以现当代诗人传记史料问题为研究对象,既非常敏锐地抓住了现当代诗人传记书写中非常突出的史料问题,又对这些史料问题进行条分缕析的理论探讨,不但于传记研究具有意义,而且对整个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的“史料转向”进行了及时的回应,并提出了可资借鉴的研究范式。
二
“史料”最早被提及且作为一种研究材料,是源于历史研究领域,进而形成“史料学”。作为一种基础的研究材料,“史料”的来源是比较广泛的,凡一切能作为研究论证的材料都可称为“史料”,有学者从历史研究的角度进行了较为严谨的限定,“史料”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其一是地下发现的资料,如古代化石、甲骨、铭器等;其二是文字记载流传下来的史料,其中有直接的史料和间接传闻来的史料,又以直接史料即所谓第一手资料为重要”。这里包括了地下(考古)和地上(文字)的史料。随着技术手段的发展,史料来源也逐渐多元,如声音、影像等也开始作为史料而被使用。
史料使用的原则,“坚持史料的第一性和多样性”,即追求史料的真实性。而真实性又是传记的重要衡量标准之一,所谓传记“史与诗”二维之中的一维,是传记的显著特征。基于传记的这种特征,在使用传记时,往往遵循“自传优先,他传靠后”“第一本传记优先,此后的传记靠后”的原则。其内在逻辑依然是史料的真实性。真实性是传记书写的重要标准,这一目标的实现反过来成为传记的显著特征,因此,区分中国现当代诗人传记史料价值的标准就是史料的真实性。
如何来区分或者说划分现当代诗人传记史料真实性呢?张立群借鉴文学史料学中的层位划分,提出了“现当代诗人传记的史料层位划分”:“自传”是第一层位,“他传”是第二层位,第一二层位之外的可资传记书写的其他材料为第三层位。初看上去,对现当代诗人传记史料的这种层位划分并无多少新见,以文学史料学对史料的层位划分方法来对传记史料进行模式化处理。其实这样的划分自有其价值,张立群比较细致地分析了第一层位的“自传”所涵括的对象,并不局限于作为文体的自传,还包括回忆录、口述史,以及日记、书信、游记等,因为这些材料在真实性上较为相近,是传主本人留存的史料。在分析第二层位“他传”时,论者提出了与通常使用他传原则(第一本优先)不一样的观点,“晚近诞生的用心之作由于资料占有多、把握最新研究动态,其史料价值往往高于多前年出版的同一传主之传记”。这些分析及观点对传记研究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廓清了传记研究中史料分类不清的问题,为传记真实性追求的实现作出了理论探索贡献。
按史料真实性标准,对现当代诗人传记中的史料价值进行层位划分,从宏观上论证了传记史料的层位与等级,为传记史料的使用提供了方法论。但是在具体操作上如何尽最大可能实现传记史料的真实性呢,张立群由此详细论述了“现当代诗人传记史料的生成与实现”。
通常情况下,我们会把传记作为研究的史料基础,但实际上“从传记中获得的主要是史料线索,还不是史料,从传记线索中扩展史料是我们使用传记的目的,而传记本身并不能成为我们史料的基本来源,就是作家的自传也不能成为史料来源的依靠,在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时,作家传记属于‘有意’的史料,或者说是次料,是第二手材料”。真实性是传记的显著特征,可传记包括自传不能作为研究的基础史料,甚至只能是“次料”“二手材料”。那么传记的真实性何在?现当代诗人传记又该如何进行史料的生成与发现?
这里涉及到哪些人物可以作传,因为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作传。这不是否认人人平等的价值观念,而是基于社会现实。传记重要目的是:“表现一种特定的人生、一段特定的历史,从而实现‘人性的纪念’、完成‘人生的示范’的同时,帮助人们认识传主在特定历史进程及时代本质中的特殊作用,达到‘认知的快乐’,发挥一般意义上的认知功能。”要实现这样的目的,只能选择那些有重要影响与价值的人物立传,因为这些人物自己或者他人对生平经历有意地留存历史印迹,且对社会历史进程有影响,对读者有认知的快乐,他们有诸多可以作为立传的史料。现当代诗人就属于可立传的人物范围之内,他们立传的史料比较充分,具有传记史料价值的要求。但是要实现史料的真实性要求,不能仅靠史料的丰富和信息量大,还要对材料进行考证,注意“引用材料是否新而全、注释是否精准、结论是否正确、有无新的发现、文字有无错讹”等。张立群以徐志摩传记中关于徐志摩、林徽因、陆小曼之间的爱情细节为例,强调对相关人物不同传记版本进行横向比较的重要性,并对徐、林、陆研究中的关键问题,如徐、林是否是“真爱”问题,林对徐的态度问题,“八宝箱”问题等进行一一考辨分析,提出了新的见解。
史料的真实性应该包含两方面的意思,一是史料本身的真实性,不是伪史料;二是使用史料的真实性,不能因叙事需要而任意删削、曲解史料。张立群在“现当代诗人传记的史料价值构成”和“现当代诗人传记史料的生成与实现”中,分别就传记史料的真实性问题进行论述,指出传记史料真实性的可能及限度,很有分寸感,“真实是任何一部传记追求的境界和渴望达到的目标,但绝对的、纯粹意义上的真实是不存在的,而人们在阅读过程中不言自明的传记真实,在标准的衡量下转为一种‘相对真实’和‘文本真实’”。哪些传记相对来说既能保证史料真实又能实现传记真实呢?“经历多年准备、出自研究者之手、内容多而全的传记,会是众多同一传主传记中的优秀之作。”
三
史料只有为研究使用时才能体现价值,史料价值的大小取决于研究问题的大小,如果没有研究问题对史料的统领,史料仅仅是一堆材料而已,谈不上价值。虽然傅斯年认为“史学就是史料学”,但学术界认同此观点的不多,史料只可视为寻找历史之指路碑,可视为历史之代表或片段的痕迹,却并不是历史之自身。余英时在谈他研究中国思想史时指出其方法:“中国思想史的研究,和一般的历史研究一样,必须从某些预设或假定开始;如果没有预设或假定,则思想史的大量文献仅仅是一堆杂乱无章的原始资料,根本无法整理出条理来,更不可能从其中找到思想变迁的历史线索”。余英时这里所说的预设或假定就是统领史料的研究问题,只有由研究问题出发,才能把散乱的史料组织起来,形成线索,凸显其价值。
传记中的史料是为传记服务的,为传记作者主观条件(如传记家素养等)所影响,传记作者对史料的掌握、解读、使用等都会影响史料真实问题。传记中的史料只有以传主为中心,实现传记作者传记写作目的,才能体现史料的价值。正如有学者在论述文献史料价值所说,“文献史料的价值其实最终还是体现在它与作品认知、作品解读的关系中。也就是说,文献史料只有在它有助于文学作品意义把握的时候才是有价值的,否则就只能成为一堆垃圾”。
传记史料的价值与意义,对于传记中的史料是如此,传记作为研究史料亦是如此。韦勒克在论述传记价值时,也强调“传记解释和阐明了诗歌的创作过程”中的作用,同时他又指出不能夸大传记的这种价值,因为在他看来,“任何传记上的材料都不可能改变和影响文学批评中对作品的评价”。韦勒克既承认传记的作用,同时限定其作用,传记中的史料如记叙诗人书写诗歌的过程,能为解读诗歌提供一定的帮助,而不能代替诗歌批评本身。
韦勒克对传记的这种观点其实包含了一个传记书写的永恒性问题,即传记“史与诗”的问题,传记之所以不同于纯粹史料的编辑,就在于有传记作者情感、观念等散落在传记书写过程中,传记作者的这一书写作用就体现在传记之“诗”中。“史”是传记追求的目标,而“诗”是传记写作必然存在的一种客观效果。这是由传记作者的角色与工作所决定的,“理解传记问题的基本视点就是,从原则上看,无论一个人在表达什么、掩饰什么,他总是在传达自身,他的所有思想、言论与行为都存在于一个富有弹性的传记之网中”。即使传记作者尽全力地贴合传主的生平经历,用史料说话,不抒情、不议论,其情感思想等仍然会留存在传记中,只不过程度不同而已。若虚构和想象影响了史料的真实性,就成了传记文学,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传记了。
张立群对传记作者与传记史料的关系作了较为充分的论述,强调作为传记主体之一的传记作者对传记史料真实性的重要影响。尤其是传记作者的写作态度与写作能力,这两大因素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本传记的水平与质量。写作态度,正如杨正润所说:“应当有正确的目的,心术应当端正,应当出自公心,不能带有私利,对传主的记述和褒贬都应当公正,这也是麦卡锡所说的‘传记家的誓言’。”写作态度的核心是真实、客观、公正。写作能力,张立群从传记作者的学术能力、史料搜集考证能力和写作能力三个方面加以论述。张立群注重学者、研究者在传记学术能力上的优势,“学者、研究者由于秉持自己的学术态度,拥有多年的研究经验,熟悉本学科的研究动态,有综合独到的见解,可以客观公正地评价传主,从而很容易抵达传记‘四长’(“德”“才”“学”“识”)的层面”。传记作者的史料搜集考证能力,张立群详细分析了传记作者的眼光对史料搜集与甄别的影响,指出该能力在传记书写中实现“史”追求的重要性,并以卓如书写《冰心传》的过程加以例证。写作能力,张立群特别指出传记作者“感悟传主”与必要而合理的“想象”“虚构”及推测能力,传记作者要用心灵体验传主,理解其所思所想、喜怒哀乐,才能走进传主的内心世界,写出令人信服的传记。这一点,对于现当代诗人传记写作尤为重要,诗人独有的特性及其人生经历,传记作者若不能深入诗人内心、感悟传主,写出来的传记往往会言不及义。而合理的“想象”与“虚构”不但可以丰富传主的形象和强化传记的表现力,而且还可以深化传记的价值。
传记“史与诗”两个标准维度,其实现全系于传记作者。中国现当代诗人传记史料问题的中心,最终聚焦在传记作者,尽管传记作者可以把自己的情感倾向、价值判断与审美追求散落在传记中,呈现一种“诗”的风貌,但从另一个层面上看这也是一种真实,关于传记作者自己的一种真实。这就涉及到对现代传记的认识与理解,“现代传记是将人生转化为艺术的加工整合,使琐细、重复、杂乱的生平具有了整体性和秩序,便于理解和把握,体现了创造的过程,但这一艺术与虚构技艺大大不同,要遵照传记本身的逻辑与性质:传记书写不过是将如艺的人生用必要的艺术手法进行的呈示,在根本层面上,艺术从属于真实”。也就是说传记的“诗”要从属于“史”,即真实性是传记的第一要义。而传记的真实性,既要求传记史料的真实、传记作为史料的真实,也要求传记作者写作的真实。而其中史料真实最为基础,也最为关键。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张立群注目于中国现当代诗人传记的史料问题,尤其是强调居于传记写作中心的写作者,抓住了问题核心,所论述的问题也切中肯綮。
结语
张立群的“中国现当代诗人传记”研究,是传记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研究的重要成果;在版本辑录和史料收集方面、传记史料理论与方法方面,都作出了贡献;在一些传记案例分析上,也有比较精细独到的见解,让人耳目一新。当然,关于中国现当代诗人传记,仍有诸多可继续研究地方,正如张立群自己所说,这是一个新的研究领域,许多问题还未思考得十分清楚,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比如为什么要在众多的现代传记中选择“中国现当代诗人传记”作为研究对象,是否是因为“诗人身份特性”或“诗人传记的‘诗性’”?
总之,“中国现当代诗人传记研究”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张立群在广泛收集中国现当代诗人传记版本的基础上,对中国现当代诗人传记史料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理论与方法探究,具有重要价值与意义,可作为传记研究、现当代诗人研究及文学史料研究的一种可资借鉴的研究范式。
注释:
[1]关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料研究热的事例很多,李强在《“史料”何以成为“方法”——论中国当代文学史料研究》(《文艺争鸣》2019年第10 期)一文中对2016-2018年中国当代文学史料研究热点事件及学者论文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梳理。
[2]李怡《百年中国新文学史料的保存、整理与研究》(《新文学史料》2017年第2 期)详细梳理了自新文学发生以来至今在史料方面的保存、整理与研究情况。
[3][16]李怡:《发现现代中国文学史料的意义与限度》,《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2017年第1 期。
[4]谢泳先后出版《中国现代文学史料概述》(厦门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中国现代文学史料的搜集与应用》(台湾秀威咨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版)和《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刘增杰出版《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中西书局2012年版)。
[5]谢国桢著:《史料学概论》,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0页。
[6]张宪文著:《史料与史料学研究》,见《江苏社科名家文库·张宪文卷》,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318页。
[7]谢泳:《建立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的构想》,《文艺争鸣》2008年第7 期。
[8]系统提出“文学史料层位划分”的是潘树广、涂小马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料学》(上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参见该书第130—131页。
[9][11][12][13][14][20]张立群著:《中国现当代诗人传记史料问题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51页、35—36页、71页、28页、71页、97页。
[10]谢泳著:《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28页。
[15]余英时:《综述中国思想史上的四次突破》,见《中国文化史通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1页。
[17][美]雷·韦勒克、奥·沃伦著,刘象愚等译:《文学理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68—74页。
[18][21]梁庆标:《编译前言·主体的复归与传记的挑战》,见梁庆标选编:《传记家的报复:新近西方传记研究译文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页、2—3页。
[19]杨正润著:《现代传记学》,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8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