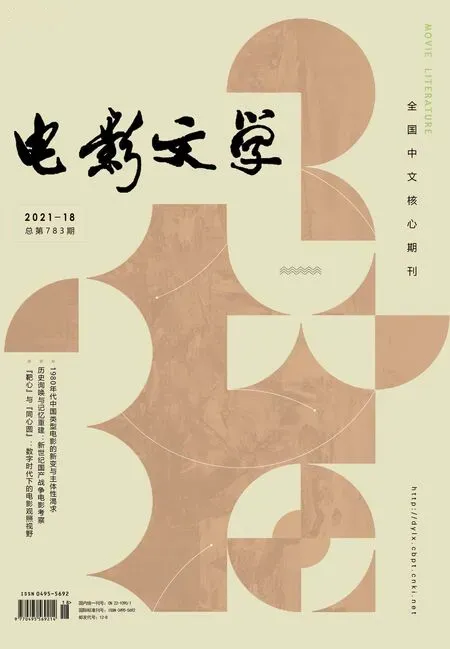《候鸟》:叩访哥伦比亚被遮蔽的历史
谷佳维
(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天津 300071)
哥伦比亚电影《候鸟》(P
ájaros
de
verano
)作为2018年度戛纳电影节“导演双周”单元的开幕影片,由西罗·格拉(Ciro Guerra)与克里斯蒂娜·加列戈(Cristina Gallego)联合执导。这个艺术组合此前已合作完成了三部作品——格拉任导演、加列戈为制作人,其中《蛇之拥抱》(El
abrazo
de
la
serpiente
,2015)成为哥伦比亚唯一一部获得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外语片提名的影片。格拉与加列戈一贯致力于运用电影语言对哥伦比亚当代历史进行个人化的书写,作品带有实践新历史主义的显著特征。例如,《流浪的影子》(La
sombra
del
caminante
,2004)通过描述两位主人公的伦理与情感对抗,聚焦该国的游击队与武装暴力问题;《蛇之拥抱》则以亚马孙流域一位土著族裔的视角出发,探讨本土文化与西方文明之间的关系;而在《候鸟》中,创作者通过讲述主人公个人命运的起落,对困扰哥伦比亚至今的毒品问题的源头进行了追溯,重构了该国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早期毒品贸易史。《候鸟》的创作理念展现出两位导演的新历史主义品格,正如加列戈所指出的:“这是一种进入未知领域的渴望……我们试图编纂一份没有写出来的记忆,一份活生生的记忆。我们并不想讲述出现在图书馆书架上的故事,而是想讲述一切无声的东西。”本文从导演参与哥伦比亚国家历史建构的意图出发,考察影片如何借助挖掘边缘人物的沉默话语,颠覆在毒品贸易这一话题上占据主流地位的“美国叙事”,并通过提供本土化的“哥伦比亚版本”,召唤本国民众的集体记忆,从而使塑造新的民族认同成为可能。
一、以边缘视角撬动主流叙事
长久以来,在哥伦比亚毒品贸易史与毒品战争史的相关文艺作品中,“美国叙事”一直占据主流地位。大量的美国电影以及《毒枭》等电视剧的生产“成功地”将“贩毒”事件打造成为一种奇观,在全球范围内吸引了大批观众。“美国版本”的绝对优势使得“报纸、电视新闻、互联网、电影里甚至小说中,都传播着存在于幻想的毒枭形象。这其中的大部分故事是基于一种对强悍、勇猛与暴力的‘超人’神话,以及追求奢华、充满‘冒险’的生活方式的构建”。格拉对上述情况公开表示了忧虑:“目前为止,电影院不是在吸引反思的目光,而是制造偶像、上演暴力与毒品文化的狂欢……巴勃罗·埃斯科瓦尔成为这么多人的偶像,这是一个悲剧。”正因如此,导演拍摄《候鸟》的重要动机之一,就是“不要让这个故事只从国外讲起”,这体现了创作者的新历史主义品格,即提倡用“小写历史”(histories)对“大写历史”(History)进行解构,从而质疑大写历史的必然性与真实性。
具体来说,电影《候鸟》对哥伦比亚毒品贸易史的反思以及对“美国版本”的解构,是通过深入历史裂隙、以边缘视角撬动主流叙事得以实现的。影片的主人公拉帕耶是一名放牧为生的瓦尤族(el wayúu)青年。20世纪60年代末,为了凑够迎娶新娘的丰厚彩礼,他留意到美国“和平队”志愿者对于大麻的需求,从此开始了贩毒生涯。作为哥伦比亚最大的原住民族群,瓦尤人居住在该国北部的瓜希拉沙漠,拥有强大的传统和极具特色的文化。电影在人类学家的监督下进行了充分的前期调研工作,并通过聘请相当数量的瓦尤原住民加入创作团队,保障了作品在处理原住民文化相关细节时的准确性。影片借鉴瓦尤颂歌“哈伊奇”(jayeechi)的结构,将故事分为五个“乐章”,同时使用土著语言瓦尤纳基语(Wayuunaiki)进行拍摄,并采用了新历史主义倡导的人类学“厚描”(thick description)的手法,对瓦尤部族的文化传统进行了充分展示:包括母系氏族的构成、以游牧和纺织为主的生活方式、以物易物的贸易手段、对梦境与死后世界的解读、婚嫁和丧葬习俗等。而其中着重描绘的,是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瓦尤“信使”(palabrero)制度——拉帕耶的舅舅佩雷格里诺便是一名信使,拥有这一身份的人负责游走在不同部族之间,传递消息、解决冲突,其传递的话语等同于口头形式的契约,代表了瓦尤人以道德作为保障的对话机制。电影通过多个场景表现了佩雷格里诺如何行使信使的权责——包括代表拉帕耶向对方部落提亲、代表部落驱逐冒犯道德规条的合作伙伴、发生流血冲突时前往对方部落求和等。在瓦尤传说当中,信使以鸟类命名,是部族之间和平的使者,这显然成为了《候鸟》片名的重要来源。
然而,“候鸟”不仅象征着瓦尤古老的传统,同时也指向了电影中表现的,毒品贸易早期在瓜希拉沙漠起降、将大麻运往美国的轻型飞机。这种金属制成的大鸟的到来标志着资本主义的野蛮侵袭,它为原住民群体带来了畸形的经济繁荣,同时也撼动甚至摧毁了他们的道德准则。影片的后半部分,毒品贸易的巨大利益以及外来人的干涉和唆摆引发了瓦尤部族之间的仇视与激烈冲突,本应备受尊重的信使居然在和平谈判中被杀,象征了传统的彻底失落。通过对瓦尤人这一边缘群体的聚焦,《候鸟》为我们提供的,是一种迥异于“美国版本”的历史叙事。在这一关于毒品贸易史的“哥伦比亚版本”中,瓦尤人被遮蔽的历史碎片被精心捡拾和拼接,其手法与新历史主义倡导的“轶闻”(anecdote)相类,使作品拥有了令人“惊奇”(wonder)的力量,吸引人们驻足观看,并对已形成的刻板印象进行反思。通过对鲜活个体生命的关注以及对边缘历史的发掘,电影向我们展示了毒品贸易如何令原住民的契约被损毁、绵延千年的传统道路遭遇中断,从而解构了“美国版本”主导的,以毒枭的偶像化与暴力美学为特征的主流叙事。
二、召唤集体记忆、建构民族认同
“文本的历史性”与“历史的文本性”由学者蒙特洛斯(Louis A.Montrose)提出,是新历史主义的重要命题。在这个意义上,文化、历史等被视为社会性文本,与文学、艺术之间具有互文性,相互指涉、相互影响,彼此在共识层面展开对话与协商。文学和艺术并非简单、被动地反映文化的特征,而是能够通过自身的优势对文化进行塑造和重建。这一将文学艺术视为构建历史的能动力量的创作理念在《候鸟》当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正如格拉所说:“我的电影首先是为哥伦比亚人制作的,我想让他们更加接近自己的本质,接近让我们成为我们的那些深刻的历史。”
格拉强调,迄今为止“贩毒仍是哥伦比亚社会公开的伤口,被当作巨大的耻辱”,正因如此,该国国内讲述毒品贸易史的电影“不超过五部”。而在上述有限的作品当中,不难觉察“美国版本”的强势入侵使得哥伦比亚本国的创作者们往往也会不自觉地认同这一“外来者”叙事视角。对此,加列戈敏锐地指出,当本国人拒绝对这一问题加以正视,“别人就会替我们说出来,而别人谈论我们的方式是把我们当成贩毒者、恐怖分子和最坏的人”。毒品贸易造成的深层文化创伤令哥伦比亚人陷入了集体无意识与结构性失忆,而“美国版本”的大量生产则强化了这段不光彩的历史带给民众的难言的挫败感。从这个意义上说,《候鸟》的出现正是对这段真切存在却被刻意回避的哥伦比亚人集体记忆的殷切召唤。
值得说明的是,《候鸟》对“美国版本”的解构并未局限于偶像崇拜与暴力美学层面,而是延伸到了对毒品贸易根源的挖掘上——影片当中,正是美国和平队的志愿者诱使主人公走上了毒品贩运的道路。成立于1961年的和平队声称其宗旨是为需要帮助的第三世界国家提供训练有素的“中等人力资源”,实际上则出于反共形势的需求,通过附带政治枷锁的援助项目输出美国文化与价值观,其中更隐含了第一世界凌驾于第三世界之上的不平等权利关系。《候鸟》运用视觉语言挑战了“美国版本”将哥伦比亚人粗暴地塑造为“贩毒分子”的叙事,通过让主人公拉帕耶占有视点镜头,突出其叙事中心的地位,将哥伦比亚人从一贯“被看”的客体转换为“观看”的主体,使其重获被剥夺的话语权。例如,电影其中一幕运用过肩镜头描绘了拉帕耶冷漠地望着和平队员们吸食大麻后狂欢的场景。当同伴向他靠近,调侃“大麻真是全世界的快乐源泉”时,他讽刺道:“就只是他们的快乐罢了。”通过令原住民叙事主体以“白眼”的姿态“观看”和平队志愿者,电影完成了自身的叙事批判,不仅对美国自诩的第三世界救助者的形象进行了颠覆,更凭借赋予沉默的声音以可见性,为哥伦比亚民众提供了审视本国毒品贸易史的崭新视角。
格拉表示:“让拉美人观看拉美电影,这对我们行业的发展和民众的精神成长都是至关重要的。”《候鸟》浸润了创作者对于哥伦比亚毒品贸易史的深入思考,而这种思考是“美国版本”囿于自身的立场和角度无法提供的。电影讲述的故事可被视为一个隐喻,“一个更阔大的东西的缩影”,即在现代化的进程当中经历了曲折与挫败的“哥伦比亚的缩影”。通过“与死者对话”(speak to the dead),当代哥伦比亚人寻找到了被遮蔽的先辈在历史上留下的足迹,靠近了鲜活的个体生命并与之产生心灵的共鸣,从而使观看和反思电影成为了“自我塑造”(self-fashioning)的契机——新历史主义认为,主体的产生虽然并非自觉、自动的过程,而是文化、权利与意识形态作用之下产物,但对于主体所拥有的阐释和建构功能,我们依然可以怀抱信心。《候鸟》向历史的幽暗处聚光,尽管其展现的历史是碎片化的、边缘的、模糊的,却真实地存在于哥伦比亚民众的集体记忆之中。记忆面向过去,但并非完全属于过去,反而与当下紧密相关,与当今人们的需求无法分割。电影召唤着当今的哥伦比亚人共同叩访历史,从中感知并确认民族的情感记忆,进而感知当下、确认自我,走出集体无意识与结构性失忆的困局,为自我的现实存在找到合理的解释路径。
在《候鸟》的结尾,创作者为观众展示了虚构与现实层面都未能解决的问题:拉帕耶的家族骤然兴盛继而衰败,当一切落幕时,唯一幸存的只有他尚未成年的女儿。女性原本是瓦尤氏族的核心角色,她们通过梦境与祖先连结,获得祖先的启示。然而,当这个小女孩试图挣扎着生存下去时,却发现自己早已“忘记了祖先的知识”,成了一个“不会放牧的瓦尤女孩”。小女孩的命运令观影者忧虑,同时也使哥伦比亚人不得不深入思考,如何疗愈文化的深层创伤,如何面对国家道路曾经丧失的历史,以及依旧艰难的现状和充满希望的未来。
《候鸟》中的信使佩雷格里诺曾说,“记忆必须口口相传,赶在风将它吹散前,将它变作鸟的歌声”。值得关注的是,近年来,运用本土视角讲述本国的当代历史,已经成为哥伦比亚相当一部分文艺工作者的共同理念——除《候鸟》外,导演劳拉·韦尔塔斯·米扬(Laura Huertas Millán)的短片《迷宫》(El
laberinto
, 2018)、作家胡安·加夫列尔·巴斯克斯(Juan Gabriel Vásquez)的小说《坠物之声》(El
ruido
de
las
cosas
al
caer
, 2011)等,都对该国的毒品贸易史进行了解构和重塑。我们有理由相信,越来越多此类作品的出现将帮助哥伦比亚民众摆脱被动接受“美国版本”定义的命运,成为“自我的主要建构者”,在领悟个人命运与国家历史的连结中,塑造新的民族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