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镜重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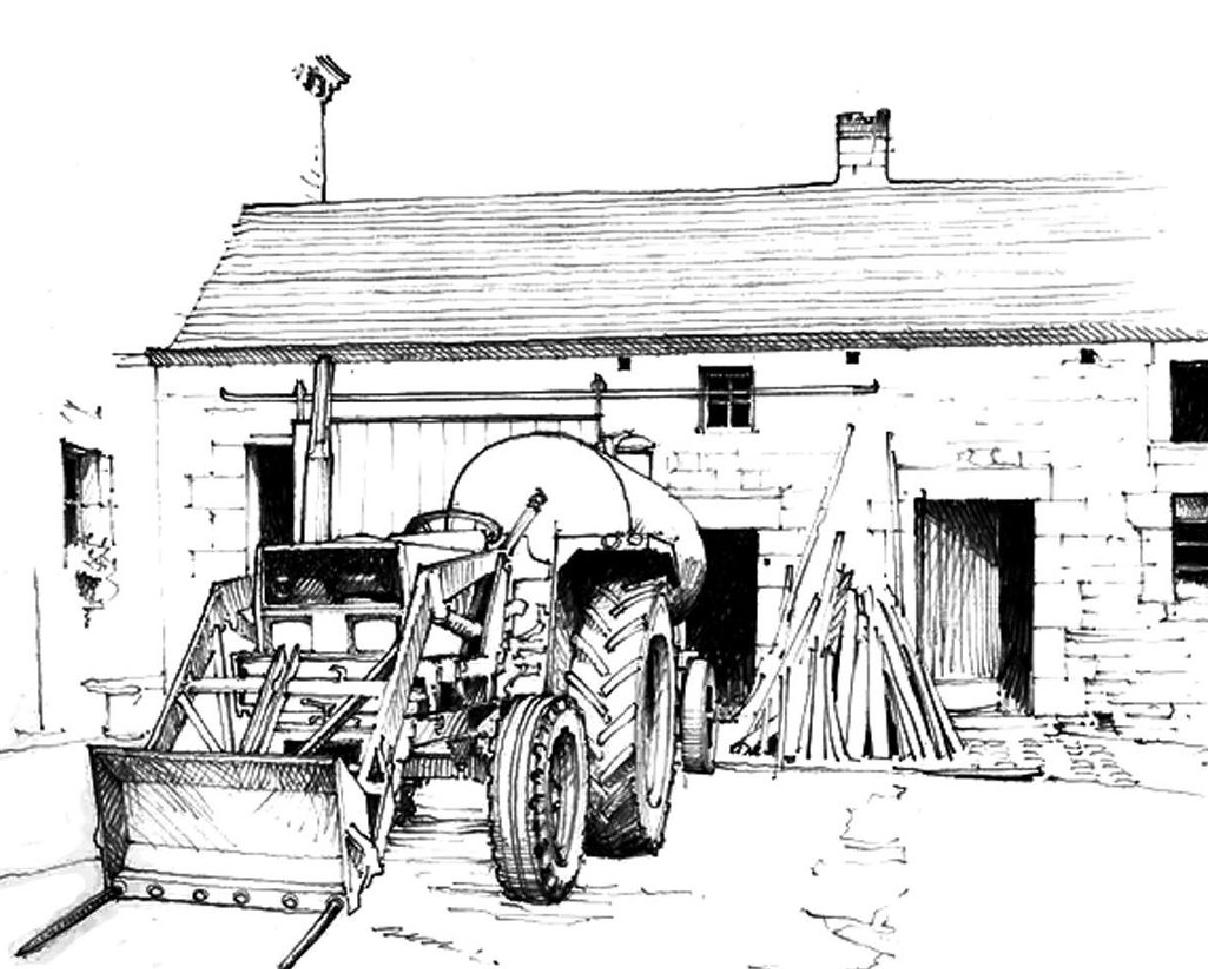
作者简介:
祁和山,江苏省作协会员。作品散见《时代文学》《四川文学》《雨花》《黄河文学》等杂志。
1
老孙是叉车工,主要负责金工车间的坯件或半成品周转任务,把它们铲运到各种床子前,厂区里就开始机声隆隆。下午没什么事,他把叉车停在角落,在上面半坐半躺,闭目养神,或四处转转,看到有人谈话过去听听,偶尔插上两句。常常出来几分钟就有电话追过来,喊他铲运东西。
他最爱去的地方是铣床。铣床工姓张,叫晓梅,四十出头,肤白,精瘦,长着一张狐狸脸,老是皱着眉,斜眼看人,嘴角上扬,说话咬牙,好像所有的男人都讨她便宜又不给钱。他们在背后说她是飞机场,我仔细观察过,确实只见罩不见胸。老天爷是公平的,胸再大点儿,她头就要仰上天了。俗话说一白遮三丑,我总觉得她白得不正常,至少不是白里透红的白。
机械厂是和尚庙,除了库房和办公室,车间里的女工少得可怜,即使不好看的女人,只要身上的零部件不差,嘴巴甜些,干活就不会吃亏。两个金工车间,四个女工,老孙原来雨露均沾,在她们之间转悠,后来只围着张晓梅一个人转。估计拿下别人轻而易举,没有成就感。另外三个女工里,有一个也是铣工,她的铣床和张晓梅的铣床靠在一块。不过,她长得丑又邋遢,没人打她主意,最多拿来胡乱开玩笑。
食堂在东北角,三四百米远,每天吃中饭,老孙把电动车停在车间门口,张晓梅不慌不忙地出来,横坐在老孙后面,像电影电视剧里跟丈夫骑毛驴回娘家的小媳妇,一路呼啸着直奔食堂。张晓梅找位置坐下,左顾右盼,老孙去窗口排队,打两份饭菜端过来。肩不挑手不拎,一个班最多开两三小时的叉车,可能家里伙食又不错,老孙一天到晚红光满面,精神头十足,不像快要退休的人,估计到时候退而不休,拿双份钱。老孙原来在轧花厂上班,下岗后开饭店,几年后跟单位一样破产倒闭。有人说,小大妈吃饭不收钱还倒贴,把饭店活活吃垮了。他笑而不语。到底什么原因,只有他清楚。他从不主动谈这方面的事,更不解释,始终是个谜。
大家喊他孙师傅和老孙,背后也有喊孙猴子甚至猴子。全厂只有他姓孙,一听指的就是他。我们不在一个车间,但是天天见面,竟然叫不出他名字。其实也不奇怪,门卫三根子,厂里上上下下人前人后喊了十几年。一天他姑娘来找他,问了几个人,都说我们厂没有这个人。他姑娘急了,人家都喊他三根子。众人笑了,哦,三根子,晓得晓得,你早说嘛,去办公室送报纸信件了。
老孙一天到晚穿得客客气气,板寸头,皮鞋能照见人影,戴着黄澄澄的大方戒,离得近会闻到若有若无的香味,好像随时参加宴席。这都不是重点,老孙之所以是老孙,不说说领带就对不起他。天热没办法,否则他脖子上都要挂领带,每天不重样,没有一百也有大几十条。如果老板和他在一块,像是给他扛旗打伞的跟班。
小舅子的朋友开物流周转站,缺少一个开叉车的,想介绍我去。他叫我尽快学会了,最好拿个证。我打听过了,在技校报名并考试,费用四百八。理论和路考都不难,只要到现场,很少不过关的。厂里有两辆叉车,只有老孙一个叉车工,另外一辆红叉车随处停放,他忙不过来时,车间主任就爬上去帮忙。有现成的叉车,我也从没摸过它,心里多少有点儿紧张。我想到了老孙,请他临场指导一下。
冰箱里有一包中华香烟,过年招待客人剩下的,省得买了。每年过年都会剩一两包,我不吃烟,但不能眼睁睁看着它发霉扔进垃圾桶,拆开后想起来就吸一支。老婆说我是乌龟吃大麦,白白糟蹋粮食。我也不分辩,女人很多时候是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你若较真会真有麻烦。我在金工车间转了一圈,没看到老孙,先去上厕所,半路上正好遇见他。车间里人多眼杂噪声大,不便交流,这种地方最好了。我拦住他说,孙师傅,跟你说件事。他不吱声,笑眯眯看着我。防止他多心,我首先声明,小舅跟人合伙开了个物流周转站,想叫我去开叉车。他说,蛮好的嘛,不要在一棵树上吊死。我说,可是我不会开,想请你教教我。他说,简单呢,爬上去就开,还有一辆叉车钥匙不拔,你随时能开,不过要背着些干部,看到了不好。我說,从来没摸过,你能不能教一次?他说,不碍事,一有机会我就教你一下。我说,好的好的。
前后没人,我掏出那包中华烟,他大概以为是红杉树,没拒绝,松垮垮握着。两种烟的外壳都是红通通的,不细看差不多,但价格相差两倍多。我刚要走,他烫手似的把那包烟塞到我手里,说不要不要。送出去的东西怎能要,我抓着香烟的手伸进他外套口袋里,指头一松,它滑了下去。我说,我不吃烟,拿住了。人家看见了以为我们在打架,难看死了,我还要上厕所呢。他不再坚持,说,好的,我就不客气了。你想学的时候喊我一声,简单呢。说老实话,如果特意去买,真舍不得,最多红杉树。因为叉车不是他家的,换成别人,打个招呼,或者丢给他一两支香烟了事。
第二天下午,他出来闲逛,突然想起答应过的事,把我带到红色叉车前说,这辆叉车是老式叉车,带离合器,会开它别的叉车都会开了。他讲解了一些叉车主要部位的作用和操作步骤、注意事项。我有些忐忑,希望他能手把手地示范一下,他说,没事,简单呢,你单独开,我在旁边看着。我一扭钥匙,点火,踩离合,挂挡,车子向前缓缓滚动。我很兴奋,无意中瞅了眼后视镜,满脸通红,脑门上挂满汗珠,摇摇欲坠。老孙说,不是会开了嘛,我说过了很简单。前后不到两分钟,他叫我下车,说被干部看见不好,等他们不在的时候随便开,没人说话。把叉车停在过道旁,我意犹未尽地拍拍它厚重的屁股。
下班时我发现叉车还停在车间里,大喜,等他们全走了,我跑去把门拉上,爬上叉车前进后退拐弯,偌大的车间里响起了持续的轰鸣声。窗外天色渐黑,看看手机已开了半小时,赶紧下来。下次训练铲运东西,先从空木箱开始,再增加难度。
2
我在装配车间,有产品需要铲运,组长就打电话给老孙。有时他一喊就到,有时金工那边太忙能等半天。一次,组长打过电话他迟迟不来,这批组装的产品明天发车,还要去试压和喷漆,他说你不是老爬上去开吗,把它铲到试压池。我摩拳擦掌,犹豫一下说,干部看到不好。他说,不碍事,他们说话由我对付,不要耽误发货,孙猴子不来上班工厂难道就关门了。以前都是偷偷摸摸,光明正大地开还是头一回。一次真枪实战,比演一百次习强。
我把叉车开过来,把两条长臂伸进大阀门下面,再升高,大阀门向前一歪,在惊叫声中倒在柱子上。出师不利。我浑身冒大汗,组长说法兰盘是圆的,应该先往后仰再升高。他们用行车把阀门吊正,我重新操作一遍,这次稳当当地把阀门铲转到西边车间。老孙来的时候,还剩一只阀门,他跟我一块把它们铲走。我心有余悸,他说,正常,熟能生巧,多铲几趟就好了。干部看到我开叉车,没吱声,等于默许了我的行为,悬着的心终于落下来。
装配车间需要叉车就由我负责了,驾驶技术突飞猛进,有人说孙猴子现在轻松多了,更有时间往飞机场那里跑了。有人说,就怕他被人家男人把腿打断了,出来混迟早要还的。那人说,你们不晓得吧,飞机场的老公赌吃嫖样样沾,根本不问她们娘儿俩死活,没钱就跟她要,要不到就打。众人听了,神情各异。我说,老孙天天去,得手了没有?组长说,飞机场精呢,恐怕连根毛都没摸到。他在飞机场面前真像个孙子,样样事情做,上班先去她那里看看,如果有东西需要铲运,会第一个帮她完成。还给她洗工作服,带零食,一大袋,做得最多的是卖苦力。他在铣床边跟张晓梅拉呱,碰到要铣的工件比较重,搬上搬下,张晓梅只管用手指摁摁按钮。老孙做这些事时,一点儿也不藏着掖着,很坦然,就像张晓梅是他失散多年的老婆,他在将功补过。
我半信半疑。一次下雨,上厕所时从金工车间里过去,快到铣床时一抬头,老孙正往工作台上放大轴。大轴长三十几厘米,十几斤重,一根轴上要铣四个键槽。老孙把大轴放好后,捏出一根香烟点上,不知跟张晓梅说了什么,哈哈大笑,好像中了五百万。张晓梅还是那种表情,心愿意不愿地操作着床子。车间里的人熟视无睹,没有人朝这里看一眼,好像就应该这样。我目光在他们身上多停留了一会儿,老孙捕捉到了,冲我笑笑。我也笑了笑,再看就少见多怪或不礼貌,头也不回地往前走。
不管怎么样,在叉车这一块,他至少是我三分之一的师傅。自从那次教我分把钟,见到他,我会点个头或者笑一下,算是打招呼。他也客气,每次都回礼。那天我铲运东西,老孙也在铲运,相遇时他冲我说话,两辆车的轰鸣声太大,我听不清他说了什么。他又说一遍,我还是没听清,我不想掉头,开走了。
他脸上标志性的笑容不见了,阴沉沉的,好像大雨欲来。他这个样子已不是一天两天,我点头或微笑,他却爱理不理。我很奇怪,我没有借他钱不还,没有说过他坏话,没有跟张晓梅说过话,更没碰过她一根手指头。想来想去,没有任何地方得罪他,但他的态度分明跟我有深仇大恨。我不解,也不想去求解。问心无愧的同时,心里多少有些不快,你不睬我,我还不睬你呢,有什么了不起的。你是国营单位出身,我也是,而且第一份工作还是跟你同系统。我还给你一包香烟,中华香烟,除了我谁能做到。叉车是厂里的,谁都可以开,我不过尊敬你一下,你倒客气当服气了。再看到他,视而不见。
我在场地上干活,老孙过来说,以后尽量不要开叉车。我有些惊讶,看着他一时不晓得该说什么。他说,开叉车又不是你分内的活,开得再好也不多给你一分钱工资。一旦出了什么安全方面的事情,吃力不讨好。我愣住了。以前鼓励我开,现在不准我开,唱的哪门子戏。我说,他们干部看到也不吱声,不碍事。他脸色更加阴暗,说,你听就听,不听拉倒,我是为你好。我不以为然,需要开叉车的时候还是爬上去。那天,我刚把叉车发动起来,有人说,老孙气死了。组长说,二五卵子,人家小郑铲转东西,减轻了他许多负担,换作我高兴都来不及。那人说,他嫌工资低,正在跟干部要求往上涨,你去铲东西不是挖他的墙脚吗?我恍然大悟,原来是这么回事,怪不得处处摆脸色给我看。你有想法可以明说,为什么让我猜谜语?你累我更累。我不是个眼里没水的人,只要你开口,我不可能不配合的。
我从车上跳下来,不知者不罪,现在晓得了再开就是我的错,说一千道一万,我不能挡了人家财路。组长说,你不要听孙猴子的话,车子又不是他家的,凭什么不準你开,换作我反而更要开,气气他。我意志坚决,没有再往车上爬,算了吧,都是打工的,窝里斗不好。组长只得打电话喊老孙。他来了,看到叉车就停在旁边,说,怎么不开?组长说,你不准人家小郑开,人家就不开了。他笑了笑说,我有什么权利不准他开,他要开就开,没人绑住他手脚。一连几天,我不摸叉车,闲下来多歇歇也是好的,何苦没事找事做还受气。
喊老孙,即使来也慢吞吞的,车间主任急性子,亲自上叉车。他忙,关键是不想老开,怕掉价,开几次后不耐烦了,去找生产科夏科长。为了摆脱叉车纠缠,他帮老孙说了两句好话,夏科长也不愿得罪人,反正又不要他掏腰包,乐得做个顺水人情,同意每天给老孙增加十块钱。叫他好好干,以后不要得寸进尺。一天两天看不出来,一年下来就可观了,捡到的钱。
老孙脸上又眯眯带笑。
3
有一批待组装的零部件要清洗,组长让我开叉车,我说,老孙马上又不高兴,我不想出人命。组长说,已经加给他了,现在他巴不得你一天到晚不停地铲呢。我本来不想再开,让他独领风骚。又一想,不是开飞机坦克,你不开有人开,还不如我自己开,多锻炼锻炼。老孙说,你技术快赶上我了,老早就能独当一面了,怎么还不去你小舅子那边开?我说,提到这个事我就来气,驾驶证都拿到手了,又不要我去。也不能全怪他,周转站不是他开的,说话没用。老孙笑笑,没吱声,我心里突然咯噔一下,竟然有些发虚。
下半年老加班,辛苦了,老板把一家酒店的二楼全包下,举办元旦大会餐,犒劳犒劳大家。多少年不举行大规模聚餐了,我们很开心。男工们穿得跟平时差不多,女工们个个花枝招展,张晓梅还抹了口红,大厅里的灯光很亮,把她的脸照得更嫩更白。大家三三两两地谈天说地,有的跟服务员要来扑克,掼蛋,围了两三圈人看热闹。说是随便坐,也不能乱坐,一个普通工人硬要跟干部坐一块,浑身不自在。酒席如相亲,也要讲究门当户对。
我们这一桌几乎都是本车间的。我们离门口最近,老孙来得迟,进来后一屁股坐在我旁边。他属金工车间的,但在厂里到处跑,除了领导桌子,不管坐哪里都没毛病。
老孙穿得比平时还讲究,像個老新郎官。我面前正好放着白酒和饮料,担负起敬酒的重担。我站起来挨个儿倒酒,都给面子,或一杯或半杯,不想喝的,被我一劝也倒了一点点。唯独老孙,无论怎么劝,油米不进。一桌人几乎都开了口,让他多少喝些,他右手捂住酒杯说,胃不舒服,不喝。有人起哄,说我这个桌长没威信。组长把酒瓶拿过去说,我替老哥哥倒上,就几滴,热闹热闹。我们跟他喝过几回酒,半斤不在话下,而且他在家里也天天喝,今天怎么回事?
有人给厂里的马屁精论资排辈,老孙得票最高稳居排行榜首位,被尊称孙老大。老孙身上正常放着高中低档三种香烟,看人点菜。我不太相信,从来没看过他拿错烟,估计他不会明目张胆地做,背着人干的。那天加班发货,他把产品往集装箱里铲运,结束时已七点多,夏科长说大家辛苦了,上饭店。老孙酒喝多了,手不做主,先掏出十一块一包的红南京,散给我们。夏科长从厕所回来,他捏出一支,刚要递过去,突然又缩回去,从另外口袋里掏出二十块一包的红杉树,弹出一支,递过去,夏科长说,我吃烟不分牌子,随便。老孙不语,笑眯眯地扬了扬下巴。夏科长拿了一支,老孙的打火机吐着火苗已恭候多时。我说,我敢打赌,你口袋里肯定还有一包。老孙往后退了一步,说,就两包就两包。有人说,副总来了。他说不可能呀,却扭头去看,我们大笑。
组长一直举着酒瓶。
老孙把酒杯翻过来放在桌上,双手抱胸往椅背上一仰。有人打圆场,算了算了,老孙不是滑头,实在不吃就算了,可能真不能喝。我把组长手里的酒瓶拿过来,说,不喝拉倒,我还舍不得给他喝呢。他每个月总有几天不方便,请大家多多谅解。众人一愣,大笑。他说,小绝怂没大没小的,不上规矩。有人不真不假地说,白酒不吃,饮料也不准吃。众人说,对对,饮料也不准吃。他拉长声音说,就不吃,我专门吃菜。你们要是连菜都不准吃,我就到别的地方吃。他说着话,四处张望,眼珠子盯住东南方向不动了。
我顺着他目光看去,张晓梅在那里。
夏科长原来在别的桌上,那里坐着一个他不喜欢的人,端着酒杯非要跟我们挤挤。夏科长年轻,没官架子,我们吃吃喝喝老喊他。他有时候推掉一些我们认为上档次的饭局赶过来跟我们喝酒,比如,那些同僚或副总,甚至老板的宴请。当然,他也回请我们,相处得一直融洽。桌子不大,坐十个人较宽松,十一个人就嫌挤了,我们还是开始腾地方。老孙把酒杯翻过来,笑眯眯地说,我要跟夏抖长弄两杯。我有些生气,稳稳地坐着说,刚才说胃不好不能喝,现在一看到干部又能喝了。老孙面不改色地说,难得跟夏科长喝酒,再疼也要喝。你不倒,酒瓶给我自己倒。夏科长说,给老孙倒上,倒上。组长一伸手,把我面前的酒瓶拿过去,给老孙倒了满满一杯。我冲组长一竖大拇指,他点点头,也竖起大拇指。大家看着,不吱声,笑得意味深长。膀子紧挨着膀子,夹菜都费劲,我趁机站起来说,夏科长你坐我这里,我去跟大军坐,正好有件事要问他。
我拉开椅子往外走,坐到有空位置的地方,斜对面是张晓梅,别人谈笑风生,她低头玩手机。
副总主持晚宴,致开幕词,请老板上台讲话,然后甩开膀子吃喝,胡乱敬酒。一杯酒下肚,老板唱歌,抛砖引玉,大厅里吆五喝六,鬼哭狼嚎,乌烟瘴气。快十点钟才结束,饭店离小区三四里,我走来的。老孙喝了不少酒,走路歪歪扭扭,嘴里像塞着块大肥肉,说话嘟嘟囔囔。夏科长建议到茶楼斗地主,顺便醒醒酒,反正明天放假,玩到天亮也不碍事。老孙热烈响应,带头叫好。出了酒店大门,他看了眼手机说,不好意思,今天有点事要办,下次再陪领导打牌。夏科长叮嘱他,路上注意安全。
老孙骑电动车回家,路上躲让行人摔了下来。令人费解的是,他家在北边,他在东边跌的跟头,打电话给老孙儿子的是女声。老孙儿子赶过来,老孙坐在地上直哼哼,四周不见一个人。老孙儿子见老孙不能动弹,晓得伤得不轻,打了120。等救护车的时候,他打电话给夏科长,不顾老孙反对,发了一顿牢骚。夏科长他们吓得扔掉扑克牌,直奔医院。老孙的大腿骨断了。伤筋动骨一百天,他待在家里静养,我毫无悬念地接了他的班。他住院,不少人去探望,我也去了,跟他们一样出了三百块。老孙老婆在一旁说,真想找跟他在一个桌上喝酒的人算账,不负责任,喝这么多还敢让他骑车回来。
我们装聋作哑,不吱声。这种场合,如果强调他是自己主动要酒喝,喊他打牌醒酒也不去,会引发家庭大战。老孙肚里明白,朝她瞪眼珠,说,多大的事啊,都是一个厂里的。我说过多少遍了,不准再提,命中如此躲也躲不掉,不怪任何人。去小灾破大灾,高兴才对。我说,你怎么开到东边去了?他笑着说,当时晕头转向,就好像有人推着向前走,根本做不了主。他老婆出去打热水,我说出第二个疑问,听说是个女的打电话给你儿子的,你认得她啊?他笑眯眯地说,认得呢,是我相好的。有人不放心,问真的假的,说出来让我们也欢喜欢喜。他说,不要瞎想,老哥哥要退休的人了,精力有限。那个女人是过路的,看见我瘫在地上疼得动不了,从我口袋里拿出手机打的电话。
我们都不太相信,明显有漏洞,他不承认也不能逼着他承认。真有问题,事情反而尴尬了。首先厂里一关过不去,因为副总已表过态,医保无法报销的费用由厂里承担,休养期工资一分钱不少。这种情况,毕竟相当于工伤,如果节外生枝,走势就不一样了。
4
张晓梅的眉头好像皱得更紧,也难怪,现在全靠自己把工件搬上拿下。老孙拜托过我,上班先给她铲运东西,有空再帮帮忙,一个人带着要中考的儿子,上面还有老的,老公又不学好,整天不归家。前者我做到了,后者我做不到,无论出于何种考虑。张晓梅其实蛮凶的,或者是霸道,以前没看出来,只是觉得她古怪、高冷,很难接近。一批活划算,而她暂时做不到它们,就把工装夹具全领出来,锁进自己的工具箱,另一个铣床工万事俱备,床子却动不起来,急得直转,光有猪肉没有火,干瞪眼。那个铣床工是去找车间主任。主任调解半天,张晓梅就是不拿出来。主任也没办法,开了张空头支票给那个铣床工,下次有划算的生活先给你做。
老孙上班,张曉梅已经是车间保管员。这个岗位属于行政人员,脱产了,既轻松又清闲,每天下班前统计一下车间里各工种领料情况。仓库和车间的保管员,一般人做不了,要有后台,没听说她有什么硬关系,否则也不是铣床工了。做了保管员的张晓梅眉头松了许多,偶尔还跟人说笑。我去干老本行,老孙也干老本行,他闲下来找各种借口去车间办公室。傻子都看得出来,他醉翁之意不在酒,但张晓梅冷淡多了,确切地说比老孙摔断腿前冷淡多了。老孙说十句,她说一句,有时候哼都不哼一声。张晓梅很少出去乱逛,在里面玩玩手机或发呆。办公室里有四个人,老孙去的次数多了,有人说,老孙,你老往这里跑,有人看到会吃醋的。老孙说,只要你不吃醋就没人吃醋,就是家里老公,同事之间说两句话也不可能吃醋的。那人摇摇头,不再废话。
我认真而严肃地警告过他,只是没说破。即使我亲眼见过副总跟张晓梅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这种事也不好明说,一旦被当事人晓得后果很严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整我的方法不止一个。除非不想在这里混,关键是我不想失去这份工作,外面就业形势不妙,不能意气用事。老孙右手转了转左手上的戒指说,大不了滚蛋,还有年把就退休了,怕哪个啊。
话说到这份上,我也摇摇头。
夏科长找到我说,你今天开叉车。我随口问道,老孙呢?他没请假呀,刚才我还看见他呢。夏科长说,他跟你对调,以后你开叉车,他装配。我高兴死了,能开叉车不错,不要整天脏兮兮的还轻松。很快,我又觉得不妥,如果答应等于落井下石,更说不清了。夏科长说,你不要有顾虑,副总安排的,叫你开你就开。我说没有叉车驾驶证,被开发区查安全的逮到不得了。他说,你去考个证,简单呢,费用报销。
老孙受了窝囊气,再待下去脸上没光,肯定会二话不说拍拍屁股走路,还有年把时间随便找个差事做做,一晃就过去了。
他没走,连想走的意思都没有。他表情平静,还带着标志的微笑,服从领导安排。装配也是人做的,那么多人能做我为什么不能做,人家老蒋比我还大两三岁呢。不把我调去打磨或者拖铁屑,已经很不错了。我怕老孙误解,特意跟他解释了一下,把当时跟夏科长的谈话一字不差重复一遍,再三强调,不是抢你饭碗,我拒绝领导会不高兴。他说,理解,不怪你。替人打工就这么回事,他们嘴大我们嘴小。你就是不开别人也会开,地球离开谁照转。让他们开还不如让你开。
不是我的错,我仍然觉得有些对不住老孙,开着叉车在众人目光中穿行,常常如坐针毡。
老孙除了喝酒,还喜欢斗地主,中午不休息,一直斗到上班。两块五块十块十五块,哪怕再多,也敢往桌上坐。他很少做地主,除非手里的牌有八九成把握赢才伸手抓底牌。有一回我在他后面,他摸了三把炸一对小王都回掉了,因为限炸,把弹炸拆开走。我直咂嘴,他也咂嘴,我就不吱声了。最后地主胜利,事后我说了,他们一点不奇怪,说正常。他欢喜别人按他的牌路走,比如他手里对子多,对家走单,两次一走,他就把牌一合,放在桌上。地主出牌,他左一个不要,右一个不要,把你心口急得生疼。
做了装配工,他还是天天中午斗地主,还是穿得客客气气,领带照打,脏工作服比我们洗过的还干净。大戒指不戴了,环境不同,再戴让人笑话。他很少有时间往办公室跑了,不过,一有时间就去,张晓梅干脆不搭理他了。他在里面抽一支烟,跟别人东扯西扯两句,回来。
张晓梅病了,白血病,已确诊。厂里募捐,工人三百,基层干部五百,副总级别的一千,老板出了一万。老孙出了三百,张晓梅来厂里交接工作上的事,他又给了她一张银行卡。他死活不说卡里到底多少钱,被逼急了,冒出一句,我一年的工资。张晓梅去大城市治疗,我们再也没有看到她,听说在家里休养,病情时好时坏。
张晓梅不来,老孙也辞了职,走的时候没骂任何人。我们给他送行,饭桌上问他,还有三四个月就退了为什么要走?他说,没劲。我说,老实交代,代价那么大,跟张晓梅有没有上过床?他说,小绝怂没大没小,不上规矩,你把我想成你了。
大家不相信,一片起哄声。他喝了一大口酒,右手抹了把嘴唇说,在座的都是弟兄们,今天我就实话实说了,张晓梅的鼻子跟我初恋的鼻子很像。我拼命回想张晓梅的鼻子,无特别之处,很普通很普通,一点印象没有。我说,她人呢?你们可以旧情复燃,重温旧梦,破镜重圆。
老孙叹口气,眼圈红了,又喝了一大口酒,说,不在了,不在了,早就不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