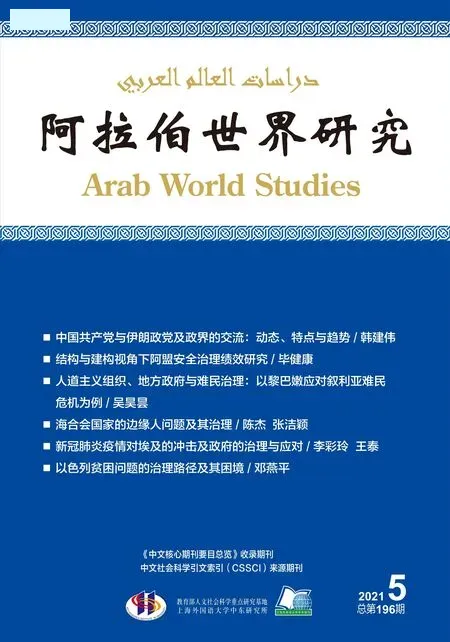结构与建构视角下阿盟安全治理绩效研究 *
毕健康
长期以来,由于敏感复杂的民族宗教问题、纠结难解的边界争端、国内冲突的外溢效应、久拖不决的阿以冲突、地区强国的博弈争雄,特别是域外大国的干涉乃至军事打击等因素,中东冲突纷扰,安全问题突出,安全“赤字”严重。鉴于安全是发展的基础和前提,以联合国为首的国际组织与地区组织把安全治理作为优先议题。狭义的安全治理指的是国家、地区组织和国际组织为了维护国际、地区、国家与人的安全而签订的条约协议,建立的机构机制(其中最重要的是联合国安理会),以及化解冲突、建立和维护和平的行为与实践。基于此,本文讨论的安全治理,即是以地区组织为治理主体的传统安全治理。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国际交往和安全治理中,地区主义兴起,地区组织发挥了重要作用。1945年3月成立的阿拉伯国家联盟(下文简称“阿盟”),是世界上最早出现的地区组织之一,却在推进阿拉伯地区一体化与地区安全治理上的作为有限。阿拉伯世界及中东的地区主义发展明显落后于西欧,也滞后于非洲、拉美和东南亚地区,以至于西方学术界提出在地区主义问题上的“中东例外论”。中东地区被称为“没有地区主义的地区”,或者“黑洞”。(1)Cilja Harders and Matteo Legrenzi, eds., Beyond Regionalism? Regional Cooperation, Regionalism and Regionalization in the Middle East, Burlington, Farnham: Ashgate Publishing Company, 2008, p.1, p. 89; 马怀信:《试析中东地区主义及其发展前景》,载《西亚非洲》2005年第6期,第46-47页。无论1990~1991年海湾危机与海湾战争的爆发,还是阿盟被断然排斥在马德里和平进程之外,抑或是在2003年阿盟在调解伊拉克战后重建以及“阿拉伯之春”后阿盟在斡旋叙利亚内战中双双失败,均凸显出阿盟安全治理低效失效,西方唱衰阿盟之声此起彼伏。

国内学者对于阿盟的研究比较薄弱。赵军和陈万里对阿盟在中东安全治理绩效及其评估标准提出了以下观点:“在中东地区冲突解决和管理中,对于阿盟的绩效判定不能仅从事件结果和最终成败来考察,而应判断其制度框架及其机制程序的原则精神在解决问题上是否起到决定性或重要作用。”(8)赵军、陈万里:《阿盟斡旋中东地区冲突的绩效评估》,载《国际观察》2013年第6期,第63页。
本文认为有必要历史地、实事求是地对阿盟安全治理的绩效进行研究。不容忽视的基本事实是,在埃及被驱逐出阿盟、阿拉伯世界全面分裂之前,阿盟的安全治理总体上成功的案例数量众多。埃以和约造成阿拉伯世界分裂,1991年海湾战争进一步撕裂阿拉伯世界,严重冲击了阿拉伯民族主义,造成阿盟安全治理绩效严重滑坡。本文在借鉴国内外学术成果的基础上,扼要梳理地区主义理论,通过案例分析在不同类型的地区冲突中阿盟对传统安全治理的绩效差异,并从结构与建构两个层面剖析阿盟安全治理的绩效问题,这对于阿盟安全治理绩效评估、观察阿盟转型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或许有所助益。
一、 地区主义理论及其参考价值
二战以来,以欧洲一体化为先锋的地区一体化与地区主义实践,极大地推动了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界对地区主义的理论探索。约瑟夫·奈提出,地区就是由地缘关系和一定程度的相互依赖联系起来的数量有限的国家,地区主义则是指“在地区基础上结成的国家间联盟或集团”(9)Joseph S. Nye, ed., International Regionalism: Readings,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 1968, p. 5.。这个基于战后西欧经验的概念,显然不适合发展中国家成立的地区组织,因此厄内斯特·B.哈斯指出,需要区分地区合作、地区体系、地区组织、地区一体化和地区主义。(10)房宪乐:《新功能主义理论与欧洲一体化》,载《欧洲研究》2001年第1期,第13-20页。
关于地区主义,有两种重要的直接相关的理论。第一种是自由主义学派的功能主义与新功能主义理论。功能主义理论认为,敏感的高政治领域如政治、安全或军事不容易开展合作,某些功能部门开展合作,就会产生“外溢”效益。合作从某个功能部门向其他功能部门扩展,是“功能外溢”。合作从功能部门向政治领域扩展,则是“政治外溢”。哈斯认为,功能性合作只有超越单纯的实用性目标,才能真正实现国家之间的一体化,形成新的政治实体。所以,政治一体化是地区一体化的根本,政治精英是一体化的中坚力量。(11)秦亚青:《国际关系理论:反思与重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67-68页。第二种是现实主义学派的政府间主义理论,主要是研究国家之间的讨价还价及其与地区主义关系的理论。该理论认为,“政治外溢”很难发生,只有在符合民族国家利益时一体化才能推进。“一体化进程是旨在使国家利益最大化的政府间讨价还价的结果,国家利益是理解地区一体化现象出现和发生动力的所在”(12)邢瑞磊:《比较地区主义:概念与理论演化》,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69-70页。。地区一体化大多在“低政治”的政策领域(如电讯、贸易等)内发生,而在“高政治”领域(如国防、外交)内国家小心翼翼地保护自己的主权。(13)Daniel Silander and Don Wallance, ed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The Humanitarian Crisis in Syria, London: Routledge Taylor and Francis Group, 2015, p. 114.政府间主义沿着现实主义学派的路径,坚持以主权国家为分析单位,这种分析路径更接近于本文的研究目标——阿盟——的实际。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三大学派,现实主义与新现实主义、自由主义与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的理论及其争鸣,对于认识地区主义和阿盟70多年来的是非功过,均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现实主义把世界或地区的无政府状态视为先验存在,强调国家利益特别是国家的生存与安全是一国外交战略与政策的出发点和根本动力,因此国家之间的争霸与冲突是国际关系的本质和常态。肯尼思·沃尔兹的新现实主义把焦点转向国际体系结构,所以又称为结构现实主义。沃尔兹所谓的结构,就是“国家之间实力的分配”,主要是大国之间实力的分布。作为处于结构现实主义理论核心的自变量,国际体系结构决定国家的国际行为,因此又被称为“结构选择”。(14)秦亚青:《国际关系理论:反思与重构》,第119-120页。
自由主义信奉自由、和平与合作,着力发现和平与合作的条件。在功能主义和新功能主义之后,以1984年罗伯特·基欧汉出版《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为标志,新自由制度主义兴起,并挑战结构选择论,提出“制度选择”,认为国际制度选择国家行为。基欧汉指出,国际体系的权力结构不能对国家的许多行为做出充分解释,“在相同的结构条件下,体系进程也会产生重要的因果意义。体系进程的最重要标志是包括国际组织、国际规制和国际惯例在内的国际制度”(15)秦亚青:《译者前言》,载[美]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国际机制一旦建立,就具有自主性,不再附属于权力结构。国际机制通过奖励合作行为和惩罚不合作行为,影响国家行为,进而促进国际合作。约瑟夫·奈认为,国际体系进程就是单位之间的相互作用,这种进程反过来影响单位的行为。(16)秦亚青:《国际关系理论:反思与重构》,第37页,第133-134页。
与现实主义信奉权力,自由主义崇尚合作不同,建构主义迷恋文化(共同理念),认为文化建构国家身份,国家身份建构国家利益,国家利益决定国家行为。对于现实主义的核心概念“利益”,玛莎·芬尼莫尔是这样批驳的:“利益并非在那里等待被发现,利益是通过社会互动建构的。”(17)秦亚青:《译者前言》,第5页。亚历山大·温特和芬尼莫尔均强调,理念和过程可以解释身份和利益的社会建构,但这种理念和过程构成自己的结构,从而对国际行为者产生影响。建构主义的这种唯心主义转向,力图回答国际关系中的一个基本问题:谁是敌人,谁是朋友?在建构主义者看来,刀锋不是问题,问题在于锋利的大刀刺入谁的心脏。
二、 成与败之间: 阿盟地区安全治理
阿盟在调解地区冲突、促进成员国和平解决争端上,毁誉参半。有研究指出,在新月地带和阿拉伯半岛的核心区域之内,阿盟的斡旋活动成功率较高。在中东地区的政治意识形态危机中,阿盟同样表现出色。在所有斡旋活动中,阿盟通过与其他国际组织合作,以派遣代表团方式或阿盟秘书长亲自参与的斡旋活动成功率较高。此外,数据还显示阿盟在多数中东国家的大规模内战中斡旋活动表现欠佳。(18)赵军、陈万里:《阿盟斡旋中东地区冲突的绩效评估》,第68-69页。
审视阿盟在中东安全治理上的成败绩效后可知,20世纪7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是两个关键的时间节点。在《埃以和平条约》签订之前,阿拉伯世界内部没有陷入全面的分裂与对抗,阿盟在中东地区问题的斡旋调解上积极有为,在化解冲突、管控危机乃至阻止战争的爆发或结束战争上,均有许多成功的案例。比如,1958年阿盟成功地进行斡旋,化解了埃及与苏丹边境冲突。在1961~1963年伊拉克与科威特危机中,阿盟派驻阿拉伯威慑部队,既维护了科威特的独立、主权与安全,又迫使英国军队迅速撤离科威特。(19)Hussein A. Hassouna, The League of Arab States and Regional Disputes, New York: Oceana Publications, Inc., 1975, pp. 92-106.在1963年爆发的阿尔及利亚与摩洛哥边境冲突中,阿盟秘书长与理事会轮值主席国伊拉克代表主动介入,1964年阿盟峰会在开罗的举行,对于两国通过直接谈判和平解决争端均发挥了重要作用。(20)Ibid., pp. 215-235.
然而,埃及开创中东和平进程造成阿拉伯世界的分裂,不仅导致自身被驱逐出阿盟,还极大地冲击了阿盟的向心力和实力,直接影响阿盟在地区安全上的干预实力和调解能力。即便如此,阿盟仍然派驻阿拉伯威慑部队,强势介入黎巴嫩内战,最终于1989年促成《塔伊夫协议》,结束了长达15年的血腥内战。90年代初,海湾危机和海湾战争再次严重撕裂阿拉伯世界,阿盟未能化解危机。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解放”科威特,阿盟在随后启动的马德里和平进程中干脆被拒之门外,这一切导致所谓中东主义(Middle Easternism)风行一时。阿盟处境日艰,甚至被怀疑存在的必要。阿拉伯国家在阿盟的未来规划上分为三个阵营。第一个阵营把阿盟置于美国和以色列倡导的中东秩序之下,摩洛哥国王哈桑、约旦国王侯赛因以及一些阿拉伯知识精英,属于这个阵营。叙利亚、也门、利比亚和黎巴嫩为第二个阵营。它们坚持泛阿拉伯主义,拒绝中东主义,认为后者无非以色列的霸权企图。第三个阵营采取折中立场,接受所谓的新中东秩序,同时维持阿拉伯主义的名义。埃及、沙特、巴解组织和阿尔及利亚属于这个阵营。(21)Michael N. Barnett, Dialogues in Arab Politics: Negotiations in Regional Orde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232.
纵观70多年来阿盟的安全治理,中东显然存在几种类型的地区冲突或安全危机:阿拉伯国家(阿盟成员国)与地区非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冲突与危机,其中以阿以冲突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阿拉伯国家之间的边境冲突或安全危机,这类危机数量最多;域外大国入侵造成的危机、战争及战后重建,其中以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及其战后重建,以及至今仍未解决的叙利亚危机和利比亚危机最为典型。下文的三个典型案例从正反两个方面揭示了造成阿盟安全治理绩效高低的原因。
(一) 力所不及: 阿盟与阿以冲突
自成立伊始,阿盟担起在域外强权面前保护阿拉伯国家的重任,包括抵抗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以色列)、维护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权利、促进阿拉伯国家团结合作三大使命。这其中,抵抗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既是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兴起的强大动力和1945年阿盟成立的直接诱因,又是激发阿拉伯世界团结合作、同仇敌忾地对抗以色列的不竭动力。因此,有学者指出:“自二战以来,阿以冲突及其根本问题——巴勒斯坦问题——始终是型塑阿拉伯体系的结构及政治话语的重大力量,主导阿拉伯政治议程,构成阿拉伯政治结构的基础。”(22)Ibrahim Awad, “The Future of Regional and Subregional Organization in the Arab World,” in Dan Tschirgi, ed., The Arab World Today, p. 149.
阿盟在协调阿拉伯国家的政策和动员阿拉伯国家的资源对抗以色列方面,虽然存在各种各样的分歧与不和,但总的来说,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它大致是成功的。对于联合国分治决议,阿盟感到极为愤慨且拒不接受。1950年阿盟理事会通过决议,禁止成员国与以色列谈判政治、经济或军事协定,或与以色列媾和。1964年阿盟举行第一届峰会,成立巴勒斯坦解放组织(1976年巴解组织被正式批准加入阿盟)。1965年突尼斯总统哈比卜·布尔吉巴公开谈论与以色列的和平,阿盟理事会直截了当地予以拒绝。1967年喀土穆峰会通过了著名的“三不”决议,即不承认以色列、不与以色列直接谈判和不与以色列媾和。1973年十月战争期间,阿拉伯国家展现出空前的团结,海湾产油国对以色列、美国等实行石油禁运。阿盟专门成立了阿拉伯抵抗局(the Arab Boycott Office),为巴勒斯坦难民提供资金支持。(23)Ramy Lakkis, Arab Regional Integration: The Politics and Economics of a Fragmented Nation, Saarbrucken, Germany: Lap Lambert Academic Publishing, 2013, p. 98.
然而,在美国强有力的支持下,以色列势力日益强大,阿盟对以色列的强硬政策逐渐陷入困境,埃及开创的和平进程又引起强烈反弹。1978年巴格达峰会对一个“背叛”(巴勒斯坦事业)的阿拉伯国家采取非同寻常的立场。安瓦尔·萨达特总统批准《戴维营协议》后,埃及这个阿盟创始成员国和最重要的阿拉伯国家,被驱逐出阿盟。到20世纪80年代末,阿拉伯世界终于接受了以色列的存在和埃以和平的现实,但海湾战争后美国独霸中东,阿盟又被完全排斥在马德里和平进程之外。“阿盟过时论”“阿盟瘫痪论”喧嚣尘上。有报道说,虽然没有国家退出阿盟,但有的国家已经开始设想取代阿盟构建新的地区组织了。(24)Michael N. Barnett, Dialogues in Arab Politics: Negotiations in Regional Order, p. 213.
在阿盟的地区安全议程中,阿以冲突与巴勒斯坦问题非常特殊。阿盟不是调解方,而是站在阿拉伯人的立场上,聚合阿拉伯力量,动员阿拉伯资源,对抗以色列。巴勒斯坦问题并非阿拉伯人造成,从根本上讲阿盟没有足够的物质实力与制度能力,解决巴勒斯坦问题。阿盟在阿以冲突和巴勒斯坦问题上发挥的作用,既成功又失败,既有效又失效。这是域外强权长期强力干预的产物。
(二) 凯旋而归: 1961~1963年伊拉克与科威特危机
1961年6月19日,科威特正式独立,旋即引爆严重的伊拉克与科威特危机。阿盟做出快速反应,进行斡旋并派驻阿拉伯威慑部队,成功地管控危机,展示出阿盟在调解阿拉伯国家之间争端上的实力。
由于历史原因,伊拉克认为科威特是伊拉克的一部分,属于巴士拉省。因此英国殖民势力退出后,伊拉克就应“收回”科威特。正因为如此,刚刚获得独立地位的科威特,1961年6月20日正式申请加入阿盟,意在获得阿盟的保护。伊拉克迅速做出强烈反应,6月25日伊拉克总理卡希姆将军公开宣布伊拉克对科威特享有主权。随后,伊拉克任命科威特现任谢赫为巴士拉省管辖的科威特区长官。翌日,科威特谢赫重申科威特的独立地位。6月29日谣言传开,媒体报道说,伊拉克军队准备武力兼并科威特,伊军向科威特边境地区开进。6月30日,科威特正式请求英国提供军事援助,沙特阿拉伯也接到类似请求。7月1日,英军登陆科威特,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
当时的阿盟处于不利的地位。一方面,英军重返科威特是阿盟和阿拉伯国家所不愿看到的,埃及强烈要求英国立即撤军。埃及支持科威特独立,主张在人民自决基础上以和平手段解决科威特问题;另一方面,科威特还不是阿盟成员国,而且1961年6月28日阿盟收到伊拉克的备忘录,正式宣布对科威特的主权要求,称科威特是“伊拉克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这种情况下,1961年7月1日,阿盟秘书长出访巴格达,与伊拉克政府官员协商,以和平解决危机。7月4日,秘书长访问科威特,翌日前往沙特,进行穿梭斡旋。
1961年7月5日,当阿盟秘书长仍在海湾斡旋调解时,阿盟理事会就科威特的入盟申请,举行第一次会议。7月20日,虽然伊拉克表示强烈反对,但理事会议仍然通过决议:(1)科威特政府要求英国尽快撤军;(2)伊拉克不得武力吞并科威特;(3)支持科威特依据阿盟宪章表达的与其他阿盟国家结成联盟或联邦的任何愿望;(4)欢迎科威特王国成为阿盟成员国;(5)协助科威特国加入联合国;(6)为了维护科威特的独立,阿拉伯国家将提供有效援助,授权阿盟秘书长“采取必要措施实施该决议”。(25)Hussein A. Hassouna, The League of Arab States and Regional Disputes, p.101.在阿盟秘书长的协调下,以沙特提供的军队为主,由埃及、苏丹和约旦军队组成的阿拉伯威慑部队,取代了英国军队,于1961年10月下旬开始在科威特执行任务。
这场重大危机的迅速解决,成为阿盟早期众多成功调解阿拉伯国家间争端与冲突的经典案例之一。阿盟在英军介入,并且阿拉伯大国伊拉克是争端国的情况下,向世人充分展示了阿盟在斡旋阿拉伯国家之间的争端及其管控冲突、维护地区和平上的能力。
(三) 折戟沉沙: 阿盟对伊拉克战后重建的斡旋
伊拉克似乎是阿盟组织陷入困境一个重要因素。1961年伊科危机,20世纪90年代初海湾危机与海湾战争,以及21世纪初伊拉克战争及战后重建困境,都严峻考验着阿盟组织的现实作用。对于2003年美国侵略伊拉克的战争,阿盟的立场和政策是坚定和明确的,即反对美国侵略伊拉克,呼吁美国立即撤军;维护伊拉克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保持伊拉克的阿拉伯性(Arabness)。然而,恰恰是这两个基本立场,使阿盟在伊拉克战后重建的斡旋中无功而返。
正是谴责美国侵略阿盟成员国伊拉克的政治逻辑,引发战后阿盟与美国主导的伊拉克政府不断发生冲突,危机不断。2003年5月伊拉克大规模战事结束后,伊拉克在阿盟的席位一直空悬,阿盟不乐意承认美国占领当局任命的伊拉克临时政府。在美国的幕后施压下,2003年9月上旬,阿盟勉强允许伊临时政府代表伊拉克,但双方关系仍然紧张。2004年3月29日阿盟峰会上,阿盟秘书长欧姆鲁·穆萨暗示伊拉克政府不合法。当时,伊拉克外长兹巴里提出动议,向伊拉克派驻阿拉伯维和部队。穆萨回应说,由于这个要求只能由“合法政府”提出,因而是“不可能的”。他指出:“可以肯定,阿拉伯部队不能加入到占领另一个阿拉伯国家的部队之中。”(26)Ibrahim Al-Marashi, “Regional Organizations as Conflict Mediators? The Arab League and Iraq,” in Cilja Harders and Matteo Legrenzi, ed., Beyond Regionalism? Regional Cooperation, Regionalism and Regionalization in the Middle East, Hampshire: Ashgate Publishing Ltd., 2008, p. 144.与此同时,穆萨也不看好2005年1月举行的伊拉克选举,称伊拉克不会成为中东民主国家的榜样。
对于阿盟而言,维护伊拉克的阿拉伯性近乎天职。穆萨批评伊拉克宪法草案未能把伊拉克称为“阿拉伯国家”,宣布整个阿拉伯民族反对伊拉克宪法。然而由于美国的侵略打开了伊拉克民族与教派纷争的潘多拉之盒,伊拉克库尔德人与什叶派对伊拉克的阿拉伯认同渐行渐远,对于阿盟怨言尤多。什叶派认为阿盟宽恕萨达姆·侯赛因镇压什叶派,对1988年萨达姆的化武袭击缄默不语。阿盟公开与伊拉克逊尼派接触,利用全国和解会议赋权逊尼派。2005年10月23日,穆萨访问伊拉克,在库尔德地区议会演讲中声明:“库尔德不仅是伊拉克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是阿拉伯世界和中东的重要部分。”有评论嘲弄道:“在沉默的议会,穆萨说库尔德斯坦是阿拉伯世界的一部分。”(27)Ibid., pp. 147, 149.原复兴党人也抨击阿盟的全国和解倡议,宣称阿盟受到美国的操纵,穆萨根据美国国务院的指示访问伊拉克,并指责穆萨计划在出访伊拉克时到监狱探视萨达姆。
阿盟竭力深度参与战后伊拉克和解与重建进程。2005年11月,阿盟在开罗举行伊拉克和解预备会议,但阿盟的斡旋很快以失败告终。阿盟是否错过了最佳的介入时机?阿盟在伊内战爆发之前介入,公正地谴责暴力,有利于树立阿盟公正调解方的形象,进而在伊拉克民众中获得合法性和信誉?或者,阿盟缺乏足够的奖惩机制和资源?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均有助于认识阿盟何以在伊拉克无功而返。但从根本上说,阿盟是在伊拉克履行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其原因主要包括:第一,美国作为伊拉克战后重建的主导者,对于伊拉克战后重建有自己的利益、立场和政策,是不可能让阿盟在伊拉克战后重建进程中发挥主导作用的。这是一个绕不开的结构性问题。第二,由于历史、文化、民族和教派的原因,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伊拉克国民的认同问题并未得到根本解决。什叶派和库尔德人对阿拉伯民族、伊拉克祖国没有认同感。恰恰相反,他们正准备抓住难得的机遇,构建联邦制的伊拉克以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了却数十年来压抑已久的政治心愿,这与阿盟维护伊拉克统一与阿拉伯性的目标相左。
三、 结构与建构: 两种诠释路径
从前述传统国际关系理论视角,通观二战以来中东地区主义实践特别是阿盟安全治理的是非成败,崇尚合作的自由主义学派最缺乏解释力。阿盟在推进地区经济合作上成效不彰,“功能外溢”严重不足,更没有将合作从低政治的功能部门扩展到高政治领域的所谓“政治外溢”。不过,现实主义与建构主义两大流派对于我们考察阿盟在地区安全治理上的成功与失败,及其在地区冲突与安全争端斡旋中绩效的高与低,提供了较为客观的视角。
(一) 结构: 阿盟安全治理低效的现实主义解析
现实主义学派对国家利益和权力结构的认识,贴近国际关系和地区政治现实。从权力结构角度看,阿盟作为国家间组织,受到域外强权的极大制约。国际政治的高度关联性,决定了阿盟从来不是也不可能是一个封闭的地区组织,域外强权对其内聚力、制度构建及调解斡旋等均产生了重大影响。就美国在中东的利益及政策而言,美国过去和现在都反对任何实质性的阿拉伯一体化,因为统一的阿拉伯政策或框架势必加强阿拉伯人的地位与讨价还价能力,从而有效抑制美国霸权,也不利于海湾石油输出和美国控制世界油价,更不符合以色列的国家安全利益。正如拉希德所言:“对(中东)地区有影响的国际行为者向阿拉伯执政精英施加压力,目的在于削弱阿盟及其代表的阿拉伯人格。有一种美国与以色列的联合压力,旨在分裂阿拉伯国家,迫使它们在不平等的基础上建立双边关系,我们在马德里和会上见证了这些操作,阿盟甚至不被允许参加会议。”(28)Ramy Lakkis, Arab Regional Integration: The Politics and Economics of a Fragmented Nation, pp. 114-115.
大结构决定小结构,美国霸权挑动阿拉伯大国相互制衡,搞乱阿拉伯世界,从而削弱阿盟。从本源上看,阿拉伯世界的碎片化与不稳定,是西方殖民统治刻意留下的遗产。雷蒙·辛内巴什和伊赫特沙米指出:“它们(欧洲殖民列强)把不稳定(冲突与修正主义)铸造进(阿拉伯)国家体系,这并非(阿拉伯)国家体系自身与生俱来的无政府状态,而是(殖民统治)造成的(阿拉伯)国家体系的特殊结构的根深蒂固的缺陷,主要是国家与认同极不一致,不平衡与碎片化,(由此造成不满意的大国与小国比肩而立),以及核心(国家)对地区的持续渗透。”(29)Ibid., p. 108.
老殖民主义撤退后,域外强国一直千方百计地阻止阿拉伯地区强国的崛起。而地区强国作为轴心力量往往是地区秩序的保障者,强大有效的地区组织建立在地区强国的基础上。罗伯特·基欧汉的研究表明,一个实际的霸权强国有助于国际体系中出现强大的(国际或地区)组织。霸主可以促进地区组织的建立,与此同时,地区组织促进地区强国的产生。小伊尼斯·L.克劳德认为:“地区组织往往围绕地区强国而建立,具有太阳系的特征,附属成员国围绕中心的太阳而运转。”(30)Tawfig Y. Hasou, The Struggle for the Arab World: Egypt’s Nasser and the Arab League, first edition, London: KPI Limited, 1985, p. 162.苏联在华沙条约集团和美国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起到的核心作用,以及美国在美洲国家组织发挥推动作用,说明地区强国是区域组织的主要受益者和推动者。处于体系轴心的强国,促使其他成员国采纳其政策建议。东盟和阿盟发展的滞后,从反面证明地区强国对地区组织发展的重要意义。
阿盟在宗旨设定与制度设计上,又反过来强化了阿盟内部相互制衡,难以产生自己的核心或主导国家。阿盟作为独立的阿拉伯国家组成的国家间组织,以维护来之不易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为宗旨,实际上强化了殖民者留下来的碎片化结构。虽然对阿拉伯统一有着强烈的感情,呼吁团结、合作乃至进行各种统一的尝试,但阿拉伯民族的共同利益始终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存在,是一种虚体。阿拉伯国家领导人实际上把本国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把政权的生存和自己的统治放在第一位。因此,阿盟在制度设计上从来不具有超国家性,在决策上实行一国一票,全票通过的决策机制。阿盟成员国互不干涉内政原则(阿盟宪章第8条),阿盟平等型权力结构和决策机制,均成为制约阿盟在地区一体化与地区安全上行动能力的因素。如何改革阿盟决策机制,是阿盟转型面临的难题。
(二) 建构: 阿盟安全治理低效的文化阐释
阿盟是一个具有双重性的特殊组织,它既是联合国承认并与之开展合作的地区组织,又具有浓厚的泛阿拉伯色彩。“阿盟不仅是一个地区组织,也是一个民族主义组织。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关系不仅代表地区秩序,而且代表泛阿拉伯地区秩序。把阿拉伯民族主义因素引入到对阿盟角色的分析,是一个绕不开的出发点。否则,就不能理解阿盟自1945年成立以来动力机制的许多方面。”(31)Ramy Lakkis, Arab Regional Integration: The Politics and Economics of a Fragmented Nation, p.87.
阿盟的双重性和内在结构性纠结,植根于阿拉伯民族认同与国家的分裂这个残酷现实。广泛分布在西亚北非的阿拉伯人(阿拉伯民族),分裂成20多个独立主权国家,造成阿拉伯人对阿拉伯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二元对立与严重撕裂。对于阿盟而言,就是麻袋与土豆的关系:阿盟只是一个麻袋,麻袋口打开,土豆(阿拉伯国家)散落一地。对于阿盟推动地区(阿拉伯)一体化而言,造成两方面的负面影响。一方面,阿盟在推进自身的制度构建与能力建设上受到严重掣肘,长期裹足不前,具有超国家性的欧盟不是阿盟的发展方向。另一方面,阿盟作为地区组织缺乏自身的组织利益和内在动力,也不能在阿拉伯民众中培育自己的支持者。
具有一定历史和现实基础的阿拉伯认同,在“虚”与“实”之间漂浮不定。迈克尔·N.巴尼特曾指出,阿拉伯政治是符号政治(symbolic politics);“在阿拉伯政治中,大棒不管用,舌头更有力”。(32)Michael N. Barnett, Dialogues in Arab Politics: Negotiations in Regional Order, p.3.阿拉伯领导人经常利用空中的电波,把自己的阿拉伯对手描绘成突破阿拉伯共识,违反阿拉伯民族利益之人,甚至称之为阿拉伯人的敌人,动员其民众上街游行示威,影响乃至控制对方的外交政策。1958年黎巴嫩指责埃及煽动内乱,联合国要求埃及停止“阿拉伯之声”电台广播。对此,纳赛尔答曰:“如果你要求我解除电台武装,你就是要我彻底解除武装。”(33)Ibid., pp.3, 44.阿拉伯国家间政治的特殊性在于,砖块和石头会伤人,但阿拉伯领导人受到符号与演说的特殊威胁。
这样,阿拉伯认同之“虚”,在阿拉伯政治中转换成“实”,即阿拉伯国家特别是阿拉伯大国操纵其他阿拉伯兄弟国家,为本国利益服务的工具。这是负能量的“实”。与此同时,阿拉伯认同这个“虚”,如何转换成正能量的“实”——阿拉伯民众普遍认可、阿拉伯各国共同接受而且在政治运作中具有可行性和可操作性的“共同利益”?这是阿盟成立70多年来,阿拉伯世界矢志追寻而尚未解决的难题。纵观历史,阿拉伯民族和阿盟从感情和利益的角度,在“共御外辱”(主要是对抗以色列的重大威胁和反抗美国的霸权政治)上,大致可以保持一致,阿拉伯认同发挥重要作用。然而,在正向建构阿拉伯共同利益,或者说把阿拉伯认同之虚转换成正向的阿拉伯共同利益上,迄今未取得突破性进展。这让以舌头灵活语速极快闻名于世的阿拉伯人感到困惑气馁。摩洛哥国王哈桑在1985年阿盟拉巴特峰会开幕式致辞中不无感慨地指出,没有共同语言的欧洲经济共同体尚能在重要问题上达成一致,开会时“微笑而幸福”。它“为我们提供了现成的武器”,(我们务必)负责地讨论问题以便实现共同利益。约旦国王侯赛因感慨地回应,当“解体取代聚合,地区主义取代泛阿拉伯团结,阴谋取代和谐,霸权政治取代手足情深,毁灭取代政治”的时候,阿拉伯民族不可能(在一体化上)取得进展。(34)Michael N. Barnett, Dialogues in Arab Politics: Negotiations in Regional Order, p. 203.
阿拉伯人时时强调的手足情深是一种古老而质朴的感情,却在遭遇冰冷而强硬的国家利益时,显得那样的软弱无力。这种政治实践中难以测度的美好情感,往往转变成阿盟会议上面红耳赤的激烈争吵与相互攻讦甚至“兄弟阋墙”。这样,阿拉伯文化,植根于共同的语言、历史与宗教的共有理念,逐渐分化出阿拉伯各国的国家利益,却没有建构出阿拉伯民族的共同利益,因而阿拉伯各国在地区政治与国际政治进程中往往各行其是,造成阿拉伯世界的分裂与乱局。在阿拉伯文化未能成功建构阿拉伯共同利益的现实下,西方的价值观渗透乘虚而入,撬动阿盟走上了一条欲速则不达的转型之路。
四、 阿盟转型面临挑战
20世纪90年代初,萨达姆大军侵占科威特,阿盟无力化解危机,埃及、沙特等阿拉伯国家效命于美国麾下的多国联军“解放”科威特,终止了阿拉伯团结与阿拉伯主义(Arabism)这些动人而又在现实政治中扰乱阿拉伯政治的口号与理念。由此引发的阿盟无用论、阿盟过时论促使阿盟逐渐走上转型之路。
(一) 阿盟转型的动力
阿盟与欧洲近在咫尺,因而在经济、政治、价值理念和具体的机制建设上,长期以来深受欧洲的直接影响。人权成为超越国家主权与统一的普世价值,阿盟在后“阿拉伯之春”的动乱中提倡“保护的责任”。事实上,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阿拉伯与伊斯兰世界颁布了一系列人权宣言或人权宪章:《1981年伊斯兰人权普世宣言》《1990年开罗伊斯兰人权宣言》《2004年阿拉伯人权宪章》《2008年伊斯兰会议组织宪章》和《2014年海湾合作委员会人权宣言》。(35)Matthias Vanhullebusch, “The Arab League and Military Operations: Prospects and Challenges in Syria,” International Peacekeeping, Vol. 22, No. 2, 2015, pp.156-157.
与此同时,欧盟通过一系列具体政策杆杠,直接撬动阿盟转型。2012年1月,欧阿倡议明显地体现出阿盟的政策变化。阿拉伯—欧洲草案,亦即把阿盟的叙利亚和平计划提交联合国安理会投票通过的草案,赞赏人权的全球原则与保护的责任,从而“修改了对其成员国主权的原则”,为俄罗斯和中国所否决。2012年11月,欧盟和阿盟外长会议在开罗召开,决定重启欧盟—阿盟关系,其具体成果之一,就是当年启动的阿盟早期预警与危机应对中心。2012年开罗宣言为欧盟—阿盟政治对话奠定了基础,2014年转变为欧盟—阿盟战略对话,议题涉及危机预警与管控、反恐、跨国有组织犯罪和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等。(36)Elisabeth Johansson-Nogues, “The New Eu-Arab League Dialogue: The Contours of a Cooperation,” Mediterranean Politics, 2015, Vol. 20, No. 2, pp. 297-298.欧盟与阿盟签订打击伊斯兰恐怖主义的安全条约,赋予阿盟解决叙利亚国内外危机的政治资本。(37)Matthias Vanhullebusch, “The Arab League and Military Operations: Prospects and Challenges in Syria,” p. 161.
非洲联盟对于阿盟转型的影响亦不可小觑。2002年非洲联盟正式成立,大有后来居上之势,在维护非盟内部和平与安全、地区主义职权扩展上超越了阿盟。2003年12月,非盟成立和平与安全理事会。阿盟起而效尤,2009年3月2日成立阿拉伯和平与安全理事会(Arab Peace and Security Council)。(38)Farah Dakhlallah, “The League of Arab States and Regional Security: Towards an Arab Security Community?,” British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 Vol.39, No.3, 2012, p.411.根据阿盟负责多边关系事务的瓦勒·阿萨德主任的说法,此举意在以更为制度化的冲突管控和解决机制,补充阿盟传统的争端解决方式,后者主要取决于秘书长的影响力。不过,阿拉伯和平与安全理事会仍处于草创阶段,只是向阿盟理事会提供建议。
(二) 阿盟转型的方向
阿盟转型的方向,从价值层面上说,就是接受人权高于主权和保护的责任这样的西方理念。就制度构建和能力建设而言,则是修订宪章,改革决策机制,从协商一致全票通过转变成多数通过。2005年,阿盟正式修订宪章第6条:“理事会以全票通过,决定采取必需的措施驱逐侵略。如果不能全票通过,以出席会议和参加投票2/3多数成员国通过决议,侵略国的投票不计入多数票。”对第7条也进行了修订:2/3成员国(代表)出席,构成举行理事会议必需的法定人数。在不能全票通过的情况下,采取下述措施:(1)将决议推迟到下次会议;(2)如果情势紧急,在一个月内举行紧急会议;(3)如果协调一致没有转变成投票(一致通过),对于实体问题,可以出席国家的2/3多数通过有效力的决议……(39)《阿盟宪章》(修订版,阿文版),阿盟官方网站,http://www.arablegalnet.org, 上网时间:2021年1月5日。
伴随阿盟决策机制的重大调整,阿盟软化不干涉内政原则,在地区冲突中逐渐从斡旋调解、政治解决滑向军事化。有学者指出:“1990~1991年海湾战争持久地改变了(阿盟)取向,在阿盟的外交(斡旋)方式中引入了军事化。伊拉克令人瞠目结舌的侵略与沙特阿拉伯同样令人惊诧地召唤美军,为(阿盟)历史性的变化搭建了舞台。”(40)Mohammad-Mahmoud Ould Mohamedou, “Arab Agency and the UN Project: The League of Arab States Between Universality and Regionalism,” p. 1225.2011年阿盟公开支持在利比亚设立禁飞区,中止利比亚的成员国资格,为北约军事入侵利比亚铺平道路,一些海湾国家直接派兵,加入北约打击利比亚的战斗。阿盟在叙利亚的军事卷入后果极为严重,正如阿卜杜勒·巴利·阿特旺(Abdel Bari Atwan)指出:“阿盟早些时候就决定支持以武力实现(叙利亚)政权变更,同意向叙利亚反对派提供现代化武器以加快这一进程,这直接有助于冲突的军事化,为圣战团体进入战场铺平了道路。”(41)Ibid., pp. 1127-1128.
(三) 阿盟转型的挑战
阿盟的转型既是自身发展的需求,更是欧盟和美国竭力推动的产物。这种“西化”进程符合阿拉伯世界的实际,有利于阿拉伯地区一体化和地区安全与和平?从目前来看,阿盟的这种转型面临严峻挑战。
首先,阿盟的转型背弃了数十年来奉行的不干涉内政原则和协商一致全票通过的决策机制。虽然迎合了西方鼓吹的人权高于主权原则,可以提高决策效率,然而过于超前,脱离阿拉伯世界的实际,使阿盟决议面临无法实施,进而损害阿盟权威、分裂阿盟的巨大风险。众所周知,由于各种原因,阿拉伯世界是一个冲突频仍、纷争不断的地区。阿盟通过决策机制改革,匆忙地深度、强行介入冲突,风险极大。改行多数通过制以后,讨论和通过决议的效率得到提高,但一纸决议难以实施。重大政治分歧是不能用投票简单粗暴地解决的,相反,未经充分协商讨论、达成共识至少达成默契的投票,反而加剧矛盾、扩大分歧。经过反复协商,劝和促谈,以政治手段解决争端弥合分歧,这样的成功案例不胜枚举。在1970年约旦发生的“黑九月”事件中,埃及总统纳赛尔在阿盟框架内进行斡旋调解,不是化干戈为玉帛了么?相反,“阿拉伯之春”以来,阿盟在涉及中止成员国资格这样的重大问题上违背一致通过原则,强行中止利比亚和叙利亚的阿盟资格。依靠军事手段特别是借助西方武力解决利比亚问题,军事干预叙利亚内战,引狼入室。姑且不论阿盟是否具备足够的军事整合能力,以军事手段解决政治问题,本末倒置,委实凶险。
其次,阿拉伯国家体系结构制约阿盟的重大转型。阿盟成立伊始,就受制于内部权力结构。在协商成立阿盟的过程中,以伊拉克为首的哈希姆王朝与埃及法鲁克王朝竞争,埃及在沙特阿拉伯的支持下占据优势。埃及在阿拉伯世界和阿盟的主导地位,在1973年十月战争后由于油价飙升,遭到严重挑战。沙特阿拉伯为首的海湾阿拉伯国家以雄厚的石油美元及其在世界经济中的战略地位,在地区格局和美国战略大棋局中的地位急剧提升。相反,埃及在外交上转而依赖美国,经济上依赖沙特等阿拉伯石油输出国,雄风不再。事实证明,海湾合作委员会的成立,既增强了沙特与埃及博弈的筹码,又对阿盟构成直接挑战。沙特与埃及龙虎相争,是阿盟内部面临的最大挑战。当海湾合作委员会秘书长认为某些阿拉伯国家的威胁超过以色列时,(42)时任海湾合作委员会秘书长阿卜杜勒·比沙拉宣布,对海湾国家的根本威胁不是以色列,而是一些阿拉伯国家。参见Bahgat Korany, “National Security in the Arab World,” in Dan Tschirgi, ed., The Arab World Today, p. 166。阿盟的转型前景令人堪忧。
再次,阿盟转型成功与否,最大的挑战来自于域外强国。1991年启动的马德里和平进程,直接排挤阿盟,意在为阿盟敲响丧钟。政治方面,美国挟海湾战争后独霸中东的威势,与以色列一唱一和,大力倡导中东主义。经济方面,推出西亚北非经济峰会,稀释阿拉伯经济合作与一体化进程,意在把以色列的经济和技术优势转变成政治优势。西方学术界迅速跟进,阿盟过时论喧嚣一时。这一切收效甚微,然而攻心为上,西方从价值观层面成功进行渗透,在“敌”与“友”这个关键问题上搞乱阿拉伯世界和阿盟。在决策机制上推动阿盟改革,取得实际进展。但这种脱离阿拉伯国家实际的变化却不利于阿拉伯国家和阿盟自身的转型。
五、 结语
若干年来,西方舆论与学术界高调唱衰阿盟,认为阿盟之所以在安全治理上作为有限、绩效低下,根源在于阿盟的决策机制出了问题。协商一致、全票通过的原则造成阿盟决策久拖不决,效率太低。然而,对叙利亚战争的斡旋,恰恰是在阿盟2005年修改宪章,改行三分之二多数票通过之后。而且,无论阿盟呼吁联合国介入利比亚危机,甚至阿盟个别成员国直接派兵参加北约对卡扎菲政权的军事打击,还是中止作为阿盟创始成员国的叙利亚的成员国资格这个“空前壮举”,都是阿盟转型和阿盟在西方“人权高于主权”“保护的责任”口号下“积极作为”的重大举措。阿盟对利比亚和叙利亚两场战争的军事介入与高调制裁,都起到了适得其反的效果。本文认为,阿盟在欧盟和美国舆论与价值理念的诱导下,抛弃多年来行之有效的政治协商与一致通过决策机制,放弃阿盟秘书长穿梭访问灵活斡旋的传统优势,在对叙利亚战争的介入中把所谓的人权置于叙利亚国家主权之上,是得不偿失的作法。
在对阿盟安全治理的绩效评估中,西方世界往往把自身安全利益放在第一位,立场优先,结论在前,不顾阿盟发展历程的客观实际,削足适履地进行论证,无非价值渗透和话语霸权。西方一再渲染阿盟无用论,阿盟过时论和阿盟崩溃论,理由是阿盟在一些地区冲突的斡旋调解中没有成效。然而,联合国与阿盟在联合国斡旋叙利亚战争中失败,却没有因此高调出现联合国过时论或联合国崩溃论,也没有出现要求废除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一票否决的决策机制的浪潮。历史一再昭示,以制裁或军事打击介入地区冲突,若非自身利益驱使,很难作出其他解释。政治争端或政治冲突,最终只能通过政治方式解决,以军事手段解决政治问题,只能加剧冲突,延长危机。只要没有域外强权蛮横干预,阿盟的斡旋调解最终会产生效果。20世纪60年代“阿拉伯冷战”时期持续多年的也门战争和1975~1990年黎巴嫩内战的最终结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这显示出现实主义学派结构论的现实解释力。因此,阿盟在阿拉伯国家自身制度建设及阿拉伯共同利益的建构上任重道远,切不能被西方误导,南辕北辙,走上错误的改革与转型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