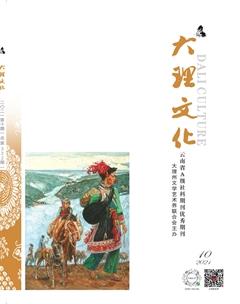你不能假设生活
钱会芬
丈夫的单位今天下午聚餐。独自吃过晚饭,我洗了个澡,在阳台上边玩手机边晾头发。就在我准备起身离开阳台的时候,一个女人进入了我的视线。
此时太阳距离西山顶很近,就像一个迟暮的人,散发着缺乏温度的光。
那个女人就在这昏黄的天光中迟疑地朝着这个小区走来。不是本地人,我一看就知道,她没有在一个小县城常年居住,对一切了然于胸的那种笃定和从容,也没有乡下人那种惶惑甚至紧张。她并不急于赶路,而是边走边四下观望,仿佛是在辨别方位。
我正在卫生间梳头,就听到一阵敲门声。就在拉开门那一瞬间,我怔住了,门外站着的竟然是刚才看到的那个女人。
“我就觉得你应该在家。”她说,那口气仿佛是一个和我一起生活多年,熟悉我生活规律的人。
“你是谁?”我问,“你找谁?”
“哎呀!你还是这样性急,让我先进去。”她不满地抱怨道。
她侧身就进了屋,说:“先给我倒杯水,我可是真的渴了。”
我把水递给她时,她已经斜躺在沙发上了。喝完水,她长呼了一口气,说:“我去洗一把脸吧,真是风尘仆仆啊!”她站在客厅环视了一圈,就朝卫生间走去。
她是谁?看面容似曾相识,可是我真不认识她。
从卫生间出来,她又深深地斜躺在沙发上,还拉过一个抱枕垫在身后,扭了几下身子,似乎找到了最舒服的姿势。
“你可能暂时不认识我,你就叫我隐得了,先听听我的故事吧。”我并没听清她说的是ying,还是yin,不过为了方便,我就叫她隐吧。
那年我21岁,没有谈男朋友。隐说,因为我不想一辈子就生活在这样一个地方,我渴望我的世界更辽阔一些。还有就是我希望我爱的人,他要能够为我打开生命的另一扇窗。于是我决定出去转转,我想我未来的爱人应该在很远的地方,我兴许能找到他。
我去了一个非常非常遥远的地方,叫梅思丽沙漠。我不清楚为什么听上去像个女人的名字。出发之前我了解过,这片沙漠面积三万多平方公里,是一个世界闻名的大沙漠的尾巴那部分,因为面积不大,环境相比也不是十分恶劣,所以常有世界各地的驴友到这里体验徒步穿越沙漠的感觉。我到达那里的时候,刚好有四名中国人结伴准备行动,三男一女。虽然他们在我来之前就已组成了队伍,但我发现他们彼此并不熟悉,而且对了解队友也没表现出什么兴趣。以前看到一个新锐作家说过这样的话:爱好旅行的人都是无情的人,因为他们知道结束了这一段行程就各自天涯,很快又要去结识新的人开始下一段旅程,久而久之,在他们心中,一切都只是匆匆过客。看来这话不无道理。我加入了他们。我们一行五人是在一个黄昏进入梅思丽沙漠的,当地人告诉我们,晚上走会凉爽一些,这对我们有利。刚进沙漠时还很燥热,随着太阳落下夜晚到来,寂静和黑夜就降临了。
我边走边东张西望,这是我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接触沙漠,总想找到一些和以前不一样的东西。当我发现天空中那么大的星星,我惊呼起来:“看,天上结满了柿子!”可是我的惊呼并没有获得回应,队友们都在闷声不响地低头走路,只有一个黑皮肤的男人皱着眉头瞥了我一眼,就像我的话令他不快似的。好在一个长头发的姑娘一手扶着那个男人的胳膊,一边回头对我说:“节省体力。”我把她称作苏吧。苏说了那四个字后再没声响,直到后来分头行动时。我原以为我们可以在行进过程中分享一些新发现,彼此交流一些想法,可是这些人只是想着向前走,横穿沙漠,到达对面的目的地。
我忽然觉得隐的故事似乎跟我有某种联系。我坐到隐的身边,她所讲的丝丝缕缕的背后,一定隐藏着跟我有关的更多秘密。
隐抬起眼睛,仿佛她的目光穿透了眼前的墙壁,穿越了小区林立的高楼,穿越了外面世界的千山万水,回到了那片沙漠。
她接着讲,第二天中午,随着太阳逐渐升高,气温迅速回升到38摄氏度,这对于我们是一个艰难的体验。我们决定休息一下,等太阳最晒的那段时间过去再行动。沙漠里一片寂静,举目四望就是一个个橘红色的高高低低的沙丘,这些沙丘沉默着一直排列到天的尽头。帐篷里很快传来鼾声。我坐在帐篷外一个角落里,我可不想就这样去睡觉。前一晚在夜色中,周围一片漆黑,都没能看清沙漠的样子。我极目远望,眼前仿佛是一片无边无际的大海,沙丘不过是海面翻卷起的波浪,对!这是海的另一种存在方式。正当我这样想着时,感觉有人在我身边坐了下来。就是那个黑皮肤的男人,我就叫他乔吧。乔坐下后,眯起眼睛看向远处。
“发现什么新鲜玩意了?”乔说。
“没有。”我回答。
“那有什么好看的!不睡觉?”乔说着就准备起身。
“我发现这其实是一片海。”说实话,那时我心里还是渴望有人和我说说话的。
乔果真又坐了下来。
“海!你说这是海!这个说法倒不错!”
“也许这是另一种样子的海。”
乔扭头看我,我发现这个皮肤黝黑的男人长着一双比他的皮肤还要黑的眼睛。当他的目光落在我脸上时,深深地皱了一下眉,仿佛我的表情让他不快似的。
“走吧,够了。”乔一边说著一边钻进了帐篷。
我们在前面六天走了将近七十公里,第八天,我们来到了一片洼地。这里矗立着一些石墙,说是墙,只是有一些大致墙的样子,在这一片洼地里,就像是一个敞开着的肚皮里的一段一段腐烂的肠子。这里应该是一个什么古老建筑的遗迹。肠子在洼地里制造出几小块阴凉,让我们得以坐下来喘一口气。当我们坐下时,发现墙角处竟然长着几蓬小草,而且还开出了几朵小黄花。苏和乔并肩坐在一起,我看到苏和另外两个男人如获至宝地把小草连根拔起,拍拍土就送进嘴里大嚼起来。进沙漠这么些天,除了啃压缩饼干就是喝水,任何一种别的味道,对舌头来说都是一种享受。乔看了看小草,把身子往苏的那边挪了一下。在这一望无际的砂砾地上,这些小生命多么让人怜爱。我趴下去闻了闻,金黄色的小花里竟然还有一股凉丝丝的清苦的气息。乔转头望向我,眉头又皱了起来。就在我要直起身的时候,突然瞥见草丛中有一块青绿色的东西,拿起来一看,竟然是一块石头。这块石头和鸡蛋一般大,形状也像鸡蛋一样一端尖,一端圆,只不过是扁的,差不多有一个手指头厚。我把石头拿在手里翻来覆去地看,它不像沙漠里的石头,沙漠里的石头质地不太硬,而且都是黄色或者黑色的。这块石头质地紧密,放在手里掂一掂,大约有80克左右的样子,它通体青绿色,却在中间部分隐约有一道弯曲的、稍显白色的纹路,就像一片长满青草的土地上流淌着一条小溪。我把石头给他们看,乔说:“这是什么?上帝的眼泪!”是的,它太像一滴水,或者说太像一滴眼泪了。
酷热的天气,加上每天只吃压缩饼干和水,缺乏维生素,我们嘴角都起了泡,又疼又痒,心情更加焦躁。那颗石头一直被我带在身上。上帝的眼泪!说真的,我很喜欢乔为它取的这个名字。正午热得无法入睡,当我看到“上帝的眼泪”,仿佛看到一片生机盎然的草地,那些充满生命力蓬勃生长的草,让我觉得整个世界那样辽阔自由,内心深处涌起一种难以言说的感动,我很快就会平心静气地睡去。疲惫不堪的时候,我看着那条“小溪”,就会想起我小时村子前面那一条清澈的小河,身上就觉得有了力气。这颗石头就像和我有某种渊源,它仿佛能和我内心最隐秘的依赖和渴望相通。
“石头!青绿色的石头?”我的自言自语打断了隐。我一边喃喃着,一边努力回忆,就像要从一大堆灰土里扒出童年时的彩色玻璃球。它是否曾经出现在一个我遥远的梦境中?
隐抬起头满眼期待地看向我,就像看一个就要从睡梦里醒来的人。她挪了一下,和我挨近了一些。她为什么这样看我呢?
她接着说:进入沙漠越深,气温越高,空气越干燥,到第12天下午,我们仿佛置身于一片火海中,最糟糕的是水快要喝完了,而我们在此时迷失了方向。不是迷路,沙漠里根本没有路。我们躺在一个沙窝里,七嘴八舌,争论不休。从见到他们那天起,我们从来没有说过这么多话。苏说,应该往3点方向走,她记得很清楚,前天经过的那个深红色的沙包在9点方向。可是回头去看,那个红色沙包连影子都看不见。另外两个男人则坚持往5点方向走,并让我们相信他们的感觉,而感觉这玩意儿在很多时候不过是自我解嘲的代名词。我像往常一样把“上帝的眼泪”握在掌心,那时我真不知道该听他们谁的。忽然我感到迎面吹来一阵轻风,像天上最轻盈的一缕云彩,轻轻地拂面而过,空气里似乎有一丝清凉。
“往12点方向走。”我说。
他们都扭头看我。
“先往12点方向走,前面有水,我们把水储存够了再说。”
“你犯迷糊了吧?这四下里一片火海,不可能有水!”苏说。另外两个男人则不置可否地沉默。
“刚才从12点方向吹来一阵风,风里有水的气息,你们没闻到?”
“犯傻吧?哪里有风?这里怎么可能有水?”一个男人说。
“相信我,前面一定有水。”我一再坚持。
“别听她胡说八道!如果找不到水,耗费了体力不说,连现在这点水都喝完了,我们就只有等死!”苏和另外两个男人说。
就在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时,一直不吭声的乔说:“这样吧,我们分成两组,我和她(乔指了指我)往12点方向去找水。”乔指了指那两个男人,“你们俩和苏一组,但是方向要一致。”苏想了想说她愿意和那两个男人一起往5点方向走。
乔对那两个男人说:“你们一路上要照顾好苏。”
乔说:“记住,到后天,无论情况怎样,我们还来这里汇合。”
他们三人走时,乔让他们带走了全部的水。苏临走时看我一眼,又看乔一眼,她的眼神告诉我,希望和乔一起走的是她。我真不知道她在这十多天里是怎么喜欢上乔的,也许是从她扶着乔的胳膊扭头告诉我“节省体力”时就开始了吧。
我和乔走了一天,第二天黄昏,又渴又累的我们终于发现了一个小水塘。它在两堵隆起的狭长的沙丘中间,大约有一百多平方米的水面。当我和乔踉踉跄跄地奔过去时,我依稀看到水面闪了一下眼睛。我们喝饱水,把所有能装水的东西都装满了。离开水塘之前,我把“上帝的眼泪”清洗了一下,它身上沾了我多少汗水呀!我和乔急忙往回赶。可是当我们回到沙窝时,并没有看见苏他们。沙漠里很少有标志物,有时你往前走几天,眼前的景物和你刚开始时见到的毫无二致,稍不小心就容易迷失方向。怕和他们错过,我们只好在沙窝里等。待了两天后,我们决定往5点方向去找他们。我曾问过乔为什么选择和我一起,乔说:“在那一瞬间我觉得我应该相信你。”我多次打量那颗石头,我纳闷为什么在我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突然就吹来一缕凉风,也许这是上帝冥冥之中在拯救我吧!
讲到这里,隐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似乎累了。她把期望的目光投向我。我突然觉得手心发凉,就像握着一块石头,低头看,手里却什么也没有。
隐接着说,我们一直走,不知在沙漠里度过了多少个白天和黑夜。我们一直没看到苏和另外那两个男人,或许他们已经走出了沙漠,或许他们又走错了方向,也或许他们已经倒下了。谁知道呢!在这满世界的沙丘里,没有时间,没有空间,有时甚至没有意识。到后来,我们甚至把苏他们给忘了,我们唯一的渴望就是什么时候一抬眼,赫然看见沙漠的边缘。但是这样的希望越来越渺茫,我甚至怀疑我们根本没有往前走,而只是在原地兜圈子,眼前的一切都是昨天看到的,除了沙丘还是沙丘,除了死寂还是死寂,那时我想,要杀死一个人,根本不需要用刀或枪,只要把他留在沙漠里。水也快喝完了,干粮也所剩不多,我以为我会永远留在沙漠里了。喬把水省着给我喝,一天只敢啃手指大一块饼干。有很多次,我浑身僵直地躺在松软的沙子上,真想闭上眼睛不再醒来。当我看到“上帝的眼泪”,我想,我不能就这样死,我一定要活着走出去,我要去寻找那个地方,在那里,草儿恣意生长,小溪自由流淌。在那里,我所有失去的生命力都会重新回到我的身体里,我的生命会重新焕发光芒。想到这些,我就挣扎着站起来,在乔的搀扶下继续向前走。有几次我神志不清,哭嚎着要跳进村前的那条小河里洗一个凉水澡,可是那条小河总是我走近一步它就后退一步,我永远也到不了河边。每当这时,乔就把“上帝的眼泪”放在我的胸口上,我会慢慢地平静下来,在他怀里沉沉睡去。
“上帝的眼泪”,它像是我灵魂的栖身之所。
终于在一个晚上,当筋疲力尽的乔搀扶着我爬上一个沙丘时,我们看到远处移动的灯光,那是车灯,距离我们大约500米左右,说明我们快要走出梅思丽沙漠了。意识到这一点时,我的心扑通扑通狂跳起来,或许是身体长时间处于虚弱状态,心脏受不了这突然到来的惊喜,我眼前一黑就失去了知觉。
当我恢复意识时,我发现自己躺在一张床上,眼前是白色的墙,我盖着白色的被子,右手上挂着吊瓶。乔坐在床边,他也在挂吊瓶,睡着的他双眉舒展。我的呻吟惊醒了乔,他看到我,眉头又皱了起来,“你终于醒了!这是诊所。”他一边说一边伸过没挂吊瓶的那只手来握住我的手。
“‘上帝的眼泪在哪?”我问。
“扔了。”乔说。
“扔了,扔哪里了?你怎么能把它扔了?”我提高了嗓门。
乔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不扔,我怎么能把你背到公路边,500多米的路程。”
我没说话,静静地看着他的眼睛,他又皱起眉头,低声说:“扔了就扔了,那就是一颗不值钱的石头。”
我突然明白,眼前这个给过我很多温情的男人,冷静、睿智,令我心动,尽管我和他经历过万般艰难,经历过生与死,但能让他放在心上的,也仅仅是我这一副躯壳罢了,至于我灵魂深处的渴望,他可以像对一颗石头那样弃之不顾。他不知道,有些人,他们灵魂的依凭恰恰是一些不值钱的东西。
我问乔:“如果那是一颗比我值钱的钻石,那么,此时埋在黄沙中的该是我吧?”
乔生气地说:“没有如果!生活是不能假设的。”
当我有力气走出房间的那天,我离开了这个喜欢皱眉的男人,没有给他留下只言片语。
隐讲完这些,叹了一口气。
我突然觉得内心有一种深深的失落,仿佛一些我一直不愿意直面的东西突然赤裸裸地摆在我的眼前。我神经质地拉起另一只手,一阵熟悉的温热在身体里浸润开来,是的,在很多时候,我唯有两手相握,让他们互相安慰。一低头,才发现那一只竟然是隐的手。
隐喝了几口水,平复了一下情绪,接着讲:
我走遍了梅思丽沙漠周边的村庄,四处打听苏和另外那两个男人的消息,可是什么消息也没得到,也许他们已经永远地留在了梅思丽沙漠,也或许他们已经回到了原来的生活。
24岁那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认识了姜。他大学毕业6年,搞海洋生物研究,在一个海滨城市有一套130平米的房子,据说他的父母是搞房地产开发的。我对他的家庭背景不感兴趣,也从不过问。由于工作关系,他经常出海,也因为工作关系,他和附近渔村里的渔民混得很熟。和姜熟悉之后,有一次他便问我,要不要跟他一起出海。在这之前,我一直生活在一个边远闭塞的小县城,对于海,只是在文字中接触过,在电视上看过。因此,我一口答应。
我们是坐一个渔民的船出海的,是一艘钢质的近海机动渔船。启程时,天还没完全亮,东边海天相接的地方有一抹狭长的亮白色,渔民告诉我们,那是太阳升起的地方。渔船在黑黝黝的海面上滑行,此时的海就像一匹无边际的黑色丝绸,四周也是一片暗黑,如果不是发动机的声音提醒我,我真以为我们正在进入一个幽灵之地。我和姜坐在船头,看向远处那一抹亮白色。早春的风很大,吹得衣襟刷刷响,寒冷并没有减少空气中的腥味,我努力忍受着一阵阵恶心的感觉,姜扶我坐下,拿出一瓶风油精,滴一点在我的太阳穴上,边按边揉说:“就知道你会晕船,事先准备的,别紧张,我第一次坐船也这样,以后就习惯了。”不知是风油精的作用还是姜的话安慰了我,我真的很快就觉得舒服多了。
东邊天空的那一抹亮白色渐渐变成亮橙色,太阳就要升出海面了。姜指着那些橘色的云朵,激动得像一个孩子。
“快看,那里有一匹马。哎,看这边,那朵云像不像奥特曼?”
我问他:“你每次出海都这样?”
姜垂下眼睛有些羞涩地说:“平时这个时候我就坐在船头,一边喝酒一边看云彩。”接着,姜说:“在海上看云彩和在别处看不一样,你看四周,没有山或树木,就这样辽阔无边,看着这些云彩,不知它们将飘向何处,你会想到生命中的很多不确定,很多可能性,这样想着,你会觉得自己已经离开了物化的世界,你已经接纳和包容了一切,和天与海融为一体。虽然你最终还是要回这个世界,但是,当你经历过这种体验后,你会发现生命原来可以这样辽阔、自由!不过,你不会懂这些。”姜说着这话的时候,望向远方的双眼既迷离又忧伤。那时,我很想对姜说:“不!我知道,这就是我一直渴望和寻找的。”
“生命的自由与辽阔!”我重复着这句话,又一次打断了隐。多么熟悉的话,好像一个相处多年的朋友,不知什么原因就疏远了,忘记了,现在又突然隐约记起。
隐看着我,她似乎在等我继续说点什么,但我脑海里一片迷雾,感觉有一些东西,曾经很珍贵,但是现在想要抓住,它们却若隐若现。
隐只好接着说,这个男人,他像一本书,为我的灵魂打开了一扇窗,又像一座灯塔,让我透过迷雾,看到了光亮。内心深处有一道温泉喷涌而出,我不禁热泪盈眶。
“太阳出来了,快看!”姜推了我一下。
喔!一轮橘红色的太阳就像挣脱了羁绊,一跃而出,那么新鲜,就像刚从树上摘下的一个硕大的金桔,海面上金光闪闪,就像有一万条金鱼在游动,整条船沐浴在朝阳的光芒中。姜情不自禁地抓起我的手用力举起来,仿佛要这样来迎接崭新的一天。在金色的阳光中,我和姜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隐停了好一阵才又接着讲,似乎快要没力气了似的往我肩头靠了靠。我突然觉得我和她是那么熟悉,仿佛她是从我身体的某个地方分离出去的一部分,我跟随她故事里的喜悦而喜悦,悲伤而悲伤。
姜在客厅里摆了一个很大的鱼缸,养了两条红金鱼。姜很喜欢它们,每天都给它们喂食,有时他会对着鱼缸吹口哨。他说,鱼能通人性。周末无论多忙,姜都要清洗鱼缸,不让鱼缸里有鱼食残渣。从海上回来之后,我和姜就住到了一起。姜很喜欢每天下班回来吃我做的饭,晚上搂着我入睡。姜不止一次说:“你就是上天给我的礼物。”姜给我许多零花钱。姜的父母很有钱,姜不需要依靠工资生活。而我打算慢慢熟悉这个城市后就找份工作,我不屑让任何男人养活我,包括姜。而姜却不以为然,他说:“工作会让你劳累,我不喜欢那样的你!放心吧,你不工作我们也能过得很好。”姜在那次之后就没有带我出过海,他说那些时候海风太大,怕我受不了晕船,他每次出海回来都会给我带回一个形状古怪的贝壳,或者一个小巧的海螺。而我还是盼望着春天过完后能和他一起出海。那天,我百无聊赖地在客厅里转来转去。姜出海6天了,说要一个星期才回来。这时我看到鱼缸里那两条金鱼贴着缸壁游来游去,嘴巴一张一合,像是饿了,我就抓了几颗鱼食扔进去,两条鱼吃完鱼食,仍然不停地张合着嘴,好像还没吃饱,我又喂了几颗。过了一会儿,只见两条鱼肚子胀得鼓鼓的,肚皮向上浮了起来。这时我才想起姜说过,喂鱼食一天最多不能超过4粒,否则鱼会被胀死。这下怎么办?姜回来我该怎么对他怎么说呢?我心里忐忑不安。第7天下午,姜回来了,他习惯性地看向鱼缸,鱼缸里空空如也。我强作镇静地向他解释,姜还没听我说完,就爆发了,他一只手叉着腰,一只手把鱼缸拍得当当响,说:“我走时是怎么告诉你的?你没有好好记着吗?连这么点事都做不好,你一天在家,心思都用在什么地方去了?”我突然发觉在姜的眼里,我还不如他养的金鱼。那晚我早早上了床,姜上床后,像往常一样搂住我,不停向我道歉,说他连续在海上漂了一个星期,非常疲倦,没有控制住情绪,让我原谅他。他从背后温存地抱住我,吻着我的耳朵说:“我爱你,我也不喜欢和你生气,我希望我们在一起的每一天都是快乐的。”他热烘烘的男人的气息缭绕在我的颈间,唇间,我原谅了他。
夏天到来时,我决定出去工作。姜知道后,软磨硬泡地劝我放弃这个想法。他说,我们现在生活得挺好,我不需要去工作。他说,他喜欢每天下班回到干净整洁的家里吃我做的饭。他还说,他就喜欢我现在这个样子。而我依然坚持我的想法,我绝不依靠谁来养活,我要有自己独立的生活,我要在工作中感受外面广阔的世界。姜终于大发雷霆。他说,我就喜欢天马行空地胡思乱想,不安分,既然他能让我衣食无忧,我就该在家相夫教子,独立、思想只属于男人,对于女人来说有屁用,照顾好丈夫和孩子才是女人的本分!
天啊!这是那个在晨曦中和我谈生命的自由和辽阔的男人吗?我现在才明白,他不过是把我当做一个能顺遂他心意的倾听者而已,我从没有走进过他的内心,他也从没有接纳我。那天清早在船头,他不是说我不懂这些吗?当时我竟没理解他说这句话的意思。在他看来,我永远也不会懂这些,女人只是缸里的鱼,笼中的鸟。他需要的只是我这具作为他社会意义上的女人的躯体,他需要的是我能像他养的宠物一样顺从他,这和乔,又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呢?
我问姜:“如果我们认识的时候我就有工作,是否你就不会和我走到今天?”
姜说:“没有如果,生活不需要假设!”
第二天,我离开了姜的家。临走时,我给姜留了一张字条,上面写着:对不起,鱼缸太小!
隐喘了一口气,用她的另一只手抓住了我的手,就在那一瞬间,我的脑海里划过一道闪电,我终于抓住它们了,我想起来了……
我问隐:“你是谁?你到底是谁?”
隐说:“难道你还没看出来。我是二十多年前离开你的,那时你还那么年轻,满脑子那么多美好的梦,但你却不敢跨出一步去寻找,我为你着急,为你惋惜,于是我就替你去了。这一去就是二十多年,可是,原谅我,我没能替你找到!离开姜后这些年,我碰到过很多男人,可正是他们让我的希望一点点消失,后来我渐渐觉得,也许喬和姜是对的。
生活就像一条逼窄的隧道,不问出处,不问方向,只要跟着前面的人走,你会获得安全感,即使偶尔碰到一条岔道,又有几个人有勇气迈出一步,走向不可预知呢?既然绝大多数女人都是这样生活,我为什么不呢?现在,我累了,我回来了。这些年,你过得好吗?”
“隐!”我干涸的眼里已经流不出眼泪,我紧紧地握着她的手说:“谢谢你!”
我接着说:“我不知道现在自己过得好还是不好,但那又有什么意义呢?”
天色已晚,这时我听到钥匙开门的声音,是丈夫回来了,就在丈夫进门的瞬间,隐用尽全身力气和我融为一体。
“刚才你在和谁说话呢?”丈夫问。
没等我回答,丈夫又说:“怎么不开电视?听说这两天正在放一个电视剧,收视率极高,快打开看看。”
我说:“有什么好看的,那是别人的生活。”
丈夫奇怪地看我:“别人的生活就是我们的生活。”
沉默了一会,我说:“如果刚才我是在和另一个我说话,你相信吗?”
“没有如果,人不可能有另一个自己。生活中没有假设。”丈夫说。
编辑手记:
《进城的大树》是一篇颇具现实生活气息的小说,小说里的生活可能就真实地发生在现实生活中,作者用“进城的大树”来比喻农村进城来照顾孙辈的老人,生活习惯的不同,教育程度的不同以及观念的不同,必然使得这“进城的大树”虽然有丰富的营养和管护,却在移植的过程中枝丫、根脉被斩断,难以吸收足够的阳光和营养。小说里的婆婆素珍就是这样,她不习惯城里的生活,和儿子儿媳生活习性的不同导致她离家出走回农村。这可能是现在很多人面临的现实生活,城乡的异质性必然导致“进城的大树”需要更多的理解以及时间的适应,作者用生动形象的比喻和集中爆发的冲突矛盾探讨了城乡不同、习惯不同的两代人该如何相处的现实问题。
《你不能假设生活》这是一个女人对生活的假设,一个女人与另一个自己的对话,那个敲门而进的“隐”,向“我”述说了两个故事,在梅思丽沙漠里和乔的故事,在小县城里和姜的故事,两个故事都是现实生活的隐喻,一个故事隐喻着灵魂的栖息和被抛弃,“上帝的眼泪”所象征的灵魂终是被抛弃在沙漠里。另一个故事隐喻着生命的自由与辽阔,鱼缸象征着生活的牢笼和爱的牢笼,而寻求生命的自由和辽阔必将冲破牢笼。其实,两个故事都是女主人公的想象和假设,那个不速之客“隐”就是另一个“我”,她替我出去寻找和体验,她替我去过假设的想象的生活,但是生活本身是不能假设的,无论是隐喻的灵魂,还是自由的生命,很多生活的想象都是不能假设的,这便是生命的真实状态和生活的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