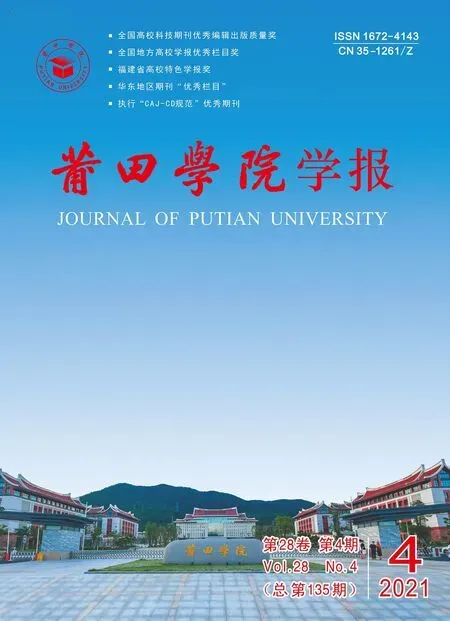《史记·伯夷列传》成文考
陈毅超
( 厦门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系, 福建 厦门 361005 )
自宋王安石以来, 《史记·伯夷列传》[1]2121-2129(下文简称 《伯夷列传》)的真实性便屡遭质疑[2], 清代梁玉绳更是列八证以说明此文 “不可信”[3]。 考察他们辩伪的依据, 大抵是 《伯夷列传》 有与儒家典籍相抵牾的部分。 然而, 《伯夷列传》 的母本原本就不是正统史家典籍或儒家经典, 通常被认为是 《吕氏春秋 · 诚廉》[4]267-269或 《庄子·让王》[5]965-989其中的一篇。若是将 《伯夷列传》 中的伯夷故事分解开来,就会发现其包含 “相让孤竹” “文王善老” “叩马而谏” “义不食周粟” 等多个情节, 而这些情节所表达的思想或分属于不同的诸子学派。 这些思想之所以最终杂糅在 《伯夷列传》 中, 或是诸子辩论的结果。
一、 《伯夷列传》 的母本:《庄子·让王》 与 《吕氏春秋·诚廉》
《伯夷列传》 之母本, 极有可能来自于 《庄子·让王》 与 《吕氏春秋·诚廉》 的其中一篇。虽然司马迁称 “余悲伯夷之意, 睹轶诗可异焉”[1]2121-2129, 然而据 《伯夷列传》 所叙 “……尧让天下于许由, 许由不受, 耻之逃隐。 及夏之时, 有卞随、 务光者”[1]2121-2129, 其顺序与 《庄子·让王》 一篇一致, 因而司马迁在编纂 《伯夷列传》 前必然看过该文。 尽管不能武断地否认 “轶诗” 存在的可能性, 但想必 “轶诗” 也与 《庄子·让王》 或 《吕氏春秋·诚廉》 有脱不开的干系。
更大的争论来自于 《庄子·让王》 与 《吕氏春秋·诚廉》 两者, 由于两篇文字的相似性,其中一篇极有可能摘抄另外一篇。 理论上讲,《吕氏春秋·诚廉》 摘抄 《庄子·让王》 可能性更大, 但自宋苏轼以来[6], 《庄子·让王》 的真伪便屡遭质疑, 罗根泽、 张桓寿等[7-8]更是认定《庄子·让王》 杂抄 《吕氏春秋·诚廉》, 因而二者孰先孰后就成了一个无法简单论断的问题。罗、 张二人认为 《庄子·让王》 篇后出的证据如下: 一是 《庄子·让王》 的故事散见 《吕氏春秋》 诸篇, 二是 《吕氏春秋》 字词较古, 而《庄子·让王》 所用字词较新[7-8]。 此外张桓寿还认为: 《庄子·让王》 将 《吕氏春秋》 中 “尧让天下于许由” 和 “子州支父” 两个故事糅合成一个故事, 且其叙述后加议论的行文手法与《吕氏春秋》 更为接近[8]。 关于诸如罗、 张的观点, 程苏东有一精辟的总结: “……罗、 张等人的研究基于两个前提: 第一, 今本 《让王》 与《吕氏春秋》 的用字均严格保留了其 ‘原本’ 的面貌; 第二, 《让王》 与 《吕氏春秋》 两者中有且仅有一种是完全意义上的原生文本, 两者之间必然存在非此即彼的传抄关系。”[9]然而事实却是, 不管是 《吕氏春秋·诚廉》 还是 《庄子·让王》, 其文本都可能在传播过程中发生较大的变化, 从阜阳双古堆出土的 《庄子》 残简来看, 文字方面今本已与汉本存在一定的差距[10](见表1)。

表1 《庄子》 汉本(阜阳双古堆汉简)和今本文字比较
此外仍有一点颇为关键, 即 《庄子·让王》篇所赞扬的杀身卫道的行为, 事实上和 《庄子》全书的观点并不相合[11]。 《庄子》 一书其他篇章如 《大宗师》 批评伯夷叔齐 “不自适”[5]232,《骈拇》 批评伯夷 “残生伤性”[5]323。 关于此种矛盾, 程苏东认为 《庄子·让王》 存在一处阙文, 这段阙文如今还可以从 《吕氏春秋·仲春纪·贵生》 中看到: “子华子曰: ‘全生为上,亏生次之, 死次之, 迫生为下。 ……’ ”[4]38-42
在这段文字之前, 正好出现了 《庄子·让王》 与 《吕氏春秋·贵生》 的同文, 而这段文字所说的 “全生” “亏生” “死” 又和 《庄子·让王》 一篇相对应, 因而极有可能是 《庄子·让王》 的阙文。 此外, 其 “死次之, 迫生为下”的观点恰好解答了 《庄子·让王》 故事意旨与《庄子》 一书相抵牾的原因: 收录者并非鼓吹这种投死的行为, 而是出于对 “迫生” 的排斥,而认定了以死卫道这一行为的合理性。
其次, 《庄子·杂篇》 很可能并非出自一人之手, 因而其观点与书中其他地方有相冲突之处也不难理解, 如 《庄子·天下》 之行文, 显然是杂家笔法。 因而不足以说明此篇是抄自 《吕氏春秋》。
二、 诸子争辩与伯夷叔齐故事的演进
从 《论语》 到 《庄子·让王》 的时代, 伯夷叔齐二人的故事确实经历过层累式的演变, 演变的重要动力是诸子之间的辩论。
在孔子的时代, 对于伯夷叔齐的宣传, 就已经形成了一种社会舆论。 所谓 “民到于今称之”[12]230, 可见最早鼓吹伯夷叔齐的并非是孔子。 《述而》 篇孔子与子贡的对话更是耐人寻味, 当子贡发问 “伯夷、 叔齐何人也” 时, 孔子并没有回答二人的事迹, 只是对他们的人格做了定性, 子贡此后也没有追问这次定性的依据。可见, 子贡与孔子不仅都知道伯夷叔齐, 也都默认对方知晓二人的事迹。 足见在当时, 对伯夷叔齐的宣传应当已经很普遍。
孔子主要鼓吹伯夷叔齐的节操和廉洁, 事实上, 他并没有言及二人相让孤竹与归于西周的故事。 但后世经传家在解释 《述而》 的这段对话时, 都会默认存在二人相让孤竹的背景, 如《论语注疏·述而》 篇便以二人相让孤竹之典故回答孔子不入卫之缘由[12]89-90。 但如此解释, 将无法理解 《论语·公冶长》 中的一句话: “伯夷、 叔齐不念旧恶, 怨是用希。”[12]66-67首先, 伯夷叔齐不念的是谁的 “旧恶”? 是彼此吗? 还是他们的父亲? 这都解释不通; 其次, 如果隐去“相让孤竹” 这层背景的话, 会发现对这段记载的理解省去了许多曲折——子贡首先询问孔子对这两位 “逸民” 的评价, 孔子说他们是 “古之贤人”, 这就是肯定了他们隐逸行为, 子贡又发问: “他们隐逸之后, 是否会因此而感到遗憾?”孔子回答说: “求仁得仁罢了, 有什么遗憾呢?”因此, 子贡认为孔子出于道德的考量, 不会出仕帮助卫君。 最后, 在 《孟子》 的论述中, 也没有出现有关 “相让孤竹” 的内容, 对于二人隐逸的原因, 孟子的解释是: “治则进, 乱则退。”[13]215,669和所谓的 “相让孤竹” 没有关系。而人们在追溯 “相让孤竹” 的故事时, 会发现其本身是带有相当的恶意的。
曰: “伯夷叔齐实以孤竹君让, 而终亡其国, 饿死于首阳之山。 实、 伪之辩, 如此其省也。” ( 《列子·杨朱》)
杨朱曰: “伯夷非亡欲, 矜清之邮, 以放饿死。 展季非亡情, 矜贞之邮, 以放寡宗。 清贞之误善之若此。” ( 《列子·杨朱》)[14]
后世的补辑者虽将两段话归于一书一人, 然而很明显这两段话分别是出自名家与道家, 但二者对于伯夷叔齐的态度一致。 值得注意的是,《列子·杨朱》 中这两段话对伯夷、 柳下惠(即展季)的批评, 和 《孟子》 是对应的。
孟子曰: “故闻伯夷之风者, 顽夫廉, 懦夫有立志。 闻柳下惠之风者, 薄夫敦, 鄙夫宽。” ( 《孟子·尽心下》)[13]976-977
所以, 将 “相让孤竹” 的故事理解为对儒家伯夷叔齐传说的反拨是完全有理由的——儒家尊伯夷叔齐为 “古之贤人”, 其他学派便诋毁二人; 儒家称誉伯夷叔齐之廉, 其他学派便指责二人因廉洁而伤生。 但公正地说, 并非只有攻击儒家的学派为了宣扬特定的观点推动了伯夷叔齐形象的改变, 儒家为了传达特定的价值观, 也参与了这一过程——如上文所说, 赋予伯夷叔齐二人形象以商周易代历史背景的正是儒家。
孟子曰: “伯夷辟纣, 居北海之滨, 闻文王作, 兴曰: ‘盍归乎来! 吾闻西伯善养老者。’ ” ( 《孟子·离娄上》)[13]512-514
那么孟子为何要给伯夷故事加上商周易代的背景呢? 事实上, 孟子对于伯夷的隐逸行为, 还是持保留的态度, 这或源于孟子对于士人出仕有一种别样的执着[13]420-426。 尽管孟子亦曾批评伯夷 “隘”[13]249, 但伯夷毕竟被孔子定性为 “古之贤人” 了, 因此, 为了强调伯夷隐逸精神与道家避世态度根本不同, 孟子以 “危邦不入, 乱邦不居” 的 “知命” 精神, 来论证伯夷隐逸行为的合理性。 由此, 孟子选择了 “伯夷归周”的故事以强调伯夷 “治则进” 的态度。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 孟子不知道或不承认所谓 “不食周粟, 饿死首阳” 的传说——所谓 “治则进,乱则退” 强调的是明哲保身的处世之道, 与“饿死首阳” 舍身殉道的精神相互矛盾。
然而, 很可能令孟子没有想到的是, 他所择取的这一段原本用以论证西周政权合法性的文字, 由于 “归隐首阳山” 这一个细节的插入,反而变成了否定西周政权合法性的论据。 “归隐首阳山” 只是将儒家原本用以指涉商朝或其他势力的言论掉头指向了自身, 从而将儒家 “不降其志, 不辱其身”[12]252-253与 “不以贤事不肖者”[13]829-830的矛头转而指向以武王为代表的周朝。 因此, “义不食周粟” 极有可能是针对孟子“二老归周” 所创造的。 “昔周之兴” 的故事,既认同了孟说, 又对其进行了彻底的批判, 可谓操矛入室。 一方面, 这一故事认同孟子所说的商周易代的背景, 认同儒家对伯夷叔齐二人的评价, 甚至还赋予孔子 “不念旧恶, 怨是用希”一个圆融的解释, 它让商朝成为 “旧恶” 的具体所指——伯夷叔齐正是出于 “不念旧恶” 的理念, 所以坚决反对伐商; 可另一方面, 这个故事却巧妙地将二人置于周初统治者的对立面, 在孟子原本 “治则进, 乱则退” 的精神上赋予其崇高和悲壮的意义, 使其一转原本的圆滑画风,转变为一场为反抗时代而 “杀身成仁” 的悲壮故事。 这个故事编造得天衣无缝, 以致于它一进入正史就深入人心。
三、 司马迁的调和与立意
比较 《伯夷列传》 与 《庄子·让王》 的文本, 会发现司马迁进行了6 处改动: 1)在“归周”与“义不食周粟”之前加入“相让孤竹”的背景; 2)将武王 “与盟” 的故事替换为武王 “伐纣”; 3)将伯夷叔齐 “相视而笑” 的情节删去,加入 “叩马而谏” 的情节; 4)该故事加入了“太公” 这一角色; 5)将二人 “相视而笑” 的部分内容改写为 《采薇歌》; 6)除 “神农” 外, 又加入 “虞、 夏” 以作为鼓吹的对象。[1]2121-2129
应当说, 司马迁的这种改写主要是为了整合诸多材料, 各种传说之间毕竟存在矛盾, 如“相让孤竹, 饿死首阳” 与 “义不食周粟而饿死首阳” 是互斥的, 而 “归周” 与 “避周” 之间,也有不通之处。 司马迁采取了折中的办法, 他在保留伯夷叔齐二人高尚品质的同时, 又加入了太公这一原本也处于 “归周” 队伍中的人物, 缝合了孟说与 《庄子·让王》 两系故事之间的漏洞, 缓和了伯夷叔齐二人与周朝的矛盾。 此外,由于比起 “与盟”, “伐纣” 的正当性要高得多,所以武王在这一故事中由原本的反面形象转变成中性的形象。 伯夷叔齐 “叩马而谏” 所表达的是纯正的儒家道义, 不再有原本故事所强调的复古无为的思想。 对武王的批判则由 《采薇歌》来承担, 不再那么尖锐。 以虞夏置换神农的笔法, 也抹淡了原本故事中禅让理念的道家色彩。
太史公此处的改写极其高明, 他抹去了《庄子·让王》 这个故事对儒家赤裸裸的恶意。其效果从宋代的经传中可以看出, 《论语注疏》在注 《论语·公冶长》 “不念旧恶, 怨是用希”时直接套用了 《史记》 中的背景, 甚至到后来,人们在批判 《伯夷列传》 不合儒家义理的时候,都忽略了这个故事母本原来的思想背景。 当然,这种改写应当是因为缺乏史料, 按理来说, 伯夷叔齐不足以被单独列传, 但司马迁仍作 《伯夷列传》, 并置于列传之首, 司马迁固有其用意。司马迁的史学观念标新立异, 他不仅仅致力于理清帝王和贵族的世系与事迹, 记载重大的历史事件和社会状况, 还对那些有才有德, 却因 “儒、墨皆排摈不载” 而 “湮灭不见” 的贤人游侠投以特别的关注[1]3181-3189。 从这个角度讲, 《伯夷列传》 与其说是伯夷叔齐的独传, 不如说是七十列传之序。 司马迁表达了自己的野心, 即使“六艺” 不载, “诗书虽缺”, 他也要凭借自己的努力使得这些不 “附青云” 而名 “不称” 的古人得到他们应有的称誉。 这种执念或来源于司马迁自身的志向, 当他将 “鄙陋没世, 而文采不表于后” 的恐惧推及前贤之时, 自然会为那些“没世而名不称” 的君子感到深深的惋惜。
四、 结语
考察伯夷叔齐形象在 《伯夷列传》 前的演变, 会发现其恰如顾颉刚所说, 发生过层累式的积淀[15]。 先是产生 “相让孤竹” 的故事, 随后又产生 “二老归周” 的说法, 最后由 “昔周之兴” 这一背景加以统合, 从而形成 《庄子·让王》 中的伯夷叔齐形象。 然而推动这一形象发展的并非顾颉刚所说的时代观念, 而是诸子之间的辩论。 此后, 司马迁为了缓和 《庄子·让王》伯夷叔齐故事对儒家的激烈批判, 也为了解决诸子传说之间的矛盾, 用儒家道义置换故事原本的思想, 使得故事更加圆融, 从而形成 《伯夷列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