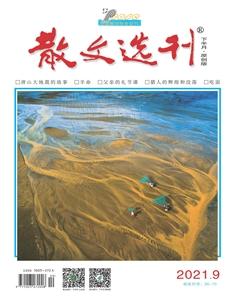猎人的辉煌和没落
杨启彦

上世纪80年代,我到乡下教书,结识了非老师。他是一位老猎人,十里八乡,名声如雷贯耳。
狩猎,我们老家叫跑山、撵山。满山遍野瞎跑,灰头土脸,野人似的,但对非老师猎获归来的酒局,不离不舍。那些年月,我们的粮油供应本都由单位保管着,长时间闻不到肉腥,能吃到点野味是多么不容易啊。非老师扛枪出了门,我们几个小青年就深夜不睡地候着。凌晨两三点,或者三四点,他终于回来了。大伙像绿头苍蝇嗅到屎臭味般围了上去,七手八脚抢着帮忙,生火的生火,找锅的找锅。猎物细细剁了,油炸了上桌,一干人围着喝酒。天快亮了,酒也干了,才散场子。然后,是下一次漫长而焦灼的等待和期盼。
非老师给乡下枯燥乏味的生活平添了许多乐趣。他常乘着酒兴,给我们讲狩猎的事。他说,没月的时候,傍晚到了山上,猫着腰,贼兮兮地在密林中伏着,竖着耳朵听野鸡飞动的声音。天黑定了,鸟就不再飞了,记住它最后停留的那片区域,打开手电光去找,跪着爬着找——夜间,鸟是不动的。找到后,手电光照定猎物,“嗵”的一声,一条火龙疾飞而出……有月的时候,戴了头灯,伏在荒草地里,竖起耳朵听。月亮升高了,人只嫌耳朵不够用。有时伏两三个小时,也没有等到兔子,虫子把身体叮了个遍。有时不大一会儿,草地里就传来“嚓嚓嚓”的声音,那是兔子吃草了。估计了兔子的位置,举枪,突然打开头灯,射向兔子,扣动扳机,火龙映红了夜空,兔子应声而倒。这样的夜晚,我们就忙乱得鸡飞狗跳,比水还淡的日子,有了甜蜜,有了欢笑。有时,老非也会把一只生擒活捉的野鸡或野兔卖掉,用来购买弹药,更换枪证,也有时用来给老母亲看病买药。我们虽然有一丝遗憾,也能理解他。卖掉猎物,救急生存,而我们一次不吃,不会死人。老非有时也会很沮丧,忙碌一整夜,只弄到几只老黄雀或是两三只小松鼠。我们就会安慰他:十跑九空嘛,哪有常胜的将军。
然而,老非竟封枪了。他讲述时的声音都充满了追悔和没落。那是一次大型的围猎活动,派出所的老张也带着功勋卓著的大黄狗来了。非老师负责老鹰山西面的垭口。大黄狗的叫声战栗了整座山头,人们的传令声一阵紧似一阵。不多会儿,一只小黄牛一样的麂子被大黄狗撵着,飞奔而来,像一道闪电。“嗵”一声,老非的枪响了,可不幸的是,地上躺着的,不是麂子而是大黄狗。猎人们围拢来,充满了惋惜,老非啊,吃了一辈子素,倒把手伸进猪油罐子里了。老非黯然神伤,一屁股坐在地上,半天一言不发。
按规矩,猎人误伤了人或是家畜,就应洗手封枪,否则要遭报应,灾难临头。“非老师封枪了”。这给他辉煌的人生,抹上了无法消除的污点。他反复只说着一句话,语调是無尽的感伤,明明瞄准了麂子的,却偏偏打了大黄狗。
上世纪90年代中期,政府收缴了枪支,不准打猎了。非老师很高兴,他说日子好了,市场上的肉都吃不完,用不着跑山了,让野鸡、野兔、小麻雀们也过安生日子吧。不几年,非老师退休了,他到城里买了房子,带孙子,还养了很多鸟和兔子。木条装钉成的栅栏里,整整三大栏兔子,摆满了阳台,最上层是鸟笼。那个夏天,我见他打着伞,背着草,一身泥巴地在街上走着,像个农村的老头子。我劝他说:“市场上的草多便宜,不用亲自到野外去。”他说:“市场上只要买点饲料就可以了。野外多好啊,泥巴、小河、青草的味道多好闻啊。一到野外,人就清爽了,健康了。”我开玩笑地说:“当年你可是有名的猎手啊,现在倒成兔崽子们的‘奴隶了。”他也笑了,说:“奴隶好,奴隶好,又休闲又养生。最闹心的,是孙子不让杀兔子,这龟孙子要把兔子放回山里去。”于是背地里,非老师常常在孩子们去学校的时候,杀了兔子,给我打电话。我便屁颠屁颠跑了去,两人偷偷地背着孩子吃兔肉。
这样的生活,非老师一过就是十多年。
再次见到他,是在几年前,他正在医院的走道上,一瘸一拐地挪动。奔走如飞的老猎人,变成这样,我有些心酸。扶着他慢慢坐下来,他的两个膝盖,疼得厉害。他有些悲观地说:“到底还是遭天谴了,杀生太多,这双脚的使用期限怕是到了。”我说:“不就是骨质增生吗,医生总有法子的。”我给他介绍了桐子叶泡酒擦,他鸡啄米似的点头。后来我给他买了硫酸软骨素片,说这个能营养骨头呢。他高高兴兴地收下了。
非老师就这样蹒跚着了,日复日,年复年,跑山成了陈年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