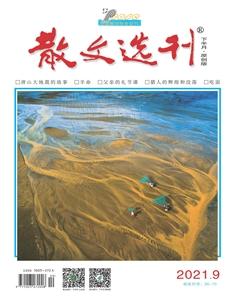一条狗
宋扬

狗命贱如斯。跟了我家的狗,命更贱。
岳母安完心脏起搏器一周后,医生宣布她短时间内不宜再独自一人生活。岳母虽极不愿意,也只得敬畏着听从医生的话,随我们进了城。进城前,我们载她回老宅收拾屋子,往返皆匆匆。鸡鸭鹅一次性全处理了,有生命的只剩“桩桩”。乡下,有人惦记狗肉,我们不敢敞放“桩桩”,大门一锁,钥匙交给幺爸,让帮着给它碗剩饭。
最后一次看“桩桩”,是回老家吃一个百日宴。宴后,我们把吃剩的给“桩桩”打包了满满两袋,冻在冰箱里,等幺爸取。原以为够它吃好几顿的了,没想到它风卷残云,几分钟就吞下了一整袋——它太饿了。幺爸家经营着一家酒坊,忙生产,忙销售,三顿作两顿的,哪顾得上一只狗!
十年前,岳父赶集,回来的路上捡了“桩桩”。刚进家门时,“桩桩”还只是一小团麻黑麻黑的肉团,在寒风中瑟缩着。岳父偕岳母在外打工多年,说是替建筑大老板当管理,没少下苦力,但到年关,挪到手的钱尚不及一个小工。他供妻读中师,供妻弟读大学,又好围朋结友抽烟喝酒,哪有余钱?
那段日子,房地产生意不好做。一次,老板上工地视察,工地板房办公室里,岳父心爱的收录机咿咿呀呀惹老板心烦,老板一迁怒,收录机粉了身碎了骨。岳父性子也刚,铺盖卷儿一捆,回了老家。
然后造新屋。妻和妻弟各凑了三万块钱,才勉强给他们修起几问砖房。曾经风光无两,一时老境颓唐,岳父精气神不再,身体亦每况愈下。
以前破破烂烂的草房只有一些锅碗桶碟,似乎也用不着狗去看护。新房造好后,“桩桩”回来了。再后来,岳父脑溢血不在了,“桩桩”还在。
那天,岳母一大早去了山上做农活,挨近中午回家,才看見岳父倒在床下已不知几个钟头——他大概是起床太急,加之有高血压,血往上冲……
并没有发生和某些电影里一样的狗向旁人报警,救活主人的事,无人知晓“桩桩”当时有没有狂吠不止,它也没有奔到山上找回岳母。也许,在“桩桩”看来,岳父倒在那里,只是换了一个睡觉的地点,摆了一个与往日不同的姿势而已。岳父是“桩桩”的菩萨,“桩桩”却不是岳父的救命稻草。“桩桩”不是一只有灵性的狗。
岳父去世后,我们把岳母接到城里住过一段时间。她闲不住,让我们给找个活儿做。她听力不好,对助听器很不习惯,说耳朵里有蜂子飞,一直嗡嗡飞,又像有火车在跑。听力不好,与人说话就吃力,岳母连广场舞大妈的圈子都融人不了,更别说找工作。好不容易在一个家具卖场扫上地,可卖场生意不好,很快关了张。岳母自行主张,坚持回了老家。她去20里地之外的妻舅家接回“桩桩”时,“桩桩”已寄人篱下整三个月。
被我断定灵性不够的“桩桩”在经历了丧失男主人,被女主人丢下又接回几件大事后,仿佛越来越懂得了一个家、一个窝的弥足珍贵。岳父在世时,家里喝茶打牌的、祝寿拜年的还算闹热;主心骨不在了,门庭陡然冷落。“桩桩”逢人便吠的霸气也慢慢钝了——年头到年尾,没人上门,它能吠谁呢?
岳母的听力日渐委顿,“桩桩”的耳朵却一天天灵光起来。每次回老家,我的车还在离家几十米外的徐三茶铺时,它兴奋的吠叫便传来。它居然能隔了几十米从每天来来往往的众多机动车中听辨出我的汽车的声音,闻嗅出我们身上挥之不去的,与它身上一样的,与这个家的一砖一瓦、一筷一碟同样的独有气息!是孤独,锤炼出它特殊的听觉和嗅觉。终日被拴在围墙内的“桩桩”的世界,注定没有白天,只有黑夜和孤独。
父亲说,三十多年前他当村主任,每次去乡上开会,我家的那条老狗都要去渡口等他回家。那年,全乡轰轰烈烈的打狗运动突然开始了,说是狂犬病肆虐。政策一刀切,拴养的也不可豁免。怎么办?与其让狗被工作队打死拖走,不如自行解决。如此,老婆娃儿还能得一顿狗肉打牙祭——我家的碗里,已半年不见荤腥,顿顿酸菜、豆瓣下饭,我和几个堂兄弟口水唆嘴角,终日挂着,父亲也觉得好像有一只只饥饿的嘴在抢夺他胃里的最后一星油水。就这样,父亲和大伯用一根铁丝勒住老狗的脖子,结束了它的生命。父亲作这个决定时,有没有片刻的犹豫?我无法想象老狗哀号着挣扎着望向父亲的眼神,那会是怎样的震惊、悲屈、绝望与痛恨!这条狗后来被父亲多次提起,父亲的话语里有无奈,有愧疚。但我想,假如重回彼时彼境,让父亲再做选择,他依然只能那般决绝。
狗命如斯。
一条狗的寿命有多长?三爸家的那条老狗与涛弟是同一年生的。涛弟已三十岁,有了两个娃儿,今年,狗死了。多数犬种的寿命不过一二十年,也就是说,狗与人无论多么长久的陪伴,总有一个要先走,或如我的岳父,或如三爸家的老狗。
“桩桩”整十岁了,已算一条彻彻底底的老狗。吃完打包的饭菜,它摇头摆尾地跑到我的面前。我摸它,它温驯而满足地享受我沿同一方向的抚摸,享受来自我掌心的温度。我给它拍照,它一副泪眼汪汪的样子。它已经明白,我们此番回来是待不久的——它从我们收拾家什、装袋蔬菜和大米的手忙脚乱中早已知晓又一次别离的到来。它不叫不跳,只默默看着我们。我们从堂屋走向灶房,从院坝东南角走到西北角,它的目光也从堂屋走向灶房,从院坝东南角走到西北角,眼沁沁地。这次,我们不敢把它送到20里外的妻舅家。临近年关,回乡的人多了,有的连不值钱的玉米、谷子也偷。那是岳母的口粮,一粒一粒都是汗,总得看着。
锁上围墙大门的那一刻,我和“桩桩”再次四目相望,我说:“‘桩桩,你要守好家,我们过几天就回来了。”
一别又是月余,我们终是没能回去。晚饭时,岳母怯怯地说,她梦见“桩桩”死了,缩在围墙内的草窝中,执意要回去住了。我的心,被什么狠狠刺了一下,眼泪几乎就要流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