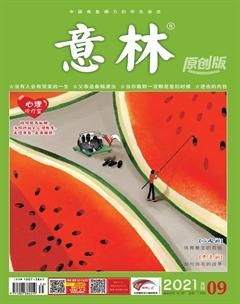父亲是条摇滚虫
林一芙
一个人意识到父母之恩,就是这个人成年之时。一个人意识到父母之恩,就是这个人能肩负责任之时。第一次为人子女,我们都很青涩。
血缘亲情,没有什么是不能原谅的。此生为家人,就是所有的人都抛弃你,我也不会离开你。即使相顾无言,青春叛逆,仍是一生一世的父母子女。
生命最大的残酷——我只能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做你们的子女。当我懂得你们时,你们已经老了呀!第一次为人子女,让我们彼此关照,用爱相处,用情相助。
1
小時候,老师问我们长大以后要做什么。话音刚落,别的小孩众说纷纭,有的说做画家,有的说做科学家。那时候我以为所有厉害的人都是“某某家”,书法家、画家、科学家……我也举手,说我要像我爸一样,做个摇滚家。
我记得当时老师摸了摸我的头,告诉我那叫摇滚乐手,这是我第一次记住了父亲的职业。
后来我才知道,玩摇滚的人是没有家的。
从有记忆开始,父亲回家的次数便屈指可数。有一次,他半夜演出完,醉醺醺地回到家,看见熟睡的还是小婴儿的我,一时酒劲上头,开了瓶白酒就往我嘴里灌。幸亏母亲被我的哭声吵醒,及时拦下来。她心疼得不行,吼父亲:“你这个爸爸是怎么当的?”父亲像个做错事的孩子一样,局促不安地靠着墙根站着,酒醒了一大半。
这件事成了母亲的笑谈,只有我耿耿于怀,以此作为父亲不负责任的罪证。
2
父亲曾经自负地觉得,身为他的女儿,生出来的第一声啼哭都会是自带韵律的。结果,等我长大,嗓子都唱劈了,还是不能从老师那里换来一个及格。我爸不信这个邪:玩摇滚的爹怎能生出一点音乐细胞都没有的女儿?
直到有一次我被舞蹈老师夸奖有天赋,我爸大喜过望,自以为上天把他的艺术天赋换了种形式过继给了他的女儿。父亲为我规划好了成长轨道,每周末去少年宫学舞蹈,等到小学毕业,初中直接上艺校。
他周末不再去排练,更多的时候是带我去少年宫学舞蹈。那时候的爸爸,放到今天来看,就是个名副其实的潮爸。别人记忆里的爸爸都是骑着吱吱呀呀的破自行车,而我记忆里的爸爸则每周末骑着摩托车、昂着脑袋风驰电掣地从街头驶过。
我在舞蹈室练舞,父亲就背着写有“舞”字的粉红背包笨拙地站在门口。每当我从教室里出来,他就殷勤地迎上来问我“今天练得怎么样”“老师有没有表扬你”。我每次都面无表情地从他身边经过,心里想的是,终于结束了乏味又痛苦的训练。
到上初中的时候,身边很多同学的家长都已经有了小汽车,而我爸还骑当年那辆破摩托。
他在一家琴行教吉他,没课的时候,还兼职推销琴。推销琴是有回扣的,但他月月“吃零蛋”。琴行的人揶揄他:人是有“才”,却是缺“财”。
他把梦想都寄托在我的身上,我却开始暗自打退堂鼓。
一次,我们被老师带去户外演出。演出地点是远郊的一个新楼盘。结束时天色已晚,老师挨个给家长打电话,让他们把孩子接回去。其他的家长开着汽车来,陆续把自己的孩子接走。我爸一个人骑着旧摩托“突突突”地停在我跟前,大手一招:“上来吧,还愣着做什么?”我不知道是因为太委屈,还是那天天气真的太冷了,眼泪和着鼻涕就顺着冻红的鼻尖淌下来。为什么别人的父亲都可以开小汽车来,而我的父亲这么孬?
父亲给我戴安全帽的时候,我说:“爸,我不想练舞了。”他错愕地看着我,试图劝说我,以为我还是小时候那个用玩具就能哄好的孩子。但这件事我已经预谋了很久。
“那是你的梦想,不是我的。”
“我不愿意像你一样,在台上像条龙,在生活里却不如一条虫……”
他一路上没再讲过话。
晚上,他的房门半掩着,我生怕他不同意,偷偷在门口听着。屋内没人说话,只有重重的叹息声,还有突然高亢起来的歌声:“我不再回忆,回忆什么过去。现在不是从前的我……”
那首歌,父亲已经好久好久没唱过了。
回到房间后,我很快就睡着了。我对自己说,我没有必要为他的梦想埋单,我是对的。
我告别了仅仅就读半年的艺校。幸好,初一的课程不难,我很快就跟上了。
3
父亲还在琴行里教书,也开始努力推销琴。有天,琴行的人给他算业绩的时候说:“什么时候开窍了?”
他买了辆便宜的二手车,偶尔还是会送我上学。我们俩彼此沉默不语。路过艺校的时候,我突然感受到他的目光不拐弯地投射在我身上。我顺着他的目光转过头去,他赶紧匆忙地握紧方向盘:“别看我,看书。”
之后的日子里,我再也不做软开度训练,安安分分地读书、考大学。
去大学报到的前几天,他给我办了个成人仪式,趁我妈不在的时候偷偷带我去夜场。
那是他曾经唱过的夜场,人很杂。有身穿露脐DJ服的小阿姨带着笑走下台来,用手抚了下我的脸。她看起来很年轻,可是在一闪而过的走马灯下,依然显得疲惫而沧桑。
“哟,这是你的女儿啊?长这么大了。”
“可不是,9月份就要去读大学了,明天我就送她去上海。”我爸伸过手,很有力地揽了一下我的肩。
小阿姨凑近我,轻轻吻了一下我的脸颊。“你爸爸当年可是我们乐队里的一把好手,后来有了你……”她看了看父亲的眼色,换了个话题,“不过谢天谢地,你也长成个大姑娘了。”
父亲带我开了人生的第一瓶酒。有父亲在身边,我放心地喝到满脸通红。他说:“带你来见识一下,免得好奇。以后要是朋友约你,你可千万别来。”父亲顿了顿又说:“这么不能喝,看上去都不像我的女儿。”那是爸爸第一次对我说“你不像我的女儿”,失落里带着一份骄傲。
他红着眼眶,好像在说:爸爸只能陪你走到这儿了,前路叵测,你要自己保重。
4
父亲曾因为我的存在放弃了自己引以为傲的梦想,为我营造安稳的家庭。后来,他希望我能继承他的梦想,但他一次又一次地放手,让我成为和他完全不一样的人。
摇滚是反叛、是颠覆,而爱是在任何处境下的深情久伴。
我上大学那会儿是2011年。那年春节我回了一趟家,春节联欢晚会上旭日阳刚在唱《春天里》。两个老男人嘶声唱着:“可当初的我是那么快乐,虽然只有一把破木吉他,在街上在桥下在田野中,唱着那无人问津的歌谣……”
我爸抱着他的老吉他跟着唱。他是真的老了,声音远不如从前,只有按弦的手还灵巧。
我以为他在追忆昔日时光,结果他不由分说地把我搂进怀里。电视里的歌正唱到“那时的我还没冒起胡须,没有情人节,没有礼物,没有我那可爱的小公主”。
“可是我有可爱的小公主哦!”他搂着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