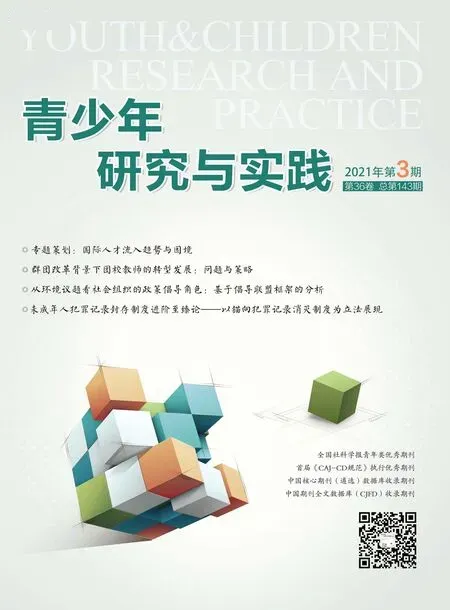临终关怀志愿服务供需错配的困境与突围
——基于1040份样本的实证分析
袁 蕾
(浙江传媒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8)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人们不仅需要“优生”,还需要“优死”。“死亡和临终最终将从隐藏的处境中移出,进入一个更加开放、公共的讨论中。”[1]于是,临终关怀越来越被世人关注。以“临终关怀”为关键词,筛选慧科新闻检索数据库2009—2020年间的媒体报道,共能搜索到17401篇。从2009年的90篇,到2020年的3156篇,媒体的关注度逐年增长。随着热度的增加,临终关怀志愿服务也开始兴起,一些高校纷纷成立临终关怀志愿服务队。然而在实践中,志愿者存在能力有限、服务单一、容易陷入“自我感动”的误区等问题;而病患与家属往往“有求无应”,志愿者提供不了他们真正需要的服务。因此,本研究提出一个假设:临终关怀志愿服务存在“供需错配”的矛盾。
一、文献综述与问题意识
临终关怀的研究强调应用性,主要关注临终关怀作为一项基本公共服务,如何能够有效推进。国内关于临终关怀服务的研究,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一)临终关怀的比较研究和历史研究
沈秀敏等人通过对国外六千余篇文献进行可视化数据挖掘,认为国外临终关怀领域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护理、临终者、死亡教育等三个方面[2]。王星明在研究西方主要国家的临终关怀模式后,认为政府重视,民众积极参与是西方主要国家临终关怀事业迅速发展的重要原因[3]。还有一些学者具体分析某个国家的模式,如苏永刚等人通过对临终关怀起源地——英国的临终关怀发展现状的研究,提出中国临终关怀事业发展的对策建议[4]。有学者梳理了我国临终关怀服务的历时性演化过程及其特征。如刘继同、袁敏全面回顾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陆地区临终关怀服务体系建设的历史和时代特征,勾勒出中国特色临终关怀服务体系的前景图[5]。可以说,在临终关怀的比较研究和历史研究方面,都是比较系统完整的。
(二)主体参与临终关怀服务的长效性机制研究
有学者指出,当前我国临终关怀事业尚处于发展的初期阶段,专业的志愿者人才储备远远不能满足现阶段的需求,培育和提升志愿者的综合服务能力显得尤为重要[6]。有学者关注到在校大学生参与临终关怀志愿服务质量的情况,指出大学生志愿者参与临终关怀服务应以导医、慰问、死亡教育等非医疗护理的形式为主;虽然接触患者的机会较少,但临终关怀服务对大学生的共情和倾听能力提出了较高的要求[7]。有学者认为,“医务社工+志愿者”是提升临终关怀志愿服务的可行模式,如为有需要的患者提供陪伴、倾听等服务;对家属进行情感关爱,协助家属完成病人临终的心愿,帮助家属顺利度过悲伤期[8]。此类研究注重从社会机制层面分析各主体如何参与到临终关怀事业中来。
(三)从个体层面对临终患者的心理特征及其护理方式开展的微观研究
不少研究立足关照临终患者的生理层面,从医护的角度探讨临终关怀的医学护理内容,以及临终关怀的价值、效果。有学者指出,临终关怀护理在改善患者心理状态的同时,还能够缓解他们的不良情绪,提高患者的满意度,进而获得良好护理效果[9]。近几年,学界越来越关注临终者的精神和心理层面,如李永娜等通过实践和调研,提出了精神、心理、生理三位一体的临终关怀整合模型[10]。
回顾已有研究可以看出,学界对于临终关怀服务的研究包含政策研究、微观心理研究以及中观机制分析,在临终关怀的意义价值、社会主体有效参与等方面,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总体来看,仍缺乏基于实证调查的分析,尤其是大样本的数据分析。同时,研究在指向性上有所不足,即注重价值层面的呼吁,缺乏对当前实践问题及原因的分析。因而,本文关注的问题在于:当前临终关怀中,志愿者这一社会主体参与情况如何,为什么会出现临终关怀服务“供需错配”,影响志愿者参与临终关怀服务的主要动机和因素何在。
二、调查方法
本研究采取定量分析方法,通过方便抽样,进行问卷调查。调查覆盖了北京、上海、广东、浙江、江苏等11个省、直辖市。
(一)问卷设计
本次问卷调查目的在于探究大众对临终关怀的认知度、接受度、满意度和需求度。认知度是指大众对临终关怀的概念、内容、接收渠道、开展对象的了解程度,以及对临终关怀志愿服务的了解程度。接受度主要是指人们对临终关怀服务开展的必要性、成为临终关怀志愿者的意愿、对临终关怀服务内容的接受度等方面。满意度是指对临终关怀志愿服务、对临终关怀相关工作人员的服务态度、对临终关怀发展现状的满意程度。需求度主要是指临终关怀服务的获得渠道、对社区附近开设临终关怀机构的态度、本人或家人接受临终关怀的意愿、对临终关怀服务的需求及志愿者年龄层次的需求。
(二)调查对象与步骤
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1088份,收回1040份有效问卷。参与调查的男性占44.21%,女性占55.79%。调查对象涉及各个年龄层次,20岁以下、20岁至35岁、36岁至50岁、50岁以上的调查对象,分别占29.85%、29.69%、29.20%和11.26%。调查对象中,本科学历占比最大,有71.29%。大部分调查对象的家庭年均收入在10万—20万元,占比为40.46%。同时,74.55%的调查对象无宗教信仰。
三、数据分析
(一)认知度、接受度、满意度均对需求度有正向强影响力
将认知度、接受度、满意度三项作为自变量,将需求度作为因变量,进行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如表1所示:首先,认知度会对需求度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优势比(OR值)为2.162。这就意味着认知度增加一个单位时,需求度的增加幅度为2.162倍。其次,接受度会对需求度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优势比(OR值)为4.341。这意味着接受度增加一个单位时,需求度的增加幅度为4.341倍。第三,满意度会对需求度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优势比(OR值)为2.636。这意味着满意度增加一个单位时,需求度的增加幅度为2.636倍。由此可知:认知度、接受度、满意度三项均会对需求度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

表1 认知度、接受度、满意度对需求度影响的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
(二)认知度:公众对临终关怀的认知仍旧浮于表面
82.20%的被调查者表示曾听说过临终关怀,但一知半解,认识较为浅层。67.05%的被调查者不清楚临终关怀的对象及具体含义,64.44%的被调查者不了解当地政府是否出台相关政策,55.46%的被调查者不了解当地社区医院是否提供临终关怀服务。这些数据表明,临终关怀志愿服务尚存在覆盖率低、群众了解不够等问题。
1.年龄对群体的认知度有明显影响。年龄对于临终关怀的认知度影响显著(Chi=70.30,P=0.00<0.01)。在“是否听说过临终关怀”这一问题中,35—50岁的调查对象选择“是”的比例是93.85%,70岁以上的调查对象中超半数未听说过。年龄对于临终关怀政策的了解程度影响显著(Chi=49.65,P=0.00<0.01)。50岁以上的调查对象中,有25.60%关注过临终关怀的政策出台,而50岁以下的调查对象中,仅有3.30%的人关注过。综上,相对而言,30—35岁青壮年群体对临终关怀的知晓度更高,但并不关注相关政策的出台;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群体对临终关怀了解少,但对相关政策出台更关心。
2.受教育程度和家庭年平均收入对认知度有正向影响。受教育程度对于临终关怀的认知有显著性影响(Chi=54.55,P=0.00<0.01)。关于“是否听说过临终关怀”,拥有博士学历的调研对象选择“是”的比例为100.00%,高中以下学历选择“否”的比例为52.38%。家庭年平均收入对于临终关怀的认知度同样影响显著(Chi=39.26,P=0.00<0.01)。家庭年收入在50万元以上的人听说过临终关怀的比例为93.33%,家庭年收入在10万元以下的人听说过临终关怀的比例为32.05%。可见,受教育程度及家庭年平均收入对临终关怀的认知度有明显的正向影响,学历越高或家庭年平均收入越高,则对临终关怀的认知度越高。
3.目前临终关怀宣教路径以传媒为主,社会覆盖率低。近五成的被调查者表示自己是从报纸、杂志、电视等传统媒体或微信、微博等社交平台了解到“临终关怀”。少数被调查者表示是从朋友、家人亲戚、医疗机构、社工志愿活动了解到“临终关怀”。同时,调研数据显示,近九成的被调查者表示身边的人没有接受过临终关怀服务。
(三)接受度:大众并未从内心接受临终关怀
87.60%的被调查者认同临终关怀的必要性,并且愿意成为志愿者。但大部分被调查者对一些临终关怀服务内容不能接受。
1.年龄、受教育程度及居住地区与接受度有较强关联。年龄对于临终关怀服务必要性的认同影响显著(Chi=16.32,P=0.00<0.01)。20—50岁的调查对象中,91.90%的人肯定了临终关怀的必要性,但50岁以上的调查对象中,有22.00%的人对此持否认态度。受教育程度对于临终关怀服务必要性的认同影响显著(Chi=45.10,P=0.00<0.01)。对“临终关怀是否必要”这一问题,博士学历的人选择“是”的比例达100.00%,高中以下学历选择“是”的比例为40.48%。长期居住的地区对于临终关怀服务必要性的认同影响显著(Chi=11.17,P=0.01<0.05),城市地区的认可度明显高于平均水平。
综上所述:根据交叉分析的结果,20—50岁的调查对象比50岁以上的调查对象更多地接受其必要性,说明现在临终关怀服务实际效用有限。同时发现,受教育程度越低,越不认同临终关怀服务的必要性。相较城市,非城市地区对临终关怀服务的必要性认同度更低。
2.宗教信仰与是否愿意成为志愿者有较强关联。宗教信仰对于调查对象成为临终关怀志愿者的意愿显著相关(Chi=22.46,P=0.00<0.01)。信仰佛教的人选择“愿意”的比例为80.39%,信仰基督教、天主教、道教的人选择“愿意”的比例分别为58.10%、66.70%、55.60%,信仰伊斯兰教的人选择“不愿意”的比例为100.00%。
3.当下临终关怀服务内容实际接受度较低。在“临终关怀服务中哪些服务您不能接受”这一题中,大部分被调查者选择了其中1—2项不能接受的服务。可见,现实中大众对临终关怀服务内容的实际接受度较低。
(四)满意度:临终关怀志愿服务存在供需错配问题
大部分被调查者表示对医疗护理类志愿服务满意。但调查中,不少调查对象仍有诸多不满意的地方。
1.志愿服务存在满意度虚高问题。虽然绝大部分被调查者表示对志愿者的服务满意,但与之成鲜明对比的是,近八成的被调查者表示对志愿服务不满意的原因在于“不知道从何寻找临终关怀相关服务团队”“志愿者服务时间没有保障,无法做到一对一服务”“志愿者提供的服务不是病患/病人家属所需要的”。这说明目前临终关怀志愿服务并未精准匹配到需求对象,服务对象对志愿服务持保留态度,反映出满意度虚高的问题。
2.最需要服务的群体对志愿者呈中立态度。服务对象年龄与对临终关怀志愿者的态度显著相关(Chi=57.16,P=0.00<0.01)。20—50岁的被调查者持中立态度的比例为52.00%,50岁以上的被调查者持中立态度的比例为36.84%。
(五)需求度:精准化志愿服务项目缺口大
大部分被调查者表示能够接受其所在的社区医院开设临终关怀机构,并认为费用应由多方综合承担,应将其纳入医保。大部分被调查者不愿意让患病接受临终关怀服务的原因在于志愿者的陪伴无法代替家人的陪伴,并表示更希望接受专业医护及情感陪伴方面的服务,希望志愿者的年龄层次可以覆盖20—50岁年龄段。
1.临终关怀服务的社会接受度受社会因素制约。年龄与对在社区附近开设临终关怀机构的态度呈显著相关(Chi=37.10,P=0.00<0.01)。调查数据显示,对于“是否愿意接受在社区附近开设临终关怀机构”这一问题,20—50岁的被调查者选择“不”的比例为38.00%。年龄超过50岁的被调查者反对的比例更高。一线城市的被调查者更愿意接受在社区附近开设临终关怀机构。在临终关怀的社会接受度方面,年龄对于把患病的亲人送去接受临终关怀服务的态度影响显著(Chi=34.67,P=0.00<0.01),50岁以上选择“愿意”的比例为57.89%,明显高于平均水平。50岁以上老人大多自理能力差,难以照料身边患病的家属,因此意愿更强烈。62.60%的被调查者表示愿意根据亲人的意愿选择是否送亲人接受临终关怀。同时,调查数据还显示,受教育程度越高,让患病家属接受临终关怀的意愿更强。宗教信仰也影响调查对象让患病家属接受临终关怀的意愿。
2.临终关怀费用昂贵,患者经济压力大。八成以上的被调查者认为临终关怀的费用应由多方综合承担,纳入医保。近七成的被调查者表示每月仅能承担5000元以下的费用,而目前实际服务费用基本在6000元以上。
3.临终关怀志愿服务发展体系并不完善,发展困境多。30.90%的被调查者表示,“医疗人员或志愿者代替不了亲人朋友间陪伴的感情”是其不愿意送亲人接受临终关怀的最主要原因。还有20.00%的被调查者认为“医疗人员还达不到能够给予最好护理的水平”。超过六成的被调查者希望临终关怀志愿者的年龄在30—50岁之间,12.9%的被调查者希望志愿者与被照护者年龄相仿。50岁以下的被调查者更希望临终关怀志愿者是30—50岁。九成以上的被调查者认为目前的临终关怀存在相关专业机构少、医护人员及志愿者队伍不专业不稳定、缺乏政策法律保障、社会投入资金少等问题。
四、对当前我国临终关怀志愿服务的建议
根据本次调研,临终关怀志愿服务存在供需错配的假设成立。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速到来,整个社会对临终关怀的需求越来越大,相应的志愿服务品质也亟待从无序往有序的“持续发展”转变。
(一)观念困境的突围:用传统儒家文化开展生死观及生命教育
临终关怀目前的困境纵然有政策制度尚不健全的原因,但思想文化的深层次原因也需要分析挖掘。在大部分中国人眼里,死亡就意味着“什么都没有了”,面对死亡,人就会绝望。因此,要提高临终关怀服务的有效性,降低临终者对死亡的恐惧是最核心问题。“临终关怀事业的核心之一,是要在人们的医护观念中形成正确的生死观。”[11]在临终关怀服务中,降低临终者身体的疼痛感主要靠医学手段来完成。而克服心灵上的恐惧并非一定要借助宗教文化。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中,就有非常丰富的内容。对死亡的理性思考与追问,可以让我们有更加清明自觉的死亡态度。“有生者必有死,有始者必有终,自然之道也。”[12]这些植根于传统文化的生命教育和对生命价值的探索是志愿者可以作为的。
(二)政策困境的突围:构建专业机构、社区、家庭三位一体的服务模式
通过“专业机构—社区(村集体)—家庭”的三位一体服务模式,临终关怀志愿服务可以在不同层面提供不同的服务。一是专业机构提供全方位的临终服务。在医院的临终关怀科室、社区的临终关怀服务站点等专业机构中,病患可以获取专业的医疗服务,比如通过药物减轻疼痛程度、借助医疗器械进行各类治疗等。二是村(社区)负责牵线搭桥。作为专业机构和家庭之间的沟通者,社区或村集体应该作为临终关怀事业的科普者、倡导者、规划者。社区或村集体可以通过社区医院提供部分临终关怀服务,也可以以更灵活的方式进行上门服务,还可以和各类志愿组织合作,提供更为立体的临终关怀服务。三是家属亲友提供情感支持。居家的临终照护,最不缺情感的关怀。亲友可以通过完成家人心愿、陪伴等方式,在情感上减轻病患的痛苦。在家庭层面,也需要一些有医护专业背景的志愿者上门提供帮助,以减轻病患身体上的疼痛。
(三)服务困境的突围:志愿者的多元化、服务的精准化及培训的系统化
临终关怀志愿服务要解决供需错配问题,归根结底还得落脚到服务者及服务内容是否为被服务者所需这个基础性问题上来。一是志愿者多元化。一方面,引入阅历更为丰富、时间更为充裕的志愿者。另一方面,打破单位、组织的壁垒,组建一支庞大的、涵盖各年龄层的、拥有各种技能的志愿者队伍。二是服务精准化。制订服务菜单,解决供需错配困境。志愿服务设立初级菜单目录,再通过访谈探寻服务对象的外在和内心需求,根据地域特色及团队人员等具体情况,为需求确定解决方式,明确菜单各项服务具体内容。先进行定点试运营,适当改进菜单上一些不合适的内容。三是培训系统化。做好临终关怀志愿服务,需要对志愿者的认知、态度、技能开展全方位的评估和培训。由于服务对象情况特殊,相比其他志愿活动,临终关怀志愿者本身的心理疏导不能忽视,要时刻关注志愿者的心理变化,为他们提供专业的心理辅导。
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基于调查数据的分析,得出当前我国临终关怀事业发展的现状及特点,主要结论如下:
一是公众对于临终关怀事业的认知度存在较大差异,受年龄、受教育程度以及居住地域等因素影响较大。总体而言,公众对于临终关怀的认知度较低、重视程度不够,且存在一些认识误区。这也体现出我国临终关怀事业所面临的主要困境。因而,提升公众对于临终关怀事业的认识水平,是推进临终关怀事业积极建设的重要方向,也是促进公众积极参与的重要保障。
二是大众并未从内心接受临终关怀。在调查样本中,有87.60%的被调查者认同临终关怀的必要性,并且愿意成为志愿者。但大部分被调查者对一些临终关怀服务内容不能接受,即看似社会接受度较高,但实际接受度较低,原因在于公众并不认同临终关怀的价值。这与中国传统文化有一定关系。在国人传统认知中,料理和面对亲人死亡主要是亲属或是家庭内部的事情。因而,在谈及临终关怀事业尤其是将其归为一种公共服务时,大多数受访对象表现出一定的否定态度。
三是临终关怀志愿服务存在供需错配问题。从志愿服务供给来看,存在着诸如不知道从何寻找临终关怀相关服务团队、志愿者服务时间没有保障、无法做到一对一服务等问题,体现出志愿者提供的服务无法有效满足患者及其家人所需。在需求方面,大部分被调查者表示能够接受其所在的社区医院开设临终关怀机构,并认为费用应由多方综合承担,应将其纳入医保。被调查者表示,不愿意让患病的家属接受临终关怀的主要原因在于志愿者的陪伴无法代替家人的陪伴,而更希望接受专业医疗及情感陪伴方面的临终关怀服务。这体现出当前志愿服务在临终关怀事业上存在显著的结构性困境,供需错配问题成为重要挑战。
因而,未来推进我国临终关怀志愿服务参与,应当注重从平衡供需关系的角度入手,在资源整合与投入、保障机制建设以及志愿者培训等方面进行有针对性的强化。同时,应当积极探索社会服务市场化机制建设,将第三方社会组织有效地纳入志愿服务,增加临终关怀志愿服务的参与主体,激活社会闲置资源,促进临终关怀事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