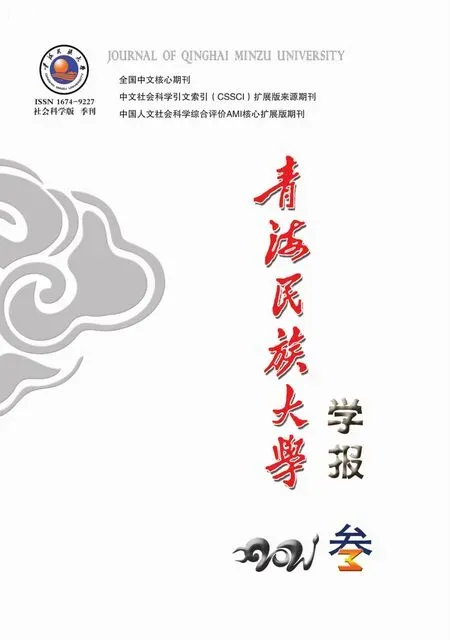从“娘娘崇拜”看互助土族地区多元宗教文化的交融
徐长菊
(青海民族大学,青海西宁810007)
河湟地区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繁衍生息之地,自秦汉以来,众多民族的先民便耕牧其中,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河湟文化。青海省东部地区地处河湟谷地,历史悠久物产丰富,汉族、土族、藏族、回族、撒拉族等多个民族在这里交融共生,孕育了各民族既个性鲜明又多元共生的河湟文化。土族是这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也在其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丰富多彩的文化面貌,是“既有自己原先萨满教文化圈的内容,又有羌藏文化圈和汉文化圈的一种融合性文化”。[1]由于河湟地区多民族交往与交流,多元文化的碰撞与交融的背景,土族更是形成了丰富多元的民间信仰体系,呈现出以藏传佛教为主体,道教、萨满教、苯教等多元共存的特点。本文试以互助土族“娘娘”崇拜为例,说明多民族间文化的交流与交融过程。在互助土族民间社会当中,道教女神“娘娘”是十分活跃的神祇之一,在各地村庙中供奉较多,被视为地方保护神。土族信众也同时赋予“娘娘”以新的名号——“佛爷”,以及本土的祭祀仪式和土族的侍神人员,从而道教女神不再只属于汉族的文化体系与传承。然而,困境也一起产生,道教的宗教场所——“道观”与修行人员——“道士”极少在土族地区分布,这是我们考察一种宗教在当地传布与否的通常标准。其核心的教义、教仪也始终未被土族人尊奉与传播,这样的局面,有着深刻的历史、现实的根源。
一、从“娘娘”到佛爷”:神祇的身份转变
“娘娘”是广泛受祀于互助土族地区的道教女神,据统计,在互助县各个乡村的村庙中,供奉“娘娘”的村庙有80 余座,在土族人口聚居较多的东山、丹麻、东沟、五十等乡镇中供奉“娘娘”的村庙多达20多座,具体分布如下表所示:
在丹麻、五十、东沟等乡镇供奉的娘娘,被称为“勒木桑”,土族民间的说法是,“勒木桑”娘娘是三姊妹,就是汉语中的云霄、琼霄、碧霄三位仙姑,即三霄娘娘,是道教中感应随世的仙姑正神。其形象是坐于一顶小轿中的女子,容貌娇美,着色泽鲜亮的宽袖长袍,是典型的明朝汉族传统服饰。“娘娘”的神轿有“明轿”和“暗轿”之分,“明轿”的轿帘可以揭开,人们可以一睹女神仙容,“暗轿”则轿帘紧闭,除了为神轿装藏的活佛和制作神像者,无人见过娘娘的相貌身形。据当地人介绍“暗轿娘娘”,是“三霄娘娘”中最小的一位,因为是以处子之身修炼成仙,所以不将容貌在世俗之人面前展现。互助地区丹麻和五十镇的东家村、浪家村和土观村三处村庙中供奉的即为“暗轿娘娘”,都是当地颇为灵验的娘娘庙,而且是属于“一卡码”。“卡码”是当地方言,意思似乎是指存在着某种内在的联系或者相似性。但为什么属于“一卡码”,村民们也语焉不详。当地还有其他村庄也有供奉“暗轿娘娘”的情况,却没有被纳入这个“卡码”范围之内。与汉族地区不同的是,“娘娘”在土
族村庄中有了一个新的名称——“佛爷”,这也是土族地区对所有的崇拜对象的统称。“佛爷”并不特指佛陀,亦可以用来称呼菩萨、护法、道教神仙以及各种被崇拜的精灵。土族人对“佛爷”的态度是包容的,他们不在意庙中的“佛爷”什么出身,什么来源,也不了解各位佛爷的神格和原生职能。但是“佛爷”的神轿必须由藏传佛教活佛装藏加持,其神力与灵验程度与此直接相关。“佛爷”存在的意义是满足崇拜者所有的祈求,在享受香火供奉的地域中,“佛爷”必须是万能的。人对神的祈求,当然会有很多“不灵验”的情况发生,但是人们往往不会怀疑神的权威,而是检讨自己祭祀、祈祷的过程是否合乎规范,是否令神感到满意。

表1 互助土族地区供奉“娘娘”村庙一览图
道教女神“娘娘”并非本土的神灵,她是外来的,田野调查中多有“娘娘”神像是大水冲来的说法,实际上她应该是随着道教一起流传到河湟地区的。一般认为,道教在河湟地区大规模的发展与传播,是在明代初年。随着大批汉族移民向青海的迁徙,道教信仰也伴随而来。此时,从全国范围看,道教的发展已经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衰落,其原因是在明清时期,道教内部再未能出现杰出的代表人物和理论创新,而在国家统治层面上,对宗教的支持重心,明显向藏传佛教转移。但在青海地区,道教随着大量移民流传而来后,却受到了当地统治者的重视与支持,从而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而且与青海本土民间信仰的交流与融合也同步发生,渗透到了当地人的日常生活当中。道教在进入互助土族地区时,也走进了当地居民丰富多彩的信仰世界,而且是深受藏传佛教影响的文化体系之中。随着不同文化体系之间的冲突与融合,道教众多的神仙成功地实现了与土族地区原有神灵以及佛教护法神的和谐相处,而跻身于土族地区的神坛之上,成为土族民众宗教信仰中的合法存在。因此,尽管并未有土族人宣称道教是他们的信仰,但道教神祇在土族地区被广泛供奉与祭祀却是不争的事实。
二、偶发性危机仪式——多元文化的交融
在民间信仰的体系中,根据一个仪式是经常举行还是偶然举行,将之分为岁时仪式和偶发性危机仪式两种类型。岁时仪式通常与农业生产周期相关联,是一个或者多个村庄在农事生产关键的节点时举行的集体性祭祀仪式,土族地区祭祀“娘娘”的仪式称为“梆梆会”,学界已有较多研究,笔者拙文《新时代民族地区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以互助土族地区传统祭祀仪式为例》[2]即是专门针对“梆梆会”的探讨,此处不赘述。而危机仪式都带有偶然性,一个人何时患病、是否失窃、出门办事是否顺利等等,吉凶祸福都不可预测,因而,人们常常在这种不确定后果支配的焦虑情绪之下,求助于神灵的保佑和赐福。治病赶鬼、占卜、驱魔等仪式常常在村庄中举行,此类仪式系偶尔为之,也即所谓“偶发性危机仪式”。在供奉“娘娘”的村庄和地区,人们各类仪式的祭祀、祈求对象,就是“娘娘”。
人们通常会认为“娘娘”是因为其女性的身份以及女子生育的功能而受到崇拜与祭祀,但是在土族民间“娘娘”的职能远不止“送子”所能概括。她以女性特有的细腻与母性的博爱,护持着特定区域内所有人与生灵的幸福与安康,而且娘娘的影响正日益扩大,外村、外乡甚至外省慕名而来的人逐年增多。在笔者的田野调查中,D 村中一位在村庙中“伺候”(不是村庙的管理人员,但主持和参与请神活动,其地位与常人无异,被村民公认具有沟通人、神的能力)“佛爷”(即娘娘)的阿爹(当地对老年男性的尊称)告诉我,他们几个阿爹已经五天五夜没有休息了,因为这几天“佛爷”很忙,到庙里问事的,请“佛爷”到家中“坐”(进行禳解活动)的人太多,需要排队等候。“阿爹”已经见过很多与我一样的采访者,在与我交流时异常地从容,他自述先前有甘肃、省城和一些大学的人到他跟前来“写”(访谈、调查)。
问:您从什么时候开始“伺候”佛爷的?
答:有十几年了,我五十几(岁)就去了(庙里),今年七十了。那个时候的一个阿爹,慢慢地把佛爷随不上了(意思是不能准确揣度佛爷的心思,导致问事不利,传达的神意与对治方法也不再奏效,不再灵验),我从小对这些“好到”(感兴趣),正好村上的人们也叫我试着“秉一次”佛爷(尝试沟通人和神,表达人的祈求,传达神的指示),再往后我“秉”的次数越来越多,也“由得很”(灵验,大致是他传达的神的指示能够符合实际情况,解决方案奏效)。
问:您学过怎么“秉佛爷”吗,或者是你们家族有过会“秉”的长辈吗?
答:这个不用学,全看你和佛爷的缘法(缘份),我们家以前没人会。
问:你们5天5夜没休息,都在忙些啥呢?
答:不是我们忙,是佛爷忙啊!这几天去了一趟北山(互助县的一个藏族乡),一趟姚马(互助东沟乡的一个土族村庄),庙里问来的人(来求娘娘看病、解惑、占卜等事)也多。一般“捻弄”(指各种禳解活动,后文中有描述)的,都在晚上。
前几天,村上一个阿奶(老年女性)病着不成,儿子就庙里看来了,我们捻弄着看了,佛爷意思是要到阿奶家里去坐。
问:那阿奶得的是什么病啊?
答:阿奶上房顶头晒粮食时候摔下来了,可能腰摔折了,送着县上医院里治了十几天,大夫们说是下半身瘫痪,再站不起来了。儿女们心不肯(不忍心),问佛爷来了,佛爷说是要到家里去坐(这个有点现场办公的意味)。我们四个阿爹、一个青苗头(村民选举产生的村庙、村务的协助管理人员)和司机(佛爷有自己的专车,是一辆皮卡车改造后加上了集装箱,佛爷出行也依赖现代交通工具,一般到了村口后下车,由四个人抬着轿子进村)就去了。半路里遇上尕丫头的一茬事情,耽误了些时间,不过佛爷有卡码(把握、掌握事态的发展)的,关系不大。
问:阿奶的身体能恢复吗?
答:佛爷当时就看着了,肯定是瘫痪不了。阿奶身上带了一件亡人的东西,还给就成。禳解不了的事儿,佛爷会直接说,我们也就不捻弄。
问:亡人就是死去的人吗,他的东西要怎们还呢?
答:阿奶自己知道了,她的大丫头前几年跳到水库里自杀了,阿奶把丫头的一条腰带没烧给,自己用了。大概丫头想要自己的腰带了,亡人和我们不一样,不高兴了就会“抓只”人(给人带来麻烦或伤害)。佛爷说了,把丫头的腰带烧给,房背后埋一个黑碗,碗里再埋给阿奶身上的一点贵重东西。当时阿奶的小丫头取了阿奶的一只金耳环,一起埋了。佛爷说一个星期以后看。①
在田野调查中,流传着很多不能以理性的观点来证实的,只能用“奇迹”一词来诠释的事件,正如任何一种宗教体系中承认的“神迹”一样,在信仰者看来,它们是真实存在的。“神迹”乃是宗教赋予神的基本神性,对于神能够创造神迹的事件的信仰,是一切宗教的特征。“信仰”也即宗教的观念,是一切宗教情感和宗教体验得以产生的基础,“神”必定拥有着超人的力量、智慧与权能,能够完成人类所不能完成的事情,也因此而成为人们信仰和膜拜的原因。“神”将自己的能力与智慧在各类神奇的事件中的展现就形成“神迹”。“神迹”的特征在于其“令人感到惊奇的、特殊的反常性”,能够用自然科学的知识或者当地人的知识体系话语所说明和解释的事件,不是“神迹”,也就是说其特征在于对自然法则的破坏与颠覆,就如伏修斯所言:“……所以由于神的命令,处女能够生子,瞎子能够看见,死人能够复活,这当然是违反自然界所谓必然的秩序,违反自然界的必然性的。”[3]而在民间,“神迹”也的确在人们口耳相传的记忆中真实地出现过。人之所以崇拜神、信仰神,在于相信通过自己一系列表达信仰和崇拜的行为、仪式,可以得到神的喜悦与恩赐,尤其是可以满足人力无法完成的要求和愿望。神也正是通过超自然力量所创造的神迹,表现他对人类生活的干预,回应人的祈求,表现神的仁慈,从而,使人折服与信仰。阿奶的儿子初中文化程度,接受过现代义务教育,农闲时间到县城、省城打工,也算是村子里见过一些世面的年轻人。他不拒与外界交往,也乐于和我们交谈交流,他直言自从靠上佛爷以后,家里的事情都顺利了许多,他隔三差五到庙里去问一下佛爷,还从庙里请了一块直径约5 厘米的铜镜悬挂于家中堂屋的中梁之上,正对着院子中“中宫”方位,据言,这镜子便是佛爷的眼睛,时刻注视着家中的情况。在他们的影响之下,他的亲戚朋友们对这位娘娘佛爷的兴趣也与日俱增。阿奶的一个外甥女,刚离婚不久,由于前夫暴戾,导致女子身体和精神都饱受摧残,离婚之后情绪一直不好,阿奶便让儿子也到庙里去问一下佛爷。这也是此次田野调查中直接观察到的一次求神仪式:
晚上7 时以后,我随着这对表姐弟一起来到娘娘庙,女人们不被允许进入大殿,这位表姐便在院子里正对着大殿远远地跪下来。院门外贴有告示牌,月经期女子,一月内进过医院、暗房(产妇房间)、服丧期间的男女均不能进入村庙。庙中大殿正在重建,三架七檩的新殿气势恢宏,属于庙宇修建中最高的一种规格,殿顶用了鎏金瓦覆盖,造价必然不菲,一个只有200多人的小村庄,村庙如此气派者在互助地区并不多见。庙宇的规模彰显着其经济上不凡的实力,据介绍,所有的经费都是佛爷自己挣来的,村民们并没有被摊派。
佛爷的神轿暂时被安置在偏殿之中,殿内油灯、电灯都通宵不灭。两位阿爹在偏殿门前,一前一后站立,将一根缠有哈达的木棒扛在了肩上,事后我得知哪根木棒是一根轿杆,它同轿子一样具有同等的象征性意义,它的出现就代表着佛爷的亲临。站在前面的阿爹口中念念有词,不一会儿两人开始身形一致地做出一前一后的摆动,动作幅度不大。表弟站在阿爹身旁问着什么,阿爹们根据表弟的陈述向佛爷发问。因为佛爷并不开口说话,神意通过阿爹身形的移动来传达,身体前倾表示“是”,后仰则表示“否”,在大约20 分钟的询问之后,仪式结束。神意最终归结为:该女子虽然已经离婚,但是前夫未完全死心,还会有纠缠。如果想彻底摆脱,则要在一周以后的夜晚,带来前夫的一件贴身衣物、一个黑碗、一张红纸来进行进一步禳解和安置。一周后的仪式,两位阿爹一如前次一样扛了轿杆,指示表弟在红纸上粗略画了三个人形,两女一男形象,阿爹们扛着轿杆从纸上跨过,之后和黑碗以及表姐前夫的衣服一起,被放入大殿旁边的一个小房间。里面已经放置了很多黑碗等物。仪式结束后,阿爹告诉这位表姐,佛爷已经将她和前夫断开了,以后不会再有麻烦事出现。②
这个仪式中,巫术与“禁忌”都有着明显的体现,由于人们对所信仰的对象在观念中有着意识,在情感中有着体验,就产生了惊奇、恐惧、依赖、畏怖等情绪。而人内在的观念,以及对某种对象的体验与情绪,必然要通过外在的行为表现出来,在与神圣对象的交际中,人们对自己言语、动作的约束和限制,即是“禁忌”。通过对自己言行的控制,引发神的怜爱,或者至少避免由于对神的亵渎和冒犯而引起神的不悦。被允许进入村庙的人,必定是“洁净”的,月经期的女子,到过医院和“暗房”的人,由于在人们通常的意识中与污秽物相关联,因此必须自觉地回避这个时期或状态下出现在神的面前,否则被视为是对神圣场所的污染,是对神灵的冲撞冒犯。“献祭与祈祷”也在仪式中被使用,这是信仰者与信仰对象,也即人与神之间交际和沟通的又一重要方式,同样表达了人们对神的情感与态度。“神”究其本质而言,乃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异己力量的人格化,必然引发人们内心中依赖、敬畏等的情感,将此种情感表达于行为中,可以是限制自身的言行,也可以是奉献礼品换取神的帮助、阿谀奉承求得神的慈悲关照、卑躬屈膝获得神的垂怜等等,就是“献祭”与“祈祷”。
在实物的献祭中,哈达和油灯是最为常见的,也可以直接用现金作为供养,但是食物几乎不再出现。这或者与人们日益提高的生活水平有关,献祭品以珍贵稀有为佳,现代社会中温饱早已不是人们的问题,连人都不在稀罕的东西,用来供神在人们的观念中是对神的不敬。而实际上,神作为抽象的存在,他们享用供品也是抽象的,食物的供奉在仪式结束后通常都被仪式的举行、参与者享用,这些在庙中服侍佛爷的庙管、阿爹们大多年事已高,早已不再拘泥于口腹之欲的满足,所以,以现金或者购买庙中提供的哈达等物品,或者是人意的表达,而并非神意的选择?人与神交际的本质,无外乎是人与人交际的投射与写照,人对神的塑造,对神性的建构在此彰显无余。女子在阿爹的建议下,“请”(从阿爹处购买)了一条哈达,搭在了大殿之中,他解释说在人死后,献给佛爷的哈达会变成一条绳,在亡人的魂魄前往转生途中经过大河或者深渊时,这条绳子可以提供救助。
“阿爹”就是沟通人神的中介人员,但他们的身份并非道士或者道教在家的修行人员,从未接受过相关的培养与训练,也并不知晓“娘娘”作为道教神祇的身份。他们熟谙各类禳解的仪式,尽管并不知道为什么用到黑碗、黑盆,只说是佛爷的意思,是一种禳解的办法。能用于安置的物品还有很多,比如犁铧、车轮、磨盘、狗头、鸡头、女人的头发、兽骨等等,当我问及具体在什么情况下使用什么物品禳解时,阿爹思考良久后表示并没有规律可循。这也正是民间信仰中巫术与习俗的特征:“传统宗教包括一大批非常具体地定义的,仅仅是松散地组织起来的宗教实体,零乱地汇集了一些繁琐的仪式和泛灵论的生动形象,它们使自己能够以独立的、部分的和即时的方式卷入任何一种实际事件中去。……它们在意义问题出现时——每次死亡、每次歉收、每次自然与社会的不幸事件——从神话与巫术的武器库蛊选择这一种或者那一种武器依据适当的象征,寻找机会解决它们。……正如传统宗教对基本的精神命题所采用的解决方法是各自分离的、没有规律的,它们的特征形式也是分离的,没有规律的。”[4]
极具藏文化特色的物品——哈达,和佛教常见的器物——酥油灯在村庙中的出现,在当地人心目中并无突兀的感觉,在他们看来,哈达以及油灯本来就是敬献给佛爷最贵重的礼物。村庙中备有黑碗、黑盆等用于禳解仪式的器物并不奇怪,但是供佛的油灯和哈达也常备着以供人们选购,实际上是民间宗教体系中发生的一个变化:一是藏文化和佛教文化的再一次浸漶,但是并不是生硬的照搬,而是对其意义的改造性接受,哈达在藏文化语境中并没有对灵魂的牵引的“绳”的象征;二是商业化的逐步延伸,用于出售的哈达和油灯,无疑会为村庙带来经济收益,这种情况在各个佛教寺院中已经屡见不鲜,或许在以后,村庙中也会设立类似“法物流通处”的设施,出售香烛、黄表纸等祭祀用品。这样的分析对阿爹们来说是多余的,因为在他们看来,藏传佛教原本就是他们最正宗的信仰,村庙中供奉的也是正儿八经的“佛爷”,娘娘的出身,即便不便于过多地讨论,但是还是有一位阿爹向笔者解释了为什么说“娘娘”是真正的“佛”:
我们庙里的“娘娘”,又称为“勒木桑”,是从西藏来的佛爷,西藏有一座寺院就是专门供“勒木”的,前年从西藏来了一位活佛,专门寻访到我们庙里,拜了佛爷。“勒木”佛爷原先姊妹有五个,两个被水冲走了,现在剩下三个。我们庙里的佛爷最早是我们祖上一个小伙子到隔壁村上当长工,给人家犁地的时候从地里翻出来的。当时佛爷给他说了话,小伙子就把佛爷(的塑像)背回来供在庙里了,后来隔壁村子说是佛爷从他们的耕地里出来的,应该他们供,还抢过、偷过佛爷。我们害怕佛爷走了,用铁绳锁过,再往后我们两家商量成了,他们村是佛爷的娘家,但是我们村庙里供着,他们可以到庙里看佛爷,问事情。③
具体是西藏的什么寺院,是一位什么活佛来拜了“佛爷”,佛爷是如何从西藏来到当地的,以及被水冲走的两位的下落等阿爹语焉不详,只说自己记不清楚了,经书里也没有记载。那么阿爹的意思,是否言指“勒木”即为藏传佛教中的护法女神吉祥天女——拉姆呢?在以往的研究中,有过不明就里的研究者将二者混为一谈,误认为骡子天王拉姆亦称为“勒木”,因此不排除学者们不恰当的言论被村民听到,并作为了自己村庙中供奉的佛爷来自西藏的证据的可能性。因为土族人在广义上是藏传佛教信仰者,西藏是藏传佛教的圣地,来自圣地的佛爷,身份理所当然要比本地的或者外地的佛爷尊贵一些。无论是以讹传讹,还是当地人的有意攀附,这个说法的纰漏是显而易见的,拉姆作为藏传佛教的著名护法神,其形象最突出的特征便是骑在一头骡子之上,而且呈忿怒像,在藏传佛教寺院中都有供奉,土族人家中也有供奉其唐卡的。村庙中供奉的娘娘“勒木”是汉族女子的形象,而且乘轿出行,民间也多有三霄娘娘之说法,可见二者并不是同一尊佛或者神仙。至于活佛来拜娘娘之说,在理论上根本不可能,佛教僧人皈依佛、法、僧三宝,不拜任何世间神祇,对着一顶轿子中的女神朝拜,被视为僧人对信仰的背叛。
三、神祇与教义的分离:多元文化的整合
道教在互助土族地区的存在是尴尬的,因为从未有土族人宣称道教是他们的信仰。而我们考察一种宗教在某一地区的流传,主要是观察当地是否有该宗教的活动场所和职业修行人员的存在。在互助土族地区,藏传佛教信仰在现实生活和学术研究的领域,都颇受关注,身着褐赭色僧衣的阿卡,与以佑宁寺为代表的藏传佛教寺院无不彰显着藏传佛教在互助地区强大影响与实力。但是道教,则从未在这一区域形成过作为一种制度化宗教应当具有的影响与表现。制度化宗教都具有相当严整的体系,由宗教观念、宗教情感、宗教行为和宗教的组织制度四个基本要素构成。宗教观念泛指对神道的信仰,是对神、神性物和神圣力量的观念,相信这些力量能够对人的生活产生影响,具有着人类所不具有的力量,是宗教中最核心的要素;宗教的情感是对宗教观念的体验而产生的依赖、敬畏、恐惧等的情感;人们的观念和情感通过一定的行为表现出来,形成祈祷、献祭、巫术、禁忌等宗教仪式与行为;而宗教组织则是对以上各个要素的整合,是对宗教信徒的组织化、宗教观念的信条化、宗教体验和理想境界的目标化以及宗教行为的规范化与利益化。道教作为一种制度化的宗教,本身具有着以上四要素,但在互助地区的传播中,却没有将这些要素体现出来。
但是,互助土族地区对道教神祇的信仰却是不争的事实。女神“娘娘”最初的职能也许只与生殖、繁衍相关,但是在她走入各地的村庙之中成为方神之后,她的神力扩展到了与当地人们生活相关的方方面面。而在祭祀“娘娘”的乡村集体仪式之中,“喜神”“东岳大帝”“五道将军”等道教神祇也有专门的仪式和祭祀环节,并不似其他诸神鬼只是作为村庙中延请的客人,享受宴会的集体款待。因为,“喜神”“五道建军”“东岳大帝”等神仙的职能,直接关乎着人们的喜乐与繁衍,从而受到特别的对待。同时,“娘娘”等在土族地区又有着另一个称呼——“佛爷”,他们神轿的装藏也必须由藏传佛教的高僧来实施,高僧人物甚至可以号令、斥责“娘娘”佛爷,在村庄中举行旨在娱乐诸神的“梆梆会”时,还要注意对佛教护法神箭的回避。由此可见,道教神祇在互助土族地区的地位,与他们在道教系统中的地位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他们俨然成了佛教诸尊的下属以及臣僚。他们作为方神委身于村庙之中接受人们的供养,他们的职能行使与发挥均受到佛教的制约与限制,他们神圣力量的来源也不再是自身的能量,而是源于佛教经卷与高僧的加持。尽管“娘娘”佛爷至今依然在土族乡村社会中存在有巨大的影响,但是其间藏传佛教的影响已经远远超过了道教本身的意味。而且,对于道教神祇的祭祀,无论是偶发性的危机仪式,还是集体性岁时祭祀,主持这类仪式的教职人员,不是道士,而是当地民间宗教的职业人员——法师,他们自称为“神教”的神门弟子。法师们主持着祭祀道教神祇的仪式,在一些舞蹈环节,他们会换上道袍,并在外面加上一件花布的坎肩,无疑是对道教传统以及远古时期“在女曰巫”的自然宗教的追溯,但现在的仪式却以“神教”的方式进行,以及充满着浓烈的藏传佛教气息。道教的仪轨,没有被执行,道教的核心信仰也不为人们所知晓,当地并不存在以修炼成仙为目标的修行者。因此,道教神祇与他们所属宗教最本质的要素——教义发生分离,依托于当地民间信仰而存在,并深受藏传佛教的影响与制约,就是道教在互助土族地区流传的方式与特征。
这样一种特征的形成,是文化的整合与重构,也即不同民族和文化体系的交流与融合,体现着当地居民的主观性选择。“人们需要的不是高级的文明产品,而是某种适合于他们的情况和最易找到的东西。”[5]道教是伴随着明清时期大规模的汉族移民的迁入而流传到土族地区的,道教文化在其形成和发展的初期,也主要只是汉民族的信仰。当道教传播到土族地区,当地的文化形态与外来的宗教体系都面临着文化间的交流与碰撞,以及由此引发的深刻变革。
(一)道教本身的改变
在明清之前,汉族人口几乎不见于河湟地区,元朝时这里定居的农户不多,基本都是各个从事游牧的少数民族。直到明朝初年,明军大兵进入河湟地带,接着又是大批汉族移民的迁入,这些人大多数是祖籍南京一带的征戍军士和他们的家属。这些人员的到来,给河湟当地藏、土、回、蒙古等民族的人们,带来了新的文化、观念的冲击,也给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注入了新鲜的血液。至清朝乾隆十一年时,在青海农牧区71万人口中,汉族占到了22 万多,约是当地人口总数的31%。乾隆以后,汉族人口仍然源源不断地进入青海地区,到咸丰、同治年间时,汉族人口已经达到了46 万人以上,占当地人口总数的40%[6]。随着汉族人口的大量迁入,汉文化也随之进入河湟地区。文化的交流从来都是双向的,由于大规模的人口迁徙,汉族人口数量众多,随他们一起到来的汉文化也表现出了很强的独立性和综合性。因此,汉文化在与当地的本土文化的交融对抗中,不仅被土族文化所影响,更多的也是对当地文化的整合和改造,对土族民间信仰等文化影响的力度很大。
在各个民族民间信仰之间的交流与吸纳过程中,都倾向于将对方文化体系中精华的,也是最具生命力的部分吸收到自己的信仰体系中来,并人为地制造理论依据,说明这就是本土的原生文化形式,同时,也积极调试自身信仰中不再适合社会发展的要素,加以改造或者剔除。总之,就是多途径寻找创造灵感,互相效仿、吸收,营造一个新的信仰世界,这是不同质文化接触碰撞后,文化发展的主要方式。文化体系的变迁与重构,反映着一个民族社会的发展程度和生活状态。具体到宗教信仰层面而言,主要是土族民间信仰对道教的吸收与改造。众所周知,道教是在中国本土环境中,以西南等地少数民族的民间信仰、中土汉族的巫术等为基础,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一种宗教形式,其在发展历程中,由于有与佛教等人文宗教相对抗的需要,又不断借鉴了佛教文化的诸多理论而完成了自身的理论化、制度化发展。道教在元、明之际就已经传入了土族地区。《西镇志》有载,明宣德十年(公元1435 年),李英在西宁建广福观,设道纪司,在《西宁府志》等文献资料中也记载了土族地区有玉皇阁。宫、观、阁是典型的道教场所,也是道教在当地存在的标志性建筑。道教在传入土族地区以后,发展速度很快,而且其发展的特点是佛道合璧,道中有佛、佛中有道,甚至还将一些萨满教的内容也吸收了进来。
道教能够被土族地区接纳,并在土族地区以这样的方式流传,是有理论依据和历史根源的。因为道教本身就是巫术衍化发展的自然结果,道教的理论、仪式当中巫术性、咒术性色彩非常浓厚。有研究者指出,道教就是理论化、系统化了的巫教,“不过,道教产生后,为散漫无章的民间巫教提供了一个上层框架,许多民间宗教的神灵被组织进道教的神谱中,道教在民间巫教的影响下也变得日趋复杂。当然,这不是说道教取代了民间巫教,民间巫教仍然是与道教并行的发展,事实上是将道教化为自己的一个组成部分”。[7]而任何一种能够流传下来的文化和宗教体系,在其向外传播的过程中,无一例外地都会选择理论化、本土化的形式。理论化是发展自身,是与其他文化体系抗衡的结果。本土化则会抵消在传播过程中遇到的当地文化的对抗,从而,在不同地区结合当地文化因素,形成各地不同的传播形式与存在方式。道教在土族地区,就是不断完善自身的理论体系,又广泛与当地原生宗教相融合的发展,直到目前,在土族地区,一些宗教活动中,道教道士、阴阳先生和“勃”联手,为人们祈福禳灾共同行事的场景屡见不鲜。
(二)本土宗教的多样性基础
土族的宗教信仰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在现代社会中,都是一个复杂的体系,这与其民族与文化形成过程中多种民族成分的融合有关。研究表明,土族文化的形成是一个不断对其他文化多方位吸收和深层次整合的过程。土族在族源上是多元的,成分十分复杂,学界主要有吐谷浑说、蒙古人与霍尔人融合说、阴山白鞑靼说、突厥说以及多元融合说,目前较为流行的是吐谷浑说和蒙古人说。我们暂且抛开各种不同的见解,不做孰是孰非的判断,但是土族成分的复杂性毋庸置疑,在其形成过程中的确融合了蒙古、藏、吐谷浑、突厥等民族的成分,这样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和多样化的内部构成,也造就了土族文化的多元性与丰富性。
在土族特殊的宗教文化体系之中,构成其主体民族的蒙古和吐谷浑,都从遥远的北方草原迁徙至青海高原,他们都保留了浓郁的萨满教信仰遗存。而最早生活在青海高原的古羌人,也发展出了庞杂的原始宗教体系。在土族先民迁徙、发展、重组的历史过程中,不断有新的民族群体和民族文化加入进来,始终伴随着强烈的构成成分重组和社会文化变迁。民族迁徙致使生活环境发生改变,与之相处的人群也不断变化,接触到的文化类型也越来越多样。在这一系列的变迁之中,原先文化的传统、文化的一致性以及群体的一体化都被打破。人们不断在新的自然地理环境和社会文化背景之中,寻求新的社会形势、价值观念和适应途径。宗教信仰领域也发生着巨大的变迁,原有的信仰内容,有的被剔除、有的被保留、有的则被其他文化整合改造,改头换面出现。所有的改造与变迁,都取决于人们的选择与需求,表现了人对环境的主观能动的适应。土族先民在走到青海高原后,开始在这里繁衍生息,与周围群体交往、交流,其文化也经历了一个连续发展的历程,他们长途跋涉而来,继承和保留了蒙古族原有的萨满教文化,并以此为基础,不断吸收和融合了新的民间信仰成分,最终整合出了自己新的民间信仰形态。在这个新的体系中,他们原有的原始信仰内容,与当地的自然崇拜内容并不冲突,而佛教文化也因为早在蒙古高原的蒙古汗国时期就已经开始流传,而很容易与当地的佛教文化达到一致和认同。藏传佛教也在青海地区以后的历史发展中,成为宗教领域不容忽视的主导力量,对青海地区历史文化、政治经济等方面发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藏传佛教的影响
元朝时,藏传佛教萨迦派得到元王朝的推崇,发展迅速,势力大盛,在青海地区也广泛地传播。《土观宗派源流》中记载了“最早宏传者萨迦派”。元代时在互助地区修建过最早的萨迦派寺院,就是以后郭隆寺也即现代佑宁寺的前身。当时居住于互助地区的土族先民,已经大多信奉了藏传佛教。明王朝在土族地区的施政,一方面建立了一套世袭的土司制度,另一方面继承和发展了元朝的宗教政策,对宗教上层领袖加以册封,通过他们来实现对民族地区的统治。但与元朝不同的是,明王朝一改元代独尊萨迦一派的做法,而对各个教派都平等地加以封赏。这样,既继承了元朝“僧徒化导”的策略,也防止了个别教派专权坐大,做到了各个教派之间的制衡。在这段时间,藏传佛教宁玛派、噶举派等也得到了在青海传播的机会。明朝初年,在青海乐都的瞿昙寺因为其主持三罗喇嘛归附明朝,收到了朱元璋亲赐的匾额,三罗喇嘛也出任西宁僧纲司的“都纲”一职,管理西宁卫各处喇嘛教事务。公元15世纪初,藏传佛教格鲁派的势力逐渐进入青海地区。互助、民和等土族地区自明代以来,广建寺院,寺院数目众多。据记载,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大师的大弟子释迦也是在明永乐和宣德年间,曾两次在进京觐见皇帝的途中路过青海,他在青海大力弘扬格鲁派教义,并在民和地区马营等地主持修建了著名的灵藏寺和弘化寺。以后在互助地区修建了甘禅寺,这些都是土族地区最早的格鲁派寺院。明朝万历三十二年(公元1604年),在互助地方兴建了郭隆寺,成为该地区显教讲院之发端,以后经过不断发展扩建,终成“河湟诸寺之母”,过去互助、大通、乐都一带的藏传佛教寺院都是郭隆寺的属寺。格鲁派的发展势头日渐迅猛,土族地区的黄教寺院不断增多,出现了“番僧寺族星罗棋布”的局面。到了清朝时期,《宗教流派镜史》中有“昔时安多境内虽有少数萨迦及噶举教派,现已完全转成格鲁一派矣”之语,足见当日格鲁派的兴盛程度。乾隆年间,格鲁派在土族地区的发展达到了鼎盛,清王朝在土族地区的黄教寺院中先后封授了七个呼图克图,四个堪布,格鲁派也几乎成为当地居民的主要信仰。
总之,土族的宗教文化体系,是在各种文化不断相互吸收、融合的基础上形成的,是一个多元的文化系统。但是,这种多元并非是各种文化的简单拼凑,而是一个文化重构的过程。在这个重构的过程中,尽管“土人的风俗受它的汉人邻居和近亲西藏人的影响,但还保持着它的原形”。[8]土族有着自身的文化体系,宗教亦是一样,当道教信仰流传到互助地区,除了道教本身的本土化,土族地区的文化也对它进行了整合,“文化作为有机体,不仅表现于它自己内部各因素之间是和谐的、整合的,而且要求外来因素融进这个有机体,从属于自己的主导观念,或者说,它正是依据自己的主导观念去选择外来因素,吸收某一些,排斥另一些,改造其他一些,以期维系自己的生存”。[9]游牧生活向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变,迫使人们产生了对与农业相关的神灵的依赖与崇拜,而人们功利性的信仰则导致对宗教的选择,往往只注重神祇的功能,而并不关注教义的普及。
注释:
①③访谈对象:东某,65岁,土族,D村村庙管理人员,访谈时间:2019年6月。
②仪式地点:互助D镇D村村庙;仪式参与人:乔某,女,土族,38岁,某村村民;伊某,男,32岁,土族,乔某的表弟,某村村民;仪式时间:2019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