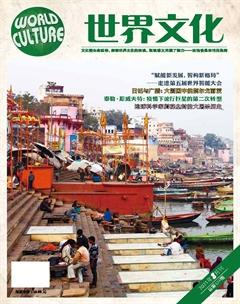女性的沙漠和沙漠中的女性
李永红
玛丽·奥斯汀(Mary Austin,1868—1934)是美国20世纪初的著名女作家。继1903年发表成名作《少雨的土地》后,她又于1909年发表了广为人知的短篇小说集《无界之地》。尽管“生态女性主义”是1970年代才出现的学术概念,但作为美国环保运动先驱和旗帜鲜明的女性主义者,奥斯汀的作品已展现出对生态女性主义基本理念的思考与探索。
女性的沙漠
奥斯汀在《无界之地》中对沙漠进行了一番细致入微的描写,将之塑造成与传统认识大相径庭的女性形象——神秘而强大的斯芬克斯,寓意深远。
在20世纪初的美國西部文学中,把西部自然塑造成女性的也并不鲜见。在男性作者笔下,自然的形象大致可归纳为三种原型:母亲、处女和情妇。例如,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在其影响深远的著作《美国历史上的边疆》中将西部喻为一位“慷慨无私的母亲”,用其物质财富滋养着她的儿子。而在更多人眼里,西部未开垦的土地更像头戴花冠、面罩白纱的纯洁处女,等待男性拓荒者去揭开她神秘的面纱。著名的美国西部研究学者亨利·纳什·史密斯就将其专著标题设为《处女地:作为象征和神话的美国西部》。而正如美国著名环境史学者卡洛琳·麦茜特在其《自然之死:妇女、生态和科学革命》中所分析的,把西部视为“情妇”,是因为人们在西进过程中遭遇了恶劣环境和气候带来的危险、疾病和死亡,将西部的狂野、原始和未开化特质等同于与文明对立的无序和混乱,需要通过粗暴征服和驯化,来维护文明世界的秩序。
女性生态主义者Kolodny指出,不管将自然作为母亲、处女还是情妇,都代表了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文化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解读,其共同点是将自然置于“他者”的从属地位,要么被动地等待男性的温柔入侵或粗暴征服,要么奉上土地和资源,无条件地满足人类无止境的索取。然而,奥斯汀在她的《无界之地》中颠覆了男性视角下的自然形象。

显然,奥斯汀笔下的沙漠不是纯洁而柔弱的“处女”,也不是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情妇”。虽然她有着性感迷人的外形——黄褐色的皮肤与秀发、诱人的曲线,但她的气质更接近神秘莫测的斯芬克斯,让男人有顶礼膜拜的冲动,却生不出非分之想。她不拒绝甚至可以说是诱惑人们前来探险、淘金、寻宝,但对于带着野心妄图征服她的白人男性,她却是“最危险的”。她会“像猫戏老鼠一般”把他们掌控在自己的股掌之间,直至他们灰心丧气、大败而归,如《威尔斯先生的回归》中的威尔斯一样狼狈逃离沙漠,或者“被沙漠吸干了,像葫芦一样悬挂在藤上”,如故事《米涅塔的不祥之物》里自私贪婪的男人们。而她,却一如既往地神秘、独立、充满魅力,没有什么能撼动她分毫。
奥斯汀笔下的沙漠也不是无私奉献的母亲,她没有取之不竭的物质宝库。相反,她能提供的生存资源非常有限,只有那些懂得如何获取并珍惜这些资源的生命体才有机会存活下来。她更不是从属者,而是主宰者。在沙漠里,“不是法律,而是土地本身设置了界限”。在这片土地上,生命呈现出其最本真的状态,人并不比动物更高贵,白人也不比印第安人享有更多特权,在面对沙暴、炎热和干渴等考验时,为了生存,生命个体本能地彼此靠拢,形成平等而和谐的生命联结。因此,一个女人可以和一个男人并肩对抗沙暴,从而认识到女人并非天生的弱者;一个来自“文明世界”的白人男子可以抛弃种族偏见,倾心仰慕一个印第安女子;一个孤独的牧羊人可以和一棵树、一只羚羊心意相通,结成亲密的心灵伙伴。在这无界之地,沙漠的生存规则打破了文明世界的种种人为秩序和界限,男人和女人、白人与印第安人、人和自然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和谐状态。
在奥斯汀笔下,沙漠不是背景,甚至不是配角,而是绝对的主角。奥斯汀是将环境作为角色而非背景引入小说创作的先驱。在其发表于1932年的著名文章《区域主义和美国小说》中,奥斯汀明确指出环境在人们生活和艺术创作中的核心地位,认为“环境应作为独立的角色参与故事的建构,引发故事情节的发生与发展”。她不仅在故事《大地》中给沙漠做了一个细致入微的画像,将其塑造得有血有肉有灵魂,在其他的故事中,沙漠也是人物命运的控制者或引导者。例如在《米涅塔的不祥之物》里,沙漠是一只无形的大手,把贪婪的人们引上毁灭之路。而对“行走中的女人”而言,沙漠是为她治疗心灵创伤,帮助她摆脱束缚、获得新生的原始力量。

奥斯汀通过人格化的手法,将沙漠女性化,从而在自然和女性之间建立起亲密联系;另一方面,奥斯汀笔下的女性沙漠又呈现出强大的主体意识,消解了男性中心主义意识形态下自然作为从属性“他者”的形象。
沙漠中的女性
印第安女子:沙漠中的真人性
从沙漠素描像可以看出,无论是外貌还是气质,奥斯汀笔下的沙漠与印第安女子有着高度的相似性,例如,她们大多都有丰满的乳房与臀部、健康的肤色、褐色的秀发、诱人的曲线、饱满的嘴唇,甚至拥有“狂野之力”。20世纪初的美国,印第安女子是在种族与性别双重歧视下卑微的存在,但奥斯汀却从她们身上看到了令人叹服的沙漠特质——力量、激情、耐性、率真和无穷的创造力,以及勇敢、善良、无私等高贵品质,因此她勇敢地为她们正名,称赞她们为“真正的女人”。
这些印第安女子与她们生存的沙漠之间存在天然的纽带联结,沙漠既是她们的家园也是庇护所,她们熟悉这片土地上的生存规则,因此有远超于外来者的生存能力。在奥斯汀笔下,她们是善良和爱的化身,常常搭救被困于沙漠中的白人男子。无论是作为柔情似水的女人,还是坚韧强大的母亲,她们为所爱之人的无私付出都令人动容。
《阿瓜迪奥斯》中的卡塔梅内达就是一名甘愿为爱献身的印第安少女。这个温柔善良的姑娘在迁徙途中与白人探矿员相遇并相爱了,在族人继续前行时,她选择留在爱人身边,靠爱人的定期补给和捕猎幸福地生活着。可是好景不长,一天他们的供给被偷了,随后探矿员染上了痢疾,他生病期间沙暴来了。沙暴覆盖了所有的路径,给养没法在预定时间送达,他们不得不带上仅有的食物和水出发寻找下一个水源。风暴一直在持续,四周都是茫茫白沙,卡塔梅内达带着处于半昏迷状态的爱人跋涉了三天,一路上把所有的食物和水都给了爱人,凭着在沙漠生存的本能,她把爱人安全带到了黑山脚下的泉水边,而她自己却力竭而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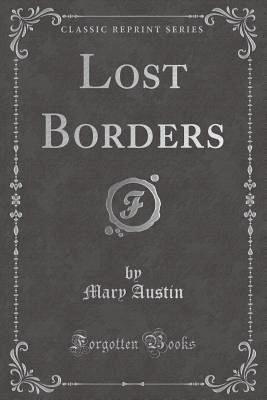
卡塔梅内达为所爱的人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但在爱人的心中获得了永生。和她相比,肖肖尼族女子塔瓦的付出最终收获的只是爱人的背弃和伤害。故事《开垦地》也以白人男子加文和印第安少女塔瓦的爱情开篇:加文在沙漠中探险,迷路后昏迷,被塔瓦的父亲搭救并获得了塔瓦的爱情。痴情的塔瓦爱得热烈而投入,然而康复后的加文却选择返回白人定居的开垦地。无法舍弃所爱的人,塔瓦选择离开族人和沙漠追随加文,一路上无微不至地照顾他。然而,一旦割断了与沙漠的天然联系,塔瓦就只能茫然无措地独自面对这个并不友善的文明世界,不可避免地沦为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的双重受害者,她不仅完全失去了所爱的男人,更失去了自身的尊严。为了生存,她嫁给了当地一个派尤特人,逐渐从小巧、苗条的少女变成肥胖的中年妇女。她为爱离开了能够庇护她的现实中的沙漠,却被放逐到了更为残酷的社会沙漠。她来到了肥沃的开垦地,却只能作为低等的“他者”卑微地生活在文明社会的贫瘠之地。
和塔瓦一样经历了被所爱之人背弃伤痛的特沃兹却有着截然不同的结局。她凭借对孩子的爱,从自然中汲取力量,从而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特沃兹也是肖肖尼族的女子,在一次沙漠风暴中救了英国男子桑德斯,特沃兹对桑德斯悉心照顾,帮助得肺病的他恢复了健康,还用爱滋润了他孤独的心,两人有了可爱的女儿。康复后的桑德斯要回归“文明社会”。出于英国人的所谓道德感,他觉得自己必须对女儿负责,必须把她带回去接受文明教育,使她不至于成长为一个野蛮人,因此他狠心地将年幼的女儿从特沃兹身边夺走,丝毫不顾及这样做会带给一个母亲怎样的痛苦。然而,越接近文明世界,桑德斯的内心越纠结,因为他深知自己的家人不会轻易接受这个有一半印第安血统的孩子,孩子的存在也会影响到他的声名。正当桑德斯左右为难之际,特沃兹又一次“解救”了他。一贯柔顺的她赶到父女俩留宿的客栈,把孩子从桑德斯怀里抢了过来,坚定地对他宣告:“她是我的!”“是我的,不是你的!”然后带着女儿“高傲地转身朝沙漠走去”,将男人给的钱抖落了一地。
特沃兹能从男人带给她的伤痛中恢复过来,一方面,身为母亲的责任感就是最好的药剂,对孩子的爱让她坚强。就像奥斯汀的代表作《少雨的土地》中印第安手工艺术家赛亚维所宣称的,“男人一定需要一个女人,而女人有孩子就够了”。另一方面,她本能地更贴近自己生活的那片土地,沙漠就像庇护所,给她“原始的力量”,使她获得生活下去的自信和勇气。
白人女性:沙漠中的重生者
《无界之地》同样描写了一群白人女性,就像奥斯汀本人一样,她们大多是跟随丈夫或家人来到西部的。她们原本在文明礼教的束缚下,作为男性的附属品被禁锢在室内,家庭就是她们全部的世界。但当她们或被动或主动地接触到这片沙漠后,逐渐对外部世界和自我有了新的认知,这促使她们努力挣脱父权社会加诸她们的性别角色和责任,蜕变成充满活力、自立自强的女性。奥斯汀称赞这些女性有着“非常伟大而单纯的灵魂”,能够“让灵魂在荒野里发光”。通过她们的故事,奥斯汀旨在唤醒更多的“文明”女性们认识到自身潜藏的和沙漠一样强大的力量。
故事《威尔斯先生的回归》中的威尔斯太太就是一位被逼走出家门从而获得新生的女性。她曾是一个普通的家庭主妇,随丈夫来到沙漠,将丈夫当作家庭的顶梁柱。当威尔斯先生为了寻找沙漠矿藏花光了积蓄,抛下她和四个孩子离家时,她几乎被击垮。面对物质上的日渐贫困,她陷于精神上的迷茫、无助和绝望之中。在丈夫离家近一年后,她才彻底放弃坐等丈夫归来解救她的幻想,为了自己和孩子们的生存,她被迫走出家门去工作。逐渐地,通过自己的劳动使生活重新走上正轨: 居室装饰一新,院子里种上了玫瑰。她自身也发生着变化,“丰满了,强壮了,步伐充满了弹性”,全身散发着自信的魅力。丈夫离家的三年,威尔斯太太逐渐学会自立,感受着从未有过的独立和自由。
很显然,是女性化的沙漠引导了威尔斯太太,作为母亲的她通过与自然建立亲密联系从而找寻到自我,因为“自然从不会犯错,不会让抚养孩子的母亲没能力养活他们”。奥斯汀在作品中反复提到“原始的力量”,这种力量虽然是自然所独有,女性——尤其是作为母亲的女性——却可以通过与沙漠结盟而获得这种力量,从而冲破父权社会强加给她们的种种束缚,重新认识自我价值。
文明社会的女性在与荒野的亲密接触过程中逐渐发现自我、重塑自我——这一主题在故事《行走的女人》中得到强化。故事的主人公“行走的女人”是奥斯汀塑造的最成功的女性人物之一。虽然是白人女性,她的身上却有印第安女子的影子:独立、自信、享受自由、敢爱敢恨,甚至男人提到她时都会带着敬意。没有人知道她的真实姓名,她也没有固定的住所,人们只是看到她行走在沙漠中,向人们讲述她的见闻,其中包含着生命的智慧。在她看来,生命的本质是找到三样东西:工作、爱情、孩子。而她的感悟始自一次沙暴。在那次可怕的风暴中,她和牧羊人菲伦共同努力保住了羊群。在与菲伦一起对抗自然灾害的过程中,她感受到自己的力量和价值——是男性的伙伴而非附庸,“和男人一起工作……他说干,我就干。而且我做得很棒”。这种全新的感觉唤醒了她对自我的了解和尊重。这次经历也让她和菲伦彼此间从欣赏到爱慕,他们一起度过了整个夏天,那段“一起工作,一起爱”的美妙时光自然而然地带来了生活的第三个馈赠——孩子。可惜孩子没能长大,他俩也没能走到一起。在生命的最低谷,她意识到“除了自己的双脚没有可以帮她走出困境的东西了”,她就这样“走向开放、干净的自然,最后被自然的清明治愈”。她不再使用自己原有的名字,而像印第安人一样习惯于人们称呼自己“行走的女人”,因为她“已经彻底摆脱了所有的社会价值观念,知道什么才是对她最好的,并且在最好的到来时能够抓住它”。在奥斯汀看来,“最好的”不仅指和男人一样拥有工作、恋爱和生育的权利和机会,还指原始之力,它教会女主人公坦然地接受自己的欲望及其后果,哪怕没有婚姻的保障也不感到羞愧。
如果说威尔斯太太是被迫走出家门,走向更广阔的外部世界,从而重新认识自我,“行走的女人”则是主动地挑战社会传统给女性在工作机会、社会角色、婚姻家庭等方面设置的种种限制,勇敢地追求与男人一起工作的权利、获得自由真挚爱情的权利、做母亲的权利,这也是奥斯汀毕生的理想和追求。
自然是女性获得力量的源泉。奥斯汀用她的《无界之地》为女性的沙漠和生活在沙漠中的女性画像,不仅体现了沙漠和女性间亲密的联系,也颠覆了男性中心主义社会强加给自然和女性的从属性“他者”身份,唤醒人们对自然和女性价值的重新认识,表达作者对重构人与自然、两性间、种族间和谐、平等、公正关系的愿望和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