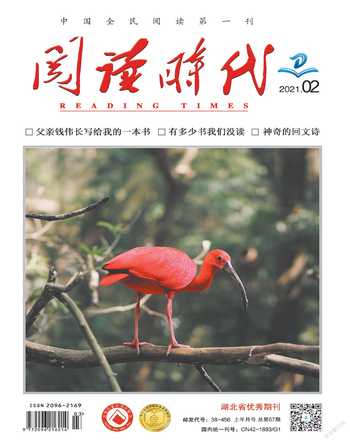入“水浒”世界 览“两宋”风华
虞云国
从《水浒》阅读到《水浒》随笔
我对古典文学与中国历史的兴趣,启蒙于《水浒传》与《三国演义》。没上小学前,每天晚饭后,与父亲守着收音机,津津有味地听苏州评话《水浒》或《三国》,成为儿时温馨的记忆。离家不远有家老虎灶,附设的茶座每天下午有说书艺人讲扬州评话“武十回”之类,多次蹭听过白书。上小学后,偶有小钱,放学没事也光顾过小人书摊,一套《水浒》连环画就是这样看完的。记得最后是《梁山泊英雄排座次》,显然是据简本画的。好几年后才读七十一回本《水浒传》,也许早知根底,感动的劲儿似乎赶不上看小人书。
1977年高考恢复,我有幸进入历史专业,对宋史感兴趣,才知道宋江起事轰轰烈烈,靠谱的史料十分有限。对历史上宋江是否投降,是否打过方腊,当年有一波争论,文章也多浏览过。大学阶段通读了《宋史》,大三写了第一篇宋史论文。而后留校,再读研究生,专业仍是宋史,却从未回到《水浒传》上来。
世纪之交,陆灏先生把《万象》杂志办得风生水起,也发过我几篇宋史随笔。有一次,他建议我以《金瓶梅》为主题,将小说与历史穿插着写点随笔。在专业学习中,我对陈寅恪的诗文证史法心折不已,颇有学步之想,一经说动,有点跃跃欲试。但《金瓶梅》仅取《水浒》片段“借尸还魂”,故事虽说宋代,作者却是明人,社会背景与语言名物也都植根于明代。倘把历史与小说串起来写,到底以宋为准,还是以明为准,抑或兼顾两个朝代,如此而为,效果碍难理想,行文势必缠夹,况且我对明史仅具常识,遂主张改从《水浒传》切入。蒙他首肯,在《万象》上开写《水浒》随笔,这才重回儿时留恋的《水浒传》,读写结合,断续至今。
我写《水浒》随笔的思路与原则
在文史学界,《水浒传》成果汗牛充栋。我虽酷嗜古典文学,毕竟缺乏中文专业训练,倘若再从文学史研究与文学鉴赏下笔,绝无优势可言。以史学考证而论,继余嘉锡《宋江三十六人考实》,施展的余地也已逼仄有限。我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是写什么与怎么写。
建炎南渡后,勾栏说书就讲开了宋江故事。孙立、杨志、鲁智深与武松等好汉已在“说话”里崭露头角,长篇话本《宣和遗事》也略具《水浒传》的雏形。宋元之际,龚圣与撰《宋江三十六人赞》,与今本《水浒传》三十六天罡星,角色出入仅数人而已。入元之后,杂剧也演梁山故事,现存《水浒》杂剧,大部分情节汇入了其后成型的长篇话本。元明之际,对其前《水浒传》话本有过一次汇总性整理(整理者是否施耐庵迄未定论),百回本主干已基本完型(一百二十回本征田虎、讨王庆部分迟至明代才补入)。今传百回本《水浒传》对宋代特定现象颇有“宋时”“故宋”等解释性交代,显然是元代说话人口吻,也是这次汇总整理时清理未尽的残骸遗蜕;反观元代的类似交代,百回本《水浒传》未见留痕,这也确证《水浒传》是宋元两代说话人的集体创作。
作为话本小说,创作当然有夸张失实处,尤其叙述战争情状与描写道术魔幻,但大部分叙事的场景与细节必以宋代社会的尘世光影与生活风俗为依据。一般说来,文学的读法定位《水浒传》乃是艺术虚构的可能性存在;而社会史的读法将其作为了解北宋晚期历史的社会史料,从而获得比官修《宋史》有关记载更具体的细节认识,就像恩格斯把《人间喜剧》当作“巴黎上流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来读那样。
但社会史读法仍有开拓的空间,那就是将《水浒传》里场景与细节的文学性描述作为宋代社会的形象史料。小说必有虚构,但所有虚构都跳不出作品形成时代的历史真实(举例来说,电脑行世前,艺术虚构绝无可能对其有逼真的描述)。这种阅读取径,能把文学叙事的小说文本转化为历史研究的社会史料,进而既对《水浒传》,也对宋代社会生活的理解,双双开辟全新的视角。
一旦打通历史学的读法与社会史的读法以及文学的读法,在《水浒传》再阅读中,经过细心梳理与认真发掘,就能发现两宋诸多的制度礼仪与风俗名物,在小说里都有不经意的细节遗存,足以将这些文学叙事转化为具体而微的社会史料,倘若再取其他文献对勘互证,不仅《水浒》研究可以另辟蹊径,随笔写作也能别开生面。我的《水浒》随笔,就是由这一思路催发的。
我写《水浒》随笔时,不敢高攀陈寅恪的诗文证史法,却不时以邓云乡说《红楼》作为范本。我的随笔写作,一是主要着眼于《水浒传》里的风俗名物;二是以《水浒传》叙事为切入点,与我搜罗所及的其他文献对照印证。之所以有意选择风俗名物,无非宋史学界虽有研究,但一是颇有空白而有待深入;二是其成果表述过于学术化,难为一般读者所喜闻乐见。作为宋史学者,仍有用武之地。我期盼每篇随笔,能为读者开启一扇窥望宋代社会的户牖;也奢望集腋成裘,形成规模效应,构筑起一条巡礼的长廊,在整体上对了解宋代社会有所帮助。
在取用史料与小说互证时,我定下一条总原则:以宋代记载为主料,兼及元代文献,而基本排斥明代史料(除非其追记或考证宋元史事)。在史料类别上,既有四部分类里属于史部的著作,也涉猎子部里笔记轶闻与类书谱录等典籍;还特别关注集部的文学性史料,包括诗歌(宋元诗词、元代散曲等)、小说(学界有定论的宋元话本)与戏曲(现存元杂剧与宋元南戏)。我欣喜发现,文学性史料对风俗名物的形象描述,无论数量,还是质量,往往是其他史料难以企及而无法取代的。
《水浒》寻宋之旅的甘苦与体悟
历时20年的《水浒》寻宋,我犹如身在旅途,频见杂花生树而欣然有得,遭逢柳暗花明而喜不自禁。
有评论说我的《水浒》随笔,“各种史料和掌故信手拈来,考证又不失趣味”。信手拈来真不敢当,都是孜孜矻矻博览穷搜,才收入囊中为我所用的。在素材积累中,我追求多多益善,来者不拒;讲究众体兼备,不拘一格。但下笔为文时,为选择最合用的原材料,挑剔近乎苛刻,再精心剪裁与刻意琢磨,尽可能打造成一件精致的工艺品。例如《太平歌》那篇,我在元杂剧里不仅查到对货郎唱词的细节叙述,而且找到卖糖果小贩的吟唱片段,便把臂入林与读者共享其顿挫婉转的悠扬与回肠荡气的酣畅,从而对燕青唱的“貨郎歌”能有感性的认知。
也有评论说,在我的所有著作里,《水浒寻宋》读起来最轻松。我也得坦承,实际写作却并不轻松。为了每篇随笔呈献一份相对完整的知识,我深感绝不比写一篇论文来得容易。先从《水浒传》里选定风俗名物,再去处理缤纷杂陈的囊中材料,而后将落英碎玉拼缀成绚烂可观的画卷,都得花一番匠心。以《一枝花》为例,先以蔡庆的绰号切入,叙述唐宋男子的簪花风俗与梁山好汉的相关例证;接着以男女戴花的审美需求引出花卉种植业,进入农业范围;然后延伸到鲜花销售,涉足商业流通;续说纸花绢花的制造营销,推及手工业;再说莳花业与制花业之间的竞争,最后回到元代男子仍然簪花上来,整篇文章一气呵成,读来不失轻快之感,但落笔之前谋篇布局却是苦心经营的。
《水浒寻宋》是我写得很用心的一本书。如何让随笔雅俗共赏,此中甘苦,冷暖自知。
为了读者读得有趣,首先必须写得有趣。在叙事议论上,我尽可能处理得轻快诙谐些。例如《铁扇子》那篇,证实了宋朝仍是团扇与折扇的并行时代,再回到宋清绰号“铁扇子”,下结语说:“既然是铁铸的,便不会是收放自如的折叠扇,而只能是形制固定的团扇。足下以为如何?”追加了一句诘问,文章便波俏而谐趣。在选材上,我也尽量追求幽默感。《钱塘潮》篇末引用俗词形容被狂潮打得精湿的观潮客:
头巾如洗,斗把衣裳去挤。下浦桥边,一似奈何池畔,裸体披头似鬼。入城里,烘好衣裳,犹问几时起水?
然后戏谑地指出,这些看客落水鬼似的烘好衣服,第一句仍问:潮汛什么时候来的?“对钱塘潮的痴狂,真可令人一噱。”想必读者披阅至此也会莞尔。
有些高头讲章式的史著往往行之无文,私心颇不以为然,有心尝试着把《水浒》随笔写得有点美感。恰到好处地点缀诗词曲中名篇佳句,行文油然而生水灵之感。《一枝花》讲鲜花销售,我引蒋捷《卖花人》词云:
担子挑春虽小,白白红红都好。卖过巷东家,巷西家。帘外一声声叫,帘里丫鬟入报。问道买梅花,买桃花?
其中有人物,有动作,有色彩,有对话,有场景,读者仿佛亲眼看见一幅城市风俗的水墨白描画。
《水浒寻宋》的改版与配图
十余年前,我的《水浒》随笔曾结集出版过。这次全面改版,一是增加了《客店》《打火》《气毬》《圆社》《戒石》《神算子》等多篇新作,还收入了有关《水浒传》的书评。二是改进旧版篇目统编的不足,将全书归为“读法篇”“地名篇”“市肆篇”“游艺篇”“器物篇”“风俗篇”“规制篇”与“人物篇”八类。“读法篇”作为总体性导读,以下六篇展开社会风俗百态,最后殿以李师师、高俅兩大名人与梁山人物的结局分析,多侧面地展现了宋代社会生活的历史长卷。三是订正旧版个别讹误同时,借助新的积累与研究对部分旧作颇有增补或改写。四是插图旧貌换新颜,力图超越一般的图文配。
既然是历史随笔,在打造图文本时,就应追求历史感与审美性的统一与融合。故除封面借用中国画大家戴敦邦先生惠允的“清风寨宋江看花灯”外,主要考虑取资于宋元绘画与明代版画:有美文阅读之余的美感享受,能印证随笔叙事,能补足文字表述不够清晰的细节。
寻觅最佳插图的过程,让我领略了“众里寻他千百度”的滋味。两宋度牒的实物照片久觅而不得,后在参观应县木塔时偶见陈列照里赫然有辽朝度牒,虽非宋物,仍有“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的快意,立马拍摄收藏,插入新版《水浒寻宋》。
希望我在《水浒》寻宋之旅上的所见所闻,能为广大的读者带来分享的愉悦。
(作者系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宋史研究会理事)
责编:马京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