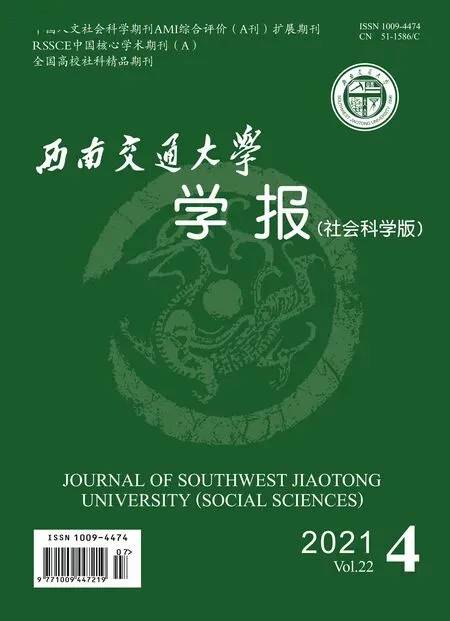上海图书馆藏宋本《新刊山堂先生章宫讲考索》的文献价值
《新刊山堂先生章宫讲考索》(以下简称《考索》),南宋章如愚编纂。章如愚,字俊卿,号山堂,婺州金华(今浙江金华市)人,自幼颖悟,登宁宗庆元二年(1196)进士第,仕至国博宫讲。未几,改知贵州(今广西贵港市),政绩大著。开禧(1205—1207)初被召,上疏极陈时政,忤韩侂冑,罢秩归乡。乃结山堂数十间以讲道义,故远迩之士咸尊师之〔1〕。著有《考索》,又撮其要为《卓约》二十卷,以便于举子业者〔2〕。史称其尚有文集百十卷,今皆已散佚,惟《考索》犹存。《考索》以分门别类的方式考察古代典章制度,尤其详于宋代时政,《四库全书总目》称其“言必有征,事必有据,博采诸家而折衷以己意,不但淹通掌故,亦颇以经世为心,在讲学之家,尚有实际”〔3〕,《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亦云“南宋率多类事之家,是书最为精博”〔4〕,可见评价颇高。
《考索》初刻于南宋理宗时期,在宋末曾被多次翻刻。宋刻本皆为一百卷,分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集,每集十卷。目前已知至少有三种宋刻本:(1)金华曹氏中隐书院刊本,存甲集十卷,现藏中国书店;(2)□山书院刊本(1)按,“□”者,原有其字,或残缺不清,或已被挖除,难以识别,下同。,存丙集四卷、丁集十卷、己集十卷(2)按,丙、己二集据傅增湘《藏园订补郘亭知见传本书目》及上海图书馆之著录皆归入□山书院刊本,详见下文。虽然丙、己二集在版式、行款等方面与□山书院本之丁集皆相同,但□山书院本翻刻自中隐书院本,版式、行款也与中隐书院本相同,也不能排除二集是中隐书院刊本的可能。由于没有确切的证据,姑且仍依旧录,以免徒添争论。,丙集现藏中国国家图书馆,丁、己二集藏于上海图书馆;(3)未知何处刊本,存木集十卷(3)按,所谓“木集”乃书贾挖改,其原本亦以十天干分集。通过比勘,此木集十卷对应今本后集卷五十五至卷六十四,正好接续上图所藏己集之内容,则此木集当原为天干十集中之庚集无疑。、□集十卷,现分藏中国国家图书馆及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
除宋本外,《考索》尚有元延祐圆沙书院本(以下简称元本)、明正德慎独斋本(以下简称明本)和清《四库全书》本(以下简称清本)。宋本原为十集百卷,今元、明、清本皆分前、后、续、别四集,凡二百一十二卷,前集六十六卷,后集六十五卷,续集五十六卷,别集二十五卷,乃是经吕中等人增补之后的本子,已非宋本之原貌。
今存《考索》的几种宋刻本皆已残缺不全,而上海图书馆(下文简称上图)所藏丁、己二集尚有二十卷之多,占宋本原书五分之一,这无疑给我们了解宋本之原貌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契机。学界对上图所藏宋本《考索》之情况也有过一些探讨,如李伟国《〈山堂考索〉的作者和版本》〔5〕、琚小飞《〈群书考索〉四库底本考论》〔6〕,但二人都误以为上图所藏丁、己二集为中隐书院刊本。又如台湾陈暐仁《〈新刊山堂先生章宫讲考索〉宋刻本考述》一文对宋本《考索》在清代以来的著录与收藏情况考察颇详,但由于地域条件所限,对上图所藏丁、己二集之情况则不甚明晰〔7〕。可见目前学界对于宋本《考索》的认识仍然不很准确,对于几种宋刻本之间的关系也未曾深入研究,对于上图所藏丁、己二集之内容及价值更是不甚了解。笔者因研究需要,曾亲至上图查阅馆藏宋本《考索》,今不揣浅陋,略加考述。
一、上图所藏丁、己二集的基本面貌
(一)丁集
丁集十卷,宋刻巾箱本,版框尺寸10.7cm×6.6cm,半叶十三行,行二十字,小字单行,字数同,白口,左右双边,双黑鱼尾,尾上记字数,版心记“丁几”,左栏外有书耳标注小题。目录后有碑形牌记,题“□山/书院”。目录及每卷卷首书名下“丁集”二字皆以墨盖子白文别出。每卷标题“礼门”“礼器门”上有花鱼尾,各小题皆以黑底白文别出。
卷首为目录,题“新刊山堂先生章宫讲考索目录丁集/山堂先生宫讲章如愚俊卿编”。目录始于第一卷《礼门·群祀类》,终于第十卷《礼器门·博物类》。此集经过后人重新装订,目录有误置,卷七《后服类》自“王孤之妻服”以下二十七条及《舄屦类》《佩玉类》《采就类》皆错入卷十《鼎类》“豕鼎”条之后,正文不误。目录终顶格题“新刊山堂先生章宫讲考索目录丁集”。
卷端题“新刊山堂先生章宫讲考索卷之一丁集/山堂先生宫讲章如愚俊卿编”。正文卷一至卷三为《礼门》,始于《群祀类》“后土”,终于《射类》,对应元、明、清本前集卷三十五至卷三十七;卷四至卷十为《礼器门》,始于《卤簿类》,终于《博物类》,对应元、明、清本前集卷四十至卷四十六。
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卷十“子部类书类”著录有宋本《考索》丁集十卷:
新刊山堂先生章宫讲考索目录十卷丁集宋章如愚撰
宋刊巾箱本,半叶十三行,行二十字,白口,左右双阑,版心记“丁几”二字,上方记字数,阑外标篇名。每卷首书名下标阴文“丁集”二字,目后有碑形牌子“□山/书院”,字为白文。
按:此书与袁抱存克文所藏本同式,惟此犹单篇草订横式为足贵耳(述古堂送阅,索五百元。戊午)。〔8〕(4)引用时标点有改动。
此集又载于《藏园订补郘亭知见传本书目》卷十下“子部十一类书类”:

从版式、行款及牌记来看,傅增湘所见之丁集当即上图所藏者。所谓“目录十卷”,是指丁集前之目录,非谓《考索》全书之目录。此外,傅增湘特别强调,此集“为单面草钉未折中缝之横册”,而非宋代常见的蝴蝶装,甚是少见,故尤为珍贵。但傅氏说“此书与袁抱存克文所藏本同式”则不然,袁克文所藏为四周单边本,与中隐书院本及□山书院本皆不同,为另一种版本,详见下文。
(二)己集
己集十卷,宋刻巾箱本,据上图著录,版式、行款与丁集相同。目录及每卷卷首书名下“己集”二字皆以墨盖子白文别出。各卷标题“地理门”“赋税门”“财赋门”上有花鱼尾,文中各小题皆以黑底白文别出。
卷首为甲集前之汪有开序,写于南宋理宗淳祐戊申(八年,1248),其文如下:
读万卷书,一节之不知,不足以言博学;论古今事,一字无来处,不足以言实学。事事必提其统,言言必究其归。考之有据,索之无遗。非殚见洽闻、真积力久之君子,其孰能与于斯!世之耳剽目窃,□出于胸臆;拈枝摘叶,不探其本根。观所用未必误、扣所出未必知者,何足进此!山堂先生自有书契以来至于今日,经史子集传记之书,充栋汗牛,反覆披览,门分类析,编辑成书。上下数千载,铺列数百条,援古证今,举纲撮要,凡大议论、大制度、大沿革,嘻!尽之矣!士大夫得而熟之,岂惟可膏场屋之笔端,与宾客言亹亹无倦,在朝廷言便便唯谨,指引辩证,博洽详实,岂止武库、五总龟邪?惜哉!书成而白玉楼召矣,后生晚学,罕见大全,同抱遗恨。惟中隐曹君尽得之,惧其传之不博,有孤先生之用心,镂梓以示同志,凡一百卷,厘为十集。摹印未尽,纸价增矣。第恐学者得书之易,不思其用力之艰,临用捡觅,平时漫不加意,又岂先生之志欤!先生姓章,讳如愚,字俊卿,仕至国博宫讲,“山堂”其自号,“考索”其书之旧名云。淳祐戊申良月望日,后学朝奉郎监行在榷货务汪有开敬题。
由于章如愚并没有留下序跋之类的说明文字,使我们对《考索》的编纂方式、成书过程以及编定时间等内容缺乏具体的了解。此篇序文虽然不是章氏所写,但汪有开与章氏时代相近,甚至可能亲见其人,其序文之价值可想而知。序文内容则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1)书名“新刊山堂先生章宫讲考索”,既称“新刊”,则此前可能已有他本流传(或刻本、或抄本、或稿本);又言“后生晚学,罕见大全”“惟中隐曹君尽得之”,则此前即使有他本流传,汪氏亦以为并非足本〔1〕。
(2)“凡一百卷,厘为十集”,则今日所见宋本以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分为十集、每集十卷之编次乃是出于曹氏中隐书院,未必合于章书之原貌。
(3)“仕至国博宫讲”,既称“仕至”,则非初授,而明本章如愚小传称“初授国子博士”,则误矣;称“‘山堂’其自号”,则明本所谓“及卒,门人谥为山堂先生”者〔1〕,亦误矣。
(4)既言“书成而白玉楼召矣”,则《考索》当是完本,而如愚可能在成书之后不久即去世,序文写于淳祐八年(1248),则章如愚当卒于此年之前。
汪有开序后为甲集目录之上半部分,题“新刊山堂先生章宫讲考索纲目甲集/山堂先生宫讲章如愚俊卿编”,“甲集”二字以墨盖子白文别出,其目为:
第一卷 六经门 易类
第二卷 六经门 书类
第三卷 六经门 诗类
第四卷 六经门 周礼类
第五卷 六经门 礼记类
第六卷 六经门 春秋类
第七卷 六经门 六经总论上
第八卷 六经门 六经总论下
显然,汪有开序及此甲集纲目残叶都是误置于己集之前,并非己集所固有。通过对比发现,此甲集纲目残叶正好与中国书店所藏中隐书院刊本《新刊山堂先生章宫讲考索》甲集十卷之目录下半部分相连接,其目如下:
诸子百家门 孝经类 论语类 孟子类
第九卷 诸子百家门 诸子类 百家类
第十卷 百家类 字学类 韵学类
将此二目相合,正好是甲集十卷的完整目录。可见汪有开序及甲集目录残叶原本当与中国书店所藏甲集存于一处,后被撕裂而误置于己集之前。傅增湘曾见过甲集十卷,《藏园订补郘亭知见传本书目》卷十下“子部十一类书类”:

傅氏所见甲集十卷即今中国书店所藏之本。傅氏记载丁集时,曾言及丁集尚有“目录十卷”,而此不言者,当是其时甲集前之汪有开序及目录已被一分为二,傅氏只见目录下半,未见序文及目录上半,故略而不载。中隐书院本牌记既称金华曹氏刊行,当属浙刻,但傅增湘特别指出,以字体雕工而论,其风格应属建本。论其缘由,或是建阳刻工受雇至金华雕刻,或是中隐书院于建阳设有书肆,雇佣当地刻工雕刻,而牌记仍称浙刻。要之,中隐书院本当与建阳书坊有一定关系,然书阙有间,真相如何已无从知晓。
据笔者目验并结合傅增湘所见,可知甲集为宋刻巾箱本,板框尺寸10.6cm×6.9cm〔10〕,半叶十三行,行二十字,小字单行字数同,白口,左右双边,双黑鱼尾,版心记“考甲几”,尾上记字数,尾下记叶数,间记刻工姓名,左栏外有书耳记篇名。目录后有“金华曹氏中/隐书院刊行”双行牌记。目录及卷首书名下“甲集”二字皆以墨盖子白文别出。各卷标题“六经门”“诸子百家门”上有花鱼尾,文中各小题亦皆以墨盖子白文别出。
中隐书院本与□山书院本相比,在版式、行款、每集卷数等方面多有相同,但并非同一版本,通过汪有开序已知《考索》十集百卷的编次出自中隐书院本,则□山书院本当是翻刻前者。
甲集纲目之后为己集目录,缺第一卷《地理门·州郡类》上半部分,始于“颛顼帝喾始别九州”,终于第十卷《财赋门·杂赋类》。每类下又各分子目。目录终顶格题“新刊山堂先生章宫讲考索目录己集”。
卷端题“新刊山堂先生章宫讲考索卷之一己集/山堂先生宫讲章如愚俊卿编”。正文卷一至卷八为《地理门》,始于《州郡类》“谨按天文分野”,终于《水利类》,对应元、明、清本前集卷五十九至卷六十六;卷九为《赋税门·田赋类》,对应元、明、清本后集卷五十三;卷十为《财赋门·杂赋类》,对应元、明、清本后集卷五十四。又,卷十《财赋门·杂赋类》“财赋总论”条缺“侈皇甫镈程异晓其意”以下内容,并非完卷。
二、相关书目对上图所藏宋本《考索》的误记
作为版本学领域目前最权威的书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以下简称《书目》)对宋本《考索》在国内的收藏情况有过记录,其中就包括丁、己二集:
新刊山堂先生章宫讲考索丙集十卷宋章如愚辑 宋刻本存四卷四至六、八北京图书馆
新刊山堂先生章宫讲考索丁集十卷己集十卷宋章如愚辑 宋刻本 上海图书馆
新刊山堂先生章宫讲考索□集宋章如愚辑 宋刻本 存十六卷 天津图书馆〔11〕
书中指明宋本《考索》之丁、己二集藏于上图,丙集残存四卷藏于北京图书馆(1998年更名为国家图书馆),而天津图书馆(天津市人民图书馆1982年更名为天津图书馆)所藏为□集十六卷。宋本每集十卷,而《书目》称天津图书馆所藏该集为十六卷,当有误。《书目》并未著录各集之版式及行款,而《(稿本)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以下简称《稿本》)作为《书目》的征求意见稿,对各集之记载则更为详细:
新刊山堂先生章宫讲考索丙集十卷宋章如愚辑 宋刻本 十三行二十字白口左右双边存四卷四至六、八北京图书馆
新刊山堂先生章宫讲考索丁集十卷己集十卷宋章如愚辑 宋刻本 十三行二十字白口、黑口不等四周单边 天津图书馆
新刊山堂先生章宫讲考索四卷宋章如愚辑 宋刻本 十三行二十字白口四周单边双鱼尾有刻工 上海图书馆〔12〕
与《书目》相比,《稿本》除了注明版式、行款等信息外,对各集的卷数及收藏单位的著录也有所不同:《书目》中收藏于上海图书馆的丁、己二集,在《稿本》里却藏于天津图书馆;而《书目》中藏于天津图书馆的□集十六卷,在《稿本》里变成了藏于上海图书馆的四卷;惟北京图书馆所藏丙集四卷,二目记载相同。《稿本》后经翁连溪先生编校为《中国古籍善本总目》(以下简称《总目》),对各集的著录如下:
新刊山堂先生章宫讲考索丙集十卷宋章如愚辑 宋刻本 十三行二十字白口左右双边存四卷四至六、八 国家图书馆
新刊山堂先生章宫讲考索丙集十卷己集十卷宋章如愚辑 宋刻本 十三行二十字白口、黑口不等四周单边 天津市人民图书馆
新刊山堂先生章宫讲考索四卷宋章如愚辑 宋刻本 十三行二十字白口四周单边双鱼尾有刻工 上海图书馆〔13〕(5)按:书中“己”误作“已”。
从这段引文可以看出《总目》对《稿本》的因袭情况,但《稿本》著录天津图书馆所藏丁、己二集,《总目》却改成了丙集、己集,以至于丁集十卷凭空消失,而反有两丙集。二目既已著录丙集十卷(存四卷)藏于国家图书馆,翁先生当不至于再有此误,疑是《总目》原作丁集、己集,而排印时才将丁集误作丙集。若如此,则《总目》与《稿本》对宋本《考索》各集之著录皆相同,而我们需要解决的则是《书目》和《稿本》之间的异同问题。
通过对比可以发现,宋本《考索》丙集残本四卷藏于国家图书馆,《书目》和《稿本》皆无异议,二目之不同主要在以下三点:(1)宋本《考索》丁、己二集是藏于上海图书馆还是天津图书馆?(2)二目所载之宋本《考索》□集是藏于天津图书馆还是上海图书馆?(3)此宋本□集是十六卷还是四卷?
首先看第一点,宋本《考索》丁、己二集是藏于上海图书馆还是天津图书馆?通过查找相关资料,我们发现上海图书馆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馆藏善本进行过编目,后来整理成《上海图书馆善本书目》(以下简称《上目》)一书,书目中卷三“子部类书类”对馆藏之宋本《考索》有过明确记载:
新刊山堂先生章宫讲考索丁集十卷己集十卷宋章如愚辑 宋刻巾箱本 半叶十三行 行二十字〔14〕
虽然书中只记录了丁、己二集之行款,并未说明版式,但已清楚注明丁、己二集藏于上海图书馆,而非天津图书馆,此与笔者所见相合。且经笔者目验,上图所藏丁、己二集皆为白口、左右双边,而非《稿本》所载之白口、黑口不等,四周单边。可见《上目》与《书目》记载不误,而《稿本》之说有误。
再看第二点,《书目》和《稿本》所载之宋本《考索》□集是藏于天津图书馆还是上海图书馆?根据《上目》记载及笔者目验,上海图书馆所藏宋本《考索》只有丁集十卷、己集十卷,再无他本,则此宋本□集当如《书目》所记藏于天津图书馆,《稿本》谓藏于上图者,非是。
最后看第三点,藏于天津图书馆的宋本□集到底是十六卷还是四卷?我们知道,宋本《考索》每集皆为十卷,而《书目》云十六卷,必然有误。既然如此,那是《稿本》所谓的四卷吗?若为四卷,则必是残卷,是否有此可能呢?答案是否定的。
经考证,天津图书馆确实收藏过宋本《考索》□集,不过既非十六卷,也非四卷残本,而是十卷,为完整的《官制门》一集,目录与正文十卷俱存,为袁克文旧藏,现藏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袁克文《寒云日记》丁巳(1917年)二月十六日曾记载其得书经过:
于寓沪某家以八百五十元购得《新刊山堂先生章宫讲考索》十卷,乃宋刊宋印巾箱本,高四寸二分,阔二寸五分,版心高三寸一分,阔二寸,刻印俱精。此书向无宋本见于著录,惟元圆沙书院及明刊本。此十卷为官制门,虽非完帙,而目录只十卷,首尾无缺,想是一集之全者。惟标题下有分集标明墨钉,为人铲去,固不可考。……
《新刊山堂先生章宫讲考索》十卷,宋章如愚辑,每半叶十三行,行二十字,白口,有字数,间有刻工姓名,目录标题兼行大字,“官制门”三字亦如之。目录后有鼎形无字印,栏外有耳题,宋讳多缺笔。藏印有“毛表之印”、“虞山毛氏汲古阁收藏”、“汲古后人”、“古虞毛氏奏叔图书记”、“毛表私印”。〔15〕(6)原文误字颇多,引用时已改正。
此集十卷十册,第一册书后有袁克文手书题记,并赋《春日杂诗》一首,其文如下:
《山堂先生章宫讲考索》十卷,宋刊宋印,精好足赏,虽非全帙,而目录首尾无缺,当是一集之完者,细审标题下俱有修补之痕,显为恶估铲去标明集次墨钉,以冒称完帙,不复见宋本原来面目,惜哉!盖元明诸本已非宋本分集之旧矣,诸藏家著录之最古者,为元圆沙书院巾箱本,每半叶十五行,明本每半叶十行(7)按,明本每半叶十四行,此处有误。,标题俱曰“群书考索”(8)按,元圆沙书院本书名《山堂先生群书考索》,明慎独斋本书名《群书考索》。,无有标“章宫讲”者,宋本之罕异,不亦可贵耶。丁巳二月十六获于春申江上,寒云。
《春日杂诗之一》
十卷山堂珍宋椠,何须完璧乞圆沙。十三十五分行格,宫讲标题况独差。〔7〕
丁巳为民国六年(1917),春申江即上海黄浦江,则此书是袁克文1917年2月16日寓居上海时以八百五十元的高价购得。书中所钤“毛表之印”“虞山毛氏汲古阁收藏”“汲古后人”“古虞毛氏奏叔图书记”“毛表私印”等印皆为清初毛表之藏书印。毛表(1638—1700),字奏叔,号正庵,虞山(今江苏常熟)人,明末著名藏书家、刻书家毛晋第四子,以医学名世〔16〕。毛表早年亦曾藏书、刻书,此集康熙年间当为其所藏。据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之著录,书中尚钤有“天津市人民图书馆珍藏图书”“天津图书馆注销章”,则此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为天津图书馆收藏,后方归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
根据袁克文的记载及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的著录可知,此□集十卷十册(卷九叶九为抄补),宋刻巾箱本,版框尺寸10.5cm×6.7cm,半叶十三行,行二十字,白口,偶有线黑口,四周单边,双黑鱼尾,尾上记字数,尾间记卷次,尾下记叶数,间记刻工姓名:庭、应芹、芹、齐、子、震。左栏外有书耳标注小题。目录标题兼行大字,“官制门”三字亦如之。每卷标题“官制门”上有花鱼尾,各小题或记“朝代”“官署”“帝号”等皆以墨盖子白文别出,内文引用年号时以括弧标示。目录后有鬲鼎形无字牌记。各卷卷端首行标题下方原刻有某集,现已全被剜去。此集为宋本某集十卷完整的《官制门》,对应元、明、清本后集卷十一至卷二十。
此□集之版式等方面与中隐书院本、□山书院本多有不同:(1)中隐书院本与□山书院本皆为白口、左右双边,此集则为白口、偶有线黑口、四周单边;(2)中隐书院本为双行文字牌记,□山书院本为双行文字碑形牌记,此集则为鬲鼎形无字牌记;(3)此集之目录标题及“官制门”三字皆兼行大字,中隐书院本与□山书院本则皆单行小字;(4)此集文中各小题或记“朝代”“官署”“帝号”等皆以墨盖子白文别出,内文引用年号时以括弧标示,中隐书院本与□山书院本皆无之。从这些不同可以看出,此集当是与中隐书院本、□山书院本皆不同的第三种南宋刻本,应是翻刻二者之一。但这三种刻本卷端题名同为“新刊山堂先生章宫讲考索/山堂先生宫讲章如愚俊卿编”,版框尺寸几乎相同,其他如十三行二十字、白口、双鱼尾、书耳等方面也多相同,傅增湘谓中隐书院本“以字体雕工论,是建本而非浙本”,则或许此三者皆为福建刻本〔7〕。
综上所述,《书目》《稿本》《总目》三书所载宋本《考索》各集之情况互有正误,现总结如下:
第一,如《书目》之著录,宋本《考索》丁集十卷、己集十卷藏于上海图书馆,而非天津图书馆;其版式为白口、左右双边,而非白口、黑口不等、四周单边,《稿本》与《总目》之记载有误。
第二,国家图书馆所藏丙集十卷,现存四卷(四至六、八),半叶十三行,行二十字,白口,左右双边,三目所载皆无误。
第三,天津图书馆所藏为□集十卷,半叶十三行,行二十字,白口、黑口不等,四周单边,有刻工,三目所载皆有误。
三、上图所藏丁、己二集的文献价值
宋本《考索》原为十集百卷,后经南宋吕中等人增补为今本之四集二百一十二卷,元、明两代刊刻时亦屡有增改。通过对比宋本丁、己二集与今本之内容,不仅可以校订今本文字之错漏,亦可借以考察后人增改之方式,对于还原宋本之早期面貌、了解南宋类书之编纂方式等都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一)校订今本文字
宋本丁、己二集之所以可贵,在其刊刻较早,未经后人窜改,最大程度上保留了文本原貌,对于校勘今本文字之讹脱衍倒、注文误阑以及补正引文出处等都具有重要作用。
1.校订讹误
根据丁、己二集可校订今本文字之讹误,如己集目录第二卷《地理门·州郡类》“高齐北国土宇”“唐改郡为州”二条,前者元本“高”误作“家”,明本误作“后”,后者元、明本“唐”皆误作“高”(9)元本参照中华再造善本2006年影印北京大学藏元延祐七年圆沙书院刊本,明本参照中华书局1992年影印明正德十三年慎独斋刊本,下同。;第六卷《田制类》“国郊甸稍县都图”条,元、明本皆将“国”误作“周”、“图”误作“鄙”;第七卷《田制类》“北齐给受田令”条,元、明本“给”皆误作“始”。文中之讹误者,如丁集卷一《礼门·群祀类》“山川”条“虞氏秩于山川,徧于群神”,元、明本“徧”皆误作“偏”;《六宗类》“司中、司命,所司有殊”,元、明、清本“殊”皆误作“一”;卷二《释菜释奠类》“孔子祠七十二贤”条“老莱子”,元、明本“老”皆误作“者”;《祈报类》“星变水旱,皆免三公”,元、明、清本“变”皆误作“火”;《牲牢类》“血腥爓孰”(10)按,明本“爓”误作“爛”,“孰”作“熟”。条“凡阳祀用骍牲,阴祀用黝牲”,元、明、清本“黝”皆误作“大”;卷五《礼器门·车辂类》“月令车马之制”条“《玉藻》曰:天子龙衮以祭,元端而朝日”,元、明、清本“端”皆误作“冕”;己集卷一《地理门·州郡类》“唐天文志曰”条“韩据全郑之地,南尽颍川、南阳”,元、明本“据”皆误作“样”、“川”皆误作“州”;卷二《州郡类》“唐郡名”条“唐郡名”,元、明、清本“郡”皆误作“都”;卷七《田制类》“唐口分世业”条“唐口分世业”,元、明、清本“分世”皆误作“田分”;卷九《赋税门·田赋类》“禹五服之赋”条“又其外五百里曰要服【要束以文教】”(11)按“【】”内为小字注文,下同。,元、明本“束”皆误作“东”;卷十《财赋门·杂赋类》“和买预买”条“和买预买”,元、明、清本“预买”皆误作“预置”。
2.校订脱漏
对照丁、己二集可校订今本文字之脱漏,如丁集目录之《群祀类》《乡饮酒类》《大饮蒸类》《射类》《冕服类》《后服类》《舄屦类》《佩玉类》《采就类》《带类》《佩鱼类》《贽仪类》《圭璧类》《笏类》《樽罍类》《爵斝类》《器用类》《鼎类》《宝玺类》《印绶类》《符节类》《刀剑类》《博物类》、己集目录之《州郡类》《风俗类》《夷狄类》《要害类》《户口类》《版籍类》《田制类》《营田屯田类》《水利类》《田赋类》《杂赋类》,元、明本皆脱“类”字;丁集目录第六卷《礼器门·冕服类》“诸侯始冠之冠”条下有“服制”条,元、明本皆脱;第八卷《圭璧类》“玄璜”条下为“四圭有邸”“两圭有邸”,元本脱“两圭有邸”,明本脱“四圭有邸”;己集目录第二卷《地理门·州郡类》“府号郡名多沿唐旧号不同者七”条下有“唐所无者十四”一条,元、明本皆脱;第五卷《舆地图类》,元、明本皆脱“图类”二字;第十卷《财赋门·杂赋类》“天禧”条下有“米”条,元、明本皆脱。文中脱漏亦多,如丁集卷五《礼器门·旂常类》“旗”条“皆一时之观美而已,岂古制哉”、“旜物”条“孤卿建旜,大夫士建物”,前者元、明、清本皆脱“岂古制哉”四字,后者皆脱“士”字(12)清本参照中国台湾商务印书馆1985年《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下同。;卷六《冕服类》“却敌冠”条“晋制卫士服”,明本脱“服”字;己集卷九《赋税门·田赋类》“魏文增赋”条“魏文侯时,租赋增倍于常,或有贺者。文侯曰:‘今户口不加而租赋岁倍,此由课多也。譬如彼治冶,令大则薄,令小则厚,治人亦如之。夫贪其赋税不爱其人,是虞人反裘而负薪也。徒惜其毛,而不知皮尽而毛无所附’”、“秦孝公坏井田”条“秦孝公十二年,初为赋。纳商鞅说,坏井田,开阡陌,制贡赋之法”(13)按,明本“二”误作“三”。,前者除“魏文增赋”标题四字外,元、明、清本皆脱漏整段条文,后者皆脱漏“秦孝公坏井田”标题六字(14)按,元、明本目录中皆不缺。,易使人误以为“秦孝公”云云乃“魏文增赋”之内容。
3.校订衍文
参照丁、己二集还可校订今本文字之衍文,如丁集卷一《礼门·群祀类》“类祭造祭”条“要之,劣于正祭与旅也”、《六宗类》“寻郑本意,以五星十二次各共成功”,前者元、明、清本皆“与”上衍“既”字,后者皆“二”后衍“二”字;己集卷一《地理门·州郡类》“周体国经野”条“周体国经野”,元、明、清本皆“周”后衍“并”字;卷二《州郡类》“升改废置州郡”条“夔:开置遵义”,元、明、清本皆“置”后衍“渝”字。
4.校订误倒
利用丁、己二集也可校订今本文字之误倒,如己集目录第五卷《地理门·版籍类》“宋”“齐”“后魏”“唐”四条,元、明本“齐”“后魏”皆误倒;第六卷《田制类》“国郊甸稍县都图”条,元、明本“郊”“甸”皆误倒;第七卷《田制类》“成帝时兼并者多”条,元、明本“者”“多”皆误倒。
5.校订注文误阑
参考丁、己二集可校订今本注文阑入正文之误,如丁集卷一《礼门·群祀类》“后土”条“大宗伯曰‘王大封则先告后土【后土,土神也】’”、“大祝‘建邦国先告后土,用牲币【后土,社神】’”、“山川”条“于是自崤以东,名山大川祠曰太室【嵩高也】”,卷二《祈报类》“帝曰:‘此法前代所传,不用巫觋,盖防亵慢。可令长吏精洁行之【注】’”,卷五《礼器门·车辂类》“诸侯大夫等车辂”条“太守则乘藩车【陈遵】”;己集卷一《地理门·州郡类》“剑南道”条“而郡国百有八焉【省前汉八,置五,改旧名七,因旧九十六,少前汉三也】”(15)按,宋、元、明、清本“三”皆误作“二”。自“七”以下十一字,卷九《赋税门·田赋类》“成周九赋九式九贡之法”条“周公作《周官》而理财之法益详,以九赋敛财贿【邦中、四郊】”(16)按,宋、元、明本“详”皆误作“诗”,元、明本“中”皆误作“车”。,元、明、清本皆注文阑入正文。
6.补正引文出处
还可以丁、己二集补正今本引文之出处,如丁集卷一《礼门·群祀类》“祭亲蚕”条“诏后亲桑以奉祭服,为天下先【景帝纪】”,卷二《恭谢类》“太常礼院言:‘恭谢请如明堂故事,用銮驾仪仗。’从之【国朝会要】”,卷三《射类》“射礼”条“燕射之侯则画熊、麋、虎、豹、鹿、豕之形以象鹄,此三射之别也【陈礼书】”;己集卷三《地理门·风俗类》“总论”条“以此显示众庶,未有辇毂之内治而天下不治矣【临川文】”,卷六《田制类》“任民之法”条“凡欲下地之民生齿之繁以及中上者,而后无慊,此富而庶之术也【同上】”,卷九《赋税门·田赋类》“贡助彻之名”条“此周人所谓彻也【杨】”、“假田免”条“初元元年,江、海、陂、湖、园、池属少府者,以假贫民,勿租赋【元纪】”、“北齐旧制”(17)按,清本“旧”误作“田”。条“垦租送台,义租纳郡,以备水旱【通鉴】”(18)按,宋、元、明本“义”上皆衍“租”字,清本衍“其”字。,元、明、清本皆无出处。
(二)考察后人增改方式
通过比勘宋本丁、己二集,可以发现今本《考索》既有吕中之增补,亦有书肆之附益,其方式主要是修改文字、增设门类、补充字句、调整次序、合并条目。
1.修改文字
后人对宋本《考索》之增改首先体现在对文字的改易上,如宋本《考索》之书名皆作“新刊山堂先生章宫讲考索”,元本则改为“山堂先生群书考索”,明本则删减为“群书考索”,清本同明本。丁、己二集刻于南宋,文中所用“本朝”“国朝”等字样,今本多改为“宋朝”,如丁集目录第七卷《礼器门·后服类》“本朝后服”、第十卷《鼎类》“本朝玺”、己集目录第二卷《地理门·州郡类》“本朝肇造混一”、第五卷《版籍类》“本朝舆地图”、第七卷《营田屯田类》“本朝”、第八卷《水利类》“本朝水利”、第九卷《赋税门·田赋类》“本朝赋”,元、明本皆改为“宋朝”。其他修改者,如己集卷七《地理门·田制类》“宣公税亩”条“【注:公田之法,十取其一,今又履其余亩,复十取其一】”,元、清本同,明本“今又”之后改为“税其亩,是十取其二矣”;卷八《水利类》“秦凿郑国渠”条,元、明、清本皆改“郑国”为“溉田”;卷九《赋税门·田赋类》“成周立赋税之名”条“稅给郊社宗庙百神之祀”、“折纳轻重”条“折纳轻重”,前者元、明、清本皆改“郊社”为“社稷”(19)按,元本“稷”误作“社”。,后者皆改“折纳”为“哲宗”。
2.增设门类
除了修改文字之外,今本《考索》每有后人增补之门类,而不见于宋本之中,如丁集卷一至卷三为《礼门》,始于《群祀类》“后土”,终于《射类》“弓矢”,下接卷四至卷八之《礼器门》,而元、明、清本在其间尚有《礼门·旌旗类》以下凡二十五条(见今本前集卷三十八至卷三十九)为丁集所无,其目如下:前集卷三十八《礼门》“旌旗类”“佩绶带”“冠带”“衣裘”“卤簿仪卫”“门观宫殿”“台观馆阁楼室”“唐车舆衣服令”“唐洪文定制礼仪”“洪文沿革”“王俭学士馆”“宋朝三馆”“龙图”“天章”“宝文”“显谟”“徽猷”“敷文”“焕章”“华文”,卷三十九《礼门》“祭祀”“礼制”“礼器”“冕服”“车”。陈先行先生以为此二十五条内容乃宋本之阙漏(20)按,今本前集卷三十八至三十九共有二十五条条文,陈先生以为十九条,当是误以卷三十八为《礼门·旌旗类》,其下十九条条文皆属于此类,而又漏记卷三十九之五条条文。其实“旌旗类”当衍一“类”字,与其下十九条条文并无隶属关系。,吕中增广时补入〔1〕。可见吕中之增补并非直接置于原文之下,而是另设门类,以示区别。这也是为什么《考索》有很多门类相同但内容却不同的部分存在的原因。
3.补充字句
今本亦有补充宋本之字句者,如明本前集卷四十五《礼器门·爵斝类》“玉爵”条“取呼者也”后有“秦、汉、晋、宋以后,或因或革,莫能考其实,元复用之”一句,卷五十九《地理门·州郡类》“西汉郡国”条“拓土分疆,又增十四【弘农、临淮、西河、上谷、朔方……】”之“上谷”二字,后集卷五十三《赋税门·田赋类》“贡助彻之名”条“取于百亩是为彻【吕东莱】”(21)按,明本“取”误作“助”。之“东莱”二字、“除租”(22)按,宋、元本为“令半田租”条,说见上文。条“景帝元年诏曰:今年令半田租”之“诏曰今年”四字、“赀不过二万免”(23)按,宋、元、明本“赀”皆误作“此见”,元、明、清本“二”皆误作“三”。条“被灾之郡不满十万,勿收租税【本纪】”之“本”字、“后周旧制”之“旧制”二字,宋、元本皆无,其“元复用之”云云,断非宋元人语,乃明正德年间刘洪慎独斋刊刻时增补无疑。可知《考索》除经吕中增补之外,尚有书肆之附益,其文本面貌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4.调整次序
今本《考索》分前、后、续、别四集,与宋本相比,除了内容上的增补之外,门类次序亦有调整。如己集卷一至卷八为《地理门》,对应今本前集卷五十九至卷六十六;卷九为《赋税门·田赋类》,卷十为《财赋门·杂赋类》,对应今本后集卷五十三至卷五十四。而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木集十卷,卷一至卷六为《财赋门》,对应今本后集卷五十五至卷六十,卷七至卷十为《财用门》,对应今本后集卷六十一至卷六十四〔17〕(24)按,此处转引自李红英《四库全书总目·〈山堂考索〉条辨证——兼谈〈山堂考索〉的版本源流》,但李氏将“六十”误作“六十一”,“六十一”误作“六十二”。,正与己集相接续,可见此木集当原为庚集,而为书贾挖改。若依宋本之次序,己集卷九至卷十应对应今本后集卷一至卷二,庚集十卷应对应今本后集卷三至卷十二,此宋本十二卷为《赋税门》《财赋门》《财用门》,但今本后集卷一至卷二十皆为《官制门》,可见宋本之门类次序已被更改。
5.合并条目
今本亦多有合并宋本之条目者,如丁集目录第四卷《卤簿类》《车辂类》分为两条、第五卷《车辂类》《旂常类》(25)按,宋本“旂”误作“祈”。《冕服类》分为三条、第八卷《圭璧类》《笏类》分为两条,元、明本皆合为一条,分别作《卤簿车辂》《车辂旂常冕服》《圭笏》(26)按,元、明本正文中并未合并。。文中己集卷九《赋税门·田赋类》“除租”条后有“令半田租”条,元本同(27)按,元本“令半田租”四字标题未以黑底白文标出,且“令半”误作“今年”。,明、清本皆与“除租”合为一条,且无“令半田租”四字标题(28)按,明本目录中不缺。;“汉山泽园池税”与“少府”为两条,元、清本同,明本则合为一条。
四、结论
《考索》初由金华曹氏中隐书院刻于南宋理宗淳祐八年(1248),其后屡经翻刻。目前已知至少有三种宋刻本:中隐书院本、□山书院本及一种未知何处刊本。中隐书院本是现存《考索》的最早刻本,也是其他宋刻本之祖本,□山书院本与未知何处刊本均由中隐书院本而来。中隐书院本与□山书院本之版式皆为白口、左右双边,而未知何处刊本则是白口、黑口不等、四周单边,可见□山书院本翻刻自中隐书院本,未知何处刊本则可能翻自二者之一。上海图书馆所藏宋本《考索》丁集十卷、己集十卷,丁集目录后有“□山/书院”双行牌记,知为□山书院刊本。己集前附有中隐书院本甲集目录残叶及汪有开序,学者多因此误会二集为中隐书院本。
宋本《考索》刊刻时间最早,在最大程度上保留了《考索》的原始形态,在校订今本文字、还原宋本早期面貌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但宋本《考索》迭经吕中之增补与书坊之附益,二者通过修改文字、增设门类、补充字句、调整次序、合并条目等方式,使《考索》从宋本之十集百卷变为今本之四集二百一十二卷,其文本面貌也在不断发生着变化。丁、己二集虽然只有二十卷,但对于考察后人之增改方式、探讨《考索》文本的生成过程、进而考察南宋类书之编纂方式等,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宋本《考索》十集百卷的编次出自中隐书院刊本,恐已不是章如愚之原貌;而十集百卷本后经吕中等人增补为四集二百一十二卷,亦不复中隐书院本之原貌;此四集二百一十二卷本在元、明两代刊刻时亦多有增改,恐亦非吕中等人之原貌矣;而元、明之四集二百一十二卷本再经四库馆臣之删改而成《四库全书》本,虽元、明本之原貌亦不可见矣。可见即使在刻本时代,文本的面貌也不是固定不变的,文本的生成是一个长期的动态过程;而在这个动态过程之中,原本的作者已经退场,新的作者——出版者、读者迭次出现,不断塑造着文本的形态:出版者通过刊印不断对原书进行增改、重编,直接扮演着作者的身份;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也会对原书进行加工、增补,也在以作者的身份改变着原书的面貌,而文本的生成就是在作者——出版者——读者三者之间的互动中最终完成的。当然,政治因素也在文本面貌的塑造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四库全书本《考索》的形成就是很好的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