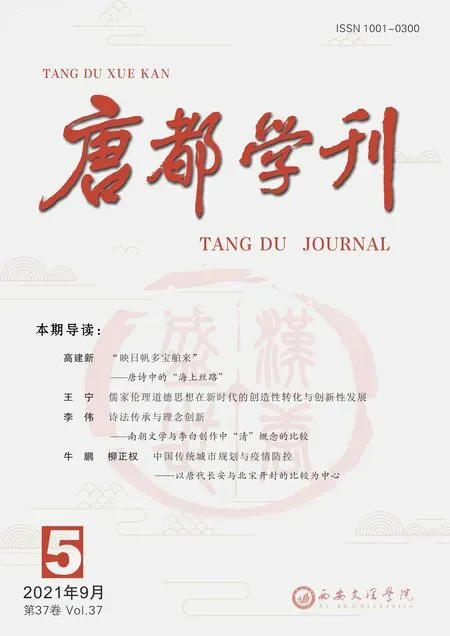家国分野:唐代“国忌行香”问题再探
吴凌杰
(中山大学 历史学系,广州 510275)
行香即上香,是一项较为传统的佛教活动。在唐代,每逢死生大事,人们总要去寺庙行香祈福。所谓的“国忌”即指君王的忌日,故“国忌行香”之意为每逢君王的忌日,嗣皇帝等人昭告天下臣民前往寺庙为大行皇帝行香。学界对唐代“国忌行香”现象的探讨,最早可追溯到日本学者大谷光照先生所撰《唐代の仏教儀礼》一书[注]参见大谷光照《唐代の仏教儀礼》,有光社(日本东京),1937年版。, 而后那波利贞、古濑奈津子等先生接续前言,探讨了“国忌行香”与时政朝局之关系,诸多论述颇为精当[注]参见那波利贞《唐代社会文化史研究》,创文社(日本东京),1974 年;古濑奈津子著、郑威译《遣唐使眼里的中国》,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 年版。。国内学界对此问题的介入较晚,随着敦煌文献不断被整理与出版,国内学者遂多以敦煌文献中的《书仪》等为史料来源,研究了“国忌行香”的背景、过程,以及它与儒家礼制、太庙庙数的关系、进而探讨了地方诸侯与中央政府的互动等问题,取得了瞩目的成果,呈现出后来居上之势头[注]参见刘俊文《敦煌吐鲁番唐代法制文书考释》,中华书局,1989 年版;周一良、赵和平《唐五代书仪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吴丽娱《唐礼摭遗——中古书仪研究》, 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严耀中《从行香看礼制演变——兼析唐开成年间废行香风波》,载于《论史传经——程应镠先生纪念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年版;冯培红《敦煌本〈国忌行香文〉及其相关问题》,载于《出土文献研究》第 7 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梁子《唐人国忌行香述略》,载于2005年《佛学研究》;张文昌《论唐宋礼典中的佛教与民俗因素及其影响》,载于《唐史论丛》第10辑,三秦出版社,2008年版;霍存福《唐式辑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年版;吴丽娱《敦煌书仪与礼法》,甘肃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王丽娜《唐代大寺的政治功能探析——以长安荐福寺的活动为中心的考察》,载于《历史教学》(下半月刊),2019年第4期。。近年来,有关唐代“国忌行香”的研究,则以聂顺新先生的成果最为突出,他以《续通典》中的佚文为基础,刊发了一系列论文,对“国忌行香”问题展开集中探讨,诸多结论为本文所用,值得关注[注]参见聂顺新《影子官寺:长安兴唐寺与唐玄宗开元官寺制度中的都城运作》,载于《史林》2011年第4期;《河北正定广惠寺唐代玉石佛座铭文考释——兼议唐代国忌行香和佛教官寺制度》,载于《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元和元年长安国忌行香制度研究——以新发现的〈续通典〉佚文为中心》,载于《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2015年第2期;《张氏归义军时期敦煌与内地诸州府国忌行香制度的差异及其原因初探》,载于《敦煌研究》2015年第4期;《长安开元观与唐玄宗的都城宗教政策》,载于《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唐代国祭行香制度渊源考论》,载于2019年《唐研究》。。 除唐代外,学界对其他朝代,诸如宋代的“国忌行香”问题也有所关注,其中以聂文华先生为代表,他在其博士论文《礼制中的政治秩序:以宋代皇帝丧葬礼研究为中心》第三章“忌:历日与庙制”中,深入探讨了“国忌行香”在唐宋之际的演变与著录载体的区别,进而分析背后的政治意义,其结论对本文的研究有所裨益[注]参见聂文华《礼制中的政治秩序:以宋代皇帝丧葬礼研究为中心》,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7年。近年来,聂文华先生再次围绕“国忌行香”问题撰写了一系列论文,即将刊发,可期待之。感谢聂文华先生向笔者惠赐大作,在此谨致谢忱!。总之,对唐代“国忌行香”问题的探讨,目前学界主要集中在政治与宗教、地方与中央关系等方面,但将“国忌行香”与帝王丧葬礼制研究相结合的论述相对较少,故本文不揣浅陋,尝试前行,论述诸多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斧正。
一、“国忌行香”的起源与属性
有关“国忌行香”起源的记载由来已久,典型出处见于宋人赵彦卫所撰的《云麓漫钞》,在其书卷3云:
“国忌行香”起于后魏,及江左齐梁间,每然香熏手或以香末散行,谓之行香。[1]
赵彦卫认为“国忌行香”起源于北魏,但很显然并不具有说服力,因为同为宋人的吴曾在《能改斋漫录》一书中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其书卷2云:
忌日行香。始于唐贞元五年八月,敕天下诸州,并宜国忌日,准式行香。然行香事,按《南山钞》云,此仪自道安法师布置。又《贤愚经》云,为蛇施金设斋,令人行香僧手中。《普达王经》云,佛昔为大姓家子,为父供养三宝,父命子传香。此云行香僧手中与传香,今世国忌日尚行此意。至人君诞节,遂以拈香为别矣。按,《唐会要》开成五年四月,中书门下奏:天下州府每年常设降诞斋,行香后便令以素食宴乐,唯许饮酒及用脯醢等。以此知唐朝虽诞节,亦只云行香。姚令威以为行香始于后魏江左,非也。[2]
可见,有关“国忌行香”的起源,在宋代就形成了多种不同的观点,此后争论一直延续,直至今日也有不同看法,因此处并非本文之重点,故而采用了聂顺新先生的“隋代说”[注]目前学界对“国祭行香”的渊源还有不同的看法,如梁子的“贞元二年说”、那波利贞的“汉末魏晋说”等,此处采用聂顺新先生之观点,参见聂顺新《唐代国祭行香制度渊源考论》,载于2019年《唐研究》。。
那么“国忌行香”有几种类型呢?目前学界似乎较少措意,在谈及“国忌行香”时,多模糊的将之作为一种固定祭祀的礼仪,笔者认为此制度并非是不言自明的,需要进一步辨析。有关唐代“国忌行香”的记载有很多,其中以圆仁所作的《入唐求法巡礼记》记载了唐玄宗、唐敬宗、唐武宗三次“国忌行香”最为典型,兹移录于下:
(开成三年十二月)八日,国忌之日。从舍五十贯钱于此开元寺设斋,供五百僧。
(开成五年)十二月八日,诸寺行香设斋当寺。李德裕宰相及敕使行香,是大唐玄宗皇帝忌日。
(开成六年正月)四日,国忌。奉为先皇帝,敕于荐福寺行香,请一千僧。[3]146
由上可见,开成三年的“国忌行香”对象为敬宗、开成五年“国忌行香”对象为玄宗,开成六年“国忌行香”对象为文宗。敬宗薨于宝历二年十二月辛丑(827年1月9日),行香时间为开成三年十二月八日(838年12月28日);玄宗薨于宝应元年四月甲寅(762年5月3日),行香时间为开成五年十二月八日(841年1月4日);文宗薨于开成五年正月四日(840年2月10日),行香时间为开成六年正月四日(841年1月30日)。据此推知,除文宗薨日与“国忌行香”间隔为一年外,玄宗与敬宗的薨日据“国忌行香”日早已过去了十余年或近百年,此时“国忌行香”,绝非敬宗与玄宗葬礼之部分,而是地方官员对他们的祭祀,属于追祭性质。
除了追祭性质的“国忌行香”外,还有一种“国忌行香”,即处于丧葬流程中的“国忌行香”,如上文所述唐文宗“国忌行香”之事,便是在其周年忌日举行。类似记载见于《唐会要》,其卷3“高宗于感业寺见武氏”条云:
贞观十年,文德皇后崩。太宗闻武士彟女,有才貌召入宫,以为才人。时上在东宫,因入侍悦之。太宗崩,随嫔御之例,出家为尼感业寺,上因忌日行香见之,武氏泣,上亦潸。[4]47
又后卷23云:
天祐二年八月八日,太常礼院奏:“今月十三日,昭宗皇帝忌辰,其日,百官阁门奏慰后,赴寺行香,请为永式。”从之。[4]350
唐高宗于感业寺遇武后之事较为典型,并为学界所熟悉。唐太宗于贞观二十三年五月(649年7月10日)病逝,武后被迫削发入感业寺为尼,而唐高宗遇武后则在永徽元年五月二十六日(650年6月30日),此时恰逢“国忌行香”于感业寺,距太宗去世一年,当为太宗丧期之流程。唐昭宗死于天祐元年(904),此时“国忌行香”为天祐二年(905),太常礼部所言亦如前。此类史料较多,不复赘述。
由此可见,唐代的“国忌行香”确实拥有两种模式:一种为丧葬礼制流程中的“国忌行香”,一般为此年皇帝的丧日的期年举行;另一种为追祭性质的行香,是一种常态化礼仪属性的祭祀活动,故此二者不可混为一谈。
二、“国忌行香”与唐代帝王丧葬礼制
从上述可知,唐代的“国忌行香”具有双重属性,且性质不同,那么在讨论时,就必须将其分开而论。
(一)帝王丧葬流程中的“国忌行香”
首先为丧礼流程中的“国忌行香”。前揭可知,行香日要晚于下葬日,多为期年而行。那么为何要选定为期年而行呢?想要追溯此问题,就必须明了唐代帝王葬礼之步骤与日期。一般而言,唐代帝王的丧葬步骤现已无法得知,但大体内容可从《通典》中所引《大唐元陵仪注》以及两《唐书》《唐会要》等政典中寻觅,现以材料较为丰富、较为典型的代宗为例,将表格列于下:

表1 代宗葬礼事例年表

续表1
从表1中可见,帝王丧葬一般由三部分构成:一是“丧纪”,即从“崩”到“殡”,这一步骤夹杂着“复、沐浴、含、设铭、悬重、小大敛、小大敛奠”等近十余个程序,这些步骤的持续时间较短。以代宗为例,他于六月十日崩至当月十五日便殡于太极殿,即所有程序在五日之内便处理完成;二是“葬纪”,即从“发丧”到“入圹”,这一步骤夹杂的“祖奠、遣奠、葬仪”等环节也较为迅速,从十一月十六日启殡到二十五日葬于元陵,中间相隔仅为九日;三是“祭纪”,即从“虞祭”到“禫”,中间夹杂着“小祥、大祥”等环节,这一步骤则穿插在整个丧礼当中,如代宗的小祥时间为六月二十二日,七月五日便已经禫变除服,此时距离丧日仅过去二十五天,这种短丧体现了唐代帝王丧期最大之特点 “以日易月”,即每过去一日即可抵当一月,按照王肃之学,三年祥禫为二十五月,此时权制之下,折合为二十五天,当是实行此制度之明证。
由于唐代帝王丧礼的步骤多依照儒家礼制,基本在一年内就举行完毕,那么为何“国忌行香”要定于一年之后呢?这就需要弄清楚“期年”在帝王丧礼中的特殊地位。
因“以日易月”的权制,故使得原本三年丧期的儒家经典理论被简化为了二十五天[注]笔者按:因郑王学说对“三年丧期”定义的不同,故在唐高祖、太宗时期,多实行“三十六”日的权制,而后改为王肃的“二十五”日,至唐后期则多选择郑玄的“二十七”日的权制,总归多在一个月内完毕;相关讨论可见洪家琪、吴凌杰:《挽歌:唐代帝王葬礼中的政治符号》,载于《保定学院学报》2020年第2期。,进而导致了唐代帝王丧礼大多在一年内结束,现将唐历朝帝王丧期列于下:

表2 唐代帝王葬期一览表
从表2中可见,除了玄宗与肃宗的葬期超过一年外,唐代的其余诸帝皆在一年之内就举行完毕了丧葬流程。[注]唐玄宗与肃宗之所以会超过一年,盖因安史之乱的缘故,致使丧礼无法按照正常的礼制流程走完,故在“殡”这一阶段较为漫长,进而使得葬期推迟。参见吴丽娱《终极之典:中古丧葬礼制研究》,中华书局,2012年版;聂文华先生在论述唐宋“国忌行香”日期上的区别时,指出唐代皇帝忌日成为国忌在死后的第二年,而宋代则在大祥后。其实二者的礼制精神相同。参见聂文华《礼制中的政治秩序:以宋代皇帝丧葬礼研究为中心》第171页。既然一年之内丧期即可结束,按儒家礼制学说,此时诸人便可除服出丧、归附礼乐。但实际并非如此,因为除了实行儒家丧礼外,皇帝本人在实际生活中常实行另外一套制度,即皇帝私下所遵循的“家礼”(亦或称“私礼”),其典型为心丧之制[注]吴丽娱先生对权制与三年丧有过仔细的探讨,她认为权制和心丧出于国家和皇帝个人家族伦理和感情的需要,也是对古礼的维护与变通,从而使得统治者实行起来摆脱了“不孝”的愧疚与压力,也使得朝政得以顺利运行,所以权制是有必要的。参见吴丽娱《关于中古皇帝丧服“权制”的再思考》,载于《中国史研究》2014年第4期。有关学术史回顾可见吴凌杰、洪家琪《国恤:唐代帝王丧葬礼制研究的回顾与反思》,载于《天中学刊》2019年第6期。, 据《贞观政要》云:
太宗谓侍臣曰:“朕昨见徐幹《中论》复三年丧篇,义理精审,深恨不早见此书。所行大疏略,但知自咎自责,追悔何及!”因悲泣久之。[5]
可见,虽然权制之下的儒家丧礼早已结束,但却只是代表着国家层面公礼的终止,在私底下的生活中,皇帝还可以实行“心丧”来延续自身的哀思。这时,丧礼的性质发生了转变,即在“公礼”层面时,皇帝以严格的儒家教条为核心,但在“私礼”时,则放弃了儒家礼制的约束,采取了更为灵活的丧事流程,其中往往就会受到宗教仪式的影响[注]有关于皇帝“公、私”礼的实行问题,日本学者尾形勇先生有过阐述,他认为中古时期的君王有着公、私两个场域,在不同场域,帝王所采取的态度的不一。参见尾形勇撰、张鹤泉译《中国古代的“家”与国家》,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321页。。虽从现今所存的唐代帝王丧葬礼制的文本记载中,很难找到宗教因素的身影,但从唐皇陵的出土文物上,却能揆诸一端,如在出土的唐中宗陵墓的镇墓石上,清晰地铭刻着道家的敕令,兹移录于下:
中央黄天,承元始符命,告下中央□□土府洞极神乡四统诸灵官,大唐中宗孝和皇帝,灭度五仙,论质□阴,今葬定陵宫室,庇形后土,明承王文,安慰抚恤,黄元哺饴,流注丰泉,练冶形骸,骨芳肉香,与神同元,亿劫长存,中岳嵩高,明开长夜九幽之府,升擢魂神,沐浴冠带,迁上南宫,供给衣食,长在光明,魔无干□,一切神灵侍卫安镇□如元始明真旧典女青文。[6]
可见,镇墓石是典型的道教因素的产物,它的主要作用是昭告各方神灵庇护死者。从文中“庇形后土”一语可知,祭后土仪式存在于中宗的葬礼[注]有关祭后土仪式的探讨,可参见雷闻《郊庙之外——隋唐国家祭祀与宗教》,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近些年来,吴丽娱、汤勤福等先生探讨了宗教因素与唐代祭祀礼制的关系,诸多结论颇为精当。参见吴丽娱《也谈唐代郊庙祭祀中的“始祖”问题》,载于《文史》,2019年第1辑。汤勤福《唐代玄元皇帝庙、太清宫的礼仪属性问题》,载于《史林》2019年第6期;汤勤福《集权礼制的变迁阶段及其特点》,载于《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汤勤福《宋代御容供奉与玉清昭应宫、京师景灵宫的礼仪问题》,载于《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因此,我们可大体推断出,虽然唐代帝王丧礼是依照儒家精神制作的,但在实际操作上依旧包含了宗教因素的存在,只是不见于史书记载而已。既然代表着国家“公礼”的儒家丧礼都含有宗教因素,那么作为皇帝私人的追悼之礼,则更是按照其喜好而安排,其中佛教在其中的影响巨大,如七七斋、百日祭等仪式屡见史书,在七七斋上,《资治通鉴考异》“开元四年六月癸亥条”云:
《睿宗》《玄宗实录》皆曰甲子。按下云:“已巳,睿宗一七斋,度万安公主为女道士。”今从《旧·本纪》《唐历》。[7]
又《大唐故越国太妃燕氏墓志铭并序》云:
东都寺观,恩敕咸为设斋……中官为造肖像二铺,广崇净业,兼制铭文……振古莫俦。[8]
吴丽娱先生在分析上述材料时,她认为宗教因素在皇家丧礼中已有出现,继而到唐后期变得非常普遍了,只是它们从不被作为国家礼典的规定而已[9]。此观点极具洞察性。
诚如上文所言,唐代帝王丧葬礼制中,早已浸润了宗教因素,此时的“国忌行香”,应当与“七七斋”“百日斋”一样,作为传统的佛教习俗,在唐代流传业已良久,并同属于帝王丧葬礼制流程的一部分。倘若我们将研究视域稍及后世,便可见丧葬流程中的“国忌行香”,作为一项基本的丧葬仪式对后世也产生了较大影响。譬如宋代,当时史料中可明确找到丧葬流程中的“国忌行香”之记载,据《宋会要辑稿·历代大行皇帝丧礼》云:
咸平元年三月十五日,诏以小祥忌,京城内外前后各十五日禁音乐,废朝七日。
二年三月大祥,群臣进名奉慰。是月,止于长春殿视事,朔望罢朝,百官起居去舞蹈,京城禁乐一月。至是前后各三日不视事。是月除常祭外,至撤灵筵时,帝又特设祭奠,躬护神御至祭所,别命学士具祭文。
五月二十九日,释祥服,废朝三日。六月二十九日,禫除,不视事,群臣进名奉慰,退赴启圣院行香。帝虽以易月之制,外朝即吉而内庭实服通丧也。[10]
宋太宗死于至道三年三月,而此时的“国忌行香”为咸平二年,在时间上已经为死后第二十八月,这与唐代权制的“二十七日”相关,盖宋人在礼制上为了展现自身的孝思,特意在 “二十七月” 祥禫之期满后,于“二十八月”举行行香,在时间上虽较唐代多了一个月(“权制”之下即多了一日),但究其根本可见性质与唐代并无不同。由此可推,唐宋时期帝王丧葬礼制,在“祭纪”部分的流程顺序应该为“虞祭、小祥、大祥、禫、国忌行香”,从虞祭为始,以“国忌行香”为终,生者对死者的沉痛之思逐渐衰退,在丧服上也愈发减轻,最终禫礼除服,归附常服,并用“国忌行香”的方式告祭死者,从这个角度即可知代表佛教因素的“国忌行香”与儒家的祥禫之礼在帝王丧葬流程中具有同等的地位。
通过以上论述,可得出两个结论:第一,唐代帝王的丧礼可分为公、私两个层面,在公层面时,帝王多遵循严格的儒家礼制,实行三年丧制下的“权制”之策,而在私层面时则多根据自身的喜好,一般多为亮喑三年,丧期无数;第二,宗教因素对于唐代帝王丧葬礼制影响巨大,其中丧葬流程中的“国忌行香”即是佛教对儒家丧葬礼制侵蚀的产物,此时“国忌行香”具有与祥禫礼相等同的重要性,它与祥禫礼一道构成了唐代帝王葬后的祭祀之礼,并对后世(诸如宋代)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注]吴丽娱先生对此持相同的观点,她将之浓缩表述为“儒学为体,佛道为用”。参见吴丽娱《试论唐宋皇帝的两重丧制与佛道典礼》,载于《文史》2010年第2辑,第221-228页。而聂顺新先生对此持怀疑态度,认为“国忌行香”是儒释道三教融合下太庙祭祀制度的一种延伸与推广,即便“国忌行香”从属于唐代帝王丧葬礼制,也在绝非其核心流程,而是外围与边缘部分。感谢聂顺新先生向笔者交流此观点,在此谨致谢忱!。
(二)追祭性质的“国忌行香”
与丧葬流程中的“国忌行香”不同,它的举办并非完全按照“期年”之制,如前所述,开成时期举办的玄宗与敬宗的“国忌行香”,此时距离二者去世已过去了几十年,故为当时人们对前世帝王的追祭。
有关追祭性质“国忌行香”的事例较多,除如前所列的高宗、文宗、昭宗三帝外,在史书中还存在许多其他的材料,以岳珂《愧郯录》卷13《国忌设斋》条为例[注]转引自聂顺新《元和元年长安国忌行香制度研究——以新发现的〈续通典〉佚文为中心》,载于《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2015年第2期。,其文云:
高祖五月六日忌……太穆皇后窦氏五月二十一日忌……太宗五月二十一日忌……文德皇后长孙氏六月二十一日忌……睿宗六月二十日忌……昭成皇后窦氏十一月二日忌……玄宗四月五日忌……元献皇后杨氏三月二十三日忌……肃宗四月十八日忌……章敬皇后吴氏正月二十二日忌……代宗五月二十一日忌……睿真皇后沈氏十月二日忌……德宗正月二十三日忌……昭德皇后王氏十一月十一日忌,福寿寺、元(玄)真观各设五百人斋。然则唐制固甚侈,今几止二十之一。[11]
可见,仅在德宗元和年间,就曾举办过不下十次的“国忌行香”,这一类的“国忌行香”皆具追祭性质。聂顺新先生对此段材料进行过整理与勘正,兹录于下:

表3 德宗元和元年“国忌行香”表
由表3并结合前述,以玄宗为例,文宗开成五年(840)祭玄宗时间为十二月八日,而德宗祭玄宗时间为四月五日,可见不同皇帝举办“国忌行香”的时间不同。[注]除了不同皇帝“国忌行香”的时间不同外,实则同一皇帝在不同年份“国忌行香”的时间也有不同,至于行香的顺序则更为不同,学界对此的研究还较为模糊,不同学者提出不同的看法,如梁子认为“国忌行香”的时间是按照新逝皇帝的忌日为准;吴丽娱与霍存福则指出“国忌行香”的时间与日数与太庙中神主迁祔直接相关,由于此争论并非本文侧重点,故不展开论述。参见梁子《唐人国忌行香述略》,载于2005年《佛学研究》;霍存福《唐式辑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年版;吴丽娱《敦煌书仪与礼法》,甘肃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且举办的地点也有所不一,如高宗“国忌行香”地点为胜业寺、会昌寺,而太宗为青龙寺、经行寺。由于寺庙大小不一,使设斋的人数有所不同,多可达500人,少则为250人。囿于现今长安城内佛寺存毁不一,故寺庙的位置、规格与设斋人数的关系暂且失考。[注]有关长安城图示与寺庙分布状况,可参见韦述撰、杜宝撰、辛德勇辑校《两京新记辑校 大业杂记辑校》,中华书局,2020年版;并见辛德勇《隋唐两京丛考》,三秦出版社,2006年版。
追祭性质的“国忌行香”,除了由皇帝在京城举行外,各府州长官也要在当地寺庙举行,表达臣属对皇帝的孝思,从而体现地方对唐中央的服从。有关记载见于敦煌文书S.5637;P.2854;P2854V《国忌行香文》《先圣皇帝远忌文》等,冯培红、赵和平、吴丽娱等学者早有研究,兹不赘述[注]原文及论述可参见周一良、赵和平《唐五代书仪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吴丽娱《唐礼摭遗——中古书仪研究》,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冯培红《敦煌本〈国忌行香文〉及其相关问题》,载于《出土文献研究》第7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近年聂顺新先生整理了一方《河北正定广惠寺唐代玉石佛座铭文》,笔者认为此铭文极具价值,特移录部分铭文于下:
开元十五年,和私皇后四月七日忌,高祖神尧皇帝五月六日忌,太穆皇后五月廿一日忌,太宗文武圣皇帝五月廿六日忌。十八日。开(元)十六年,昭成皇后正月二日忌,和私皇后四月七日忌,高祖神尧皇帝五月六日忌,太穆皇后五月廿一日忌,中宗孝和皇帝六月二日忌。右已上九忌,同造玉石像一区,并光座举高九尺。朝请大夫、使持节恒州诸军事、检校恒州刺史、仍充恒阳军使萧诚,宣义郎、守恒州长史、上轻车都尉卢同宰,朝请郎、行参军、摄司功崔谦。专检校法师僧金藏、都维那僧贞演、寺主僧道秀、上坐僧玄明。贞元十一年三月廿八日,移此功德于食堂内安置。都检校重修造、寺主开元寺僧智韶、上座僧道璨、都维那僧惠钦、典座僧幽岩。[12]
这一佛座铭文,记载了河北恒州地区的官员于开元年间建造的佛像,记录了地方对唐朝皇帝与皇后九次的“国忌行香”。从参与者可见,有当地刺史、军使、长史等人,他们同属于地方的高级官员,不仅表现了臣属对帝王的孝思,而且表现了地方对中央的臣服。
再如前引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一书,所载开成三年(838)淮南节度使李德裕等人于扬州开元寺祭敬宗等,皆为地方高级官员对先帝的祭祀活动。此类记载,较为繁复,不复赘述[注]此类“国忌行香”学界探讨较为彻底,他们从地方与中央的政局互动、中古礼制的转型等视角出发,对之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因本文探讨重心不在此处,故较为简略。参见严耀中《从行香看礼制演变——兼析唐开成年间废行香风波》∥《论史传经——程应镠先生纪念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年版;冯培红《敦煌本〈国忌行香文〉及其相关问题》,《出土文献研究》第 7 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陈祚龙《关于玄、代二宗之间通行的“国忌”日历表》,载于《大陆杂志》,1976年第4期;刘俊文《天宝令式表与天宝法制——唐令格式写本残卷研究之一》,载于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编《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三),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追祭性质的“国忌行香”较为繁复,且时间不一,较丧葬流程中的“国忌行香”而言,形式多变。它在中央由皇帝举行,在地方上由地方官举行。不同皇帝举办“国忌行香”的日期不一,同一皇帝不同时期举办的“国忌行香”也不一样。在地方上,由地方官举行的“国忌行香”,不仅可以体现出臣属对帝王的孝思,还可以表现地方对中央的臣服。
总之,唐代的“国忌行香”具有双重性质,即分为丧葬流程中的“国忌行香”与追祭性质的“国忌行香”,两者无论是在举办人、时间以及蕴藏的礼制含义均有所不同,因此在探讨时不能将之混为一谈。
三、“国忌行香”的举办地与流程
基于以上论述,可知唐代“国忌行香”是佛教对儒家礼制的浸透与影响,那么“国忌行香”到底是怎样举办的呢?它的举办地与举办流程又是如何呢?这便是本小节所要探讨的内容。
有关“国忌行香”的举办地,在中央上,主要在长安城内,以胜业寺、会昌寺、兴福寺、兴唐观等寺观为中心,如前引岳珂《愧郯录》对举办地的寺庙有着明确的记载,从现存的两《唐书》《册府元龟》等史料中所见,大体也都在长安城内的寺庙之中,并不会离开京城。地方上的“国忌行香”,则多集中在当地府州的寺庙,如前引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载:
(开成三年十二月)八日,国忌之日。从舍五十贯钱于此开元寺设斋,供五百僧。[3]146
又《唐会要》卷50云:
(开元)二十七年五月二十八日敕,祠部奏,诸州县行道散斋观寺,进式,以同、华等八十一州郭下僧、尼、道士、女冠等,国忌日各就龙兴寺、观行道散斋,复请改就开元观、寺。敕旨:京兆、河南府宜依旧观、寺为定,唯千秋节及三元行道设斋,宜就开元观、寺。余依。[4]541
再又《唐六典》卷4“(尚书礼部)祠部郎中员外郎”条云:
凡国忌日,两京定大观、寺各二散斋,诸道士、女道士、僧、尼,皆集于斋所,京文武五品以上与清官七品以上皆集,行香以退。若外州,亦各定一观、一寺以散斋,州、县官行香。应设斋者,盖八十有一州焉。[13]
可知,地方“国忌行香”的位置,主要集中的州府内的寺观,而且对寺观有着明确的规定,并非任意寺观皆可,如唐玄宗时期就明确将天下八十一州的“国忌行香”,从原来由“龙兴寺、观”负责,改为由“开元官观、寺”负责。可见寺观作为民间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唐政府对它的控制十分严格,结合史书中记载的朝廷多次禁毁淫祀事例[注]有关唐代淫祀与政府的治理措施,学界研究较多,兹列举典型成果如下:严耀中《唐代江南的淫祀与佛教》,《唐研究》,1996年第2卷;雷闻《唐代地方祠祀的分层与运作——以生祠与城隍神为中心》,载于《历史研究》,2004年第2期。有关敦煌地区的佛寺专题性研究可参见王秀波《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三界寺研究》,上海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陈菡旖《唐五代宋初敦煌开元寺研究》,上海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年;高雪《唐五代宋时期敦煌灵图寺研究》,上海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年;卢雅凝《唐五代宋初敦煌大云寺研究》,上海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7年;莫秋新《唐宋时期敦煌报恩寺研究》,上海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8年;叶如清《唐宋时期敦煌大乘寺研究》,上海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9年等。有关学术史回顾可参见赵玉平《唐五代宋初敦煌佛斋礼仪研究》,上海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5年。,即可了解唐廷对宗教有着严格的管制措施。
有关“国忌行香”的流程,由朝廷举行的“国忌行香”参与者众多,如前引文所见,五品以上的文武官、七品以上的清流官以及男女道士、僧尼皆要到场。据梁子先生考证,到场的官员要按照官位秩序站立,并由富有经验的法师引导诸人焚香、唱赞、上斋文等仪式。地方举行“国忌行香”的流程,大体与朝廷举办的相同。据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载:
(开成三年十二月)八日,国忌之日。从舍五十贯钱于此开元寺设斋,供五百僧。八日,国忌之日。从舍五十贯钱于此开元寺设斋,供五百僧。早朝,(诸)寺众僧集此当寺,列坐东北西厢里。辰时,相公及将军入寺,来从大门。相公、将军双立,徐入来步。阵兵前后左右咸卫,州府诸司,皆随其后。至讲堂前砖砌下,相公、将军东西别去。相公(东)行,入东幕里,将军西行,入西幕下。俄顷,改鞋澡手出来。殿前有二砌桥,相公就东桥登,将军就西桥登。曲各东西来,会于堂中门,就座。礼佛毕,即当于堂东西两门,各有数十僧列立,各擎作莲花并碧幡。有一僧打磬,唱“一切恭敬、敬礼常住三宝”毕。即相公、将军起立取香器,州官皆随后取香盏,分配东西各行。相公东向去,持花幡僧等引前,同声作梵,如来妙色身等二行颂也。始一老宿随,军亦随卫,在廊檐下去。尽僧行香毕,还从其途,指堂回来,作梵不息。将军西向行香,亦与东仪式同,一时来会本处。此顷,东西梵音,交响绝妙。其唱礼,一师不动独立。行打磬,梵休,即亦云“敬礼常住三宝”。相公、将军共坐本座,擎行香时受香之炉,双坐。有一老宿圆乘和上,读咒愿毕。唱礼师唱为天龙八部等颂,语旨在严皇灵。每一行尾云敬礼常住三宝。相公诸司共立礼佛,三四遍了,即各随意。相公等引军至堂后大殿里吃饭,五百众僧,于廊下吃饭。随寺大小,屈僧多少。大寺卅,中寺廿五,小寺二十,皆各坐一处长列。差每寺之勾当,各自弁供。[3]146
可知地方官员在“国忌行香”时,与朝廷大致相同,参与人上都有官员与僧道,只是此时的官员阶级较朝廷官员为低。在“国忌行香”时,由节度使等人主持,前来的官员分列东西而立。节度使等人先礼佛再焚香,焚香的方位为东西二向,官员紧随其后,遵循相同的流程。在礼佛与焚香时,为了表示对诸佛的尊敬,需要由僧人时时打磬、唱颂梵呗。当流程结束后,官员包括节度使等人都要留下享用斋饭,沐浴更衣。相似的记载还见于敦煌文书S.5637;P.2854等处,兹不赘述。
总之,“国忌行香”的整个流程是完全依照佛教流程运转,朝廷与地方的做法并无区别,大体流程都是由皇帝(节度使)带领百官入寺观,先礼佛,再焚香,最后上表称述此次前来的目的,并为死者祈祷。在这一过程中,皇帝(节度使)不再具有最高的权威,他们需要听从僧人的指挥行动,僧人在“国忌行香”中扮演着先灵圣神的媒介,通过打磬、唱颂梵呗等步骤,使得皇帝(节度使)相信他们的孝思为死者所知晓,从而促使整个“国忌行香”流程的顺利运转。
四、结语
本文对唐代“国忌行香”事例的探讨,发现唐代“国忌行香”事例可分为两种类型,即处于丧葬流程中的“国忌行香”与追祭性质的“国忌行香”。
丧葬流程中的“国忌行香”属于皇帝丧葬礼制中的“私礼”,多依照皇帝个人的喜好与信仰而行,并不属于儒家丧葬礼制的一部分。皇帝一方面通过举行丧葬流程中的“国忌行香”,拔高了它的地位,使得它与儒家的祥禫礼具备了相同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促使宗教中的丧葬因素浸润到儒家丧葬礼制之中,导致中古丧葬礼制发生了较大的转型,并对后世(诸如宋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追祭性质的“国忌行香”属于唐皇帝与地方官员的自发性佛教行为,它的举办似有“随意性”。即在中央上,表现为不同皇帝举办“国忌行香”的日期不一,同一皇帝在不同时期举办的“国忌行香”也不一样。在地方上,除了举办时间不一外,还可以体现出地方与中央在政局上的互动关系,即地方官举行的“国忌行香”,不仅可以体现出臣属对帝王的孝思,还可以表现出地方对中央的臣服。
“国忌行香”作为佛教礼制,其举办地与举办流程是完全佛教化的。反映在举办地上,可知举办地主要为官方钦定的大寺观,并非任意的寺庙皆可;反映在举办流程上,则是僧人是“国忌行香”流程的主导,皇帝(节度使)皆处于信徒的角色,听从僧人的安排,进而使得僧人成为皇帝(节度使)与死者沟通的媒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