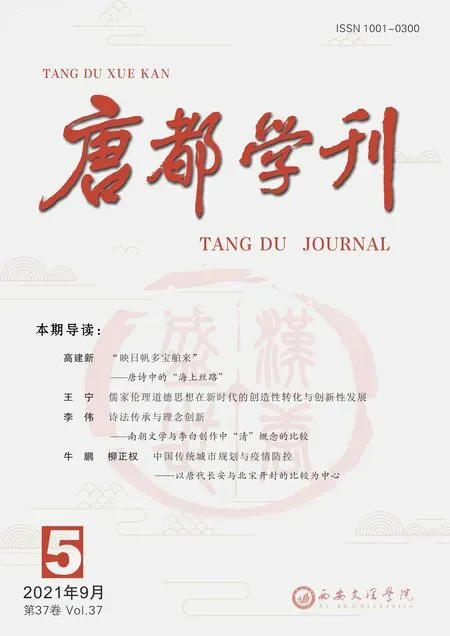中国传统城市规划与疫情防控
——以唐代长安与北宋开封的比较为中心
牛 鹏,柳正权
(武汉大学 法学院,武汉 430072)
柳正权,男,湖北钟祥人,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法律史、法律文化研究。
中国古代疾疫多发,早在殷商时期就有“疾年”的记载,此后文献中屡有“疫”“大疫”“疠作”“时疫大行”等记录。唐宋虽是中国古代瘟疫的低发期[1],但也未免疾疫侵扰之苦。邓拓先生在《中国救荒史》一书中认为唐代疫灾次数有16次,宋代有32次[2]17、20。张剑光先生在《三千年疫情》中认为这一统计遗漏是十分明显的,唐代明确标有时间的疫灾不下于20次,宋代有51次,其中北宋22次,南宋29次[3]127、196。这些研究均以宏观视角考察了唐宋时期的疫灾,揭示了疫灾发生的频次、时空规律等,还原了当时的疫灾情况,但缺乏针对具体城市的微观考察。唐代长安与北宋开封作为国家当时的政治和经济中心,也有多发之疫灾,史料记载的详细及遗存的丰厚为全面梳理两地疫灾发生频次及其危害提供了可能。故本文依托相关文献对其进行全面梳理、比较,分析两者之间差异的原因,并进一步讨论城市规划与疫情防控之间的关系,以期能为当前城市规划工作提供借鉴。
一、唐代长安与北宋开封疫灾频次与危害的比较
(一)疫灾发生频次的比较
关于唐代长安与北宋开封疫灾发生的次数,不同学者的统计不尽相同。首先,就唐代长安疫灾发生的次数,陈丽认为唐代史料中有关瘟疫的记载始于贞观十年(636)终于大顺二年(891),255年间共发生21次,其中与长安有关的4次[1]。龚胜生认为唐代发生过疫灾35次,其中与长安有关的5次[4]。另有些学者如李曼曼、郑秋实等统计认为唐代发生疫灾四十余次,其中与长安有关的5次[注]相关研究可参考李曼曼《唐五代瘟疫与社会研究》,安徽师范大学2006年硕士学位论文,第8—9页;郑秋实:《唐代疫灾防治研究》,中央民族大学2012年硕士学位论文,第8—13页。。其次,就北宋开封疫灾发生的次数,学界统计差异也较大。陈丽认为两宋共发生疫灾15 次,与北宋开封有关的为5次[1]。龚胜生认为北宋时期有记载的疫灾年份59个,其中与开封有关的12个[5]。邱云飞认为北宋时期发生瘟疫14次,其中开封占6次[6]。韩毅认为两宋共发生204次疫病,其中发生在开封的占27次[7]。包伟民教授认为,北宋开封大范围疫情时有发生,《宋史》《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992至1127年间的“京师大疫”有十次之多[8]779。
我们认为,所谓疫灾是指瘟疫流行所致的灾害,应是传染性疾病在一定范围内大面积传播,对人类健康和生命造成严重危害的疫情。史书中记载的疫情一般都是比较严重的,故本文对疫灾的统计以史料有明确记载为依据。在史料范围上,为保证记载的准确性,主要以正史和方志记载为依据,以政书、类书、个人文集、笔记小说等为佐证或补充[注]有研究者指出,中国古代疫灾记录系统大体包括四个子系统:一是正史记录系统,二是方志记录系统,三是档案实录系统,四是其他记录系统,如政书、类书、个人文集、笔记小说、医书档案等。参见龚胜生《中国疫灾的时空分布变迁规律》,载《地理学报》2003年第6期。。统计发现:唐代历289年,长安有明确记载的疫灾共发生5次,平均约58年一次。另需说明的是,五次疫灾之中,有两次均发生于公元682年,一次在六月,一次在冬季,或可认定为同一场疫灾。北宋历167年间,开封有明确记载的疫灾共发生14次,平均约12年一次,且经常连续数年大疫不止。比如在公元992年、994年以及公元1060年、1061年、1064年、1065年开封都曾连续发生疫灾(见表1、表2)。据此,根据笔者之统计,北宋开封疫灾发生的频次远高于唐代长安。

表1 唐代长安疫灾情况统计表
(二)疫灾造成危害的比较
史书中关于疫灾造成危害的记载虽比较简略,但从这些简略的记载中我们亦可感知当时疫灾横行给城市生活造成的惨状,特别是北宋开封的疫灾危害要明显大于唐代长安。唐代长安的五次疫灾除公元682年发生的两次疫灾造成较多人口死亡外,其他三次疫灾所造成的危害并不大。比如公元700年和707年发生的两次疫灾,范围自京师至山东,但造成人口死亡不足千人,除去死于饥饿之人,真正在长安死于疫灾的人口数或不足百人。公元636年发生在关内和河东的疫灾,史料仅记载“大疫”,但并未具体描述其危害。
与之相比,北宋开封的疫灾危害明显更重,“疫死者众”“百姓疫死”“死者甚众”“病者比屋,丧车交路”“疫死者几半”等记载触目惊心。淳化三年(992)五月开封的疫灾“疫死者众”,淳化五年(994)六月开封再次出现大疫,虽然具体后果史书没有记载,但从宋太宗得药方后慌忙派遣医官煮药分发来看,疫情应该是比较严重的。至和元年(1054)正月,汴京大疫。韩琦在《安阳集》中记载此次疫情“时疫暴作,民中其疾者,十有八九”。宋仁宗“碎通天犀和药以疗民疫”,同时在二月正式下诏:“乃者调民治河堤,疫死者众,其蠲户税一年,无户税者,给其家钱三千。”[9]嘉佑二年( 1057 )夏,京师旱疫。欧阳修在致汝州友人的信中描述“今夏京师大热,疾疫尚未衰息。”韩维也描述此次疫灾称:“京兆府暑甚,疫,人病多死。”即使在北宋末年,开封城仍不时有疫病传播且危害严重。钦宗靖康二年(1127),金兵将开封城团团包围,城内外交通隔绝,运输中断。由于大批人口被围,本就狭小的京城卫生条件更加恶劣,“城中疫死者几半”。徐梦莘在《三朝北盟会编》中描述此次疫灾对太学诸生的影响称:“城中太学自城围闭之后,诸生淡食,多有疾病,迨春尤甚,日死不下数十人,七百人中,死亡者三之一。”由此,疫灾对北宋开封造成的危害之大可见一斑。

表2 北宋开封疫灾情况统计表
(三)两者之间差异的原因
通过上述梳理、比较发现:相比北宋开封,史料记载唐代长安的大规模疫灾明显较少,且造成危害也更小[注]有研究者在疫灾地理学研究中将北宋开封列为一级疫灾中心,可见开封疫灾发生之频繁。参见龚胜生、刘卉:《北宋疫灾地理研究》,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1年第4辑,第22—34页。。那么究竟何种原因导致两者之间的差异?学界对此主要有三种解释:首先,有学者认为北宋开封疫情记载增加的原因主要是史料遗存的丰厚和文本叙事面增宽的结果。比如于赓哲教授认为唐代的文献是精英士大夫阶层的文献,是“城市的”文献,而宋代虽然城市化程度比唐代大为增加,但其文献却有更大的涵盖面,这全拜印刷术的普及和国民普遍教育程度的提高以及地方治史风潮的兴起,所以宋以后史料更为详细,也更多地关注政事、军事以外的社会事件,疾病记载日渐频繁[10]。其次,有研究者认为北宋开封疫情增加的原因与人口密度、流动性、居住环境以及生活习惯的变化有关。比如梁赓尧先生认为宋代疫病容易流行与城市卫生环境恶化有关,而卫生问题的产生又与当时城市人口大量增加密切相连[11]。包伟民教授也认为城市人口密度的增加以及卫生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导致疫病流行[12]。最后,也有学者关注到城市布局与疫情流行之间的关系,认为坊市制度的解体使疫病流行变得更加容易,导致北宋开封疫情多发[13]。
上述解释各有道理,虽然一方面文献记载缺失或报灾制度不完备固然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对唐代长安疫灾发生频次与造成危害的统计,但却不能否认客观上唐代长安的疫灾发生频次与造成危害要低于北宋开封。另一方面北宋开封与唐代长安在自然环境、人口密度、流动性等方面差异并不大,人口密度、流动性、居住环境以及生活习惯变化的理由难以完全成立。具言之,首先在自然环境方面,唐代长安与北宋开封的自然环境并无明显差异。就空间维度而言,唐代长安今指陕西西安,北宋开封即今日河南开封,两地相距约500千米,空间上的距离尚不足以使自然环境包括气候、水土等产生明显差异。就时间维度而言,唐代长安与北宋开封在建都时间上仅相距五十余年,时间上的跨度也不至使气候、水土等自然环境迥异。因此,无论从空间维度还是时间维度看,唐代长安与北宋开封在自然环境方面的差异并不明显。即使两城市之间存在细微差异,也不足以对疫情的发生与传播产生影响。其次在人口密度方面,唐代长安与北宋开封均为百万人口的大城市,人口密度较大。关于唐代长安和北宋开封的人口数量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重要话题,不同学者对人口总数的估算差异较大,因此笔者采学界通说之观点。唐代长安人口数量以持百万人口说者最众[注]这一观点20世纪90年代以来不断受到学者的质疑和挑战,他们的考证细腻,推算严谨,其研究方法和视角值得重视,相关研究成果综述可参见张天虹:《再论唐代长安人口的数量问题——兼评近15 年来有关唐长安人口研究》,载于《唐都学刊》2008年第3期。,考古勘查实测表明唐长安南北长8.6千米,东西宽9.7千米,周围共36.7千米,面积为84平方千米[14]。故唐长安城的人口密度约11 905人/平方千米。关于北宋开封,包伟民教授在《宋代城市研究》一书中估算开封新旧城区内大致有58万人,与城区面积53平方千米相对照,则人口密度为10 943人/平方千米,即使在北宋后期人口密度有一定的增长,也在12 000—13 000人/平方千米之间[8]749。因此,在人口密度方面,唐代长安与北宋开封相差不大。最后,在人口流动性方面,唐代长安与北宋开封都是国家当时的政治和经济中心,人口流动十分频繁。这一点可由流动人口在人口总数中所占比例得到证明。关于唐代流动人口,韩愈曾在上书唐德宗的《论今年权停选举状》中认为“都计举者不过五七千人,并其僮仆畜马,不当京师百分之一。”[15]在此次上书中,韩愈为反对停举可能对选举人群体所占比例有所保留,但也承认仅选举人群体占唐代长安人口总数的比例可能已达1%。此外,唐代的流动人口还包括进京游历的士人,地方政府派遣的进京使臣以及驻京机构人员,承担运输、建设任务的各地民夫,涌入城市的私营商人和手工业者,短期进京探亲的家属,流连京师的外国商人、使团、留学生、游方僧道等[16]。与之相比,北宋开封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流动人口数量或许更多,但在各学者的估算中所占比例也多在1%~3%之间。这一比例虽略高于唐代长安,但却并非影响疫情发生和扩散的决定性因素。综合上述分析,我们认为,城市布局的变革对疫灾发生频次与造成危害的影响不可忽视,但学界对其论述却不够深入[注]综观学界已有研究,笔者仅见于赓哲教授的相关著作中论及城市布局对疫病流行的影响,相关研究成果可参考于赓哲:《唐人疾病观与长安城的嬗变》,载于《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期,第47-57页;于赓哲:《唐代疾病、医疗史初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00-216页;于赓哲:《中国中古时期城市卫生状况考论》,载于《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5年第3期;于庚哲:《从疾病到人心——中古医疗社会史再探》,中华书局2020年版,第114-116页。,尚有进一步讨论之空间。
二、分区规划思想的变革与疫情防控
为维护封建礼制和等级秩序,中国传统城市规划一直遵循分区规划的思想,并为后世所传承。《周礼·考工记》载“左祖右社,前朝后市”是最早关于城市分区规划的规定。春秋时期,管仲赋予城市分区规划新的内涵,《管子·小匡》中提出:“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不可使杂处,杂处则其言哤,其事乱。是故圣王之处士必于闲燕,处农必就田野,处工必就官府,处商必就市井。”此后,分区规划思想一直延续至隋唐时期,并在唐长安城的规划与建设中被发展至巅峰。具体而言,在分区规划思想指导下,唐长安城的布局分为宫城、皇城和外郭城三城[17]16,其中宫城主要为城市的政治功能空间,皇帝在此居住;皇城为政治功能空间之辅助,主要为各类重要衙署区[注]有研究者指出,长安城皇城内没有民居,除外朝和祖社外、主要为官署。计有六省、九寺、一台、四监、十八卫。东宫官署一府、三坊、三寺、十率府,亦均置皇城中。参见李瑞:《唐宋都城空间形态研究》,西安地图出版社,2006年版,第73页。;外郭城为居住功能空间和商业贸易功能空间,以坊里为区域单位,共有109坊,分三种类型。首先是市坊,长安东西两市分置于皇城左右前方,各占两坊之地,为城市商业贸易功能空间;其次是以居住为主的坊里,在外郭城中占地面积比例最大,为城市居住功能空间;再次是功能单一的坊里,如个别大型寺院、园林、军营校场等独占一坊之地(见图1)[注]关于唐长安城各坊的研究,可参见杨鸿年《隋唐两京考》,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07-292页。杨鸿年《隋唐两京坊里谱》,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通过这样的城市布局,唐长安城实现了严格的功能分区,政治功能空间、居住功能空间和商业贸易功能空间三者分割,互不打扰。功能分区的城市规划虽非为疫情防控而设,但对于疫情防控而言:一方面,居住区与市场交易区分离的做法可以避免细菌或病毒感染,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疫情发生的可能;另一方面不同类型的居住区分离,限制了人口市内流动,即使发生疫情也可避免大范围传播,客观上有助于疫情防控。

图1 唐代长安城平面图图片来源:《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版,第721页。
宋代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一方面居住区与市场交易区的分离难以满足居民日常生活需要;另一方面,由于商贾地位的提高,王公贵族和平民百姓的居住区也再难明显划分,从而导致城市分区规划的思想开始发生变化。在新的规划思想指导下,北宋开封的城市布局不再严格实行功能分区,逐渐演化成坊市混杂,出现复合功能空间。具体而言,北宋开封的城市布局虽依然分宫城、内城和外城三层,但已突破了城市功能空间划分的限制。一方面,内城的城市功能高度集中,不仅体现都城的政治功能,还附载着经济、军事、宗教、居住等其他配套功能。另一方面,北宋开封的商业功能空间突破了东市、西市的固定空间限制,而是流动地弥漫于街巷、桥头、城门乃至寺院等城市空间[18]。这两方面的变化导致北宋开封在城市规划上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一改传统坊市分设制度,不再严格限制分区,复合功能空间开始出现。复合功能空间的出现使人口的市内流动更加频繁,虽有利于商品流通,便利生活,但一旦发生疫情就会迅速扩散,不利于疫情的预防与控制。
三、封闭坊市制度的解体与疫情防控
分区规划思想的变革也推动了封闭坊市制度的解体。唐代以前,城市规划实行封闭坊市的管理模式。至宋代,随着商品经济发展,封闭坊市制解体,开放街巷的管理模式形成。日本学者加藤繁早在1931年发表的《宋代都市的发展》一文中指出,传统坊制与市制的崩溃是宋代都市发展的重要现象[19]。申言之,传统坊制与市制的崩溃并非简单城市布局的变化,更是城市管理模式的变革。若将城市管理分为社会管理与市场管理两部分,那么坊制构成了社会管理的根基,市制则奠定了市场管理的框架[20]。因此,关于封闭坊市制度的解体可分坊制与市制两方面叙说。
(一)坊制与社会管理的变化
传统坊制构成了唐代长安社会管理的基础,其起源可追溯至奴隶制时期的人口聚居体“邑”。西周金文之中开始出现“里”的称谓,东汉后期“坊”的名称也开始出现,此后“里坊”[注]关于里与坊的关系,学界有不同的观点,有研究者认为里和坊是两种不同的组织系统;有研究者认为里即坊。笔者赞同里即坊的观点,只是坊的出现多是针对城市而言,而里多针对乡村而言,其本质都是中央集权下地方基层行政单位。参见杨鸿年:《隋唐两京考》,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07-209页。成为负责对居民实行监管、宵禁、赋役征收的基本行政单位,至唐代发展至顶峰[注]关于坊里制起源的考察,可参见朱玲玲:《坊里的起源及其演变初探》,载于《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2期。。唐代长安被认为是传统封闭坊制管理的代表,在具体管理上采取以下四个方面的措施:
第一,坊与坊之间设墙隔离,禁止翻越坊墙;封闭坊制最为突出的特点是坊墙的设置,先秦文献之中就有关于坊墙设置的记载。《诗经·郑风·将仲子》载:“无逾我里……无逾我墙”,表明先秦时期里与里之间已有严整的墙垣系统。唐代长安城的坊墙设置更加规范严整,考古发掘表明,长安城各坊的墙基厚度大致相等,都在2.5—3米之间[17]215。同时,翻越坊墙的行为也为法律明确禁止,秦律已将“越里中之与它里界”的行为规定为犯罪行为,唐律进一步明确“翻越市、坊墙垣者,责杖七十”。第二,坊墙设坊门并禁止擅自向街开门;坊的四周有围墙隔离,围墙上设有坊门,以供坊内居民之出入。同时,为避免坊内居民擅自出入坊内,除三品以上高官之住宅及坊内三方路绝者外,法律禁止向街开门,皆由坊门出入[注]《唐会要·街巷》载:“非三品以上,及坊内三绝,不合辄向街开门。”。第三,设官吏严格看管坊门;封闭坊制下对坊门的看管十分严格,多设官吏专职看管。《管子·立政》载:“审闾,慎筦键,筦藏于里尉。置闾有司,以时开闭。”要求细心看管坊门,同时设置官吏按时开闭坊门。唐代长安亦设坊正掌管坊门钥匙,同时设坊角铺,由卫士、彍骑分守。第四,定时开闭坊门实行宵禁;唐长安城在坊门管理上还要求定时开闭坊门,“五更开坊门,黄昏闭门”,闭门之后坊内居民不得出入,街道也禁止行人,违反这一规定的人将受到唐律制裁[注]《唐律疏议》载:“令其主司定罪,庶人杖以下决之;官吏杖以下皆送于大理”“坊正市令非时开闭坊市门者,处徒二年”。。上述管理措施的目的并非在于防疫,有研究者指出其目的或是在于加强治安管理减少犯罪以及控制居民便于赋役征收两方面,但就效果而言,这些措施从根本上限制了人口市内流动,客观上有助于预防疫病的发生与扩散。
至宋代,封闭坊制开始解体,代之而起的是按街巷分地段规划的开放坊巷制。北宋开封作为开放坊巷制的代表,相比唐代长安,在坊制管理方面的变化集中在:第一,取消坊墙设置;坊里周围不再设围墙,而是呈开放型结构,各坊建有“坊表”,在“坊表”上书写坊名以作区分。第二,宵禁制度崩溃;随着坊墙的取消,坊门消失,宵禁制度也随之崩溃。这些管理措施的变化固然更加满足商品经济发展需要,也在一定程度上方便了居民生活,但从疫情防控的角度考虑,却也更便于疫情的传播与扩散。
(二)市制与市场管理的变化
唐宋之际城市市场形态的演变是学界长期关注的话题,自20世纪30年代日本学者加藤繁的开创性研究以来,关于中国传统城市市场形态由唐代封闭市制转变为宋代开放街市的认识已成为学界共识。唐代长安的市场管理延续传统市制精神,集中体现于三个方面:一是坊市分离,二是市场官设,三是严格监管。首先就坊市分离而言;唐代长安延续了封闭结构的市制以及东西两市的对称布局,将市置于特定区域,并与居民区分离。文献记载和考古挖掘显示,唐长安城的东西两市各占两坊之地,四面各开两门,“市内四方奇珍皆所积集”。其次,就市场官设而言;与坊市分离相对应,市场的设立与关闭必须由政府决定。比如唐中宗景龙元年(707)曾下敕令明确非州县之所不得设市。最后,就严格监管而言;市场官设的前提下,严格监管本就是应有之义。唐代设市令专职市场管理,并配有市丞、市佐、市史、市师等辅助管理。《唐六典》载:“京、都诸市令掌百族交易之事,丞为之贰”《唐会要》亦载:“大都督府市令一人,掌市内交易,禁察非伪,通判市事。丞一人,掌判市事。佐一人,史一人,师三人。”
宋代,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封闭市制崩溃。一是为满足居民生活需要,封闭的市制为开放的街市所取代;二是由于城市人口已溢出城郭,形成新的聚居区,城郭周边形成非官设的“草市”;三是宵禁制度崩溃,开封城内形成热闹非凡的“夜市”;四是“草市”与“夜市”的存在导致北宋开封的市场缺乏监管[注]关于宋代市制的变革,前人研究成果颇多,比较有代表性的可参见宁欣《唐宋都城社会结构研究——对城市经济与社会的关注》,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成一农《古代城市研究方法新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传统市制这些方面的变革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其积极意义值得肯定,但从疫情防控的角度看,开放市制并不利于疫情的预防和控制。
四、当前城市规划工作之借鉴
正如美国著名历史学家麦克尼尔(William .McNeil)在其著作《瘟疫与人》中指出的:“传染病在历史上出现的年代早于人类,未来也将会和人类天长地久地共存。”[21]如何防控传染病传播,避免疫灾发生是人类要关注的永恒话题。城市规划作为疫情防控的重要一环,在疫情防控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好的城市规划可以有效避免疫情发生与传播。从唐代长安与北宋开封的比较看,北宋开封疫灾多发且造成危害也更大,其根源或许就在于城市规划体制的变革。当然,由于史料记载的欠缺,关于疫灾发生频次过高是否是坊市结合的规划体制引起,疫灾危害的扩大是否是封闭坊制崩溃的原因造成等问题均缺乏明证,从而导致证成有很大困难。但从这种比较中我们仍可推论,城市规划体制的变革确实对疫情的发生与扩散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可为当今城市规划与建设提供镜鉴。
具体而言,当前城市规划工作可借鉴中国传统城市规划的经验,在城市规划中平衡好两对关系。
第一,城市功能分区与复合功能区建设之间的关系;通过唐代长安与北宋开封的比较发现,分区规划并划分不同的功能区,减少人员的无序流动,可在一定程度上预防传染病的发生与传播。因此,当前城市规划应将疫情防控纳入规划之中,考虑不同历史时期城市功能分区的内容和特点,顺应不同历史时期的要求,提出与之适应的城市功能分区规划,在城市功能分区与复合功能区建设之间寻求平衡,特别是对可能造成传染病发生的工业区、市场交易区等应严格与居住区分开。
第二,开放街区与封闭住宅小区建设之间的关系;2016年颁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提出,新建住宅要推广街区制,原则上不再建设封闭住宅小区。然而,封闭住宅小区固然存在交通不便、资源利用率低下、居民出行不便等问题,但开放街区在治安管理、交通安全等方面也存在诸多不便。同时,唐代长安与北宋开封的比较也表明,开放街区管理显然并不利于疫情防控。在2020年新冠病毒暴发期间,对小区实行封闭管理甚至一度成为应对疫情的主要举措。因此,城市规划在开放街区建设的同时也应考虑做好公共卫生危急时刻住宅小区的封闭隔离,平衡好开放街区与封闭住宅小区建设之间的关系。
第三,结合当前城市规划管理工作的实际,唐长安城实行坊与坊之间设墙隔离的做法显然不具有可操作性,但或可借鉴其经验通过设立“卫生隔离带”等方式实现城市不同功能区之间、居住区之间甚至各小区之间的隔离,建立控制疫情的空间隔离带。前世不忘,后世之师。以史为鉴,择善而从。从历史的经验中汲取智慧,完善我国城市规划中的防疫功能,是我们在抗疫斗争中获得的最宝贵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