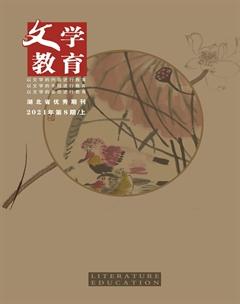林语堂翻译理论中的道家精神
周可悦
内容摘要:林语堂是中国著名的语言学家,翻译学家,其翻译代表作品有《老子的智慧》即《道德经》,《浮生六记》等。在林语堂的翻译巅峰时期-旅居美国时期中,通过中西方文化差异的比较,在博览中国传统优秀文学哲学作品的基础上,坚定了要让西方人不仅要知道更要“读懂”中华文化的目标,希望能通过翻译将中国优秀传播文化辗转至西方,并将此作为自己的翻译动力,传播了许多经典哲学思想和中国理念,其中就包括以老子、庄子为代表的道家精神。林语堂一生都在提倡道家精神,并将其作为自己的生活理念。为了能够对林语堂的翻译作品翻译思想有更深刻的理解,我们必须要对其翻译作品中所体现的道家精神进行分析总结,体会其翻译作品所传达的道家思想,使更多中西译者收到启发。
关键词:林语堂 道家精神 中西影响
林语堂曾言“老子的隽语,像粉碎的宝石,不需装饰便可自闪光耀。”可见,道家精神在林语堂心中就像自闪光耀的粉碎的宝石,其地位不可被替代。林语堂之所以一生都崇尚道家思想,离不开时代背景,家庭环境,个人经历这四个方面的影响。
1925年中国人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政府内部存在严重腐败,国内革命形势高涨,越来越多的人主张打到段祺瑞执政府,林语堂就是其中之一。在此时期林语堂与周作人共同主张“费厄泼赖”(Fair play),主张在新旧矛盾冲突中找到一种力量的平衡,不要穷追猛打,不要过于固执执着于结果,对失败者不攻击。但是这一理念被鲁迅等人所抨击,鲁迅为此还写以《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进行抨击。由此,林语堂深刻意识到西方文化中的“民主”与“自由”等先进独立思想在中国还无法实现。紧接着,1927年“四一二”政变与1933年6月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副会长杨杏佛遭国民党特务袭击重点身亡事件的相继发生,更让林语堂希望破灭,厌倦革命,从而选择去脱离革命,逃避社会,回归自然,追随道家思想的生活理念。同时,当时社会上流行着文化复古主义,让林語堂对中国传统道家文化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分析,并坚定传播道家思想的决心。
林语堂曾言“在造成今日的我的各种感染中,要以我在童年和家庭所深受者为最大。”林语堂出身于一个相对贫苦的家庭,其父林至诚是一个乡村牧师,是林语堂最珍贵的启蒙老师。即使当时家庭环境贫苦,但是其父坚持让林语堂学习西方知识,拓宽眼界,这给林语堂在日后研究西方文化决心从事翻译工作为西方翻译到家道家文化打下基础。在童年经历中,令林语堂印象深刻的是高山。年轻的林语堂总喜欢高攀上高山,从高山顶上俯瞰人群,感叹人类的渺小,对自然产生敬畏之情。这一思想与道家的自然思想不谋而合,并让他在成年后形成了所谓的“高地人生观”。“高山”在林语堂心中不仅是一种自然景观,而已内化为一种符号,一种象征,甚至是一种宗教信仰的砝码,成为影响林语堂一生的东西。[1]
一.林语堂翻译作品的道家精神
1.崇尚自然
林语堂欣赏自然的美丽,崇尚生命的可贵,赞扬安静闲适的生活,这是他致力于文学的原因,也是他接受道家理念的基础。[2]传统道家主张要顺应自然,遵循自然规律,以自己的存在为前提,强调万物的变化性,并强调朴素辩证法。而林语堂在自然思想的基础上更强调生命的可贵性,在生命中痛苦与快乐是并存的,强调自身在心理上的舒适与安逸,不追逐名利,不给自己施加过分压力。他认为“人生这种生活的真享受的目的,大抵不是一种有意的目的,而是一种对人生的自然态度。”[3]在作为具有“西洋性”的中国近代文学性质小品文《浮生六记》的译文中,林语堂也在第六章养生之道的原文基础上进行了自己的理解,并在翻译过程中提出“the type of gaiety that bears sorrow so well”,最悲惨同时也可以被认为是最活泼快乐的生活方式就是善处忧患的活泼快乐的生活方式。在《道德经》的译文中,更突出自然的理念。在《道德经》的第二章中老子提出“万物作而弗始”,要求人们要听任万物自然的兴起而并为其创始,强调要让万物自己生长兴起不加以干预,在林语堂的译文中,林语堂将“弗始”翻译为“do not turn away from them”,我们都知道“turn away from”指的是远离,可见,在林语堂心中始终要顺应自然,亲近自然是更重要的,要在感受自然的神奇魔力,充分发挥自己对于自然的想象力,并将自然的理念融入日常生活中。
2.主张“为我”思想
林语堂曾言“在一切人类的历史活动中,我只看见人类自身任性的不可捉摸的难预测度的选择所决定的波动和变迁。”[4]传统道家提倡不以天下为根本的原则,并强调国家统治者不能损害个人利益,要减少对私人活动的干预和控制。作为西方的重要文化特征,个人主义并非是利己主义和以自我为中心,其强调的是自我意识的重要性和独特性,强调将自我价值社会中的体现。在中国五四运动“人的解放”思想运动高潮的时代背景下,深受西方文化和道家文化影响的林语堂也进一步提出了精神自由,个人不可被替代,个人具有无限可能等思想。在林语堂的译作种,他将“情理”解释为“Reasonableness”,这个单词在字典中有两个意思。其中一个是“the state of having good sense and sound judgement ”还有一个是“goodness of reason”.林语堂很好地把握了情和理的关系,他不单单强调reason,即客观存在的不可改变的宇宙规律和事实,还强调sense,即人心理所想所感知的情愫的重要性。只有将情与理相结合才能更好地认识事物,寻找价值。林语堂是把“情理”放在人生之根本,即只有懂“情理”的人,才是最贴近人生和最有教养的人。[5]
3.“上善若水”与“返璞归真”
在林语堂的翻译作品中存在一种“文化补偿”的现象,我认为这种现象体现出林语堂翻译中的阴柔一面,也就是注重归化,将译文翻译得更加富有“情感”,更具有细腻的美感。在翻译作品中,译者不得不基于作品本身,以作者角度将原文知识转化为另一种语言,那么林语堂则以一种文化补偿的形式,既具体阐释作者思想使读者更易读懂,也在一定程度上在不改变原译作基础上表达自己的思想。文化补偿作为一种思想交流过程中信息传递的一种方式,采用语言变通与补充等方式,将原文的信息意思传递给外国读者,其实用性和有效性得到很好的证明。在中英翻译中,林语堂常常在翻译完整整句话之后用()来补充说明自己的见解,帮助读者更有效的接收信息。例如在《道德经》的第二十八章中,林语堂将 “知其白”译为“he who is conscious of the white(bright)”, 在字面意思翻译“白”这一字为“white”之后,林语堂又在其后添加了“bright”一词,意思是明亮,帮助外国读者更好地理解“白”这一词的含义(明亮单纯的状态)。通过在单调的本义后加以自己理解的词句,也无异于是一种回归原文意义的返璞归真的行为了。
二.道家思想的西方传播
林语堂先生通过对《道德经》《庄子》等代表道家思想的作品的翻译,使西方人更明白道家中“自然”“万物”“无为”等思想的真实含义,不止浮于表面,并将其融入自我的生活中,寻求自我的真正价值。其次,林语堂先生用道家精神的传播架起了中西两方文化交流的桥梁,在中西文化碰撞交流下,使中西文化间的距离拉近,在保存两者特色的同时结合西方民主自由独立思想的影响以及许多外国人无法深刻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情况,林语堂先生将道家思想的核心内容以西方思维呈现出来,使更多外国人对道家文化有了更深刻更清晰的认识。他希望西方社会减少对东方的敌意和误解,纠正西方文化对东方的误解,降低中西方文化差异。[6]
通过对林语堂先生在翻译作品中所体现的“为我”“自然”“上善若水,返璞归真”的道家思想的分析,以及其对中西文化交流的影响,我们可以深刻了解道家文化在林语堂先生的生活与文学创作中的突出作用,通过传播道家思想,更让更多西方学者理解道家思想,体会中国传统文化,并使更多中西翻译者受到启发,秉承传播中华优秀文化的宗旨,产出更好的译作供中西学者借鉴交流。
参考文献
[1]彭英艳.时代的浇铸 心灵的指向[J].邵阳学院学报,6(3):116-119.
[2]叶雯昕.弦论儒家与道家对林语堂思想的影响[A].文学评论.现当代文学, 2136(2018):43-44.
[3][4]林语堂.中用哲学,生活的艺术[M].华艺出版社.
[5]李喜华.论道家文化对林语堂“为我”思想的影响,22(3):121-126.
[6]林语堂.论翻译[M]//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7]秦楠.目的论视角下林语堂汉译英翻译策略研究[J].联运光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9(1):43-46.
(作者单位:中国计量大学人文与外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