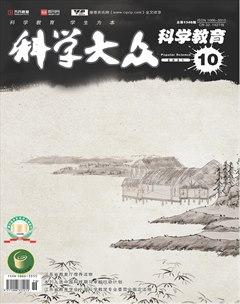《一千英亩》的生态空间批评解构
王雷雷
摘 要:本文从文学地图叙事、时空体叙事和生态女性主义空间三个交叉研究热点切入简·斯迈利的《一千英亩》,帮助读者更好地在文本与理论层面的实践中解读这部小说。
关键词:一千英亩; 生态批评; 空间批评; 文学地图; 时空体; 女性主义; 叙事
中图分类号:I71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3315(2021)10-106-002
近年来,在文学批评与文化研究领域内“空间”作为一个研究术语成为人文社科研究的重要文化议题。尤其是自20世纪后半叶起,西方学术界自地理学学科内部开始经历了一场“空间转向”(spatial turn),研究者们逐渐将批评兴趣转至“空间”本身,并将之看作一种重要的解读范式【1】。由于“空间”的概念本身具有很强的适应性和契合性,几乎可以和绝大多数的文学批评思潮进行交叉研究,所以空间批评理论在文学界应用越来越广泛,并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
简·斯迈利的畅销小说《一千英亩》是1992年美国普利策奖和国家书评人协会奖的得主,被批评界美誉为美国中西部的《李尔王》。从一开始在数学标题(一千英亩)中,斯迈利就以她的数字、直径、尺寸、限制和最重要的对空间的独特感知向读者和评论家提出了挑战。作者的感知明显超过了农场长度和宽度的肤浅概念,有着独特的空间体验。本文就以这部小说为例,结合西方空间批评领域的新动向,从文学地图叙事、时空体叙事和生态女性主义空间三个交叉研究热点切入,帮助读者更好地在文本与理论层面的实践中将生态批评和空间批评理论研究结合起来。
1.文学地图叙事
从文学界到科学界,人们一直习惯于以时间的线性顺序来阐述故事和定位事件。近来学界才开始转向关注基于空间结构的阐述模式,将叙事学(narratology)与空间化的讲述模式联系起来,衍生出一系列关于空间叙事理论(spatial narratives)的研究,尝试从叙事学角度理解时间与顺序的意义生成。弗兰科·莫莱蒂(Franco Moretti)在文学批评领域采用了文学地图来探寻空间化叙事的可能性。他在《图表、地图、树图:文学历史的抽象模型》一书中提出可以采用大数据可视化方法来解读文学作品中以地图、图表等空间形式出现的叙事结构。莫莱蒂给出了两个基本点:首先,地图“突出了文学形式的空间边界(place-bound)性质:每一种形式都有它獨特的几何形状、边界、空间禁忌和最喜爱的路线。其次,地图揭开了叙述的内在逻辑:一个由情节组合在一起并自我组织的符号域。文学形式是两种同样重要的力量相互冲突的结果:一种来自外部,一种来自内部。文学史惯常的、本质上唯一真正的问题是社会、修辞及它们的关系”【2】。
小说《一千英亩》一开篇就是这段话:“在686号县道上以每小时六十英里的速度,你可以在一分钟内驶过我们的农场。686号县道向北和卡博特大街相交,形成一个丁字路口。卡博特大街也是一条乡间的柏油大道,唯一不同的是它向西五英里纵贯卡博特镇......沿着泽布伦河的曲线继续延展三英里......地球毫无疑问是平坦的。”【3】
作者好像在绘制地图,她使用了数字、长度、角度和形状等数学和几何术语间接地告诉我们农场的长度和宽度:知道被隐喻为李尔王的农场主拉里梦寐以求的农场大小是1000英亩,长度和宽度需要通过使用剩余的可用细节来计算。长度是由以规定的速度(每小时六十英里)在农场前经过的时间(一分钟)决定的。这种对空间数学测量的强调在小说中一再出现;作者一开头就谈到了“我(吉妮)父亲拥有的六百四十英亩的广袤土地”,吉妮强调她最初选择的测量方法,指出“这辆(别克)车是六百四十英亩的精确测量方式,而车速使广袤的土地也变得渺小”。同时埃里克松一家的三百七十英亩土地被拉里所觊觎,因为这样“我们就能拥有从686号县级公路和凯博大街交汇处向外延伸的一整圈土地”,“一千英亩,就这么简单”。作者不断使用数学术语来比较大小和尺寸,一千英亩上复杂的社会关系被圈在这小小的地图上,拉里的霸权地位和野心在这里展露无疑,而三个女儿,特别是大女儿吉妮在地图中被边缘化,但又无法摆脱这张地图,和土地一样成为被剥削的对象。
数字话语还被用来描述意象,强调文本对象的视觉维度,在父亲拉里眼里,“整整的一片,六百四十英亩,贷款早已付清,什么钱都不欠了。这片黑色的土地平坦、富庶、松软,裸露于风雨之中,和地球表面任何一片土地别无二致。”而吉妮看到的是“水源毒化了,表层土壤毁了,机器越买越大”。起初吉妮“认为我们(和二妹罗丝)会在这一千英亩上相伴永远”。但“过去却在我脚下萎缩溶解化水,而在其中心的,变化得最厉害的就是罗丝”。通过使用表示颜色、形状、大小、位置的文字,作者绘制了一张生动的地图。她告诉读者,需要反复的精确观察才有权发表观点,而不能囿于囫囵的理解。
2.时空体叙事
巴赫金的“时空体”(chronotope)中强调“时间的标志要展现在空间里,空间则要通过时间来理解和衡量”。在时空体中,历史时间在特定空间中凝固静止,这个空间“充塞了时间,而且是狭义的历史时间,即过去历史的时间”(钱中文,1998:275)。作者一开篇就测绘地图,却得出了一个令人困惑的结论:即与科学家的发现相反,地球是平的。在这里,人们可能会困惑为什么作者复位了这种地心说。原文中过去时的was可能暗示了一个遥远的过去,在莎士比亚创作《李尔王》的时代,当时人们无疑认为地球是平的,任何人如果持有异议,就会经历伽利略的灾难性命运。因此,在一个群体中反对公认的事实(信念)是危险的,甚至是致命的。而斯迈利似乎在冒这个风险,试图挑战男性的统治地位。她的《一千英亩》是当代的《李尔王》,时间的嬗变使父女关系被重新解读:遥远的过去李尔王大女儿和二女儿为了父亲的领地露出种种丑恶嘴脸,伤透老父亲的心;小女儿则是正义的化身,为老父亲夺回领地。当代“李尔王”拉里的大女儿吉妮和二女儿罗丝却是被困在父亲一千英亩的土地上,伤痕累累,小女儿凯瑟琳背负着两个姐姐的殷切希望摆脱了父亲的控制在大城市安了家,却转过头来成为父亲对付两个姐姐的帮凶。斯迈利的文本叙事创造了一种挑战男权的阅读自然的方式,一开始自然空间和女性一起被禁锢在过去的维度,而女主人公吉妮要打破时空维度,和土地一起解放出来。
书中还提到“一分钟”的时间现在被呈现为一个非常巨大的空间,土地因为车速从广袤缩小到微不足道。谈及对空间的感知,坐在快速行驶的汽车上,一千英亩的确会变得无足轻重;但当时间线被拉长,涉及拉里祖孙三代人在这个空间中的探索和生活,狭小的空间也变得开阔和厚重,因为作者需要数百页文字才能告诉我们那个空间里到底发生了什么。时空体反映了小说世界中时空动态变化的节奏,斯迈利的小说可以从具体到抽象,构成一张张并置的地图,也可以通过时空的嬗变从抽象到具体,对那个空间上发生的事情(感知、思考和感觉)实时展示,反映女儿和妻子对父亲、丈夫和情人的复杂情感和现代农民对抗工业化的充满心酸的现实境遇。
时空体超越了肤浅的外观,提醒读者注意目力所及的层面下有着另一番天地:“当我还是一个稚龄学童,在学校里学习哥伦布其人其事的时候,不管老师怎么说,我总认为远古的文明自有其道理。地球仪也好,地图也好,都无法让我相信泽布伦县不是宇宙的中心。毋庸置疑,泽布伦县的地面确实是平的。在这里任何滚动的球体(诸如种子、皮球、滚珠之类)到最后必然会停下来。一旦停下来,它必然会扎根到厚达十英尺的表层土当中去。”。历史的凝固使小小的泽布伦县成为吉妮心目中宇宙的中心,女性的悲哀就在于被困在狭窄的、依赖的、私人的、生育的、家庭的、自然的劣位空间。
3.生态女性主义空间
空間与女性的交叉研究催生了女性主义地理学(feminist geography),其多样化研究中两个议题尤为值得关注。其一是空间对女性身份构建的重要影响。其二移动性(mobility)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概念。移动性是美国文学的深层结构之一,长期以来为男性所专有。男性可以在不同空间自由穿梭,而女性往往被束缚在有限的空间。提及哥伦布证实了作者的发现使命:吉妮最后空间意识觉醒,要完成从女性劣位空间到男性优位空间的跳跃,追求自由独立的人格。女性主义把女性身体和土地进行类比,并认为两者都被男性所利用。事实上,作者看透了美国男性对土地和女性的看法是如何反映了他们的空间意识:“他拥有这块土地”;她还提示男性拥有优位空间后衍生的权力秩序“农民们能根据农场的情形迅速猜测到其主人如何”,以及“农场的外观如何,取决于农场主的性格。”
此外,空间秩序的展现隐含着权力运作的模式。《一千英亩》对土地的看法粗看充满了美国的梦想,因为它把美国描绘成一个“开放的土地,为强大、雄心勃勃、自力更生的个人提供无限的机会,让他走上顶峰”[5]。但细读会发现这绝对是对美国梦的批判。它首先破坏了家庭和个人的幸福;其次它是纯粹男性化的,充满对女性的剥削。换句话说:“吉妮通过讲述她的农民祖先对价值所有权和不断增加生产的意识形态的坚持,通过反讽男性创造性暴力完成的国家建设的主流叙事,将土地和妇女被毒害和被迫缄默的缘由追溯到美国梦”[6]。作者一再暗示她希望找到新的探讨维度,解构传统的女性疆域,冲破空间束缚,实现独立自主的梦想。这可能是女性摆脱以性别歧视为基础的宗法社会的重要女权要旨,而宗法社会的支柱是将妇女作为土地对待。小说的中心陈述:“我认为,景观路两边所见向我揭示,目力所及的层面之下有着另一番天地”。作者把地球描述成平的是试图打破土地和女性被恶意对待的封闭圈,不希望“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农场”一直遭遇迫害。作为小说主人公和叙述者的吉妮想去别处安身,而不是回到男性主导的状态。但农场禁锢着她,使她无处可去。作者就安排她像种子一样,放弃线性运动而选择垂直向下发展,在深深的土层中扎根,探索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和看待世界的视角,找到生活的希望。
4.结语
像“会扎根到厚达十英尺的表层土当中”的种子一样,作者深入视野以下的空间,其主要目标是为被迫缄默的女性和被毒害的土地说话,赋予她们希望。从地形上看,她冒险进入了一层层的话语和土地,从“十英尺厚的表层土下”挖掘出了自然和人类的真相。生态批评常常承载着道德、警示和教益;经常为了有益于虚构的人物,在道德上具有启发性。空间叙事通常都会呈现被凝视客体的预期的力量;它发出的声音是可推断的、与心灵相通的;它产生的意义是预言性的”[7]。生态批评和空间批评的结合在未来将发挥愈来愈举足轻重的作用。
参考文献:
[1]马特.城市生态批评理论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
[2]Morett,F.Graphs,Maps,Trees:AbstractModelsforaLiteraryHistory[M]LondonandNewYork:VersoPress,2005
[3] SmileyJ.A Thousand Acres[M]New York: Ballantine Books,1992
[4]钱中文主编.巴赫金全集第三卷[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5] Slotkin, R.. Regeneration Through Violence: The Mythology of the American Frontier1600-1860[M]. Middleton, Connecticut: Wesleyan UP,1973
[6] Carden, Mary P. “Remembering/Engendering the Heartland: Sexed Language, Embodied Space,And Americas Foundational Fiction in Jane Smileys A Thousand Acres.” Frontiers,1997:181-202
[7] Cunningham,V.“Why Ekphrasis”Classical?Philology,102.1(Jan.2007):57-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