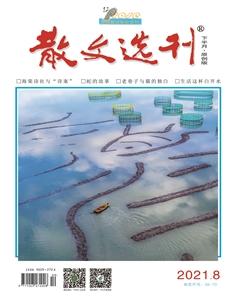老巷子与猫的独白
艾红
老巷子很老,瓦分不出是黑的还是灰的,瓦上住着的烟囱遍体投射着岁月的伤痕,砖块歪歪扭扭地罗列着。
那只猫,在老巷子白杨树底晒着太阳。流浪的猫随处可见,但这只波斯猫,与众不同,在别的猫翻捡垃圾桶寻找食物时,它却冷静地坐在树下,看着南来北往的人和车流走来走去。我以为它是有主人的,毛发干净,身上一尘不染,脖子上还戴着一个铃铛,眼神风清月明,气质很好。我远远地观察着它,不敢轻易靠近。我们互不打扰,都小心翼翼地端详着彼此。
这只波斯猫让我想起了小时候,家里住平房,也养了一只猫。它白天躺在窗台上晒太阳,在阳光里抓自己的影子,盯着我碗里的食物,像个跟屁虫一样跟着我。晚上趴在我的脚下睡觉,它顽皮的时候缠着我上蹿下跳,一次它打翻了我的墨水,我训斥了它一顿,晚上它竟然钻到帽盒子里睡觉。有一天,猫失踪了,再也没回来,母亲说,猫老了,回山上了。自此,我伤心了好长时间。老巷子能勾起我沉甸甸的乡愁,在我回忆的时候,波斯猫跳上一堵墙,果断离开,我望着它的背影眼眶湿润。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变得越来越敏感,那些生长在巷子深处的窄路、草木,粗糙的房子,简单的栅栏,还有架上的青豆,都会不由自主地把睡在我体内的乡情唤醒,更别说一只猫。
第二次遇到波斯猫的时候,是我到孩子所在的城市办事。办完事,在孩子家小住几天。孩子们还没下班,我心里惦记着那只猫。信步来到老巷子,波斯猫泊在一截儿矮墙上,毛发有点脏,铃铛还在,目光呆滞了许多。它瘦了,我转身在巷子里的小卖部,买了一根火腿肠,一个面包。拆了火腿封口,唤着“咪咪咪”,试图靠近它,波斯猫谨慎地看了我一秒钟,噌地跃上白杨树,不理我。我放下食物,躲在一边,偷看它的反应。不一会儿,波斯猫下了树,闻了闻石板上的食物,圆眼睛四周撒目了两下,用粉红的小舌头舔了舔火腿肠,然后抿了一口,继而埋头狼吞虎咽地吃起来,面包也吃得所剩无几。确定波斯猫是遭主人遗弃的,我慢慢走过去,轻声细语和它说话。吃饱了,在阳光下,它耐心细致地洗着爪子和尾巴,不反感我的存在,对我也温柔起来。巷子里行人很少,有几个下班的男女,步履匆匆,经过我们时,冷漠得毫无表情,心如灰白的天空,可见猫在老巷子里的境遇。
老巷子大多被天南地北的打工者租住,黄昏时分,总有南腔北调的对话声,暖风一样扑面而来。我问猫,你好吗?你也许和我一样都不属于这里,我是为了孩子,这几年差不多每个休息日我都贡献给了这里。周五的晚上,我坐一宿火车来到这里,周日的晚上再坐一宿火车回单位上班,不能休息,脑袋迷迷糊糊,还要处理日常工作。在这里,你和我的命运一样,都是天涯沦落人。
真想把你带回家,可是铁路不让。如果有缘,希望每次来到这里,你还在。现在,我只能为你买一些吃的,不能给你一个家,因为孩子住的楼房是租的。如果有一天,孩子有了自己的居所,我也退休了,如果你愿意,如果咱们有缘,我会给你买一个属于你自己的窝。回到家,就能听到你“喵喵”快乐的叫声,让快乐相互感染,缓解工作和生活上的压力。你看行吗?眼下,我和一只猫对话,我不是讨价还价,对于生活现状,猫,我觉得你应该懂我,就像我懂你。
波斯貓扬长而去。它有它的世界,我有我的领域。我很想与猫成为朋友,这几天,一有空闲,我便来老巷子,白杨树是波斯猫栖息的所在地,它钟情于一棵白杨树,难道前主人是在这里丢弃的它?时光深处,它在义无反顾地等那个熟悉的陌生人?我以诱人的食物以及发自肺腑的倾诉,和猫的关系日益亲密。有一天,它奔跑着、低吟着扑向我,在那个相同的时间、地点、老树下,我们终于依偎着抱团取暖。
就这样,我和猫每天都要见面。无论刮风下雨,白杨树下我们畅所欲言,它坐在我的脚前,哼着一首歌,那首歌是我在世间听过的最悦耳的音乐,它让我暂时忘记了生活的不易,也陪伴我度过最美好的夜晚。
一晃,冬天如期而至,再次来到这所城市,再次经过老巷,白杨还是那棵白杨,波斯猫却失去了踪影。
一天过去了,一场雪覆盖了城市和老巷后,我问过在此居住的人,他们纷纷摇头,表示不知。
第二天,我在小区门口,看到一个身着黑色呢子大衣的女子,抱着一只波斯猫,它脖子上的铃铛似曾相识,我和它擦肩而过时,那双深邃的眼睛如电光石火划过我的心灵。
盯着女人和波斯猫消失在人群中,我居然如释重负地舒了一口气,为猫,也为我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