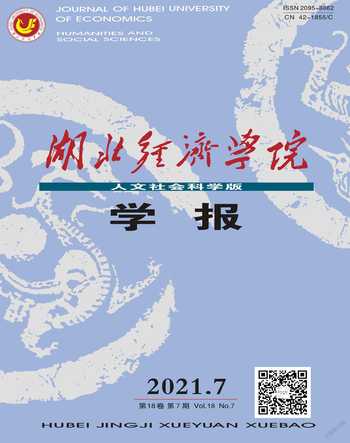《一位女士的画像》中伊莎贝尔神经症人格的治愈之路
段玉婷,于元元
摘 要:《一位女士的画像》以其国际主题和对人物细致入微的心理描写闻名。但实际上,小说更是主人公伊莎贝尔的成长史,这突出体现在其神经症人格的产生和治愈过程中。本文将运用霍妮的神经症人格理论,对伊莎贝尔神经症人格的形成原因、应对策略以及治愈过程进行分析,阐明其幼年时期产生的基本焦虑对神经症人格形成的作用,以及在文化环境改变的影响下,神经症人格的发展与治愈对婚姻抉择的改变,从而对伊莎贝尔的婚姻结局进行重新解读。
关键词:《一位女士的画像》;霍妮;神经症人格;治愈;婚姻抉择
一、引言
《一位女士的画像》是美国著名小说家、心理现实主义奠基人亨利·詹姆斯的早期代表作之一,以细腻的笔触叙述了单纯的美国姑娘伊莎贝尔在父亲离世后随姨妈来到欧洲大陆的故事。在世故老练的欧洲人面前,其不谙世事的性格与不符主流价值观的人生追求将她带入了梅尔夫人和奥斯蒙德设置的婚姻陷阱之中,但最终识破骗局的伊莎贝尔做出了成熟的婚姻抉择,留在了奥斯蒙德的身边,为自己的婚姻以及继女担负起应有的责任。小说中的国际主题,即老谋深算的旧大陆与追求自由独立、单纯的新大陆之间的碰撞与博弈,一直是众多读者和评论家关注的重点,这与作家詹姆斯个人穿梭在两种文化之间的人生经历相关。学者们还将注意力放在小说中的女性人物上,从女性主义的视角对人物的心理、性格和生活经历进行深入阐释与分析。本文认为,伊莎贝尔的种种不符常规的行为与独特的思想并不仅僅和她身上体现的新时代女性气质与特点相关,更是受到她的神经症人格的驱动和影响。在与复杂的社会环境接触过程中,伊莎贝尔的基本焦虑泛化成了对充满敌意的外界社会的焦虑,但是也随着对社会真相认识的加深,其神经症人格逐渐发生变化,这些都体现在她的婚姻抉择之中。本文将运用霍妮的精神症人格理论,对伊莎贝尔神经症人格的形成原因、采用的应对策略以及治愈过程进行分析,阐明其幼年时期产生的基本焦虑对神经症人格形成的作用,以及在环境的影响下,神经症人格的发展与治愈对其婚姻抉择的改变。
二、霍妮与神经症人格理论
卡伦·霍妮是美国新精神分析学派的先驱和奠基人,她对弗洛伊德的经典精神分析理论进行了继承与发扬,但同时也提出了与弗洛伊德不同的观点与理论。霍妮最著名的成就之一就是社会文化神经症理论,在这一理论中,她将社会文化环境对神经症人格产生和发展的影响纳入考虑范围之内,这是经典精神分析忽视的地方。“霍妮批判了弗洛伊德的理论过分强调人类行为中的生物学因素而忽视社会与文化因素的重要作用的倾向。”[1]106并且,在霍妮看来,导致人们出现心理问题甚至形成神经症的最深层原因是社会文化环境,“其中的人际关系障碍是造成神经症的关键因素和直接原因”[1]106,这与弗洛伊德坚持的由于“性本能的障碍”导致神经症的结论也是截然不同的。在文化日益交融、人口流动性不断增强的工业化社会,霍妮的理论更全面与客观地解释了处在这种复杂社会环境中的人的心理问题。
三、伊莎贝尔基本焦虑的形成、投射与泛化
在神经症人格理论中,霍妮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概念。基本焦虑是其中的核心概念之一。霍妮认为,基本焦虑来源于儿童时期对父母的基本敌意。由于父母未能满足子女在儿童时期对于安全感、温暖和爱的需要,于是子女便形成了对父母敌对的情感,即基本敌意。但由于年幼缺乏独立生活的能力,并且对父母怀有敌意会使其产生负罪感,在这种不得已的依赖和心理矛盾的冲突之下,基本焦虑便形成了。基本焦虑对儿童未来人际交往和内心冲突的进一步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产生基本焦虑的儿童,倾向于认为外界处处潜藏着敌意,总是会被一种孤立无助感裹挟着。长此以往,他们会将产生于不和谐的亲子关系中的基本焦虑,投射和泛化为对充满敌意的外界社会的焦虑。因此,要分析《一位女士的画像》中伊莎贝尔神经症人格,首先需要阐明她的基本焦虑产生的原因,以及基本焦虑投射和泛化的过程。
伊莎贝尔出生和成长在美国,自幼母亲去世,三个姐妹由父亲抚养长大。在这样的一个家庭中,首先,伊莎贝尔缺乏母亲的关心与疼爱,由于与姐妹伊迪丝和莉莉安的性格迥异,姐妹之间关系并不十分亲密,因此也未能充分从姐妹身上获得缺乏的母爱。其次,父亲对她的教育与影响是其产生基本焦虑的最主要原因。伊莎贝尔的父亲对于孩子的教育和爱护是不充分的,在很大程度上也不符合当时社会主流文化的要求,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父亲对其的过度保护。虽然伊莎贝尔的父亲希望女儿们能做到见多识广,并多次带她们去欧洲大陆旅行以开阔眼界,但他总是将人世间丑恶痛苦的事情排除在女儿们的视野之外。在伊莎贝尔看来,“她得到了最好的一切...她可没碰到特别不愉快的事,...,那种不愉快的经历她甚至知道得太少。”[2]35因为这些都被她的父亲“从她的生活中排除了出去”[2]35。因此,伊莎贝尔对于现实生活中的痛苦和快乐并没有足够清晰的认识,缺乏实践的空想和理论一直占据她的头脑。她虽然积极寻求知识和渴望探寻更广大的世界,但“她还太年轻,太渴望生活,对痛苦还知道的太少。”[2]59第二,父亲对其缺乏真正的教导。伊莎贝尔的父亲给予她的教导是不充足和不全面的,并不能使其真正地认识当时的社会现实、正确地应对和处理生活中各类事物与人际关系。例如,伊莎贝尔并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学校教育,她曾经去过一所“为小女孩提供奠定知识基础的机会”[2]25的学校,但是由于不满学校的规则,只上了一天便“赖在家里没有再去。”[2]25她的父亲对于女儿这种任性行为并没有加以管教与责备,也没有在知识学习方面给予太多指引性的建议,因此,独自阅读文学作品成为伊莎贝尔主要的知识和指导来源。第三,父亲对其既溺爱又关心不够。伊莎贝尔的父亲对女儿们总是持有一种溺爱态度,尤其是在经济方面。尽管后期当在家庭经济上已经捉襟见肘时,“他还是让孩子们尽量获得一切享受...她们要什么有什么的单纯意识,没有受到丝毫影响。”[2]37在经济方面父亲对女儿无条件的宠爱,使伊莎贝尔对金钱无任何想法,正如她所承认的那样,“对钱的事,我一窍不通。”[2]28但是,父亲对女儿们的关心也是不够的。他曾经将女儿们托付给一个法国女佣照顾三个月,但这个女佣却和同旅馆的一个俄罗斯贵族私奔了。她的父亲轻易把女儿交给如此不负责任的人长达三个月,由此可见他对女儿们照料的忽视。
以上三方面体现了伊莎贝尔的父亲对其不合理的管教与不充足的爱。父亲的教育并不符合当时社会的要求,这种教育导致伊莎贝尔在与外界进行人际交往的过程中产生障碍,进一步引发对于外界的焦虑泛化。与社会要求相悖这点可以从伊莎贝尔的姨母杜歇夫人和周围人对其父亲教育方式的评价中看出来。杜歇夫人完全不赞同她的妹夫对女儿们的管教,她“与妹夫发生了口角,指责他教育三个女儿的方式不对头”[2]28,这次争执也是多年來双方断绝联系的主要原因。此外,周围人对于她父亲的评价也是相当负面的,认为“他糟蹋了自己的一生”,“有的人甚至毫不客气地指责他,说他不关心自己的几个女儿”[2]36。由此可见,对于伊莎贝尔生活的时代,父亲的教育方式是不符合社会主流的。因此,此种教育对女儿性格和人格的形成以及未来与外界的交往易产生负面影响。
伊莎贝尔十分清楚周围人对父亲教育的不赞同,在她的内心深处或许也明白父亲的管教并不合理。但是伊莎贝尔并没有对父亲产生敌意,而是将这种敌意投射到威胁她想象中完美状态的外界。霍妮认为,“受到压抑的敌对冲动往往并不投射到事实上与之相关的那个人身上,而是投射到别的事物上”[4]42,因为对亲密的人如父母、丈夫、朋友等产生敌意,则“不符合对权威尊重、对爱情忠贞、对朋友赞赏的现存关系”[4]42。因此,伊莎贝尔不自觉地选择将基本敌意以及焦虑都转移到外界他人身上。她极力想维护父亲在自己心中完美、负责的形象,维护完美、安全的生活假象。但是实际生活并不像其想象中那么美好与幸福。她也有过苦闷的时候,对着祖母老房子里公事房的一只旧沙发,“她不知向它倾诉了多少孩子的悲哀”[2]25。在成长的过程中,伊莎贝尔总是以一种想象的、天真的视角看待世界,担心外界会打破她的理论和对于美好世界的幻想。最终,其基本焦虑逐渐泛化,变成了对于他人与环境的焦虑。
四、伊莎贝尔的神经症防御机制
为了应对潜在的威胁并减轻焦虑,人们会采取不同的防御机制,即十种“神经症的需要”。在《我们内心的冲突》一书中,霍妮总结了这些防御机制,将其归纳成了四种神经症人格倾向,即“亲近人、对抗人和回避人、心目中树立理想化形象”[3]165。前三种神经症人格倾向主要是个人与外界的互动,最后一种是个人对于自身内部的防御机制,即不断创造病态的理想自我,企图遮盖真实自我。身心健康的人会根据自身情况,灵活运用这些机制来应对焦虑,但神经症患者倾向于过度单一地使用某一种或两种,造成自身严重的混乱与冲突。霍妮还提出了神经症判断的双重标准,除了临床表现外,还有“以个体所在的社会文化为背景来观察个体的行为是否符合群体的标准”[3]167,这点体现了霍妮对于社会文化环境影响因素的重视。
由于童年时期父亲不充分的教导和爱护,以及伊莎贝尔想要维护自己受到了父亲精心照顾与完美教育的这一谎言,使她产生了基本焦虑。在与外界的互动过程中,投射与泛化的焦虑使她对生活没有清晰的认识,并在人际交往中产生障碍。她拥有自己看待生活的一套理论,“时刻考虑着自己的成长,要求自己完美无缺,关心着自己的进步”[2]59。为了缓解焦虑与外界潜在的威胁,伊莎贝尔产生了自己的神经症需求,并逐渐形成了回避型神经症人格倾向。
具有回避型神经症人格倾向的人群通常采取的防御机制是退缩。退缩不是指与世隔绝,隔断与外界的交流,“而是指脱离他人,不让他们对自己的外部需求或内部需求发生影响。”[4]61退缩策略的不断运用,使得具有回避型神经症人格的人逐渐孤立自我。伊莎贝尔的自我孤立者形象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首先,伊莎贝尔对独立与自由的执着追求颇为明显。自我孤立者“对独立的需要是强迫性的、盲目的。它的表现是:患者对任何稍微类似强迫、影响、义务等的东西都过度敏感。”[5]42小说第一章杜歇夫人在信里对她的描述便是“颇能自主”[2]11。此外,当表哥拉尔夫将他母亲把伊莎贝尔带到英国的行为描述成收留时,她质问道“‘收留了我?”[2]20,“刹那间还露出了痛苦的表情”,并急切地补充道“我更重视我的自由”[2]21。由此可以看出她对于独立的执着追求,她承认姨母的好意,但也明确她来欧洲是为了探寻更广阔的世界,追求更大程度的自由,并不会因此而寄人篱下。并且,保持独立与自由还有一个好处,对于具有回避型人格倾向的人群来说,如果回避了,就没有什么事能够伤害到自己。伊莎贝尔通过追求绝对独立,回避了外界对于自己理论和对世界美好幻想的破坏,维护了自己内心安全隐秘的状态。第二,伊莎贝尔对孤独的偏好,这点可以从她对书房的选择中体现出来。当她住在祖母家里时,她选择了一间堆满旧家具、散发着霉味的房间,因为这里不容易被发现和被打扰。“整栋房子都可以随她使用,她却偏偏选择了这间最凄凉的屋子。”[2]26选择孤独是具有回避型人格倾向的人群以一种非攻击性的方式抛弃他人的手段,孤独能够阻止与他人的联系,从而防止依赖或伤害的产生。第三,伊莎贝尔对优越地位的要求,尤其是对“与众不同”的追求。在美国时,那些追求她姐姐的年轻人不敢轻易接近她,由于她“博览群书的名声...使她变成了史诗中的女神”[2]37,“他们是不敢跟她打交道,他们相信,必须做好特殊的准备,才能跟她谈话”[2]37。她的姐夫也评价她是“用外国字写出来的”[2]33,不喜欢她的“与众不同”。自我孤立者认为,“自己高贵的品质别人应该一看便知”[5]44,对于那些奢望娶她的男人,她简直觉得可笑。由此可以看出她对自身优越感的肯定。伊莎贝尔的与众不同实际上就是不断使用神经症防御机制的结果,这使得她非攻击性地抛弃了他人,继而在与人交往的过程中出现障碍。她不愿依附任何人,永远保持高度的自信与追求自给自足的状态。她想探寻更广阔的世界,认为痛苦和任何不愉快存在于世间别的角落,她不想选择不去体验这些,却总是不自觉将自己想象中童话般的生活与外界隔离开。这种矛盾状态与焦虑来源于她没有认识到生活的真实面目,即痛苦无处不在,以及疏离真实生活导致的人际关系障碍。
五、伊莎贝尔在婚姻抉择中神经症治愈过程
当伊莎贝尔来到欧洲大陆后,她接连经历了来自古德伍德先生、沃伯顿爵士和奥斯蒙德的求婚。在进行婚姻抉择的过程中,伊莎贝尔对神经症防御机制的运用经历了三个阶段,即从刻板坚守,到松懈动摇,最终到灵活转变。霍妮指出,由于人际关系障碍导致的神经症是一个持续的过程,“认清造成冲突的环境对解决神经症有更大的帮助”。[3]167伊莎贝尔转变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外在环境的改变使她认清了内心焦虑的原因。首先,生活环境的改变,即由单一的、人际关系简单的美国家庭环境,来到了充斥陌生人尤其是老谋深算的欧洲人的旧大陆;其次,个人经济情况的逆转,即获得了杜歇老先生留下的大笔遗产,使其经济方面获得独立;以及婚姻陷阱的重创,令伊莎贝尔认识到生活的苦难,这些都导致其采取的神经症防御机制在不断改变。由于认清了造成冲突的环境以及防御机制的调整,使她不再执着于她的神经症需求,做出符合社会环境要求的成熟决定,最终她的神经症得到了治愈。
(一)刻板坚守
在嫁给奥斯蒙德前,面对婚姻抉择,伊莎贝尔执着于单一的神经症防御策略,对外是追求独立平等、绝对自由,对内是创造理想化自我,保持完美不犯错。首先,伊莎贝尔这类具有回避型神经症人格的人群,不希望外界对自身需求产生影响。因此,在刚到欧洲时,涉世未深的伊莎贝尔决不允许婚姻对独立自由的追求产生任何限制。伊莎贝尔并不像当时社会中传统妇女那样十分向往稳定的婚姻生活,例如分别嫁给律师和军官的两个姐姐,婚姻制度对她来说会变成一种束缚与桎梏,因此,在面对婚姻选择时她虽谨慎但也非常固执。在追求者方面,她认为“如果有一道光芒照亮了她的心,她就会毫无保留地献出自己……这个幻景使她畏惧,而不是觉得可爱。”[2]59她对周围认识男子的爱慕嗤之以鼻,想象有个完美的人成为自己一生的伴侣,但同时还对此感到恐惧。因为她清楚在婚姻中女性容易处于弱势附属地位,了解婚姻会带来家庭的限制和道德责任,这些都对追求自由独立造成威胁。在刚来到英国时,面对美国的戈德伍德先生和英国贵族沃伯顿,伊莎贝尔拒绝了这两个看似满意的追求者。戈德伍德是美国富商,是一位充满活力与雄心壮志的年轻人,但伊莎贝尔认为他“从来不符合她关于一个可爱的人的观念,她猜想,这就是她对他如此反感的原因。”[2]135他整天谈论的内容、穿的服装都太单一普通,这不符合她心中完美伴侣的条件。而沃伯顿勋爵是符合这个观念的,但他高贵的身份地位与雄厚的经济情况又使伊莎贝尔感到沉重的负担与束缚感。沃伯顿勋爵为她提供的“那种‘迷人的安全感,不是她所向往的最重要的东西。”[2]125伊莎贝尔寻求的是未知的、更宽广的未来为她创造的自由感,而不是以贵族太太的身份,过着传统安稳的狭窄生活。此外,当时她还未接受姨父的遗产,经济情况与沃伯顿勋爵相差甚远,这种经济方面的弱势地位,也在阻止她接受求婚。其次,伊莎贝尔对理想自我的执着也在婚姻抉择中发挥重要作用。“她有着不可遏制的欲望,要把自己想得十全十美...一个人要做人,就得做一个最好的人,就得意识到自己处于完美的状态。”[2]56伊莎贝尔希望能依靠自己最英明的判断,为自己觅得最完美的婚姻,害怕错误的选择破坏自身完美状态。因此,因两次求婚导致的恐惧心理,以及对自由、独立和完美等神经症需求的执着追求,使年轻的伊莎贝尔最终放弃了这兩个在当时社会令人满意的求婚。
(二)松懈动摇
在婚姻方面,伊莎贝尔对独立自由的绝对坚持,在面对阴险狡诈的奥斯蒙德时发生了松懈与动摇。首先,受到梅尔夫人的蛊惑与哄骗,伊莎贝尔接受了奥斯蒙德的求婚,这可以看作是她对社会要求的一种妥协。奥斯蒙德随性的生活和虚伪的艺术家身份,在她眼中是对自身独立和自由的保障。她认为奥斯蒙德自由的灵魂和独特的审美能带领她领略更广阔的世界,了解更多的知识。虽然妻子的角色会给她带来特定的责任和义务,但是和传统婚姻相比,这段婚姻是可以接受的,因为这没有违背她的神经症需求,也没有危及将来对神经症需求的实现。其次,伊莎贝尔没有再执着于自身的完美,而是将对完美的要求投射在了未来丈夫身上,她愿意尽自己的力量帮助丈夫追求更完美的生活,从而实现自己的价值。这可以看成伊莎贝尔对沉迷于理想自我的动摇。这位久居欧洲的美国人,伪装成一位举止不凡、品味高雅的艺术家,在伊莎贝尔看来,他追求着美与自由,对社会似乎有着深刻见解,同时他的经济情况并不像之前两位追求者那样会给她带来压力,相反,她正好可以用获得的遗产来帮助这位艺术家追逐理想,这也解决了伊莎贝尔对如何处理这笔财产产生的烦恼。威斯布(Weisbuch)认为,在伊莎贝尔看来,她可以完全地、并安全地将自己交给这个一无所有的完美之人。[6]115令伊莎贝尔对神经症需求松懈动摇的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即最初展现在她面前的奥斯蒙德和女儿帕西之间“相互依赖”的父女关系。伊莎贝尔基本焦虑的来源是与父亲不和谐的亲子关系。“伊莎贝尔感到父亲的遗弃比她意识到的要严重得多...自由和无父把女主人公分成了两个互不相关的部分—一部分是人为地决定要做自己的主人,另一部分是对支配和服从形象的黑暗迷恋。”[7]奥斯蒙德与帕西之间的亲密举止以及帕西对于父亲的顺从,使伊莎贝尔产生艳羡的情感,并使其一直坚持的自由部分开始被另一部分掩盖。这反映出其对亲密父女关系的追求,以及想对之前不良亲子关系进行弥补的企图。于是,她选择嫁给了奥斯蒙德,从而跌入了梅尔夫人为她设置的婚姻陷阱之中。
(三)灵活转化
婚后伊莎贝尔随奥斯蒙德住到了意大利,婚后的生活并不似她想象的那般美好与自由。奥斯蒙德逐渐显露出了他的权威与冷淡,无论是对于妻子还是女儿帕西,他才是家中真正掌握话语权的人。伊莎贝尔渐渐意识到,奥斯蒙德并不真正理解她,只是将自己当做他的收藏品中一个美丽艺术品。家里昏暗的光线暗示着她的世界越来越狭窄和黑暗,婚姻没有如其所愿将她带入更宽阔的世界,她追求知识和自由的梦想开始被现实生活击碎。此外,奥斯蒙德对女儿帕西的操控让伊莎贝尔识破了他虚伪的面目。他一心想让帕西嫁给富有的沃伯顿勋爵,破坏了女儿和穷小子的爱情。极其恶劣的父女关系以及奥斯蒙德塑造的绝对顺从的帕西,让伊莎贝尔意识到,奥斯蒙德不会为她提供自己长期执着追求的自由,相反,只会主导和控制她。对奥斯蒙德和梅尔夫人关系的识破最终使她彻底醒悟,她明白了自己并不是嫁给了爱情,这场婚姻只是安排好的骗局。在这场婚姻中经历的各种事件和接触到的各色人群,使她真实地体验了真正的生活,即生活中苦难、邪恶与痛苦是与幸福快乐相伴的,两者并不是完全对立。随着环境的改变,切身体验过险恶的人生后,伊莎贝尔开始以实际的角度审视生活,面对真实自我。“神经症人格的治疗是让病患者发现、发展本身的潜能,并积极发挥其潜能的建设力量达成自我实现。”[8]86伊莎贝尔逐渐直面自己的错误与不完美,意识到自己能勇敢面对痛苦与磨难的潜能与信心。并且,她还认识到,在人际复杂的社会环境中,自己对自由、独立一味地渴求是不切实际的,会使自己不能看清和处理好与他人之间的关系,并最终给自己带来无限的烦恼与痛苦。认清造成冲突的环境后,她的神经症防御机制开始发生转变,不再是单一展现回避型人格倾向,而是更加灵活地应对生活中的焦虑。因此,当她参加完表格拉夫尔的葬礼后,她还是决定回到与奥斯蒙德的婚姻中,承担自己选择的后果,并为继女帕西负责。实际上,这种敢于担当的精神才是伊莎贝尔一直追求的人格独立,因为真正的自由独立是相对的,正如威斯布(Weisbuch)所说,“回到奥斯蒙德,伊莎贝尔因此击败了他扼杀自由的力量,肯定了自己。”[6]117至此,伊莎贝尔的神经症人格倾向得到了有效缓解,神经症得到了治愈。
六、结论
本文利用霍妮的神经症人格理论对主人公伊莎贝尔的心理成长过程进行了剖析,解释了其基本焦虑形成的原因以及泛化的过程,阐述了其经历婚姻陷阱前后采取的神经症防御机制以及其最终改变,从而使神经症得到了治愈。从美国来到欧洲,随着文化环境与人际关系的变化,伊莎贝尔对于外界的认识产生了巨大改变。她最终真正地融入了生存的社会,承担起自己应负的责任,切身地去体验人生的幸福与不幸,从而获得了相对的精神自由和人格独立。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段失败的婚姻骗局拯救了她对神经症需求的执着追求,使她不再是那个单纯、无知、头脑中充斥着自己那套理论的美国小姑娘,成长为了一位稳重、有责任感的成熟女性,能结合自己的生存环境,做出理智、符合社会要求的决定与行为。
参考文献:
[1] 刘启珍.试论霍妮对弗洛伊德的继承与批判[J].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5):104-107.
[2] 亨利·詹姆斯.一位女士的画像.项星耀,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3] 張灏,李乐平.霍妮新精神分析理论研究综述[A].国际中华应用心理学研究会.国际中华应用心理学研究会第五届学术年会论文集[C].国际中华应用心理学研究会:国际中华应用心理学研究会,2007:6.
[4] 卡伦·霍妮.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冯川,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
[5] 卡伦·霍妮.我们内心的冲突.王作虹,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0.
[6] Weisbuch, Robert.“Henry James and the Idea of Evil.”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Henry James.Ed.JonathanFreedman.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0.
[7] Veeder, William. “The Portrait of a Lack.” New Essays on The Portrait of a Lady. Ed. Joel Porte.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2007:60.
[8] 张爱群,郭本禹.凯伦·霍妮的神经症人格理论及其价值[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33(11):85-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