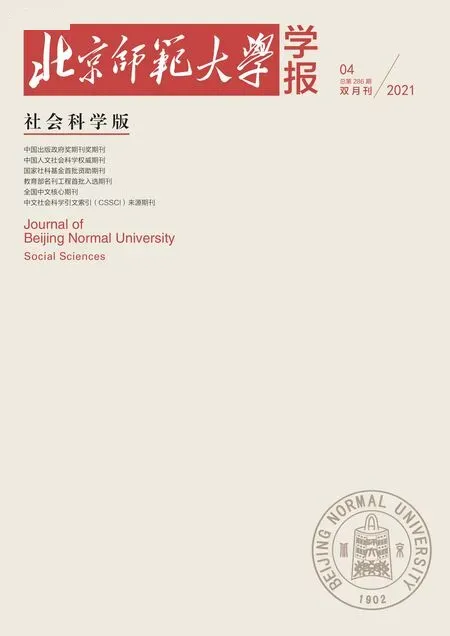论近代英国的卫生检查制度
王广坤
北京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北京 100875
随着19世纪英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人们的居住环境日益拥挤,工业污染不断滋生,各类疾病传播肆虐,卫生状况不断恶化。因此,19世纪中后期虽然是学界公认的英国社会繁荣鼎盛的“维多利亚时代”,但平民大众却面临着工业化城市化转型时期的生存挑战,尤为让人关注的就是公共卫生,其恶劣程度已经使当时民众陷入到“濒临死亡的绝境中”(1)参见Ahthony S.Wohl,Endangered Lives:Public Health in Victorian Britain,London:J.M.Dent,1984。。这样来看,虽然1837年维多利亚女王登基时英国社会较为富裕,但其实已受“可怕”与“破坏稳定”的社会问题困扰,主要表现就是当时“几乎没有或根本没有试图规范公共卫生”(2)〔英〕西蒙·赫弗:《高远之见:维多利亚时代与现代英国的诞生》,徐萍、汪亦男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前言,第iii页。。此种社会背景下,做好公共卫生管理就成为当时英国政府必须重视的事务,而要想科学高效管理,就必须深入调查了解卫生领域的具体问题,构建系统化的卫生检查制度。
从19世纪中后期开始一直到1914年一战爆发前,英国都是世界上实力最为强劲的国家,被称为“大英帝国”,幅员极其广阔,“覆盖了地球陆地面积的四分之一”(3)〔英〕劳伦斯·詹姆斯:《大英帝国的崛起与衰落》,张子悦、解永春译,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8年,第360页。。英国公共卫生管理作为此时能让英国达至国家巅峰状态的重要保障,目前国内外学界有关研究成果极多(4)见王广坤:《19世纪英国公共卫生管理史研究》,《全球史评论》,第14辑,2018年,第189-203页。。但专门针对近代英国卫生检查制度构筑与评介的论著却并不多见,很多研究都是将其作为英国公共卫生管理体制建设的一环而加以介绍(5)国内学界目前尚无专门性论著介绍近代英国的卫生检查制度。国外学界相关论著主要有:Tom Crook,“Sanitary Inspection and Public Sphere in Late Victorian and Edwardian Britain:A Case Study in Liberal Governance”,Social History,2007,32(4),pp.369-393;Celia Davies,“The Health Visitor as Mother’s Friend:A Woman’ s Place in Public Health,1900—1914”,Social History of Medicine:The Journal of the Society for the Social History of Medicine,1988,1(1),pp.39-59;Francis Vacher,The Food Inspector’s Handbook,London:Methuen,1892;Albert Taylor,The Sanitary Inspector’s Handbook,London:H.K.Lewis,1893;J.Brand,Doctors and the State:The British Medical Profession and Government Action in Public Health,1870—1912,Baltimore:Johns Hopkins Press,1965,pp.65-81;B.G.Bannington,English Public Health Administration,London:P.S.King & Son,Ltd.,1915,pp.82-99;Tom Crook,Governing Systems:Modernity and the Making of Public Health in England,1830—1910,Oakland: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16,pp.106-147。这些研究虽涉及卫生检查,但较少关注其制度建设并作出论述评介。。本文试图参考前人研究,在阐明英国卫生检查制度构建与实施的基础上,评析卫生检查制度所折射出来的英国政府卫生决策的基本特点。
一、卫生检查制度的构建
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化国家,在进入19世纪后,英国城市化进程加速,致使城市拥挤、污染增加、疾病横行、公共卫生状况恶化。为应对此困境,英国政府全面介入公共卫生管理,于1848年成立中央卫生委员会(The General Board of Health),后又于1858年创建医疗部(Medical Department)、1871年成立地方政府事务部(Local Government Board)等机构,促进公共卫生管理工作(6)王广坤:《19世纪英国公共卫生管理史研究》,《全球史评论》,第14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第189-190页。。
在此三个重要阶段中,政府都极为重视卫生检查。第一阶段的卫生管理主要遵从1848年《公共卫生法》,这部法案于1848年8月通过议会辩论,成为国家大法(7)〔英〕弗雷德里克·F·卡特赖特、迈克尔·比迪斯:《疾病改变历史》,陈仲丹、周晓政译,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第134页。。法案非常重视中央对地方的检查工作:“在代表中央意志的大都市伦敦首先创建中央委员会,然后再广泛任命检查巡视员,去管理地方上的那些分支委员会。”(8)Kathleen Jones,The Making of Social Policy in Britain 1830—1990,London:Athlone Press,1991,p.34.伦敦的中央卫生委员会主要工作就是调查英国各地公共卫生状况,并提出相关管理意见:第一,当有超过十分之一的纳税人申请在该地区实施公共卫生法时,委员会有权命令一个检查员进行细致检查,根据调查报告确定法律应用。第二,委员会可任命若干检查员,以监督地方卫生管理工作,并参与法案实施监管,还可通过地方检查员的实际调查情况,来接受或决定应对地方反对意见的上诉。第三,委员会可聘任卫生医务官(Medical Officers of Health)(9)主要指的是那些在公共卫生管理中具备相应医学知识的人士,是英国政府公共卫生管理工作实践中最为重要的依赖者,很多事务都需要听取他们的意见,甚至直接由他们来判断、筹划和作出最终定夺。,直接部署和指导其进行具体的卫生管理工作(10)1848 Public Health Act,http://www.legislation.gov.uk/ukpga/Vict/11-12/63/contents/enacted,pp.721-784.。
自1215年《大宪章》颁布以来,英国人就非常看重保护自由权利,而1848年法案却过分强调中央集权,这导致崇尚自由自治的各地政府强烈不满。中央政府为此颁布了1858年《公共卫生法》,试图协调中央与地方的矛盾。它的主要内容是:将中央卫生委员会管理公共卫生事务的权力移交到枢密院,并成立医疗部;赋予枢密院制定防疫法等权力,议会负责防疫工作所产生的费用,由枢密院指导使用;枢密院可在必要时,调查地方卫生状况;中央卫生委员会的卫生医务官职务也转到枢密院,并根据其工作需要安排助手,卫生医务官1500镑的年薪及助手薪酬由议会承担,他要随时向枢密院报告公共卫生状况,并在每年三月份向议会提交年度总结报告。1859年7月,英国议会通过该法案(11)⑦⑨ John Simon,English Sanitary Institutions,London:John Murray,1897,pp.277-278,240,288.。

西蒙极为重视卫生检查工作,早在伦敦担任卫生医务官时,他就为英国公共卫生管理确立了基本规则,要求污染物检查员(Inspector of Nuisance)必须定期向他汇报伦敦各区域的基本卫生状况;要求伦敦地区的人口登记部门、监狱及济贫院等单位认真做好人口死亡的数据统计,并向他提供具体信息。他再以此为依据,每周指导下水道委员会的工作。1849年,他强调,卫生工作必须要参考来自各教区的疾病信息与地方卫生状况的报告(13)柳润涛:《约翰·西蒙与19世纪中后期的英国公共卫生改革》,南京大学2013年硕士学位论文,第16页。。
为做好卫生检查工作,西蒙根据1858年《公共卫生法》第二条到第五条的规定,充分利用医疗部所赋予的检查和报告国家卫生状况之权力,对以医生为主体的卫生检查员报告极为重视,视其为社会管理的必要参考。在他看来,英国卫生管理需要科学知识的指导,高资质的卫生检查员的意见至为重要。因此,他任命的卫生检查员大都是医生,具备专业知识,工作态度认真,调查报告细致。这个团队中,“有着许多杰出素养的医务人员,有些是医疗部兼职检查员,枢密院一天予以3英镑薪酬,不过大部分是全职固定的卫生检查员,这些人有17人之多,大部分都非常年轻。他们中的优秀成员西顿(Seaton)、布坎南(Buchanan)和斯隆(Thorne)还分别于1876年、1879年和1892年担任了中央卫生医务官”(14)C.Fraser Brockington,Public Health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Edinburgh:E.& S.Livingstone,1956,pp.201-202.。在大量高素质医生的辅助下,西蒙先后对英国社会中的白喉疾病、霍乱袭击、伤寒入侵等威胁公共卫生的事件进行了详细调查,向议会呈送了十几份调查报告。
有赖于强大的医生检查体系,仅在1867年,西蒙就与英国113个地方卫生机构频繁通信并进行实地调查。1870年,随着热病复发,西蒙又先后联系了200多个地方卫生机构,对66个城镇进行实地调查(15)Anthony S.Wohl,Endangered Lives:Public Health in Victorian Britain,p.157.。为强化检查监督体系,从1869年开始,枢密院在科学实验室调查团队之外,又任命两名终身检查员布坎南和拉德克里夫(Radcliffe)从事卫生调查工作。对此,西蒙特别强调:“这将会对我们的整个工作产生深远的间接影响。”(16)⑤⑥ John Simon,English Sanitary Institutions,pp.317,275,323-324.因此,西蒙虽然没有固定的助手,但却有大量卫生检查员听命于他,他也能知人善用,并将其凝聚为团队力量。与西蒙有紧密联系的卫生检查员有16位是医生,其中不少于8人成为皇家学会会员。这些人的检查报告新颖充实,崇尚社会调查与走访巡视。疾病流行时,他们走访了每个城镇、每条街道及每幢病房,收集了大量与疫病相关的信息,并记录了针对性处理措施。

二、卫生检查制度的发展

卫生管理的混乱局面尤其体现在英国济贫法服务体系上,它的存在,造成英国公共卫生管理有两套独立系统。甚至在传染病爆发时,济贫法医疗服务体系所属的济贫法医生也不将济贫院患病、死亡等卫生状况交给卫生医务官,这导致西蒙等人在统计地区或国家死亡率时非常困难。它反映了英国公共卫生管理的制度缺陷,因为并无法律规定济贫法部门应与地方卫生管理当局鼎力合作。
1869年,英国医疗协会和社会科学协会联合委员会向政府提交请愿,倡导全面检查并审视英国公共卫生管理状况,形成调查报告以引导政府进行改革。他们主导成立了皇家卫生委员会,委员会经过两年时间,检查了近百座城镇,揭示了“公共卫生的立法与管理存在令人震惊的繁杂、混乱、失衡与低效”。有鉴于此,皇家委员会主张以地方政府为中心,发挥中央检查与监督职能,整合卫生管理职能:“地方政府原则已经证实是国家精神的核心,地方在中央监督下的管理是我们政府的显著特色。这个理论要求地方机构应该做他们能做到的一切,不管国家层面需要做什么通盘考虑民族利益的规划,地方事务必须由地区负责处理”(17)③ C.F.Brockington,A Short History of Public Health,London:J.& A.Churchill Ltd.,1956,pp.30,30-31.。
根据调查,委员会发现地方卫生管理鱼龙混杂,根据1848年和1858年《公共卫生法》,各地成立了许多地方卫生机构或专门委员会,1866年《公共卫生法》也让地方成立了许多“排污机构”和“污染物清理机构”;此外,还有地方法案授权下的各类地方治理与改进委员会。职能划分上,地方也不统一,在一些自治城镇,地方卫生机构可负责道路、照明、供水、排污等事务,而地方改善法却规定,排污委员会承担下水道、排污管理,市政议会建立的排污机构也负责同样工作,甚至有公路委员会也承担部分责任。这种纷繁复杂的设置使管理无法统一。报告指出:“在所有地区,每个领域的管理人员都不一样,每个厕所有厕所管理员,每个猪圈有猪圈管理者”,分工无法统一,指令不能协调。同一地方也会出现不同的卫生管理员,常导致“当下水道管理员想设立医院时,他没有足够的医务人员来执行此项工作”,而“当污染物检查员已准备好进行卫生改进工作时,他却并没有被授权提供这样的服务”。所以,尽管卫生法案在某些地方取得了很多成就,但是法案的复杂性及某些领域内权力的互相重合,再加上中央政府的管理不力,使得卫生法案在很多地方并未发挥功效(18)B.G.Bannington,English Public Health Administration,p.30.。

这份报告的核心要点在于设置统一的卫生管理主导机构,以便能“指导卫生检查与医疗实践等事务,提供必要建议,批准地方建设大规模公共卫生工程,发布临时指令,接收控诉和请愿,颁发紧急医务条例并汇总整理医学报告等”。而对于中央机构的行为规范,调查报告也提出意见:为履行职责,中央应有充分的监管和检查权。西蒙对此非常肯定,他这样写道:“这份自1869年开启的,一直持续到1871年春季的报告经过了百千名实践证人的仔细观察,其影响意义几乎可以和四十年代的卫生调查报告相媲美,对公共服务的许多方面产生了巨大影响力,报告使得关于这个主题的许多普及性知识得到促进,其显示出来的那些富有建设性意义的修正意见尤其重要。比如,它建议复杂多变的权威应该予以简单化,不相联系和统一的法案应该得到全面调整。”在西蒙看来,报告的核心意见是“现有的分散与让人迷惑的不同卫生法案应该得到统一集中的权威表达”,“卫生管理的法律在整个国家应标准化、具有全面普及性且具有强制约束力”,并且,“所有授权给地方要求的权力应该由一个负责任的地方当局统一掌控,实践中认真履行,并接受上级机构的协助”(19)⑤ John Simon,English Sanitary Institutions,pp.327-328,373-374.。

从内容上看,这些法案都极为重视中央与各级地方政府的卫生检查工作,并且在检查体系的规划上予以更为细致的科学设计。这在1872年颁布的《公共卫生法》中体现得尤为典型,这部法案将公共卫生管理方式分为农村和城镇两种类型,农村由济贫官员们(The Boards of Guardians)进行监督,城镇由城镇委员会(Town Councils)和地方局(Local Boards)负责,规定每个地方都需任命卫生医务官与污染物检查员。相比于1848年《公共卫生法》仅限于城镇和人口众多的地区,1872年《公共卫生法》极大地强化了农村地区的卫生管理。而且,地方政府委员会可同时掌管卫生管理和济贫服务,通过各地检查员报告,决定地方当局的财政花费、划分地方卫生管理边界、批准和修改地方法规。这部法案意义重大,它为整个国家创建了统一的卫生管理体系,使卫生管制深入到每个区域(21)C.F.Brockington,A Short History of Public Health,p.31.。此外,这部法案也鼓励强化西蒙支持的国家医学体系(State Medicine),于卫生管理工作中强制要求政府当局必须聘用卫生医务官与卫生检查员(22)Tom Crook,Governing Systems:Modernity and the Making of Public Health in England,1830—1910,p.110.。
三、卫生检查制度的实施

1871年地方政府委员会成立后,基本遵循了皇家卫生委员会的建议,注重构建以高素质卫生检查员为基础的卫生检查制度。检查工作也日益科学细致,在19世纪90年代,曼彻斯特市政当局已经有了28个卫生检查员,包括4个烟雾检查员、2个肉检查员以及6个工厂车间检查员。在1896年,城市中的46270栋房屋,2480座工厂、矿山,451座不卫生交易场所和屠宰场受到审查,共发现了29984处“不洁净的混乱所在”。而伦敦郡议会(London County Council)在20世纪初期雇佣了多达260名卫生检查员,仔细巡查这个城市的方方面面(23)Tom Crook,“Sanitary Inspection and Public Sphere in Late Victorian and Edwardian Britain:A Case Study in Liberal Governance”,Social History,2007,32(4),pp.372-373.。
卫生检查员的基本职责是发现“污染物(nuisances)”,并作出清除规划。这个词源于中世纪,但到现代得到拓展,特指妨害公众舒适和体面生活的各类事务(24)1855年以前,这类事务更多指的是环境卫生而非医疗领域,1855年以后,逐渐倾向于特指医疗事务。参见James G.Hanley,“Parliament,Physician,and Nuisances:The Demedicalization of Nuisance Law,1831—1855”,Bulletin of the History of Medicine,2006,80(4),pp.702-732。。此类事务主要包括不卫生的居住环境、商业环境以及有毒的烟囱和壁炉等物件。在发现问题后,根据1872年的法律规定,卫生检查员需要直接对聘用他们入职的地方机构负责,其工作需由当地聘用的卫生医务官指导,必要时可以开会讨论。一般而言,城镇地区检查员需向卫生医务官报告调研结果,而农村地区则直接向地方管理当局汇报检查情况(25)Tom Crook,Governing Systems:Modernity and the Making of Public Health in England,1830—1910,pp.110-111.。19世纪60年代以后,由于医疗科学的不断发展,人们“对环境卫生关注度有所下降,‘涵括性(Inclusive)’的卫生管理范式逐步让位于‘隔离性(Exclusive)’,关注重点聚焦于染病的人及地方,通过发现、隔离、消毒等方式处理问题。‘预防医学’和‘个人卫生’替代了‘环境卫生’,关注个人的细菌感染取代了重视环境清洁的空气改造”(26)Michael Worboys,Spreading Germs:Disease Theories and Medical Practice in Britain,1865—1900,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




为做好检查工作,检查员也注重在集会上分享工作经验。布莱斯就强调:“不管法律赋予我们进入英国人私人领地权力有多大……如要确保高效进入私人领地检查还是需有赖于检查员表现……所有民族中,英国是对于房屋居所隐私权最为看重的,这条原则决定了如果官方公务人员进入时不敲门、未得到允许贸然闯进以及没有脱帽子的话,就会激怒房屋主人。”(30)A.Wynter Blyth,“Address:Conference of Sanitary Inspectors”,Public Health,1892,5,p.10.这就要求检查员必须具备较好的与人沟通能力,对人有礼貌,且在检查过程中温和理性。
这些经验有助于推进检查员的工作,促使他们将官方活动与关注人的隐秘情感联系起来,将自己塑造成能抚慰公众的国家公务员代表,这在访问濒死者的受感染居所时,起到的作用更大。检查员对自身的形象塑造较为成功,通常被视为公众的“朋友”及“指导者”,很多人因此非常认可检查员,将其称为“卫生传教士”、“净化使者”。在检查员看来,他们的工作确实也是在弘扬健康卫生方式的“说教”,这在接种天花疫苗与个人卫生事务方面体现得尤为明显(31)A.Wynter Blyth,“The Education,Status and Emoluments of Sanitary Inspectors”,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Society for the Promotion of Health,1897,18,p.195.。
四、卫生检查制度评析
随着19世纪中期以来英国公共卫生状况的恶化,中央政府开始全面介入卫生管制。为有针对性地进行管理,英国政府非常重视卫生检查工作,构建了以污染物检查员与卫生医务官为主导的卫生检查制度。他们勤奋工作,向各级政府汇报各地卫生工作的不足与缺陷,引导政府加以完善,这使得英国社会原本恶劣的公共卫生状况得到显著改观。在卫生检查普及推广过程中,英国民众的卫生意识也得到强化,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开始形成,医疗服务得到普遍重视,英国人口死亡率和流行病发生率日益下降,国民体质普遍增强。就整个国家而言,中央控制下高效卫生检查体系的确立,无论对于国家传染病防控体系的构建,还是对于同各类城镇发展相适应的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建设都意义重大。
不仅如此,卫生检查员的工作也有助于塑造具有高尚道德的国家公务员形象。一本专门针对卫生检查的书籍就强调:“礼貌端庄与善良优秀的特征必须体现在其所有的工作实践中,任何粗鲁或傲慢的官僚气息都不应出现在其行动中。”(32)⑦ Albert Taylor,The Sanitary Inspector’s Handbook,pp.29,82.特殊的工作性质使得检查员普遍具有温柔细致的性格特征,检查行为耐心细致且优雅温和,主要采取劝服、鼓励、引导与教育等方式进行。这种工作形式影响了后续英国公务人员的行为方式,使得维多利亚时代后期的政治领域出现了一股情感主义浪潮,那就是尊重公共意愿,引导和培育公务人员的同情心与温柔性格(33)H.S.Jones,Victorian Political Thought,Basingstoke:Palgrave Macmillan,2000,pp.69-73.。在这一方面,卫生检查员是以身作则的引领示范者,他们普遍都重视温柔性格的培育,通过教育鼓励、劝导说服的方式进行卫生管制。这在后续英国女性卫生检查员的任命雇佣中表现得更为明显(34)Celia Davies,“The Health Visitor as Mother’s Friend:A Woman’s Place in Public Health,1900—1914”,Social History of Medicine:The Journal of the Society for the Social History of Medicine,1988 1(1),pp.39-59.。而且,卫生检查员同时也是政府官员,他们不仅关注卫生水准,提出调整与改善的建议,同时也是地方问题原始档案的记录和保管者,有助于人们了解和把握地方政府漫长历史的方方面面(35)Tom Crook,Governing Systems:Modernity and the Making of Public Health in England,1830—1910,p.108.。


从法律而言,虽然它是保障卫生检查员安全与检查工作顺利进行的关键,但检查员一旦遭到上诉,法律也会对他们不利,因为法院会要求检查员公开案件细节,公开讨论其工作,质问他们对违法行为的理解及其行动的正当性。在1906年,治安官就曾质问一个检查员,怀疑他是否有权检查一个有问题的排水管,理由是这类事务通常都是由房主来确定的。针对这种情况,有学者在卫生检查员指南书出版后不久,就发出过这样的警告:指南虽然非常详尽地对卫生检查员们的工作进行指导,让他们在所有与传染病相关联的领域发挥像私人医生般的作用,但因其行动权受到房主的极大限制,因此即便检查员所做的隔离或清除污物等工作很有必要,也极易遭人误解,被认为其滥用权力,受到辱骂攻击(39)“Review of the Sanitary Inspector’s Handbook”,Glasgow Medical Journal,1893,40(4),pp.308-309.。

为应对污染物处理程序及其后续影响,检查员也有资格请求法律服务。诽谤是其碰到较多的案例,公众可通过这种手段来加深人们对检查行为的非议,此方面的许多案例都与贿赂有关,因为有时这种行为是很难被确切定义的。比如一位面纱店员就认为检查员始终是“暴露于黄金诱惑之下”的人,公众也对此深信不疑。而且,被检查者也更容易受到舆论同情。1890年的一次案件就是典型,原告凯迪(Candy)同时将地方卫生检查员博维(Bovey)与授权其进行检查的卫生医务官普劳斯(Prowse)告上法庭,他以自己的丧女父亲身份吸引舆论同情,愤怒地指责博维与普劳斯两人毫无道德良知,竟然在自己外出为夭折女儿筹备葬礼之际偷偷潜入其住宅,在其不知情的情况下将自己的女儿下葬,认为按照1875年《公共卫生法》中的第142条规定,在未能拿到法律许可证之前,普拉斯并没有资格授权闯入民宅,因而博维是在违法做事。虽然博维与普劳斯结合当时的卫生恶化情况对其行为作出了合理解释,还指出原告妻子也支持这么做,但这件事情还是闹得沸沸扬扬,最后审判也是以让被告承担诉讼费用以抚慰原告悲伤情感而告终(40)“Law Reports:Action against a Medical Officer of Health and Inspector of Nuisances”,Public Health,1890,3,p.116.。这种照顾个体意愿的判决非常不利于卫生检查制度的正常运行。
因此,英国的卫生检查体系虽具有一定的强制性,体现出政府权威,但它更有着极为深刻的自由印记,人们可凭借自由意愿对抗卫生管制。这显示出近代英国的卫生检查既是政治工作,也是伦理任务,需忍受个人自由意志的放肆挑衅。
五、结语
随着近代英国公共卫生状况的恶化,政府开始全面介入公共卫生管理,卫生检查作为中央政府进行卫生管理规划发展的必要参考,受到极大重视。卫生检查制度构筑发展,大量卫生检查员受聘上岗,他们勤奋好学,充分利用设备,全身心投入卫生检查工作中,并着力创建团队,强化职业认同,提升政治影响力。在他们的努力下,英国政府决策层充分了解到国家各个领域的基本卫生状况,进而能颁行法案,有针对性地科学管理相关事务,从而促进了英国社会公共卫生状况的改良,也使广大民众身心健康获得有力保障,为后续英国的福利国家建设奠定了基础。对此,有学者指出,卫生检查的全面实施与检查员团体构筑及政治影响力的扩大使国家能准确掌握各地的不足和缺陷,有针对性地强化了对整个社会的公共卫生乃至食品和水资源质量等民生事务的管理,极大提升了维多利亚后期及爱德华时期(1871—1910)整个英国社会对抗各类疾病的能力(41)Philip Harling,“The Centrality of the Locality:The Local State,Local Democracy and Local Consciousness in Late-Victorian and Edwardian Britain”,Journal of Victorian Culture,2004,9(2),p.219.。
但是,由于卫生检查带有权威监督的强制色彩,因此也受到了公众的质疑。它体现出近代英国社会发展的基本特征,凸显了国家权威和公众意愿之间存在着持续不断的博弈,且后者通常还是具有优势的。就卫生检查制度运行的实践来看,社会大众的自由意志极为强势,能左右卫生检查制度的实际施行。这意味着在英国这样一个崇尚自由主义的国家,所有的政府管理者及卫生管制人员虽有管辖社会的权力,但都要受“个人自由神圣不可侵犯”原则的约束。
而在具体的卫生检查制度实施运转过程中,检查员也必须要直面公众责难和舆论发酵的威胁。当检查员细致地检测公众时,公众也在审视着他们,随时准备用个人自由意志进行对抗。在许多英国民众看来,卫生检查员根本就是一群“无孔不入的官僚”,随时准备侵犯私有财产,闯入私人领地。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英国社会中,这种对卫生检查工作的仇视态度和言辞表达在许多大众读物中都极其常见。比如在1897年,当时的流行性报刊《泰晤士报》(Times)上就登载了许多针对卫生检查员的谩骂,有人说他们是“卫生恐怖制造者”,也有人说他们是“无比挑剔的怪人”以及“事事都要管的老太婆”,各种辱骂言辞应有尽有(42)“The Powers of Sanitary Inspectors”,British Medical Journal,1897,2,p.1018.。英国民众的这种态度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此后英国政府卫生决策的基本底色:尽可能尊重个人自由,如非必要,政府不会强求民众接受卫生管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