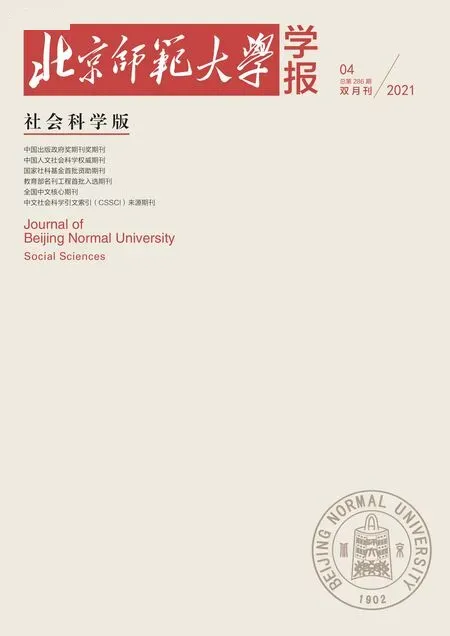儒家道德教育具身性的当代阐释
李申申,常顺利
1.河南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开封 475004;2.信阳学院 教育学院,信阳 464000
当今,我国道德教育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便是德育实施中“知行不一”、“身心分离”的问题。如果认真地对我国的德育历史进行历时性考察的话,我们会发现,“知行合一”、“身心合一”反而是我国传统德育文化的鲜明特色。那么,儒家德育文化中是否本身就潜藏着某种以西方现代性为蓝本而建立起来的德育体系所不具备的某种特质呢?是否因为在西学东渐的现代教育体系建构中,我们丢失了这一特质而导致了德育实施中“知行不一”、“身心分离”的问题呢?
一、具身德育提出的背景及其思考
(一)具身德育的提出是西方学界对其自身传统的反思
德育的具身性或称具身德育,是强调道德主体的身体与内部心理相互作用的德育范式,它反对仅仅将身体作为主体内部道德心理与环境相互作用的中介和容器,而将身体纳入到个体进行道德建构过程的中心(1)陈潇等:《具身道德:道德心理学研究的新取向》,《心理发展与教育》,2014年第6期。。它强调主体的生理体验在道德建构中的重要作用。
具身德育是针对德育过程中重“心”轻“身”的离身德育而提出的,而离身德育在西方有着深远的历史渊源。离身德育模式可以溯源到古希腊时代。从追求道德概念的“本质”出发,苏格拉底提出了“美德即知识”的论断,将道德教育视为一种知识教育。柏拉图提出了理念世界与感性世界的二元世界观,进而提出肉体是灵魂的监狱。他认为,灵魂的本质最贴近理念世界,因此教育的过程是以心灵训练为主的“回忆”的过程。亚里士多德从他的灵魂说出发,认为植物灵魂、动物灵魂、人的灵魂分别对应人先天所具备的三种不同的心理特性,即营养、欲望和理性,而理性是人类最高贵的品质。作为社会控制者的统治阶级,应该通过心灵的教育来发展理性,躯体的训练是与以欲望为主导的底层人民相适应的。因此,亚里士多德不仅提出了身心二元论的思想,而且还进一步指出心灵的教育是比躯体的训练更高贵的教育。欧洲中世纪,则是在浓郁的基督教氛围中,为拯救灵魂而对肉体进行惩罚,将神与人、灵魂与肉体加以二分。近代哲学家笛卡尔的心物平行论,更是将道德品质的培养视为“理性人格”的养成,德育成为了与身体无关的“离身”的心灵训练。而洛克早就看出离身德育存在的问题,他从“一切知识来源于经验出发”,指出无论是智力教育还是道德教育都需要身体活动的参与,并进一步指出体育不仅具有健康的价值,也具有道德训练的价值。自然主义教育家卢梭在《爱弥儿》中也指出感官训练的重要性。在他看来,“锻炼感官并不仅仅是使用感官,而是要通过它们学习正确的判断”(2)〔法〕卢梭:《爱弥尔》,上册,李平沤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年,第161页。。但是,身心二分的去身性历史传统在西方学界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以冷峻的、二元对立的理性眼光看待和分析问题,以及身体的缺席,成为西方主流的认知方式,由此带来的消极后果不断引起人们的反思。
当代西方“具身性”哲学思潮的兴起,指向以近代笛卡尔为代表的“心物平行论”哲学的去身性以及由此所带来的困境。在这一思潮中,法国哲学家莫里斯·梅洛-庞蒂为其著名代表。梅洛-庞蒂在其以身体现象学、知觉现象学为基调的著作中,对“具身性”进行了较系统地阐述。在梅洛-庞蒂那里,“身体性”是其哲学的主调,他对知觉的身体性以及身体的意向性进行了揭示。他认为,知觉是主动的,是向真实世界,即胡塞尔所谓“生活世界”的原初开启。对知觉的分析中必须将意识同身体的内在关系纳入考虑。身体不只是一件物质性的东西、一个科学研究的对象,它同时也是经验的永恒前提。梅洛-庞蒂指出,人的知觉不是身体被动反映客观世界的结果,而是身体参与到了知觉塑造的过程之中了。他说,世界的问题,可以从身体开始。“身体的突出是对于纯粹意识的克服,是为了让意识摆脱超然状态。……于是主体不再是笛卡尔意义上的自然之光,它受制于自然倾向,受制于身体、世界、他人的关系。”(3)杨大春:《语言·身体·他者——当代法国哲学的三大主题》,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第151页。“思想不是依据自身,而是依据身体进行思考”,“身体对心灵而言是其诞生的空间,是所有其他现存空间的基质”(4)〔法〕莫里斯·梅洛-庞蒂:《眼与心》,杨大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63页。。“灵魂和身体的结合不是由两种外在的东西——一个是客体,另一个是主体——之间的一种随意决定来保证的。灵魂和身体的结合每时每刻在存在的运动中实现。”(5)〔法〕莫里斯·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姜志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125页。杜威也指出:“通过构成身体的机制以及表达,意志(及其他心智活动)已经赋予了它自己具体的存在。”(6)〔美〕杜威:《杜威全集》,第2卷,张留华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61页。因此可以说,西方“具身性”哲学思潮的兴起,直接指向近代以笛卡尔为代表的“心物平行论”哲学,间接指向传统西方哲学中的去身性以及由此所带来的困境。
具身哲学思潮的兴起,影响到西方具身认知心理学的产生。具身认知理论反对传统的认知理论将心智活动与感觉运动相割裂的身心二元论,强调主体的生理体验在认知结构形成中的重要作用。“具身认知”认为,认知是包括大脑在内的身体的认知,身体的解剖学结构、身体的活动方式、身体的感觉和运动体验决定了我们怎样认识和看待世界,决定了我们的思维风格,我们的认知是被身体及其活动方式塑造出来的,它不是一个运行在“身体硬件”之上并可以指挥身体的“心理程序软件”。因此。认知是身体的认知,心智是身体的心智,离开了身体,认知和心智根本就不存在。
具身哲学、具身认知思潮对当代西方教育理论与实践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使教育中身体的“在场”、具身性教育被提上了日程并日益兴盛。在道德教育领域,则提出了具身德育的概念。在具身性教育的倡导中,承认“默会知识”(又称“缄默知识”、“内隐知识”)的存在及其地位,成为其重要基础。“默会知识”的概念由英国物理化学家、哲学家波兰尼在其名著《个体知识》中首先提出,它主要是相对于显性知识、明确知识而言的。波兰尼认为,默会知识是一种个体知识,与个体的个性、经验以及所处的情境交织在一起,它深深植根于个体行为本身,与认识主体须臾不可分离,默会知识的获得必须经过“寓居于身体”。由此可见,“默会知识”是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知识,是一种经常使用却又不能通过语言文字符号予以清晰表达或直接传递的知识。“默会知识”的提出,是对传统的实证主义将知识看成是完全客观的、静态的一种挑战和质疑。
(二)中国传统德育恰是一种具身德育
在中国文化语境中,“身体”是心身合一的完整体,既包含智慧的心灵,也包括血肉之躯。诚如有学者指出:中国古代“身体哲学所关注的身体并不是完全常识意义上的身体,而是古代哲学家心目中的一种身体”,“是经过现象学还原的、现象学意义上的身体,所以说它是一种具有本体论意义的身体”(7)张再林:《作为身体哲学的中国古代哲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256页。。
建基于“身体哲学”之上的中国古代教育是一种以育德为根本的“人的教育”,是启迪人生智慧的教育。教育的过程就是培育人追寻并实践涵盖天地人总规律的至高真理——“道”的过程。而人对“道”的尊奉和追寻是一种理性的活动,这种活动是人的身心两方面共同努力的过程。因此,中国传统教育历来奉行身、道不可分离。《中庸》明确说,“子曰:‘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8)《中庸·第十三章》,王国轩、张燕婴、蓝旭、万丽华译:《四书》,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120页。,“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9)《中庸·第一章》,王国轩、张燕婴、蓝旭、万丽华译:《四书》,第118页。。孟子说:“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10)《孟子·公孙丑上》,杨伯峻:《孟子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73页。许衡认为,“道”应是“众人之所能知能行者,故道不远于人”,否则“高远难行之事,则便不是道了”(11)许衡:《〈中庸〉直解》,淮建利、陈朝云点校:《许衡集》,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13页。。王夫之认为:“性者道之体,才者道之用,形者性之凝,色者才之撰也。故曰,汤、武身之也,谓即身而道在也。”(12)《尚书引义卷四·洪范三》,王夫之撰,船山全书编辑委员会:《船山全书》,第2册,长沙:岳麓书社,2011年,第352页。王艮更是明确地说:“身也者,天地万物之本也,天地万物,末也”,“身与道原是一件,至尊者此道,至尊者此身。尊身不尊道不谓之尊身,尊道不尊身不谓之尊道”(13)王艮:《王心斋全集》,陈祝生等校点,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33、101,37页。。因此,张再林教授认为,较之西方的意识哲学,中国古代哲学特有的属性就是“根深蒂固的‘身体性’(the body of subject)。这种‘身体性’表现为中国古人一切哲学意味的思考无不与身体有关,无不围绕着身体来进行,还表现为也正是从身体出发而非从意识出发,中国古人才为自己构建了一种自成一体,并有别于西方意识哲学的不无自觉的哲学理论系统。我们看到,这种‘身体哲学’不仅是对中国哲学本来面目的真实还原,同时,还使其以一种‘准后现代’的气质与特性,与西方后现代主义的后意识范式的哲学殊途同归,并从中体现出一种不无前瞻和具有现实批判眼光的人类新的时代精神”(14)张再林:《作为身体哲学的中国古代哲学》,序,第3-4页。。蒙培元教授指出:“与西方形而上之‘理念’不同,古人所谓的‘大道’实乃下学上达、显微一体的‘身道’。”(15)蒙培元:《古为今用:走向世界的中国哲学研究——〈评中国古代身道研究〉》,《陕西日报》,2015年5月8日,第5版。因此可以说,中国古代哲学不仅推崇精神,而且也对肉体持有一种乐观主义态度,“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16)《孝经·开宗明义》,汪受宽:《孝经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2页。,这与柏拉图将理念与肉体进行二分、视肉体为灵魂的监狱的观点截然不同。
二、儒家道德教育的具身性特质
传统的儒家德育思想中蕴含着明显的具身特性。古代中国人不仅通过认识“仁”、“义”、“忠”、“信”等道德概念的本质规定性来完善品德,而且还通过以“修身”为核心的“修齐治平”的实践路径来追求“圣王”的道德境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源远流长,蕴育了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品格,……支撑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今天依然是我们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强大精神力量。”(17)《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年,第158页。因此,我们可以通过对儒家道德教育的具身性和幸福观的挖掘,来探究中国传统社会个人品德的完善与个人幸福实现的关系,并从中收获对当代中国道德建设和幸福中国建设的启示。
(一)当下呈现:儒家德育的情境化
儒家德育的具身性集中表现在“修身”思想上。四书之一的《大学》,其核心内容是“三纲领”和“八条目”(18)“三纲领”是指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八条目”是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三纲领”指明了传统中国人的终极追求,那便是“止于至善”;“八条目”指明了追求至善的修养方式,这一方式在本质上是一个“內圣外王”的过程。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实际上就是“內圣”的过程,齐家、治国、平天下则是指“外王”的过程,而能够将“內圣”和“外王”连接在一起的就是“修身”。作为“內圣”和“外王”桥梁的“修身”便是中国人追求至善的关键。因此,“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19)《大学·第一章》,王国轩、张燕婴、蓝旭、万丽华译:《四书》,第106页。。而修身的过程,就是在具体的情境中身体和精神二者融为一体地同步得到升华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无论是通过格物、致知来达至诚意、正心的思想,还是后来发展了的孟子的“良心”说和王守仁的“良知”说,都是在具体的情境中加以实现。故而,情境化的德育模式乃是儒家德育具身性的显著特征之一。
儒家中的心学一派,尤其陆九渊、王阳明等人,其提倡的学说似乎给人一种只讲心性而与情境无关之感,但事实并非如此。阳明心学中的“见在良知”和“当下呈现”就是对情境化这一特征的深刻发挥。“见在良知”和“当下呈现”作为继王阳明之后当代新儒学重要的哲学命题,起源于熊十力先生与冯友兰先生的一次论争,而后被作为“在场者”的牟宗三先生生动地记录下来。熊先生认为,“良知是真真实实的,而且是个呈现,这须要直下自觉,直下肯定”(20)牟宗三:《牟宗三先生全集》,台北: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4年,第78页。。“见在良知”本由孟子“良知”、“良能”说发展而来,借用佛教术语加以阐发。“见在”据《俱舍论》所载,意为“自然出来,不假造作安排者”,同时也指现在这一时间范畴(21)《佛学大辞典》,台北: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年,第2000页。。“良知”在心学一派的儒家看来,是“不虑而知”、“不学而能”的一种先天道德。“见在良知”表达了人的道德情感是在现在的具体的道德情境中被激发和显现出来的。那么,人被激发的道德情感又是如何呈现的呢?王阳明认为,“良知的本体”具有活动的本性,即由心灵的感动到达躯体活动的“当下呈现”。在道德情感上,它表现为“心自然会知,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22)王阳明:《传习录》,上册,扬州:广陵书社,2016年,第6页。。在道德实践上,则正如《传习录》中所言:“君子之酬酢万变,当行则行,当止则止,当生则生,当死则死,斟酌调停,无非是致其良知,以求自慊而已。”(23)王阳明:《传习录》,中册,扬州:广陵书社,2016年,第68页。可见,“见在良知”和“当下呈现”的命题凸显了中国传统道德哲学的几个特征:首先,道德是一种具体情境的呈现。其次,道德的活动是一种“智性的自觉”,即作为一种理智与情感参与其中的经验活动。再次,德育的过程表现为外在的情境激发先验的道德观念,进而使“可能的德性”转化为“实在的德行”。在这一过程中“身体”居于核心地位,“良心”需要“身体”参与外在的情境才有激发的可能性,“当下呈现”的过程更需要“身体”的积极行动。所以,“见在良知”和“当下呈现”显示出了阳明学说的情境化特征。而与此同时,强调向外求索来进行身心修养的程朱理学,其格物致知的理论虽与陆王心学路径有别,但同样强调“知”与“行”、“身”与“心”的融为一体,其情境化的活动特征亦非常明显。程颐把“格”理解为“至”,把“格”当作获得伦理知识和践行道德行为原则的手段。而朱熹则把“格”解释为“穷”、“尽”,指出“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24)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3页。。这一过程正是在情境之中展开的过程,是知与行、身与心一体的内外交养的活动过程。
(二)肉身证道:儒家德育的自省性
儒家德育的自省性,有两层含义:作为修身方式而言,儒家强调个体要经常对自己的言行进行反省,以达到“诚意正心”的目的;作为修身的目的而言,“自省”意指道德自决意识的自我觉醒,也就是儒家所说的“成圣成贤”。

其次,从修身目的上来考察儒家德育的自省性。儒家认为,“修身”的目的是为了培养理想人格,也就是“希圣希贤”。据《大戴礼记·哀公问五仪》中所载,孔子认为圣人就是“知通乎大道,应变而不穷”(32)刘向整理,张兆裕编著:《荀子》,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5年,第349页。的人。《中庸》中对圣人有类似的描述,认为圣人能“发育万物,峻极于天”(33)《中庸·第二十七章》,王国轩、张燕婴、蓝旭、万丽华译:《四书》,第130页。。孟子则认为,追求“成圣成贤”是人的天赋倾向,人生来就具备追求善的可能性,也就是“四端”,并提出“人皆可以为尧舜”(34)杨伯峻:《孟子译注》,第255页。。荀子虽然主张人性本恶,但也认为通过“化性起伪”可以向善,因此提出“途之人可以为禹”(35)王先谦:《荀子集解》,沈啸寰、王星贤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442页。的观点。儒家德育所追求的“圣人”目标首先是内在修行功夫的结晶,它与康德所强调的人应该出于自身的理性而引导自己的行动,从而成为自立、自决的道德主体的思想又极为相似。
由上可见,人类自古以来并不一直存在身与心、灵与肉的天然对立。相反地,中国人认为身体是父母精血所化,应该存养爱护;欲望虽然寄托于身体,但可以通过“修身”而达至道德自决的境界。具身的道德也可以实现人类追求至善的理想,因为“肉身亦可证道”(36)“肉身证道”这一概念是针对基督教的“道成肉身”的概念提出的。本文是指当身体进入道德领域,其自身便具有了超越性的形上维度,这一超越性的维度使道德主体完成了身体有限性与无限性的矛盾统一。这一概念的最终依据在于,中国传统儒家观念中人类自身最高价值的实现并不依赖于彼岸世界上帝的拯救。。
(三)圆善功成:儒家德育的圆融性
道德就其本质而言,既是调节社会关系的平衡机制,又是主体追求自我实现的超越范式。儒家德育的实践特性就表现在它一方面以“五伦”关系的规范来追求人与人关系的最大和谐,另一方面又将道德的完善与以“自我实现”为目的的幸福观相结合。
在中国人看来,个人遵循道德和收获人生的幸福存在着朴素的因果关系。这种因果关系让中国人相信道德与幸福是一体的,所谓止于至善就是在道德的生活中获得幸福,即牟宗三先生所说的圆善。牟宗三先生曾经尝试用“智的直觉”(37)牟宗三先生通过将康德的“自由意志、灵魂不朽、上帝存在”三大悬设化于“无限智心”,并将其作为圆善可能的最后依据。和“诡谲的相即”(38)“诡谲的相即”强调,德福关系既不是分析关系,也不是简单的综合关系,而应该看作相互转化的辩证关系。等概念来证成儒家理论体系中德福的一致性。但是,这种重圆善而轻功成理论体系经常被批评为“本质上是一种极端精英主义”(39)张俊:《牟宗三对康德圆善的超越与局限》,《孔子研究》,2008年第4期。。因此,我们不妨尝试从人文的角度在普通中国人的生活追求中感受一种德福关系的朴素认识,它就是将“圆善”与“功成”、“身”的物质性的、功利性的福报与“心”的超脱性的福报统一在德性幸福中的一种生活方式。
1.身:感性之乐的幸福
由于幸福一词本身内涵的多样性,很难找到一个确切的现实指涉来充当幸福的充分表现形式和等价物。所以,以一种完全抽象的角度来对幸福进行客观的描述几乎是一种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此,“乐”更适合来表达普通中国人对幸福的直观心理感受。感性之乐是传统的中国人对幸福最基本的感受,它既包括孟子的“父母俱存,兄弟无故”(40)杨伯峻:《孟子译注》,第285页。的亲情人伦之乐,也有孔子的“三月不知肉味”(41)⑧⑨ 杨伯峻:《论语译注》,第68、67、58页。的闻韶之乐。由此,感性之乐的基本内容,既包含忧虑亲人身体康健的内容,也包含五官对应外界刺激的审美体验。而前者包含对“父母兄弟”的祝福之意,后者表达出对上古君王嘉言懿行的崇敬之情;前者反映“孝悌”之德,后者反映对“帝范之君”由赞颂而追随之德。可见,感性之乐既是传统的中国人追求幸福的基本层面,又是身体与内部心理相互作用的德育过程。传统的中国人这种对幸福的特殊理解,使得幸福在中国超越了现世欲望的满足,而具有了德育的价值。
2.心:理性之乐的幸福

3.“身心合一”的理想人格
安乐哲认为,中国哲学中的“身体”是一种“身心互渗的过程”(43)安乐哲:《自我的圆成:中西互镜下的古典儒学与道家》,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69页。。因此,中国哲学中“心性”与“身体”乃是一个统一体的两个侧面。这其中就包含传统的中国人对于“德-福”、“身-心”等关系的辩证认识。就“德-福”的关系而言,“闻韶之乐”的感性幸福和“孔颜乐处”的理性幸福归根到底是一种德性的幸福。因为“闻韶之乐”并不仅仅源于一种音乐的感官刺激,更是追忆古代贤王的德教之乐。“孔颜乐处”本身就是一种超越物质享受的德性幸福。因此,对于传统的中国人而言,无论是感性幸福还是理性幸福都是一种德性幸福。就身体与心灵的关系而言,传统的中国人只在“身心一元”的前提下讨论二者的区别,而不会用身心二分的方法来认识二者的关系。“仁”是传统的中国人所追求的理想人格,而郭店楚简《五行》中的仁字是身心二字上下结构组合而成的,这说明传统的中国人所追求的理想人格必然是一种通过“身心合一”才能达至的人格。总之,感性之乐与理性之乐既表现为一种“德福一致”的圆融追求,又是“身心合一”的德教过程。因此,圆善功成的道德实践逻辑并不需要繁难的逻辑推理,它却可以作为内嵌于传统文化基因中的绝对命令而被信仰和传承。可以说,儒家德育的实践化是在主体的道德行动中收获对道德准则的肯认,并在这种肯认的过程中达致感性幸福和理性幸福、道德和幸福的圆融与完满。
三、儒家道德教育具身性的形成基础
对于中国传统文化而言,儒家道德教育的具身性具有我固有之的特性。那么,传统的中国人为什么会采用这种“身心一元”的德育模式呢?它在具体的历史时空中又是依靠什么样的社会基础得以运行的呢?也许我们可以从“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和“差序格局”的传统社会的考察中得到一些答案。
(一)“一元世界”:“形上”维度的解释
1.“天人合一”的宇宙人生观
一个文明图式中总存在着一个价值内核,如果我们尝试对中国的传统道德文化进行“基因测序”,会发现传统中国的道德文化具有明显的一元论特征。这种一元论的思维方式将天地人纳入一个大系统中,认为各个方面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且“一损俱损,一荣俱荣”。而所有的“存在”所共同遵循的是至尊的“道”,只不过是“理一而分殊”(44)《河南程氏文集》,卷第九,《答杨时论西铭书》,程颢、程颐:《二程集》,王孝鱼点校,第609页。,“在天则为天道,在地则为地道,在人则为人道”(45)《河南程氏遗书》,卷第二十二上,程颢、程颐:《二程集》,王孝鱼点校,第282 页。。从文化场域的角度来看,中国人对天的理解主要有两种:一为“自然之天”,一为“伦理之天”,而以后者为重。这一思维方式是由中国传统各家各派,尤其是由同源于《易经》,而向不同方向发展、交融互补的儒、道两家所共同秉持。《易经》明确说:“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46)《易·上经·乾卦》,黄寿祺、张善文:《周易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19页。

总之,与西方“二元论”世界观不同,儒家无意为现世的感性世界树立一个完美、至善的理念世界来反观、批判现世世界。在中国人的道德生活中,“人”具有了与“天”同在的道德主体性。“天”与“人”是以“仁”为逻辑起点。因此,中国人理解的好的生活,必然是一种德性的生活,一种存在于现世而非理念世界的生活。所以,中国哲学中,那种“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的“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念在本质上并不是一个本体论的命题,而应从价值哲学的视域将其理解为对生命存在形式的一种解释。“伦理之天”并不作为人顶礼膜拜的客观存在,而是与人的生命合二为一的统一体。这种一元论的哲学思想使传统的中国人不仅把自己作为认知道德的主体,更是作为“我欲仁,斯仁至矣”(64)杨伯峻:《论语译注》,第73页。的道德行动者,在“参天地,赞化育”的生命实践中,与天地万物发生联系。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发现,儒家的道德理性是在感性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2.“主客一元”的认识论
在“天人合一”的观念中,主体与客体、思维与存在是几乎不具有边界的模糊存在,这就导致儒家在认识论上不会采取“主客二元”的方式去认识世界。孟子提出的“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的命题实际上也是一个认识论问题。这一命题将“尽心知性知天”的认识论根基建立在了“心物不二”的一元论之上。宋明时期,理学家和心学家们将这一命题实现了理论化。张载的认识论是“大心体物”,即通过发明本心将“心之知”和“物之知”内外交融,达到认识宇宙本质的状态。正是这种基于一元的认识论,汤一介在谈到横渠四句时指出,“为天地立心”就是“为生民立命”(65)汤一介:《论“天人关系”》,《中国哲学史》,2005年第2期。。相比于张载,程颢的“浑然与物同体”(66)《河南程氏遗书》,卷第二上,程颢、程颐:《二程集》,王孝鱼点校,第16页。的观点更具有一元认识论的特点。他提出,人通达“天理”的方法就是“体贴”。所谓“体贴”,就是要用身体去体会、体察、体悟,要靠经验,身体力行地参悟学问(67)温海明:《从认识论角度看宋明理学的哲学突破》,《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而将中国传统哲学中“主客一元”的认识论发挥到极致的当属王阳明。王阳明提出:“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本体便是知,知之所在便是物。”(68)王守仁:《王阳明全集》,吴光等编校,第6页。王阳明的这一观点旨在说明,心通过意识连接外物,人的生活被赋予意义的过程即是心与物情境式交融的过程。儒家“一元论”世界观使得传统中国人的道德理性是一种建立在感性基础上的实践理性,“身心合一”、“知行合一”的具身德育模式也就成了自然而然的选择。因此,与苏格拉底认为“美德即知识”不同,儒家认为,人的道德是在具体的生活情境中表现出来的。道德不仅仅是通过对道德概念本质的把握获得的,更是在具体的生活情境的应用中达到“习矣而不察焉”(69)杨伯峻:《孟子译注》,第279页。的境界。以孔子的道德教育实践为例,孔子对于“仁”、“礼”、“忠”、“孝”等核心概念并未做出逻辑学上的解释,而是根据弟子们在生活中遇到的具体问题对“仁”、“礼”、“忠”、“孝”等概念进行解释。如,《论语·为政》中孟懿子、孟武伯和子游问孝,孔子并未解释什么是孝,而是依据三人的身份和具体的家庭情况给出行孝的不同做法,即“无违”、“父母唯其疾之忧”、“色难”三种不同的答案。
(二)“差序格局”:社会学维度的解释
道德把握世界是通过善恶评价的方式实现的(70)黄云明:《论道德的本质》,《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1期。。传统中国的社会结构,为儒家通过道德教化的方式实现“化民成俗”的目的提供了天然的道德评价机制,而这种道德评价机制也为儒家具身性德育模式提供了运作机制。
1.差序格局下的乡土中国
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将社会类型划分为乡土社会和公民社会,前者又称礼俗社会,后者又叫法理社会,传统中国属于典型的乡土社会。在乡土社会中,人的社会关系是通过血缘和地缘关系建立起来的,呈现出“差序格局”。所谓“差序格局”,就仿佛将一颗石子投入一潭止水之中,石子溅起的涟漪形成水的波纹,一圈一圈地荡漾开来,就形成了多重同心圆结构的“差序格局”。费孝通先生认为,儒家所谓的人伦即是“从自己推出去和自己发生社会关系的那一群人里所发生的一轮轮波纹的差序”(71)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7页。。早在1947年,美国著名社会学家雷德菲尔德(Redfield)在《乡土社会》一文中就对乡土社会的典型特征作了如下概括:“这样一个社会规模小而孤立,无文字,同质性高,群体团结意识强;其谋生方式由传统习俗所制约……家族群体为行动单位,(社会)由神圣而非世俗的力量主导。”(72)阎明:《“差序格局”探源》,《社会学研究》,2016年第5期。可以看出,雷氏采用了韦伯以来社会学研究的“理想型”建构,但是雷氏对乡土社会的描述只适用于文明程度低的原始部落,而并不适用于中国的传统社会结构。费孝通先生用“差序格局”来描述传统中国乡土特征就更加接近对传统中国的客观描摹:“差序格局”展示了一个双向互逆的多重同心圆社会网络关系结构,就是从“己”到“天下”,即 己 → 家 → 国 → 天下;反之,是从“天下”到“己”,即天下→国→家→己。也就是说,费孝通先生认为“差序格局”中的传统中国,人与人的关系是一个能放能收的过程。然而,翟学伟教授指出费孝通的理论犯了一个“合乎逻辑的错误”,他认为中国社会的最小单位不是个人,而是扩大的家庭。因此,中国人不会为了自己而牺牲家庭,相反他们会为了家庭牺牲自己(73)翟学伟:《再论“差序格局”的贡献、局限与理论遗产》,《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因此,当“差序格局”中的关系往回收的时候应该是天下→国→家的过程。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概括出儒家道德教育何以通过社会教化方式进行的社会结构的特征:首先,传统中国是由一个个低流动性的小规模社会团体组成的。其次,家族是传统中国社会基本的行动单元,中国社会的典型特征是家族本位。再次,传统中国人具有明显的“泛家化”倾向,国与家的边界相对模糊。最后,在传统中国,人与人之间相处的行为准则由其在差序格局中所在的位置决定。由此,在“差序格局”中,乡绅即乡贤起到了承上启下的组织作用。因此,中国传统乡村文化也可称之为“乡绅文化”或“乡贤文化”。
2.差序格局下的儒家德育运行机制
差序格局下的乡土中国会对德育模式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可以从以下几点来进行考察:
首先,正由于传统中国是由一个个低流动性的小规模社会团体组成的,因此可以说传统中国的一个家庭可能是与另一个家庭世代比邻而居的,一个村庄即是一个人一生的活动范围。其次,由于家族是传统中国社会基本的行动单元,也就意味着一个村庄共同生活的人应该都具有或近或远的血缘关系。这种血缘家族制虽有其局限性但也有其正向功能,对当时和后世都曾有其积极的正向影响。最显著的,就是它以血缘为基础,对人们相互之间在形成浓厚情感方面产生了较大作用。在西周时期,这一体制相对于商王朝的用人殉葬制和用人做祭品制,有着相当大的进步作用,它对于联络各阶层民众的情感,发展社会生产力,确实起到了不少的作用,因而出现了周初的“太平世”。孟子也曾论及这种以血缘情感为纽带的社会,形成了“死徙无出乡,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74)《孟子·滕文公上》,杨伯峻:《孟子译注》,第108页。的社会民俗和风尚。再次,由于传统中国人具有明显的“泛家化”倾向,这就不仅使得家与国、公与私的概念相对模糊,同时也使得儒家“亲亲而仁民”(75)杨伯峻:《孟子译注》,第298页。的伦理原则可以将忠与孝、悌与义等不同层次的价值观念具体到日常“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76)杨伯峻:《论语译注》,第20页。。乡绅们在乡间承担着传承文化、教化民众的责任,同时参与地方教育和地方管理,引领着一方社会的发展。“惟地方之事,官不得绅协助,则劝诫徒劳,绅不得官提倡,则愚迷弗信。”(77)《樊山政书·批延川县岁贡张清泉禀词》,樊增祥:《樊山政书》,卷十五,台北:文海出版社,1973年,第1275页。乡绅作为儒家道德武装过的文化精英,自然也就有了被普遍认可的“德高”权威。而实际上,在乡村充当仲裁者身份的乡绅一般也是家族中的长者。“绅士居乡者,必当维持风化,其耆老望重者,亦当感劝闾阎,果能家喻户晓,礼让风行,自然百事吉祥,年丰人寿矣。”(78)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27页。乡绅们“敦孝弟以重人伦,笃宗族以昭雍睦,和乡党以息争讼,重农桑以足衣食,尚节俭以惜财用,隆学校以端士习,黜异端以崇正学,讲法律以儆愚顽,明礼让以厚风俗,务本业以定民志,训子弟以禁非为,息诬告以全良善,诫窝逃以免株连,完钱粮以省催科,联保甲以弥盗贼,解仇忿以重身命”(79)《圣谕十六条》,陈淑均、李祺生编修:《噶玛兰厅志》,卷三下,台北:大通书局,1984年,第120页。。因此我们可以看出,乡土中国形成了一种由家庭、社会、学校三位一体的道德评价机制。这种全覆盖式的评价机制使得任何道德失范行为都必须以几代人的名声为代价,儒家道德准则因而具有了很强的约束力。另外,由于乡绅是在日常生活中完成其对本地的教化责任的,所以往往以外化的行为为榜样,同时以族规和家训等形式对普通民众进行心灵训练,因此也就产生了“身心合一”、“知行合一”的具身性德育模式。
四、儒家具身性道德教育的现代价值
儒家道德教育的具身性在解决当前道德教育“身心分离”、“知行不一”以及“家庭、学校、社会道德教育相分离”等问题时具有重要的现代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儒家德育的情境性是“身心统一”的过程,也是“知行合一”的过程,更是一种“良心”的教育。例如,前已述及的儒家心学一派所倡导的“见在良知”强调人在具体的生活情境中面对道德问题所引发的心理体验,“当下呈现”则强调道德主体由“良知”引发的针对具体情境对道德责任的行为实践。值得注意的是,“见在良知”和“当下呈现”必须一体考虑,才能真正对儒家德育的情境性特征进行把握。只考虑“见在良知”会误认为儒家德育是一种不可证明的神秘主义规训,而只着重认识“当下呈现”又容易把儒家“当行则行,当止则止”的道德实践等同于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中关于德性的“实践智慧”。实际上,“见在良知”和“当下呈现”使得道德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当它被嵌入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时,它仍然处于活生生的和不断实现的过程中,并且这种生活会“责成我们造就出本已存在的东西”(80)〔加拿大〕查尔斯·泰勒:《黑格尔》,张国清、朱进东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年,第575页。——良心。当市场超越民族国家的界限成为一种世界性主宰力量时,生存与良心便一并成为道德意义上的绝对命令。当现代人在玩笑戏语中追问良心价值几何时,实际上就是在追问我们民族曾经的道德基石是不是也可以用市场的规则来衡量。在这样的背景下,借用儒家德育的传统资源来呼唤“良心”教育绝对不是一次无奈的文化抵抗或临时的危机应对,而是在伟大复兴的征途中必须进行的民族道德的现代重构。
其次,儒家德育的自省性彰显了人在道德领域的主体性,其反省的过程也是一种智性的道德修养。儒家德育的自省性反映了主体道德建构由自我反省到道德自觉的过程,其道德的完满追求是“成圣成贤”的人生境界。这不仅为当代德育提供了提高自我修养的有效途径,而且也是帮助主体树立理想信念与自觉的责任担当的重要教育资源。这种“肉身证道”的修养路径与自觉意识,其本质内涵有两点:一是,人在道德领域的主体性得到了充分地彰显。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天、地、人三才并列,人的德性完善并不是神性在人身上的展现。相反地,“人”和“天”是一个统一和谐的整体,人通过践行“仁”而达至天道。二是,人通过自省完善道德,是一种智性的道德修养。这种道德修养方式兼顾一般的道德原则和具体的道德情境。一方面,儒家德育的自省性是黑格尔所强调的以“思想的本身为内容,力求思想自觉其为思想”(81)〔德〕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39页。。这一层面的道德反思,强调主体道德理性功能的发挥,其旨在对一般道德原则本身进行反思。另一方面,儒家德育的自省性是经验中的反思,即如杜威所说的“识别我们所尝试的事和所发生的结果之间的关系”(82)〔美〕约翰·杜威:《民主主义与教育》,王承绪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58页。。这一层面的道德反思,强调主体应该在遵循一般的道德原则的基础上,在具体的道德情境中进行能动的道德实践。
再次,儒家德育的圆融性为道德教育提供了一种动力机制,也为德育的实施提供了两种迥异的可能。儒家德育的圆融性使得道德完满与人生幸福相结合,使得儒家道德可以以世俗的形态深入人心。“圆善功成” 的观念将道德本真性与目的性巧妙地相统一,德福关系的统一使得道德行动主体获得了道德行动的原初动力。与此同时,这种既重视“圆善”又重视“功成”的德福观念,为德育的实施提供了路径上的分野和对象上的分众。就德育路径而言,“圆善功成”的观念实际上提供了两种不同的道德建设路径。一是,牟宗三式的重视因道德自觉的建设而收获内在超越式的幸福的道德建设路径。二是,借用“善恶有报”、“余庆余殃”等观念使人们依靠现世的积德行善来收获功利性福祉的道德建设路径。就德育对象的分众而言,“圆善功成”的观念为德育的精准实施提供了一种可能。对于社会精英人群而言,德育的实施应考虑人们超越性价值的实现,可以将该群体的道德追求引向一种永恒的崇高事业;对于普通民众而言,如果只是将道德故事塑造成史诗般的不朽传奇,那种短暂的感动只是赋予了道德本身一种正当性的有力辩护,普通民众并不一定因这种情感认同而将道德理念转化为道德实践。所以,普通民众的道德教育应该强调一种对道德行为的物质性报偿,这种对幸福的即时感受会再次强化某一道德行为并转化为下次的道德动机。
最后,儒家德育的运作机制为现代德育的实施提供了具有系统论价值的历史借鉴,差序格局的社会结构为当今道德教育提供了重点突击方向。儒家以“五伦”为核心的道德体系顺应了多重同心圆结构的“差序格局”社会结构,其德育模式采取了具身性的社会教化来实施。这种将个体嵌套于所在环境的德育模式为现代德育将家庭、学校、社会道德教育相结合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借鉴。如果不能将道德教育纳入整个社会环境中来实施,那么道德就不可能成为一种生活方式而具备公共价值。当今道德文化建设的主要问题是把道德文化建设简单地当作道德口号的宣传,而不是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因而使得道德文化成为一场华丽的表演,而不是共同体一致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那么,道德文化建设如何才能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呢?张江华在《卡里斯玛、公共性与中国社会有关“差序格局”的再思考》一文中指出,中国社会的公共领域实际是私人领域的扩张和转化,差序格局中的圈子文化,催生出了卡里斯玛式的公共供给关系,使得圈子中心个体的道德性变得尤其重要(83)张江华:《卡里斯玛、公共性与中国社会有关“差序格局”的再思考》,《社会》,2010年第2期。另:卡里斯玛(Charisma)是德国社会学家韦伯从早期基督教观念中引入政治社会学的一个概念。韦伯认为,卡里斯玛是这样一类人的人格特征:他们具有超自然、超人的力量或品质,具有把一些人吸引在其周围成为追随者、信徒的能力,后者以赤诚的态度看待这些领袖人物。本文借此概念表达在中国差序格局的社会结构中,普通人对圈子中心精英人群所默示和践行的道德准则追随和模仿的倾向。。儒家德育的运作机制是将整个社会生活和个体的身心整体都纳入其中,而这种德育模式在考虑整体的同时没有陷入到一种大而无当的危险之中,其原因就在于,它充分发挥了“乡绅阶层”作为差序格局社会中中心个体道德性的榜样作用。这启示我们应该将当代社会精英的道德建设作为全社会道德建设的重点突击方向,而当代社会精英自身应该有一种自觉的道德意识。这种自觉意识应该时刻提醒自己,精英的符号不是社会特权群体的标志,相反地,它意味着一种对自己的言行将作为整个社会所垂范的榜样而产生的审慎和自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