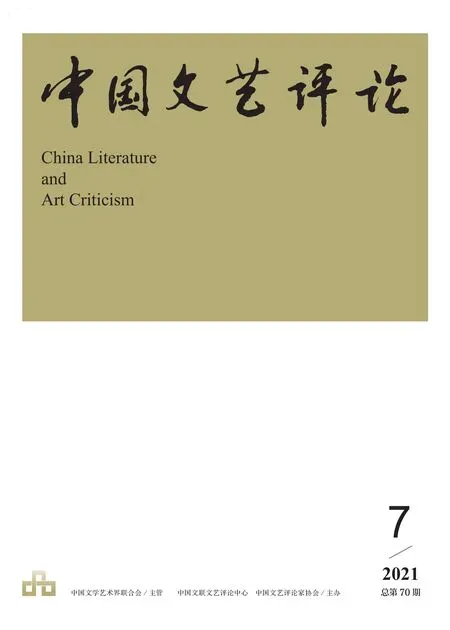数字交互舞蹈:脉络、原理及其中国实践
田 湉
“数字”是一个相对纯粹的技术概念。它是描述真实世界的一种特殊方式,是一种编码感官数据(声音、音乐、动作、布景、服装等)的特殊技术,它允许信息被交流、改变、操纵,最终以一种复杂的、潜在的智能方式被解释。
“数字表演”是表演的一种新范式,它“涉及计算机技术与现场表演艺术的结合,以及美术馆装置和基于计算机平台的网络”。广义的“数字表演”作品中,计算机技术发挥着关键作用,“包括现场戏剧、舞蹈以及多媒体表演艺术、机器人虚拟现实表演、使用电脑感应、激活设备或电讯技术的装置及戏剧作品,以及通过计算机屏幕访问的表现性作品和活动,包括网络剧场活动、MUDs、MOOs、虚拟世界、计算机游戏、CD-ROM和表现性网络艺术作品”。新技术使人们对戏剧和表演的本质产生了怀疑。当计算机成为表演行为和创作的重要工具,这无疑突破了传统戏剧、舞蹈等表演艺术中作为编剧、编导、表演者的边界。
数字表演艺术的理论来源可以追溯到未来主义。未来主义视觉艺术在艺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但是未来主义表演在很大程度上于剧场历史中被忽视了,尽管许多重要的未来主义宣言都是专门针对戏剧这类舞台艺术而不是视觉艺术的。“1909年至1920年间,意大利未来主义表演理论和实践奠定了数字表演的基本哲学和美学策略的基础。”那里的未来主义者们致力于一种新的综合和技术的表演形式,他们赞颂“机器”以及那个时代的“新技术”,寻求艺术与技术的结合以及不同艺术形式之间的跨界融合。
1915年,“未来合成剧院”的宣言用大写字母高喊:任何有价值的东西都是戏剧的。未来主义的领袖菲利波•托马索•马里内蒂(Filippo Tommaso Marinetti)也是一个剧作家,他将大量精力投入到表演实践中。1916年,未来主义者们探索出了一个数学公式,就像一个用来激活虚拟事件的计算机代码,被称之为“合成戏剧”。“合成戏剧”的元素包括绘画、雕塑、塑料、自由的文字、合成的噪音、语调、建筑等;而未来主义表演的基本原则和风格元素包括逻辑、塑料动态、平行动作、照片动态、发光透视法、虚拟演员、机器崇拜、“压缩”、“同时性”等,这些最终形成了数字表演艺术的核心。包豪斯设计、建构主义版式、达达主义蒙太奇和超现实主义电影等,也都成为了计算机参与其中的方法论先驱。
未来主义诞生于一种对重大的、改变生活的“新技术”的信仰和迷恋,“当代数字表演中的概念和实践不仅构成了一个可以追溯到未来主义的谱系,而且从根本上扩展了未来主义项目”。可以说,数字表演艺术以艺术创作和表演实践的方式呈现出了这种对“新技术”的信仰和迷恋。而当代的剧场表演从业者们,也延续了这样的观念和剧场实践。
一、数字舞蹈剧场的先声
数字化为剧场艺术带来了新的美学范式以及互动体验。被誉为“光之女神”的美国现代舞大师富勒、德国包豪斯的剧场大师施莱默和美国现代舞大师坎宁汉,都是投身数字舞蹈剧场实验的先驱者。这里并非要将他们的作品冠上“数字化”一名,而是他们无疑都在那个时代带来了革新的舞蹈形式,以及在灯光、服装、多媒体技术上的创新。
1.富勒
洛伊•富勒(Louis Fuller,1862—1928)是20世纪最受瞩目的现代舞者之一,她被认为是第一位将舞蹈和剧场灯效、电影新技术相结合的艺术家。她对数字表演艺术的探索从19世纪末开始一直延续到1923年,正值电影技术诞生时期。她较为著名的作品是《蛇纹石》(Serpentine
,1895),作品中,她将闪烁的灯光、自制的舞蹈服装以及电影投影、阴影效果结合在一起,以此来改变她在现场表演中的身体形态,试图让自己的服装在舞动过程中不断发光、变色。像当今的数字舞蹈艺术家一样,富勒减少了对身体本身的探索,而是用灯光、电影阴影等其他方式让作品呈现出一种具有幻影的表达效果。
图1 富勒作品《蛇纹石》(1895—1908)

图2 富勒作品《蛇纹石》(1895—1908)

图3 麦格雷戈灯光装置作品 《FAR》 (2012)

图4 麦格雷戈AI实验作品 《生活档案》 (2019)
富勒作品可以被看作是韦恩•麦格雷戈(Wayne McGregor)使用舞台灯光、多媒体的一种先期实验。麦格雷戈(1970—)是一位编舞兼导演,英国数字舞蹈的领军人物之一。2011年,他被授予一枚大英帝国司令勋章。他擅长使用“旧”技术来产生“新”效果,是最早唤起舞蹈技术的先驱之一。在他的作品《遥远》(FAR
,2012)中,照明的图案通过他的舞蹈而逐渐破碎,使其看起来从一种形状变形成为另一种形状,舞者身体各部分都可以照亮或形成阴影笼罩其他人。2019年7月,麦格雷戈使用AI探索编舞流程,现场展示了新作品《生活档案》。这是他正在进行的项目,该项目使用机器学习来创建以AI驱动的编舞工具,该工具预测并产生新的舞蹈动作。他将作品资料库中的五十多万个动作进行互动,以创建自己的编排,使用者可以通过一种有趣的方式来探索舞蹈。2.包豪斯
1922年,奥斯卡•施莱默(Oskar Schlemmer)的未来主义舞蹈《三元芭蕾》(Das
Triadische Ballet
)令包豪斯之舞风靡一时,为当前许多数字表演艺术的探索提供了重要的先期实践基础。在《三元芭蕾》中,施莱默设计了机器人服装,利用机械设备在舞台上快速移动,并将女性表演者的头部和手放置在科幻风格的银色金属球中。而在《棍舞》(Pole
Dance
,1920)中,施莱默在舞者身体上、关节上架满棍子,在舞者舞动身体时造成各种各样的几何图案,同时将身体在黑色剧场中隐去,让观众的注意力集中在形状不断变化的由棍子形态带来的几何视觉上。施莱默在20世纪20年代就已经将剧场中的叙事、空间、线条、平面、杂技抽象化到了新的高度。1923年,包豪斯(Bauhaus)的艺术家们首次公开展出了题为“艺术与技术——新的统一”的表演,打破舞台的狭窄界限以重新配置戏剧形式。包豪斯舞蹈剧场预示出了对人工智能机器人的基础构想,这在今天仍不过时。人体在空间中进行了彻底的重新定向,这种思维方式等同于数字环境和网络空间中对舞蹈本身的重新配置。
3.坎宁汉
1966年的《V变奏曲》(Variations
V
)促成了默斯•坎宁汉(Merce Cunningham)与美国本土机会音乐、前卫作曲家约翰•凯奇(John Cage)、美国电机工程师马克思•马修斯(Max Mathews)、韩国摄影艺术家白南准(Nam June Paik)等人的密切合作,他们共同探索音乐、舞蹈和技术之间的交互融合。1999年,坎宁汉的作品《两足动物》(Biped
)通过运动跟踪系统与计算机电脑软件的结合进行舞蹈创作,是较早的以追踪交互技术为媒介尝试互动的舞蹈作品。
图5 奥斯卡•施莱默 《三元芭蕾》 (1922)

图6 奥斯卡•施莱默 《棍舞》 (1920)

图7 默斯•坎宁汉《V变奏曲》 (196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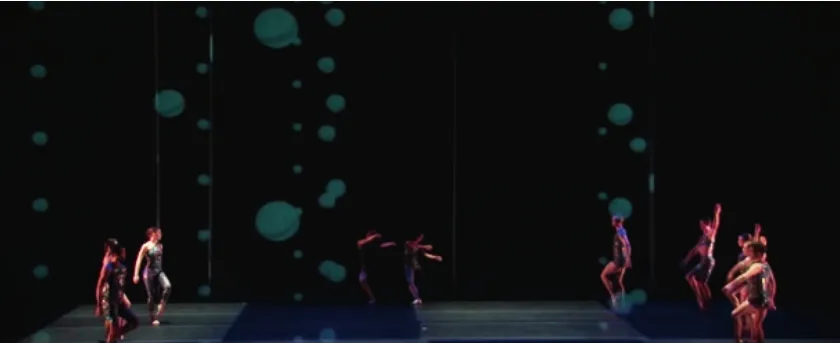
图8 默斯•坎宁汉《两足动物》 (1999)
当下,对数字舞蹈剧场进行探索的艺术实践仍在持续。一些大学和研究机构,一边研发新的数字交互技术和人体追踪技术,一边寻求与艺术家、舞蹈家的表演合作。艺术家Young Hay和香港城市大学计算机科学系合作,在叶国祥教授的指导下研发了Body-Brush系统,这种由身体驱动的界面可带来视觉美感,使用基于视觉的系统跟踪单个表演者,并使用该数据创建艺术品。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夏洛特分校软件信息系统系以及舞蹈与戏剧系共同制作完成的交互式舞蹈表演系统Dance.Draw,将舞者身体在空间中的运动输入到投影,呈现出可视化效果。挪威数字交互舞蹈团队在开展VIBRA项目时,使用NGIMU传感器和Myo臂带,以此探索交互舞蹈的表现力和艺术可能性等,同时,也有一些专门的数字交互舞蹈表演团体如德国纽伦堡回文舞蹈团(Palindrome Dance Company)、纽约三驾马车表演团体(Troika Ranch Performance Company),他们近20年来一直在做交互舞蹈作品,并不断寻求与技术设计师、编程设计师的合作。
二、数字交互舞蹈的原理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即开始广泛使用数字技术和计算机的时候,数字舞蹈一词就经常被应用于欧美戏剧表演和艺术创作中,许多交互式舞蹈系统在表演过程中使用了基于视觉的舞者动作跟踪系统,将数据应用于音乐和视觉效果的生成或转换。“在20世纪的最后十年,计算机技术在现场戏剧、舞蹈和表演中发挥了动态的和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新的戏剧形式和表演流派出现在互动装置和计算机系统上。”
1.定义
有关“数字交互舞蹈”的概念提出及其在中国的创作实践,笔者在《数字交互舞蹈的编舞原则及其身体策略》一文中已有描述:“数字交互舞蹈需要编舞与机器及其系统设计的高度整合。通常的数字舞蹈表演环境下,舞者的身体通过软件/交互系统连接投影仪以唤起数字舞蹈模式主体,数字舞蹈模式主体通过计算机揭示出来并促使舞者进一步介入,当交互系统影响输入时,数字媒体的输出就会改变环境中感知的舞蹈或动作的表达。”
在这里必须明晰的一点是,数字交互舞蹈并不等同于跨界艺术实践中数字影像和身体的配合式表演。这是两个不同的层次,后者在舞台剧、大型文艺演出中运用频繁,但它主要是以同台的方式来进行且没有互动和对话关系的表演,即提前预设好的身体动作与灯光、多媒体视觉效果、装置等媒介的配合式表演。唯有由身体与其他媒介(声音、装置、光影、多媒体投影)的牵制关系产生了实时“交互”,并由交互技术带来身体的幻象和舞台视效,才算是数字交互舞蹈。数字交互舞蹈是“由人机交互、体感交互等交互技术带来的实时表演创作呈现,其中技术是关键因素,即媒体技术与身体的互感构成了一种‘活’的画面,在这里,媒体与‘身体’共存”。
数字交互舞蹈的表演环境与传统剧场/舞台不同,舞者的身体和动作只构成了交互舞蹈表演的一端,而另一端是构成“可交互的”另一表演要素,这正体现了数字交互舞蹈的“交互性”。“交互”指的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相互影响并共同工作的事物;而在数字交互舞蹈表演环境中,可以结合的交互因素和条件有很多,比如音乐、灯光、视频、计算机视觉、机电仪器、烟火技术、智能织物等。因此,“摄像机、数据投影仪、麦克风传感器、微控制器和各种软件工具等,都被组织和安排参与到创作和表演中,因此,声音、视频、3D动画、运动图形、生物反馈、光等,都成为数字交互舞蹈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2.分类
数字交互舞蹈通过感官设备读取舞者的动作姿态,而能够读取舞者动作姿态的设备通常依赖的是“运动跟踪技术”,这也是科技为舞蹈提供的最主要的互动形式之一。“运动跟踪技术”使舞者在现场表演中可以对交互对象——声音、灯光、图形、机器人等剧场要素——进行控制或彼此相互牵制。目前,许多不同的技术已经被用于跟踪人体运动。本文采用外文文献中该领域运用最多的亚历克斯•穆德(Alex Mulder)1994年的分类法,将人体移动跟踪技术分为三大类:“Inside-in”系统、“Inside-out”系统和“Outside-in”系统,后两者多用于虚拟现实(VR)分类中。
(1)从内到内系统(“Inside-in”系统)指的是用放置在舞者身体上的传感器进行身体运动跟踪的方式。从计算机上看,舞者的身体往往会有一个类似骨骼的结构附着在身体上,当舞者移动时,关节机械部件也会移动,测量表演者的相对运动。
(2)从内到外系统(“Inside-out”系统)指的是不依赖任何外部传感器的由内向外追踪技术,这种技术是在虚拟现实(VR)中常用的位置跟踪方法,它不需要划定移动范围,而是通过计算机视觉等技术辨识所追踪的点和周围环境的相对位置关系来定位。它拥有更多样的移动性和更高的自由度,但技术上没有从外到内追踪系统那么精准。
(3)从外到内系统(“Outside-in”系统)指的是依靠各式外部追踪设备的位置追踪方式,即用外部传感器来感应舞者身体上的源或标记,如将摄像机位置固定等,因此它更适用于当舞者在舞台上的位置相对固定的情况,而不太适合在舞蹈表演中跟踪细微的身体部位或多个舞者。这类系统有较高的准确度,但它的缺陷是当追踪舞者的传感器的测距丧失或被物体遮挡时,就无法获得位置的讯息,舞者可移动的范围受限。
数字交互舞蹈作品《西河剑器》曾在中国舞蹈家协会主办的“一同走过——新中国舞蹈艺术70年(1949—2019)”国家大剧院展览“艺术+科技”板块中呈现,通过RealSense视觉处理器和深度摄像头,跟踪舞者身体和脚下的位置。值得一提的是,《西河剑器》是国内首次以“数字交互舞蹈”命名的公开演出,这在中国观众的视野中是新颖独特的。
通常情况下,数字交互舞蹈“通过感官设备读取舞者的动作姿态,将其转换为数字信息,由计算机程序进行处理并呈现为可实时输出的、可实时塑造的舞蹈表演”。追踪舞者运动的目的,是为了将舞者的运动映射到交互的另一端形成声音或呈像。对于计算机视觉而言,重点在于投射的材料与舞者的动作之间的关系,即“输入”与“输出”之间的关联,有对应、相似或因果等关系。舞者的动作可以被看作是“输入”,而由计算机视觉(或其他设备)产生出来的交互效果可以被看作是“输出”。数字交互舞蹈作品的好坏,在于最终的“输出”以及舞者和“输出”之间的关系。这是一个较为简单的映射关系,意味着运动和交互对象(声音/呈像)之间的一一对应。
三、数字交互舞蹈的特性
我们对数字交互舞蹈进行探讨的原因有很多:它是新兴的、前沿的、科技性极强的数字表演艺术种类;它可以让作品本身跳出线性时间框架;它增强了舞蹈表演者即兴创作的潜力;它令舞者对身体运动意识和控制力产生明确的目的性并在表演过程中为舞者提供灵感;它促使舞者的肢体或行动控制不同交互元素,如灯光、图形和装置,从而带来新的艺术形式和艺术体验感……在此,将从舞蹈艺术的核心要素——时间、空间、身体——三方面来论述数字交互舞蹈的特性。
1.时间的自由性
时间在数字表演的艺术实践中一直是一个哲学话题。在数字交互舞蹈作品中,舞蹈和音乐可能会让整个表演变成一个可无限循环甚至可被改变的作品。当现场表演和计算机虚拟图像结合,现场“活的”和“虚拟的”结合,就会引发特定的时间扭曲效果,它表现出存在并运行于时间之外的艺术体验。这不仅扰乱了观众对传统剧场时间的理解和体验,而且挑战和超越了“非时间性”或时间蒙太奇等已确立的后现代观念。
在表演中,舞者可以摆脱线性时间的束缚,尤其在即兴式的交互舞蹈设计中,时间并不在编导、导演的控制范围内。舞者的肢体动作与交互对象的关系行为可以是直接的、高度同步的,也可以是间接的、异步的、随机的。“在时间上不给舞者设置限定,时间自由是舞者们参与互动舞蹈的一个重要动机。”交互舞蹈令舞者能够在表演过程中对多媒体呈像产生直接的影响,打破固定化的、线性的表演时间概念。因此,大部分交互表演场所在非表演情况下,也可以供观众或游览者进行交互体验。
2.空间的虚拟性
数字交互舞蹈作品中,被摄影机捕捉的媒介化了的身体(mediated body)参与其间,数字空间彻底改变了物理空间的概念和感知力,模糊了物理空间和数字空间的边界,模糊了虚拟与真实。
“数字交互舞蹈中的身体仍然在空间中展开,但是,它的空间是数字化的。数字化的空间观念改变了我们对剧场物理空间的感知。……互动艺术本身意味着在数字化空间中的‘虚拟’存在。”“虚拟”一词可以追溯到拉丁语Virtualis,意为“潜力”“力的力量”。“虚”的东西并不是被剥夺了存在的东西,而是具有发展成为实际存在的潜力或力量的东西。在数字表演艺术中,“活”的舞者身体和媒介化的、非“活”的、模拟的虚拟技术之间必然存在巨大的内在张力。在交互舞蹈环境中,由舞者身体触发的预编程图像作为数据在物理空间和网络空间中都得到了处理。“虚拟”空间中的表现力,同样代表着编程设计、多媒体艺术家的“必要的想象”,它意味着探索技术本身就是一个新的艺术创造的过程。
艺术家需要展开对物理和虚拟两个空间及其关系的探索。尽管环境投射是“虚拟”的、“假”的,但与物理环境或身体之间的互动关系却是直接和“真实”的。
3.身体的交互性
数字交互舞蹈的本质仍是舞蹈作品,舞蹈作品依赖于舞者的身体,这一本质并未动摇。但身体的本质不再是舞蹈表演中的唯一,相反,身体作为数字化参与的媒介之一,必须与交互的另一端产生互动。“数字交互舞蹈中最为核心的正是媒介与媒介之间的交互性。媒介的一端是舞蹈的物质载体身体,另一端是使用的媒介技术。”
“交互”一词通常与“自动化”混淆。“自动化”是指通过机械或电子方式自我操作或自动控制,而“交互”则意味着两个平等的事物之间的互动。杰弗里•肖(Jeffrey Shaw)的《可读的城市》(Legible
City
,1989—1991)和丹尼斯•德尔•法韦罗(Dennis Del Favero)的《场景》(Scenaria
,2011),这两个作品都是数字交互和沉浸式的艺术作品,利用身体来构建独特的艺术体验。杰弗里的作品通过固定自行车和屏幕延伸身体,而《场景》则利用了运动感应技术。有意思的是,在不断表演的过程中,杰弗里和丹尼斯进化、升级了整个作品,即由身体交互性带来了作品的不完成性。自1960年代中期以来,杰弗里就开始了在艺术和电影领域对新形式互动体验的追求,他创造了很多利用前沿技术的实验装置。他曾在香港欧塞奇基金会举办的个展“所见即所得”(WYSIWYG)上,将自己五十多年来的创作成果做了集中展示。在每一件艺术作品中,身体通过他们的动作表演融入到沉浸式的虚拟世界中,使其以艺术品的方式展开;又通过身体运动的姿态和行为形成这种交互性,并由此带来了作品的“不完成性”和“不确定性”。
四、数字交互舞蹈的中国探索
21世纪的表演艺术是多元的。正如2018台北艺术节的策展人邓富权所说:“艺术不该存在于自己纯粹的框架中,应该要跟社会有更密切的对话——这就是我所谓的未来学,未来肯定是有风险的,未来就是要新、要思辨。”数字表演艺术在21世纪初被中国艺术家们所瞩目,新媒体交互式表演更是引起了表演艺术领域的极大兴趣。电影、戏剧、舞蹈等艺术形式的表达正趋向真实世界和虚构世界的融合,趋向运动图形、文本与人类以及彼此之间在传递信息时的相互配合。而数字交互舞蹈也伴随着数字表演在国家大型文艺活动、实景演出、舞台剧等艺术形式中的风靡,日渐清晰、独立起来。
1.数字表演艺术在中国
沉浸式的艺术环境、数字化的交互舞蹈创作/表演的新阶段已经到来。国家大型文艺表演、实景演出、舞台剧、开放性剧场中,越来越多的导演、编舞用到了数字化表演,将声像图文等多向兼容的媒介形式整合出现。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张艺谋导演将“长轴画卷”数字化,由美籍舞蹈家沈伟编导、多名现代舞者在数字影像的画卷上用身体为笔触,画出中国山水画的水墨线条,较早介入到了数字化的表演艺术中。再看近年来各类综艺节目,如2017年江苏卫视跨年演唱会上的全息特效“鲸鱼”、《国家宝藏》中供表演用的可升降LED透明柱、2020年湖南卫视跨年演唱会现场舞台的LED异形屏幕……这些都催生了中国数字表演艺术的发展。
随着科技的发展,数字化剧场作品层出不穷:《镜界》(2014)由上海音乐学院代晓蓉教授、赵光教授和舞蹈家黄豆豆联合创作,作品中,全息投影技术呈现虚拟舞者影像,高速摄像机追踪舞蹈动作并对舞蹈动作作出艺术化处理。中美联合制作的原创百老汇舞台剧《春江花月夜:赛珍珠》(2015)以跨媒介的艺术方式讲述了女作家赛珍珠的一生。音乐剧《阿曼尼莎罕传奇》(2016)通过抽象的影像参与舞台,形成虚实的叙事空间。国家艺术基金项目多媒体民族器乐剧《笛韵天籁》(2018)用抽象的影像展现了舞台空间情节与气氛的转化。沉浸式长笛演奏表演《十绝句•墨影》(2019)“将舞台空间中的装置、演奏员、观众融为一体,为观众呈现了一场多变的立体空间音画表演”。系列舞台剧《对话•寓言:2047》中,张艺谋导演将中国古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以艺术的方式,创造性、实验性地搬上舞台,他“将舞台表演形式确定在新型科技如机械臂、无人机等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木筒号子、壮族坡芽歌书、内蒙古呼麦等的结合基础上,一端指向古老的传统,另一端则指向崭新的科技和未来”。
在数字剧场的理论研究方面,中国导演、艺术家们也在反思,思考有关21世纪数字表演艺术的研究和探索,“数字技术的威胁在于仿真动摇了现实原本的唯一性以及真实性,也渗透进现实镜像的剧场,机器人、合成人(赛博格)等被形容为‘入侵’式地替代人类演员,并对现场性构成挑战。尤其以批判性的后人文主义视角对传统的革新,技术不再是工具,舞台也不再是人的舞台,这成为21世纪表演艺术最有争议性的发展趋势之一。”2019年由歌德学院(中国)举办的“排演数字时代:21世纪的剧场”系列研讨会,邀请了德国、韩国与中国相关领域的创作者、制作人和学者参与,这是剧场表演、戏剧人面对数字时代和人工智能当下发展的思考转向,共同探讨数字化剧院以及戏剧表演艺术应如何立足。
要说中国的数字化演艺,不得不提的是中央美术学院费俊教授,他做了大量数字化演艺工作和沉浸式演出:大型沉浸式实景演出《今时今日安仁》,以碎片化的影像表演空间唤醒观众对民国生活方式的体验;国宝数字体验展《东方智美》将八件国宝和《千里江山图》数字化;《归鸟集》则是位于大兴国际机场的一个公共空间的数字化装置,观众可以和自然、天气、季节、航班互动……数字媒介从屏幕中释放出来,被应用在国家大型文艺表演、电视综艺、舞台剧、公共空间等表演场所中,以不同的数字形态和媒介方式呈现。
2.数字交互舞蹈在中国
新技术为舞蹈表演、作品创作提供了新方法,数字交互舞蹈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大量新的以及不断更新着的虚拟现实设备、运动跟踪技术等,为交互舞蹈提供了创造的无限可能。
国家大型文艺活动中的舞蹈表演,开启了中国数字舞蹈表演的先河。“2016年中国杭州G20峰会‘最忆是杭州’的文艺表演中,《美丽的爱情传说》用LED扇屏与舞者刘福洋、骆文博进行互动演绎;2018年中国青岛上合峰会‘有朋自远方来’文艺表演中,《天涯明月》用多媒体制造的月亮的阴晴圆缺与布满LED灯的40多位群舞演员舞动水袖进行互动演绎;2019 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开幕式中,《绵延的芬芳》用彩色游动地球仪与独舞演员李祎然进行互动演绎。”
真正具有实时交互关系的作品,往往是纯粹的舞剧或舞蹈作品,这也许是因为当下实时交互技术并没有那么成熟,较小的表演环境较为可控。舞剧《游园惊梦》(2014)、《尘香疏影》(2018)、《界》(2019),舞蹈《西河剑器》(2019)、《平行》(2020)、《宇宙手谈》(2020)等,均是由舞者、表演者和多媒体影像、灯光追踪等在舞台表演中产生实时关系的中国数字交互舞蹈作品。在2019年6月北京舞蹈学院《界》的演出中,以舞蹈与灯光、装置、影像、互动技术、电子音乐的跨界形式,“从彼此的界限,找到融合的边界,从而达到新的世界”。“《母陀罗》中,刘岩的手势动作提前设置了追踪感应器,通过编程完成现场的实时交互。”
数字交互舞蹈的编舞方式有一套自身的潜在原则:“作为一种新的艺术表现形式,在新的环境中向创作者们提出了新的要求,由此产生了新的编舞观念和新的身体策略。编舞家需要找到最有效的交互设计方式构成动作,形成视觉空间。这涉及交互原理和设计、数字化空间以及编舞和编程艺术家的通力合作。”
令人感到庆幸的是,交互舞蹈的技术门槛正在不断降低,不再仅限于技术精英或经费充足的项目所使用。“感应设备、无线个人通信和计算机视觉的广泛使用,迅速地使交互式舞蹈成为作曲家、编舞家和舞者可以访问的媒介。”相对于过去繁复的、昂贵的动捕技术或视效追踪,已有很多类似Dance.Draw的便携式交互技术使用无线接口,轻便易安装且成本低。例如“Dance.Draw可以在任何Mac OSX系统上运行,系统可编程好预置的可视化图像,设定音轨。每次表演前只需要不到10分钟的时间来设置笔记本电脑、鼠标和投影仪的连接,有时舞者拿着鼠标对屏幕中的可视化图像进行控制”。
中国数字交互舞蹈的创作表演才刚刚起步,它具有高度实验性,现在仍在实验的道路上,有很多需要解决的问题和思考的方向。比如将不同的传感器组合使用,以传达更准确的动作数据;有序有效地共享这些数据以适应不同的映射和媒体;当舞者逐步进入编程轨道,将舞蹈创意的数字化效果最大化;运动跟踪过程中的延迟性调整等。同时它也带来了一些思辨性的终极问题:艺术和技术的紧张和协商关系中,技术如何服务于舞蹈而不是征服舞蹈本身?在这其中,编舞、艺术家们应该做些什么?尽管编舞家、舞蹈家们正在尝试用数字技术来做表演实验,但最关键的仍是内容本身。数字技术只是增强和实验的工具,而不是从根本上重新配置艺术或社会本体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