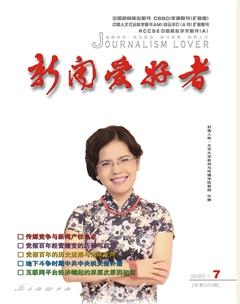移动支付作为媒介实践所交会的三种意义与反思
朱冰清
【关键词】媒介实践;移动支付;意义;反思
波斯曼在《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一书中,强调“隐形的技术”这一观念,他指出,“生活在技术垄断里的人有一个特点,他们多半意识不到技术的起源和结果”。[1]在波斯曼的论述中,语言、数字、统计学以及其衍生出的民调、排序、评分等都被认为是技术,它们之所以能成为“隐形”的,是因为人们过于相信技术(technology)和技艺(technique),并且相信只有它们独立于人的存在时,才能达到更高的效率,由此人变成了“技艺动物”,而这正是波斯曼所要批判的现象。“这个观点很危险,因为谁也没有理由去反对用理性的方式去应用技艺,并以此实现个人的目的”。[2]
移动支付技术虽然功能多样,但作为一项媒介技术本身,它所具有的符号意义和工具意义被直接而充分地展现,因为无论什么人,都一定十分明确自己与技术接触的根本意图,而在表述技术时,也会习惯性地赋予它一定的引申含义或象征意义。不容忽视的还有一个层面,即在本体论意义上,比如技术作为一种存在方式、技术逻辑等,则类似于一条隐藏线索贯穿其中,隐而不现,但却在前两者的实现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商界精英往往借用技术的逻辑去说服自己和同行迎接新技术的未来,而使用者们会以信息时代的新观念来进行自我暗示,以表明自身行为的正确性。作为积极消费者的人们则无疑是经历了技术和资本带来的双重异化,例如“双十一”的凌晨人们拿着手机抢购,却因网络拥挤无法付款而感叹“有钱花不出去”时,正是这个逻辑的表现。需要指出的是,技术在本体论上的意义仍然是人们以强烈的愿望附加于其上的,并不是技术本身具备了此种意义。
一、作为工具的移动支付
工具层面是大多数人对于移动支付最直接的理解,这也就是为什么人们常常会提到“使用”二字。在国家层面,移动支付成为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被作为“数字经济”“新经济”等经济发展的“零边际成本基础设施”而得到政策支持,成为国家运用新技术实现经济转型和增长的有力手段。在商业层面,移动支付被视作连接商业版图的重要一环,企业运用移动媒体的交互性实现了用户的增长,并通过尽可能多的功能让用户停留在移动支付的界面中,满足用户多样化的需求。用户通过使用移动支付产生的数据信息又进一步帮助企业理解用户行为,在此后的商业活动中为用户提供更为精准的营销。对于其他行业来说,随着移动支付作为一个便捷的支付入口,极大地提高了人們付款的效率,因此在诸如地铁、公交、医院等行业都积极配合移动支付的接入。在个体层面,人们出于“方便”的目的而使用移动支付,移动支付不仅为人们省去了需要耗费在许多付款事宜上的时间和精力,也为人们通过时间复利、薅羊毛等行为获利提供了条件。除此之外,正是由于金钱本身以及移动支付企业的“社交化”运作,使得移动支付也成为维系“人情社会”的一种重要工具,当然在此过程中也出现了圈层隔离的问题与数字反哺的需要。技术功能是对主体价值的投射,但当前这种价值并没有得到充分的讨论,人们只是站在各自的价值体系中去评估它作为一种技术的自然特性和作为手段的意义。
在给移动支付“命名”(赋予含义)的过程中,人人都能成为“文本盗猎者”。对国家而言,移动支付是国家发展的象征,“新四大发明”就是这一象征的经典表达,它蕴含着科技的发展与民族复兴的重要内涵,更标志着一种超越民族与国家的人类贡献。企业从自身营销的目的出发,将移动支付的形象与社会发展联系起来。在他们的话语中,移动支付既是社会“信任”的基础,也是未来美好生活的“解决方案”,它为人们提供了一年一度重要的节日仪式,更引领着年轻人时尚前卫的生活理念。对于个体而言,虽然不少人接受了国家和企业提供的意义并内化于自己的行动中,这是人们合理化自身行为的重要起点。但日常生活本身才是创造的源泉,人们出于自身的需要采取了多样化的实践方式,并尝试为移动支付提供新的含义,例如利用移动支付来达到管理和规训的目的,更常见的情况是将网络购物视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以打发无聊的时光和暂时逃避学习工作的压力。
二、作为符号的移动支付
正如斯图尔特·霍尔所言,“各种事物、概念和符号间的关系是语言中意义生产的实质所在。而将这三个要素联结起来的过程就是我们称为表征的东西”。[3]人也是文化和符号的动物。人创造文化,又被文化创造。人生存于世界上,也就意味着人在文化中。而文化总是体现为各种各样的符号,器具用品、行为方式、思想观念皆为文化符号或文本。符号的基本功能在于表征(representation),符号之所以被创造出来,就是为了向人们传达某种意义。符号的形式(发音、书写、形象、物件等)即“能指”,和一个在人们头脑中与这一形式相关联的观念(“所指”)关联而成,意义形成的过程也就是表征。在消费领域,鲍德里亚的研究早已对物品的符号意义展开了解释:“物品在其客观功能领域以及其外延领域之中是占有不可替代地位的,然而在内涵领域里,它便只有符号价值,就变成可以多多少少被随心所欲地替换的了。”“无论是在符号逻辑里还是在象征逻辑里,物品都彻底地与某种明确的需求或功能失去了联系”。[4]即便某种定义已被组织机构以大众媒介的力量给生产出来,人们依然具有重新解读的能力。这便是霍尔所说的“解码”,也是詹金斯所说的“文本盗猎”。麦克卢汉在发出著名的“冷媒介”“热媒介”时,也关注了个人与文本互动的命题,虽然他主要聚焦于媒介自身形态导致的差异。
在对于符号的利用中,经由对于技术的编码解码,国家形象、企业形象和个人形象被建立起来。宏观层面的结构性力量试图通过符号的宣传来塑造爱国、自律、环保的现代公民。对个人而言,并非所有人都能对以上价值形成统一的、“正确的”解码,这些意义其实是一种外在的“附加”,但这些正面宣传赋予了技术合理性。另一方面,人们对于移动支付的意义塑造主要取决于它对于个人生活的现实意义。因此,在这个层面,个性化的编码更多体现的是“为我所用”的特征。移动支付被作为国家发展、高科技生活和个人身份(比如消费者、环保人士、管理者等)等方面的认同被呈现。然而这样一种认同依然是对原有价值的强化,或者是对于其他意义的挪用。更重要的是,在发展背后带来的危机和焦虑却并没有形成一些新的编码或抵抗性的解读。
三、作为本体的移动支付
移动支付蓬勃发展的态势使得一部分参与技术实践的主体感受到掌握科技发展方向对于自身和行业未来的重要作用。因而,将之作为本体论的声音也逐渐出现。数字烏托邦逐渐成为“理想化自由市场‘公平竞争的象征”,而“机器的‘嵌套层级制则成为本地大亨的符号性替身”,他们使人相信“控制信息即控制世界”。[5]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中国商界精英对于数字乌托邦思想的热捧。在移动支付的发展过程中,企业发挥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在“代偿机制”与“技术崇拜”的并行理念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技术崇拜”被视作一种超越商业目的,以“社会服务”为目标的积极意义,它在某种程度上抵消了传统文化当中对于商业的负面评价。这确实与中国现阶段的发展状况与发展目标联系在一起,但正是这样一种理念造就了技术本体论的广泛传播。对个体而言,人们在实践过程中将移动支付视为与生活息息相关的“生存技术”,即便产生了隐私安全焦虑,也无法动摇人们对于移动支付本身的依赖与情感上的牵绊。
本体论意义上的媒介技术是要探讨技术对人的根本性的作用,人们意识到技术的强大力量,并开始作出选择。技术的崇拜者、追捧者会强化技术的本体作用,顺应技术的“发展趋势”,将自身纳入到可见范围内的发展趋势当中,并积极地预言媒介技术发展方向。而技术批判者会发现人的需求和价值,夺回主导技术发展方向的主动权,呼吁人们提升对于形塑技术的掌控能力。更多的人处于中间地带,技术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尚未成为他们思考的重点,他们既无法割舍技术发展带来的好处,也在技术可能威胁到自身时感到恐惧,因此观望着技术的发展态势,在凭借技术获利和警惕利益受损中谨慎行事,在乐观和悲观之间焦虑着,徘徊不定,临界点只在于获利和损失之间的平衡点被打破的瞬间。在这个意义上,大多数技术实践者缺乏重新反思技术的能力和动力,而是关心自身如何更好地适应技术发展的潮流。从这个意义上说,“技术为何物”的问题并不存在。
四、反思媒介技术:以社会建构的取向
而实际上,包括互联网在内的许多新技术仍然处于“未决定”的状态,移动支付发展至今也并不是一个确定无疑的事物,而是需要被社会价值所解释的人造物,它需要体现塑造者的利益和需求。随着新的行动者加入,人们应当有共同决定技术发展的可能,而不是通过现有的情况猜测技术发展的方向,从而决定自身的行为。这在社会建构论者看来,是一种本末倒置的行为。
(一)反思的起点:媒介技术与社会的关联
延森在提出“元传播”(meta-communication)这一概念时,实际上是指出了人们进行数字媒体实践时遵循的一种技术框架,但这种技术框架并不仅仅由技术本身的形式决定,而是一个人与技术互动的过程,人们在参与媒介实践时也在生产框架本身。所以延森在麦克卢汉的“媒介即讯息”(“形式超越内容”)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功能超越形式”,因为人们使用媒介首先是为了通过其功能实现目的。“元传播既指涉关于传播的传播,又包含着信息状态的传播,还包含着传播者角色的传播。尽管任何媒介中的任意传播实践都包含着元传播,但数字媒介孕育了独具特色的元传播类型,它重构了传播的形式、内容与功能”。[6]也就是说,人的媒介行为受到具体媒介技术的限制,而媒介技术就像语言的语法一样,当语言表征具体事物时,语法则规定了语言使用的规则。这在很大程度上描绘了当前媒介实践的现实。
技术逻辑对人们的日常媒介使用影响深远,即使许多移动支付用户自身尚未意识到这一点,更没有意识到自身行动的意义。比如,对许多人来说,之所以使用移动支付并不断尝试它的新功能是由于想要获得更多的便利,而对便利的需求以及便利之所以能够实现是由于移动支付已经具备了这些功能。在这种思路中,人们自始至终没有从技术的逻辑中跳脱出来,移动支付的载体——媒介技术已经成为潜在前提,而不是需要思考的对象。但事实上,我们在手机上付款的操作流程正是遵循了移动媒体的逻辑才得以实现。可以肯定的是,无论从使用体验还是从行业发展的角度来看,它与刷卡或使用现金都有着本质的区别,但人们却(出于各种不同的原因)有意无意地忽略这种区别。以下是我们认为在移动支付的发展过程中,值得重视的一些现象。
(二)日常生活的媒介化进阶
消费作为日常生活的一个基本要素,它对于日常生活的意义毋庸置疑。日常生活资料的获取与消费活动所满足的是人的食欲、性欲、安全等最基本的生理需要,当我们在一个“元媒介”(meta-media)的时代探讨媒介化的问题时,尤其不能忽视那些被“媒介化”了的媒介(要素)。正是由于支付功能本身的进入,“消费”这一日常生活的基础才被更进一步地媒介化,而支付这一行为的变化及其带动的相关产业变革都意味着消费和生产越发需要遵循媒介技术的逻辑。它不仅表现为消费的媒介化(比如线上线下购物都需要通过手机,人们可以在接入互联网的任何时间和地点通过手机消费),更体现为技术依赖的深化(因为媒介技术已经深入到日常生活的最基础层面),还涉及更广泛的行业媒介化(这体现为越来越多的行业为了满足用户支付方便的需求,纷纷接入移动互联网)。而这一切都是以日常消费的方式展开的,它们根植于人自身的消费需求当中。
(三)媒介实践具有消费色彩
我们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媒介实践具有消费的色彩,这体现在内容付费、知识付费和内容平台对于用户的金钱奖励。除了前文所言的内容付费之外,近几年知识付费更是成为互联网行业关注的焦点。有调查研究显示,自2013年“微博大号、微信公众号等自媒体崛起,(知识付费)商业价值显现”,而2014年之后随着“微博、微信相继开通付费赞赏功能,伴随移动支付的逐步完善,知识付费开始成型”,直到2016年以来一系列知识付费互联网产品的最终上线,才标志着中国知识付费体系的“正规化”。[7]2016年上线的“得到”App作为中国知识付费行业的代表性产品,将知识付费推向更广泛的人群。知识付费的本质是将知识作为商品进行生产和消费,这被一些行业分析者称为“泛知识的内容产品化与商业价值转换过程”。这时经过精心挑选和整理的信息满足了人们在信息爆炸状况下对于信息筛选的渴求,因此被当成商品出售。
在这类交易中,重要的是人们由于“知识焦虑”而产生的购买行为,至于人们在消费之后是否真正获得了知识增长,却往往不在知识提供方的考虑范围之内。以致知识付费行业的现状是“缺乏相应保护机制和评价标准”。[8]这引发了业内人士对于知识付费“建立内容准入机制、知识商品评价体系、售后保障机制”的呼吁。此外,以“趣头条”“喜马拉雅FM”为代表的内容平台均以现金奖励、积分兑换优惠券和商品等方式吸引和鼓励用户花费更长时间来阅读或收听内容。在媒介化的作用下,以上这一切又继续促使“日常生活的重心转向消费领域,包括娱乐和硬件在内的消费行业的增长,使其成为经济中规模最大、最引人注目的部分,进一步强化了这一点”。[9]当然,除了显性的消费,还有不为人们所察觉的数据交易。在大数据时代,只要接入移动互联网,人们的所有行为都可以被转化为他人的“生意”。当越来越多的事物被当作商品进行交易,人们在消费更多的媒介内容和服务的同时,也正在产生能够被他人消费的更大商业价值。
(四)商业推动技术文化变迁
探讨支付功能与媒介实践“层叠”的意义在于它让我们看到了一种新的“跨界”形式以及这种形式本身带来的观念、思维以及行为方式層面的变化。因为消费本身也是文化行为。“人们为最为琐碎的日常物品赋予象征意义。对于他们来说,物质产品不仅仅是有特定用途的物品:产品还有作为价值标志的文化角色”。
目前,这样一些变化主要被商界精英所关注和思考,用于探索未来商业模式的变化。例如,吴声将当前一些成功的新型商业模式称为“新物种”(在他的论述中,“在线信用”也属于其中一种),而这些“新物种”的存在方式是适应技术推动下的“人的升级”,从而为人们提供“意义覆盖”。因为“消费升级”的实质是“认知升级”。“智能设备和人、社交网络和人、技术和人的关系正在推动人本身的进化,全新商业场景下的用户已经与传统概念上的消费者截然不同。‘人本身发生了变化、进化、异化和云化,商业模式因此发生了本质性的位移,而这种位移同时为新物种的孕育提供了另一种可能和土壤”。[10]人的变化是由技术变化带来的,那么为了适应技术与人的变化,商业必须坚定地站在技术潮流的前端,为人们消费新技术提供机会和文化层面的意义。
“技术本身的糅合性和互联网改造所有产业的必然性,让产业的价值模式发生了范式转移”。“技术覆盖是意义覆盖的基础动力,意义覆盖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技术进化引领的用户行为进化、生活方式进化,是人们对生存意义一次次的升级”。[11]这一思路与凯文·凯利并没有什么实质上的区别,但吴声作为“中国互联网原创商业思想的重要研究者和实践者”,其思想对于中国的互联网行业发展而言具有更重要的本土化意义。虽然吴声认为企业应随着用户的思维方式变化而转变策略,但事实正是由于企业站在技术的前端,其商业理念的变化带动了“意义覆盖”,否则他的论断便会失去指导意义。在跨界融合如此普遍的今天,我们尤其需要意识到的是在技术与社会文化之间,商业所起到的关键性桥梁作用。
五、结语
移动支付作为一种媒介技术在中国发展至今,既有它在“初级工具化”阶段所体现出的因技术特性而产生的价值,技术脱离了它产生的情境,并与其他要素结合起来去实现新的目的,这一过程本身就是社会选择的结果,更需要人们继续探索它在新社会情境中的进一步发展。正如芬伯格所言,“在次级层面,各种技术对象彼此结合起来构成了一种生活方式的基础”,我们应当关注社会所确立的意义系统以及价值观(社会规范、伦理、审美等方面),使得社会本身成为形塑技术的重要基础。
参考文献:
[1]尼尔·波斯曼.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M].何道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82-84.
[2]尼尔·波斯曼.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M].何道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82-84.
[3]霍尔.表征:文化表征与意指实践[M].徐亮,陆兴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25.
[4]鲍德里亚.消费社会[M].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66-67.
[5]特纳.数字乌托邦:从反主流文化到赛博文化[M].张行舟,译.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3:242.
[6]延森.媒介融合:网络传播、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的三重维度[M].刘君,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89.
[7]易观.2017中国知识付费行业发展白皮书(附下载)[EB/OL].(2017-12-09)[2019-10-13]http://www.199it.com/archives/661664.html.
[8]吴俊宇.内容付费的三个层次,知识付费的三点反思[EB/OL].(2017-12-22)[2019-10-13].http://www.woshipm.com/it/885008.html.
[9]Ralph Schroeder.‘The Consumption of Technology in EverydayLife:Car,Telephone,and Television in Sweden and America in Comparative-Historical Perspective[J/OL].Sociological Research Online,2002,7(4).
[10]吴声.新物种爆炸:认知升级时代的新商业思维[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28-33.
[11]吴声.新物种爆炸:认知升级时代的新商业思维[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28-33.
(作者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生)
编校:郑 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