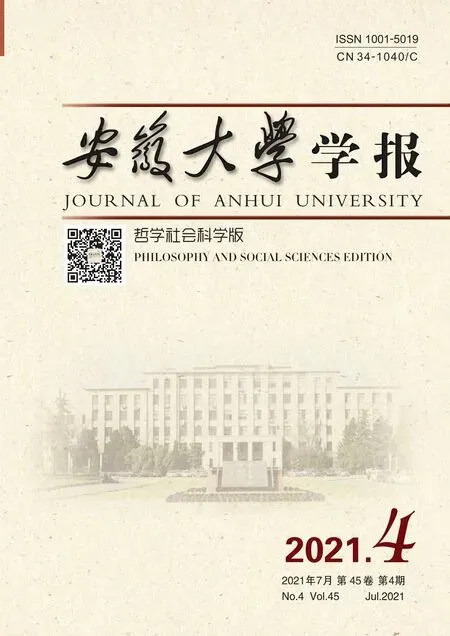塑造名山:徽州社会与乌聊山的开发和形塑
孟义昭
乌聊山,一名富山,又名庙山,其山之东峰称东山。乌聊山原是徽州一座并不起眼的小山,自然条件也无任何特殊之处,但经过历代开发与形塑,至北宋时期成为徽州名山。自南宋罗愿《新安志》开始,徽州地方志书在编纂“山川”一门时,往往首先刊列乌聊山。该山“近而尊”的特点,也被着重提及。所谓“近”,是强调乌聊山的地理位置,距徽州府城最近;所谓“尊”,则是指出乌聊山的地位,在徽州山川中最为尊崇。对于这座徽州历史上极为重要的名山,学界鲜少关注,目前仅见章毅考察了元代乌聊山汪王庙的演变,此外尚无关于乌聊山的专论。本文从乌聊山人文景观入手,考察乌聊山的开发史及其与徽州社会文化的关系,揭示一座小山成为地方名山的主要途径。
一、乌聊山的早期开发
唐代以前,是乌聊山的早期开发阶段。这一时期,乌聊山先后出现毛甘故城、新安郡城两大人文景观。建设城市,是人类开发山川的最高水平。在早期开发中,乌聊山就曾建有两座城池,在徽州各地山岳中遥遥领先,显示出其开发的高起点、高水平特征。
毛甘故城处于徽州建城史上的初级阶段,也是乌聊山出现最早的重要人文景观。据《元和郡县图志》载:“乌聊山,在县东南二百六步。上有毛甘故城,后汉末,贼毛甘万户屯于此,吴将贺齐讨平之。”李吉甫明确指出,毛甘故城在乌聊山上,为毛甘屯兵时所筑。由于史料所限,毛甘故城的具体形态尚无法得知。
东汉末年,毛甘为山越首领之一,率部族屯于乌聊山,依阻山险,聚众自保,不纳赋税,与孙吴势力对峙。除山岭之险外,乌聊山之所以成为山越的重要据点,原因大致有二:一是乌聊山在歙县核心区域,地理位置重要;二是其山泉水丰富,用水方便。乐史在《太平寰宇记》中说:“乌聊山,在县东五步。按《吴记》:‘歙率毛甘领万人屯乌聊,孙权遣贺齐平之,分黟、歙为六县。’盖歙县已在此。其山为泉水所凑,城西有四水合流。”正是因为乌聊山具有位置重要和取水近便的优点,才成为毛甘的屯兵建城之处。在乌聊山早期开发史上,山越是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
对于孙吴来说,山越的存在是一个巨大隐患和威胁。陈寿就曾评说:“山越好为叛乱,难安易动,是以孙权不遑外御,卑词魏氏。”山越长期而又反复的叛乱,牵制孙吴军力,损耗政权实力,使孙权无暇也无力与曹魏对抗,向外扩张势力范围。山越凭借山险不纳租赋,在客观上也减少了孙吴财税来源。为消除心腹之患,增强自身政权实力,建安十三年(208),孙权遣贺齐进讨黟县、歙县山越。乌聊山并未真正发生战斗,而是在林历山山越战败的情况下,毛甘等人选择投降自保。贺齐的功绩被后人追述,他在明代被徽州人选作“名宦”,祭祀于徽州府学遗爱堂。
贺齐征伐山越之役,是改变徽州行政区划的一件大事,在徽州行政区划史上意义深远。徽州地区由丹阳郡下辖的黟县、歙县,分为黟、歙、始新、新定、黎阳、休阳等六县,并升为独立的新都郡,郡治在始新县(治今浙江淳安)。一郡六县的行政区域,开启了徽州郡级行政建制的时代。
太康元年(280),晋武帝平孙吴,改新都郡为新安郡,郡治仍在始新县。南朝梁元帝承圣年间,置新宁郡,辖黟、歙、黎阳、海宁四县。开皇九年(589),隋朝改新宁郡为歙州,辖黟、歙、海宁三县,州治在黟县。大业初年,隋朝废歙州,复设新安郡,郡治在休宁县。义宁年间,郡治移于歙县。武德年间,唐朝改新安郡为歙州。在东汉末年至唐初期间,徽州建置沿革十分复杂,而乌聊山在其中扮演着不可忽视的角色。
隋朝末年,天下大乱,汪华起兵,据有新安郡,迁郡治于休宁万安山,兼有宣、杭、睦、婺、饶等州之地,号称吴王。义宁年间,汪华将新安郡治迁至歙县乌聊山。汪华选择乌聊山作为郡治,主要原因是:首先,汪华当年起兵时,曾屯兵于乌聊山,对乌聊山较为熟悉,并且富有感情。其次,乌聊山为徽州形胜所在,地理位置极为重要。南宋徽州人罗愿曾撰写《汪王庙考实》一文,其中就指出此山形胜对汪华迁移郡治的影响:“新安郡治,自昔屡迁,今治歙县乌聊山之西,则实始于王。乌聊者,郡之形胜。自汉建安之乱,县人毛甘以万户守之,逮王之起,复屯其上,后因迁治其旁云。”再次,东汉末年,毛甘屯兵乌聊山,在山上建城,为在此山创立郡治、建设郡城奠定了重要基础。
汪华迁新安郡治于乌聊山后,依山兴建郡城,使乌聊山开发达到新的历史高度。据罗愿《新安志》载:“乌聊山,在县西北三百五十步,高二十八仞,周八里。汉建安之乱,歙人毛甘以万户屯此山,为吴将贺齐所破,因置新都郡。隋末越国公起兵,亦屯于此。及义宁中,州自休宁迁治此山之下,则城东、北、南皆践山为之,西有四水合流。”新安郡城三面倚山,一面临水,雄挟阛阓,对徽州城市建设格局影响深远。
北宋宣和年间发生“徽州徙州治事件”,又称“徽州迁城事件”。在该事件中,徽州知州卢宗原捕捉时机,顺应民意,放弃溪北新城,将州治迁回乌聊山旧城,从而奠定此后数百年徽州郡城发展的基本格局。卢宗原修筑乌聊山旧城,只是在旧城基础上加修,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徽州城布局。因此,在徽州文献书写中,乌聊山旧城为汪华所筑,成为一般的表述方式,较少提及卢宗原筑城之事。如弘治《徽州府志》提到徽州建置沿革时就说:“今乌聊山之城,汪华所筑。”在提及城池时又强调:“本府城在乌聊山,唐越国公汪华在隋义宁中称吴王时所筑。自休宁万安山徙治于此,东半抱山,西半据平麓,筑以为城。”乾隆《江南通志》采纳此说:“(徽州府)府城在乌聊山麓,唐汪华筑,东半抱山,西半据平麓。历宋至元,代有修补。”光绪《重修安徽通志》也采此说:“(徽州府)城在乌聊山麓,隋义宁元年汪华筑,东半抱山,西半据平麓。”由此可见汪华筑城乌聊山的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
二、庙山的形成
贞观末年,汪华在长安逝世,永徽年间归葬歙县云郎山。汪华自逝世后不断受到褒崇,其事迹流传渐广,形象日益高大,被视为“新安之神”。在汪华尚未归葬歙县之前,徽州民众即为其创立祠堂,地址在州署之西,此即后来的汪王庙。大历十年(775),歙州刺史薛邕将祠庙迁至乌聊山东峰,号“越国公汪王神”。元和三年(808),歙州刺史范传正又迁祠庙于乌聊山南阜。
罗愿在《汪王庙考实》里分析薛邕将汪王庙迁至乌聊山的原因:“按今乌聊山之祠,相传云:邕尝以王功德奏闻,奉敕立庙,然必于山者,则以王初起尝驻兵其上故也。山起州之东北,而极于南。所谓东峰者,今人别谓之东山。所谓南阜者,即此山之最高处,今人呼为庙山。”汪华在隋末曾屯兵乌聊山,是薛邕最终选择将祠庙迁至该山的根本原因。宋代徽州人胡伸在《唐越国汪公华行状》中说:“郡人自公入朝,即生为立祠,没益严奉,水旱必祷,今乌聊山庙是也。自唐刺史薛邕、范传正、吴圆、陶雅之属,皆有增葺。及章圣东封,始载国朝祀典,其后褒爵益崇,事具有司。”可见乌聊山汪王庙地位之高。


徽州下辖各县也建有汪王庙,供奉汪华。徽州人祭祀汪华时,视乌聊山汪王庙为正庙,弘治《徽州府志》即指出:“忠烈庙在古城岩,即万安山,以祀唐越国汪公华。公在隋起兵,据郡保障六州,时治于此山。故正庙在歙之乌聊山,宋赐额忠烈,而此山复有专祠,建自宋淳熙中。”乌聊山汪王庙为祭祀汪华正庙,在徽州地位最高,各县汪王庙皆为其行祠。元代徽州人程文说:“唐越国汪公庙,在乌聊山最显。”明代程敏政说:“唐歙州总管越国汪公有庙,在歙之乌聊山,始贞观己亥,著于令甲。历代因之,号其庙曰忠烈。属邑之人,走乞灵无虚日,又各即其地为行祠。”徽州下辖各县之人,除在行祠祭祀外,多赴乌聊山进香祷告。成化年间,在朝为官的程敏政曾得赐假回乡省亲,抵家第三天即赴篁墩拜谒其先世祖程灵洗庙,次日又赶赴乌聊山谒汪王庙。程敏政在《寿汪君尚愉夫妇六十序》中解释道:“盖二公者,皆有大功于新安,故庙至今,子孙繁盛,亦略相等。”身为朝官的程敏政尚且不辞劳顿去乌聊山祭拜,信奉汪王神的徽州普通民众当更为虔诚。

香火旺盛的汪王庙,据说极为灵验,有求必应。至元十八年(1281)正月,祁门县盗寇作乱,元朝官兵前往讨伐。时值春季,徽州雨水偏多,山路崎岖,道途泥泞,兵马行进速度缓慢。据事后元军将领回忆:
尔所谓越国汪王神者,始吾未知其何如神。迨祁门告有乱者,甲子及甘侯护偏师以往。入春苦淫雨,至是雨甚,泥淖载途,士马艰于行。乙丑至邑,雨益甚。人谓邑距贼巢尚百三十里,山路崎岖,若未霁,兵行尤不易。吾惟兵贵速,少迟,贼或披猖,平民受害滋夥。因念邦人每诧越公之神,为果有灵,其能请于上帝,转雨为霁,使吾事亟集,则神平昔受庙食,有爵封命号,享民牲醪之奉始无愧。夜午,雨忽止,翼日丙寅昧爽,清飙徐兴,氛霾尽解,霁景泛空,徒旅踊跃。贼出接战,一进挫其锋,再进离其群,三进薄其境。一日间,直捣其穴而平之。讫事,复雨。夫雨与霁悬于天,非越公其神其能,密赞大造,开阖阴阳,岂遽与吾意之所期者应?可谓灵也已。
时人将战争中的天时,归功于汪王神的相助,认为正是在汪王神助阵下,才取得战争的胜利。因此,凯旋之后他们作《歙乌聊山忠烈庙享神辞》,赴乌聊山汪王庙献祭。在徽州,每遇水旱疾疫,必赴乌聊山汪王庙祈祷,成为一种文化现象。胡伸对此现象已有关注,发出“水旱必祷,今乌聊山庙是也”的感叹。
除汪王庙外,作为徽州祭祀重地的乌聊山还建有其他祠庙。岱岳庙,又名东岳庙,在乌聊山汪王庙之前,创立于北宋宣和年间,是徽州祭祀东岳泰山之神的场所。徽州府城隍庙,创于乌聊山,直至明代洪武三年(1370)才移建南山门内。玄坛庙,在乌聊山汪王庙后,祭祀赵元帅。义勇武安王庙,在乌聊山,原为万山堂基址,元代至大元年(1308)创建此庙。至正十二年(1352),经历兵燹,庙仅柱立,且素无常住,道士以盂饭自给。明朝初年,迎仙观道士穆师暹避迹于此。穆师暹重建该庙,并对其进行一系列的改造:“重塑王像,构门屋、两庑。升级转折而上,前创三亭,榜曰物外、城市山林、蓬岛,创小阁,曰空青,有轩曰西爽、曰环翠,庙后建祐圣殿,幽邃轩豁胜他庙。又置田于歙、绩,命徒徐尚质、沈尚文为甲乙住持,仍编为迎仙观户籍。”灵顺庙,位于乌聊山东峰(即东山),“其神五人,皆封公”。通真庙,在乌聊山麓。双节堂,在乌聊山麓,为祭祀马可道夫妇的场所。关帝庙,在府治乌聊山,有司春秋致祭。张文毅公祠,在府城乌聊山,祀左副都御史张芾。
在乌聊山上,以汪王庙为中心,前有岱岳庙,后有府城隍庙、玄坛庙,环以其他祠庙,形成一个庞大的祠庙建筑群。尽管这些建筑存在时代差异,未必都同时共存,但并不妨碍乌聊山成为徽州的祭祀重地。也正因此,乌聊山被徽州人称作“庙山”。
三、文人活动与乌聊山文化形象塑造
北宋时期,徽州州学两度迁至乌聊山,成功塑造该山的儒学文化形象。至此,乌聊山上形成城池、祠庙、州学三大类型人文景观,并对徽州社会产生全方位的影响,成为徽州最重要的名山之一。
自唐代开始,徽州州学设在州城东北隅。太平兴国三年(978),学址迁至乌聊山上。景德三年(1006),州学大修。嘉祐四年(1059),因山高地狭,“不足容众”,徙于南园。熙宁四年(1071),由于南园濒临江水,地势低洼,常有泛溢之患,学址又迁回乌聊山。直至元祐初年,州学再次徙至南园,乌聊山学址遂废。州学再度迁出乌聊山,也是由于同样原因,即“山高地狭,不足以容众”。尽管州学最终迁往他处,但乌聊山的儒学文化记忆依然存在,吸引无数文人登山歌咏。
南宋诗人戴复古曾游历徽州,写下七言律诗《新安寒食》等。在徽州游冶期间,戴复古曾登乌聊山览胜,并作《乌聊山登览》:“抖擞嚣尘上翠微,旁溪寺上坐题诗。忽闻啼鸟不知处,细看好山无厌时。风扫云烟开远景,人携香火谒丛词(祠)。客来千里登临意,说与时人未必知。”一句“细看好山无厌时”,将文人对乌聊山的喜爱表现得淋漓尽致。该诗为大量官私典籍转录,影响颇广,对提升乌聊山名气发挥了较大的作用。清代人洪亮吉曾至乌聊山游览,作诗题咏:“女墙沿山百千级,客到女墙皆却立。城南暝色似拒人,一片昏鸦堞楼集。山颓五石皆陨星,突处尚带天光青。山僧煮茗饷山客,五客一人蹲一石。”山上落星石当时已裂为五,洪亮吉对此也有生动描述,可见其诗写实程度。
拜谒汪王庙,是文人登乌聊山的重要活动。宋末元初,方回登览乌聊山,谒汪王庙,并作《乌聊山庙登览》:“寒斋兀兀味残书,一上崔嵬计未疏。下界喧卑离市井,平皋洒落见樵渔。断鸿淮汉三江外,古树隋唐五代余。忽忆浮溪偃王句,顾瞻遗庙意踌躇。”元代宁国人张师鲁拜谒乌聊山汪王庙,作《乌聊山神祠》:“龙舟抗锦帆,天下逐隋鹿。雄图江浙上,千里瞻左纛。竟想虬髯姿,挈地归荒服。英风不可泯,血食有遐福。锡诰启王封,祈年谒州牧。气和余沴消,云委嘉生熟。我登乌聊山,祠宇炳绀绿。揭虔祷灵荚,阅繇得嘉卜。洊攀丹桂枝,似愧青苜蓿。神意倘终惠,亲来报工祝。”张师鲁醉心科举,专程登乌聊山,谒汪王庙,祈祷据说极为灵验的汪华神为其赐福。
傍溪寺远眺,也成为文人登乌聊山的活动之一。傍溪寺,大中祥符元年(1008)创立,原址位于长乐下乡铜山里,绍兴年间徙至乌聊山。程敏政和友人登乌聊山傍溪寺远眺,并作诗曰:“宝坊高出旧城东,百里山川一望中。竟日倚阑题不尽,夕阳遥射竹林红。”傍晚时分,从乌聊山傍溪寺远眺山川城池,是徽州文人作诗的重要题材。洪亮吉游傍溪寺,作诗题咏:“西风泠泠响天关,炊烟一城飞出山。炊烟飞青水烟白,衬得斜阳满江赤。新安古刹皆李唐,此刹势复凌层冈。石厓中飞云缕缕,佛顶古苔堆寸许。”


每逢重阳节,徽州人往往选择乌聊山作为登高之地,上山览胜。至元二十年(1283)九月九日,杨公远邀集友人同赴城南紫阳山登高。宋省斋未及赴约,独自登乌聊山,以度重阳佳节,并有诗赠杨。杨公远作诗答和:“我辈登高崄更遥,闻君独步上乌聊。休嗟昨日浑无兴,须信明年尚有条。节后黄花香未减,年高黑鬓雪偏饶。拂笺续罢新诗句,回首重阳越一朝。”元代徽州人唐元与友人在重阳节共登乌聊山,作七言律诗:“节意萧然易得愁,乌聊晚望且悠悠。百年驹过人将老,九日山寒菊未秋。云入楚天兄弟隔,波横黟练古今浮。旧游何在论心少,沽酒同君向市楼。”
不仅重阳节,春天登乌聊山也是不少文人的雅好。明代人田艺蘅曾在徽州任官,于春季二月登乌聊山,环眺徽州诸处胜景,发出感叹:“昔人谓州在万山中,视他郡最高,测之与双天目齐,理或然也。”
自宋代开始,徽州不少文人雅士选择在乌聊山麓营治宅舍。宋代歙县人罗汝楫致仕,在乌聊山南麓筑室,“疏岩斸壑,亭榭爽旷”。元代唐元,其家四世皆居乌聊山麓。洪武七年(1374)夏季,唐元之子唐桂芳复筑室于乌聊山麓故居旧址,此即文寿堂。明代中期,徽州商人汪存应也效仿文人,在乌聊山麓建友爱堂,居室十分华丽。
城中之山的幽静,对习惯城市生活而又喜爱山水之趣的文人来说极具吸引力。精明的商人看准商机,在乌聊山下开设客店牟利。明清之际人施闰章游历徽州时,描写城内乌聊山下客店:“乌聊山下好幽居,百尺寒松覆草庐。秋雨松涛声不绝,虞卿闲著几篇书。丛菊禁霜解作花,紫阳山畔晚蒸霞。谁将雪窦泉来试,有客新贻茅舍茶。”
读书乌聊山,成为不少文人的选择。明代歙县人方时化在城内选择乌聊山和仙姑井,作为读书之处。其好友休宁人程嘉燧诗中有“舟中日夜闻鸣沙,疑坐山城繁雪花。仙泉林亭湛清华,晨光瀌瀌临万家”之句,就是分别描写乌聊山和仙姑井。所谓仙姑井,相传为宋代郑仙姑所居,也在乌聊山下。
围绕读书乌聊山这个话题,徽州出现不少相关神仙传说。罗愿《新安志》载录一则:“新安多佳山水,又有前世许、聂遗风,以故人多好仙。始谢谏议微时,读书乌聊山。市人有汪四者,心爱敬公,旦就市得钱,暮辄携以相资。尝数日不来,公下山问之,人云已盗驴窜去矣。及公登第,为蜀中县令,一日有道人来访者,乃汪也。与坐书室,汪起,画壁为岩洞,有朱门金锁,解腰间钥开之,挽公同入。公请归白嫂,汪遂先入。比出,壁屹立如故,汪亦不复见。”该则传说颇有影响,为弘治《徽州府志》等典籍抄录,流传渐广。读书乌聊山,也成为徽州较具代表性的文学意象。
文人游览山中胜景、营治宅舍、读书山中等活动,使乌聊山名声大噪,儒学文化形象更加丰满。如何将名气日增的乌聊山纳入徽州山水景观的表述体系,是摆在当时文人面前的一个重要任务。
四、乌聊山与新安八景
乌聊山汪王庙内,原设钟楼。弘治九年(1496),应僧人正晓、景祥之请,徽州知府祁司员重建钟楼。弘治十七年,时任徽州知府何歆认为:“钟楼与谯楼近,取其钟鼓相节奏也,在处皆然。今钟楼偏寓,钟鼓不复相应,非制也。”在何歆的主持下,钟楼从乌聊山汪王庙迁往徽州府治东南处。在钟楼矗立在乌聊山的岁月里,乌聊晓钟成为山中一大胜景,也是徽州士人品赏的著名景观之一。

新安八景之说,并非始于唐文凤。元代散曲名家张可久就曾提出新安八景:花屏春晚、练溪晚渡、南山秋色、王陵夕照、水西烟雨、渔梁送客、黄山雪霁、紫阳书声。名声日隆的乌聊山,未能进入这位庆元文人关于徽州山水景观的表述体系。
与张可久不同,对于徽州本土文人来说,乌聊山则是魂牵梦绕的地方。至元二十四年(1287)十二月,年届六旬的方回极为狼狈。当月二十八日,路途泥泞,方回长途跋涉,到达句容县。夜宿客店,没有床榻,仅二凳一毡,条件十分简陋,又遭到店妪不友好的对待,危坐终夕。次日岁除,他写下“句容破店无卧榻,一夜打坐如禅僧……客中知我何如人,店妪无赖肆讥侮”之句,气愤之余,思乡之情油然而生。这一年为丁亥年,是方回的本命年。在当年除夕,为加紧赶路,他经过白土市时没有住旅店,深夜无奈投宿农家,竟与牛同屋。至此狼狈已达极点,方回在除夕夜作诗纪事:
灯下见异物,非马非骡驴。藏牛于屋内,云以避穿窬。终夕噍草声,去枕才咫且。从者各僵仆,不异犬与猪。平生几今夕,亦尝分郡符。军府炽庭燎,丽谯侈门符。宾客候兵卫,儿童奉屠苏。焉知穷且老,狼狈逃村墟。疮痏腰膂破,痒痛皮肤枯。大风鼓天地,啸鬼号鼪狐。使其伏榛莽,岂不戕厥躯?遥遥乌聊山,有竹有琴书。我故念我家,儿女亦念予。目睫竟不交,炯然如鳏鱼。晓行付一笑,终夕空嗟吁。作诗纪此事,异时示吾雏。
方回为徽州人,家在乌聊山下。在困窘至极时,方回想起“遥遥乌聊山,有竹有琴书”的生活图景,乌聊山不仅是其思乡的著名景物,更是徽州的重要地标。徽州人思乡之情生成之际,乌聊山往往是最容易被想到的地标之一。
方回的朋友也将乌聊山视作徽州的地域象征。钱塘人仇远雅好游历,题咏各地山川,性喜交友,与方回来往密切。方回去世后,仇远作五言律诗《怀方严州》五首,最后一首曰:“八十一年休,云何不首邱。岂无商女恨,肯作贾胡留。书籍从人卖,田园有子收。乌聊山在望,风雪去悠悠。”念及歙县故人,仇远似乎眼前浮现徽州重要地标乌聊山的风雪悠悠之景。
对于外地人张可久提出的新安八景之说,徽州人似乎并不完全认可。因此至明朝初年,徽州本土文人唐文凤重新品评新安八景,才将“乌聊晓钟”选入其中。新安八景内容的变化,不仅反映出徽州本土文人在品赏徽州山水景观中话语权的增强,也是乌聊山名气进一步提升的生动体现。
在乌聊晓钟进入新安八景后,乌聊山作为徽州地域象征被不断强化,并反映在徽州内外的文人作品中。
清朝初年,苏州人尤侗获得新安友人所赠墨、茶。在谢启中,尤侗说:“松烟出自庐山,石花产于蒙顶,兼斯二妙,独有新安。乌聊山下,丸作龙纹;灵岩洞中,片如玉乳。”尤侗提及徽州所产之墨时,直接以“乌聊山下,丸作龙纹”来概括。在这位外地人看来,乌聊山作为一个文化符号,是徽州的象征。
乌聊山成为徽州象征符号之一,在乾嘉时代洪亮吉的事例中也可得到体现。当时旧仆朱禄忽染危疾去世,洪亮吉心情悲痛,至胡唐寓所索饮,酒醉而归,赋诗一首,有句曰:“我前与君同里井,三十六峰悬倒景。乌聊山头笋堪煮,更摘乡园雨前茗。”酒席上,吴文桂拿出问政山笋、松萝茶给在座之人品尝,故洪亮吉诗中有“乌聊山头笋堪煮,更摘乡园雨前茗”之句。但奇怪的是,洪亮吉并未直接以问政山笋入诗,反而说是乌聊山头之笋,并在诗后注曰:“时吴上舍文桂出问政山笋及松萝茶啖客。”以乌聊山笋代替问政山笋、乡园之茗替换松萝名茶,是祖籍徽州的洪亮吉对故乡的真情流露。洪氏此举,是乌聊山作为徽州地域象征的最好反映。
五、结 语
徽州地处山区,不乏名山胜景,但地方志书在编纂“山川”一门时,往往首先刊列乌聊山。这种书写方式,不仅体现在徽州地方志书上,还影响了官修地理总志、正史以及私人地理著作对徽州山川的表述。无论是《大明一统志》《明史·地理志》,还是《广舆记》等,都采用“徽州山川,首列乌聊”的书写方式,将其他山川列于乌聊山之后。这一书写现象的出现,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嘉靖《徽州府志》载:“若稽新安,奠高山大川。郡城内东南,近而尊曰乌聊山,一名富山,磅礴治城,雄挟阛阓,有东汉毛甘万户营址,有唐越国汪华庙宇,山麓有越国迁郡旧址。”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里也抄录嘉靖《徽州府志》这一记载,强调乌聊山在徽州山川中“近而尊”的特点。正是由于乌聊山具有“近而尊”的优势,才促成“徽州山川,首列乌聊”书写现象的出现。
乌聊山在徽州山川中“近而尊”的特点,是在城池、祠庙、州学等人文景观的共同塑造下形成的。在历史文献中,毛甘故城大量而又频繁出现,是对徽州山越历史的文本记忆。隋朝末年,汪华将新安郡治迁至乌聊山,并倚山建筑城池。唐宋时期,徽州仍然沿用汪华所筑之城。尽管北宋宣和年间发生“徽州迁城事件”,但徽州州治最终迁回乌聊山旧城,从而奠定此后数百年徽州城发展的基本格局。从东汉末年的毛甘故城,到隋唐以后的城池,乌聊山与徽州城不仅在地理位置上具有“近”的特点,也在历史发展中具有唇齿相依、层次更深的“近”的关系。乌聊山在徽州山川中的尊崇地位,不仅与上述徽州建城史密切相关,而且是在更为复杂的历史进程中形成的。在乌聊山上,以汪王庙为中心,形成一个庞大的祠庙建筑群。尽管这些建筑可能存在时间错位,但徽州民间信仰在空间上的这种集聚性,使乌聊山成为徽州的祭祀重地,并被塑造为徽州民间信仰的生成地和归属地。乌聊山被世人称作“庙山”,也正根源于此。徽州州学两度迁至乌聊山,成功塑造该山的儒学文化形象。文人游山、营治宅舍、读书山中等活动,则扩大乌聊山的名气,丰富其儒学文化形象。从时间上来说,乌聊山在徽州山川中“近而尊”的特点形成于北宋时代。当时州城、州学、汪王庙、岱岳庙等都已在山上创立,徽州城市发展、文化教育、社会生活、信仰习俗等方面均受此山影响,使乌聊山地位空前尊崇,并成为徽州名山。因此,南宋前期罗愿在编纂《新安志》时,意识到乌聊山的尊崇地位,将其列为徽州山川之首。这种“徽州山川,首列乌聊”的书写方式,正是对北宋时期乌聊山名山形象塑造成功的追认。
徽州名山众多,乌聊山只是其中一座。如何将名气日增的乌聊山纳入徽州山水景观的表述体系,是摆在当时文人面前的重要课题。从张可久的新安八景之说,到唐文凤重新品评的新安八景,两个版本在内容上出现巨大变化,特别是后者增入“乌聊晓钟”这一景观。地域景观表述体系的变化,不仅反映出徽州本土文人在品赏徽州山水景观中话语权的增强,也是乌聊山名气继续提升的生动体现。而乌聊山作为一个文化符号,则成为徽州的象征。
从乌聊山的名山生成史可以看出,对于自然条件并不突出的小山来说,人文历史的塑造是其成为名山的主要途径。山水与人类社会之间,存在明显的互动关系。山水所在范围内的人文景观,是人与山水互动的结果,也为由山观史、由水观史提供了可能性和切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