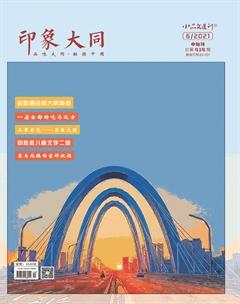民族融合的大同亮点
李生明


大同,因其所处蒙古高原南端和黄土高原东北边缘以及北半球400毫米年等降水量线上的特殊地理位置,自然成为北纬38度-北纬43度范围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碰撞、摩擦的拉锯地带,成为中原汉民族所建王朝的边防和北方游牧民族南下中原的重要关口,同时也成为民族交流融合的平台和纽带。
“大同”寓意“大融合”
从地缘学上讲,大同地区是历史上中原汉民族与草原民族争战拉锯之地,因而也是农耕文化与草原游牧文化共生共存、多民族混居的地带。从秦汉至明清的2000余年间,此地共发生60多次较大的攻防战争,为古代史上山西乃至全國发生战争密度最大之地。然而,纵有太多金戈铁马,蕴含着人类本初告别厮杀、远离战争的朴素理念,期望“天涯静处无征战,兵气销为日月光”的“大同世界”,依然是历史发展和演变的大趋势。
“大同”之名,是由汉代的“平城”渐次演化而来的。汉代统治者将此连年鏖战征伐之地命名为寓意和合、和谐、和睦的“平城”。当然,夹在太行山与阴山余脉之间,本身的盆地特征也是当初命名的一个自然因素。唐代曾在北部边防设置大同军节度使,此军名被后世用作地名“大同川”。大同川在唐代“中受降城”西,即今内蒙古包头市敖陶窑子。之后,大同军节度使迁至“燕云十六州”之一的云州。至契丹族建立的辽代,统治者依然想一统天下,便于公元1044年将此作为由北向南征战全国的“桥头堡”,正式改名为“大同”,客观上顺应了各族人民世代祈求和平大融合的意愿。
汉民胡人互化时为常态
胡人是中国古代中原汉民族对北方边地和西域民族的统称,后泛指外域民族。我们日常食用的胡麻、胡芹、胡桃、胡萝卜、胡椒、石榴、葡萄、番茄等食物,都属于民族交流融合背景下的“胡化”产物。
《魏书》曾记载当时中亚、西亚、西域46个国家共109次的朝贡记录,除来自各国的外交使节外,还有包括官僚、姻亲、商人、僧侣、工匠、伎乐各色人等的西域胡人在平城定居。这些西域胡人,主要是今西北地区包括塔里木河流域于阗、龟兹、疏勒、鄯善等国诸民族,也有中亚昭武九姓粟特人、西亚的波斯人、南亚天竺诸国人等。云冈石窟中雕刻的气鸣乐器、弦鸣乐器、膜鸣乐器中,既有汉魏旧乐琴、筝、笙之类,也有龟兹筚篥,印度和波斯的箜篌、琵琶,合以弹指、抃(拍掌)、吹指等。1965年、2000年,在大同御河之东原雁北师院(今大同大学)出土的北魏平城时期的胡俑,很可能就是当时来自异域人士的写真。
历史上的大同,耕地与草场相间,窑洞与毡帐并立。这里既是汉民族传统耕作之地,也是北狄及其后匈奴、东胡各部族流动寄居生活之地。大同作为一个历史舞台,拓跋鲜卑建立北魏,契丹建立辽,女真建立金,蒙古人建立元,还有匈奴、柔然、突厥、乌桓、慕容鲜卑、鞑靼、沙陀族、瓦剌部等民族,都在此上演过战争与和平的一幕幕活剧,并留下诸多文明印迹。可谓胡人汉化、汉人胡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汉胡一统成为当时官府和百姓生活的常态。
有“大唐从北魏走来”一说
战争与和平是民族交往过程中不可分割的两种状态,其中不乏民族融合的领军人物,比如大同千年历史铭记的两个代表人物:赵武灵王和北魏孝文帝。
赵武灵王是春秋战国时期赵国虚心好学的一代明主,为改变赵国的落后面貌和军队战力,他不畏阻力,果断放弃汉人的战车和服饰,招募胡人骑兵,强令国人穿着胡人服饰,学习胡人骑射,极大地提高了赵国将士的骑兵战力。他还抛弃民族偏见,选贤任能,大胆起用胡人,重用出身于楼烦和匈奴等少数民族的人才,使赵国的戎狄外族之臣成为他的一批得力助手。同时,实行汉臣和戎狄大臣异地交流任职,加速中原文化与草原文化的融合进程。由此,大批出身低贱和有戎狄背景的胡人脱颖而出,并一度使游牧文化在赵国占据了主导地位。
北魏孝文帝是向汉民族学习的集大成者和最大功臣。孝文帝作为少数民族的杰出政治家,大力推行汉化改革,倡导学习汉族的生活方式和典章制度,鼓励穿汉服、讲汉语、改汉姓。孝文帝带头将自己的名字改为元宏,同时不拘一格选用人才,重用汉人,还鼓励鲜卑贵族与汉族通婚。北魏平城针对游牧民族与汉人的生活习俗,实行“一国两制”政策,设置管理南北两边州郡有关事务的南部尚书与北部尚书,同样极大地促进了民族融合。
孝文帝之所以不自恃拓跋本部族的优越性,不过分看重所谓拓跋皇室血统的纯正性,是因为他从文明程度较高的汉族身上看清了民族融合的大趋势,内心坚定了“大同”的理念而决意“汉化”。之后,大唐继承了孝文帝这种自信、开明、开放、博爱、包容、飒爽的鲜明民族性格,自觉融入中华民族新鲜有力的血液中,使得中华文化在文明进程中更具国际范儿。正是在此意义上,文化学者余秋雨提出“大唐从北魏走来”的论断。
选自《山西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