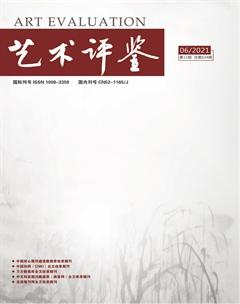比较视野下中外动画电影的叙事差异研究
孙韵岚
摘要:动画既是一种视觉艺术,也是一种叙事艺术。动画与电影在萌芽初期表现出了诸多的不同,随着动画与摄影技术相结合,“动画电影”这一概念得到了广泛的使用,二者在叙事層面也逐渐趋近同一。受美国动画影响,我国动画在萌芽初期表现出以喜剧类型为主的短片叙事模式,本土化发展过程中又出现了影戏思维。本文结合具体影片片例,从更深的层面思考造成中、日、美三国动画在叙事层面的差异。
关键词:动画电影 叙事结构 比较研究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359(2021)11-0169-04
动画是一种基于视觉感官建立起的艺术形式,同时又为观者提供了可以娱乐与消费的故事。萌芽初期,动画与电影表现出了诸多不同,“动画电影的真正普及与发展,则是在动画与摄影技术结合之后”。这种普及不仅仅预示着动画和电影在技术层面的融合,二者在叙事层面也存在着诸多的相似性。受美国动画影响,20世纪20年代我国动画在叙事上表现出以喜剧类型为主的短片叙事模式,经过本土文化的融合与转变又出现了影戏思维。本文按照国内对动画叙事研究的一般路径,结合具体片例分析中、日、美三国动画在叙事层面的差异,尝试从结构和情节等更深层面思考造成动画电影叙事差异的原因。
一、“叙事”概念的产生及其跨媒介发展
从广义角度来看,“叙事”似乎伴随着人类社会同步产生,人类个体或族群发展的过程中有讲述与倾听的需求,并试图通过口述、文字、图形等多种形式记录下人类自身的发展史,以此来传递或表达某种信息、情绪与观点。从词源来看,现代意义上的“叙事”概念是经过了几次发展之后得到的统一认知。国内学者对此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如余丹学者在肯定了胡亚敏教授对于“叙事学”研究的基础上,经过详细梳理史料,介绍了“叙事”在我国发展的渊源,认为该词最初在古汉语中并非是作为合成词出现的,又分别对“叙”与“事”展开解读。作为文学概念的“叙事”是在《文心雕龙》中首次被使用,“刘勰将其作为一种独特的叙述及表现手法”借以形容蔡邕与潘岳的作品,“在一定程度上注意到‘叙事的形式美学价值及意味”。祝克懿学者指出“叙事”意识远比现代意义上的“叙事”概念产生的要早,可以追溯至柏拉图时期,柏拉图将叙事与模仿相区别。现代意义上的“叙事”已经随着跨学科发展的背景突破原本单一学科术语,其“内涵与外延已经在现代语境下大大丰富,以这种现代意义为核心建构的叙事理论已经逐渐取得基础学科的地位”。中、外电影的剧作模式与文学保持着紧密关联,文学扩展到电影领域之后,信息需要更换不同的组织形式以顺应跨媒介叙事的需求。与此同时,自1905年由任庆泰拍摄的我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开始,影戏共生的发展路线便逐步开始形成,影响着我国电影叙事的表述形式与组织结构。
二、中、美、日动画电影叙事研究述评
(一)围绕中国动画电影展开的现有研究
关于动画电影叙事的研究,国内大多采用专题研究或比较研究的方法。例如,林清所著的《中国动画电影》,“中国动画电影”也是解读本书的重要关键词。首先,该词指明了本书是以1941年我国首部动画长片《铁扇公主》为研究起点,与短片类动画相区别。目前,关于中国动画的研究大多是按照时间脉络划分的,并且习惯将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时期的作品做“捆绑式”的研究——不区分长、短片,统称为“美术片”,把动画悬置于“艺术”之高阁,反映出将艺术与商业割裂开来的潜在含义,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国产动画商业化发展的可能。但事实上,动画短片与动画电影除了播放时长之外,在画面风格、剪辑手法、叙事结构、受众群体等多方面都存在着差别。所以,本书的研究策略可以视为是对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时期“美术片”概念的一次细化;另一方面,我国动画的起源其实还存在着较大的争议。现有资料仅表明中国动画始于20世纪20年代,但第一部国产动画的创作时间、片目、与作者都因史料不全尚未有明确的论断。其次,“中国动画电影”不仅指明了研究对象,还说明了研究意义——从叙事层面指导中国动画电影,是实现商业价值最大化的有效途径。如果抛开宣发环节,仅仅从创作层面来看,动画电影与实验短片最大的差别不在画面的视觉呈现上,而是集中在叙事部分。在实验短片中有繁多的视觉组织方式,这些创作手法很少能在动画电影中看到,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动画电影更多的要考虑到商业回报性。如果资金、人员和时间协调合理,画面风格的差异将不再成为区分实验动画与动画电影的标准。例如在2017年上映的由多洛塔·科拉别和休·韦尔什曼共同执导的《至爱梵高·星空之谜》,创作者联合了125位画师,在长达95分钟的影片中用梵高的画风为观众拼凑出这位伟大的画家在临终前的内心世界。实验动画体现出了服务于作者的特点,而动画电影则需要在叙事方面做好作者表达与受众接受的平衡。如果从叙事角度展开动画电影的研究,我们就可以发现自20世纪40年代初到80年代末我国美术长片为何在商业价值方面没有为后世国产动画留下可以复制或学习的宝贵“遗产”,也能够帮助动画从业者找到一种更为可行的叙事策略以收获更大的市场价值。本文是在叙事学领域内展开思考,横向对比了中、美、日三个国家首部动画长片的异同;纵向是以1941-1985年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生产的9部长片为主要研究对象,着重围绕“结构”“角色”“情节”“改编”等四个方面进行深入的研究,试图找到动画艺术在结合各国民族文化的土壤后产生了哪些嬗变,还有儿童文学对动画叙事的影响与关联。
(二)中、日、美首部动画长片的异同
著作首章从策划、剧作的取材与主题、女性角色、改编等几个方面对比了中、日、美三国的首部动画长片。在美国大萧条时期,迪士尼为了维持公司生存、保存现有的核心制作团队,将创作重点转向了能获取更多收益的动画长片。《白雪公主》是欧洲流传已广的故事,最经典的版本出自于1812年的《格林童话》,迪士尼创作的《白雪公主》(1937年)与前者有较大的差异,首先,叙事框架上采用了“三幕架构”的形式——“灰姑娘式的开端,睡美人式的结局,中间部分是白雪公主式的发展”。其次在细节方面,小矮人由原著700多岁的老人形象化身为孩童。白雪公主是因为小矮人们糟糕的生活现状,才决定留下来照料他们的日常起居,以“母子”的身份消减了原著人物关系中的“性”尴尬。最后,歌舞表演是迪士尼动画的“保留曲目”,也是早期动画遗留下的娱乐精髓。早期动画中多见以动作叙事取代情节叙事的“视觉杂耍片段”,这种不含有逻辑衔接的嬉闹式杂耍表演逐步演变出顺应故事情绪展开的歌舞段落,如同绘画的装饰风格在视觉艺术中得到的应用,反映出创作主体具有较强的舞台展演构思,企图呈现出与现实生活迥异的视觉奇观。
1940年初《白雪公主》在中国的热映直接促使中国的首部长片创作提上日程。《铁扇公主》(1941年)同样采用了“耳熟能详”的民间故事改编策略,尝试与西方的公主一较高下。林清認为创作者万氏兄弟将原作中的反派公主形象改编为值得被同情的“弃妇”,最终的胜利也不是单纯依靠艺高胆大的孙悟空,还因为有唐僧英明果敢的决判力以及百姓们的携手作用,反映出上海在孤岛时期的艰难处境,暗示了只有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才能共渡难关的决心。此外,原作第六十回“牛魔王罢战赴华筵,孙行者二调芭蕉扇”改为了猪八戒调芭蕉扇,八戒在与牛魔王妻、妾周旋的过程描写强化了其好色的形象,也使后文中牛魔王变身为孙悟空骗得八戒的信任这一情节更为可信。于1958年制作完成的《白蛇传》奠定了日本动画成人化的方向,主角是白蛇和青鱼,结局改为白蛇为了救许仙的性命而放弃仙法,降为凡人,因此怀慈悲之心的法海放二人一条生路,悲剧转为了大团圆的结局。我们可以发现三部作品具有较为紧密的关联,其一,按照美、中、日的顺序依次产生了创作启蒙的连锁效果。其二,白雪公主与七个小矮人;师徒四人;许仙和他的宠物、小青和小白,这些都描绘出了一种“陪伴”关系,也可以理解为对主角(与观看者互为镜像)的关注或成长见证。其三,从功能方面看,动画是一种凝聚着集体意志的观念表达,成为了美国大萧条时期、上海的孤岛时期、日本在二战后第一次世界经济危机时期的民心慰藉。最后,都对原作进行了有效的改编,但又形成了各国不同的叙事策略——美国动画继续深化已有的嬉闹喜剧风格,从原本通过动作创造的无理之“嬉闹”转化为以追求叙事圆满之“喜”;中国动画则融入了道德伦理的思辨,鼓励用意识形态的“合”来消减和对抗现实、思想中的不合;日本动画虽然拓展出多类题材,但都着重刻画燃烬自我的热血精神,提倡“从忠”的牺牲之美。
三、从结构与情节思考动画叙事的差异
(一)“结构”引起的叙事差异
本文详细介绍了美式的“三幕架构”和“平衡模式”以及中式的“三段式”和“四段式”,使读者能够更为清晰的厘清中、外叙事结构的不同。第一,“三幕架构”与“平衡模式”,悉德·菲尔德概括总结的“三幕戏剧结构”对电影剧本创作具有很强的实践指导作用。影片经过“建置、对抗、结局”三幕形成了逐次推进的前进方向,也就是说在影片开始就通过精密的设计“情节点”发生的位置,在(角色/观众的)现实与理想的矛盾悬置下推进叙事进入到下一幕,以实现早在开篇便制定好的结局。克里斯汀·汤普森在菲尔德的基础上用“转折点”替代“情节点”,以加强叙事脉络中幕与幕之间层层递进的因果关联性与方向感。指出三幕架构存在以下问题:剧作内部的逻辑发展不可以简单的用页码与时间为单位进行统计;不能有效的为观众塑造角色形象、揭示驱使角色行为改变的内心变化;不具有普遍性,不涉及“很多(好莱坞影片)纯粹的延迟手段”;三幕在影片中的位置关系不具有必然性。可见,情节划分的合理性对理解电影叙事结构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主人公的目标发生转换”是导致“叙事改变方向的最经常的原因”,因此,“如果我们能利用这些目标分析情节结构,我们就能得到一个具有起始性原理的架构”。汤普森提出的“好莱坞叙事模式”是在三幕结构基础上的细化与演进:第一部分“开端”对整体框架交代的更加精炼;将原来的第二幕细化为“铺垫”与“进展”;一个短暂的尾声伴随着最后的“高潮”部分呼之欲出,衔接自然而又余音作响。第二,“三段式”与“四段式”,中国古典戏曲中的“折”和“楔子”将剧情发展划分为大、小不一的段落,在此基础之上又发展出“四段式”的中国古典戏剧结构雏形。范椁总结了作诗的四个要领:起、承、转、合;到明代时,王骥德概括了戏曲创作要有“起”“接”“中段”“后段”全篇布局的谋略。可见中、外戏剧结构的差异集中于以下两个方面:其一,“戏剧动作的运动形式”。美式是经过阶段式的“蓄力”而达到进入到下一幕的“团块的运动状态”;中式是“线点组合的运动状态”。其二,“戏剧冲突的理解和处理”。我国在营造戏剧冲突时偏重“情感纠结,而非激烈的动作对抗”。通过对20世纪40年代至80年代的9部动画电影长片进行仔细的拆分,验证出动画同样符合中国古典戏剧的结构特征。斯宾格勒认为中国文化表现出的基本象征——“道”,是由“文化形态”决定的,宗白华更加明确的指出“我们的宇宙观是时间率领着空间,因而成就了节奏化、音乐化了的‘时空合一体”,即郑传寅所认同的中国古典艺术追求的“线条”之美,也是本文作者林清所认同的“点线式结构”所表现的“时间情节”受地理和人文两大环境因素影响。
(二)“情节”引起的叙事差异
林清指出“在家/离家/回家”(home/away/home)是最为常见的儿童文学情节模式,而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时期的作品中仅有一小部分是儿童文学的“新童话”,余下的大多取材于民间文学,这就形成了强调情节重复与因果轮回的特点。例如,本文列举了民间文学情节创作的“三次原则”在《铁扇公主》《大闹天宫》《天书奇谭》等影片中的应用。“三借芭蕉扇”“悟空三出三进天庭”“蛋生三夺天书”体现出了“排比式”的渐进变化与节奏感,形成了中国特有的叙事韵律。“在家/离家/回家”模式在我国没有得到推广,首先是因为“家”的概念在中、外是有差异的,国产影片中常常会警示“离家的后果,即危险而不是刺激”。其次出自于成人与儿童对“离家”概念出现了不对等的认知:成人认为离家代表了儿童的成长,具有积极和美好的意蕴;而离家对儿童而言却意味着噩梦。
因此,可以说叙事结构与情节是形成中、外动画电影叙事差异的重要因素,而中国动画在好莱坞商业化叙事模式下又派生出了影戏观念,反映出民族文化对动画剧作创作产生的深层动因。
参考文献:
[1]陈晓云.动画电影:叙事与意识形态[J].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05):54-60.
[2]余丹.“叙事”与“narrative”在中西传统文化语境中的差异[J].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学报,2009(02):52-56.
[3]祝克懿.“叙事”概念的现代意义[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04):96-104.
[4]林清.中国动画电影[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14:51.
[5]林清.中国动画电影[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14:26.
[6][美]悉德·菲尔德.电影剧本写作基础[M].钟大丰,鲍玉珩译.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6:74.
[7][美]克莉丝汀·汤普森.好莱坞怎样讲故事:新好莱坞叙事技巧探索[M].李燕,李慧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09:22,27,74,145-146.
[8]王骥德.曲律[M].陈铎,叶长海注释.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
[9]李晓.古典戏剧结构四段论[J].阜阳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8(04):81-82.
[10][德]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M].陈晓林译.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8:124,135,1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