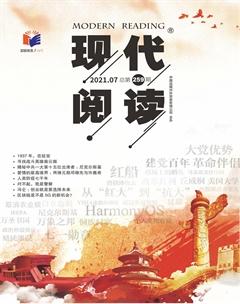罗伯特·戈特利布:我信仰阅读
1955年,一位酷爱阅读的年轻人加入了西蒙-舒斯特出版社。他一路升至主编,又跳槽到负有盛名的克瑙夫出版社当总编辑,后来还曾执掌《纽约客》。70岁时,他成为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的编辑,做出了数月狂销200万册的《克林顿传》。他,就是罗伯特·戈特利布,这位传奇出版人将带我们走进美国出版的黄金时代。
我的人生始于阅读,从此养成阅读的习惯。
阅读伴随童年时光
对我童年影响最大的书是吉卜林的《丛林之书》,我至今还保存着外公给我读的那两卷本,当时我听得如痴如醉。不过在那之前,我的最爱是多萝西·孔哈特的《乳酪甜点真好吃》。我太喜欢了,怎么读也读不够。下一本让我爱不释手的书,是赫斯特老师在我们四年级班上念的艾伯特·帕森·特哈尼的《神犬拉德》。我最近重读这本书时发现,在拉德的种种丰功伟绩中,它救过一个瘫痪的5岁女孩。在一条斑斓的铜头蛇扑向她的时候,它奋不顾身挡在她的身前,差点中蛇毒而死,而女孩受到刺激竟站起来走路了。拉德可不是一般的狗,这一点我们从书的第一段就知道了:“它有火枪手达达尼昂那般的勇气,还有非凡的智慧。无论是谁看到它那双忧郁的棕色眼睛,都不会怀疑它是有灵魂的。”赫斯特老师朗读的时候,我费了好大劲才不让人看出我在哭。正是《神犬拉德》让我发现,书籍具有神奇的力量,能让人动情,甚至改变人生。
不过,对我的童年甚至一生产生关键影响的书,是阿瑟·兰塞姆从1930年出版的《燕子号与亚马逊号》开始的12部系列小说。燕子是沃克家4个孩子自称的代号,亚马逊则是布莱克特家2个女孩的代号,他们夏天分别驾驶着“燕子”号和“亚马逊”号这两艘小船,在经过作者想象加工的英格兰大湖地区的温德米尔湖上航行。在第四部《进军“北极”》中,又有两个卡勒姆家的孩子加入进来。这两个人物形象是我感到最亲近的:他们都爱读书,害羞而孤单,是被卷入燕子们和亚马逊们探险的外来者。这些书吸引我的,并不是航行、野营、赛马或者其他不那么激烈的活动,而是这群聪明独立的少男少女,在兰塞姆的笔下,个性鲜明,受到父母信任,享受着健康成长的童年。既然沃克家和布莱克特家的孩子能接纳卡勒姆家的孩子,他们或许也能给我腾点地方。有四五年时间,我一遍又一遍地读我最爱的兰塞姆小说,特别喜欢的几本起码读了50遍。
广播电视与阅读
小时候我体弱多病(实际没那么严重),经常病假在家不去上学,痴痴地听各种广播肥皂剧。我认为所有这些感伤的通俗广播剧促成了我后来作为读者和编辑对类型小说的欣赏趣味。当然,它们都是无伤大雅的东西,剧中没什么真正恶劣的、肮脏的事情。20世纪50年代初,我从剑桥大学回国,又回到追肥皂剧的日子——正赶上《生活可以是美好的》最后一集——一切都变了:酗酒、婚外恋都有了,魅力没了。肥皂剧的市场正向电视转移。
听肥皂剧是一种特殊嗜好,夜间广播节目则是人人都听的。当时选择少。我得跟父母大闹一番才能被允许开着收音机做作业。他们不明白,当我傍晚收听《午夜队长》《小孤儿安妮》和我特别喜欢的《杰克·阿姆斯特朗,典型美国男孩》这些儿童节目时,其实我也是在做作业。我还有幸见证了漫画书上的超级英雄超人、蝙蝠侠从诞生到搬上银幕的早年历史。他们也是独来独往,戴着面具,无所不能。漫画书是家长的眼中钉,因为里面的暴力以及书中主人公与大反派的殊死搏斗,大概会诱使我们这些中产家庭的孩子使用暴力,即使达不到犯罪的程度。
总之,那是一种推崇甜美的流行文化,从平淡无奇的流行音乐到报纸上每天刊登的“漫画”,无不如此。只是我看不到那些漫画,因为我家里只订《纽约时报》,上面不登這些。所以我看不到大力水手,看不到迪克·特雷西,看不到小阿伯纳。而且基本上没有电影可看,除了我7岁时迪士尼发行的《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它伤害了我幼小的心灵:我被那个美艳绝伦又蛇蝎心肠的王后吓坏了,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
一家三口的阅读日常
大多数时候,我父母和我一样,喜欢阅读。我妈妈在没什么钱的家境中,在波士顿和纽约度过了文雅、有教养的童年。她最爱的小说是乔治·艾略特的《弗洛斯河上的磨坊》。我母亲有教养的家庭背景一定是吸引我父亲的主要因素。他来自一个更为典型的移民家庭,父亲是基本不说英语的正统派犹太人,一辈子研究《塔木德》,跟谁都处不好。我们就是孤零零的一家三口。大萧条时代结束前后,即使我们家存款还很少,我父亲就有一大奢侈消费,他会到街对面的布伦塔诺这家美国顶尖的书店,扎进他喜欢的五六本非虚构书籍之中:霍姆斯大法官与拉斯基的书信集、伯特兰·罗素、乔治·桑塔耶那、卡伦·霍尼,还有纽约市立学院著名的哲学家莫里斯·拉斐尔·科恩的著作。
我母亲则始终如一地爱读书——反复阅读旧书,从公共图书馆借的书,还有从所谓租书店里租的书——租书店通常开在文具店或者药店里,一角或者一角五分就可以租最新的热门书籍看3天。我自己嘛,到高中时这3个来源的书都看,每天晚上至少要读一本新书,以满足我强迫症一般把每一本畅销书或畅销书黑马在出版几天内就读完的愿望。我还记得一个同时有两本新书要读的危急时刻,因为直到我出发去夏令营的前一天才借到,一本是玛杰丽·夏普的《大不列颠马厩》,另一本应该是达夫妮·杜穆里埃的书。我通宵狂读,留给母亲第二天去还书。
既然书在我们家是天经地义的东西,我觉得我们一家三口都坐在餐桌前读书这种场景也是合情合理的,后来我才意识到这可不正常,这是某种特殊的心理障碍的症状。我的阅读方式也挺古怪的:可以说我是“吞”书,一目十行地浏览,而不是逐行细读。等我成为编辑时,这种浏览的习惯就必须改变了:这对迅速判断书稿好坏很有帮助,但编辑工作本身是一种缓慢的、耗费心血的过程,为了尽善尽美,我必须改变阅读习惯。
阅读改变人生
20世纪40年代初,我花了大把时间在《国家地理》随刊附赠的大幅折叠地图上追踪战事的进程,它们被我贴在卧室的墙上。1945年,也就是我14岁那年夏天,我设法让送报员每天把《纽约时报》送到夏令营,广岛原子弹爆炸的新闻使我一改往日的平静,大惊失色。那年早些时候,刚被解放的死亡集中营那些更为可怕的照片已经见诸报端。对于家里没人参战的美国孩子来说,除了影响不大的食物配给和征集银箔、橡皮筋之类的战争物资,战争基本上是发生在舞台背后的事,模模糊糊,对我来说它就像另一种连续剧。不过,我仍像所有人一样,盼望着盟军进军法国的消息。1944年6月6日上午,收音机里传来诺曼底登陆的消息,我冲出门去,把所有的晨报都买了一份。那是我一辈子最兴奋的时刻之一。
我10岁、11岁的时候,父母认为我应该呼吸更多新鲜空气,不能总是窝在西九十六街的公寓楼九楼,于是我被要求每天至少有一小时的户外活动。我家离中央公园近在咫尺,可大自然对我没有吸引力,时间一到就上楼回到我的书和广播中间。从一开始,我就觉得文字比真实的生活更真实,当然也更有意思。
我如痴如醉地追读那个时代最受欢迎的类型作家,上大学以前的阅读体验中关键性的一次是16岁时初次读《爱玛》。当我读到爱玛在博克斯山野餐的那一个著名场景中羞辱落魄的、不招惹别人但爱说话的贝茨小姐时,我的心里充满羞愧:这一幕鞭策我审视自身随意、不善待别人的行为。简·奥斯汀把我钉在了墙上。这是我第一次真正把阅读的体验与内在的自我联系在一起。我这辈子做事的原则无非是努力二字,我也不是善于哲理思辨的那类人。是小说,从那次阅读《爱玛》开始的小说,使我发现了某种道德指南针。
(摘自中信出版集团《我信仰阅读:传奇出版人罗伯特·戈特利布回忆录》 作者:[美]罗伯特·戈特利布 译者:彭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