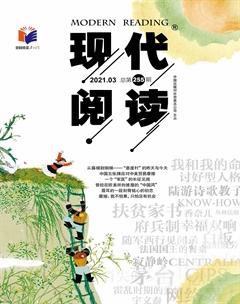有多少爱可以重来

许历农,号耕甫,1918年出生于安徽,高中毕业后入伍当兵,参加过对日抗战。1949年随国民党军队到台湾后,长期担任军中要职。曾任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台行政机构“退除役官兵辅导委员会”主任。晚年,他为反“独”促统大业四处奔走,在促进两岸和平统一的志业上再攀高峰。本文作者为许历农的女儿许绮燕,许历农到台湾时,3个月大的她被留在大陆,父女二人在开放两岸探亲之后才得以团聚。
我能记事的时候,我和我的外公外婆住在一起:我的热心快肠、乐于助人的外婆是湖北武汉武昌区人民代表,一天到晚忙里忙外的,倒是外公常常静静地和我处在一起。童年生活的那份乐趣、那份安全感,我至今难忘。
7岁那年,母亲接我回家,我开始上小学。在我自己的家里,我发现一个问题:我的爸爸和弟弟妹妹都姓张,妈妈姓王,而我姓许。这是为什么呢?我很想问问大人,但我没敢问。在我的中心,我在这个家中好像合理又好像不合理。生活像一个谜,我好些年都解不开。早几年,父母在武汉市工作,父亲是一家造船厂干部,母亲是工人。后来,遇上城市人口大下放,父母先后到了通山县。父亲到通山县后还得到了一份看守废旧车间的工作,母亲就没有工作了,每天四处寻找一些零碎的重体力活做。最苦的是母亲,无论有伤有病,她都不敢休息。黄嘴待哺,她担心的就是找不到活做,只要能找到活,无论怎样脏、怎样重、怎样苦,她都觉得是好运气。
母亲在一个废旧车间搭了两个铺,就成了我们姐弟妹几个的寝室。我作为大姐,每天带着弟妹们到学校去,放了学,我就赶快回家帮母亲做家务,做饭洗衣收拾房子,什么都做。我努力把一切做到最好,我想做孝顺的女儿,我想看到父母脸上有欣慰的笑容。可后来我越来越清楚,无论怎样努力,我都做不到这一点。
到了20世纪80年代,台湾来的陆羽儒先生在统战部门的帮助下找到了母亲和我。我这才知道我的亲生父亲还活着,并且是国民党高级将领,官至国民党中常委、“国防部总政治作战部主任”。
母亲通过录音机对我父亲说了几句话:“很想念你,不知你几时能回来,我们还能见上一面。你爱吃煎饺,我给你做。”
母亲原先一直不肯对我说我的身世,知道了父亲的下落之后,母亲主动拉我坐到她的身边,细说了以前的故事。
原来我的生父名叫许历农,曾是外公手下的兵,那时他们驻守在北平。外公很欣赏我父亲,说此子必成大器。果然,没几年,父亲就被提升为营长。母亲由外公做主,嫁给了我的父亲。
我出生在北平。呱呱落地时,父亲好高兴,给我取名绮燕。父亲说,绮是美丽动人的意思,燕是纪念我的出生地北平(燕京)。父亲的同事们打造了一份很珍贵的礼物来贺喜,那是一块玉匾,匾上刻着4个字:名门生秀。父亲很喜欢这块匾,把它看作女儿的吉祥物。这块玉匾后来一直由母亲珍藏,直到“文化大革命”中,被抄家的人拿走。
母亲还告诉我,我们许家祖籍安徽省贵池县(今池州市贵池区)乌沙镇。我的伯父是开明绅士,很早就把财产捐献给了共产党。母亲说,你也算是出自名门,你父亲还活着,就一定会来找你。到时候,你就把玉匾的事说给他听,记住,匾上的字是“名门生秀”,你爸一听就知道你准是他的女儿。我明白了母亲叙说以前、叙说玉匾的用意:她是怕有一天她不在了,我的父亲来找我时,我们父女无法确认。
知道了自己的身世,我半天回不过神来,生活处处承受艰难的我居然是名门之秀。好遥远的名门之秀啊,那好像是别人的故事,与我无关。我们母女抱头痛哭。
南京统战部发来邀请函,请我到南京定居,我考虑再三,还是舍不得养育我的这块土地,舍不得养育我的养父和生母,我谢绝了。在南京市台办的关照下,我给生父写了一封信,并寄去了一张全家福的照片。我父亲很快就回了信,信上说:“小燕,我的女儿,我很想你,恨不得时光倒转,重叙天伦之乐!”
随着大陆和台湾的往来禁锢逐渐放开,同根同祖的两岸人民又开始有了走动,可以互相通信,互相探望了。但台湾却因为父亲是国民党高级将领而不允许回大陆,好在还有一条政策,大陆的直系亲属可以到台湾探亲。
第一次探亲,我在台湾的家里住了20多天。以后,每年一次赴台省亲,每年一次回家小住。每次我都被父亲珍爱得不得了,都被一种深刻的亲情感动得不得了。家就是家,那么安全,那么舒适,那么无忧无虑。
母亲晚年无数次回忆起在火车站与父亲分别的情景。当时父亲说等仗一打完就回老家接我们母女。父亲和母亲都没有想到,他们这一别竟成永诀,一生一世不得再见。
父亲曾几次诘问我:“你妈怎么那么早就结了婚?我是十几年后才结婚,谁叫你妈这么早结婚?”父亲好像是不能谅解母亲,其实诘问包含了父亲心中巨大的遗憾和深深的失落。他遗憾的是没能和母亲永续姻缘,他失落的是那情真意切的爱。那山盟海誓的爱居然很脆弱,在现实面前不堪一击。
母亲出嫁的时候,只有16岁,正是人们说的“二八芳龄”,父亲大母亲8岁,也是少年英俊。他们感情极好。都给对方留下了美好的印象。
母亲说到父亲就说:“你爸真好,待人诚恳,会疼人,从不发脾气。”父亲说到母亲就说:“你妈很可爱,胖乎乎的,皮肤又好,性格很温顺,很听话。”我从父母的语气、眼神中深深地感受到了他们深沉久远的爱情。
以母亲的本意,她是不想再嫁,她已经没有完整的爱,再为自己谈婚论嫁。可是一个年轻的女子带着一个不谙世事的孩子,她顶不住政治和经济的双重压力,只能选择嫁人。然而,再嫁并没能使我母亲摆脱政治和经济压力。父亲已经成了一副沉重的十字架,重重地压在母亲背上,可母亲从来没有埋怨父亲一句。得知父亲还活着,母亲好激动,父亲的朋友来寻找她,统战部的同志来看望她,她热泪盈眶。她知道自己再也回不到丈夫身边,再也无法承受那份真爱,但只要丈夫还在人世,她就满足了,只要丈夫过得幸福,她就幸福无边了。
父亲从不直接给母亲什么,他总是给我一些钱,对我说:“你妈需要什么,你就買给她。”我陆续以自己名义用父亲的钱给母亲买了彩电、冰箱、住房和许多营养品。父亲以一种间接的方式对母亲晚年病中的生活,给予了力所能及的照顾。
近几年,父亲几次回大陆,见到了很多亲人,唯独没有见到母亲。母亲积劳成疾,卧病在床,不能走动,不能激动。我深知母亲经受不起见到父亲之后的大喜大悲,我真的不敢安排二老会面。我总想,下次吧,下次等母亲身体养得好些,再让她见父亲。2002年,父亲因公回大陆,附带省亲,这时母亲已经很衰弱了,我意识到再不相见恐怕就没有机会了。我想安排父亲去一趟母亲居住的通山县。可当时武汉至通山的公路正在维修,挖得坑坑洼洼,有的地段很不安全。统战部和台办考虑要对父亲负责,不让他去通山。父亲也怕给政府添麻烦,就说:“下次吧,下次我来,路就修好了,我一定去看你妈。”可是没等到下次,母亲就离开人世了。
母亲走后,我悲痛万分,一夜之间瘦了好几斤。我哭着给海峡那边的父亲打电话报丧。电话里传来父亲的声音,顿挫呜咽而又平静万分:“小燕,我已经知道了!”我一惊:“爸,隔山隔水,您怎么知道了?”父亲说:“小燕,你妈昨晚来找我了。那年我们在火车站分手的时候,你妈说的一句话是‘我好怕哟。几十年来,我都想不起来,昨天晚上一下子想起来了,你妈在我耳边轻轻地对我说:‘我好怕哟!我一惊,就知道是你妈不行了,果然,一清早你就来了电话。我这辈子对不起你妈,请你替我在你妈坟上献一束花!”我悲伤痛哭之余,惊叹父母之间生死有灵的遥相感应。
时光啊,为什么不能倒流?祖国啊,何日才能统一?海峡两岸,炎黄子孙,一衣带水,骨肉亲情,怎能够长期分离,天各一方?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愿两岸亲人早日团聚。祖国要统一,人民要团圆,中国人民不要“一边一国”!
(摘自九州出版社《许历农的大是大非》 作者:纪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