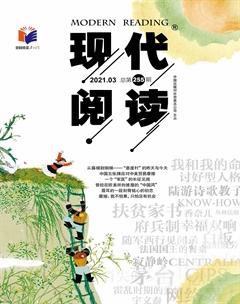断层的一边:旧时代还没有远去
谢祖墀 [美]黄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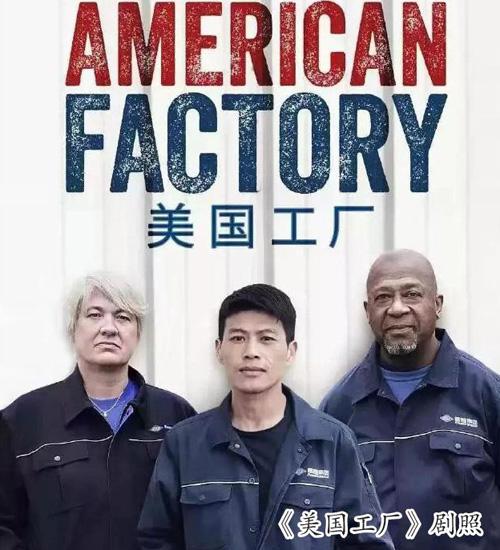

福耀玻璃董事长曹德旺从2015年开始在美国的俄亥俄州代顿市投资建厂,他看中了当地独特的区位优势。这里离底特律近,是汽车产业的核心地带;劳动力也很丰富,当地的通用汽车工厂在7年前关闭的时候,留下了一大批渴望找到工作的熟练工人;这里还有一个热情的政府,给了他1700万美元的优惠,相当于白送了一个厂房。
制造业永远在寻找成本洼地。虽然听上去不可思议,但是曹德旺认为在美国建厂成本反而比中国低。他的计算表明,在美国可以节约16%~17%的成本,从基礎材料到天然气、电、石油,这还没算运输和物流。即使是人工成本,中美之间的差距也没有那么大。
然而,问题恰恰出在人工成本上。在短暂的蜜月期之后,劳资双方开始出现了冲突。资方希望尽快盈利,他们认为美国工厂的效率和产出远远比不上中国。在国内,工人不但技术熟练,而且12小时一班,全年几乎没有节假日,而美国工人坚持8小时工作制,还有完整的周末和节假日。资方认为美国工人有严重的工作态度问题。
而另一方面,美国工人也有很多不满,他们13美元1小时的工资,
与之前在通用时的29美元1小时相差甚远。他们没有涨薪的激励,还老是被要求加班。更为严重的是由于劳动保护措施缺乏,导致工伤事故不断。工人对资方也有严重的信任危机。
最终,矛盾的焦点集中到了工会。越来越多的工人想用工会来保护自己,而曹德旺说,如果工会进来我就不玩了。这场斗争演变为一场关于是否允许建立工会的投票。
对于生活在互联网时代的我们来说,这个故事多少有点魔幻现实主义色彩。工会和8小时工作制是19世纪工人运动的口号,我们每年都要过的五一劳动节,正是为了纪念美国工人在1886年5月1日发动的芝加哥大罢工。而罢工的诉求,就是8小时工作制。这些都是以前电影里看到的情节,没想到居然离我们这么近。
那么,造成美国工厂这种局面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文化差异吗?是因为中国工人比美国工人更愿意吃苦吗?
一部2017年佛山电视台出品的纪录片《中国工厂》揭示了故事的另一面。在第一段故事《再见,老板》中,一家服装企业本来计划招700人,来了1048人,却离职了888人。负责人力资源的潘总感叹说:“以前都是工人找工厂,现在是工厂找工人。”工厂招不来人,也留不住人。心力交瘁的老潘最后也选择了辞职。
工人去哪儿了呢?早在2016年,曹德旺就批评房地产行业吸收了大量劳动力,对制造业造成了巨大的冲击。而现在的冲击者是外卖。曾经被称为“世界工厂”的东莞,2019年市里800多家企业空缺岗位近10万个,而从2013年到2018年,东莞的外卖骑手增加了31倍。为什么呢?因为薪水,以及更自由的工作方式。作为制造业龙头的富士康月平均工资是6000元,而做外卖骑手很容易就挣到8000元。难怪美团外卖的骑手中, 1/3来自产业工人。
由此来看,在追求更好的生活方面,中国工人有着同样的渴望和行动。
其实,抛开现象看本质。《美国工厂》和《中国工厂》讲述的无关文化差异,而是制造业,乃至很多传统行业的深层次危机。在缺乏技术突破和差异化的大背景下,企业之间的竞争就成为单纯的成本竞争,而人作为生产要素则被推向了极致。
制造业只是一个例子。传统模式下的矛盾也不仅仅局限于第二产业。从金融行业到零售业,甚至科技产业,我们还是能看到很多工业时代的痕迹:庞大的机构、复杂的流程、供给侧导向的思维方式,以及“996”的极致工作模式。
我们生活在21世纪,但19世纪离我们并不远。
(摘自台海出版社《竞争新边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