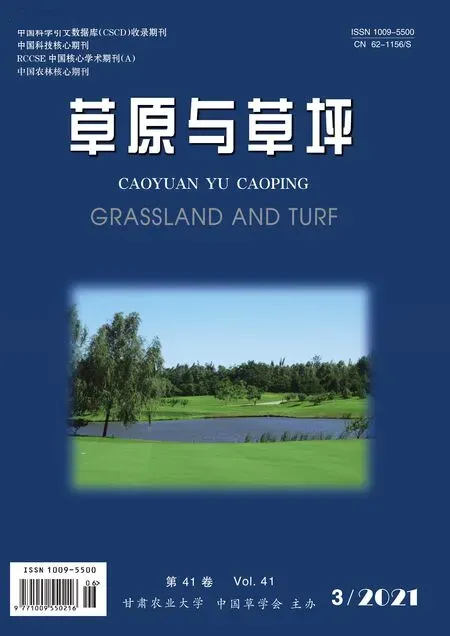放牧模式对祁连山东缘高寒草甸植被特征的影响
杜凯,康宇坤,张德罡,苏军虎
(1.甘肃农业大学 草业学院,草业生态系统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甘肃省草业工程实验室,中-美草地畜牧业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甘肃 兰州 730070;2.甘肃农业大学-新西兰梅西大学草地生物多样性研究中心,甘肃 兰州 730070)
草地是世界上主要的陆地植被类型,分布面积广泛[1]。世界草地面积约5.0×109hm2,占陆地总面积的40%[2]。我国草原面积约为3.55×108hm2,约占世界草原面积的7%左右,是世界第二草原大国[3]。我国的草原类型主要为温带草原、高寒草原和荒漠草原[4]。其中,高寒草原主要分布在我国青藏高原地区[5],受气候因素和人为干扰因素影响,该区大面积的优良草地逐渐退化,严重影响当地草地畜牧业可持续发展[6]。放牧是草地最主要的利用方式,也是影响植物群落特征的最主要因素[7]。放牧在改变植物物种组成的同时,也会改变植物群落物质和能量的分配模式[8]。然而,为追逐经济效益最大化,目前牧区超载过牧现象仍然十分突出,不合理的放牧方式不但降低了草地的生产和生态服务功能,而且直接影响牧民的生存[9]。因此,探寻科学的放牧模式对草地的可持续利用和管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10]。
放牧模式对草地植物群落特征具有显著的影响[11],放牧也会对物种丰富度和生物量产生显著影响[12]。张晓玲等[13]在青海高寒草原研究发现,全年连续放牧较冷季放牧显著降低了草地植物群落的高度和盖度以及禾本科(Gramineae)和莎草科(Cyperaceae)植物的地上和地下生物量。Li等[14]对青藏高原高寒草甸的研究发现,尽管围栏封育能够有效恢复退化草地,提高植物生物量,但是降低了植物的多样性和密度,致使群落结构单一化。吴雨晴等[15]对呼伦贝尔典型草原研究发现,划区轮牧较常牧区显著增加了植被的高度、盖度、植被多样性以及地上生物量。
祁连山地区作为青藏高原向北东方向扩展生长的前缘地区之一[16],是我国西部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对维护河西走廊绿洲生态系统的平衡和遏制荒漠化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17]。作为祁连山的主要植被类型,高寒草甸具有涵养水源、维持生物多样性和碳储存等生态服务功能[17-18]。然而,在不合理的放牧利用和全球气候变化的背景下,祁连山高寒草甸退化严重,生产和生态服务功能严重降低[19]。尽管目前对祁连山高寒草甸植被的研究较多,但主要集中在不同放牧强度和退化程度等方面[20-22],而对不同放牧管理模式的研究较少[23]。此外,目前仍不清楚在不同放牧模式下高寒草甸植被特征如何变化。
因此,本研究以祁连山东缘5种放牧模式(全年连续放牧、冷季重度放牧、冷季轻度放牧、全年划区轮牧和全年禁牧)草地为研究对象,全面系统地研究植被组成、结构以及植物群落多样性的变化,探讨不同放牧模式对高寒草甸植被特征的影响,从生产力和多样性维持角度探寻适宜的草地管理模式,以期为祁连山高寒草甸的放牧管理提供科学依据。
1 材料和方法
1.1 试验地概况
试验地在祁连山东缘的天祝县藏族自治县抓喜秀龙乡金强河谷二级阶地,地理坐标N 37°11′16.68″ ~37°12′51.01″,E 102°44′15.58″~ 102°47′20.81″,试验区平均海拔为2 960 m,属于典型的高原气候,气候寒冷潮湿,空气稀薄,昼夜温差较大,太阳辐射强烈,雨热同期,无绝对无霜期,仅分冷、热两季,植物的生长期为120 d。气温介于-11.4℃~11.2℃,平均气温0.16℃,年均降水量416.9 mm[14]。土壤类型为高山黑钙土,草地类型为高寒草甸,优势物种为垂穗披碱草(Elymusnutans)、异针茅(Stipaaliena)、冷地早熟禾(Poacrymophila)和矮生嵩草(Kobresiahumilis)等。
1.2 试验设计
通过走访牧民和查阅资料发现,目前研究区的放牧方式主要有以下5种,分别为全年连续放牧(Continuous grazing,CG)、冷季重度放牧(Heavy grazing during the dormant seasons,HG)、冷季轻度放牧(Lightly grazing during the dormant seasons,LG)、全年划区轮牧(Rotational grazing,RG)和全年禁牧(Non-grazing,NG)。因此,于2016年5月在研究区金强河谷的二级阶地上选取当地现有的上述5种放牧方式草地,各处理3个重复。CG样地全年连续放牧利用,放牧家畜为藏系绵羊和牦牛,面积为1.5 hm2,放牧率折算为5.1~5.5羊单位/(hm2·a);HG样地于每年10月中旬至次年5月中旬放牧利用,其余时间休牧,放牧家畜为藏系绵羊和牦牛,放牧率折算为5.1~5.4羊单位/(hm2·a),面积1.5 hm2;LG样地于每年10月中旬至次年4月初放牧利用,其余时间休牧,放牧家畜为藏系绵羊和牦牛,放牧率折算为4.1~4.3羊单位/(hm2·a),面积1.4 hm2;RG样地设5个面积基本相当的草地,每个小区放牧8 d,周期为40 d,于2006-2016年每年5月中旬至11月中旬进行轮牧,放牧率折算为5.2~5.4羊单位/(hm2·a),面积0.75 hm2;NG样地自2011年5月开始全年禁止放牧利用(禁牧前属轻度),至2016年已禁牧5年,面积1.4 hm2。CG、HG和LG样地已按上述方式放牧至少9年以上。
1.3 取样方法
于2016年9月初进行植被调查和采集。分别在各样地植被较为均匀、能代表整个样地的地上随机设置20个1 m×1 m的样方,总共100个样方。首先用针刺法测定样方内各种植物的盖度,其次测定每一种植物的高度(自然高度),每种植物15个重复(若样方内不够,可测样方外),然后测定每种植物的密度(以株丛为单位,根部紧密连在一起的记为一个株丛[11]),最后按种齐地面刈割,同时收集样方内的凋落物,将植物样品置于标记好的信封,带回实验室。在各刈割后的样方内用内径10 cm的根钻采集0~50 cm(一层)的土壤样品,各样地20个重复,并用清水冲洗尼龙网袋法获取根系生物量。将上述植物、凋落物和根系样品立即在105℃烘箱中烘30 min,然后转至70℃,直至烘干,称重。
1.4 数据分析
物种重要值(Ni)=(相对盖度+相对密度+相对高度+相对生物量)/4
Shannon-wiener多样性指数(H)、Pielou均匀度指数(J)、Patrick丰富度指数(S)和Simpson指数(λ)均按马克平等[24]的方法计算。
采用Microsoft Excel 2010整理数据,用SPSS 19.0(SPSS for Windows,Version 19.0,Chicago,USA)软件单因素方差分析中的多重比较方法对各样地植被特征在95%置信区间上进行显著性检验。
2 结果与分析
2.1 物种组成变化
共统计到17科,34属,39种植物(表1)。连续放牧样地的优势植物主要为异针茅(Stipaaliena)和醉马草(Achnatheruminebrians);冷季重度放牧样地的优势植物为冷地早熟禾(Poacrymophila)、异针茅、赖草(Leymussecalinus)和矮嵩草(Kobresiahumilis);冷季轻度放牧样地的优势植物为冷地早熟禾、垂穗披碱草(Elymusnutans)、异针茅和赖草;划区轮牧样地的优势植物为垂穗披碱草、冷地早熟禾、赖草和洽草(Koeleriacristata);全年禁牧样地的优势植物为垂穗披碱草和冷地早熟禾。总物种数在划区轮牧样地最多,为27种,其次为冷季轻度放牧样地,为19种,再次为冷季重度放牧样地,为15种,接着为全年连续放牧样地,为13种,最后为全年禁牧样地,仅有7种植物。禁牧5年后,植物物种数明显降低,而直立、高大型的垂穗披碱草的重要值急剧升高(高达0.96),使得阔叶杂类草从群落中消失,从而导致群落结构单一化。因此,从植物群落物种组成上来看,研究区高寒草甸生态系统的最佳放牧模式为划区轮牧,其次为冷季轻度放牧,再次为冷季重度放牧,而全年连续放牧和全年禁牧效果最差。

表1 不同放牧模式下高寒草甸植物物种组成及重要值
2.2 植物高度变化
不同放牧模式下高寒草甸禾本科、莎草科、豆科(Leguminosae)和杂类草高度变化趋势相同,均在NG样地最高,且显著高于其他样地,RG次之,接下来是HG和LG,而CG样地最低(图1)。禾本科高度在NG、RG、LG、HG样地较CG样地分别增加了5.61、4.79、3.00和2.39倍,莎草科高度分别增加了7.9、4.2、1.9和1倍,豆科高度分别增加了9.5、6.17、3.83和3倍,杂类草高度分别增加了4.25、2.5、3和2.38倍。

图1 不同放牧模式下各功能群植物高度
2.3 植物盖度变化
不同放牧模式下高寒草甸各功能群盖度呈现不同的变化规律(图2)。禾本科盖度NG>RG>LG>HG>CG,其中NG、RG、LG和HG样地较CG样地分别显著增加了8.81、6.04、3.62和2.23倍。莎草科和豆科植物盖度的变化规律相似,均在CG样地中最高,而在NG样地中显著低于其他样地。杂类草植物盖度在LG样地中显著高于其他样地,HG样地次之,而NG样地最低,LG、HG和RG样地较CG样地分别增加了0.89、0.52和0.13倍,而NG样地较CG样地显著降低了52%。植被总盖度在RG和NG样地最高(均为100%),显著高于其他样地,而在CG样地最低,显著低于其他样地(图3)。NG、RG、LG和HG样地较CG样地总盖度分别增加了0.89、0.89、0.65和0.44倍。

图3 不同放牧模式下植被总盖度
2.4 植物密度变化
不同放牧模式下各功能群植物密度表现出不同的变化趋势(图4)。禾本科植物密度NG>RG>LG>HG>NG,其中NG、RG、LG和HG样地较CG样地分别显著增加了4.52、2.78、1.92和0.79倍。莎草科植物密度在CG、HG、LG样地间差异不显著,但均显著高于其他样地。豆科植物密度在CG样地中最高,RG样地次之,NG样地最小,HG、LG、RG和NG样地较CG样地分别降低了36%、26%、14%和47%倍。杂类草植物密度LG样地和HG样地间无显著差异,但均显著高于其他样地,其中,LG、HG、RG样地和CG样地较NG样地分别增加了0.38、0.34、0.29和0.16倍。总密度在LG和RG样地最高,均显著高于其他样地,但两者间无显著差异,NG样地次之,而CG样地最小,NG和HG样地较CG样地分别增加了0.26和0.16倍(图5-A)。不同功能群密度所占群落总密度,禾本科所占比例为NG样地显著高于其他样地,而在CG样地最低;莎草科和豆科植物所占比例均为CG样地显著高于其他样地,NG样地最低;杂类草植物所占比例在HG样地显著高于其他样地,然而NG样地最低。因此,冷季轻度放牧和划区轮牧增加了植物总密度;而全年禁牧显著增加了禾本科群落密度,但却降低了莎草科、豆科植物和杂类草密度及群落总密度;全年连续放牧增加了莎草科和豆科植物的群落密度,但却降低了禾本科植物密度和群落总密度。

图4 不同放牧模式下各功能群植物密度

图5 不同放牧模式下植物群落总密度和各功能群所占比例
2.5 植物生物量变化
不同放牧模式下各功能群植物地上、地下生物量及凋落物生物量差异明显(表2)。禾本科植物生物量在NG样地最高,较RG、LG、HG和CG样地分别显著增加了0.22、1.29、3.80和66.68倍;RG样地次之,接下来为LG和HG样地,CG样地最小。莎草科植物生物量在HG和LG样地间差异不显著,但二者均显著高于其他样地。豆科植物生物量在不同样地中呈RG>LG>HG>NG>CG,RG、LG、HG和NG样地较CG样地分别显著增加了11.24、8.4、5.62和2.30倍。杂类草植物生物量在HG和RG样地间差异不显著,但二者均显著高于其他样地,LG和NG样地次之,CG样地最小,LG和RG样地较CG样地分别增加了1.53和1.30倍。地上植物总生物量在RG和NG样地间差异不显著,但二者均显著高于其他样地,LG样地次之,CG样地最小,RG和NG样地较CG样地分别增加了5.72和3.90倍。根系总生物量在RG样地最高,NG样地次之,接下来为LG样地,而CG样地最小,RG、NG、LG和HG样地较CG样地分别显著增加了7.08、6.25、4.87和3.60倍。凋落物生物量在NG样地中最高,较CG、HG、LG和RG样地分别显著增加了66.85、10.13、6.36和2.62倍,RG样地次之,CG样地中最小。

表2 不同放牧模式下植被生物量
2.6 植物多样性变化
Shannon-wiener多样性指数和Simpson指数呈现出相同的变化趋势,均在LG和RG样地最高,但两者间差异不显著,且二者显著高于其他样地,在CG样地最低(图6)。Pielou均匀度指数在RG样地中最高,显著高于其他样地,在CG样地中最低。丰富度指数在RG样地最高,LG次之,接下来为HG和NG样地,CG样地最低,RG、LG、HG和NG样地较CG样地分别显著增加了2.7、2.0、1.4和1.0倍。说明划区轮牧样地物种多样性处于最优状态。

图6 不同放牧模式下植物群落多样性变化
2.7 地上生物量与植物多样性间的关系
线性回归结果表明,植被Shannon-Wiener多样性指数、Pielou均匀度指数、丰富度指数和辛普森指数均与植被地上生物量、草层平均高度、植被总盖度、植物总密度和凋落物生物量呈显著负相关关系(除植物总密度与Shannon-Wiener多样性指数,植物总密度与辛普森指数外)(图7)。因此,可以认为高寒草甸地上生物量、总盖度和凋落物生物量超过一定的范围时,不利于生物多样性的维持。

图7 多样性与植被特征间的关系
3 讨论
生物量是反映群落结构特征和生长状况的主要指标[25]。放牧通过家畜的采食降低植物的高度、盖度,最终影响生物量[26]。本研究中,植被地上、地下生物量和凋落物生物量均在划区轮牧样地和全年禁牧样地最高。禁牧因移除动物采食、践踏等因素,植被在无外界干扰下生长,其盖度以及地上生物量均会显著增加,进而增加凋落物生物量[27]。划区轮牧样地减少了家畜过度采食和践踏,牧草会因受到适度干扰而出现补偿生长,其盖度和地上生物量会增加,进而增加凋落物生物量[28]。经过放牧干扰,植被的组成特征会发生改变,但由于物种生活型、生活史对策以及生态位的改变,形成了不同放牧模式下各功能群不同的生态适应对策[29]。全年禁牧样地和划区轮牧样地较其他样地提高了禾本科植物、杂类草的生物量,却降低了莎草科植物的生物量。一般而言,草地生态系统的稳定性也受植被地下生物量的影响[30],植物的根系在贮存营养物质、调节植物生长发育等方面起着一定的作用[31]。根系生物量在划区轮牧样地最高,全年禁牧样地次之,接下来为冷季轻度放牧和冷季重度放牧样地,而全年连续放牧样地最小,可能是因为植被为适应不同放牧压力而将地上生物量向地下转移,将能量储存在根系中。
不同放牧模式对植被群落特征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物种的组成以及多样性演替等方面[32]。物种多样性可以反映草地生态系统的持续性和稳定性[33]。因草地植被在营养价值、适口性和消化率等方面不同导致放牧家畜采食具有一定的选择性,放牧通过影响物种的侵入或迁出以及群落组成的变化进而改变植物种间竞争的格局[34]。有研究表明放牧会因家畜的选择性采食导致植物群落物物种向单一化方向发展,多样性降低[35],本研究中全年连续放牧样地物种数较冷季重度放牧样地、冷季轻度放牧样地和全年轮牧分别减少了2种、6种和14种,多样性指数分别降低了13.3%、21.5%和21.1%,这符合李佳琪等[36]得出的“去除物种是为了适应外界干扰”的生态结论。植被的耐牧性机制和避牧性机制指出,植被为适应放牧干扰会出现莲座状、丛生、匍匐等形态,甚至有毒有害植物竞争为优势种[37]。这就解释了为何全年连续放牧样地醉马草为优势种。划区轮牧样地因减少了牲畜的选择性采食机会,植被及时得到恢复和调整,维持稳定的种类组成[38],因此总物种数最高,为27种,多样性也最高。这也符合中度干扰假说理论,中等程度的干扰水平能维持较高的物种多样性[39]。全年禁牧样地因移除了家畜的采食以及践踏等因素的影响,植物对资源的竞争能力增强,直立、高大型的植被比低矮牧草在获取光资源方面更占优势,垂穗披碱草等生长加快(重要值急剧升高为0.96),而阔叶杂类草从群落中消失,从而导致群落结构单一化,物种数降低(7种),多样性也降低[14]。此外,禁牧后多样性的降低很可能是由于其植物地上生物量、植被总盖度和凋落物生物量的急剧增加引起的。从草地植物多样性维持的角度来看,适时、适当地放牧能够有效提高高寒草甸的植被多样性。
4 结论
高寒草甸生态系统经过不同模式放牧后,植物群落的盖度、密度、地上生物量、地下生物量、Shannon-Wiener多样性指数、Pielou均匀度指数、丰富度指数和辛普森指数均在全年划区轮牧样地最高,而在全年连续放牧样地最低。此外,全年禁牧样地显著提高了禾本科植物密度,而降低了莎草科和豆科植物、杂类草密度,降低了植物群落的物种数和多样性,和全年划区轮牧相比,禁牧样地总物种数减少了20种。因此,为期5年禁牧使群落结构单一化,不利于植物多样性的维持。从提高生产力和植物多样性的角度来看,全年划区轮牧是高寒草甸生态系统的最佳放牧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