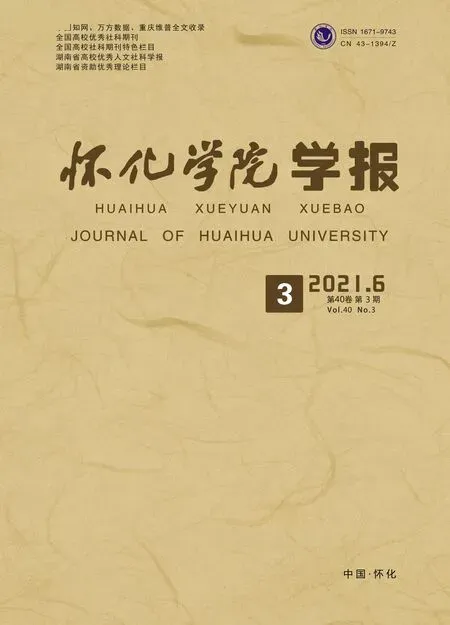乡村振兴背景下民族地区语言使用现状及困境探究
——基于贵州省从江县党郎村的语言调查
徐 林, 黄 雨
(凯里学院,贵州凯里556011)
2011 年《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明确提出“在民族地区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1]。这成为近年来在少数民族地区以及其他贫困地区施行推普工作的主要政策依据。然而,目前少数民族地区语言使用情况如何,推广普通话还存在哪些困境,值得进一步探究。
在扶贫工作过程中,语言的经济价值逐渐凸显。学界从理论层面进行了探讨。李宇明[2]认为,语言可以扶贫,认识语言的扶贫功能将为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筑起脱贫的语言大道,能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和文明进步。王春辉[3]认为,语言与贫困问题研究主要涉及语言与贫困的相互影响以及语言能力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陈丽湘[4]指出,国家语言政策与扶贫减贫战略在政策理念、帮扶对象以及发展目标上高度契合,有效提升了贫困群体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为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构筑起了坚实的语言沟通桥梁。中国语言扶贫的实践经验对于消除绝对贫困后建立缓解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苏剑[5]阐述了语言扶贫的理论逻辑、经验支持,并提出研究民族地区群众国家通用语言习得的影响因素、开发民族语言资源以及市场化服务等语言扶贫的实现路径。以上研究从理论层面证实了语言的经济属性以及通过语言实践助推中国脱贫减贫事业的可能性路径。杜敏、刘志刚[6]指出,在乡村振兴背景下,语言扶贫的可持续发展需不断拓展其内涵,才能真正实现乡村的人才振兴、文化振兴和产业振兴。《国家语言文字事业“十三五”发展规划》提出:“以提升教师、基层干部和青壮年农牧民语言文字应用能力为重点,加快提高民族地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率。加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教学,确保少数民族学生基本掌握和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7]由此可以看出,语言扶贫工作是国家精准扶贫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能有效帮助贫困人口提高基本素质、交往能力以及获取知识和信息的能力。
2020 年底,全国832 个贫困县全部脱贫摘帽,标志着我国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已经完成,确保从脱贫攻坚平稳过渡到乡村振兴。习近平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指出,要切实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各项工作[8]。作为扶贫阶段的产物,“语言扶贫”已圆满地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任务。在现阶段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过程中,要从以提升国家通用语言能力为目的的“语言扶贫”转向开发语言资源,以语言为工具,促进当地语言文化资源传承、提升语言服务能力,助力国家乡村振兴战略。
2020 年底以前,从江县是贵州省贫困发生率最高的县,也是全省脱贫攻坚的重点和难点。2020 年11 月23 日,贵州省政府新闻办召开发布会,宣布从江县等9 个国家挂牌督战的贫困县退出贫困县序列,下一阶段的工作重心转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苗族聚居的党郎村曾是从江县典型的少数民族贫困村,调查其语言使用现状,探索在当地推广国家通用语言的困境,具有区域典型性和代表性,也有助于了解其他少数民族地区的语言服务困境。基于对党郎村村民的语言使用现状进行的调查研究,本文拟结合乡村振兴战略的总体要求,针对语言使用存在的问题与困境,探讨民族地区通过语言服务推动乡村振兴工作的实践策略。
党郎村位于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从江县加鸠镇,截至2020 年5 月31 日,党郎村共有135 户469 人,其中男性252 人(53.73%),女性217 人(46.27%),全部为苗族。未脱贫42 户141人,占人口总数的30.06%,是从江县贫困发生率较高的乡村。笔者于2020 年6 月2—15 日对党郎村村民语言使用情况进行实地调研,内容主要为党郎村民族语言使用现状、党郎村国家通用语言使用现状以及党郎村村民的语言态度等。调查主要采用半结构式访谈、集体访谈和观察的方式进行。
一、党郎村语言使用现状
(一) 党郎村民族语言使用现状
党郎村位于黔东南州从江县,靠近黔南州荔波县,接近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地界。囿于历史上交通不便,与外界联系较少,党郎村村民使用的苗语与黔东地区苗语差异较大,是黔东苗语次方言中一种比较特殊的地方话,下文统称“党郎苗话”。作为单一民族的苗族聚居村,党郎村内部日常交流均使用党郎苗话,全体村民都会说流利的党郎苗话。村民对苗族文化有强烈的认同感,且苗族文化在党郎村保留较为完整。党郎苗话与同在从江县加鸠镇的加牙村、长牛村村民使用的苗话差别较大,基本无法相互沟通,与邻近的加勉乡部分村庄也不能沟通。
(二) 党郎村国家通用语言使用现状
以下分别对党郎村不同年龄段村民、不同性别村民国家通用语言使用情况进行调查。
1.不同年龄段村民国家通用语言使用情况
0—2 岁的婴幼儿群体语言能力尚不健全,3—6岁的学龄前儿童由于家庭影响存在被迫选择语言的情况,7 岁及以上的村民才有自主选择语言的能力。笔者调研期间,党郎村年纪最长的老人为86 岁。因此,本文将党郎村国家通用语言使用情况调查对象的年龄设定为7—86 岁,分为3 个年龄段,调查对象共422 名。
调查显示(详见表1),党郎村能流畅使用国家通用语言的人数为261 人,占人口总数的61.84%。党郎村7—18 岁年龄段共35 人,全部为在校学生,均能流畅使用国家通用语言;19—40 岁的青壮年群体133 人中能流畅使用国家通用语言的人数为123人,占该年龄段总人数的92.48%;41—86 岁中老年群体能流畅使用国家通用语言的人数为103 人,占该年龄段总人数的40.55%。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党郎村青壮年群体的国家通用语言使用状况明显优于中老年群体。根据调查得知,7—18 岁群体正在接受学校教育,19—40 岁群体是外出务工的主力军。由此可知,学校教育及对外交流是民族地区居民学习国家通用语言的重要渠道。受教育程度与国家通用语言使用水平呈正相关。

表1 党郎村不同年龄段村民国家通用语言使用情况
2.不同性别村民国家通用语言使用情况
不同性别村民的国家通用语言能力也不同。党郎村能流畅使用国家通用语言的村民有261 人,其中男性186 人,占比高达71.26%。
如表2 所示,党郎村7—86 岁村民共422 人。231 名男性中,能流畅使用国家通用语言的有186人,不能流畅使用国家通用语言的有45 人;191 名女性中,75 人能流畅使用国家通用语言,116 人不能流畅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根据访谈得知,现阶段青壮年劳动力在学龄期受教育层次低,当时学校的课堂教学语言多为苗语或从江方言,辍学后学习国家通用语言的主要途径是外出务工。而该村男性外出务工人数远超女性,女性首次务工一般选择跟随男性长辈或婚后随同丈夫一起外出,基本没有女性单独外出或集体外出务工的情况,因而接触国家通用语言的机会和渠道较男性少。

表2 党郎村不同性别村民国家通用语言使用情况
(三) 党郎村村民的语言态度
劳动力转移就业是党郎村村民增加家庭收入的主要渠道,但外出务工青壮年的普通话水平参差不齐。调查显示,语言态度对村民的语言水平、思维方式以及家庭经济状况都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相较于留守村民,党郎村的外出务工村民更加认同普通话的价值及其与家庭经济收入的关联。下文即以党郎村A、B、C 三个家庭为例,说明不同语言态度对其家庭的影响。
1.家庭A 案例调查分析
党郎村村民X,女,苗族,现年52 岁,婚后随丈夫到广东某市打工,帮助一位老板照料荔枝园。平时X 的丈夫用简单的普通话和老板沟通。X 与外界人员基本没有任何交流,和丈夫的沟通全部用党郎苗话进行。在广东工作期间,X 曾尝试独立务工,但因语言障碍放弃。外出打工5 年后返乡(期间未回家)。X 能够听懂部分普通话,但对使用普通话产生抵触情绪,至今未成功习得普通话。其丈夫对调查者说:“她当时(在广东) 不敢出门,因为不懂普通话嘛!一个人也不敢去菜场买菜啊什么的。有事的时候,我和老板两个人说(沟通),她和我一起做活路(干活) 就好了。……现在回家她就很舒服,大家都说苗话啊!……现在我一个人出去打工,她就在家了。……对收入有影响。”
该家庭的外出务工劳动力从2 人减少到1 人,家庭经济收入受到直接影响。
2.家庭B 案例调查分析
党郎村村民Y,男,苗族,现年48 岁。通过访谈得知,Y 小学肄业(文化程度为小学三年级),因老师上课不说普通话,在校期间未学习过普通话。后经人介绍与亲戚前往广西某工厂务工,务工初期因语言能力不足且文化程度低,务工内容多为体力活,工作艰苦、收入低,之后逐渐习得普通话,目前交流无碍。因此,Y 对子女的教育非常重视,希望创造良好的环境,让自己的孩子好好学习。问及子女学习普通话的渠道,Y 说,“现在条件好了,学校里都说普通话,回家看电视、看手机也能学习普通话。平时在家,我也会和他们用普通话聊天。……你们(调研团队) 来了,他们也可以学习普通话。……希望我的孩子以后能上大学,有稳定的工作。”
该案例中,Y 对下一代的语言教育非常重视,能够有意识地影响家庭成员进行语言学习,对家庭成员的语言管理更加明确。
3.家庭C 案例调查分析
党郎村村民Z,女,苗族,现年49 岁,曾和丈夫、亲戚、邻居一起到浙江务工多年。因工作沟通需要,Z 在务工过程中逐渐学会了普通话。逢年过节回家会积极督促子女学习普通话。Z 说:“刚到浙江时,老板安排活路(工作),有的时候听不懂,我就问老公、问朋友。一两年后,听懂(普通话) 我就知道怎么做,工资就多啦!……我懂(的) 比以前多了,感觉很好呀!可以去买东西,逛街!”“我看电视,也和其他外地人聊天。”“会说普通话,我就能帮寨子里的亲戚、邻居们。……也教他们。”
该案例显示出Z 有较强的语言意识,也会主动进行自我语言实践,充分认识到会说普通话的语言优势:能直接帮助其提高经济收入。Z 还初步影响身边的同伴、家庭成员的语言实践。目前Z 已回乡创业,成为党郎村的致富带头人。
从上述个案可以看出:1.案例中非学龄段村民的语言意识基本产生于外出务工过程中,这部分村民普遍认为普通话重要,对提高经济收入有较大帮助。但大部分留守村民对此没有意识。2.外出务工人员的语言能力个体差异明显,积极的语言实践者能更快掌握普通话,会对家庭成员和亲友产生带动作用。3.个别家庭成员能够主动对家庭内部其他成员的语言使用和学习进行干涉。
综上所述,党郎村的语言使用现状具有以下特点:第一,党郎村村民对本民族的语言文化认同度很高。第二,党郎村村民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学校教育对普及国家通用语言的作用非常明显。第三,本民族语言的交际功能在该地区已受到局限,对当地村民发展经济、提高生产生活水平产生诸多不利影响。
二、党郎村村民语言使用现状存在的困境
基于党郎村村民的语言使用现状,笔者认为,党郎村村民的语言使用目前主要存在以下四个方面的困境:
(一) 本民族语言传承保护较好,但使用范围小
作为地方优势语,苗语是党郎村村民的主要交际用语。党郎村村民所使用的党郎苗话没有可以书写的文字。因此,该村村民无法有意识地、主动地使用文字记录的方式保护当地的语言和文化。党郎苗话与周边村寨苗话之间的差异较大,其适用范围狭小。究其原因,党郎村位于月亮山腹地,与周边村寨距离较远,交通不便,这在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内严重限制了该地区村寨之间的交流与互鉴。该地理劣势给当前的乡村振兴工作也带来较大挑战。
(二) 国家通用语言使用能力较弱,限制当地经济发展
党郎村村民的国家通用语言能力远低于本民族语言能力。青壮年群体是家庭经济收入的主要依靠,但部分青壮年群体由于不会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无法与外界有效交流,外出务工的积极性受到严重打击。调查显示,截至2020 年5 月31 日,党郎村外出务工人员为136 人,74%选择到从江县内务工,22%到省外务工,4%在县外省内务工,大多从事建筑行业、加工制造业以及种养殖业等。因学历低、普通话水平低等原因,党郎村村民出省打工找不到合适的工作,赚钱较难。外出务工人员会说普通话、基本识字就可以进工厂工作,而其他人只能选择不需要特殊技能和太多语言交流的工种。国家通用语言能力较弱成为当地村民发展经济、实现生活富裕及产业兴旺的工具性阻碍,生活富裕、产业兴旺的目标实现受到很大限制。
(三) 信息传递能力弱,民族文化的价值转化不充分
强烈的民族认同感有利于传承和发扬民族文化,但受制于较为单一的语言工具和环境,党郎村村民对外交流、互动和传递信息的能力弱,使民族文化的价值转化受到了限制。在推进文化产业发展的进程中,一方面,长期处于单一语言环境的党郎村村民对主流经济、社会活动的认知和理解有限,对语言资源、语言文化的价值认识不足。村民们表示:不觉得大家习以为常的传统风俗习惯、交流互动方式等是一种独特的文化,更谈不上将其上升到产业发展的角度。民族文化向文化产业转化发展的可能性极大受限。另一方面,受限于村民对外传递信息的能力和使用国家通用语言交流的能力,民族文化直接转化为经济价值缺少了必要的媒介。语言因素导致的信息传递能力弱使其对党郎村乡风文明建设的价值体现未发挥出应有之义。
(四) 家庭语言规划意识淡薄,乡村振兴人力资本培育意识不足
区别于宏观层面的国家语言政策,家庭语言政策是从家庭层面研究语言使用的重要领域。King K.A.等[9]认为,家庭语言规划能够为家庭成员的语言观念、语言选择、语言实践等方面提供理论依据。在党郎村的调研中发现,当地村民对家庭语言教育这一概念比较陌生,对其多呈现出顺其自然的态度,认为语言教育是学校的责任,与家庭教育关系不大。长期以来,社会因素如语言理念、语言态度等对党郎村村民的影响甚微,党郎村村民在家庭语言教育方面的意识不足,尚未充分认识到语言因素对提升自我、改善经济条件和培育人力资本的作用。
三、语言服务助推民族地区实现乡村振兴的策略
2005 年,李宇明[10]首次提出“语言服务”这一学术概念,在学界引起了较大反响,同时也推动了我国语言服务的实践活动。广义的语言服务有专业语言服务和行业语言服务之分,专业语言服务是提供语言产品的服务,包括语言翻译、语言培训、语言技术、语言支持等方面的服务;行业语言服务主要是依附在各个行业领域的以语言作为工具、手段的语言服务[11]。脱贫攻坚时期以提高国家通用语言能力为目标的“语言扶贫”已初见成效。脱贫后的广大乡村地区,既面临着为进一步提高生产生活水平而继续学习国家通用语言的现实需求,又面临着保护传承民族文化的历史重任。单纯的学习或培训式“语言扶贫”已经不能满足乡村发展的需要,以技术为支撑的专业语言服务和以语言为工具的行业语言服务恰好契合现阶段乡村振兴工作的需求。所以从“语言扶贫”转向“语言服务”,通过语言服务支持乡村振兴是新时代的需求。
基于党郎村村民的语言使用现状与困境,笔者总结并提出以下三条可以在民族地区广泛应用的语言服务策略,以此助推广大少数民族地区实现乡村振兴。
(一) 以产业振兴为导向,开发民族语言文化资源产业
乡村振兴的关键是产业振兴。发展民族语言资源产业是通过语言服务促进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第一,大力挖掘民族地区历史语言文化资源,发展旅游和艺术文化产业。将本民族的语言文字与旅游、美术、音乐、影视创作等领域相结合,既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差异化精神需求,又能提高当地村民的经济收入。第二,在进一步强化普通话培训的基础上,帮助民族地区村民通过抖音、快手、微视等短视频平台,把本民族的语言资源和文化资源推向公共视野空间,引入市场运作机制,建立更有效、更长效的民族文化传承与保护机制。
(二) 以人才振兴为导向,提升语言应用与服务能力
在乡村振兴过程中,要以人才振兴为导向,切实提高当地村民的语言应用能力与语言服务能力。第一,进一步加强对基层单位工作人员的普通话水平培训,提升基层组织的语言服务能力。第二,下沉语言服务培训工作,将普通话水平培训工作下沉到村级单位,以普通话二级乙等水平为目标,分批次选拔中青年村民骨干进行普通话专项培训,将推普工作纳入民族地区的乡村振兴工作。第三,加强中小学学校教育,通过提高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素养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第四,强化民族地区的家庭语言规划意识,家庭、学校、政府三级联动,共同培养熟练掌握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双语人才,为乡村振兴有意识地培育语言服务人才。
(三) 以文化振兴为导向,加强民族文化传承服务
语言是文化的重要载体,2017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指出,要“大力推广和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保护传承方言文化”[12]。少数民族文化振兴,不仅要使用规范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还要积极保护和传承本民族语言文字。一方面,深入挖掘本民族语言的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提高对本民族语言资源、语言文化的价值认识,积极探索本民族文化价值转化。另一方面,在民族地区推广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帮助拓宽民族地区群众的表达渠道,着力提升信息传递能力,加强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和经典文献的保护和传播,推动民族地区的乡风文明建设。
乡村振兴是新时代的重大国家战略。与之相配合,语言服务能够促进民族地区产业振兴、文化振兴,有助于培养人才,保证民族地区在推广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同时,保留和传承本民族语言,并将本民族语言中阻碍经济发展的不利因素转化为具有民族特色、振兴民族地区经济的有效资源。因此,科学、合理、有效的语言服务是助推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重要实现路径,值得语言工作者和政策制定者进一步探索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