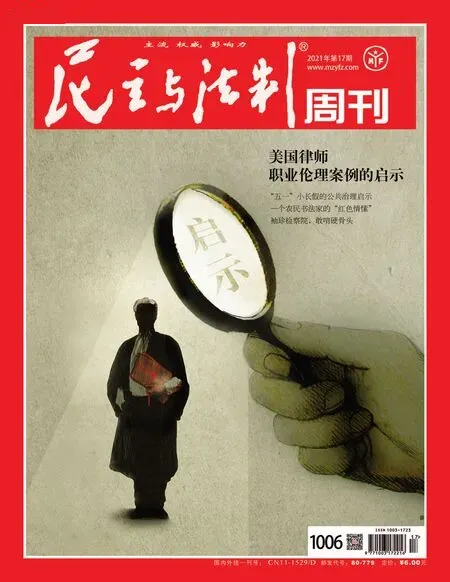尼克斯案:你会配合被告人在庭审中作伪证吗?
刘萍
在得知客户准备向法庭说谎时,律师如何做出反应?
这是律师面临的最艰难的道德困境。一方面,根据律师职业伦理规范,律师不得提出明知为虚假的证词;另一方面,客户在向法庭陈述事实时需要律师的协助,而在刑事案件中,律师的协助是被告人应得的宪法权利。
尼克斯诉怀特塞德案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首次考虑律师在被告人意图作伪证时所面临的两难处境,大法官们在判决中详细回答了这个问题,即当律师拒绝配合被告人在审判中提供伪证时,是否侵犯了他根据宪法第六修正案获得律师协助的权利。
一起因毒品引发的谋杀案
1977年2月8日,爱荷华州锡达拉皮兹市发生一起谋杀案,伊曼纽尔·怀特塞德被判二级谋杀罪。那天深夜,怀特塞德和另外两个人去了死者加尔文·洛夫的公寓,打算拿回属于他们的大麻。怀特塞德和同伴们到达时,洛夫已经躺在床上了,他们因大麻的事发生了争吵,洛夫开始对怀特塞德等人进行威胁,让自己的女友去拿枪,他伸手去摸床上的枕头,然后朝怀特塞德走去。就在那时,怀特塞德用刀捅死了洛夫。
怀特塞德声称自己是出于自卫。洛夫有暴力、好斗的名声,持有枪支,有犯罪前科。怀特塞德曾与洛夫一起在监狱服刑,他认为洛夫是个危险人物。怀特塞德在审判中坚称,他刺伤洛夫的时候是出于对自己生命安危的恐惧。
在陪审团评议的过程中,法官问怀特塞德如何评价自己的律师罗宾逊先生,他回答说对律师的代理感到满意。尽管爱荷华州对怀特塞德提起一级谋杀的指控,但陪审团选择判处了二级谋杀,初审法官判他40年刑期。
随后,怀特塞德聘请了新律师要求对他的案件重审,其中一个理由是他没有得到律师的有效协助。
被告人怀特塞德的伪证计划
在重审动议的听证会上,怀特塞德作证说,他曾给过罗宾逊律师一份书面陈述,包含着这样的意思:洛夫伸手从枕头底下掏出一把手枪,就在那时,我杀死了他。他一直希望律师能找到那把手枪,以便在审判时能够向法庭提交。然而,枪并没有被找到。在审判前夕与律师的会面中,怀特塞德透露了自己的作证计划,他准备在法庭上说他看到了洛夫手中的枪,出于自卫,他杀死了洛夫。虽然怀特塞德不记得律师具体怎样回应,但他有一种感觉,如果他作证说看到洛夫手中有枪,律师就会退出代理。正是由于这种印象,他决定不在法庭上说自己看到了枪。这使得他的正当防卫辩护未能成功,因而被定罪。
罗宾逊律师提供了一个明显不同的故事版本。在罗宾逊之前,法庭为怀特塞德指派的是另外一名律师,由于这位律师曾担任过检察官,怀特塞德觉得无法信任他,于是拒绝了。法庭随后指定罗宾逊作为怀特塞德的辩护律师。

>>视觉中国供图
罗宾逊承认怀特塞德在陈述中说他看到了洛夫手中的枪。经过进一步询问,怀特塞德表示,他实际上并没有看到过枪,但他确信洛夫有枪。罗宾逊前往案发现场洛夫的公寓搜寻了30~45分钟,但没有找到手枪。他询问了在现场的三位证人,他们都说,洛夫在被杀之前手中没有拿枪,在案件发生过程中,他们也没有看到房间里有枪。罗宾逊又询问了案发后15分钟内赶到现场的警察,警察也没有发现屋内有枪。根据这些调查,罗宾逊认为洛夫在被杀之前手里没有拿枪,他从与怀特塞德的23次会面交谈中加固了这一印象。从他接受法庭指派起的69天内,怀特塞德都没有提到他将在法庭上作证说看到了枪,而在审前10天的会谈中,他突然提出了这一点。他说,当时他在洛夫的手中看到了一个貌似金属质地的东西。律师问及他为何改变证词,他说,有一个熟人的类似案子就是因为咬定对方手里有枪而获得了成功,如果我不说我看见了枪,就死定了。
律师警告要揭发他的当事人
罗宾逊告诉怀特塞德,这样的证词是伪证,并反复强调,枪的实际存在并不是证明自卫的必要条件,只要合理地相信受害者附近的地方有枪,从而有理由相信自己处于危险之中就可以。怀特塞德坚持要作证,说他看到了“金属样的东西”。
罗宾逊说,我们不能允许他这么讲,因为那就是作伪证。作为法庭官员,如果我们允许他这样做,那就是协助他作伪证。如果他坚持这么做,作为律师我们将退出代理;如果他在法庭上真的这样做了,我们有责任向法庭披露伪证的事实,而且,我可能会被允许弹劾怀特塞德的证词。在律师的警告之下,怀特塞德作出让步。
庭审中,罗宾逊问怀特塞德,当他刺伤洛夫时,他是否认为洛夫有枪,他说是的。但罗宾逊没有问怀特塞德,他是否“看到”洛夫的手里有枪或任何东西。在交叉盘问中,怀特塞德被检察官问及在刺杀时是否看到过枪,他回答说没有。
罗宾逊出示了证据,证明有人曾在其他场合看到洛夫拿着一把短猎枪,警方对公寓的搜查可能是粗心大意,受害者的家人在案发后不久就从公寓搬走了所有的东西。罗宾逊提出了这个证据来证明怀特塞德声称的“洛夫有枪”的恐惧是有根据的。
律师拒绝配合被告人作伪证是否违宪引发争议
在怀特塞德被定罪后要求复审,他声称律师警告他不要说他看到了枪或“金属的东西”,否则退出代理,这限制了他通过自己的意愿作证的宪法权利,也剥夺了他获得律师有效协助的宪法权利。
初审法院认为并不存在无效的律师协助。爱荷华州最高法院审查了审判记录和无效审判动议的听证会,认为程序没有错误,也没有剥夺怀特塞德宪法权利的情形。州最高法院的裁决赞扬了罗宾逊律师“以高尚的符合职业道德的方式处理此事”。
三年后,怀特塞德以律师协助无效为由,向联邦地区法院申请人身保护令的救济。地方法院在一份简短的意见书中指出,被告人无权就其伪证行为获得律师的协助,因此驳回了其申请。怀特塞德继续向联邦第八巡回上诉法院提出上诉。
联邦第八巡回上诉法院推翻了联邦地区法院的裁决。上诉法院称赞罗宾逊按照法律职业道德行事,然而,上诉法院同时认为,法律职业伦理规则并不优于美国宪法的规定。根据上诉法院的裁决,怀特塞德的两项宪法权利被罗宾逊的行为所限制:第一项权利是在面临刑事指控时获得律师有效协助的权利;第二是在正当程序条款中隐含的按自己的意愿作证的权利,尽管其证词可能是不真实的。
因此,第八巡回上诉法院撤销原判,授予怀特塞德人身保护令,爱荷华州向联邦最高法院申请调卷复审此案。

>>尼克斯诉怀特塞德案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首次考虑律师在被告意图做伪证时所面临的两难处境,大法官们在判决中详细回答了这个问题,即当律师拒绝配合被告在审判中提供伪证时,是否侵犯了他根据宪法第六修正案获得律师协助的权利。 资料图
律师作为“法庭官员”的角色重于他辩护人的责任
联邦最高法院决定批准调阅此案以解决这样一个饱含争议的问题:当律师拒绝配合被告人在审判中提供伪证时,是否侵犯了第六修正案规定的刑事被告人获得律师协助的权利。九位大法官一致认为第八巡回上诉法院的判决是错误的,但进一步区分为两种意见:首席大法官伯格等五位发表了多数派意见,布莱克门等四位大法官发表了附和意见。
多数意见对刑事辩护律师的角色界定采取了明确的立场,即认为律师作为“法庭官员”的角色重于他身为辩护人的责任。这与第八巡回上诉法院的观点显著不同。上诉法院的观点显然相反,认为如果被告人坚持作伪证,律师必须至少被动地配合,而不是阻止,理由是被告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为自己辩护。最高法院对此正本清源,认为律师是“司法正义的组成部分,应当致力于寻求真相”,律师的辩护责任仅限于通过合法的方式进行,唯如此方可与其探求真相的本质相吻合。
多数意见就以下三个与本案有关的宪法问题做了回应,大多数内容被附和意见所接受。
首先,怀特塞德获得律师有效协助的宪法权利是否被侵害?律师劝阻怀特塞德按照对自己有利的方式作证,是否与其作为辩护律师的角色冲突?根据斯特里克兰案(Strickland v.Washington)确立的“无效律师协助”检验标准,须具备两个条件:律师代理行为存在缺陷,以及律师的代理缺陷给被告人带来损害。由于怀特塞德在提供伪证方面没有合法利益,不能将他的不合法期待未能实现视为受到损害,因此不符合斯特里克兰的“损害”标准。持附和意见的法官们提出了判定不存在损害的另一个理由:在他们看来,阻止怀特塞德作伪证是保护其最大利益的合理步骤,因为伪证其实难以成立,而且可能会被揭穿。这可能会导致陪审团认定他犯有更严重的一级谋杀罪,法官也会因为伪证提高他的刑期。因此,律师阻止被告人作伪证的行为并未给其造成损害。而怀特塞德主张的律师角色的冲突,不过是自己的伪证导致的,并不是法律意义上的利益冲突。
其次,被告人有按照自己的意愿作证的宪法权利,但不包括作伪证的权利。无论宪法规定的作证权的范围有多大,最基本的是这种权利不应延伸到虚假作证。被告人在合理的范围内继续享有律师的代理服务,并实际上行使了作证的权利;他最多被剥夺了获得律师协助提供伪证的权利。同样,在罗宾逊律师对被告人的警告中,我们也不能看出他违反了职业责任,即他将向法院披露被告人的伪证罪。
第三,第六修正案中被告人获得律师有效协助的权利是否包括在作伪证时获得律师协助的权利?答案是否定的。多数意见对这一点进行了详细阐述,比如被告人向律师透露,他正在想办法贿赂、威胁证人或陪审团成员,被告人将没有权利要求律师就此提供帮助或保持沉默。因此,怀特塞德无权要求律师帮助他作伪证。
虽然多数意见让我们对最高法院在律师职业伦理相关问题上的想法有了一定了解,但这恰恰是附和意见与多数意见的主要分歧之所在。布伦南、布莱克门、马歇尔和史蒂文斯等四位大法官在赞同多数意见裁决结果的同时提出,本案中唯一的联邦问题是:罗宾逊律师的行为是否剥夺了怀特塞德获得律师有效协助的宪法权利;问题并不在于罗宾逊律师的行为是否符合任何特定的法律职业伦理准则。
布伦南大法官认为,宪法没有赋予最高法院为在州法院执业的律师制定道德伦理规则的权力,法院在法律伦理方面也不享有任何法定管辖权。因此,最高法院必须谨慎行事,不能轻易宣布根据美国律师协会的准则来判断律师行为是否适合,即不要将宪法第六修正案所接受的律师行为范围缩小,以至于将律师行业的专业行为标准宪法化,从而侵犯各州制定和适用律师职业行为准则的权力。换言之,除非联邦权利受到侵犯,否则最高法院不能告诉各州或各州的律师在法庭上应该如何行事。不幸的是,法院似乎无法抗拒与法律界分享其对道德行为的看法的诱惑。布莱克门大法官遗憾地表示,这个问题很棘手,但它不是本案所呈现的问题,最高法院无权回答。最高法院关于律师对被告人将作伪证的意图应如何回应的言论,是没有法律效力的。
布莱克门大法官提出,长期以来,律师应如何回应有意作伪证的被告人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但他不认为通过联邦人身保护令挑战州法院的定罪判决是解决这一棘手问题的适当手段。当被告人争辩说,由于律师劝阻他不要作伪证,所以他没有得到律师的有效协助时,向最高法院适当提出的唯一问题是,律师的行为是否剥夺了被告人得到律师有效协助的第六修正案权利。
如同布伦南大法官一样,布莱克门大法官对使用律师职业行为准则来衡量律师在各州刑事诉讼程序中的表现这一做法表示不安。认为应由各州来决定律师在本州刑事诉讼中应如何表现,而最高法院的责任仅延伸到确保各州颁布的限制不会侵犯被告人的宪法权利。因此,布莱克门大法官赞同37个州提交的“法庭之友”建议,即应允许各州对复杂的律师职业道德问题保持其不同的做法。而在调查律师的表现是否适当之前,首先应询问被告人是否因律师的行为受有任何不利的影响,这样可以避免联邦对州法律的不必要干涉。鉴于认为本案被告人并未受到任何伤害,因此无权获得联邦人身保护令的救济,布莱克门大法官表示同意多数法官的判决。
最高法院对律师职业伦理问题没有管辖权
尼克斯案还涉及刑辩律师-客户关系上的四个程序问题:第一,律师何时“知道”被告人打算作伪证,从而有义务阻止其伪证行为;第二,当律师知道被告人打算作伪证时,应该采用何种方式进行劝阻;第三,如果律师不能劝阻被告人作伪证,他也不能退出代理,这时律师该怎么办;第四,当被告人确实在法庭上作了伪证时,律师应该怎么办。在这些程序问题上,多数意见和附和意见也保持了大体的一致。
第一个程序问题,如何判断律师何时“知道”被告人打算作伪证,最高法院没有向律师协会提供一般性的指导规则。大多数情况下,律师所面对的事实比在尼克斯案中的情形更加模棱两可。在一个案件中,证人之间的证词有出入是很正常的,律师常常分辨不出他们中谁说的是真话。美国律师协会颁布的《职业行为示范规则》(简称“示范规则”)并不要求律师只提供他们认为真实的证据,律师可以提供他不确定真假的证据。如果律师合理地认为证据是虚假的,但并未达到确定“知道”的程度,应做有利于被告人的决定,即不禁止律师将证据提交给法庭。所以律师可以提供他不确定的证据,但如果律师确定地“知道”证据是假的,则不应提交。而律师是否“知道”证据为虚假,需要结合多种情况进行判断。
关于第二个程序问题,首先肯定,当被告人通知律师他要作伪证的意图时,律师的首要职责是尽力劝阻。在尼克斯案中,最高法院对罗宾逊律师向被告人发出警告的做法表示认可,律师可以使用警告的方式来劝阻被告人的伪证,甚至包括采用比较激烈的方式对被告人进行威胁,声称如果被告人真的作伪证,他将会向法庭如实报告,或在证人席上对其进行弹劾。律师以这些方式来劝阻被告人作伪证,都不会被认为侵犯了客户的第六修正案权利。
第三个程序问题,如果律师的警告或威胁不能说服被告人放弃作伪证的意图,则律师可以退出代理,而且在退出代理后,可以通过亲自出庭作证的方式对被告人的证词进行弹劾。
在最后一个程序问题上,根据“示范规则”第3.3条规定,如果被告人已经向法庭提供了重要的证言,律师随后发现是虚假的,则该律师应当采取合理的补救措施。律师首要的适当行为是秘密规劝被告人,解释律师对法庭有坦诚的义务,就退出代理或者纠正虚假证言获得被告人的理解与合作。如果被告人能主动配合采取补救措施,则可避免律师的披露伪证造成对客户秘密的泄露。如果规劝工作无效,律师必须采取进一步的补救措施。如果退出代理没有被允许,或者不能抵消被告人虚假证言的效果,律师必须就伪证向法庭进行必要的披露。
刑事案件中的被告人面临被定罪的严酷威胁,自然会不顾一切地寻求对自己最有利的证据,包括向法庭提供篡改重要事实的证言。刑事辩护律师兼为被告人的诉辩者和法庭的官员,同时负有忠于被告人和法庭的职责,这是极其艰难的职业伦理困境,它发生在每一个律师身上,发生在每一起刑事案件中。
尼克斯案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第一次正面回应律师的这一困境,并且提供了较为明确的答复。然而,这一没有反对意见的判决却蕴含着一个巨大的争议,即布莱克门等附和意见者所主张的:最高法院对律师职业伦理问题没有管辖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