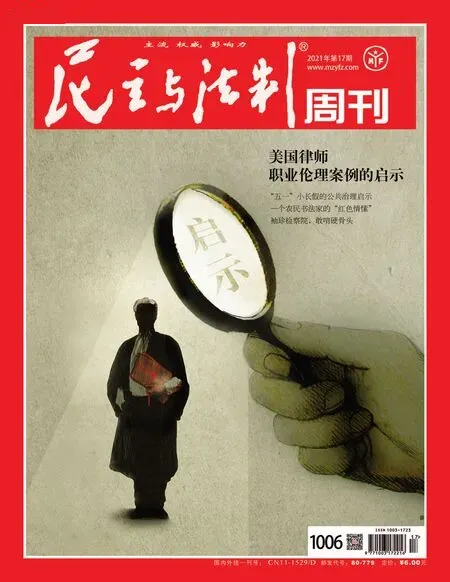斯伯丁案:你会向当事人披露不利信息吗?
刘萍
当律师职业伦理同公众的普世道德观念发生冲突时,如何取舍?
斯伯丁诉齐默尔曼一案是研究美国律师职业伦理的经典案例,它几乎出现在每一本关于法律职业伦理的教科书中,在美国的所有法学院中都被使用。它将拯救人类生命的价值与律师职业伦理“对立”起来,以探讨当律师全力为客户利益进行代理时可能出现的普世道德观念和职业伦理上的紧张关系。
律师隐瞒病情,交通事故双方达成和解协议
1956年8月24日,在明尼苏达州的布兰登市,20岁的大卫·斯伯丁(David Spaulding)遭遇了一场严重的交通事故,当时他正搭乘约翰·齐默尔曼(John Zimmerman)的车回家。19岁的约翰驾驶的汽车与15岁的弗洛里安·莱德曼(Florian Ledermann)驾驶的另一辆汽车相撞,大卫伤势十分严重:脑震荡、锁骨骨折、胸部被压碎。当时美国大多数州成年的法定年龄是21岁,明尼苏达州也不例外,因此,大卫在法律上是未成年人,两位司机同样也是未成年人。于是,大卫的父亲替他起诉了两位司机和他们的父母,即齐默尔曼和莱德曼两家人。
事故发生后,大卫的家庭医生和另外两名医学专家——一名骨科专家和一名神经学专家——分别对大卫进行了检查。大卫的医生们均认为,除了头部和胸部严重受伤之外,他的心脏和主动脉看起来正常。但神经学专家布雷克医生推断大卫可能有永久性的脑损伤。他建议斯伯丁夫妇至少在一年内不要解决这个案子,因为损害可能还没有显现出来。
根据法律和合同的规定,被告的汽车保险公司为其聘请了律师,在审前准备程序中,保险公司也派出了自己的医学专家——神经科专家汉纳医生对大卫进行了检查。汉纳医生在大卫的心脏主动脉上发现了一个主动脉瘤,它可能会随时破裂从而导致大卫的死亡。由于缺少事故前的X光片,汉纳医生无法确定动脉瘤是否由事故造成,但后来的检查表明,这是大卫在事故中受到的严重损伤之一(如果动脉瘤被发现,保险公司将面临更大的责任)。
汉纳医生向被告的律师之一报告了大卫的体检结果,然而该律师既未将动脉瘤的信息告知大卫本人,甚至也未告知其客户即两位被告,自然也未与被告们商议是否应将此信息披露给大卫。
该案于1957年3月4日开庭审理,当时大卫和家人都不知道动脉瘤的存在,相反,他们认为他正在从事故中受伤的伤势中恢复。

>>美国律师协会 资料图
之后双方达成了一项和解协议,大卫和他父亲同意以6500美元解决所有因事故引起的损害。由于大卫不满21岁,还是个未成年人,与他有关的和解协议必须得到法院的批准。大卫的律师向法院提交了和解申请,申请书对大卫伤情的描述完全是基于大卫自己医生的诊断。被告律师清楚,大卫的律师对动脉瘤的存在全然未觉。
1957年5月8日,也就是大卫21岁生日的16天前,法院批准了6500美元的和解方案。此后近两年的时间里,大卫一直生活在动脉瘤不断恶化并随时危及生命的危险之中,对此他和家人都一无所知。
两年后发现病情,原和解协议被法院撤销
差不多两年后,大卫被陆军预备役要求做一次体检,他是预备役的一员。为此,他再次请自己的家庭医生为他检查。在这次检查中,医生发现了危及生命的动脉瘤。然后,医生重新检查了在交通事故之后不久拍摄的X光片,确定是两年前的事故导致了动脉瘤,并建议大卫立即进行手术。手术去除了动脉瘤,但由于手术的迟延,大卫永久性地丧失了几乎全部的语言能力。
手术之后,大卫起诉要求撤销先前的和解协议,理由是双方在和解时对动脉瘤的存在不知情,即对案件事实的认识存在严重错误。被告律师出示了汉纳医生关于动脉瘤的报告,以证明被告已经掌握动脉瘤的信息,只是原告不知情罢了,因此并不存在双方共同的事实认识错误。考虑到辩方在和解时已经知道了动脉瘤的存在而未能披露,大卫修改了他的诉状,指控被告对其隐瞒病情的行为是欺诈性的,并且被告违反了向法庭披露事实的义务,因此应该撤销之前的和解协议重新确定赔偿数额。
初审法院同意辩方的意见,认为没有任何欺诈行为,因为辩方律师在达成和解时没有做出任何虚假陈述。法院的理由是,由于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对抗关系,被告或其律师没有义务披露有关动脉瘤的信息。
然而,初审法院同时认为,在向法院提交批准和解的申请时,双方的对抗关系已经结束,应共同致力于协助法官在案件事实的基础上确定一个公平的和解方案。此时,被告律师应该对原告申请书中有关大卫所受伤害的信息进行修订和补充。被告律师未能如实向法院披露其所掌握的重要案情,这给了法院撤销原和解协议的自由裁量权,因为法院在判断和解协议对大卫是否公平时,没有掌握全部事实,尤其是有关损害的重要事实。
明尼苏达州最高法院维持了初审法院的判决,并将该案发回重新审理,让大卫有机会就其受到的全部损害重新主张救济。大卫后来与被告达成和解,和解金额不详。
对照职业规则,如何评价律师行为的合理性
斯伯丁案发生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那时的律师职业伦理适用的是美国律师协会1908年版的《职业道德准则》(ABA Canons of Professional Ethics,下文简称“道德准则”),与现今的《职业行为示范规则》(ABA Model Rules of Professional Conduct,下文简称“示范规则”)有些差异。我们将在当时的规则之下来分析律师行为的合理性,也会尝试探讨在现有规则之下如何评价本案律师的行为。
(一)律师是否应向对方当事人披露重要信息
初审法官罗格舍克认为,被告律师不必向原告披露动脉瘤信息,这完全符合当时法律和律师职业伦理规则的要求。根据当时所适用的“道德准则”第33条,律师必须保守客户的秘密信息,只有两种例外:1.律师被客户起诉时,律师不再需要保守与被指控的事项有关的客户信息;2.当客户明示了自己的犯罪意图时,出于避免客户的犯罪行为伤及他人的必要,律师可以披露客户秘密。斯伯丁案不涉及这两种情形,因此,被告律师未能向原告方披露动脉瘤信息的行为并不违反职业伦理规则。罗格舍克法官在判决中写道:
由于某些原因,原告医生未能发现动脉瘤。由于原告律师没有使用证据发现程序,导致原告医生和他的所有代表都不知道被告及其代理人知道动脉瘤这件事。……毫无疑问,两名被告的律师都有良好的信誉,在谈判过程中,当双方处于敌对关系时,被告或其代表不需要披露这方面的信息。
今天的明尼苏达州已经转而采用1983年版的“示范规则”,该规则1.6条允许律师在合理必要的范围内,披露客户信息的例外情形已增加为七项,其中的第一项例外即为“为了防止合理确定的死亡或者重大身体伤害”,这是将他人的生命价值放在首位,允许为防止合理确定的死亡或者严重身体伤害进行合理必要的披露。这一规则的适用极为严格,要求这种伤害是合理确定会发生的,而不是推测性的伤害。即,该伤害会立即发生,或者如果律师不采取必要措施消除威胁的话,该伤害必然会发生。如果斯伯丁案发生在今天,被告律师未能向大卫披露的行为是否有违职业伦理呢?未必如此,即便我们认为动脉瘤的存在会危及大卫的生命,被告律师也并非“必须”向大卫披露这一信息。因为1.6条(b)的准确表述为,这些例外情况下,律师“可以”而非“必须”进行披露。因此,披露与否成为律师自由裁量的事项,即便律师没有披露有违一般的道德准则,但律师不应因此受职业惩戒。虽然律师具备普通人的同情心,可能倾向于披露这个信息,如果不是强制性的义务使然,律师自主性披露可能使他无法面对客户的信任。进一步讲,不利披露必然导致客户赔偿责任的加重,律师似乎没有可能为客户分担加重的责任。那么,不利披露对客户而言是公平的吗?因此,即便在现有的职业伦理规则之下,被告律师可能也不会做出对客户不利的披露,尽管动脉瘤可能随时危及大卫的生命。
(二)律师是否应向法庭披露重要信息
如前所述,初审法院和明尼苏达州最高法院都没有认定被告律师隐瞒动脉瘤信息的行为,有违任何法律或职业伦理规则。事实上,初审法官说,如果大卫在达成和解时已经成年,他会断然否决撤销和解的动议,而让大卫对他自己的医生(未能发现动脉瘤)或律师(未能充分利用证据发现程序)主张赔偿。法院意指,大卫的医生未能发现动脉瘤,以及他的律师未能充分利用证据发现程序从对方那里获得有价值的信息,都是不当的执业行为,大卫完全可以对自己的医生和律师主张损害赔偿。

>>资料图
然而,当和解方案提交法院审议时,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关系就从对抗转向合作,尤其是不得对法院隐瞒重要信息,因为法院将依赖双方提供的信息作出裁决。各个时期的律师伦理规则无一例外都强调律师应该对法庭坦诚,不应有所隐瞒、欺骗和误导。在“示范规则”3.3条的注释中,美国律师协会认为,律师负有避免破坏裁判程序适正性之行为的特殊职责,在保守委托人的秘密的同时,其对委托人的责任受到其对裁判庭坦诚职责的限制。因此,虽然在对抗制程序中,并不要求律师无偏倚地罗列有关法律,或者对其在案件中提交的证据作出保证,但是律师不得让裁判庭受到关于事实、法律的虚假陈述或者律师明知为虚假之证据的误导。因此,基于被告律师的隐瞒行为,初审法官作出了撤销原和解协议的裁决,并得到了明尼苏达州最高法院的支持。
(三)律师是否应向客户披露重要信息
既然被告律师囿于保守客户秘密的职责不能将动脉瘤信息披露给原告方,那么,律师出于对大卫生命的关切,可否建议被告进行披露呢?当然可以,律师除了诉辩者的身份外,更应该是一个良善的建议者。根据“示范规则”2.1条,“在提供建议时,律师不仅可以以法律为依据,而且可以以诸如道德、经济、社会和政治因素等可能与委托人的处境有关的因素为依据”。本案中的原告大卫和被告约翰相仿,是邻居,大卫及其家人为约翰父亲的建筑公司工作。事故发生时,大卫结束了一天的工作,搭乘约翰的车回家,两个年轻人之间可能有不错的友谊,约翰不致于对大卫的安全隐患守口如瓶吧?从时代的背景来讲,案件发生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明尼苏达州民风淳朴的乡间,人们是很难对他人生命的安危漠视不管的。更何况,被告的赔偿责任在保险额度之内的部分,实际将由保险公司支付,被告无须太担心自己的赔偿负担。
美国律师协会注意到他人支付律师费用会导致律师面临难以协调的利益冲突,因此在“示范规则”第1.8条中明确规定,律师不得接受源自非委托人的他人的酬报,除非:(1)委托人作出了明智同意;(2)对律师的独立职业判断或者律师-委托人关系不存在干预。
那么,被告在信息披露的问题上是什么态度呢?让人意外的是,被告齐默尔曼和莱德曼两家表示,他们对于大卫在车祸中遭受的未加披露的动脉瘤损伤并不知情,即被告律师并未向自己的客户披露全部信息。被告律师的这一行为让人颇为费解,但背后有一个现实的原因,即被告的律师是由其保险公司聘请的,保险公司虽然不是本案当事人,但将是最终为被告责任买单的主体,也是支付律师费的主体。这种情形带来一个律师需面对的职业伦理问题,即谁才是律师的客户,被告还是保险公司?虽然委托代理合同清晰地界定了律师和被告之间的关系,但实践中保险律师往往将保险公司视为真正的客户,从而倾向于为了保险公司的利益在保险额度范围之内解决纠纷,很多案件信息的处理未经被保险人同意,这显然违反了律师应与客户之间进行充分交流的职业伦理义务。
斯伯丁案体现了保险案件中被告与保险公司之间显而易见的利益冲突。即便在有些案件中保险公司以共同被告的身份出现,但无法改变其与被保险人被告之间的利益冲突,即律师费用和赔偿责任最终将由保险公司承担。而且,律师希望留住保险公司作为回头客,会导致律师忽略被保险人的客户身份,反而将保险公司作为真正意义上的客户。美国律师协会注意到他人支付律师费用会导致律师面临难以协调的利益冲突,因此在“示范规则”第1.8条中明确规定,律师不得接受源自非委托人的他人的酬报,除非:(1)委托人作出了明智同意;(2)对律师的独立职业判断或者律师-委托人关系不存在干预。
有一种看法认为,如果大卫了解到自己真正所受的伤害,可能会提出超过保险限额的赔偿请求,超出部分将由被告亲自承担,因此被告律师隐瞒动脉瘤信息的行为是有利于被告的,被告不可能作出不同的决定,律师节省不必要的沟通不能说是不当行为。笔者认为这种观点不能成立,理由如下:
首先,大卫在了解真正所受伤害后是否会提出超过保险限额的赔偿请求是不确定的,而考虑到案件发生的时代背景及本案的具体因素,这种可能微乎其微。本案除大卫受到严重损害之外,两辆车上的其他一些人也受到严重伤害,包括两名乘客的死亡。包括大卫获得的6500美元赔偿在内,这起事故所产生的总和解金额是4万美元,因此可以预计即便大卫的动脉瘤信息被披露,索赔的数额也不太可能超出5万美元的保险限额。
其次,即便信息的披露可能导致被告额外的经济负担,也不能成为律师对自己客户隐瞒信息的正当理由。客户的利益不限于金钱方面,也可能包括道义方面,也许被告方宁可承担超过保险限额部分的赔偿,也不愿意因为自己的拖延导致大卫面临生命的威胁。很多时候,律师把客户的目标过于简单化了,他们假设客户只可能作出自私的选择,一般的客户都会害怕增加赔偿责任。尽管律师本人在代理客户时应遵循职业道德而非一般意义上的道德,但在对客户提供建议的时候,律师不应放弃划清道德与非道德的界限。律师固然不是客户的人生导师,但处理金钱上的纠纷并非律师的全部工作,律师应考虑解决方案从道德、经济、社会等各方面对客户产生的影响,例如客户从此能否获得内心的平安、声誉是否受损,以及纠纷是否可以获得永久的平息。事实上,大多数客户会遵从律师的道德和法律诸多方面的全面建议。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律师说服被告披露大卫所面临的生命威胁是完全可能成功的,也是最终符合被告利益的,至少不应对被告隐瞒这一信息。
斯伯丁案的最终裁决使大卫获得了更多的赔偿,但由于失去了及时排除生命隐患的机会,两年后的手术使大卫永远失去了说话的能力,没有人会认为这是一个完美的结果。而如果被告律师能真正尊重自己的客户,与其进行充分的沟通和建议,或许可以避免这样的遗憾,这是本案最重要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