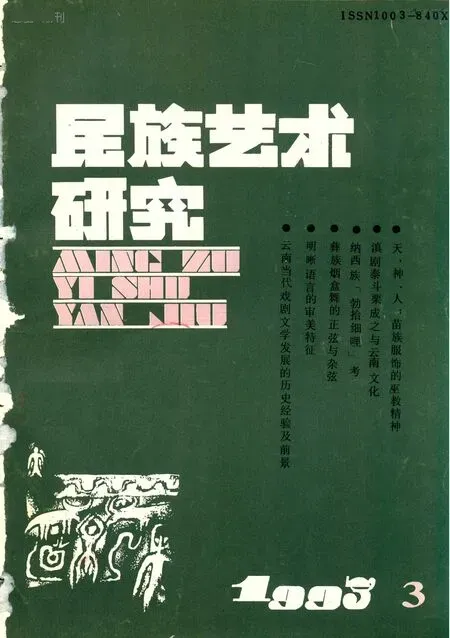联横合纵:中国少数民族音乐迈向“多元分层一体格局”的跨世纪转型
杨民康
近70年来,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经历了从“族群-地域-定点”向“民族-区域-多点”转型,并借助“历史音乐文化走廊”连通不同“区域音乐文化板块”,以形成中华民族音乐文化“多元分层一体格局”的进一步转型的学术历程。田联韬先生与他的学生们几乎全程经历和体验了这个微观学术史课题研究的基本过程。当“田联韬先生与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学术专题进行到中期阶段,由针对学科整体的综论、概览转至各个学科支脉的微观学术史的描写、阐述时,本文提出和讨论这两个相对具体的学术转型现象,意在对本专题此后两期的多篇后续性论文中将会出现的一些基本观点和论述趋向进行思考的基础上,给出一点提示性的看法,希望能够有助于读者去完整地把握本学术专题各个具体环节之间的前因后果、相互联系和整体脉络。
一、第一阶段:从“族群-地域-个案”向“民族-区域-比较”的局部化态势转型
20世纪80年代以前,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虽然已经有了相当多的研究成果,并且将其触角伸向了全国不同的少数民族音乐的分布区域及各种不同的体裁类型。但是从其规模范畴来看,这些研究课题大体上是以“族群-地域”规模范围的少数民族音乐文化定点个案研究课题为主。直至20世纪八九十年代,虽然已经有了由国家相关部门统筹、北京与地方学者共同编写规模宏大的中国民间音乐集成志书以及《中国少数民族乐器志》①中央民族学院少数民族文学艺术研究所:《中国少数民族乐器志》,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6年版。《中国少数民族艺术辞典》②中国少数民族艺术辞典编纂委员会:《中国少数民族艺术辞典》,北京:民族出版社,1991年版。等大型少数民族音乐志、辞书,但从这些重要的音乐书籍的主旨意义看,在于“对中国浩如烟海的民族民间文艺进行了一次全面、深入的普查和挖掘、抢救,系统地收集和保存了我国各地各民族民间优秀文学艺术遗产,记述了各地各民族民间优秀文学艺术的历史和现状”,并且采用了一般音乐学术志书或工具书的编纂思路和书写体例,不同地域、族群音乐文化在书中乃是按照省区行政设置分散归放和自然排列。直到20世纪初叶,《中国少数民族传统音乐》 (上、下册,2001年)、《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史》(三卷本,2007年)两部重要的学术著作正式出版,便在编纂者的学术规划和统筹之下,以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展大规模的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和民族识别工作的成果为背景,按照五十六个民族分类的划分原则,每一民族的传统音乐皆立一章,随相关民族人口数量的多寡、分布地域的大小及传统音乐丰富程度等差异状况,其篇幅字数亦有不同程度的增减。若结合族性研究与区域音乐研究两类因素一看,这类研究课题打破了以往相关课题研究主要依“族群-地域”进行孤立研究的状态,不仅在藏族、蒙古族、回族等人口较多、分布区域较广的民族中进行了多省区的局部整体性比较研究,而且在彝族、壮族等南方民族中也实现了跨省区的横向比较。从研究方法论看,开始有了更多的“跨族群、地域、文化个案”学术意图和更加看重联系、比较的研究概念、思维和分析方法的学术特点。
二、第二阶段:从“民族-区域-比较”到“走廊”—“板块”的“多元分层一体”音乐分布格局
21世纪初叶,在上述以民族、族性为背景的研究思维及方法论基础上,可以看到更多由人类学、民族学方法论引领的,以路带、通道来联系、沟通不同音乐文化区域,使之积少成多、连接成片以进行中观层面比较研究,并且出现了提倡开展中华民族音乐文化“多元分层一体”分布格局和连通“一带一路”音乐文化长廊的新的主张和学术倾向。由此而论,这一时期中国的“跨族群-地域-文化”多点音乐民族志比较研究,一方面体现出在中国少数民族内部形成的,以不同省区之间的同一民族或不同民族音乐的区域性“跨界”研究;另一方面还出现了从国内到国外,由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到跨界族群音乐研究,总体上体现了一种(区别于纯粹的“海外音乐民族志”的)“由内向外”“由我至彼”的学术思维观念和逐渐拓展、延伸的发展和形成过程。上述发生在中国民族音乐学学术界的转向,很大程度受到了中外民族学相关学术思潮和研究方法论的影响。
20世纪80年代,费孝通先生在其“继往开来”的宏观思考中提出:“过去的民族研究是按民族的单位孤立起来,分别一个一个研究,在方法上固然有其一长处,但是也有它的局限性。”③费孝通:《民族社会学调查的尝试》,载费孝通《从事社会学五十年》,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90—91页。“一个民族一个民族地研究,写它的历史,不是从一个整体,从中华民族这个整体来看各民族间的往来变动,怎样影响它们的形成、合并和分化。”④费孝通:《谈深入开展民族调查问题》,《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2年第3期。“而中国少数民族有它的特点,就是相互关系深得很,分都分不开……而民族与民族之间分开来研究,很难把情况真正了解清楚。我主张最好是按历史形成的民族地区来进行研究。”①费孝通:《谈深入开展民族调查问题》,《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2年第3期。关于“历史形成的民族地区”,费先生又提出:“从宏观的研究说来,中华民族所在的地域至少可以大体分成北部草原地区,东北角的高山森林区,西南角的青藏高原、藏彝走廊,然后云贵高原、南岭走廊、沿海地区和中原地区。这是全国这个棋盘的格局。我们必须从这个棋盘上的演变来看各个民族的过去和现在的情况,进行微型的调查。”②费孝通:《民族社会学调查的尝试》,载费孝通《从事社会学五十年》,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91页。有学者指出,费先生划分的上述“历史形成的民族地区”实际上包含两种类型:一是“板块”类型,如“北方草原”“东北高山森林区”“青藏高原”“云贵高原”等;另一种则是“走廊”类型,如“藏彝走廊”“南岭走廊”“西北走廊”③石硕:《藏彝走廊:一个独具价值的民族区域——谈费孝通先生提出的“藏彝走廊”概念与区域》,载四川大学“藏彝走廊历史文化”学术讨论会论文集(转引自中国知网),2003年。。若比较两者的作用,可见前者作为“民族(音乐)文化板块”虽然已经形成了区域文化研究的规模和景况,但仍然没有完全脱离费先生指出的孤立、静止研究的状态。而后者作为“历史音乐文化走廊”的一个重要的功能作用,就是用来联接不同的区域性民族文化板块,使之形成一个完整的、兼及汉族与少数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关系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
差不多与此同一时期,西方人类学者也在民族志定点个案研究基础上,提出了多点民族志、合作民族志等新的研究观念和设想。关于多点民族志,如美国民族音乐学家赖斯曾经指出的:“也许由于传统理论舒适的空间构建已经不足够,在过去十五年以来,社会理论开始对更新空间(space)、地方(place)、场域(location)产生兴趣。人类学家研究中的社会或村庄和社会学家的阶级或国家已经被其研究对象的发展所超越,地理学家们也正在重整他们固定不变的理论,而开始从一种社会构建、社会在空间上的映射、一种像时间一样动态的角度去理解。”④Timothy Rice.“Time,Place,and Metaphor in Musical Experience and Ethnography”.Ethnomusicology,2003,47(2):151-179。赖斯还针对场域维度提出了具有社会-地理意义的一种嵌套的论点:个体的(individual)、亚文化的(subcultural)、本土的(local)、地域的(regional)、国家的(national)、地区的(areal)、散居的(diasporic)、全球的(global)和虚拟的(virtual)。赖斯认为,虽然这些空间可以是指世界的地理位置,但对音乐体验同样重要的,也有些是指一些音乐家和观众想象他们体验音乐的思想中的场域。结合该类学者提出的“主文化、亚文化和交叉文化”的文化层理论,可以看出与费孝通先生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以及“民族文化板块”和“历史文化走廊”分析思路之间的诸多相似性特点。此外,美国人类学家乔治·马库斯时隔多年后又重新指出:早期对多点民族志的理解只是认为它与民族志调查点的移动(movement)和流动性(mo-bility)有关,强调对全球化变化所引起的新关系和程序变更的经验研究。但事实上,现有的变化中的移民研究是转型中的多点民族志的方便的样本,但是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中,后者还包括其他创新性的观点,如关注什么?如何关注和如何追踪过程?在这种对田野作业合作图景的另类建构中,现在人类学家和过去的“土著”就像搭档,他们由于对别处“第三者”的共同兴趣而联合起来。合作被认为是两个“局外人”因共同关心需要探索的事物而结成的关系。这种协作式的田野调查研究,建基于人类学家和他的报道人/搭档之间的磋商,形成了民族志的主要原始材料。⑤乔治·马库斯:《十五年后的多点民族志研究》,满珂译,《西北民族研究》2011年第3期。这类在“多点民族志”方法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合作民族志”研究思路,让我们对自己目前进行的中国与周边跨界族群音乐研究产生了一些新的联想:首先,从研究对象看,我们的课题研究是以境内少数民族音乐的定点个案研究起始,由此形成我们个体研究者与“土著民族”的“共谋”关系,并且由此建立起一种以境内少数音乐为出发点的“文化本位”(含大写的“中华民族”和小写的“对象主体”),并且将境外的同源族群音乐和中国内地的汉族传统音乐视为可以拓展和延伸的两翼,最终又将后者视为一个新的重点关注对象,这也是我们在研究过程中一直秉持“主位的”“由内向外”(与“客位的”“由外向内”或世界主义立场相对)的基本的研究取向的重要原因之一。其次,我们从事的跨界族群音乐研究,其对象包括了汉族、少数民族和境外同类族群的音乐文化,这种研究带有“首先在这儿,之后在那儿,然后又到那儿”的“多点音乐民族志”特点。由于在与“土著民族”的对话过程中经常找不到问题的答案,从而产生了“一种确定的不完整性”和“原因在别处”的观念,并且因为对别处“第三者”(如境外的同源族群和境内的汉族传统音乐)的共同兴趣以及渴望获知真相的焦虑和预期、预测而联合起来,一起去“别人的地方”“开疆辟土,拓展外域”。再者,在研究过程中,我们与其他学科学者以及政府、研究对象之间建立起了一种良好的合作“共谋”关系,树立起了“传承、建构和创新”以及“‘非遗’音乐、节庆仪式音乐和创作音乐”等新的“主、亚文化层”学术构架。最后,我们与相关刊物媒体和研究机构合作,汇集本学科的中青年精英人才,准备对自己从事的不同学术个案及其多点散布和连接状况进行有关学科学、学术史层面的学术追踪和比较分析,以期得出完整、全面的学术结论。
于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发生的,旨在解决自己内部历史与文化问题的民族学重要论点,虽然囿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主要还局限于中国学界的内部观点,尚未能与国外学术界形成有效的沟通。但是,根据后来所知的情况加以分析,上述中外民族学、人类学界的两种观点其实有着异曲同工的特点。在面临同样的文化与学术问题时,从较大的学科、学术格局和文化视阈上起到殊途同归、遥相呼应的作用。对于我们较晚一步开展,隶属民族音乐学/音乐民族志范畴层面的“区域音乐文化板块”和“历史音乐文化走廊”等研究课题来说,这两方面的学科方法论资源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指导和引领作用。
从国内音乐文化研究的角度看,早于20世纪末叶,少数民族音乐研究领域曾经受到人类学界费孝通先生提倡的“藏彝走廊”“岭南走廊”“西北走廊”以及地方学者提出的“茶马古道”“苗疆走廊”“武陵走廊”等学术概念的影响。随着21世纪的到来,习近平主席起先提出了建设“一带一路”(“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合作倡议,继而在十九大报告中强调:“全面贯彻党的民族政策,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为我们开展国内外不同音乐文化的个案研究与彼此间“交往交流交融”的研究拟定了政策性、方向性的指导意见。由此,中国民族音乐学学者通过自己进行的“板块”和“走廊”两类课题研究,逐渐连通了中国南方到北方以及汉族和少数民族音乐的不同音乐文化区域之间的关系。而从近年来中国学者进行的中国与周边跨族群音乐文化研究情况看,也在习近平主席“一带一路”合作倡议的指引下,延续了上述国内的诸区域性文化通道的南北双向连接与贯通的趋向和态势,把研究目光拓展到了对中国少数民族和汉族音乐文化与南亚、东南亚、东北亚、中亚等周边国家和地区音乐文化的比较研究上面。
三、田联韬先生与学生们的相关民族音乐学研究实践
从田联韬先生及其几代学生的整个学术历程来看,可以说同上述中国少数民族音乐文化的发展趋向高度吻合,并且始终站立在这一系列发展进程的前沿,对于少数民族区域音乐研究的整体态势形成了明确的分布布局和学术分工。
从目前该学术领域的研究情况看,正如前文所述及的,在由田联韬先生的学术论著及其学生的硕士学位论文和博士学位论文构成的学术成果环链中,包含了由“族群-地域-定点”到“民族-区域-多点”,以及通过“走廊”连通“板块”,以达至中华民族音乐文化“多元分层一体格局”的不同的阶梯形、阶段性内容成果。然而有必要强调的是,由于中国民族音乐学学科建设的薄弱性所致,隶属前两者层面的、带有“区域音乐文化板块”特点及以族群、民族、区域为对象的基础性研究,至今仍然是其中较主要的研究课题内容;而后一类“通过‘走廊’连通‘板块’”以及通过音乐文化分层(如“主文化、亚文化”“大传统、小传统”)研究以达至整体性、全局性观照的课题类型,虽然已经初见成效①相关论文参见杨民康、魏琳琳、赵书峰:《当代跨界族群音乐研究的学术格局——中国艺术人类学前沿话题三人谈之十八》,《民族艺术》2020年第5期,第148—157页。赵书峰:《流域、通道、走廊:音乐与“路”文化空间互动关系问题研究》,《民族艺术》2021年第2期,第93—102页。,但是尚处在启动和上升阶段,亟待在摸清家底、布局之后,向纵深发展。
在少数民族暨跨界族群音乐研究过程中,通过学术会议和在学术刊物上发表专题论文等途径,形成了相关学人组成的学术共同体及其某些规模化、体系性的行动与行为方式。其中一个标志性的重要举措,即2011年在北京中央音乐学院召开了“首届中国与周边跨界族群音乐暨少数民族音乐文化学术论坛”。继而在2019年又在云南艺术学院召开了第二届相关学术会议,今年又拟筹备召开第三届学术研讨会,并且将会议的规模拓展为国际性会议,以邀请国内外相关领域学者前来共商学术大计。从研究对象及学术宗旨看,如今国内的跨界族群音乐研究也有了更为成熟的学术分类和前景规划。比如在西南与周边跨界族群音乐研究领域,已经有了从少数民族音乐延伸至少数民族音乐与汉族音乐的联系与交融关系,且分别针对“沿边、路带、环山、环岛、海丝(海上丝绸之路)”诸对象类型展开全面研究的设想。从研究范围看,这个研究设想不仅考虑到中国民族音乐学研究想要通过“历史音乐文化走廊”连接“区域音乐文化板块”,以达到在汉族和少数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形成“中华民族音乐多元分层一体分布格局”的内部要求;同时还兼及了以“一带一路”音乐文化长廊连通中国与周边国家与民族音乐文化之间相互联系的“由内向外”发展要求和学术走向。从方法论看,这一时期的研究不仅受到中外民族学、人类学同类研究方法的影响,同时还显现出接受了国际民族音乐学多点音乐民族志研究方法影响的痕迹及与国际前沿研究方法接轨的学术发展进程特征。
在本专题里,拙文《开拓与引领:田联韬先生对建构中国少数民族音乐“三大体系”的杰出贡献》一文,从概览、综述的角度,着重讨论了从偏重“族群-地域-个案”研究的前一阶段到进入“民族-区域-比较”阶段初期的学术状况。同时,在该文及有关藏族、傣族和孟高棉语族、北方少数民族以及汉族、少数民族音乐文化交融的几篇文章里,也顾及了区域音乐研究及通道、路带等研究方面,对于南方五省区及三大方言区藏族音乐文化圈、云南与周边傣仂亚佛教音乐文化圈,北方地区的“走西口”“秦直道”及东北亚跨界族群音乐文化圈研究的状况皆有涉及。而在本期及下期专题论文里,将延续上述“通过‘历史音乐文化走廊’连接‘区域音乐文化板块’”的学术视角和讨论话题,把主要关注点放在中国南方少数民族音乐的区域音乐研究及跨界族群音乐研究发展状况上面,并且企望由此展现出现阶段中国少数民族暨跨界族群音乐研究所包含的前沿性、前瞻性等重要趋向和特征。
本期刊发的另外两篇文章里,集中讨论了两个“走廊”:武陵走廊和藏彝走廊。在费孝通先生开创的相关民族学理论中,作为“民族走廊”一般都身兼“民族文化板块”和“历史文化走廊”两种功用。武陵走廊地处湘、鄂、黔、渝三省一市交界地区,在目前国内学界较多谈论的诸条“走廊”中提出较晚。作为以土家族为主的多民族聚居-杂居区域,它既是一个具有“环山”地理特点的区域性民族文化板块,又是南北汉族迁徙和用于连接西南少数民族和华中地区汉族文化的一条重要通道。刘嵘、梁怡的《“武陵走廊”音乐文化研究的微观学术史叙事》,基于微观学术史的视角,通过梳理田联韬先生所指导的4位博士对武陵山区音乐文化的研究,认为其所呈现出地从聚焦单一族群到区域研究的比较视野,从文化地理学观照到“武陵走廊”学术视角的初步形成等研究范式的转换,可以管窥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在21世纪以来整体性的思路转型特征。
同样,藏彝走廊除了是一条同时连接国内藏羌彝等少数民族的茶马古道和跨国境外出的南方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之外,也是一个巨大的民族区域音乐文化板块和多元族群文化熔炉,以云南和周边国家彝语支跨界族群为主的基督教音乐文化圈,就是这座多元族群文化熔炉中,吸收了外来西方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路菊芳、孙莉的《藏彝走廊、茶马古道与南方丝绸之路——田联韬与学生们的川滇黔藏缅语族音乐文化研究》,讨论了在田联韬先生的开拓和引领下,三代学人对藏彝走廊、茶马古道文化和南方丝绸之路分布格局的学术观照,具有多点民族志视野,兼具“民族音乐文化板块”和“历史音乐文化走廊”研究的特征。作者结合田联韬先生及其两代学人的研究文献,对其与川滇黔藏缅语族音乐研究相关的学术思想、研究理念、教学实践等进行微观史学的描写和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