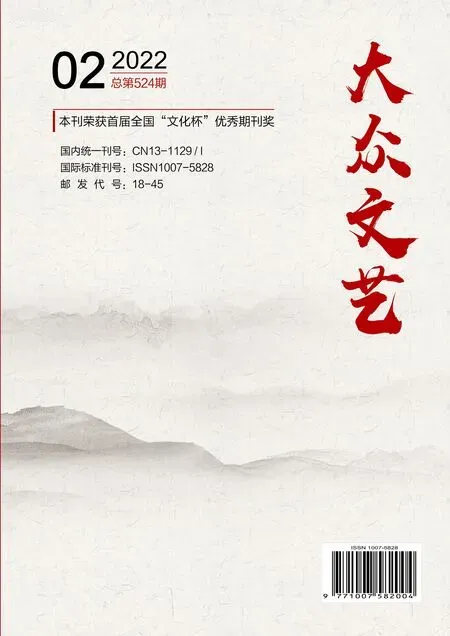生态美学视角下的袁枚园林文学研究
——以随园文学为例
(天津大学建筑学院,天津 300072)
从生态美学的视角下纵观袁枚的园林文学,可以发现其作品多有随园自然景物的参悟、造园实践的反思及园居生活的诗意描绘,这些作品落脚于人对自然形态的审美,涉及自我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宇宙等多重审美关系。这些园林文学不仅体现着袁枚诗学表达真我的自然观与审美理想,还体现了其造园实践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审美追求,与当代生态美学思想不谋而合。体现了袁枚园林文学对生态与人文的超前思考,因此,以生态美学的观点解读袁枚的园林文学作品对于当代的文学价值研究仍具有深远意义。
一、袁枚园林文学的生态美学内容
20世纪人类面临自然生态与精神生态危机,人们开始重视本心的怡然自得,尝试探索物质世界中人存在的精神性。西方生态哲学的不断完善使“生态”上升到美学概念。传统哲学中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本源思想、和谐思想、辩证思想重新获得关注,从道家哲学看,生态美学是“向着本源性的大道回归的美学”;从儒学解析,则是处理人与自然平衡关系的实践理论。综上,生态美学是具有本源性、和谐性、实践性、参与性的生态法则与审美原则。
清乾嘉时期(1736-1820)民殷物阜,人才辈出,是古典文化集大成的年代。袁枚作为这一时期“性灵”诗说的拓荒者,在学问上博习精思,从稗官野史到八股文,再到古文赋诗皆有博学。三十三岁父亲亡故后,他辞官养母并卜居小仓山(今南京市五台山余脉一带),“崇饬池馆,自是优游其中五十年。”袁枚所著《小仓山房诗文集》《随园诗话》《子不语》等皆有随园相关的诗文。
儒学与庄周之道共同影响下构成了袁枚朴素的生态美学思想体系。细读袁枚园林诗文,可以将其生态美学观概括为2部分,其一是顺随自然的生态理想,包含因地势、宜物性的原真审美理想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思辨。其二是追求人性的人文关怀,包含“著我”的实践观和诗意栖居的参与性精神追求。
二、随园文学作品中的自然生态美学
1.随园文学中追求原真自然的审美理想
前人研究袁枚的诗文多从“性灵”而论,袁枚诗文强调性情与本真,正如随园之名取义“随时之义大矣哉”,即顺随时义,进退有度。这里“随”与“真”是对应的,客观自然为“真”,尊重客观存在为“随”。诗文“发之以真性,肇之以真情。”造园也需尊重环境的本真与物的性情。“因势取景”和“因性赋形”的生态认识论与平衡人与自然“至中和”的传统朴素美学构成了随任自然、因地制宜的生态美学。
如《随园记》所述“墙茨剪阂,易檐改途。随其高,为置江楼;随其下,为置澳亭;随其夹洞,为之桥;随其湍流,为之舟;随其地之隆中而歌侧也,为缓峰袖;随其翁郁而旷也,为设宦炙。”将园林布局置于客观存在的真实环境下,肯定了自然赋形的美学特征。“因物赋形,随影换步。”认识客观事物的真我性情,不掩其本性,而后进行创造活动,是节省人力物力并延续自然审美的有益实践。“因”的生态美学更多是以提高生态效益并兼顾审美成本而论的。如《因树为屋》诗曰:“银杏四十围,叶落瓦无缝……更借树上阴,招宿丹山凤。”袁枚尊重旧貌,巧借数十围的古树枝干结屋,屋中居人,使人在树中赏四时景致,一举数得。袁枚在园林诗文中表达的尊重自然存在与运行逻辑是表达景致“真我”的基础,这种美的构建也与其诗学追求真我性情的自然灵动相呼应。
袁枚善从花木之性、山水理法感悟物理哲思,或在虚静中追求精神的本源。托物的真性以言真情,以客观的自然规律延伸到生命的情调是随园诗文的常见立意。常有描绘自然草木的荣枯,如“青苔避日葵争日”感悟到万物同在春风下而性情却各不相同的生命哲理。或在“静”“闲”之境参万物之性。如“静参诸物性,草木各成家”,又如在月色清光,白云如被的夜色中感悟人生哲学,在万籁俱寂中,体悟心灵与宇宙化合。人与自然在虚静间同化,达到心物交融,甚至超然物外与“道”合一。此种“虚静”在道家思想中被视为万物之本,这种精神的净化也可视为是自然原真的不舍追求。
2.随园文学中人巧雕琢与自然朴拙的生态思辨
生态美学提出人与自然达到生态平衡的美学原则,既尊重自然生态系统的美学特征,又肯定人的实践和价值。袁枚诗学多次讨论了天籁与人籁、天赋与修养的辩证关系,并得出诗有得天籁,也有得人巧,人巧 “浑成精当无斧凿痕”的美学观点。能够看出袁枚的自然观并非固陋反对人巧与雕琢,而是思辨认识以巧宜朴,以人工修饰自然的辩证关系。郭绍虞将其主张归纳为“大巧之朴、朴而不拙”。
在随园相关的文学作品中也常有关于人与自然辩证关系的论证。《随园三记》中提出“人之无所弃者,业之无所成也”的辩证思考。正如“叶多花蔽,词多语费”,所弃者在“以短护长,以疏彰密”的思辨。如诗文所述:南园不施人工,使人在自然之景中空游,北园则筑亭建屋,使南北两园疏密相彰;不起院墙打断山地起伏,以“十丈篱笆千杆竹”替代高墙则远景皆收,不以人工而造之物妨自然之景的真实展现。
“有为”则表现为“虽为人作,宛自天开”的“朴而不拙”。是指巧济天籁,贵在合宜,以人工与自然相补的生态哲思。首先,不拙巧于借,借景是通过人工对自然之景巧做取舍的情景再造。如《平台》描述小仓山置平台以借江湖云烟之远景,《绿晓阁》以“虚窗聚景”得以远观西山东城之景。或以窗借近景,如碧琅玕“虚窗八面”以观竹听雨。借景之法实则是将自然之景作为生态资本,以人的强化与改造建立新的生态属性与审美价值。
其次,不拙在于人巧合宜。《随园四记》中描绘人工与四时之景相补而得诗意栖居:“高楼障西”,以宜纳凉夏居,“琉璃嵌窗”,以宜无风观雪,“梅百枝,桂十余丛,” 以宜春秋闻香观花,“长廊相续”,以宜风雪行。以相宜的人工雕琢反助自然之景的更好呈现。除此外,还以人工仿自然之境,如《积水暴流命僮建闸为瀑布》和《引流泉过西亭》都施以人工理水而成景,前者瀑布白练悬空,力道强劲,为静景带来了动势;后者引泉从竹间细流绕西亭,则营造了曲水流觞的恬静雅趣。
三、随园文学作品中的人文生态美学
1.随园文学中实践的人文生态思辨
曾繁仁提出生态美学应立足唯物实践论,认为自然界的“精神”和“价值”与人的社会实践活动密切相关。从实践的角度构建了人与自然的对话,突出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体现了生态美学的创造性,基于客观存在的人的创造产生了人文生态美。这与袁枚“著我”的诗学理念异曲同工。
“夫物虽佳,不手致者不爱也;味虽美,不亲尝者不甘也。”在袁枚的园林文学中多有描述园林与人类活动的联系及其文化生态性,大量的诗文记录了随园的“一造三改”,其关乎造园事必躬亲,力求每处景致体现“我”之学问与修养、人生理想与审美志趣。以《理桂》《种梅》《制小艇》等小诗尽力描摹随园造改日常的真情实感。正是在这种事无巨细的琐事描摹,使自然之景充满人情与勃勃生机。这种源于自然又加入人文实践的生态美学,就在于人与自然动态平衡审美原则的准确把握。根据人文生态美学实践观的表达需要,通过文本将不同时空的人事景物紧密联系,使之在诗文的整体构建中发挥出超过文本表象的文化内涵与艺术魅力。
2.随园文学中诗意栖居的人文生态追求
袁枚将园林定义为“园悦目者也,亦藏身者也”,四时之间,可游可居。这种朴素的美学观点暗含了生态美的参与性特征,文学中所描绘的园居日常与海德格尔提出的“诗意栖居”似乎有着跨时空的联系,包含着人地和谐共生的生态美学观。林泉之间、水田菜畦、亭轩楼阁、祠堂坟圹,各景之性皆有不同,其中的诗意在于人在其中的生存状态,诗意的活动才是栖居的本质。
在袁枚园林文学中描绘的平凡日常充满生命力和真实情感。在袁枚看来“诗有极平浅,而意味深长者。”即以平浅事物感悟意味深长的哲思更为不易,太过超脱反而失真。既要表达人的志趣,就不能脱离人物活动。如《垦地五尺许栽禾为戏》的田间躬耕之趣;又如《钓台》所叙的夜钓之趣;还如《忙》中描绘的浇花养鹤,建池叠石理园之趣,或是如《随园张灯词》中展现的宴酣之趣。景因人而存在,诗文也是人心所得,这展现了生态美学的人文本质,即是人的存在与感受,这与袁枚“言诗之必本乎性情也”的诗学理论又有所呼应。
人性的关怀是人文生态的审美原则,激发人敏感的感官体验,甚至获得超验的通感,使心灵与感官交欢,是获得诗意的至理妙机。从内心感觉出发,创造多感官体验的艺术表达在随园文学中多有运用,对日常可见的禽鸟花木、风雨雷电、亭台楼阁施以灵动的隐喻、拟人、夸张等的修辞手法,引发情感的共鸣,如“建闸唱回波,劝水缓缓流。”将水流之声拟作人曲,并与之对话。或如造“泠泠终日碧”澄碧泉、“幽兰种溪边”的香界、“高梧拒日,曲涧引风”的凉室,以水声、泉色、兰香、风和树荫的物性创造多感官体验,使自然之景具有了文化与审美的诗意。
四、结语
从袁枚园林文学中可见其对人的本性与自然原真的追求,其所主张的真情真性,天人一体的审美思考充满生态与活性。对天籁与人籁的思辨,对“所弃”“有为”辩证认识,成为处理人与自然辩证关系的审美原则和生态法则。其人文生态美学的构建贯穿始终的是唯物的实践观,是事必躬亲的生态美学实践,是对人性的友善关怀,是人与自然、社会、自身的和谐对话。这些文字赋予了园林人学的精神向度,为现代生态美学的研究留下了宝贵的文本资料与实践经验,也为当代文学价值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