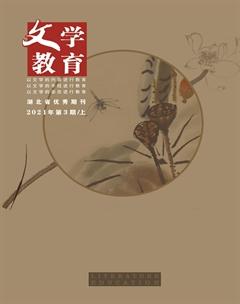新闻一束
●第11届丁玲文学奖举行颁奖典礼
第11届丁玲文学奖颁奖典礼日前在常德举行。本届丁玲文学奖小说类、散文类、诗歌类、文学评论类“成就奖”分别由作家王蒙、张承志、汤养宗、张炯获得;叶兆言、彭程、江非、南帆等12名作家分别获得小说、散文、诗歌、评论类“作品奖”;付秀莹、朝颜、江汀、张定浩等12名作家分别获得4个门类“新锐奖”。在丁玲诞辰115周年之际,第11届丁玲文学奖评选活动在北京启动,《文艺报》《人民文学》《诗刊》《小说选刊》4家学术支持单位组织开展评选工作,经过初评、复评、终评,评出成就奖4名、作品奖12名、新锐奖12名。丁玲文学奖是以常德籍著名作家丁玲的名字命名,1987年3月,由原常德地区文联和丁玲的第二故乡北大荒共同发起设立的。此奖每3年举办一次评奖活动,已举办10届,共奖励文学专著480部。2019年,常德市委、市政府修改评奖办法,改为两年一评,并由4家全国名刊具体组织评奖。该奖旨在继承和发扬丁玲矢志不渝为人民写作的精神,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奖励和推出体现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优秀作品。
●费孝通小说《茧》首次出版
近日,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刊行“费孝通作品精选”,脉络性地呈现费先生的学思历程和主要成就。费孝通一生以书生自任,笔耕不辍,著作等身。此番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费孝通作品精选”,由出版社和费孝通家人以及其后辈学人通力协作,从他七百余万字的著述中精选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凡12种,三百余万字,涉及农村农民问题、边区民族问题、文明文化問题、世界观察、学术反思等多个层面。其中,《茧》是近期发现的作者1936年用英文写作的中篇小说,为首次翻译出版,对于理解费孝通早期的学术思想与时代思潮的关系提供了难得的新维度。据介绍,这部20世纪30年代中期用英文写作的中篇小说,长期被封存于作者曾经就读的伦敦经济学院图书馆的“弗思档案”中,2016年才被发现并翻译成中文。“《茧》从未出版,译为中文后,仅约65000字。作为文学作品,它含有不少想象成分,却不完全是虚构之作。这部富有纪实内涵的小说,刻画了20世纪30年代中期苏南乡村一家新兴制丝企业与地方社会的关系图景。”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王铭铭老师介绍说。《茧》的开篇“通先生”在二战前夕的柏林,因“灯火管制”而百无聊赖,径自出门在康德大街的天津饭店就餐,巧遇自己读大学时的校友王婉秋。异国他乡遇故知,两人一晚不倦的闲聊与穿插其间的往事回忆构成了小说的全部内容。《茧》带有英式小品文特有的内敛和风趣,诸如“而现在,吃饭只是为了免于饥饿。生活规律看来只有和他人在一起时才能实现”等佳句,则不时透露出作者的洞察和睿智。
●第十二届“万松浦文学奖”获奖作品揭晓
第十二届“万松浦文学奖”获奖作品日前揭晓。葛亮的中篇小说《飞发》、郭凯冰的儿童小说《黄蒲台,青蒲台》、于立极的儿童小说《完美子弹》、沈念的散文《孤独建造时》、马兵的评论《从“祛魅”到“趋魅”:“灵学”与文学关系新论》分别获得小说、散文、理论奖。诗歌奖空缺。“万松浦文学奖”是为奖掖华语写作而设,由万松浦书院、鲁东大学、山东文学馆联合主办,秉持公正、纯粹和独立的评奖原则,倡导新思维和新语境,追求新气象和新高度。该奖每年颁发一次,分设小说、诗歌、散文、理论奖项。2021年上半年鲁东大学将举办第二届“贝壳”儿童文学周,本届万松浦文学奖特置儿童文学名额。按照万松浦文学奖的规定程序,经过终评委无记名投票,从入围作品中评选产生了最终获奖作品。颁奖活动将于2021年6月在烟台举行。
●《作家文摘》2020年度十大非虚构好书揭晓
《作家文摘》2020年度十大非虚构好书终评结果日前在京揭晓。《我们的80年代:中国的文学与文人》《丝绸之路:从蓬莱到罗马》《却将谈笑洗苍凉:晚清的政局和人物三编》《中国疫苗百年纪实》《红色交通线上的安徽人》《江南繁荒录》《查医生援鄂日记》《你和我》《上海表情》《文献中的百年党史》10本图书入选。近年来,非虚构类作品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以其观照现实、洞察历史、建构文化的特质为读者所喜爱,这也与《作家文摘》“求真、深度”的办报宗旨不谋而合。作为国内颇具影响力和公信力的文化品牌,《作家文摘》自2012年起就联合广大读者和知名文化学者,开展“年度十大非虚构好书”评选活动,通过系统梳理、回顾当年出版的非虚构类作品,甄选出兼具扎实史料、独立精神、锋锐视角和人文关怀的力作,为热爱阅读、文化诉求较高的读者群提供有针对性、有价值、有意义的参考。评选活动开展以来,吸引了上百万各界人士的积极参与,并以其专业性、权威性,在广大读者以及文化出版界获得广泛关注和高度认可。
●张炜出版长诗《不践约书》
2021年,张炜带给读者的第一本新作是一部长诗——《不践约书》,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在这部作品中,张炜以爱情为呈现线索,作家调动人文、思想、历史、哲学、文学、艺术等综合手段,以强大的精神背景和调动超出常人的写作能量,打造出的一个具有巨大冲击力的复合性诗歌文本,可以视为其代表作《古船》《九月寓言》《你在高原》的立体全方位覆盖性诗意呈现。长诗分为52节,是向一个视为知己的爱人的倾诉,一次精神告白,基于当下的回忆,逆时间之流任意回溯,来表达一个人在一个复杂多变的时代的探寻和追问。张炜的长诗一如浑厚而宏阔的交响乐,时空大开大合,意象丰富,气势磅礴,节奏鲜明而又充满悠长的韵致,抒发对自然、人生和家园的爱与眷恋。张炜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写诗。他直言诗是他“终生追求的目标。”在他看来,“诗的时代是过去了,大行其道的应该是小说。小说的边界一直在扩大,但诗仍然居于它的核心。没有抓住诗之核心的文学,都不可能杰出,无论获得怎样多的读者都无济于事。”在自序文中,张炜这样表达自己写作该诗的心路,“这部诗章虽然命名为《不践约书》,却实在是心约之作,而且等了太久。我深知要有一个相当集中的时间来完成它,还需要足够的准备。我已准备了太久。一场全无预料的瘟疫笼罩了生活,而且前所未有。多半年半封闭状态下的日子,实在是一场砥砺和考验。由忧闷到困境,从精神到肉体,持续着坚持着,直到今天。在这样的时空中,我似乎更能够走入这部诗章的深处;也只有这次艰辛痛苦却也充满感激的写作,才让我避开了一段漫长枯寂的时光。我珍惜这部诗章。”
●阿来小说《狗孩格拉》改编成电影上映
由阿来作品改编的影片《随风飘散》日前在成都举行了首映礼,这部已在国内外多个电影节获奖的作品,于12月28日全国上映。《随风飘散》由藏族新锐导演旦真旺甲执导,编剧芦苇担纲监制,索朗旺姆、更登彭措、旺卓措、才让卓玛等主演。电影改编自阿来的小说《狗孩格拉》,讲述了一对传统藏族村落中相依为命的母女,因家里没有男人而受到歧视,最终敢于打破偏见、实现成长。电影《随风飘散》已成功入选第27届金鸡百花电影节少数民族题材单元并获得该单元最佳创意剧本奖;入围釜山国际电影节“亚洲之窗”、海南国际电影节新人荣誉最佳摄影提名、罗马国际电影节最佳外语片奖、金鸡百花电影节展映、斋浦尔国际电影节JIFF最佳故事片提名、西班牙Imagine India电影节的展映等多项殊荣。
●武歆推出长篇新作《密语者》
曾以《延安爱情》风靡全国的作家武歆,日前出版新长篇《密语者》。该长篇以故事套故事的叙事方式和民间视角,呈现了风云变幻年代里天津各种小人物的百味人生,充满津味风情,同时阐述了艰苦境遇下顽强生存的人生意义。在接受采访时,武歆表示:“我应该给予我成长的这座城市更多的情感文字。”《密语者》在武歆心中蛰伏了20年,他说:“写《密语者》,是想完成关于天津的历史回顾,这片土地上蕴藏着太多的故事、有着太多的风情。”之所以选择打捞1937年到1939年的天津往事,他坦言:“1937年,日军全面占领天津,天津进入最为黑暗的历史时期;1939年,天津闹大水,水患持续三个月之久,市区百分之八十被淹,超过十万间房屋被冲毁,天津及周边六十五万民众成为灾民。洪水过后,霍乱、伤寒、痢疾肆虐。这段艰难的歷史时期,最能表现天津百姓不甘屈服、勇于抗争的民族精神。”在翻阅历史资料和图片时,他感慨万千:“应该用文学的方式把它讲述出来。书写天津历史,最好的承担者还应是天津作家。”
●艾伟《妇女简史》新书分享会在京举行
由作家出版社举办的“以小说记录当下女性命运——艾伟《妇女简史》新书分享会”日前在北京。《妇女简史》由作家出版社于2020年10月出版,包含《敦煌》《乐师》两个中篇。《敦煌》是一部女性的生命简史,探讨了女性的爱情、生活、家庭、事业,其中,对女性情感生活的书写纤毫毕现。《乐师》则可视为父女关系简史,小说讲述了一个落魄乐师寻找女儿的辛酸故事,寻找过程令人动容,在逼仄的空间里,父亲和女儿相互靠近又相互逃离,作家艾伟写出了父女关系中的爱、愧疚和宽恕,写出了生命中难以割舍的亲情。在分享会上,李敬泽对小说命名为“敦煌”比较感兴趣,他认为“敦煌”二字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地名,它被作为小说题目具有一定的指向意义。女主人公小项有她的精神诉求,先到敦煌,然后又去了拉萨,她需要一个答案。而从文学创作的角度出发,小说也需要一个精神性的结论。艾伟谈到,小说是人类经验的容器,不同经历的人在阅读小说时会有不同的体验,大家都会在小说中找到自己或多或少的影子,哪怕只是一闪而过的念头。这就是小说的迷人之处,小说像一面镜子照耀着我们内心世界中那些隐秘的想象、梦想以及欲望。
●毕飞宇希望文学苏军保持“静”的状态
毕飞宇日前当选为江苏省作家协会主席,他在接受采访时说:我们要对作协主席这个身份有一个清晰的认识,他身上确实肩负着一些责任,这个是不能回避的。写作这个事情不能说谁“引领”谁去写作,每个人都应当呈现独创性的写作风格。我要做的就是尊重和公平:充分尊重每个作家的写作探索、风格特色,公平地对待和评价他们以及他们的作品。我现在最大的渴望就是我们江苏作家能够继续“走出”江苏,获得属于他们的“茅奖”“鲁奖”。我自己拿下了“茅奖”,这对我个人当然是有意义的,但从今以后,再有哪位江苏作家拿了“茅奖”,我会像自己拿奖了一样开心。我特别想对文学苏军们说的,就是希望他们能够保持“静”的状态。“静”不仅仅是作家个人的心境状态,它还是一种文化的和美学的状态,这才是文学创造力所栖身的场域。运动员的创造是在奔跑中完成的,但作家的创造性是需要我们安静到了一定地步之后,才能够旺盛地喷涌出来。所以作家们得先“凝神”,再对世界“静观”。相反地,如果他心中只是洋溢着数票子的激情,是不可能把作品写好的。
●迟子建自称在文学上还可以压榨自己
迟子建日前在接受采访时说:二十多年前吧,我曾在一篇散文中说过:“我从未见过狰狞的鬼,却见过狰狞的人”,在我的成长经历中,遇见的灵魂卑污的人,还真是不少。人生不是世外桃源,就像日子不可能总是春天一样,你总要遭遇这样那样的寒冬。我要探究的是,这些“恶”是怎么来的?如果“恶”是社会带来的,被动或者被迫的“恶”,那么这样的恶就值得同情。“善”的脸孔可能只是一面,而“恶”却有多个面孔,所以探究恶的根源,写出复杂的人性,对我是永远的诱惑和挑战。如果说小说是一条河的话,那么细节就是涓涓细流。好的细节能够让作品闪光,也能让笔舒展灵动。比如《烟火漫卷》中有这样一个细节,黄娥驾着小汽艇单独送男客时,常因在大自然中不能自持萌生的欲望,与男客有越轨之举,于是她爱人卢木头见她单独送异性,有时会突然“发病”,躺倒在地装昏迷,阻止她出行。这就比较符合人物的真实心理状态和逻辑关系。我庆幸三十五岁完成了《伪满洲国》的写作,因为那是精力体力和才华都可以尽情释放的年华。我重要的作品确实是上世纪90年代后写就的,比如《伪满洲国》《额尔古纳河右岸》《世界上所有的夜晚》等。我依然会不紧不慢写自己的作品,没别的,我觉得在文学上还可以压榨自己。
●陈彦称《装台》就是一首劳动者之歌
根据陈彦同名小说改编的电视剧《装台》在央视一套播出,反响强烈。原著作者陈彦日前在接受采访时说:我非常熟悉《装台》里这些人物的生活,如果不写出来,我都觉得过意不去。严格讲,《装台》就是一首劳动者之歌。我觉得劳动者是美丽的,劳动的身影和姿态都是美丽的。我们的社会鼓励人们用自己的智慧、自己的双手、自己的肩膀扛起自己的生活,而不是过一种寄生的生活。我所接触的这些装台人,就是这样一群人,让我非常感动。这些装台工,他们所作的都是幕后最辛苦的工作,他们创造了如此美丽的舞台、如此美丽的灯光,而当灯光亮起大幕拉开的时候就看不见他们了。他们是普通劳动者的代表。电视剧做得很好,无论是改编还是导演都很好,尤其是像张嘉益、闫妮这样一批演员,他们都付出了非常艰辛的劳动。能看到,他们都努力贴近真实,没有用一种虚假的表演或是虚幻的场景来表现这些普通劳动者的生活,我觉得这是非常了不起的。电视剧的改编肯定会有些脱离小说,做一些新的创造,我觉得这也是对的,因为它们是不同的艺术样式。每个人对时代、对生活、对艺术都有不同的解读、不同的理解,他们所付出的创造值得我敬重。
●笛安趣谈读者和作者
笛安日前在接受采访时说:我相信一个事,就是一个好的文学生态绝对离不开一些好读者。我们的读者不够好,这不全是他们的错,跟我们常年僵化的语文教育有关。培养好的读者比培养好的作者还是更容易的。你不停地给它看各种各样不拘一格的好作品就行了,足够的氛围一定能有点成效。好作者可不能只靠熏陶。所以我在办《文艺风赏》的这些年里,渐渐觉得,我们的读者需要放松一点。我指的就是受过一定教育有一定品味的读者们,他们大多已经形成了一种潜意识,就是读到一篇小说潜意识里要求必须从中找到“意义”,找到“作者的立场与责任感”,找到人文关怀;你让他放下这些单纯欣赏一个作品本身的感染力,他马上进入到一种看电视剧的模式,要求作家在小说里给他像在电视剧里一样的满足……我只能说,这需要时间去改变。“文学”不是一个需要你焚香沐浴的东西,它同时也不是来伺候你的,好的读者能够平等地看待文学,用本能去感受它和体谅它——这是需要漫长岁月才能达成的吧。我们至少做了我们的努力,我希望他们在看“新审美观”的时候忘记意义,在看“经典重读”的时候把大师们当成是一个普通作者。
●勒泰利耶《反常》获得2020年龚古尔奖
六十三岁的法国实验作家、科学记者、数学家和语言学教授埃尔韦·勒泰利耶以其描写双重人生的小说《反常》获得了2020年的龚古尔奖。由于龚古尔包房所在的巴黎德鲁昂大饭庄被政府关闭,今年的颁奖典礼没有复现往年门庭若市的热闹景象。龚古尔学院仅通过视频会议系统宣布了勒泰利耶的获奖。勒泰利耶是科班出身的数学家,但最终转向了文学,1992年加入实验文学团体乌利波,现任该团体的主席。“数学的世界是无情的,我更喜欢文学的世界。”他告诉法国新闻周刊《电视、广播和电影》。这是首次有乌利波成员获得法国文学最高奖。《反常》是一部“逻辑与魔幻交汇”的多声部惊悚小说,仿佛写在纸上的克里斯托弗·诺兰的电影,讲述了巴黎到纽约航班上众多乘客的双重生活,在龚学院终评阶段的十票中独得八票而胜出。《反常》是勒泰利耶的第二十一部小说,2020年8月由加利马尔社出版。龚古尔奖贵为法国头号文学奖,但奖金只有十欧元,约合人民币七十九元。不过,获奖作品可借此在书市上一飞冲天,销量增长往往可达四十万册,甚至更多。
●阿特伍德最新诗集出版
2020年年终,玛格丽特·阿特伍德最新诗集《深深地》出版,随后登顶各大年终书单,其中包括goodreads2020年度书选。这是阿特伍德十多年来第一本诗集。同题的诗歌表明了阿特伍德的主题:爱和哀恸,“深爱的人,相聚在这里/在这关闭的抽屉里,/正在褪色中,我想念你/我想念那消失了的,那早先离去了的。/我甚至想念仍在这里的。/我深深地想念你们。/我深深地为你们哀恸。”阿特伍德发表了诗歌自述,发表于《卫报》,节录如下:我可以有把握地说——在找了一个小借口写了日记后——这首诗《深深地》写于2017年8月的第三个星期。在斯特拉特福(Stratford)的一条小街上,我用铅笔或滚珠(我必须检查一遍)写在一张纸上,也可能是旧信封、购物清单、笔记本页面,又或者是笔记本。这首诗歌的语言是二十世纪早期加拿大英语,当时的英语有短语“没那么糟”(less of a shit)。这个短语从来没在丁尼生的《悼念AHH》中出现过,但可能出现在乔叟的方言故事里。2017年12月,我从抽屉里拿出这首诗,勉强辨认出了笔迹,将它打成了一份电子文档。我是从文档的时间记录上,了解到了这些。这首《深深地》,一首符合它的时代精神的诗歌,却声称自己不符合它。这不完全是死亡的象征,更像是生命的象征。
●乔杜里称自己的小说并非自传类小说
阿米特·乔杜里日前在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发表了题为《我为什么写小说:它是否源于生活?是否真实发生过?》的在线演讲。整场演讲,乔杜里都在围绕“我为什么真的在写小说?”这个问题展开,或者如乔杜里所说,这是两个问题,“这是来自你的生活吗?这是真的吗?”乔杜里先是回应了人们对他的小说的质疑,他认为自己的作品并非传记或者回忆录,尽管连媒体都称之为自传类小说——当然,乔杜里会反驳说,并不存在自传类小说。乔杜里的第七部小说《少年時光的朋友》的确和他的生活存在某种相关性。小说主人公或者叙述者就是阿米特·乔杜里,这位朋友是拉姆。拉姆有毒瘾,后来进了康复中心,并从此从他的世界脱逃了。两位乔杜里都经历了同样的事情,他们都写了《少年时光的朋友》,在泰姬玛哈酒店交换了母亲和妻子送给他的两双鞋,在牛津大学读书,并尝试做音乐。乔杜里对上述答案最直接的回应是:在《少年时光的朋友》中,生活中的那些故事没有发生。再进一步讲,情节无关于故事,情节不是一个现实,情节是一种虚构。根本上讲,引用乔杜里,“时间在无畏地前进”。“困难在于对叙述氛围的抗阻,叙述氛围是某种东西已然结束的氛围……‘显示,而不是告知,这是一个空洞的指令,更真实的关键是‘如何不去重述,如何叙述当下,‘显示和‘告知会被镶嵌在其中。”乔杜里如是声称。
●《加莫内达诗选》推出中文版
日前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中文版《加莫内达诗选》。安东尼奥·加莫内达是西班牙著名诗人,1931年出生。凭《静止的暴动》(1960)获阿多尼斯诗歌奖登上西班牙诗坛。著有长诗《描述谎言》等多部诗集和诗选汇编《这光芒》(1947-2004)。曾获西班牙国家诗歌奖(1987)、索菲亚王后伊比利亚美洲诗歌奖(2006)和西班牙语世界高文学奖塞万提斯奖(2006)等。《加莫内达诗选》诗作由作者和译者从加莫内达所有诗集中精心挑选,也是诗人首部汉译诗集。加莫内达是目前健在的西班牙诗人中最德高望重的老诗人,是整个西班牙语诗歌世界具影响力的诗人之一。诗选内容来自《洛匹达斯》《时代》《寒冷之书》《损失在燃烧》《塞西莉亚》《这光芒》(1947-2004诗歌汇编)等诗集。他的诗歌风格具有鲜明的现代主义特色,语言硬朗有力,对细节的描述客观准确。内容上以记忆、痛楚和黑暗为题材,又将这些题材变得充满生机和欢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