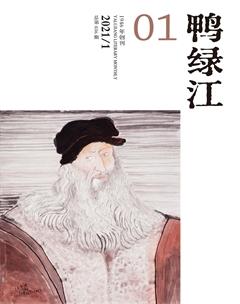刁斗的“脚印”
那天,刁斗宣布:哥们儿再有几天满六十岁,马上就吃养老金啦。起初,在场的几位大神以为这不过是妄语诓言,转而一经粗略推算,立马唏嘘不已:这岁月是在飞吗?咋连刁斗都花甲了?这岁月还真就是飞,身后拖着一张大网,把世上之人一网打尽。到头来,网里人彼此看看一张张霜打的老脸,只能感叹岁月的杀猪刀可曾饶过谁?奇怪的是世间过往,凡事也有例外,比如这刁斗就是漏网之鱼。都这岁数了,浑身却看不出时光流水的蹂躏,额上没长地垄沟,腹部没起啤酒肚,人家也没去健身房,没练背阔肌,没练肱二头肌,后身板子竟保持着几分迷人的“倒三角”;而且针对头顶的荒凉,某一天竟断然做了彻底清理,归入禿头党转而成潮男,跟中年油腻男也划清了界限。并且,他那双标志性的小眼睛照旧烁烁炯炯,时时闪出狡黠和智性的光亮,还夹带着一些暖人的东西,这无疑又有着别样的魅力,散文大咖原野就曾戏谑地夸他:看看,整个一副男版蒙娜丽莎的样貌!
说他逆龄生长,他可不以为然,声言身体是用来干活儿的,就算老抽巴了,能干活儿吃累,那也算好家伙。想当初他岁数已经一大把了,心血来潮要学开车,考下驾照后,几脚油门踩下去就上了瘾,长途驾驶成了最爱。他先载着媳妇拣远道跑了趟云南。彩云之南,那个美呀!可在刁斗那里美也是白美。他不像大多数人那样热爱大自然,无论山水还是草木,雄奇抑或柔媚,对他来说既不动心,也不吸睛。他把孤独的内心领地,永远留给自我的感受和思想。他开着快车,不图看景,光感受那嗖嗖的风声。飞奔的速度,抽象的远方,这些才让他真觉得爽,在速度中,内心激昂地回放和修正着他的奇思妙想。他曾约上朋友去跑欧洲,十个国家全用汽车轮子骨碌。他还载上老母亲,在沈阳与海南岛之间,一次又一次地飞驰往返。刁斗夫妻属丁克一族,性情斯文温婉的老母亲,便把对第二代和第三代的两份疼爱合并成一份,都给了他;而他还给老母亲的,则是在孝敬之上又附加了一份那富余出来的对儿女的娇宠。娘俩相互对望,彼此咋看都得劲。老妈将自己的耄耋老身,信赖地交付在儿子的车后座上,从地理版图的大东北直到南方尽头,一跑就是几千公里。老妈怕儿子长途行驶寂寞犯困,就给他一路背诵唐诗。老妈音色天生甜细柔美,宛如少女: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柔柔软软的清词丽句,如同大珠小珠落玉盘,叮叮咚咚撒了一路。可也许,对于提振精神,刁斗仍觉得不够劲吧,如果老妈诵读的不是唐诗,而是卡夫卡一类现代派大师的名言金句:世界和我的自我,在难分难解的争执中撕碎了我的躯体……啊呀,那一路上可就更拉风了!
其实平时在家,没有孩崽儿的嬉闹和拖累,日子无比清闲爽利,老妈很喜欢跟儿子扯家常,可总是扯着唠着,不知不觉中刁斗就抢了老妈的戏,转换成了一场他个人的演讲。刁斗是个书篓子,肚里有货,经纶满腹,一哈腰学问都会掉到地上,拥堵感也确实需要他不时地往外倒倒。刁斗的作品,不仅在外面颇有一些崇拜者,在家里,老妈和媳妇对他也满心崇拜。但媳妇在单位当个头头儿,脑子老被一摊公务占着,而闲着的老妈,眼神就乐意随儿子转,即便唠不成家常,转而听儿子纵论天下,也另有乐趣,有时听到关键处,还会拿出小本记上几笔。除了讲,刁斗还留课后作业般常给老妈列出必读书目或者文章。这些书和文章,大多是依照他的趣味选出来的,比较现代或者激进,虽然对一个老者来说阅读艰涩难懂在所难免,但戴着花镜的老妈竟能一页不落地耐心啃完,每每读毕都说,真好。
刁斗认为读书育人,春风化雨,对一把年纪的老者也是一样。可日久年深,他发现自己的努力成效不大,老妈该热爱唐诗还热爱唐诗,该体制化思维还体制化思维,老词、老思想都没大改观,与自己的语境仍然不大容易运行上同一个频道。母子的这番互动过程,只能算是行为艺术,刁斗得出的结论是:改造人其实没有可能。当然了,这并不影响他继续疼爱自己的母亲。
母亲对儿子,从小就操碎了心。半个多世纪前,儿子才六七岁或七八岁,身为少妇的老妈就逼着刁斗背唐诗。黄金年龄的妈妈教他唐诗,却没有半点黄金的感觉,因为那年头,正逢非常时期,出身不好被清理出教师队伍的妈妈下放在一个小铸造厂,整日两手硬茧、一身铁锈地清废渣、搬铁锭,她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利用三班倒那有限的休息时间,几乎偷偷摸摸地,对儿子开始人文教育的。可外面的世界对人影响太大,用摧残肉身和夺命来狂欢,这份刺激,对小刁斗的吸引足以胜过唐诗宋词,他竟以为满街的土匪流氓才是世界的本相。与此同时,发生在他家里的两件事情,又进一步强化了他的认知。一件事是说话咬钢嚼铁、处事胸有韬略的姥姥,有一天突然拿起斧子,奋力劈烂了家中几件漂亮的红木家具,然后把劈出的碎木填进了炉膛;接着,姥姥又领着他,急匆匆来到北陵大河的桥上,像干什么坏事那样东张西望之后,果断地拿出藏在包袱里的一个匣子,从桥上猛力投入河中。刁斗认得,这是姥姥的首饰盒子,姥姥一直说以后一旦缺吃少穿了,拿出一件,就可以解除全家的困顿。可现在为什么好端端地要丢弃它呢?眼看沉甸甸的百宝箱向桥下坠去,初通世事的小刁斗却仿佛蓦然开始了向上的生长。一两年后,另一件事再次以毁灭人价值观的方式,帮助了刁斗的向上生长。一介书生的爸爸本来已经逃过了许多知识分子都蒙受的劫难,可不知在哪件事上,却惹军管会的头头不高兴了,一夜之间,便被勒令离岗下乡去劳动改造。爸爸怕牵连一家老小,居然想采用和妻子离婚的无奈策略,来保障一双儿女及丈母娘能留在沈阳。爸爸去农村落户前夜,把刚刚九岁的刁斗带进一家餐馆,自己斟满一盅老白干,又给儿子也倒了一盅。爸爸红着眼睛命令道:“你要像我这样把它喝了!”爸爸说:“你喝下这杯酒,就是一个真正的男子汉了。我走后,剩下你姥、你妈、你姐和你,家里就只有你是個男人,你要懂得,男人要有男人的责任……”
怎样成为一个真正的男人,的确是个问题。胡同里那个乱呀,小刁斗想,这些勇猛之人,敢骂敢打,不怕流血,他们不叫男人还啥叫男人。他二话不说冲上街头,与天天打群架的孩子们,也可以说是小流氓们,同出同进地混在了一起。他虽然人小,可并不是个打酱油的,战场上下,都表现得有勇有谋。同时,不光打架出手狠辣,二皮脸的品性也得到了磨炼:见到漂亮女孩时,他把小眼睛眨一眨,也敢向人家送去“秋天的菠菜”;还曾将两只毛衣袖头抻长做掩护,进商店偷俩鸡蛋带回家去……
就是在这种家内吟诗诵词户外为非作歹的撕裂状态下,刁斗这个情感丰沛的男孩,内心分蘖出一隙亮光,这亮光只豆粒大,却能摇曳着膨胀,生出诱人的魅惑之感,把他小小的心灵拂弄出许多莫名的滋味与渴望。他脑子里会突然蹦出一些尚不能全懂的诗句和意境,令他的神经一凛一激的。他坚硬的心中居然开辟出一小块柔软而慈悲的领地,偶尔独自徘徊徜徉,竟煞是享受。学校到底还是复课了,但很不正规,那些没有老师监管的“自习课”,吵成一锅粥的时候非常多。于是,作为学习委员的刁斗便有了小鬼当家的天赐良机,他平常在课外书上看到的东西,以及在混社会时经历的东西,夹带着肚子里的一串串妙语好词,很快就让课堂变安静了,或者说,课堂上只剩下了他的口若悬河滔滔汩汩。这么着讲过几回之后,在一帮打架的伙伴之外,他就又有了些读书的朋友——这后一些朋友,多半可以让目光望到日后的生计,望到在空洞口号之外那个人的具体未来。关于个人未来,他们有的说要当个卖猪肉的,有的说要当剃头匠,有的要开大货车,可十二岁的刁斗脱口而出的是:当作家!
自从刁斗说出了“作家”,这两个字在他心里旋即生根。他甚至觉得这颗种子是从娘胎带出来的,只是一直在沉睡,现在是醒了发芽了。而一经发芽,它就长势惊人,读书成了让刁斗上瘾的烧脑游戏,他还真有了凿壁偷光引锥刺股的那个劲头。书也似药,善读者可以医愚。读书使他脑洞大开,十三岁就开始写诗。一个小孩写的那也叫诗?充其量是分行的句子。可是他被自己的句子整得亢奋不已,两只小眼睛炯炯如炬。他又勤奋又高产,一首接一首,写完就广泛地往外投寄,纷纷的退稿并没让他自卑或气馁。终于十七岁时,他开始公开发表作品,并且在下一年,因一首三十多行的“长诗”见诸报端而把一家国企大厂的宣传部部长吸引到身边,还对他又称文友又呼知音的。当时,十八岁的刁斗刚刚就读于那家国企大厂的技工学校,能得到高不可攀的宣传部部长的礼遇,不免让他受宠若惊,而更让他没想到的是,那也爱写诗的部长承诺,两年以后技校毕业时,他可以不下车间,径直到宣传部坐办公室去。但此时的刁斗,已懂得了志之所趋无远弗届的道理,他谢绝了宣传部部长的好意并从技校退学,转而考取了北京广播学院。
大学是一个宽广的天地,有助于人的自由发展,攻读新闻专业的刁斗,心底更加澎湃着的仍是诗情。他的诗歌接连见诸报刊,青春的憧憬,理想的眺望,是那个年龄段的必然主题。他的歌词《脚印》,被作曲家谷建芬看中并谱曲,然后由王洁实谢莉斯这对二重唱的黄金搭档用通俗唱法演绎了出来。词、曲、唱的强强相遇,取得的效果是天雷勾地火的一炮而红,据说当年收录此歌的八毛钱一张的软膜唱片,曾发行几百万张:“洁白的雪花飞满天,白雪覆盖了我的校园,漫步走在这小路上,留下脚印一串串……”一时之间,刁斗的“脚印”踏遍了大江南北。
其实,当满大街都在哼唱他的校园热歌时,刁斗已转身去了别处,只把一个不再回头的背影留给了歌迷。人类精神的原野上,高峰绵延,一望无际,他在书林里仰望着一座座别样的山峰:萨特、加缪、卡夫卡、普鲁斯特……痴情迷恋,流连忘返。《礼记·中庸》有言:“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这也正是刁斗的写照,他在脑袋里自觉不自觉地绘制着自己的精神图谱,他内心汹涌的波涛,有限的诗句已经不足以表达,他执拗地转而写起了小说。
好多年里,刁斗既是宅男又是游侠。他集中精力读书写作时,可以连续多天楼都不下,晨昏颠倒不问世事。可一般宅到三个月左右,又是他的一个极限,他又必得起程远行——倒也不一定非得远行,近行也行,只要能与按部就班的沈阳生活模式拉开点距离就行,用他自己的说法解释,就是他喜欢离开的状态。一般情况下,他的远行或近行,其目标只指向某个有趣的灵魂,某个好玩的朋友,某个谈得来的聊天伙伴,至于看美景、吃美食、览名胜,对他是没啥吸引力的。有一年在三亚和朋友聊完天,他余兴仍浓,去买返程的飞机票时,对票务人员说:沈阳、宁波、成都,哪儿折扣大出哪儿的票。弄得那个娇羞的海南妹子神色紧张,好像遇到了精神病患者或者坏人。其实,是宁波和成都都有“聊友”欢迎他去,而恰好那时他手头有点拮据,需要以尽量节省旅费开支作为选择的原则,于是他便请天意代他决定:是回家呢,还是持续“离开的状态”?
刁斗已经出书三十余种,虽然发行量始终不大,但仍然能常常遇到知音,这让他对艺术力量的神奇和莫测总感受强烈。当初长篇小说《我哥刁北年表》进入香港红楼梦奖暨世界华文长篇小说奖决赛圈时,人家工作人员来电话通知,可他对那奖项还一无所知,甚至认为,那肯定是南方口音的朋友在寻他开心。而20世纪90年代,法国一家出版社读到他的小说后,只在越洋电话里与他半通不通地交流几句,就表示要连续五年为他出书五部,以至于五年后,手握五种样书的他仍要怀疑,这法国人的一诺千金是不是童话。而前几年,他的英文小说集在英国出版后,被大名鼎鼎的《卫报》推举为年度最佳,这更让他坚信,文学能打动千差万别的各色人等,靠的只能是艺术品质,而非社会学政治学的猎奇纷争。
在刁斗的每部作品里,无论是《圣婴》中作为圣婴宿主的盛英、《我哥刁北年表》中的精神漂泊者刁北,还是《回家》中的意义消解者“我”……几乎都有他自己的影子,其灵魂都带有他自身正向或者反向的痕迹。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所有的作品,都是在写自己的精神自传,都是在解剖分析和创造全新的自己。刁斗是有强烈主体意识的作家,创新是他始终的追索,这不仅体现在他作品的形式上,也体现在思想上。在他精力充沛的好多年里,每年他都要完成二十万字的写作量,但他却并不计较是否发表以及获奖,他最看重的,只是自己在精神上有什么发现。有人说他的作品远离读者过于小众,对此他从来都坦然认可。他并不想跑马占荒大面积圈地,而只愿用心挖一口深井——从开掘自我着手,细致爬梳,顽强挺进,通过严苛的反省,去映现和探索现代人的种种精神困境,去展开对人类自身命运的思考。
作者簡介:
马秋芬,国家一级作家。先后毕业于中国作协文学讲习所七期(鲁迅文学院)、北京大学中文系首届作家班。曾先后出版长篇小说《阴阳角》,小说集《远去的冰排》《雪梦》《浪漫的旅程》《马秋芬小说选》《蚂蚁上树》,散文集《文心流浪》,长卷散文《老沈阳》《到东北看二人转》《盛京流云》等。曾获全国第七届庄重文文学奖、中国第二届女性文学奖,获《人民文学》《小说选刊》《小说月报》颁发的作品奖,多次获东北三省、辽宁文学奖等。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从1989年起,曾连任四届辽宁省作协副主席、沈阳市作协主席,现为辽宁省作协顾问,已退休。